“藝術公眾”的困境及其重構
——兼評奈特的《公共藝術:理論、實踐與民粹主義》
□張悅群
【導 讀】 在謝爾·克勞斯·奈特的著作《公共藝術:理論、實踐與民粹主義》中,藝術—公眾的全新關系在美國公共藝術場域中得到了集中探討。奈特在本書中著重對公共藝術的社會組織方式進行了仔細審視,從而嘗試探究藝術公眾在其中的客觀參與情況與真實參與程度。事實上,《公共藝術》并未主張建立一個新的所謂藝術等級制度,而主要是在公共藝術現有的維度內部提供一些延展性,而這便懸置了公共與私人、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摩擦。相較而言,一種“新型公共藝術”或許可以被視為重新連接藝術、公眾與社會的真正嘗試。
引言:“藝術公眾”的初現及其轉向
藝術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認為藝術通常是被集體地(collectively)而不是獨自地(individually)生產出來的。如果把“藝術品”“藝術家”置換為“文化產品”“文化生產者”這樣的布爾迪厄式概念,那么藝術便可以被視為由特定文化生產者所生產、由特定組織和群體以特定方式“消費”的“文化產品”。可見,藝術背后存在一整個文化生產、分配和消費網絡,這個網絡形成了某種社會場域(sphere)。霍華德·貝克(Howard Becker)所謂的“藝術世界”(the Art Worlds)就是指的這樣一種東西——其中不僅包含著技術性要素(例如,材料和技法等)、分配和展示系統(例如,畫商和畫廊)、回報或獎勵系統(藝術家收益的組織方式),而且同樣離不開鑒賞和批評系統(例如,藝術評論的寫作和發表)以及觀眾。[1]事實上,觀眾在藝術場域中并非無足輕重、全然被動的存在。如果藝術和藝術家可以被視為文化產品和文化生產者,那么藝術的觀眾或受眾自然是“文化消費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藝術社會學重新發現了藝術的受眾,或稱之為藝術的“公眾”。
“藝術公眾”的重要意義需要結合“藝術市場”的概念來理解。藝術市場體系出現于19世紀的歐洲,其深刻影響主要在于,從此藝術家的創作、生計與名聲不再取決于贊助人的個人喜好,轉而高度依賴以下活動:將作品賣給中間商(例如,畫商)、在畫廊里展覽以尋求潛在買家,以及依靠批評家提高自己的名望等。簡而言之,藝術品自此進入了全新的資本主義市場領域。一方面,在藝術品的“賣家”和“買家”之間逐漸出現了一系列全新的“文化勞動分工”——畫廊主和拍賣行經理依靠經營藝術家的名聲來獲利,藝術品也被賦予了利益指向(profithungry)的、投資炒作的形式。[2]另一方面,富裕的中產階級公眾開始活躍于這個場域中。他們的審美觀迥異于以往,不再一味追隨(美術學院等)官方機構所推崇的宏大主題或經典風格,而是將目光轉向尺幅較小、主題趨于日常的作品。這一審美判斷依據主要來自發表于報紙或雜志上的新型藝術批評文章;它們不僅告訴公眾應該喜愛何種類型的作品,還鼓勵后者去欣賞藝術家們的特殊氣質。這種產生于19世紀的新型“經銷商—批評家”體系(“dealer-critic”system)中介著“藝術家”和“公眾”之間的關系。它的兩端聯結著藝術的“生產”與“消費”,因而顯著地影響著藝術市場的“供”與“需”。
盡管逐漸成為文化消費領域的主力軍,19世紀以來的藝術公眾仍然有其局限性。首先,就藝術的界定(labeling)和評價而言,權威機構與個人的判斷仍居于主導地位,公眾的審美在總體上仍然是相對被動的和“受馴化”的。其次,這一“公眾”大多來自富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有產階層,他們不僅有能力消費藝術品,還將“經濟資本”轉化成為“文化資本”,成為布爾迪厄所謂的“文化資產階級”(cultural bourgeois),從而擁有著凌駕于其他社會階層的“文化權力”。在布爾迪厄看來,這種對藝術的熟悉和親近實際上屬于“有閑階級”(leisured bourgeoisie)的“特權”(preserve);藝術在此更像是某種社會區分標記,體現著該階級與由被統治階級所占據的“基本物質需求領域”的客觀距離和主觀優越感。[3]可以說,現代藝術世界和現代藝術面對的公眾,事實上是一種明確階級化了的公眾。
直到20世紀初“公共藝術”的發生,“藝術世界”及其“公眾”的角色才開始發生轉變。在謝爾·克勞斯·奈特(Cher Krause Knight)的著作《公共藝術:理論、實踐與民粹主義》(PubicArt:Theory,Practice andPopulism)中,藝術—公眾的全新關系在美國公共藝術場域中得到了集中探討。奈特相信,當藝術具有明確和明顯的民粹主義考量時,它就成為最完全的公共藝術;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將作品的情感、智力以及身體可及性延伸到觀眾面前。如若不然,公共藝術的“公共性”及其民主化理想就只是一種空洞的姿態。因此,奈特在本書中著重對公共藝術的社會組織方式進行了仔細審視,特別是作品安置、創作資金和創作內容等方面,從而嘗試探究藝術公眾在其中的客觀參與情況與真實參與程度。
一、早期公共藝術中的尷尬公眾與流于概念的“文化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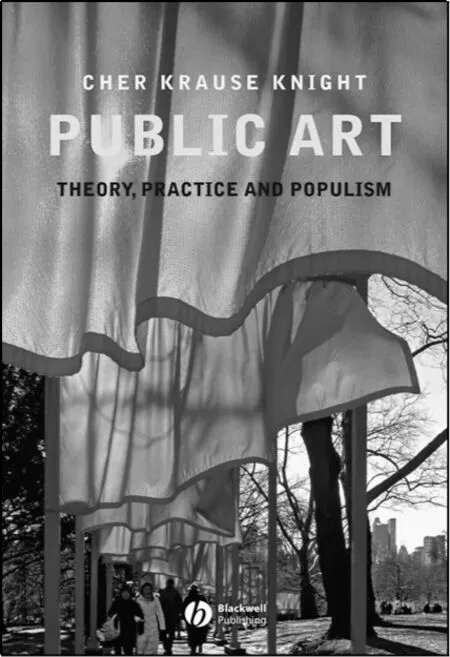
隨著“公共藝術”出現于20世紀初的美國,“公眾”的概念及其在藝術領域的地位開始發生轉變。根據蘇珊·蕾西(Suzanne Lacy)的觀點,當代美國公共藝術實踐始于1967年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主持的“公共場所藝術計劃”(Art-in-Public-Places Program,A-i-P-P)。[4]21在《公共藝術》中,奈特則把這一開端提前至1933年羅斯福新政下的“藝術公共工程項目”(Public Works of Art Project,PWAP)。[5]3在這期間,還有美國總務管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GSA)主導的“建筑中的藝術”計劃(Art-in-Architecture program,A-i-A),該計劃最初由PWAP 的負責人愛德華·布魯斯(Edward Bruce)于1934年提出,但直到1963年才由GSA 落地實施。
但不論如何界定起點,上述公共藝術實踐都被奈特劃為同一類型,即通過官方贊助來促成藝術民主化,并借此提高公共福利而非私人利益。例如,在1933年開始的“藝術公共工程項目”(PWAP)中,政府向職業藝術家支付日薪,雇傭其在公共建筑中進行創作。然而,該項目既非出于對藝術活動的特殊關照,也并未允諾聯邦政府對藝術的永久支持。奈特指出,作為新政的組成部分,PWAP 項目本質上屬于應對社會危機的臨時措施:一方面直接解決大量藝術家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間接地通過藝術的精神力量緩和彼時悲慘的經濟氣候。不難發現,“藝術公共工程項目”實踐中的“公眾”概念,是極其籠統的和含混的。
相對而言,奈特發現由GSA 主持的“建筑中的藝術”計劃(A-i-A)在這個問題上有所進步。A-i-A也常常被稱為“藝術百分比”項目,它要求每修建一個全新的聯邦建筑,其總建筑經費(包括后續可能的維修和改造經費)的百分之一的一半要被用于購買和向公眾展示美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A-i-A 為美國公共藝術確立的關鍵原則之一,便是真正的“公共”藝術應當名副其實地“歸公民所有”(owned by the citizens);不管作品是否能夠被接受和理解,它們都屬于公民的財產。[5]6然而,盡管在藝術與公眾關系問題上有了初步的突破,該項目仍未在本質上賦予公眾藝術生產的主動權。奈特指出,盡管專家委員會及公民代表是項目的必要組成部分,藝術家和作品的最終選擇權仍屬于當局即GSA,而不是公眾本身。換言之,在藝術決策權問題上,A-i-A 仍然具有明確的官方專斷特征。[6]
奈特注意到,相較于由政府贊助、缺乏實質性公眾參與的A-i-A,由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主持的“公共場所藝術計劃”(A-i-PP)則減少了對政府基金的依賴,而轉向廣泛的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該項目意圖通過回應本地社區訴求的方式來拓展藝術的受眾。其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引導社區公眾直接參與到藝術的委托和施工事宜中,包括鼓勵市民取得某一公共場址的所屬權并對其負起責任,或是鼓勵公眾自主向企業、地方政府或文化機構等籌集資金等。這表明,A-i-P-P 放棄了用絕對標準來評判藝術“質性價值”(qualitative merits)的做法,而是采取了自覺的民主化過程,以向公共監督、公共爭論甚至不一定欣賞藝術的觀眾敞開。[5]15-16
A-i-P-P 的落腳點仍在于藝術得以被安置的場址和空間。這一意識源于A-i-A 項目所確立的另一個關鍵主張,即在公共藝術中“公共空間”和“藝術品”是不可互換的。這一主張明確了公共藝術的“場址特征”——作為一種“具有場址意識的藝術”(site-sensitive art),公共藝術應當是具有“場所特定性”(sitespecific)的。[5]6-7可見,A-i-P-P 的目標主要在于“為某一公共場址購買或委托制作藝術品”。奈特進一步認為,這實際上取消了藝術真正的“公共性”,即一種無論在何種場址或空間中都能夠激活觀眾的智性、感官與情感的能力。此外,即便增加了公共參與程度,項目的基礎(資金來源)仍然掌握在機構官員和私人企業主手里。如果方案不能獲得他們的支持,作品便永無可能呈現在公眾面前。在這個意義上,奈特認為,即便在某種“公共藝術”的名目下,官員和企業主仍然是所謂的“第一公眾”(first public)。
上述公共藝術項目存在一個共同的局限。無論提出何種關乎公眾的主張,其結果大多仍是某種“空降的藝術”,而且往往出自知名藝術家之手。森尼(Senie)稱之為“plotart”,即“撲通一聲掉落在某處的藝術”;這一形象的比喻直指上述項目中普遍存在卻未必成立的假設,即“成功的美術館或畫廊藝術家同樣也是成功的公共藝術家”[7]230。杰夫·凱利(Jeff Kelley)同樣認為,大多數藝術家所做的不過是“空降”(parachute)到某個地方,然后用藝術對其進行置換。在他看來,“場所特定性”在此更像是“為某個地方強加了一處非實體的美術館區域,而這個地方此前本身就已經很有意義”[4]24。因此,上述公共藝術項目的最終目標不過是讓公眾“能夠在美術館以外的地方接觸到藝術”。與此同時,這也保留了主流藝術機構(以美術館等為代表)作為“藝術仲裁者”的角色和地位——藝術品即便走出了美術館院墻,也并未脫離其標準,而只是將私人的觀看經驗挪到了戶外。由此引發的討論也多圍繞著其藝術風格而非公共價值展開。
針對上述問題,奈特初步總結了公共藝術的基本標準,它應當包含如下幾方面:首先,公共藝術作品通常被指定給更多、更廣泛的觀眾,并被放置在相對引人注目的地方;其次,其目的主要在于提供啟迪、紀念或娛樂的審美體驗;最后,更為重要的是,對普通觀眾來說,公共藝術作品的信息和內涵應當是“可理解的”。這些標準為美國公共藝術提供了某種通行的“傳統范式”。許多批評家擔心,上述民粹主義的考量會使藝術變得平淡無奇,用前衛性換取大眾的吸引力,同時用公共關系技巧而不是大膽的方式來獎勵藝術家。但在奈特看來,討論公共藝術,就需要拋開以審美問題為中心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定性判斷;奈特始終強調,當藝術真誠地將情感和智力延伸到觀眾面前時,它就是最充分的公共藝術。
2.1 采用專家咨詢的方法 選擇15名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院長、團隊長和護理專家進行2輪的函詢,以此建立家庭病床患者上門靜脈輸液安全模式的初步框架同時改進上門輸液攜帶包。
二、公共空間的萎縮與城市公共藝術的異變
隨著各種項目和計劃的實施,具有場址特定性的藝術即“公共空間中的藝術”逐漸為人們所熟知。在這個過程中,公眾逐漸意識到,盡管伴隨著各種爭議,藝術似乎的確具有優化公共空間和塑造城市形象的能力。例如,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于1967年受委托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Grand Rapids)創作了一件名為“高速”(La Grand Vitesse)的大型公共廣場雕塑。這一方案起初由于高度抽象性和強烈的藝術家個人風格而遭到責難。但一經落成,它很快成為某種“毋庸置疑的高端都市身份的文化標志”,作為“城市標志”(civic logo)遍布包括信頭和垃圾運輸車在內的各種地方。[7]219這件作品不僅引發了社區的藝術熱潮,也激發了大急流城的市民對家鄉的自豪感。在此,“公共場址中的藝術”搖身一變,成為“城市地標”或“城市名片”。由于在客觀上拯救了因經濟衰退和社會矛盾而崩潰的內城,這類作品普遍被視為城市空間再生與活化的有效手段。
然而奈特在此提醒,就大多數公共場址中的藝術而言,其本質仍然是某種“視覺藝術”,不過是美術館藝術的戶外版本。盡管呈現出不同的造型、材質語言與體量特征,它們并未脫離傳統造型藝術的美學范疇。在這個意義上,奈特將公共場址中的藝術等同于城市空間的“視覺升級”(visual enrichment)手段——即便公共空間的外觀升級的確對城市社區的滿足感、幸福感及社區利益大有助益,這樣的公共藝術充其量也不過是某種美學“矯正物”(corrective),其功能相當于縫合社會組織裂隙的“創可貼”。[5]132-133
一如認為優秀的畫廊藝術家等同于合格的公共藝術家,大急流城對考爾德作品的期許同樣包含著另一個理想化的假設,即“公共場址”完全等同于“公共空間”。但真實的情況遠非如此。事實上,一種公共空間私有化進程的全面開展早已顛覆了自身的實際內涵,其結果便是全新的消費空間的出現。社會經濟資源的不平等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進入和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的不對等。經由私人資本寡頭政治與當地政府職能部門的共同協作,公共空間的原真性被重構為另外一副模樣:一個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間(a privatepublic space)。相較于一個真正的、可以民主地進行政治表達的公共空間,私有化了的公共空間首先必須是一個去政治化了的消費空間。
由此不難理解,公共場址中的藝術何以被并入了一種以“再市紳化”(re-gentrification)為名的城市空間更新進程。派翠西亞·菲利普(Patricia Phillips)曾抱怨,公共空間淪為房地產繁榮后被開發商所“剩下”(left over)的東西。盡管日漸式微,它卻仍然被包裝為某種友好的姿態,由公共藝術作為標示其邊界的“圍欄”。[8]無獨有偶,馬爾科姆·邁爾斯(Malcom Miles)也指出,這種公共藝術對都市更新工程的意義主要是“投機性(speculative)”的,因為“藝術的價值被獨立于城市生活問題之外”[9]。羅莎琳·多依徹(Rosalyn Deutsche)的評價同樣針對城市更新方案及其對公共藝術的操控問題。在她看來,盡管名義上要重振處于困境的都市生活,但城市更新計劃似乎主要服務于富有的市民、觀光客以及開發商。他們往往將目光聚焦于美觀和效用,并以此取消那些高度緊張的種族和階級問題。然而,正是這些問題從根本上塑造著公共空間。多依徹由此認為,城市更新計劃和公共藝術的使命乃是“使晚期資本主義城市境況具體化為一種‘自然’”,這就使得作為“領域”和“社會形式”的社區概念遭受了來自利益本位的開發商和短視政客的雙重破壞。[5]133
上述情況正是公共場址藝術面對的基本現實。士紳化了的都市空間在此意味著令人困惑的混合:它們看起來是“公共的”,但實際上是私人投入和經營的結果——它們將那些共同的空間包含在內,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分區治理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則致力于使其開發商盡可能表現出“公民的精神”。因此,奈特認為,那些提供基本設施并聲稱“為了每個人而美化地方”的開發商是在試圖用道德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努力,而這就抹平了文化差異,以及那些士紳化進程所伴生的權利剝奪和流離失所的真正現實。
如同德波認為奇觀以“擬真”取代了鮮活的經驗,以商品化了的幻想篡奪了公眾智性與社會政治參與,一種公共場址中的藝術同樣取消了城市公共空間的原真性,抹殺了空間中的公共參與。因此,在后現代消費社會的語境下,城市公共藝術不幸淪為都市奇觀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置身于劇場式的空間生產所圍合的符號世界中,作為觀眾的公眾被剝奪了參與“空間決策”的可能,因而只能以消費者的身份墜入奇觀的旋渦。
三、藝術與公眾的重新聯結:走向一種“新型公共藝術”
在本書中,奈特詳細考察和揭示了公共藝術中固有的個人與集體、精英和大眾的緊張關系。基于一種民粹主義視角,奈特對此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希望通過主動的選擇來增加觀眾的話語權。事實上,《公共藝術》并未主張建立一個新的所謂藝術等級制度,而主要是在公共藝術現有的維度內部提供一些延展性,而這便懸置了公共與私人、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摩擦。例如,奈特始終在呼吁廣泛建構藝術作品對公眾的“可及性”,但其方式之一則是對公共藝術那些私人贊助力量進行優化,或干脆直接聯合市政府和私人資金進行公私合作的項目。
相較而言,蘇珊·蕾西(Suzanne Lacy)所謂的“新型公共藝術”(new genre public art)則嘗試跳出奈特的民粹主義框架。蕾西主張,新型公共藝術的核心在于“社會介入”(social intervention)這一基本策略。[4]19這一藝術主張顯著地植根于左派思想、身份政治以及社會行動主義的土壤,并積極地追求一種面對多元受眾群體、強調社會參與的互動性藝術。相較于現代主義對藝術天才的追隨和追捧,新型公共藝術更加看重藝術家的社會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新型公共藝術孕育于20世紀60—70年代的美國城市危機。在這一時期,藝術家開始普遍加入社會
行動與公民權利斗爭的浪潮。眾多藝術家借此丟棄了現代主義式的精英傳統,而轉向了以政治多元主義為顯著特征的社會介入行動。與傳統的藝術創作與展覽形式相比,介入式藝術為觀眾賦予了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它強調將藝術的生產和公眾的接受理解視為同等重要的東西。廣泛的政治介入實踐沖擊并消解了藝術固有的邊界,并將全部可能的藝術形式都吸收到自己的系統中來。在這個意義上,全新的介入藝術的出現實際表明了藝術的真正的民主化進程。[5]111-112在政治多元主義的觀念影響下,許多藝術家開始反對自我欣賞和沉溺的體制化藝術世界,而是致力于讓藝術直接參與到當下社會問題的解決中來。這一新型藝術實踐既秉承著“行動主義”(activist)的精神,又凸顯出某種“社區主義”(communitarian)的指向。相較于單純的審美對象或藝術表現形式,新型公共藝術更像是一種交往形式和實踐過程。它并不滿足于對社會問題的隱喻性研究,而是試圖為都市社會的邊緣群體賦予切實的權利。因此,公共藝術家的努力使得藝術與社會工作的界線變得模糊。他們從不為了遷就美學的考量而犧牲作品中的社會性面向,而是努力在兩者之間做出協調,渴望成為社會變革和民主化進程中更為有效的力量。
一方面,新型公共藝術的社會介入策略集中關注當代都市社會的種種困境。在藝術家們看來,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解決不能僅僅依靠政治意識,還應當注重美學語言的使用。新型公共藝術實踐可以避免非此即彼的制度性措施,從而為社會的改革與重建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這是它在思想意識上的優勢。另一方面,新型公共藝術主動地拒斥傳統公共藝術的觀念和表現形式,而將作品與公眾的互動和有機聯結擺在了首要的位置。這可以看作是新型公共藝術在策略和形式上的優勢。通過廣泛的參與和互動,藝術家和公眾在觀念上的溝通和交流變得更為直接有效。更為重要的是,新型公共藝術拒絕墮入士紳化進程的控制。盡管表現為某種城市美化工程,士紳化進程實際上屈從于私有產權和私人利益的統治。換言之,一種由士紳化進程所主導的、虛假的公共藝術形式并不能帶來社會空間的民主和解放;相反,它會進一步深化公共空間的私人所有化和私人化管理。因此,通過拒絕與士紳化進程媾和,新型公共藝術同時拒斥了私有資本力量以及行政力量對公共空間的控制。這是它在現實層面上最為重要的優勢。
總體來說,“新型公共藝術”既是對種種“傳統公共藝術”(奈特主張的民粹主義公共藝術便算是其中之一)的革新,也是對現代主義以來精英化—資本化的藝術世界的反叛和抵抗。它既不由城市規劃意識形態以及官僚體制所主導,也不受藝術市場及其體制系統所掌控,更不試圖服務于私有化資本及士紳化的進程。也正是因此,新型公共藝術或許可以被視為重新聯結藝術、公眾與社會的真正嘗試。
自藝術市場在19世紀歐洲的出現,到公共藝術在20世紀初美國的誕生,“公眾”在藝術領域中的身份和性質發生了顯著的改變。藝術經銷—批評體系的建立,使得布爾迪厄所謂的“文化資產階級”成為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公眾”,而一系列由政府等社會機構所主導的公共藝術項目及其實踐,則凸顯了在藝術民主化進程中某種民粹主義的傾向。然而,褪去“公共藝術”這一形式外殼后不難發現,盡管伴隨著包括公眾在內的、不同力量與話語的角力,其內在邏輯仍然由官方機構、專業群體和私人資本等力量共同掌握。特別是,隨著城市更新實踐的深化和泛化,私有化進程進一步侵蝕和顛覆著公共空間的原真性內涵,城市公共藝術因而越發淪為單純的美學附屬物。顯然,奈特對一種民粹主義公共藝術的期待,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藝術公眾的尷尬境況。為了扭轉傳統公共藝術所面對的困境,重建藝術與公眾之間的有效聯結,一種具有明確社會考量和強調社區行動的“新型公共藝術”轉向值得引起關注。或許,在努力通過規劃、建設和經營藝術區、美術館的方式打造“藝術城市”的熱潮中,我們同樣需要那些具體的、微觀的和悄悄發生在社區中的藝術實驗,剝離藝術作為城市文化名片、城市影響力要素的功利性內涵,而將其重新交還給公眾受眾。
注釋
[1]Albrecht,Milton C.and Barnett,James H.with GRIFF,MASON eds.TheSociologyofArtandLiterature:AReader.London:Duckworth,1970:7-8.
[2]Inglis,David and Hughson,John.TheSociologyofArt:WaysofSeeing.Palgrave Macmillan,2005:25.
[3]Bourdieu,Pierre and Darbel,Alain with Schnapper,Dominique.TheLoveofArt:EuropeanArtMuseumsandTheirPublic.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111-112.
[4]Lacy,Suzanne.MappingtheTerrain:NewGenrePublicArt.Seattle:Bay Press,1995(Introduction).
[5]Knight,Cher Krause.PublicArt:Theory,PracticeandPopulism.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
[6]里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位于紐約聯邦廣場的公共雕塑“傾斜之弧”(Tilted Arc)的命運便充分反映了上述問題。該作品于1979 由GSA 委托實施,于1981年安裝落成并引起了巨大的公眾反響和廣泛的社會討論,最終于1989年被拆除。在作品落成之前,GSA 并未為公眾的接受問題做出努力,其拆除也并非由于公眾的抵制情緒,而是由于官方機構內部的矛盾。換言之,“傾斜之弧”的命運證明,A-i-A 并未真正兌現由公民擁有藝術的承諾,相反,它透露出來的是聯邦政府之于藝術問題的嚴重越界。
[7]Senie,Harriet F.ContemporaryPublicSculpture:Tradition,Transformation,and Controvers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8]Philips,Patricia.Out of Order:The Public Art Machine.Artforum27.4(Dec.1988):93.https:/ /www.artforum.com/print/198810/out-of-order-the-publicart-machine-34653.
[9]Miles,Malcolm.Art,Spaceandthe City:PublicArtandUrbanFutures.Routledge.199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