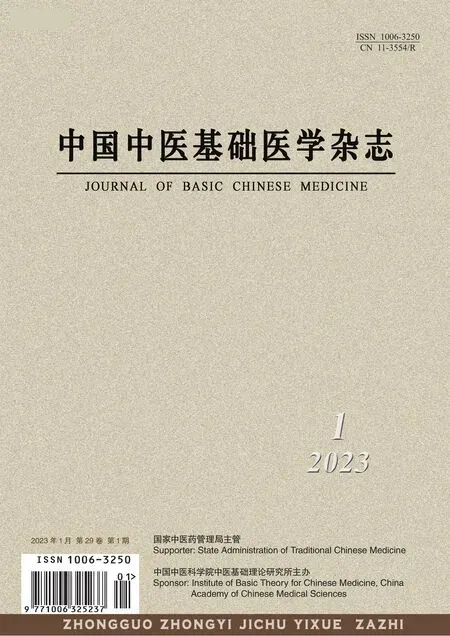中藥隱喻思維探討
馬 駿,楊曉軼,羅 強,牟德海,梁永瑞,顧曉霞,李應存,2△
(1.甘肅中醫藥大學,蘭州 730000;2.甘肅中醫藥大學敦煌醫學與轉化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蘭州 730000)
認知隱喻學先驅者Lakoff,將隱喻本質界定為“通過另一類事物和經驗來理解和經歷某一類事物和經驗”[1]。就是將隱喻置于兩種不同的概念域之間,以概括化的物理性和功能性特征為始源域(source domain,簡稱S),映射到自然和社會廣大領域,側顯目標域(target domain,簡稱T)的映射,主要涵蓋位素、屬性、關系和知識4種映射內容[2]。隱喻本屬于語言學的范疇,是語言學中的一種修辭手法[3]。近來隱喻研究炙手可熱,在多個理論領域,都有不少學者涉足隱喻。隱喻更是中醫理論發展的基石,于中醫語言中無處不在[4]。其中,中藥隱喻作為闡述藥物功效的獨特思維方法,引人遐想,拓寬了對藥物的理解、發明和應用,所以文章重點對其探討。
1 中藥隱喻的基本內涵與探究意義
《素問·八正神明論篇》云:“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這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獨悟,體現了中醫藥的特殊魅力,突出的是醫者的悟性、靈活性的特點[5]。同時,受當時科學水平和認知方法的局限,人們開始將這些“獨悟”通過隱喻來表達各種抽象概念,所謂“醫者意也,善于用意,即為良醫”[6],這種以意象思維的思維方式,典型地反映了中醫的隱喻思維特質。隱喻思維理論作為傳統醫學的原創思維,中醫學各個領域幾乎都有其醫學理念的傳承與延續,尤其在中藥的應用中頗顯特色。明代李中梓《醫宗必讀·水火陰陽論》載:“然物不生于陰而生于陽,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死,向日之草木易榮,潛陰之花卉善萎也。故氣血俱要,而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并需,而養陽在滋陰之上。[7]”這種由草木之榮枯聯想到人體陰陽氣血變化,大大推動了中藥隱喻思維的發展。清代醫家趙學敏在《串雅內編·緒論》中更直言:“醫者意也,用藥不如用意,治有未效,必以意求,茍意入元微,自理有洞解,然后用藥無不驗。[8]”病癥變化多端,不能墨守成規,以意求之有時不失為妙法。近代浙江名醫范文甫曾治黃某,“苦不寐,百藥不能治”,因用“百合一兩,蘇葉三錢,三貼而安”,謂:“我嘗種百合花,見其朝開暮合;又種紫蘇,見其葉朝仰暮垂,取其意而用之”[9]。隱喻在我們的腦海里如此自然如此普遍,因而通常被認為是不言自明心理現象的直接描述,大多數人從來不會意識到它們是隱喻[10]。因此,對中藥隱喻認知進行探討意義重大。
2 中藥多模態隱喻映射結構
中藥隱喻認知并不僅僅是單一模式映射的,更多的是以多模式隱喻映射結構共同存在。
2.1 單一映射結構
單一映射結構即S→T結構,是按照主體認知所及的相似對“象”進行比較,建立聯系與匹配,用已知S推未知T。此種映射對應取象比類的援物比類型操作方式,但是這樣論證是欠考究的。舉例來說,《本經逢原·卷二·蔓草部·旋花》謂:“凡藤蔓之屬,象人之筋”[11],僅僅是“所以多治筋病”的充分條件,如果將藤蔓之屬稱為S,將筋病稱為T,這里推理的有效性只能是由S到T,因為能夠治療筋病的并非只有藤蔓類藥物,因此僅依據T便推理出S則不符合邏輯推理的有效性。換言之,T不僅包括共象[12]的特征S,還可以是與目標域T具有相同類別的T′,因此T′推導個象S也是不具備必要條件的[13]。
2.2 “功能是特征”概念隱喻型映射結構
“功能是特征”概念隱喻,即以藥物特征為始源域,以藥用功能為目標域,通過隱喻形成組配,并以此推導有助人體某些病癥恢復的藥物配伍方略。通過對動物特征的動物藥隱喻認知研究發現,古代醫家發現動物藥功效的過程,是以對動物習性、體態的觀察為基礎,通過取象比類后得出的功效假設;當功效假設得到驗證后,醫家又通過隱喻認知的方法對動物習性、體態特征進行分析,進而對動物藥功效進行解釋[14]。如《本經逢原·卷四·獸部·象皮》謂:“(象皮)人以斧刀刺之,半日即合”[11]922,由此推理象皮具有斂瘡生肌之功,“故金瘡不合者,用其皮煅存性敷之”。不僅動物藥,通過對早期本草文獻如《神農本草經》等研究發現,這些典籍很可能更側重于應用隱喻認知對藥物功效進行論述的[14-15]。另外,現當代醫家李漢彪傳承草藥辨認秘訣:“草木中空善治風,對枝對葉能治紅。葉邊有刺皆消腫,葉中有漿拔毒功。[16]”將中藥之特性歸納,對臨床指導用藥,構建藥物與功效之間的理論橋梁,以及初步了解某一特殊藥物均具有一定的借鑒和指導意義。然而由于事物間存在極多“功能是特征”概念隱喻,并非所有具有該功能特征的事物都能夠起到調節自身的作用,一旦無限地拓展甚至濫用此概念隱喻,便會陷入中醫為唯心、不科學的境地。因此,此概念隱喻乃至中醫藥唯象思維必須加以限制,以使其處于更加合理乃至科學化的區間內進行。
2.3 復合型映射結構
始源域和目標域同時以多模態表征或激活的隱喻,即復合型的映射結構[17]。萊考夫和約翰遜總結道:“隱喻是一種思維和行為方式,而語言只是概念隱喻的外在表現形式。[18]”
復合型的映射結構往往同時包含多個映射內容,即將共象與個象綜合考慮作為始源域,以作用于機體的反應為目標域,從而推導出較為合理的施治方略。中藥隱喻思維,往往就是復合藥物不同部位、質地、生活習性及其性味歸經來論藥物功效與應用的,如《本經逢原·卷四·介部·蟹》:“凡物之赤者皆熱,惟蟹與柿性寒,所以二物不宜同食,令人泄瀉發癥瘕。妊娠忌食,以其性專逆水橫行也。其爪為催生下死胎胞衣專藥……取蟹之散血,而爪觸之即脫也,然必生脫者連足用之。[11]911”張璐認為“蟹之外骨內肉,生青熟赤,陰包陽象無疑。”因此認為蟹與“凡物之赤者皆熱”不同,其性寒無疑,在考慮共象與個象的同時,結合其功能特性知其為“催生下死胎胞衣專藥”,同時參照藥物的性味得出“惟蟹與柿性寒,所以二物不宜同食”的結論。
在運用中醫隱喻思維,也會習慣性單一型或“功能是特征”概念隱喻型映射而忽略藥物的其他映射內容,以致臨床應用失效或解釋不合理,從而使中醫隱喻思維受到嚴重質疑。此外,有學者甚至主張剔除中醫理論中的取類比象、祝由等思維,忽略中藥隱喻思維步驟,直接采用“中藥名稱跳到其對應功效”的線性思維(Jump Thinking)[19-20]模式,這種看似簡單、合理的對應方式,其實是逐漸在摒棄中醫藥優秀傳統文化,將陷中醫于萬劫不復。因此,中醫藥唯象思維需要長期合理地思考訓練過程,使之與“線性思維”等多種思維有效有機結合[21],同時必須加以限制,以使其處于更加合理乃至科學化的區間內進行,這或是中醫學立命之本。
3 中藥隱喻思維體現了物質和意識兩種形態
中藥功效認知過程中,醫家們主要通過身體感覺與取象比類兩種途徑,從而詮釋了中藥的物質和意識兩種形態。但是隨著西方醫學與思維方式的引入,中藥“去意識化”日益明顯,并逐漸由隱喻到理論,最終趨于科學化,使中醫藥的療效和發展埋下隱患。
3.1 從歷史角度看中藥的物質和意識兩種形態
關于中藥功效認知的歷史,傳說可追溯自遠古時代神農氏,西漢劉安《淮南子·卷十九·修務訓》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饒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22]”這一時期的醫家更側重于運用隱喻認知對藥物功效進行探索發現,但并未對藥物功效理論進行解釋。直至唐宋時期,對藥物功效隱解釋喻現象始見明顯。到明清時期,本草書籍中藥物功效的解釋最為詳細,醫家們更多運用隱喻認知、取象比類的方法對藥物功效進行闡發,彌補了藥物功效以往存在的詮釋不足[14]。另外,在原始宗教影響下,認為人有病是鬼神作祟,因此巫師在為人治病時,將“神”(包括符咒、驅鬼、祈禱及宗教等儀式)與“藥”兩者結合應用,此即所謂“巫醫一家,神藥兩解”[23]。對醫者而言,修持禁法就是加強與藥物功能相同的信念,而對于患者而言,通過禁法的隱喻作用不但能減輕患者對疾病的畏懼,而且能起到調節身心健康的作用[17]。如《圣濟總錄·符禁門》“五龍水法”有種行禁方法:“欲向病人家,當須存想,作白虎吐火,燒病人家屋舍,皆令蕩盡。又作龍,舐病人身肉令盡,還作充滿悅澤,然后用氣急治之”[24]。顯然這里將疾病視作可以燃燒與掃蕩的實體,施術者構想出一個燒盡和舐去病邪的動態場景。而龍虎作為威嚴的象征,被認為能夠增強禁法的力量。如此一來,“白虎吐火”和“青龍舐身”就隱喻著將疾病驅逐出家門和人體的過程[17]。符禁即是將符咒本身或個人“正氣”隱喻為“藥物形態”,存想則隱喻為“意識形態”,只有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符咒或意識才會起效。因此認為藥物具有其特性(可比作藥物的功能意識,如蜘蛛善循絲上下,故治睪丸上下之病;蟬鳴清響,能止小兒夜啼)且難以改變,臨床應用時結合其藥物組分,從而可發揮更好的療效。
3.2 中國傳統抽象思維中的物質和意識兩種形態
古代醫家對于藥物的認知途徑有二,一是身體感覺,二是取象比類。身體感知是認知的基礎,取象比類是認知的方法。中國傳統抽象思維,是認知主體憑借自身經驗加以理解和解釋,以尋找與比喻“象”的差異與共性的思維方式,是“隱喻思維”賴以進行的心理認知表征[25]。藥物部位、質地、形象等都是可以通過感官感知到的“象”“物質實在”,但這些“物質實在”必須經過“象隱喻”作為認知媒介進行意識加工,才能形成具有操作意義的“關系實在”[26]。因此,“象隱喻”的認知方式就同時體現了物質與意識兩種形態。如在隱喻認知麥芽與薄荷時發現麥芽蘊含生機,可借其發生之氣而行疏散消導之用[27],而薄荷生長則極為迅速,二者均具有“發散”之性,引申為疏肝。同時在臨床應用中發現,薄荷輕清走上,可疏散風熱,而麥芽則兼有健脾消食、退乳消脹之功,因此形成辨證用藥的法則。現代研究表明,麥芽具有助消化、降血糖、抗真菌、抑制催乳素釋放以及收縮血管等藥理作用[28-29];薄荷具有抗炎、抗真菌、抗腫瘤、抗抑郁、抗氧化、抗輻射等多種藥理作用[30-31]。顯見,麥芽與薄荷在現代醫學視域下均不具有疏肝的功效,與傳統本草著作對其功效的記載有所差異,中藥隱喻認知所得藥物“特性”,亦即中藥的“意識形態”被缺失了。因此有必要思考,盡管現代藥理學的研究方法如此前沿,中醫藥仍要堅持在傳承的基礎上吸收、創新,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古代醫家思想論述的要義,更好地發揮中醫藥的特色。
3.3 中醫藥“科學化”中的“去意識化”過程
《素問·舉痛論篇》云:“善言天者,必驗于人。”自然界中,動植物具有其最原始、最自然的本性。張璐《張氏醫通·卷十五·目門·千金磁朱丸》亦指出:“凡羽禽之目,皆自下睫而交上睫,性皆升舉,所以能飛,非若毛獸之目,悉自上睫而交下睫也,吾嘗靜觀飛走升沉之理,于茲可默識矣。[11]479”可見,醫家們對中藥的認識并非僅取其物質層面(如嘗百草),更多的是通過意識作用摸索出藥物的隱喻規律,這才是中藥發揮作用的主要內在因素之一。在以“象隱喻”為主要思維方式的古人眼中,大千世界無不是象。藥象與人象或病象本質是通過氣相感、類相應而發生關聯效應。因此,中藥隱喻思維體現了物質和意識兩種形態,其中“意識形態”在臨床中常被忽視,這很可能就是“因病用藥”或效或不效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西方醫學與思維方式的引入,中醫藥“去意識化”日益明顯,中醫藥在不斷“科學化”的同時,也為中醫藥的療效和發展埋下巨大的隱患。
中藥功效的認識過程,實際是由隱喻到理論、最終趨于科學化。需要強調的是,盡管我們可以得知藥物功效由某種或某些因子所決定,也就是從藥物組分直接對應功效的“S是T”線性思維,稱為“藥物組分決定功能”。不難看出,如果說“藥物組分決定功能”體現了藥物的物質對應狀態,那么復合型隱喻過程中的某些藥物功能甚至潛在的意識狀態就被無形地忽視了。舉例來說,中醫經絡理論之經絡以及藥物性味歸經理論,即是物質與意識有機結合的明證。《靈樞·海論》云:“夫十二經脈者,內屬于臟腑,外絡于肢節”,說明經絡是人體運行氣血、聯絡臟腑、溝通內外、貫穿上下的徑路,也是病邪出入、藥物作用的道路,但是這一理論因目前尚未在形態學上找到與古代中醫文獻描述的經絡實體結構而得以驗證。梁漱溟[32]非常贊成人的經絡屬于內證得來,認為“人身督脈、任脈之循通為道家所謂大小周天功夫;其往復流通原屬生活上自然的事情,卻是其流通鄰于機械,不復自覺;道家則通過大腦啟發其自覺,于是就清楚地認知有如此脈路。根本上這些脈路穴道不是作為一種物體而存在者,毋寧說它是一種空隙。這種空隙在活人身上有,在死后的尸體上沒有。尸體解剖上不見,而活人既不容解剖,縱然解剖終亦不可見。”顯然,這里是將經穴視作活人身上才有的脈路空隙,經氣構想出了一個可以在活人經脈流通的動態場景。而只有活人才有經氣的產生,如此一來,人的死亡就隱喻著失去經氣在經脈流通的過程,自然觀察就不到人體的經絡。因此認為,經絡理論很可能是中藥性味歸經理論成立并發揮療效的根本原因,亦即中藥的“特性”通過經絡傳導得以顯現,從而彰顯中藥物質與意識兩種屬性。因此,現代藥理研究雖然很容易探究中藥所含的“物質實在”,但很難解釋或發現中藥的“特性”。
4 結語
《本草綱目·人傀》曰:“膚學之士,豈可恃一隅之見而概指古今六合無窮變化之事物為迂怪耶?”[33]固然,醫學的形成和發展是以實踐為基礎,但是它并不只是醫療實踐的直觀反映[34]。中醫的發展夾雜著很多東西,有很多內容甚至是如今的醫學不好解釋的,因此也有人說中醫不科學。不是不科學,這里說的不科學并不是貶義,而是認識論的不同。科學是我們目前認知世界最高效的方式,但其出現僅僅只有幾百年,與中國傳統隱喻認識方式相比,中醫建立在一個和我們現在世界觀不甚相同的規則下。中醫藥學根植于中醫學哲學理論,而運用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和揭示中藥的作用機理及產生作用的物質基礎等則始于近代[35]。作為中國古代科技的代表之一的中醫藥學,僅憑實踐認識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將實踐所得的材料多多加“意”,從而探索并還原中醫藥學“隱喻思維”背后的“道”。誠然,中醫隱喻思維也有其固有缺陷,我們應用辨證的態度加以取舍,而非一味否定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