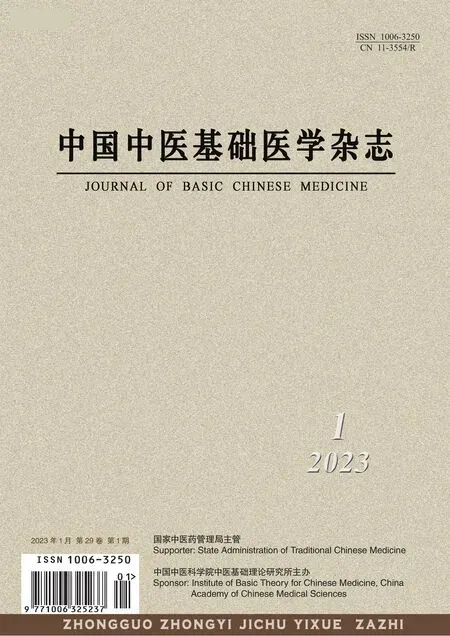2020—2021年度仲景學說研究進展?
湯爾群,黃玉燕,陳 曦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北京 100700)
仲景學說歷來是中醫學術研究的重點與熱點。縱觀近兩年相關研究成果,以“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為原則,仲景學說研究主要集中在醫史文獻研究、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實驗研究、信息學研究、循證醫學研究以及與新冠疫情結合的研究等7個方面。本文以中國知網(CNKI)“中文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和已出版專著,作為文獻來源和研究對象,對2020—2021年仲景學說的最新研究進展進行述評。
1 醫史文獻研究
現代學者多關注仲景學說的學術發展史、《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版本流傳、具體條文的校勘訓詁等方面。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處。如忽視了醫理與文理的結合,專注于文字考據而于臨床實用無補等。
1.1 學術史
學術史研究主要探討《傷寒論》不同版本的演化脈絡、流傳情況與傷寒學術發展之間的關系。如付鵬等[1]通過闡述“孫思邈本”《傷寒論》出現的學術背景,考察后世流傳主要文本和與之相關的傷寒學術流變,探討二者之間互動關系,明晰“孫思邈本《傷寒論》”單行本的出現和演變,離不開明清時期傷寒學術研究“尊經崇古”與“錯簡重訂”的學術對峙。王翠翠等[2]認為自趙開美翻刻宋本《傷寒論》后,其后較長時間內宋本《傷寒論》并不受國內醫家重視;而同時代的日本則較重視古籍版本研究,對宋本《傷寒論》進行深入考證。至江戶后期宋本已得到日本學界的普遍認可,并奉為諸多版本中的善本進行研讀。清末民初該研究思路影響國內,國內學者逐漸關注此本。
1.2 版本流傳
版本流傳研究主要考察《傷寒論》《金匱要略》不同時期版本與內容異同,有助于了解文本流傳情況,對學術研究具備參考借鑒。姚鑫等[3]對5個古傳本中的“可”與“不可”篇進行研究,認為文本章節命名大致經歷了從“病某某證”到“辨某某病形證治”再到“辨某某病脈證并治”這3個發展階段。范登脈[4]以臺北故宮博物院館藏明代趙開美翻刻宋本《傷寒論》縮微膠卷本為底本,利用現存不同朝代、不同時期《傷寒論》版本,對底本經文逐字對校,將各本異文盡收校注之中。付陽等[5]研究發現,《金匱要略》各種傳世版本中,吳遷抄本最大程度保留了北宋官刻原貌。鄒勇[6]以王叔和撰次的《金匱要略》與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逐條逐字比較,并參考《脈經》,客觀評價王叔和的撰次和發揮,以還原《傷寒雜病論》十六卷的原貌。
1.3 校勘訓詁
校勘訓詁研究,主要對《傷寒論》《金匱要略》文本進行字詞、語句分析,在某些方面存在學術觀點創新[7-9]。朱夢鷙等[10]利用中醫訓詁學方法并結合各家注解,分析《傷寒論》文本中42處“時”字,歸納其體現癥狀頻次、疾病變化過程、古代計時單位、某個時刻狀態、癥狀定時發生及探查6類含義,對研究張仲景臨床用藥、臨證觀察及時間醫學等,具有參考意義。劉辰鑫等[11]認為《金匱要略》一書得之于蠹簡,原書并非善本,雖有宋臣校注但仍能發現有數處疑似脫文。通過研究宋以前的醫學文獻,對《金匱要略》中疑似脫文之處進行補充。吳佳豪等[12]認為,《金匱要略》中的條文“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之“心氣不足”因形近而誤,當為“心氣不定”。該研究運用他校法,結合梁代陶弘景《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與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中相關條文,發現“足”為“定”之訛,“心氣不足”應為“心氣不定”,是指癥狀而非病機,即心中不安甚或煩悸、怔忡。
2 理論研究
在整個仲景學說研究工作中,理論研究依舊占據重要顯著位置。近兩年,有1/3以上數量的文獻屬于此類研究,專題涉及文本中的概念詮釋、理論思維、陰陽五行理論、藏象理論、六經理論、病機理論、診法理論、辨證體系、治則治法理論等。雖然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仍有不足之處。如有些研究者在理論探討中僅以一己之見來論述某觀點,缺乏認知高度和視野廣度,臨床驗證性實踐運用也明顯不足,故難以自圓其說。
2.1 概念詮釋
《傷寒雜病論》部分概念,因為時代變遷原意已發生變化;有些概念晦澀難懂,影響對張仲景思想的準確理解,這些都會影響到臨床運用,有必要進行厘清。張清苓等[13]詮釋了《傷寒論》之“難治”,從治病之義、針藥之用、生死之理等方面,討論了可治、不治與難治,藉此以論中醫治病之道。徐靜波等[14]對傷寒“協熱利”相關條文涵義的研究,將“協熱利”定義為“下利兼有表證的發熱”,拓展“表證發熱”概念為“在表層面的發熱”;依據疾病發展規律,將其分為衛郁發熱、衛郁化熱、里熱上炎三個層次。路瓊瓊等[15]通過對“三焦竭部”釋義與原文解析,明確“三焦竭部”是指上、中、下三焦所屬臟腑之間相互影響、互相傳變;且由于中焦脾胃的生理特性,“三焦竭部”重在中焦對上、下二焦的影響。
2.2 理論思維
仲景學說能夠一直興盛不衰,不是因為《傷寒雜病論》是一本治療外感病和雜病的專書,也不是因為其是“方書之祖”,收集了很多臨床有效的方劑,而是其為后學者展示了如何運用中醫理論思維來解決臨床實際問題,即陳修園所云:“垂方法、立津梁”。姜德友等[16]通過對《傷寒雜病論》中的各種象進行歸納、總結,找出張仲景運用象的方法及規律,對于正確把握張仲景學術思想,以及啟發中醫臨床思維具有參考。程薈蓉等[17]以“氣一元論”為認識基礎,結合《黃帝內經》中的相關理論,以精、氣、血、津液的最初病變作為綱目,從氣機聚散方面探討口渴癥(病理性)的成因,比較《傷寒雜病論》與渴相關諸方之間的聯系與差異,探討張仲景治療口渴的規律。
2.3 陰陽五行理論
《傷寒雜病論》蘊含著大量陰陽五行思想,說明《傷寒雜病論》不是一般的經驗之書而是理論之學,是對《黃帝內經》為代表的中醫經典理論繼承與發揮。如彭家柱[18]以陰陽升降、會通理論對《傷寒論》三陰三陽病證深入剖析,闡釋探究《傷寒論》中的“陰陽會通”思想。馬坤等[19]匯總古今諸家對于《傷寒論》第七條中“陰”“陽”及“六”“七”之數的論述,借鑒子午流注相關學說,提出“發于陽”,為邪氣自外而來,發病以六經傳變為主,“七日愈”為六經傳遍一周所需時間;“發于陰”,為邪氣自內而起,發病以五行生克制化為主,“六日愈”為五行亢害承制所需時間。
2.4 臟腑理論
本領域學者頗為關注臟腑間關系等理論研究。吳若霞等[20]通過梳理《內經》《傷寒論》及后世醫家的相關著作,探討張仲景在《傷寒論》中“心腎相關”理論的論述,以及對后世醫家如朱丹溪、嚴用和、葉天士等產生的影響。張盼等[21]通過對《傷寒論》重點條文、脾胃及全身氣機升降規律及烏梅丸作用機制的分析,得知脾胃與厥陰關系密切,提出以脾胃為樞論治厥陰上熱下寒證的觀點。劉派等[22]指出張仲景對于三焦的認識是在《黃帝內經》《難經》等為代表的三焦認識基礎上的綜合和超越,豐富了“三焦”的概念,疾病的病因、發病、發生發展均由“三焦竭部”(即氣化失常致三焦阻竭,相互不通)產生。
2.5 六經理論
六經理論一直是仲景學說研究的熱點。近兩年,有研究者關注從《黃帝內經》開、闔、樞理論出發闡釋六經實質;也有研究者基于《傷寒論》條文,結合臨床實際來闡釋六經理論。如陳明[23]借用《素問·陰陽離合論篇》“開、闔、樞”理論來闡釋六經理論,指出“開、闔、樞”是以六經的標本中氣為物質基礎,以氣機的升降出入為功能狀態。又如趙進喜[24]提出了三陰三陽系統論、三陰三陽體質論、三陰三陽辨證方證論,并剖析了《傷寒論》有關“傳經”“轉屬”“合病”“并病”“厥陰病”“厥熱勝復”以及“六經皆有表證”“三陰三陽排序”“寒溫融合”“三百九十七法”等疑難問題。
2.6 病機理論
學界把《傷寒雜病論》視為辨證論治的專書,一直關注局部的癥狀病機、證候病機,而近年來已有學者開始系統研究和構建《傷寒論》病機理論。劉玉良團隊研究發現《傷寒論》非常重視病機闡釋,其從病機的比較推測、病機的動態描述、寒熱病機和以脈論病機等方面進行系統總結[25-29]。如對《傷寒論》病機的動態描述,劉玉良指出《傷寒論》對病機的分析全面精細而且方法多樣,并且以動態觀念進行全局研判,其中的動態病機觀包括正邪交爭的動態病機過程闡析,病位、病性、病勢、病因病機和病性量變的精細定量等動態病機觀等[28]。
2.7 診法理論
《傷寒雜病論》涉及四診內容十分豐富,研究者多關注于診法的某一方面而缺乏系統性。如王寧等[30]指出,張仲景重視脈診與腹診相結合的臨床診察方法,可進一步明確疾病的輕重(如大結胸證與小結胸證、大承氣湯證與小承氣湯證),鑒別診斷相類似的疾病(如痞證與結胸證、蓄水證與蓄血證),辨明虛實情況(如陽明腑實兼氣血虧虛證),乃至鑒別某一個癥狀或體征(如腹急痛)。董碩[31]等分析了張仲景在臨證中利用“司內”的方法、辨證診斷的中醫思維方法,以及與現代微觀辨證相結合在臨床中的應用。肖嘯等[32]研究了張仲景“體脈合辨”思路,認為常脈受體質及身體狀態影響,臨床不可拘泥于“平脈”。汪淼等[33]梳理了《金匱要略》前22篇共48條涉及浮脈的條文,闡述了浮脈出現的部位、復合脈象多樣化、浮脈所主病機及浮脈于確立治則的意義。
2.8 辨證體系
六經辨證、方證辨證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并將其視為仲景學說的辨證精髓,而研究的泛化已導致脫離疾病來談辨證。張仲景原意“以病為綱”來“辨某病脈證并治”,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陳曉暉等[34]指出《傷寒論》除建立六經辨證體系外,其中更貫穿了氣血辨證的內容,指出在氣血傳變的過程中外邪由氣入血易郁而化熱,病有由氣入血、由氣入水以及水血之間相互轉歸。白長川等[35]認為《傷寒論》中的方證辨證體系包括主方辨證、類方辨證、合方辨證、藥證辨證、類證辨證和隨證辨證(壞病、或然證、若然證)六類,并對其進行了總結和梳理。劉南陽等[36]認為《傷寒論》方證辨證不是簡單的癥狀疊加,而是在明確病證特點的基礎上,選擇相應處方的一種思維模式,體現在方隨證變、藥隨證變、量隨證變、煎服法隨證變和劑型隨證變5個方面。馮世綸[37]認為經方辨證主要依據癥狀反應,不同于醫經、時方的經絡臟腑、五行六氣、體質、病因等辨證方法。
2.9 治則治法理論
研究者從多個角度出發對《傷寒雜病論》治則治法進行系統總結。如徐文楷等[38]歸納總結張仲景“通陽十六法”。曾思宇等[39]指出張仲景運用梔子豉湯、酸棗仁湯、甘草瀉心湯、瓜蔞薤白半夏湯等,采用辛開苦降法寒溫并用、升降同施,能使氣機復常、陰陽平衡,治療“陽不入陰”之失眠。趙開政[40]就涉及灸法取穴的相關條文,發掘整理《傷寒論》灸法理論。涂力禎等[41]歸納了《金匱要略》婦人病三篇治療婦科疾病“以治血為主,重視氣血、血水、肝脾之間的關系”的特點。
3 應用研究
學者更加關注仲景學說理論思維的臨床運用、探討具體病證的臨床辨治、六經辨證的具體運用、方證的臨床應用、具體藥物的臨床總結、配伍規律研究以及煎服法、劑型研究等,研究有深度也有廣度。但相關方面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如借助“多學科研究”名義研究經方運用,實質上僅僅是對文獻的二次分析,“新瓶換舊酒,換湯不換藥”缺乏新意;有研究以后人對方劑與藥物的應用經驗為依據,以今囿古,臆測為仲景原意,反而混淆視聽。
3.1 臨床思維
研究者多關注“血不利則為水”理論的臨床運用,并探討其在眼科、耳鼻喉科、內科、外科、婦科中的具體運用[42-46]。《金匱要略》提出“血不利則為水”,即因瘀血而致水腫的病機,指導著婦科及內科水腫病的臨床治療。方勇[44]發現這一理論對外科臨床亦有指導意義,試將其運用于臨床,并對其在治療外科疾病治療中的指導作用與現實價值進行初步探討。張仲景關于虛勞病的診治思路,也是臨床多種疑難疾病診治實踐的重要指導。如李敏[47]認為復發性流產(RSA)病機為脾腎兩虛,而《金匱要略》虛勞病機為氣血陰陽俱虛、虛實寒熱錯雜,二者病機相似,故RSA可從虛勞論治。虛勞以虛為本,故補益脾腎為其基本治則,但虛勞又有夾瘀、夾痰、虛寒、虛熱的不同,治療時當遵循“補不足,損有余”的原則。
3.2 臨床雜病論治
劉征堂等[48]推測歷節病是1組中晚期階段的風濕免疫性疾病,病機為正虛感邪,正虛包括肝腎不足、陽氣虛衰、陰血不足三方面,邪以濕邪為主,包括內濕和外濕。治療時要標本兼治,以溫通陽氣為主兼以祛邪。杜林柯等[49]指出《金匱要略》情志病證治,主要有從心肺陰虛內熱論治百合病,方選百合地黃湯以養心肺之陰治本,兼清虛熱治標;從心肝血虛、虛火內擾心神論治不眠,方選酸棗仁湯以補肝體、養肝血、清虛熱、養心安神;從心腎不交、陰陽俱虛論治夢交,方選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以交通心腎、潛鎮攝納、調暢陰陽;從心脾氣血不足論治臟躁,方選甘麥大棗湯以調補氣血、養心安神;從肝膽氣血虛弱、邪熱入里論治譫語,方選小柴胡湯解郁達邪以復少陽之機。丁元慶等[50]結合臨床對《金匱要略》中風證治進行分析研究,其內容主要涉及中風病名、病因病機、證類、治法方藥等,認為其已構建起中風診療體系。張悅等[51]建構了消渴病的證候框架,并提出相應的治法與方藥。
3.3 六經辨證應用
關于六經辨證應用于臨床的文獻有很多,包括研究六經辨證治療雙心疾病、心衰、腎性水腫、癌性疲乏、不寐、圍絕經期綜合征等[52-57]。如李令康[55]指出,臨床上心血管系統疾病伴發心理疾病的情況被稱為“雙心疾病”,根據《傷寒論》原文展開研究,發現心胸病癥、心神病癥往往相伴出現,十分契合“雙心疾病”的臨床癥狀,并且六經皆有心病,在不同時間和空間上描繪了“雙心疾病”發病進程。在辨證方面,系統分析六經辨證所示“雙心疾病”的病因病機;在論治方面,挖掘可用于治療雙心疾病的經典方劑,簡述其臨床應用現狀,為今后的治療開闊思路。
3.4 方證應用
方證研究一直是仲景學說研究的重點、熱點,近兩年更多關注方證的臨床應用,主要涉及桂枝湯證、麻黃湯證、大青龍湯證、葛根芩連湯證、葛根湯證、芍藥甘草湯證、厚姜半甘人參湯證、半夏厚樸湯證、麻子仁丸證、五苓散證、苓桂術甘湯證、小承氣湯證、茵陳蒿湯證、真武湯證、半夏瀉心湯證、麻黃升麻湯證、當歸四逆湯證、小柴胡湯證、大柴胡湯證、柴胡桂枝湯證、柴胡桂枝干姜湯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證、黃連阿膠湯證、梔子豉湯證、竹葉石膏湯證、烏梅丸證、百合地黃湯證、風引湯證、奔豚湯證、甘草干姜湯證、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證、侯氏黑散證、厚樸七物湯證、黃芪桂枝五物湯證、己椒藶黃丸證、金匱腎氣丸證、麥門冬湯證、酸棗仁湯證、溫經湯證、竹葉湯證等。
如王慧穎[58]等運用麻黃湯冷服治特發性耳聾,是對麻黃湯證運用的拓展,提出從辨證論治的層面出發,因肺氣壅滯而影響體內氣機升降失調,濁陰上逆干擾頭部的清陽而致九竅內閉之不通的耳聾,可以用麻黃湯進行治療。又如尚唱[59]等運用半夏厚樸湯治療情志失調所致失眠、抑郁、驚恐障礙驗案三則,其主癥雖各有不同,但存在共同病機,即肝郁疏泄失常,津液積聚生痰,痰氣搏結。此外,暢達[60]等撰寫《仲景活法湯方辨證及臨床》一書,對41種經方的方證進行了辨析示范,以便于把握方證的特點并運用于臨床。
3.5 用藥心得
萬田莉等[61]認為,《金匱要略》運用含川芎的9首方劑治療風疾、虛勞及婦人之疾,其特點主要為療風疾行堵截之法,治虛勞行通陽達陰之法,治婦人之病取其引陽入陰之法。李登嶺[62]從張仲景使用大黃的量、煎、服、禁方面揣度張仲景活用大黃心法,該方法也適用于對經方其他方藥的研究。張君合[63]發現,《傷寒論》中生姜出現39方(次),干姜24方(次),兩者配伍使用5方(次),認為生姜與干姜同用必須是脾胃虛寒、水氣散漫。若重用生姜則側重治療水氣,特別是水液代謝障礙,重用干姜則補陽,與生姜同用則兩者協同。車一鳴等[64]發現,經方中甘草的用量以27.8 g居多,最多可用至69.5 g,最小用至3.5 g;生甘草多用于熱證、疔毒、瘡瘍、飲證等,而炙甘草多用于表證、中焦虛弱、脾胃虛寒、中氣不足、營衛不和等證;經方中的炙甘草應當是“炒甘草”而非蜜炙甘草。張宇靜[65]通過“析藥測證”“以藥串方”的形式努力探索,還原張仲景時代諸醫者的用藥思辨規律,從“證-藥”角度全新地詮釋每味藥物。
3.6 經方配伍規律研究
經方配伍規律研究,一直是仲景學說研究的熱點。近年研究主要圍繞經方藥物中的配伍規律、經方合方與十八反的關系、經方中的藥對和角藥,以及經方量效關系等方面。
曲夷[66-72]從經方主治證候、配伍應用、用法用量等方面,探討其中當歸、桂枝、黃連、栝樓實和栝樓根、細辛、生姜、石膏等藥物的配伍規律。有研究者借用了幾何學方法來研究經方配伍[73]。馬玉杰等[74]通過分析《傷寒雜病論》瘥后方,分析出核心藥物組合為“人參、甘草、半夏、生姜、大棗”,推導出瘥后方的核心方證為“心下痞,嘔吐,不欲飲食”,各瘥后方以瘥后核心方證為基礎,再隨證加減治療非核心癥狀。王付[75-82]對經方合方與十八反的關系做了系統的研究,發表了多篇論文,從理論溯源及經方合方治驗等方面探討中藥“十八反”配伍禁忌的不合理性,并從經方合方治病中研究如何運用中藥“十八反”配伍辨治各科雜病。
關于經方的藥對研究、角藥研究也得到很多學者的青睞。有研究者[83-86]關注張仲景方的藥對研究,希望藥對研究能為臨床診療做出有益探索。角藥也是藥對的一種,是基于中醫基礎理論對可以相互作用的3味藥物進行的有機組合。有研究者[87-93]認為,《傷寒雜病論》中蘊含著豐富的“角藥”配伍形式,如橘皮、枳實、生姜、干姜、細辛、五味子,柴胡、白芍、枳實等。有研究[94-95]分析《傷寒雜病論》中半夏、葛根的量效關系及配伍用藥規律。此外,還有研究進行了中日經方本原劑量比較研究[96-97]。
3.7 煎服法、劑型
徐靜波等[98]從《傷寒論》將息法入手分析,將藥物服用時間根據時間段和次數進行整理,分析服藥時間對療效的影響,為臨床判斷藥物服用時間提供思路。鄭相敏等[99]研究發現,《金匱要略》中湯劑的服用次數是由藥性、用藥目的、病證性質、病勢緩急、療程長短等決定的。常規服用方法為每日3次,若攻邪救危可集中藥力,日服2次,長期服藥或病輕者可減少服藥次數。邪重病急者,欲取高效、速效者應頓服。姜俠等[100]以《傷寒論》原文為基礎,著重從條文主治來分析歸納大黃的炮制煎煮用法差異,總結出其炮制法主要有酒洗、酒浸、生用、去皮,煎服法有先煎、同煎、后下、麻沸湯漬之。楊澤等[101]認為張仲景運用散劑,可據制作方式和使用途徑而多樣細致地分類,其所用溶媒靈活,作用可概括為護胃安中、解毒補虛與助行藥力、因勢利導;其劑量因人體質的羸壯、藥性的峻緩、疾病的緩急各異;作用可根據治療疾病的不同而分為散水排膿,調經安胎與通閉解結。
4 實驗研究
實驗研究主要關注張仲景理論的生物學實質、仲景方藥的作用機理等。研究者對于實驗研究的態度存在正反兩面的認識。贊成者認為,實驗研究是打破中西醫壁壘的技術和方法,只有實驗研究中醫才有希望和未來,只有實驗研究才能證明中醫是科學的;反對者認為實驗研究就是工具,類似于化妝品,用來粉飾中醫的科學性,最終還是要卸妝的。實質上,這兩種觀點都是片面且極端的。如何在明確自身學術立場、保持理論本色的前提下,合理借助現代科學技術方法,在局部或者一定層面解釋仲景學說的基本規律和運用法則,探索并發現新的生命科學現象,是值得今人認真思考的重要話題。
4.1 病證本質
鄭智禮等[102]尋求“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的生物學依據,探討其對肝郁疊加慢性肝損傷大鼠模型肝細胞凋亡的影響。研究發現,“知肝傳脾”有其生物學依據且與肝細胞凋亡相關。“當先實脾”之柴芍六君子湯組對該模型各指標的調節作用優于其他干預方式。劉紫微等[103]探討麥門冬湯治療系統性硬化癥(SSc)引起的血管病變的作用機制。研究表明,麥門冬湯可通過降低SSc小鼠ACEA、VWF、TXB2的含量,增加6-keto-PGF1α的含量,減輕SSc引起的血管病變。張喜奎等[104]研究發現,桃核承氣湯可明顯改善CRF大鼠的貧血狀態及腎功能;桃核承氣湯可改善慢性腎衰竭腎纖維化,其作用機制可能與抑制Wnt/β-catenin信號通路傳導,上調APC表達,下調β-catenin、TCF4的表達有關。
4.2 方藥機理
趙冉冉等[105]探討半夏瀉心湯治療胃腸動力障礙性疾病的可能作用機制。研究發現,半夏瀉心湯可能通過調控ICC細胞凋亡相關蛋白Caspase-3、Bax、PI3K、Bcl-2及抑制NO、eNOS分泌,抑制ICC細胞凋亡,從而發揮治療胃腸動力障礙性疾病的作用。高譽珊等[106]研究發現,大柴胡湯及其拆方均能不同程度地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模型大鼠肝細胞脂肪變及腸細胞緊密連接情況,并以全方共用效果尤著,疏肝利膽、健脾化痰、通腑泄濁等治法聯合運用對改善NAFLD具有較好的療效。張婷婷等[107]研究發現,當歸芍藥散加味方可改善乳腺增生模型大鼠乳腺組織增生狀態,其機制可能與激活乳腺上皮組織Let-7a基因表達和抑制p-ERK蛋白的表達有關。李玉卿等[108]探討防己黃芪湯治療慢性腎炎的療效及對其血管微炎狀態的影響。研究表明,防己黃芪湯對慢性腎炎臨床療效顯著,可改善腎功能和血管微炎癥狀態。方穎等[109]研究發現,黃芪桂枝五物湯可減輕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其機制可能與阻斷AGEs/RAGE/NF-κB信號通路中組織細胞表面RAGE的表達,抑制NF-κB激活及其引發TNF-α觸發的氧化應激和過度炎癥反應,從而避免細胞受損和功能紊亂有關。
近年來,研究者逐漸重視網絡藥理學方法,將其運用到研究經方作用機理上。如厲越等[110]基于系統藥理學方法研究葛根芩連湯治療潰瘍性結腸炎的作用機制。研究表明葛根芩連湯可通過多靶點、多通路等對潰瘍性結腸炎發揮作用。楚毓博等[111]基于網絡藥理學的方法,探討三物白散治療胃癌的作用機制。研究發現,三物白散可能通過調節缺氧、炎癥與代謝相關因子、通路,改善腫瘤微環境,從而發揮治療胃癌作用。王夢薇等[112]基于網絡藥理學研究枳實薤白桂枝湯和人參湯治療皆主胸痹的科學內涵。研究發現,枳實薤白桂枝湯和人參湯中共有靶點及靶點所在的生物過程和通路,可以共同治療心絞痛。而枳實薤白桂枝湯特有靶點(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因子1)和人參湯特有靶點(單胺氧化酶A)作用的不同,可能是枳實薤白桂枝湯與人參湯皆主胸痹的生物學實質。
5 運用信息學、循證醫學等方法開展研究
隨著信息學、循證醫學等方法在中醫研究中的逐漸廣泛深入,研究者開始將知識圖譜、數據挖掘、Meta分析等方法運用在仲景學說研究中。
王菁薇等[113]通過人工抽取《傷寒論》原文的知識,基于Neo4j完成了《傷寒論》知識圖譜的構建。石維娟等[114]搜集醫案建立數據庫,利用頻次統計和黃金分割法分析柴胡桂枝干姜湯方證的發病規律、癥狀規律和用藥規律,用以指導本方的臨床應用。王倩倩等[115]通過對葶藶大棗瀉肺湯文獻的數據挖掘,深入挖掘出“瀉肺”的內涵一為瀉肺水,一為瀉肺熱。瀉肺中水飲時多配伍利水、通陽藥物;瀉肺熱降氣化痰濁時多配伍清熱降氣化痰藥物,且葶藶力峻多配伍護正之品。陳淼等[116]運用Meta分析方法評價桂枝湯類方治療心系疾病的安全性及療效,發現該類方治療心系疾病能夠提高臨床療效,且不良反應較小。
6 與新冠疫情結合的研究
2020年初,新冠疫情開始襲擊我國,嚴重影響我國人民的生命安全。近兩年來,全世界仍處于疫情防控階段,疫情常態化已成為社會生產生活的主題。有研究者基于仲景學說對當前正在流行的新冠肺炎(COVID-19)的病因病機進行分析,并據此提出相應的診療、防控策略。
王東軍等[117]指出挖掘張仲景疫病理論,從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的角度淺談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因病機、方證治法的認識,可為防治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提供相應的理論指導。張喜奎等[118]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外感寒濕引起的,傳染性強,流行范圍廣,屬于中醫寒疫夾濕范疇。本病的發生發展過程與《傷寒論》的六經證候較為契合:先犯太陽而后傳入陽明、少陽,危重患者可直中少陰、厥陰,后期常見邪留太陰、少陽。吳琪等[119]也持相似的觀點,認為新冠肺炎乃疫毒之邪夾寒濕侵襲人體,發病符合六經傳變規律,臨床上以六經辨證為綱,掌握疾病傳變規律,辨證用藥,靈活化裁,可以取得滿意的臨床療效。薛伯壽等[120]根據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情況,結合蒲輔周經驗,總結此次疫情為“寒濕疫”,其治療必須善用麻黃劑,“清肺排毒湯”實為張仲景相關經方的融合創新運用,可為疫情防控和臨床救治發揮重要作用。黃鴻鵬等[121]通過對新冠肺炎“清肺排毒、宣肺排毒、化濕敗毒三方”組方理念的解讀,可以看出“三方”皆以《金匱要略》治濕理念為組方指導思想,以溫藥為主調,通過在上者發汗和在下者利小便去濕,同時在重型和危重型方劑中配以行氣活血之品以祛深入血分之水濕,實現了上下分消、標本兼治。黃青松等[122]基于“差后勞復”理論探究新冠肺炎患者核酸“復陽”的中醫治療思路。研究認為,新冠肺炎(COVID-19)核酸“復陽”患者屬于疾病的恢復期,中醫病因病機為正氣不充,余邪未盡,因調攝不當或勞食誘發,屬于虛實夾雜之證,可按柴胡類方證、竹葉石膏湯證、理中湯證及枳實梔子豉湯證化裁而治,同時應兼顧愈后飲食調護,強調顧護脾胃的基本思想貫穿治療始終。
當前,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中醫藥事業發展,仲景學說研究與建設機遇與挑戰并存。黃璐琦院士對中醫理論傳承與創新指出重要路徑,主張要“基于臨床實踐不斷驗證、升華重要知識,形成新的理論,用于指導實踐,促進理論的不斷發展與完善”[123]。因此,深入挖掘與提煉仲景學術思想,并在當代臨床實踐中不斷運用、驗證、完善與弘揚,形成原創性理論認知,是促進中醫藥學術發展、提高臨床療效的基本前提。今后,通過仲景學說研究,如何實現其科學內涵的現代表達,講清楚說明白其防病治病的科學原理,仍然是本領域的時代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