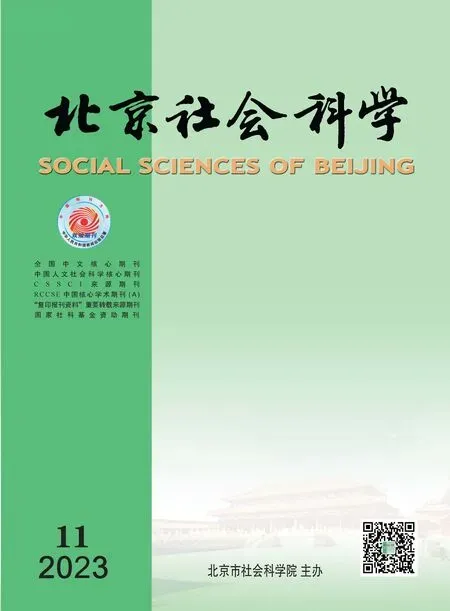慣例:一個文學理論關鍵命題的探究
龐 弘
一、引言
在當代文學理論中,尤其在涉及“意義與闡釋”的理論言說中,“慣例”(convention)是一個不可缺失的維度。在文學活動中,慣例指一系列被普遍分有并默守的閱讀規則和釋義程序。在很多時候,慣例的面目模糊、形態多變,難以被直觀體察和真切把握,但往往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滲入人們的精神世界,對其解碼文本的姿態、路徑和實際效果產生微妙影響。從經典“四要素”的視角來看,慣例可以說是“語境”的衍生物,它來源于闡釋群體所共有的生活閱歷、情感積淀和價值訴求,是復雜多變的社會情境在闡釋實踐中的動態演繹。
長期以來,人文學者在追問意義問題時,往往聚焦于作者意圖、語言性文本或讀者主觀反應中的某一環節,相較之下,慣例則被視作研究的“背景”或“補充”,其價值和合法性未能得到充分關注。近幾十年來,研究者開始意識到,意義不完全來自文學活動本身,同時也是一個交織著多重頭緒和線索的社會過程的結果,“它與我們作用于現實的方式,與社會價值、傳統、假設、制度以及物質狀況緊密相關”[1]。在這種“向外轉”的過程中,慣例之于文學闡釋的樞紐地位被不斷彰顯,其作為一個獨特文論命題的內涵也變得愈發醒目。
二、作為生活經驗慣例的特征
應該說,慣例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經驗形態。在面對一些難以決斷的問題時,我們往往會不自覺地訴諸既往的慣例;在遇到一些挑戰或打破慣例的事件時,我們又多半會感到有些無所適從。《現代漢語詞典》將慣例界定為:“一向的做法,常規。”[2]上述解釋比較簡單,基本上就是同義詞(即“常規”和“慣例”)的互換。相比起來,《牛津英語詞典》和《韋伯斯特國際英語詞典》中的定義要更為詳盡。前者認為,慣例是“構成習俗、制度、意見等的本原或根基的,或顯露或隱晦的普遍共識或認同”[3]。后者強調,慣例在日常生活中有兩層內涵:一是“在社會習俗或道德事務中被普遍認同和遵循的習慣、習俗或做法”;二是“因長期使用而被廣泛接受并確立的規則、習俗或信仰”。[4]從語詞構造上看,convention由表示“共同”“聯合”的con和表示“阻礙”“束縛”的vention組成。這說明,慣例一詞蘊含著雙重的精神取向:首先,慣例是一種法則或規約,它引導人們的思考或行動,使之無法隨心所欲;其次,慣例并非訴諸單一對象,它獨立于個體意志而存在,對一個社會或文化共同體的成員產生普遍效力。
作為生活經驗的慣例有三個特征。一是從時間上看,慣例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而是在漫長的時間進程中積淀而成,并體現出較強的穩定性和歷史延續性。比如“女士優先”或“長者為尊”,就源自人類在長期的溝通與交往中形成的慣例。二是從空間上看,慣例一般不為個體所專有,而是被同一個群體的人們所共同遵循,在某一民族、社會或文化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中國人習慣于使用筷子,法國人習慣于使用刀叉;東方人看到月亮想到故鄉,西方人看到月亮想到狼人,這些都是不同群體所默守的文化慣例。三是慣例并非形諸語言文字,亦非被明確的條條款款所框定,而是悄無聲息地滲入人們的精神世界,成為一些無須言明,但又有普遍約束力的思想參照和行動坐標。①盡管法律從未對男性和女性的象征物予以明文規定,但在去衛生間時,絕大部分人還是會將有“煙斗”圖標的認同為男衛生間,而將有“裙子”圖標的認同為女衛生間。總之,慣例并非簡單的思維或實踐體系,而是蘊含著復雜的歷史底蘊和社會文化心理;慣例的每一次形成或更替,都不只是思維或行為方式的調整,而是意味著人類精神狀態乃至“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的深刻改變。②
在人類生活中,慣例的種類不勝枚舉。從餐飲娛樂到節慶儀式,從社交禮儀到國際關系,都存在著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慣例。在文學活動中,同樣不難找到慣例的蹤跡。一般來說,人們對某些文學形象的使用會形成慣例,如芳草象征離愁別緒,紅豆象征男女愛情,流水象征時光的飛逝,烏鴉暗示荒涼冷寂的氛圍。不同的文學類型也攜帶著不同的慣例,如詩歌多半要分行,要有較強的音樂性,充斥著鮮明的象征和隱喻;小說往往以敘事為主,包含著引人入勝的懸念和突轉,以及充滿個性的人物形象;戲劇通常以沖突為催化劑,尤其強調時空的高度集中和臺詞的動作性。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亦有區別于其他藝術形態的慣例,如文學是虛構、想象和創造的產物,以抽象的語言文字為本體形態,以強烈的主觀感情為內在動因。以上這些都不是對文學的明文規定,但融入了人類的審美經驗和集體記憶,成了一些具備普遍性和可通約性的,無須追問或辯駁的文化律令。
三、從生活經驗到意義話語:慣例的理論演進
(一)維特根斯坦的“生活方式”
作為生活經驗的慣例一旦與意義問題相結合,便會呈現出更微妙、復雜、耐人尋味的狀態。在此,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發現,按照傳統觀點,意義是潛藏在語言文字背后的,普遍、永恒而絕對的存在。在語言符號及其所表征的意義之間,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系。故而研究者完全可以通過對語言性文本的開掘,對隱含其中的深層次內涵加以呈現。在學術生涯的后期,維特根斯坦對這種“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意義觀予以反思。在他看來,語言并不是一種有生命力和自主性的存在,相反,語言實質上是一種中性的、有些空洞的符號,它需要向血肉鮮活的主體敞開,通過主體的一次次參與或使用而彰顯其意義。維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意義即用法”命題。他這樣說道:“在大多數使用了‘意義’一詞的情況下——盡管不是全部——我們可以這樣解釋:一個字詞的意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5]這就像我們之所以明白象棋中“車”“馬”“炮”的意思,不是因為這些概念天然便擁有相應的意義,而是我們通過對此類概念的使用,在紛紜變幻的棋局中賦予其特定的內涵或功能;我們也不是一開始就理解什么是足球比賽中的“紅牌”“點球”“越位”,而是通過對上述規則的身體力行的參與,使之逐漸變得清楚而明晰。
基于此,維特根斯坦將“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納入關注視域。他強調:“講語言是一種活動的組成部分,或者一種生活形式的組成部分。”[6]在他看來,意義并非內在于語言符號之中,而是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以及由此所建構的文化觀念和精神體系)的產物。相應地,意義也就不可能恒定不變,而總是隨著時空的更迭和情境的轉換呈現出變動不定的形態。不難發現,維特根斯坦在一定程度上將慣例引入了闡釋活動。他試圖向我們說明,一切相對穩定的意義都不是本然的實存,也不是隱藏在字里行間有待人們來揭示的“本質”或“中心”;恰恰相反,意義帶有明顯的公共性和關系性,它不是獨立自在的體系,而是在文化、制度、習俗、慣例等因素的“合力”下生成和改變。
(二)丹托·迪基、貝克爾和“藝術界”
對慣例在意義場域中的作用予以進一步確證的,是影響深遠的“藝術界”(artworld)理論。這一理論來自美國學者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用以指代促使研究者將某一對象視作藝術品的“藝術理論的氛圍”或“藝術史的知識”。[7]在丹托的基礎上,喬治·迪基(George Dickie)對藝術界做出了更詳盡的闡發。他認為,所謂藝術界,其實是不同社會成員圍繞著藝術所形成的松散而又彼此關聯的群體,其骨干包括藝術家、藝術史家、藝術批評家、新聞記者、大學教授、藝術策展人、畫廊經營者等。這個群體營造了一種制度化的氛圍,并常常就關于藝術的一些重要問題加以權衡或決斷。迪基斷言,某一物品成其為藝術的條件有二:其一,“人工制品”;其二,“代表某種社會制度(即藝術界)的某個人或某些人授予其被欣賞的候選者地位”。[8]言下之意是,藝術從來就沒有一個與生俱來的本體屬性。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藝術,實際上來源于藝術界成員就“何為藝術”“藝術何為”“藝術如何”等問題做出的帶有普遍性和共識性的闡釋。這些闡釋的形成,歸因于藝術界成員所分有的文化經驗、審美趣味、知識積淀和認知慣例。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杜尚的《泉》或沃霍爾的《布里洛洗衣粉盒》會被視作藝術家族的一員——其關鍵不在于作品本身的形式是否精妙,內涵是否深邃,也不在于作品中是否充溢著創作者的靈感和激情,而在于藝術界成員在某些慣例的引導下所進行的“資格賦予”。用迪基的話來說,藝術界的實踐始終“在慣例的層面上運行”[8]。
對慣例之于藝術理解的必要性,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S. Becker)同樣有深入思考。貝克爾相信,藝術從來不是個體在孤獨狀態下的創造,從來不是藝術家在某一瞬間靈光乍現的產物;相反,從陳列在盧浮宮的傳世名作到鄉野村夫的手工藝品,任何我們在今天稱得上“藝術”的東西,其實是不同人集體協作、聚沙成塔的結果:“這些人擁有不同的技能和才華,來自不同的背景,屬于不同的職業群體。盡管他們的訓練和背景有所不同,但他們卻找到一種合作方式,制作了他們那種藝術典型的最終成品。”[9]更進一步,貝克爾強調慣例在藝術活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他看來,慣例乃是“創作藝術的人和閱讀、聆聽或觀看藝術的人所共有的觀看之道和聆聽之道,任何參與其中的人都對此了若指掌,因此這為他們的集體行動提供了基礎”[10]。作為一套約定俗成的話語體系,慣例為人們對藝術的評判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使人們就藝術的邊界、特征、功用、生產流程、表現策略等問題達成共識,對自身在藝術活動中的職責和義務形成最基本的認知。如此一來,人們將攜帶著相似的“游戲規則”,以大體相近的態度投身于藝術界,并由此展開協調一致的行動。
(三)庫恩和“范式”
另一個和慣例頗具相關性的命題,是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paradigm)。庫恩認為,科學共同體由致力于同一研究領域的科學家組成,他們“經受過近似的教育和專業訓練”,“鉆研同樣的技術文獻”,且能夠“從中獲取許多同樣的教益”。[11]庫恩相信,范式乃是科學共同體賴以維系的肯綮所在:“一個范式就是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東西,而反過來,一個科學共同體由共有一個范式的人組成。”[12]他進一步總結了范式的四個構成要件:其一是“符號概括”,即共同體成員不假思索地使用的各種公式或定理;其二是范式中的“形而上學部分”,即共同體成員不約而同地尊奉的信念;其三是“價值”,即共同體成員始終堅持的選擇或價值判斷;其四是“各組范例”,即科學共同體中具有標志性的研究案例,其作用在于提供最典型的研究示范,提示人們應如何對研究中出現的問題加以解答。[13]以上這些凝聚為科學共同體所獨有的話語規則或慣例體系,它們并非強行賦予的結果,而是科學家在長期實踐中逐漸積累的產物。正是它們的存在,使科學家對共同體的內涵、屬性和使命做出相對一致的理解,在某些共識性承諾的推動下投身于研究實踐。誠然,相較于不那么嚴謹、整飭的藝術界,范式具有周密、客觀、精確的特征,但在強調慣例對藝術或科學之邊界的維系上,二者又表現出顯而易見的相通之處。
通過維特根斯坦等人的理論建構,慣例逐步由一種生活經驗涉入意義場域。如果說在日常生活中,慣例是引導人思考或行動的一套普遍的法則、規范或秩序,那么,作為一種意義話語的慣例,則意味著文學共同體成員就文本及其內涵所形成的共識或默契,它為闡釋設置了一條大致穩定的邊界,使闡釋者的能動解讀始終有所節制,而不會成為無所顧忌的自說自話。
四、從“意欲類型”到“闡釋社群”:慣例論的三條路徑
近幾十年來,伴隨著文學研究由“去語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到“再度語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轉向,慣例在文學闡釋中的重要性變得愈益顯豁。在此背景下,一些研究者試圖以慣例為基點,對文本意義的輪廓加以勾畫,形成了“慣例論”(conventionalism)這一文本解讀的重要范式。透過慣例論的視角不難發現,意義并非由作者所賦予,亦非由語言性的文本所涵納,更不是由小寫、多元、復數的讀者任意創造,而是在慣例的影響下逐漸生成。布洛克(H. G. Blocker)承認闡釋的能動性和差異性,同時又堅稱,文本意義應當被限定在絕大多數人默許的范圍之內:“人們所爭論的最多不過是,在上述范圍內,究竟哪一種解釋最好。”[14]顯然,為這一意義范圍設定邊界的乃是不同闡釋者所共有的知識系統和閱讀慣例。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同樣秉持慣例論的立場。在他看來,意義并非私人化的心緒、體驗或感受,它從根本上“象征著特定時空下人類之間的契約,體現了人類所共有的行為方式、感知方式和思維方式”[1]。故而,讀者也就無法對文本加以任意擺布,必須接受慣例這一人類文化中“神圣契約”的約束。
在文學闡釋場域,慣例論通過如下三條路徑得以集中表現,即“意欲類型說”“文學能力說”和“闡釋社群說”。
(一)意欲類型說
這種觀點的倡導者是美國學者埃里克·赫希(Eric D. Hirsch)。赫希認為,意義并非凝固不變的實體,而是一種兼具開放性和限定性的“意欲類型”(willed type),亦即“一個可以由各不相同的實例或意識內容來再現的整體”[15]。作為一種類型化的存在,意義擁有延展和擴容的較充足空間,因而會基于不同解讀而呈現出豐富形態;同時,意義又攜帶著一條明晰可見的邊界,使人們的能動解讀無法越出邊界的限定,不會陷入漫無頭緒的狀態。至此,一個有些棘手的問題出現了——類型的邊界究竟由何種因素決定?赫希試圖凸顯慣例所具有的建構作用。他宣稱,文本的可理解性有賴于公眾對言語意義的普遍分有,而言語意義的可分有性(sharability),則取決于“被分有的慣例(shared conventions)的存在”[16]。
赫希指出,所謂慣例,就是將“語言使用、個別特征、法則、習俗、形式上的必然性,以及構成某個特定語義類型的社會規則”[17]等因素包容其中的文化知識系統。基于對同一套慣例的分有,創作者對其表意的方式和效果有大體明晰的期待,而闡釋者也會盡量配合創作者的期待,使釋義活動在一條相對穩定的軌道內運行。如在揚·凡·艾克的名作《阿爾諾芬尼夫婦的婚姻》中,充斥著鏡子、蠟燭、蘋果、木屐、掃帚、小狗等繁復的視覺意象,但倘若對15世紀北方文藝復興的世俗生活和文化慣例有所了解,人們便會在第一時間內領悟上述意象所負載的象征意蘊。再如豪斯曼在一首田園詩中寫道:“在蔚藍銀白的清晨/他們躺在干草堆上/彼此凝望對方/很快移開了目光。”詩中的“他們”究竟所指為何?豪斯曼沒有明言。然而,批評家羅伯特·萊利(Robert M. Ryley)堅稱,“他們”的模糊性不會對理解該詩造成太大困擾。原因很簡單,詩人已然將大多數英國讀者諳熟的慣例融入詩句之中:其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鄉村,在缺乏休閑娛樂場所的背景下,熱戀中的年輕人習慣于趁月黑風高之際,偷偷來到農場的干草堆上度過甜蜜一夜;其二,在當時保守的社會氛圍中,公眾對婚前性行為的包容度極低,故而初涉魚水之歡的愛侶在清晨注視彼此時,會產生難以掩飾的羞愧情緒;其三,豪斯曼本人是一名同性戀詩人,終其一生,他都因自己的性取向而備受懷疑、鄙薄與非難,這就決定了在一首公開出版的詩歌中,他不太可能毫無顧忌地書寫違逆倫常的同性之愛。萊利斷言,在了解上述慣例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將“他們”的類型限定為“一對在干草堆上共度良宵后感到羞澀的異性戀情侶”,而不會將其理解為別的什么東西。[18]
通過將慣例引入其意欲類型學說,赫希使文學闡釋呈現出更豐富的演繹空間,以及更復雜的社會公共屬性。但必須注意,作為一位著名的意圖論者(intentionalist),赫希基本上將文本意義與作者意圖畫上等號。在其理論體系中,由慣例所設定的意欲類型的邊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作者表意實踐的邊界;而闡釋者需要做的,則是以慣例為線索,盡可能達成對作者之意的還原或重構。這就簡化了我們對慣例的理解,同時也遮蔽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微妙互動關聯。
(二)文學能力說
這一學說的代表人物是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如果說赫希將慣例置于外在的社會文化層面,那么卡勒則更多將慣例內化于主體的經驗模式與認知結構。卡勒的觀點受到了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影響。喬姆斯基的最突出貢獻在于提出了“語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學說。語言能力不同于一般的言語行為,而是語言共同體成員所掌握的一套語用規則和語義生成機制,它保證了人們在不同情境下對語言的靈活運用和能動創造。[19]基于對語言能力的思考,卡勒試圖對文學研究中的結構主義加以重估。在他看來,結構主義與其說是對文本內部封閉單元的發現,不如說是“一種力求確立意義產生條件的詩學”[20]。按照結構主義的基本預設,某一文本或語言序列要獲得意義,“其中必然有一套使這種意義成為可能的基本的區分機制和慣例系統”[21]。這種賦予語言對象以意義的機制和系統,便是所謂“文學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
如果說語言能力是人類所共有的深層次語言結構,那么文學能力則是不同讀者所共有的深層次解碼或釋義結構,這種深度結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讀者和作者在長期的文學活動中分有的話語規則和慣例體系。在闡釋實踐中,文學能力可謂不可或缺。正是在文學能力的引導下,讀者才會以相似的姿態進入文本,從中發掘出大體相近的內涵,從而以潛移默化的方式與作者就文本意義達成總體上的契合或一致。譬如,在寫下“楊柳岸,曉風殘月”時,柳永或許并未明白無誤地想到“惜別”,但事實上已將“柳”在千百年來所積淀的象征意蘊融入詞句之中;讀者——經過長久以來的文學熏陶,他們已具備了解讀相關意象的文學能力——在接觸到上述文字時,自然很容易從中體會到強烈的依依惜別之情,從而不由自主地陷入情感共鳴。不難發現,相較于赫希對作者一極的關注,卡勒更側重于呈現作者和讀者在闡釋實踐中的互動或溝通。當然,卡勒并未否認闡釋中差異與分歧的存在,但他認為,正是文學能力在不同讀者之間所制造的共識,為意義之多元生成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或參照系:“我們注意到闡釋的差別,恰恰是因為我們將共識視作基于共有慣例的交流過程的自然結果。”[22]
卡勒對文學能力的探討在當代文論中不乏回響。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認為,人們一旦擁有相近的文化經驗或審美經驗,就會逐步將某種“相同但心照不宣的規則”[23]內化于心。這種共享的意義規則(以及蘊含其中的慣例系統),將使言語意義在某一時間節點停止其自我生產,形成較為穩定的狀態。基于此,我們才有可能說清自己的意思并理解他人之所說。約翰·塞爾(John R. Searle)斷言,意義不會如解構主義者設想的一般,隨著能指的滑動而無限蔓延或流變,相反,“在存在著一套固定的背景能力(background capacities)和意向性網絡(network of intentionality)……的前提下,意義和交流是完全確定的”[24]。在他看來,構成這種背景能力或意向性網絡的乃是主體在長期的文化交流中積累的文化知識或閱讀慣例,它保證了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的理解與闡釋被框定在一個大致穩定的閾限之內,而不會出現天馬行空、隨性所致的情況。足見,文學能力一方面揭示了閱讀的內在機制,另一方面又使闡釋者不得不遵守某些隱性的支配法則。這樣,文學能力也就為抵制意義的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提供了重要契機。
(三)闡釋社群說
這一學說的代表人物當屬讀者反應批評的頭面人物斯坦利·費什(Stanley Fish)。費什坦言,讀者反應批評聚焦于“意義經驗的‘運動性’(movingness)”,從而將研究重心轉向“讀者的積極而活躍的意識”。[25]在他看來,意義并非真切可感的實存,而只是一些飄忽不定的主觀經驗或效果。這樣,讀者在意義生產中的唯一合法性將隨之凸顯。換言之,正是讀者的能動參與和想象性建構,使意義從千頭萬緒的文本中浮現出來,獲得相對穩定的表現形態。在此,出現了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由于讀者是不同的個體,擁有不同的情感、心性、品味、價值判斷,那么,如果將闡釋的權柄完全交到讀者手中,勢必會造成意義的主觀化和相對化,以及闡釋者之間溝通與交流的失效。為回應上述問題,費什引入了著名的“闡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命題:“意義既不是穩固不變的文本的特征,也不是自由無羈的讀者的特征,而是闡釋社群的屬性。闡釋社群既決定讀者閱讀活動的形態,又制約了這些活動所產生的文本。”[26]
闡釋社群不是一個有形的群體,而是一個確保理解發生的制度化結構,是特定文化圈層的成員在意義交流中所積累的闡釋慣例、標準和規則。依照費什之見,在具體的闡釋活動中,讀者看似隨心所欲地制造意義,但事實上其一舉一動都在闡釋社群的支配之下,甚至可以說,讀者就類似于一個“中介”或“轉換器”,他們以貌似個性化的行為,將群體性的闡釋慣例付諸實踐,建構起“一個合乎慣例的,在慣例意義上被理解的對象”[27]。聯系閱讀經驗,費什的觀點不難找到印證。面對同一部《人生》,感情敏銳的女性從中讀出愛情的脆弱和速朽;向往大城市的青年從中讀出改變社會境遇的艱辛;而更富人生閱歷者,或許會從中讀出不同價值觀之間難以彌合的鴻溝。這些解讀與其說是個體讀者的“原創”,不如說是闡釋社群成員在某些規則或慣例的引導下“達成默契”的結果。
應該說,闡釋社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學闡釋的實質。闡釋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社會實踐,其根基不在于闡釋者的自主行為,而在于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復雜交互作用。因此,個體固然擁有建構意義的權利,但終究要接受某種群體性法則的規約;相反,倘若讀者一味自由發揮,而無法獲得共同體的普遍認可,那么,其闡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勢必大打折扣。更進一步,闡釋社群還有助于提供一種視域,使我們能夠對闡釋的主觀性和客觀性加以調和。按照費什的構想,意義一方面來源于讀者的發現或建構,帶有明顯的主觀性、私人性和個體性;另一方面,由于讀者總是活躍于闡釋社群內部,被隱含其中的慣例所限定,因此由讀者生成的意義又帶有明顯的客觀性、公共性和社會性。這樣,闡釋將擺脫“非此即彼”的窘迫,呈現出主客兩極“兼而有之”的狀態。用費什的話來說:
這些意義既不是主觀的,也不是客觀的,至少用那些在傳統框架內立論的人的話來說是如此:它們不是客觀的,因為它們始終是某種觀點的產物,而不是被簡單地“解讀出來”的;它們不是主觀的,因為這種觀點始終是社會性或制度性的。或者以同樣的方式推理,人們可以說這些意義既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它們是主觀的,因為它們內在于特定觀點之中,因而不是普遍性的;它們是客觀的,因為它們借以傳達的觀點是公共性和慣例性的,而不是個體性或獨一無二的。[28]
闡釋社群有助于實現闡釋的一致性和可通約性,但依然會暴露出不甚完滿的一面。原因很簡單,盡管闡釋社群可以遏止社群內部成員在釋義實踐中的分歧,但無法消除不同社群之間在意義問題上的競爭或沖突,甚至無法提供一個用于權衡取舍的相對明晰的標準。這樣,闡釋社群在建構確定性意義的同時,仍不免向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敞開大門。
總體上看,“意欲類型說”“文學能力說”“闡釋社群說”協同作用,構造了文學闡釋中慣例論的知識版圖。上述三種學說在奠定慣例論基礎的同時,也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發生器”,促使研究者圍繞著“意義與慣例”做出進一步的發揮。如趙毅衡將慣例引入符號學場域,對闡釋中的“無限衍義”(unlimited semiosis)問題予以反思。按照安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說法,無限衍義指闡釋者對文本意義的演繹沒有盡頭,“像水流一樣毫無約束地任意‘蔓延’”[29],從而造成文化相對主義的癥候。但趙毅衡篤信,艾柯所擔憂的情況不太可能真正發生。他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編碼者對其符號意義的延展程度有一個大致期待,相應地,解碼者也會盡量配合編碼者的期待,使釋義活動在某一個階段自然終止。③這樣,信息的“編碼”和“解碼”將達成——至少是暫時達成——一種動態的平衡,而平衡的出現則理應追溯至共同體成員基于某些慣例所產生的默契。上述觀點進一步彰顯了慣例在文學闡釋中的獨特作用。
五、從慣例到“交互主體性”
在文學闡釋場域,慣例意味著研究視角的調整與新變,尤其是在“作者意圖論”“文本中心論”和“讀者反應論”暴露出短板時,慣例的引入將為文本解讀帶來一些新的思路。慣例論的一個重要洞見在于有效平衡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在當代文論中的緊張。如前所述,慣例擁有復雜的多重特質,其與生俱來的發散性和變動性為闡釋者的主體性彰顯提供了空間;其根深蒂固的群體性和約定性,又使闡釋者的自由發揮始終有所保留而不會陷入言人人殊的混亂狀態。這就如有學者所言,在慣例的引導下,意義將變得像一個“柔韌的實體”(pliable entity),它似乎可以被隨意改變,但實際上處在由慣例所帶來的耐受性(durability)范圍之內,無法從結構意義上被徹底重塑。[30]對習慣于將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截然二分的人文學界,慣例暗示了一種新的兼容之道。慣例論的另一個重要洞見在于,將社會文化維度融入闡釋過程,使闡釋呈現出更具客觀性和實證性的姿態。眾所周知,對文本中確定性意義的探求始終困難重重,這是因為任何以科學、公允、恰切自居的闡釋實踐,其實都是對一個隱微難察的“他人之心”的揣測,都攜帶著程度不一的主觀色彩。理查德·帕爾默(Richard E. Palmer)坦言,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自以為窺見的歷史性意義,說到底依然“由當下的歷史境遇所構造”[31]。張隆溪直言不諱地指出,任何致力于重構文本原意的批評實踐,始終攜帶著“一種來自批評家的主觀性因素”[32],因而終將陷入尷尬的自我循環。面對上述困境,訴諸慣例將提供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基于慣例的視角我們不難發現,闡釋固然發端于主體的選擇和訴求,但又處于共同體成員所約定的疆界之內,在某些普遍的法則或慣例的支配下展開。這樣,闡釋將不完全是主體的精神操演,闡釋者也將獲得來自社會文化層面的參照與支撐,避免“以主觀意志推求客觀意義”的不可能性。
當然,對慣例的關注也存在著一些盲點或有待深究之處。首先,必須承認,闡釋者不僅是社會的一員,不僅是某一共同體的構成要素,同時也是一個擁有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主體。由此,我們便有必要追問,慣例在構造相對穩定的意義狀態的同時,是否會遮蔽闡釋者本應擁有的自主性和能動精神?或者反過來說,闡釋者在接受慣例之限定的同時,又是否保持著對慣例加以超越或突破的可能性?④顯然,上述問題將使闡釋與慣例的關系變得更為復雜。
其次,說到底,慣例是一種不斷分衍、蔓延、流變的經驗形態,或如塞爾所言,是“一張由知識、信仰、欲望編織而成的相當復雜的網絡”[33],它不存在一個明確的所指,似乎也很難被精確觀察與詳盡把握。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闡釋者將無法建構“任何能確定文本意義的非任意的慣例體系”[34],最終不得不退回對意義的主觀揣測。
再次,在強調慣例對文本意義的建構作用時,還有必要關注權力話語所產生的微妙影響。按照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觀點,權力并非可見的經濟資本或政治威權,而是一種隱性的話語形態,它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每一根毛細血管。[35]在文學闡釋中,權力表現為某種意義解讀的優先權,它決定了大多數人應該秉持何種態度,采取何種策略,對何種文本加以解讀,從中得出怎樣的答案。放眼文學批評場域,將《關雎》解讀為男歡女愛或“后妃之德”,將《紅樓夢》解讀為宮闈秘史或社會批判,將《安娜·卡列尼娜》解讀為傷風敗俗或人性解放,其實都不只是“闡釋社群”或“文學能力”問題,還涉及圍繞“話語權”所展開的激烈競爭。那么,慣例和權力在闡釋過程中將形成何種張力與糾葛?對此,還需要做出進一步的考察和辨析。
由此看來,慣例并非闡釋中不容置疑的主導,它和作者、文本、讀者、語境等因素處于同等地位,以不同方式表現各自的獨特性,從不同向度豐富文學闡釋的知識版圖。或許,我們需要從慣例論轉向一個更復雜的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過程,即促使包括慣例在內的諸多文學要素展開積極的對話、斡旋與協商,使意義不再由單一的理論話語所框限,而是作為“要素關系互動所產生的結構性或過程性的產物”[36],在多重動因的作用下釋放其難以化約的豐富潛能。當然,作為一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意義形態,交互主體性同樣不是無可商榷的。交互主體性如何發生,又如何對不同意義維度加以妥善安置?交互主體性在何種程度上是真實的存在而非闡釋者的主觀虛設?交互主體性是否將保持平等、融洽的狀態而不會走向一種新的闡釋的“獨白”?這些都是我們在后續研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六、結語
在當代文學理論中,慣例的獨特價值得到了頻繁討論。慣例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經驗形態,其作用在于為交流者提供相對穩定的框架,以促使共識或認同的形成。通過維特根斯坦的“意義即用法”和“生活形式”命題,以及丹托、迪基、貝克爾對“藝術界”的闡發,慣例逐漸由一種生活經驗步入意義場域。在文學闡釋中,慣例通過“意欲類型說”“文學能力說”及“闡釋社群說”而得以集中表現,它一方面為闡釋者保留了能動解讀的權利,另一方面又使闡釋者的解讀始終受制于隱性的意義規范,而不會陷入信馬由韁、無所節制的狀態。因此,慣例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闡釋之特殊性和普遍性、主觀性和客觀性、差異性和同一性的兼容。當然,慣例并非彰顯唯一合法性而吞噬一切差異性的意義權威,在慣例之中,同樣充斥著大量的盲點和懸而未決之處,它們形成了一個“召喚結構”,吁請人文學者投身其中,就慣例這一當代文論的關鍵命題展開更具批判性的反思。
注釋:
① 大衛.劉易斯(David Lewis)對此深有體會。在他看來,慣例意味著一致的協議,但我們從來沒有和任何人簽訂契約,以表示要一以貫之地遵守這些協議。參見:David Lewis. Convention:A Philosophical Study[M]. Oxford:Blackwell,2002:2.
② 慣例還常常讓我們想到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名的“慣習”(habitus)命題。應該說,兩個范疇都表現出一定的延續性和規約性,作為某種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或情感方式為人們所擁有,但二者又有著顯著區別。在布爾迪厄看來,慣習是基于物質條件和經濟資本所形成的“習性”(包括稟性、格調、做派、品味、生活方式等),這些習性表征著某一群體的階級定位或身份訴求,使之在社會結構中居有相應的位置。慣例則是一個相對中性的概念,它更多指人們在歷史發展和文化積淀中分有的一套關于“如何生活”“如何行動”“如何理解”的參照,而較少表現出慣習所蘊含的階級區隔意味。關于慣習的更詳盡界說參見:Karl Maton.Habitus[C]//. Michael Grenfell(ed.). Pierre Bourdieu: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48-64.
③ 比如一種名叫“沙漠王子”的西瓜,它的名字會讓人想到有益于西瓜生長的沙漠;想到住在宮殿之中,不會遭受風吹日曬的王子;想到王子和公主的浪漫愛情;甚至想到圣·埃克蘇佩里筆下和飛行員在沙漠邂逅的外星小王子。但無論如何,這種意義的發散依然有一個大致的限度,而不會出現混亂或“失控”的局面。參見:趙毅衡.意圖定點:符號學文化研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J].文藝理論研究,2011(1):43-49.
④ 如余虹便就此發出過連珠炮式的追問:“讀者個人真的只是一個輸送群體規則的‘通道’嗎?他只能被動地服從規則而對規則無所作為嗎?或者,在閱讀活動中,讀者個體對群體規則不能進行自由反思和批判改造嗎?還有,是否所有的文本都能順利進入既有規則造就的讀者‘通道’,還是有的文本拒絕進入這一通道并激發了讀者打破這一通道而重建規則本身?”參見:余虹.文學知識學——余虹文存[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