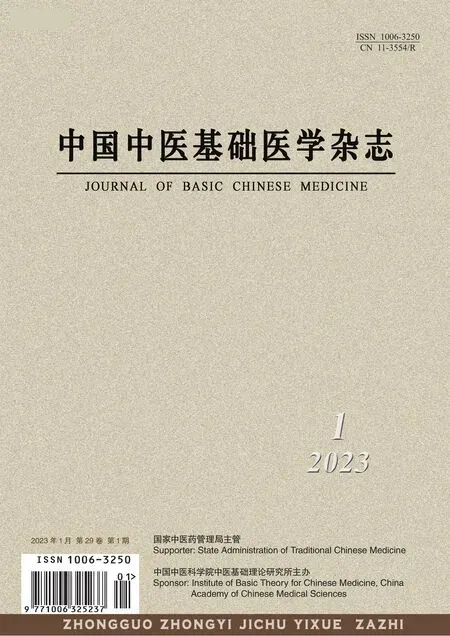王勛《慈航集三元普濟方》治疫思想鉤玄?
孫 暢,王利鋒,蘇 穎,徐方易
(長春中醫藥大學,長春 130117)
《慈航集三元普濟方》(下稱《慈航集》)為清代醫家王勛所著。王勛,字于圣,清代嘉慶年間人[1],自幼苦研醫書,熟諳《黃帝內經》《本草綱目》《脈經》等醫籍,認為“惟春溫、瘟疫,自古至今無成法可師”[2],故結合其臨證經驗,撰成《慈航集》一書。《慈航集》全書共四卷,卷一卷二主論春溫、瘟疫,卷三卷四主論瘧疾、痢疾,詳細闡述了春溫、瘟疫、瘧疾、痢疾等疫病的病因、治法及方藥。王勛尤重五運六氣,認為“人能明司天運氣,臟腑經絡,用藥合癥,方無錯誤”[2]2,基于五運六氣理論,提出春溫、瘟疫的治療方法與預防原則,首次提出六十甲子春邪時感方、六十甲子司天運氣施送正氣丸方、病愈后調理方等瘟疫用方,對現代傳染病及外感流行性疾病的防治與瘥后調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現將其治疫思想概述如下。
1 春溫之病多感風寒
王勛認為春溫發病皆因感受六氣中的風寒二氣而起。六氣包括風、熱、火、濕、燥、寒,是6種正常的氣候變化[3]。六氣氣化與人體生命活動密切相關,當六氣異常變化為六淫時就會導致疾病甚至瘟疫的發生。根據其30余年的臨證經驗,指出“病之總因,由貪涼、受寒、停滯觸其外邪而起”[2]40,將春溫的病因歸納為人體感受風寒二氣而發病。《慈航集》云:“六氣之感初,總由風寒而起,燥、火二氣亦由風寒所伏”[2]55,王勛認為六氣中風、寒、暑、濕四氣都為陰邪,感受此四氣所發病證皆為陰證,故宜以溫劑治之,而燥火二氣雖為熱邪,但春溫的發生多因感受風寒二氣,故治之宜先溫散風寒之邪,而后清燥火。故《慈航集》有“四氣之感,皆系陰邪,并非火癥”[2]2“燥、火二氣,雖系熱邪,初病總因受寒而起”[2]2之言,如甲子年為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云:“凡此少陰司天之政……寒交暑,熱加燥”[4],王勛認為此年發生春溫“雖系火燥之年,總由受寒邪而起”[2]3。《慈航集》有云:“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之感,皆系暴病標癥”[2]2“見治時邪標病,初病太陽、陽明,頭痛、惡寒、發燒”[2]2,由此可見春溫發病的癥狀表現多見惡寒、發燒等表證,且發病急切來勢兇險。王勛所論春溫“總因風寒而起”的觀點,對后世防治春溫及其他相關外感流行性疾病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
2 三虛相合易致瘟疫
王勛指出除異常氣候變化可導致瘟疫的發生,人體正氣不足亦可影響瘟疫的發生,其指出的瘟疫受病病因與《黃帝內經》所論“三虛相合”易發瘟疫不謀而合。《素問·本病論篇》云:“人氣不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聚……又遇驚而奪精,汗出于心,因而三虛”[4]398,“天虛而人虛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4]399,故三虛中人體正氣不足,缺乏抗病能力為一虛,自然氣候變化失常為二虛,在正氣不足及氣候異常的基礎上,又情志過激或飲食起居無節或外感等導致邪氣侵襲為三虛[5],三虛相合易致瘟疫。
王勛在《慈航集》中詳細論述了三虛相合致瘟疫,指出“惟貧苦閭閻受病最多”[2]38,貧苦百姓多為生活奔波,常粗茶淡飯且多勞力,故多正氣不足易感邪氣,此為一虛;“凡大瘟疫之年,或冬無雨雪,或夏多亢旱,污濁之氣上浮,無雨雪下降,一遇暴雨滂沱,污穢之氣,隨水泛溢,流入溝、渠、地、河,人渴飲之,蓄積于胃,因內受毒水;春夏之氣上升,皆不正之氣,從人口鼻而入”[2]38,因自然節律變化異常易導致不正之氣的產生,使人發病,此為二虛;“因為謀生,早起空腹出門,正不勝邪,邪乘虛入,故多受之”[2]38,“人空腹出門,瘴從口鼻而入”[2]88,強調因生活起居飲食無節而受不正之氣侵襲,此為三虛,故天虛、人虛、邪虛三虛相得則可導致瘟疫的發生。可見,異常的氣候變化是瘟疫發生的外在條件,而人體正氣充足與否是瘟疫發病的關鍵。
3 必先歲氣毋伐天和
王勛秉承五運六氣理論,認為“遵運氣之方,寒熱無偏勝,救人更多矣”,提出了各年用藥原則。《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4]307,歲運歲氣逐年變化,每年不同,因此組方用藥必須法歲而治,王勛根據歲運不同提出各年組方用藥原則,如甲己年歲運為土運,“土喜暖而惡寒,宜溫劑以助之”[2]1;乙庚年歲運為金運,“金喜清而惡燥,宜平劑以和之”[2]1;丙辛年歲運為水運,“水喜暖而惡寒,宜熱劑以溫之”[2]1;丁壬年歲運為木運,“木性寒怕燥喜疏,宜和劑以平之”[2]1;戊癸年歲運為火運,“火喜寒而惡熱,宜清劑以解之”[2]1,故用藥組方應視每年運氣特點而靈活變化。
王勛根據六十年不同的運氣特點,依司天、在泉立方,每年記錄一方,針對春溫首創“六十甲子春邪時感方”,以防疾病傳經之變,方中多以枳殼、草蔻仁、制半夏為主方,再根據當年的歲運、司天、在泉加入符合當年運氣特點的藥物,如厥陰風木司天加柴胡、赤芍,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司天加黃芩,太陰濕土司天加白術、茯苓,陽明燥金司天加檳榔,太陽寒水司天加桂枝、防風、羌活。以甲戌年為例,歲運為太宮,司天為太陽寒水,在泉為太陰濕土,為不和之年,故王勛認為該年“土上克水”,機體易出現的癥狀為“脾虛氣弱,濕聚不行,病多腫滿,氣急痰喘,四肢無力。春多時感氣虛畏寒,夏多暑濕,秋瘧脾寒”[2]8,治療時“初宜溫散汗解,解后補氣理脾,溫太陽膀胱之氣,分利陰陽”[2]8,王勛基于《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中太陽寒水司天之歲“歲宜苦以燥之溫之”[4]312的用藥法則,以白術、茯苓、枳殼、紫蘇、陳皮、桂枝、淡豆豉、制半夏、炙甘草組方,白術、枳殼、陳皮味苦以燥濕利水,理氣合營,紫蘇、桂枝性溫以發汗解表。

4 辨明表里慎用苦寒
王勛認為治療瘟疫在審察運氣的基礎上還應辨證論治,辨明表里寒熱,認為瘟疫病多在半表半里,若治瘟疫時先表后里或先里后表則多有傳經之變,導致病程纏綿,故其以內外同治的原則治療瘟疫。如《慈航集》云:“夫瘟者,疫氣也。治要解其疫毒之氣;半表半里者,內外分其邪滯之勢也”[2]38,遣方用藥上“初病蘇豉湯合平胃散,一服,外邪里滯俱解”[2]38“瘟疫正行,即用蘇豉湯、達原飲去黃芩、知母治之”[2]38,其組方中紫蘇、淡豆豉等辛溫解表以散外感之風寒,枳殼、厚樸、半夏、陳皮等運脾和胃以解內停之積滯,內外兩解分消表里之勢。王勛認為在辨明表里后施治用藥不可輕易用苦寒藥物,提出“若誤表誤里,誤用苦寒之藥,百無一生”[2]39。其論治瘟疫時強調“病之總因,由貪涼、受寒、停滯觸其外邪而起”[2]2,故治宜溫散寒邪,若用苦寒之藥則導致誤治,如治療春溫時“三陰假熱之癥,而用苦寒之藥,引賊入室,誤者甚多”[2]2;治療瘴瘧時認為“瘴乃陰邪”“治宜溫里寬中,消痰化滯,不可輕用苦寒,如誤投之,變癥難救”[2]88,治療久瘧時認為應以清淡調理、溫補和解為治療原則。
5 扶正祛邪瘥后防變
王勛治療瘟疫時扶正祛邪并重,認為不應一味地祛邪,固護正氣同樣重要,并提出“養正祛邪最為上工”的觀點。王勛指出正虛邪盛及正盛邪弱的治療方法,如《慈航集》云:“治瘟疫者,要明邪正之強弱,邪勝于正者,專固正而不攻邪,正旺而邪自遁矣;正氣勝而邪氣弱者,乘此強銳之氣,一鼓而掃除之”[2]39,故治療瘟疫時要明確邪正的強弱,邪勝于正者應以扶正為主,正勝于邪者則以祛邪為主,扶正與祛邪相輔相成,從而達到治療瘟疫的目的。
王勛在扶正祛邪的基礎上,尤其重視瘟疫的瘥后調理,以調節機體病后邪氣已祛而正氣未復,防止瘟疫復發。王勛在論春溫、瘟疫、瘧疾、痢疾的篇尾均附有愈后調理方,愈后調理亦遵循辨證論治,根據司天在泉、陰虛、陽虛、氣虛、脾虛、胎前等不同情況附愈后調理方,其中以五運六氣為基礎擬方為主,并根據司天在泉不同,列舉了子午歲、丑未歲、卯酉歲、辰戌歲、巳亥歲春溫病愈后調理方6首,春溫病愈后調理方在六十甲子春邪時感方的基礎方之上去紫蘇、淡豆豉等發表藥,加當歸、白芍、神曲等健脾益氣養血之品及與符合該年運氣的藥物,如寅申歲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以炒白芍、當歸、枳殼、炙甘草、炒柴胡、茯苓、陳皮、炒黃芩組方調理,黃芩為少陽本經藥清相火之郁除少陽痞熱,柴胡應風木升發疏相火之郁,配伍黃芩有升有降而推動氣機正常運行;辰戌歲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組方為焦白術、茯苓、枳殼、陳皮、神曲、白蔻仁、車前子,以老姜、紅棗為引,水泛土濕,濕寒傷陽,故應通陽燥濕,老姜溫中散寒燥斂,車前子利尿通淋,白術健脾燥濕滲土之濕邪,茯苓利水燥土,從而達到溫中健脾利濕之功。
王勛《慈航集》中愈后調理方還包括瘟疫愈后陰虛調理方、瘟疫愈后陽虛調理方、瘧后陽虛調理方、瘧后陰虛調理方、瘧后氣虛調理方、瘧后脾虛腹脹手足頭面浮腫調理方、胎前痢愈調理方等。陰虛調理方主要以鮮首烏、當歸、白芍為主,補益肝腎養血調血;陽虛調理方主要以人參、當歸、附子、菟絲子為主,溫補陽氣;氣虛調理方主要以人參、黃芪、當歸、白術、升麻為主,調補脾胃益氣升陽;脾虛調理方主要以白術、茯苓、薏苡仁、五谷蟲、冬瓜子為主,健脾利水滲濕;婦人胎前痢者血分先傷,故其治之以當歸、白芍、白術、枳殼為方,健脾益氣補血養血。王勛重視瘟疫的瘥后調理,為后世醫家對瘟疫的瘥后調理提供重要參考價值。
王勛《慈航集》基于五運六氣理論對瘟疫的防治及瘥后調理進行深入的挖掘與探討,創新遣方用藥,救瘟疫于未行之先,對現代傳染病及外感流行性疾病的防治與瘥后調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