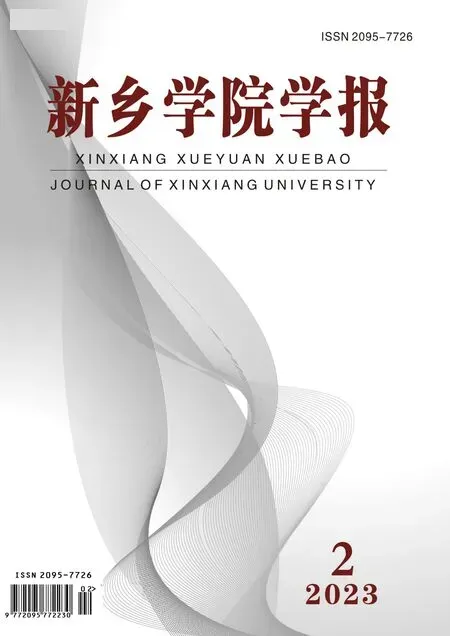歐陽修的園藝詩探究
李曉騰
(中國藝術研究院 戲劇戲曲學系,北京 100020)
歐陽修熱衷于園藝,其所著《洛陽牡丹記》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牡丹研究專書。他親自參與園藝種植和設計,所親手種植的花木不計其數,如《伐樹記》中言:“署之東園,久茀不治。修至,始辟之,糞瘠溉枯,為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1]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載:“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2]今日猶存歐公手種梅樹一株,位于安徽省瑯琊山景區醉翁亭西側。在歐陽修的詩歌作品中,園藝詩也是重要一類。園藝詩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詠物詩,其所吟詠之物都是園林中的實物,能夠反映作者的園藝思想。歐陽修的園藝詩共計109首,具體可分為游賞、實踐、品鑒、酬贈四類。其中,游賞類主要是歐陽修游園、游亭或訪客時所作的題留之詩;實踐類記錄了歐陽修親自參與的廣義的園藝活動,包括種植、采摘、插花、品果、清貢等;品鑒類側重于對園林景觀、植物造型的欣賞和感悟;酬贈類則記錄了歐陽修與友人之間相互贈送花草樹木的獨特經歷。在這109首園藝詩中,只有兩首創作年代不詳,其余皆有確定的創作時間或時間范圍。慶歷五年至皇祐二年是園藝詩的創作高峰,有詩38首,超過總量的三分之一,這與歐陽修先后知滁州、揚州、潁州的時間大致吻合。這些詩歌所涉及的園藝植物種類十分豐富,花木類居多,樹木類次之,另有瓜果類、水生植物類等。關于菊、荷、竹的詩作最多,分別為9首、9首、8首。另外,歐陽修對柳、松柏、牡丹、楠木、石榴等也都頗為喜愛。
一、園藝詩歌中的個人逸趣
歐陽修躬親參與園藝種植,并將其視為日常生活的閑情逸趣和心理寄托。這一點在滁州時期體現得尤為明顯。歐公于慶歷五至七年知滁,建豐樂亭、醉翁亭,在旁廣植樹木花草,使其面貌煥然一新。皇祐二年,歐陽修在《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詩中寫道:“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花勤。”可見其對滁州的深切感情。在這一時期,有眾多圍繞“幽谷”的園藝詩歌值得注意。歐陽修于慶歷六年發現滁州幽谷,并對其進行園藝改造。“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于泉側……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3]。現將歐陽修描寫在幽谷從事園藝種植活動的9首詩歌進行展示,如表1所示。
從表1所列詩中可知,歐陽修十分積極地對幽谷景觀進行園藝改造,除造亭外,還沿泉進行花木種植。園藝種植是一項典型的文人休閑活動,它體現了士大夫隱居樂道的情懷與追求,與儒家建功立業的思想有著一定的矛盾張力。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詩句,全然表露歸隱之心。然而,歐陽修醉心于園藝,其價值卻并非借田園以避塵囂,而是在于探索官場功名與個人休閑之間的平衡關系。如下面這首《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表1 歐陽修“幽谷”詩9首展示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枝。人生此事尚難必,況欲功名書鼎彝。深紅淺紫看雖好,顏色不奈東風吹。緋桃一樹獨后發,意若待我留芳菲。清香嫩蕊含不吐,日日怪我來何遲。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群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眾艷隨。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盛開比落猶數日,清尊尚可三四攜。
此詩以種花經歷蘊人生之思。歐陽修并未表達歸隱之志,而是將園藝生活視為官場之外的閑情寄托,委婉表達俗務、公務纏身的糾結無奈。這也側面說明了歐陽修在北宋政壇擁有相對重要的政治地位,肩負士大夫的使命與責任,以及儒家“修齊治平”的政治抱負。當對于功名的正當追求與充滿吸引力的田園生活發生沖突時,便有了“意若待我留芳菲”“日日怪我何來遲”的動人感慨。同時,由于日常事務繁雜而使人疲憊,從事園藝活動就自然成為調節生活的重要方式,能夠讓人心得到充分的放松與休養。
除了親自參與園藝種植與設計之外,歐陽修亦喜好游園,并即物抒發所感。如《竹間亭》的“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斟。興盡即言返,重來期抱琴”,“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深得歸隱之趣。再如《留題鎮陽潭園》的“謂言花縱落,滿地猶可席。不來才幾時,人事已非昔”抒發了客居之懷,《春日獨游上林院后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圣俞仍酬遞中見寄之什》的“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感慨時光流逝,《初晴獨游東山寺五言六韻》的“自憐多病客,來探欲開花”則表現了病中的幽思。從這些園林游賞詩的即物比興,可以窺見歐公的日常生活狀態。
二、園藝詩歌中的文人交游
朱熹《論語集注》釋孔子“游于藝”言:“游者,玩物適情之謂。”[4]張法在《中國美學史》中亦云:“把握‘玩’是理解宋代藝術的一個關鍵。”[5]“玩物適情”正是宋人熱衷園藝的內在思想原因。而園藝活動作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成了文人交游的流行方式,伴隨以志同道合者的情感表達。歐陽修此類詩歌的數量較多,題材也相對廣泛,可具體分為共植、互游、酬贈三種類型。
共植即文人共同參與園藝種植。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此類詩歌通常不是友人之間共植的實時記錄,而是與友人分別后的回憶與感慨。如 《寄劉都官》:“別后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繞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再如《送謝中舍二首》:“滁南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遺老說,世人今作畫圖夸。”歐陽修與謝縝先后至滁州,對幽谷共同進行了園藝改造活動,這是歐陽修頗為珍惜的一段回憶。以上詩歌表明,在歐陽修心中,與友人一同種植花木是非常愉悅的,這是友情和共同審美追求的美好見證,故而在思念對方時,共植的經歷會第一時間涌上心頭,進入詩歌作品中。
互游指文人互相拜訪對方的居所、園庭,并用詩歌記錄所見所感。這些詩歌反映了宋代園林中常見的植物種類,且通過對園林景觀的描述與評析,體現出歐陽修的園藝審美特征。如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埼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歐陽修在主人不知道的情況下拜訪其居所,詩中園林花木、池塘相掩映,具有清幽淡雅的風格,且白天、夜晚的景觀各有其趣。再如《早夏政工部園池》:“蘭香才馥徑,柳暗欲翻溝。夏木繁堪結,春蹊翠已稠。”園林中的景致豐富多樣,設計搭配有鮮明的層次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與梅堯臣之間的一組應和詩。歐陽修拜訪梅堯臣,見其家中菊花盛開,九日后,花叢枯萎,甚為感慨,便寫下一首《會飲圣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圣從》: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階前兩叢菊。愛之欲繞行百匝,庭下不能容我足。折花卻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猶馥。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階前猶對束。枯莖槁葉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綠。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欄敞華屋。奈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檐何局促。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葩無根長在目。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瓶臥墻曲。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顏不可恃,有酒當歡且相屬。
梅堯臣亦有《次韻和永叔飲余家詠枯菊》以為應和,從另一個角度記錄了同一事件[6]。兩首詩體現出二人的親密交往,到對方家中飲酒賞花是頻率極高的尋常之事,庭院里的菊花在數日間驟然枯萎,使得歐梅二公產生時光催人的無奈愁緒。不過,歐陽修將“朱顏不可待”的思考最終歸結到“有酒當歡且相屬”的瀟灑飄逸之境,賦予了休閑活動惜取當下、及時行樂的人生哲理。
酬贈詩在歐陽修的園藝詩歌中共有12首,涉及品種有松桂、牡丹、蓮花等移栽花木,海棠、櫻桃等游賞所折花枝,甚至連棗、銀杏、茶等農作物,也屬于園藝品互贈的范圍。歐陽修特意指出,這些酬贈之物“物賤以人貴”(《梅圣俞寄銀杏》),贈送禮物非以名貴、恒久為旨,而以求新、求雅為意。有些詩體現作者對所贈對象氣質品德的寓托,如“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云去無跡”(《送龍茶與許道人》),“子誠懷美材,但未遭良工”(《青松贈林子》);有些詩表達對花木的純粹喜愛,如“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為懷山中趣,愛此巖下綠”(《謝人寄雙桂樹子》);有些詩表達人世感慨,如“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答呂太博賞雙蓮》),“爭夸朱顏事年少,肯慰白發將花插”(《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這些酬贈詩以“玩”的悠游心態面對日常事物,闡發性理之趣,反映出宋代文人精神氣象、交往方式的雅致可觀。
有學者指出,宋代“文人的住居在整體格局的設計中體現出強烈的園林化傾向”[7]。歐陽修這些記錄文人交游的園藝詩歌恰恰體現了這一點。同時從詩中可見,歐陽修及許多北宋文人都將審美、生活與哲思熔于一爐,鍛造出別致而充滿意趣的士大夫生活。
三、園藝詩歌中的審美傾向
歐陽修的園藝詩歌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包含著他慧眼獨具的審美傾向。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歐陽修非常講究色彩、空間的運用與搭配。其一,園藝景觀的色彩要豐富和諧,如“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后仍須次第栽”(《謝判官幽谷種花》),“晴林紫榴坼,霜日紅梨曬”(《秋晚凝翠亭》),“姚黃魏紅腰帶鞓,潑墨齊頭藏綠葉”(《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其二,空間布局要整齊有序、相互掩映,有高低錯落之美。如“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錦窠”(《木芙蓉》),以蜀錦喻排列有序之華美;“曲欄高柳拂層檐,卻憶初栽映碧潭”(《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柳植于曲欄內,與重重屋檐相映成趣;“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興”(《新開棋軒呈元珍表臣》),指出竹要種于窗外,透過窗紗傳遞幽興。其三,歐陽修注重使用“借景”手法,主張園藝景觀要與自然環境相協調,有山、有水、有石,增加園林的和諧性和趣味性。如“朱欄綠竹相掩映,選致佳處當南軒。南軒旁列千萬峰,曾未有此奇嶙峋”(《菱溪大石》),“滁南幽谷抱千峰,高下山花遠近紅”(《憶滁州幽谷》),“生長飲泉甘,蔭泉栽美木”(《幽谷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園藝審美觀念有一個基礎要求,即可供選擇與搭配的植物種類應盡量豐富。因此,時人廣集花木,使用移栽、扦插等方式增加園藝品類,如《謝人寄雙桂樹子》:“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和圣俞李侯家鴨腳子》:“致遠有馀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這些例子,也側面反映了宋代種植技術的進步,以至于“園林相映花百種”(《送徐生之澠池》),“京師花木類多奇”“園林處處鎖芳菲”(《和陸子履再游城西李園》)。歐陽修在《洛陽牡丹記》中也說:“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為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8]可以反映當時的園藝植物更新迅速、種類繁多。
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說,歐陽修認為園藝活動要貫穿以哲思理趣,其中,“比德”與“生生”是最鮮明的兩種思想意識。“比德于物”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禮記·聘義》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9]《周易》卦辭也通過物象來比喻人世百態。宋人重于格物,對“比德”思想具有完善的繼承。歐陽修的園藝思想對這一點頗有心得,他認為,園藝種植對象要有一定的選擇性,展現個人品位與精神追求。如 “竹色君子德,猗猗寒更綠”(《刑部看竹效孟郊體》),“植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送朱生》),“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誚”“種花勿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毋栽當暑槿,寧種深秋菊”(《寄題劉著作羲叟家園效圣俞體》)。歐陽修不僅以植物的外在美感作為審美對象,也細致觀察植物形態及生長規律,將其總結為不同的德性、品質,并把個人的傾向與思考灌注其中。如《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不向芳菲趁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蔥。”《雙井茶》:“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寄題劉著作羲叟家園效圣俞體》:“菊死抱枯枝,槿艷隨昏旭。”與“比德”相關的另外一種思想是“生生”。《周易·系辭》云,“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至北宋,文人十分注重“感物道情”——在生活踐履中感受萬事萬物的內在規律。天地生物,人要對天地育化一切的德性有所理解和參贊。其中,“生”要被銘記和感恩,“亡”亦是“生”的一部分,需要被同樣尊重和欣賞。因此,歐陽修在詩歌中指出,“殘芳爛漫看更好”(《鎮陽殘杏》),“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眾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落續一開”(《歸雁亭》),“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物理固如此,去來知奈何”(《折刑部海棠戲贈圣俞二首》其二)。花開花落皆是無法更改的客觀規律,皆有意趣待人細品,對事物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可以抱有一種審美的態度,這便是歐陽修對于“生生之德”的深刻感悟。
揚之水曾言:“廳堂、水榭、書齋、松下竹間,宋人畫筆下的一個小爐,幾縷輕煙,非如后世多少把它作為風雅的點綴,而本是保持著一種生活情趣。”[10]歐陽修的園藝詩歌正有此妙處。這些清新平易的園藝詩歌,表達出愛物、惜物、體物、格物的生活態度,可視為宋人生活藝術化、詩歌生活化的重要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