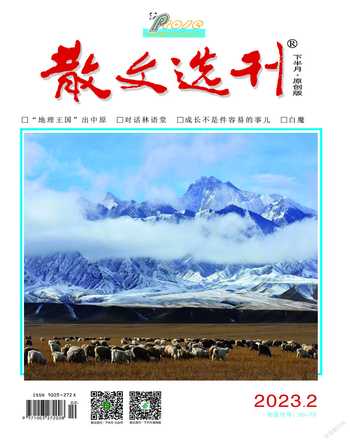白魔
白麗君

父親在山西岢嵐縣工作的時候,母親作為隨軍家屬跟著。那年,我虛歲六歲,隔一年才上學;哥哥三年級,比我大三歲;弟弟比我小三歲,也還沒上學。我們當時跟老娘(河北獲鹿縣方言,即外婆)在母親的老家河北獲鹿縣一起生活。每逢哥哥放寒假,老娘就會帶著我們兄妹仨去岢嵐尋我們的父母團聚。
那年臘月,黃昏,我老娘憐惜我們一年到頭見不著父母,怕以后跟父母不親,才專門來帶我們見見。現在好不容易見著了他們倆,下班也不陪著父母說說話,我們就跑出去找小伙伴玩,害得老娘在我們身后操著獲鹿話責罵:“跑什么,搶死啊?”罵歸罵,父母在身邊的歲月,老娘總是縱容的,父母也縱容,畢竟一年到頭見面就這些天,我們也就不怕他們訓斥,一溜煙跑出去,到家屬院的院子里與五子他們會合。
家屬院在路西,橫穿過那條大門口細瘦不規矩的南北柏油馬路,就到了對面的一家機關大院。大門口的這條路,冷冷清清的,屬于岢嵐縣的一條主街道,公檢法等主要政府部門都坐落在這條街上。我們到達的時候,這個平時屬于辦事部門的機關院子也非常安靜,大人們早已下班回家去了,沒個人影。滿院子躺著枯黃的落葉,有三排灰磚瓦房坐北朝南,每排房前種著幾棵排列整齊的大楊樹,樹上的葉子所剩無幾,幾乎光禿禿。
我們凍得鼻涕直流,風打在臉上,像刀片劃了一條口子生疼。我穿著老娘給做的沒有外褲外褂的棉褲棉襖,腳上穿著的也是我老娘給做的布底黑條絨棉靴頭,露著腳脖子,揣著手還凍得直打哆嗦,不時地用袖口抹一下鼻涕;花菊也縮縮的,把腦袋縮進衣服里,看不見脖子。但花菊穿的大紅芍藥花棉襖看起來很喜慶,給這院子增添了一點色彩,讓我覺得出來玩也好。我們試圖玩捉迷藏,五子喊了一聲“看誰先藏起來”。其他男孩子們唰一下就散開了,向院子深處跑去;我扯著花菊猶豫了寸刻,向后轉身,試圖藏在大門口左側煙囪處。然而,灰磚砌的四棱見角的高聳的煙囪下,突然站起來一個丈高的怪物,全身雪白,毛茸茸有頭有身軀,胡須也是白的,頭上有煙藍色的冠沿。它似乎蠕動著,在向我們走來。我努力看,但看不清眉眼和嘴鼻。花菊見我突然愣了,也順著我的眼睛看見了,大叫了一聲:“鬼……”藏起來的那幾個也聽見花菊的叫聲,哧溜哧溜地也都跑出來,以為發生了什么事,結果也看到了。五子的聲音像變了調門,如同刀劈開了聲帶,失了聲音一般張大了嘴,我也跟著花菊喊了一聲:“鬼——”便撒丫子就跑。一邊奔跑,一邊回頭看,怕怪物跟過來。
第二天吃過早飯,父親去上班,母親讓哥哥和我去抬水。我倆心里忐忑著,又不敢和大人說前一晚所見,就一前一后磨了半天出了門。我走在前面,用一根不算直溜的棍子抬著水桶,哥哥在后面。我們住的家屬院的大門對面就是看見怪物的那個機關大院,一出家門不幾步,快到家屬院大門口,我們兄妹倆相視一看,我頭發仿佛立起來,因為哥哥明顯看起來也很害怕的樣子。我說我怕,接著我哥也說:“昨天看見的東西嚇死我了……”
很快上班的人多了,清晨的這條街,有了些活氣。我們兄妹倆向南走,水桶一步一咣當,走兩步水桶就出溜到我這頭,我哥便伸手把桶向他那邊拉過去。
路過副食品商店時,哥哥讓我看著水桶,他要進去看看橘子糖。爸爸有時下班會給我們帶回幾塊,也許就在這店里。我把木棍子橫放在水桶上,坐在上面,歪著頭看著哥哥進去了,也想跟著,心里毛毛的。商店里亮著昏暗的燭光,煙氣騰騰,剛生著的炭爐子,從爐子蓋的縫里還滋著煙。哥哥順著玻璃柜臺走了一圈,我都替他為難,因為我知道他沒有錢。扎著兩條辮子揣著棉袖筒的售貨員問:“你買什么?”哥哥說:“我妹妹想吃橘子糖。”貨員說:“你買幾塊?”哥哥說:“我沒錢。”售貨員就從自己兜里掏出一分錢,放在柜臺后面的錢匣子里,拿了一塊橘子糖給了我哥哥。隔著門,我聽見哥哥說:“等我有了錢還給你。”接著我就看見哥哥拿著橘子糖出了副食品商店。
隨后,哥哥把糖果給我,我迫不及待就嘬起來。但挑了水返回,經過那家機關大院的時候,還會不由自主地向大院張望,擔心那怪物會突然跳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