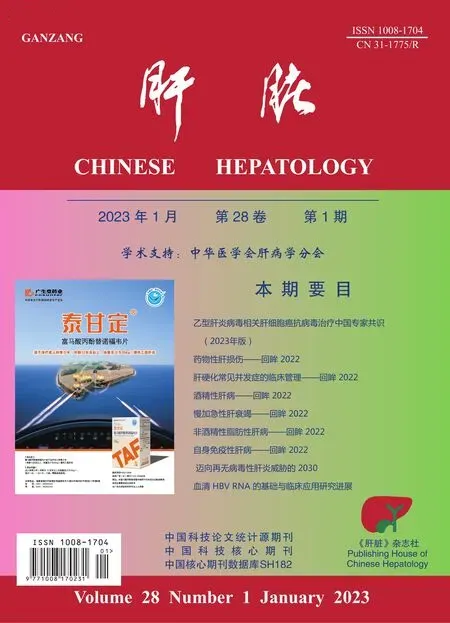肝硬化心肌病發病機制與臨床相關性研究現況
陳欣 陳琳
CCM的特征是潛在的心臟收縮和舒張功能障礙,以及心臟對不同應激表現出低反應性[1]。患者或是無明顯心功能不全的“亞臨床”表現,或是出現了活動耐力下降、氣短等癥狀,但被歸因為原發肝病的進展,而忽略了對心臟的關注[2]。當面對感染、出血等應激情況或進行經頸靜脈肝內門體分流術(TIPS)、肝移植等時,由于血流動力學的快速變化,會對心血管系統造成挑戰,增加死亡風險[3]。近年來有不少研究從CCM的發病機制、診斷標準到臨床相關性進行了討論,本文一并對以上內容進行概述。
一、發病機制
(一)高動力循環狀態 肝硬化患者心臟前負荷是降低的[4]。在CCM時由于門靜脈高壓及全身炎癥反應,血管舒張因子釋放增加,內臟血管擴張,最終會出現中央循環血流減少而外周血流增多的高動力循環狀態[5]。因此CCM患者靜息時,心臟后負荷減少會部分補償前負荷的降低。但是門脈高壓加重、細菌移位發生或運動、應激時,高動力循環狀態加劇,心臟功能進一步惡化[6, 7]。
(二)β腎上腺素能系統 學者在早期動物模型中發現膽汁酸可直接作用于心肌細胞,改變膜流動性及β腎上腺素受體密度,引起心肌負性肌力的表現[8, 9]。學者考慮高動力循環狀態的存在,使兒茶酚胺持續升高,β腎上腺素能受體出現脫敏現象和功能障礙,心肌細胞表面β受體密度隨之下調[10]。這種β腎上腺素能系統的改變在近年研究中也得到了證實。Yu等[11]在經四氯化碳處理的CCM大鼠模型中發現β1受體蛋白的減少,同時Ma等[12]發現CCM患者中抗β1腎上腺素能受體抗體(抗β1AR)較非CCM組升高,且CCM組抗β1AR水平與左心室射血分數為負相關。這可能是引起腎上腺素能受體脫敏的原因之一,也提示抗β1AR或許可作為CCM潛在的診斷標志物。
(三)內源性大麻素系統 內源性大麻素系統(endocannabinoid system,ECS)中包括有大麻素-1(cannabinoid type 1,CB1)和大麻素-2(cannabinoid type 2,CB2)兩種主要受體參與生理信號傳導[13]。許多研究表明,CB1和CB2在對肝臟和心臟的多種病理生理過程中起著相反的作用。晚期肝硬化患者中,內源性大麻素激活CB1 為主的信號通路,增加了休克、心肌病等心血管事件風險,且有文獻證實通過CB1受體拮抗劑可以顯著減輕細胞死亡、改善炎癥,逆轉ECS對心臟收縮的抑制作用[14-16]。既往在肝損傷、心肌損傷的模型中已發現CB2通路的激活有抗纖維化、抗炎的作用[17, 18]。隨后Matyas等在肝纖維化小鼠模型中證實通過CB2受體激動劑的治療可改善心臟功能障礙[19]。因此以CB1受體拮抗劑或CB2受體激動劑的治療很可能為CCM患者在接受肝移植前提供新的治療思路。
(四)膠原蛋白代謝 膠原蛋白的代謝紊亂與心臟舒張功能障礙更為密切。既往研究中已在CCM大鼠模型中發現了心肌膠原纖維紊亂和心肌重構,且在炎癥反應時可加速心肌重構的發生[11, 20, 21]。早期在CCM的大鼠模型中發現的膠原蛋白代謝紊亂表現為心肌細胞中I型膠原增加,III型膠原減少[20]。同樣地,Signe Wiese的團隊在52例肝硬化患者中通過心臟核磁發現心肌細胞外間隙(extracellular volume,ECV)增加,并與肝臟ECV增加密切相關,考慮可能由肝臟病變引起了心肌纖維化[22]。隨后該團隊進一步證實肝臟、心臟ECV增加與膠原蛋白代謝紊亂之間存在相關性,這種關系在肝硬化晚期表現更為密切[23]。
(五)心肌細胞肌絲和細胞內鈣瞬變 近期的研究中發現肌球蛋白重鏈亞型轉移和鈣瞬態振幅改變在CCM中起重要的作用。被稱為心臟“分子馬達”的肌球蛋白重鏈(myosin heavy chain,MHC)有α和β兩種亞型,α-MHC在正常心臟中起主要作用。在Honar等人構建的CCM大鼠模型中,發現β-MHC取代了α-MHC,同時在實驗組中發現心肌細胞的鈣瞬態振幅小于對照組[24]。此外,脂多糖已被證實可以通過降低心肌細胞中鈣瞬態振幅、細胞鈣儲存、降低線粒體細胞內膜電位,對心肌產生負性肌力作用[25]。同時腫瘤壞死因子也可通過改變心肌細胞的肌節長度和返回速度,影響心臟的舒張功能[26]。這種心肌細胞MHC亞型的轉移、肌節改變及細胞內鈣瞬變、鈣儲存的異常可能解釋了CCM時心肌對刺激產生的鈍性反應。
總之,CCM的作用機制十分復雜。從宏觀上涉及血流動力學的改變、炎癥反應狀態、β腎上腺素能受體下調;微觀上涉及細胞信號通路的調節,心肌細胞肌絲、肌節改變及胞內鈣轉運動力學異常,全面闡明CCM的發生機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二、診斷標準的更新
由于CCM的“隱匿性”或“亞臨床性”,臨床醫生依靠常規心臟超聲參數進行診斷是很局限的。第一次提出CCM的診斷標準是在2005年蒙特利爾胃腸肝病大會上(表1),直到2019年學者們才根據現代技術對心室功能的新解讀而更新了CCM的診斷標準[27](表2)。

表1 世界胃腸病標準大會(2005年)

表2 肝硬化心肌病聯盟提出的標準(2019年)
肝硬化患者由于使用β受體阻滯劑,且血管舒張狀態引起心臟后負荷降低后會直接影響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使其正常甚至增加[27]。因此2019年共識中加入整體縱向應變(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來評估LVEF保留的肝硬化患者心肌收縮能力[28]。此外,2005年標準中選用的評定舒張功能的指標易受容量負荷的影響,不太適用于常規需要利尿、腹水引流等治療的肝硬化患者[29]。因此依據現代技術對心室舒張功能障礙的重新定義提出了CCM診斷的新參數,且更強調在靜息狀態下對心臟舒張能力的評估[27]。同時,在2019年標準中刪除了關于支持性診斷的內容,但學者們并未否認變時及變性反應能力、心肌質量以及血清生物標志物等指標的診斷潛能。
三、CCM的臨床相關性
在一項對141名肝移植患者隨訪研究中,學者發現CCM患者發生心血管事件(包括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的風險明顯增加[30]。在Me的研究中,反映心臟收縮功能的GLS過高或者過低都與肝移植病死率增加相關[31]。同樣地,Billey在對TIPS治療后的肝硬化患者隨訪中發現20%患者會由于心力衰竭而再次入院[32]。國內研究評估了23名失代償肝硬化患者在行TIPS術后心臟超聲指標改變,發現術后早期可出現容量負荷加重,心腔擴大等表現[33]。除了肝移植或TIPS術中對心血管系統有挑戰外,術后血管收縮藥、電解質改變、感染等都可能加重心臟負擔。因此有必要在診療前及診療后對肝硬化患者的心功能狀況進行充分評估。
此外,β受體阻滯劑(non-selective beta-blockers,NSBB)常用于降低肝硬化患者靜脈曲張出血的風險。在Alvarado 團隊[34]研究結果中,與代償期肝硬化患者相比,失代償患者應用NSBB藥物后心排血量下降更多,而門脈壓力降低卻更少。這種對心血管的不利影響超過了降低門脈壓力的益處,是否提示CCM患者使用NSBB類藥物將會面對更多心血管負擔。一般來說,NSBB類藥物是具有抗心肌重塑作用的,可用于除限制性心肌病以外的其他心肌病治療,但目前不清楚CCM屬于何種心肌病表型,未來尚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探討NSBB藥物是否會對CCM患者的預后產生不良影響。
四、小結與展望
CCM是肝硬化并發癥之一,但是目前臨床對其關注不足,這種心功能的潛在障礙,又會在其他并發癥或在有創操作、外科手術時進一步影響患者預后。目前尚無診斷的金標準,且2019年專家共識中提出的評估心功能的新參數也在臨床應用中受限。通過探索疾病的病理生理過程,可能會為今后新診斷手段的發現以及特異性治療方式提供新思路。同時,未來是否有可能提出易于臨床使用的肝硬化患者心功能評分系統,以幫助醫生在制定治療策略時充分評估治療的收益與并發心血管事件的風險。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