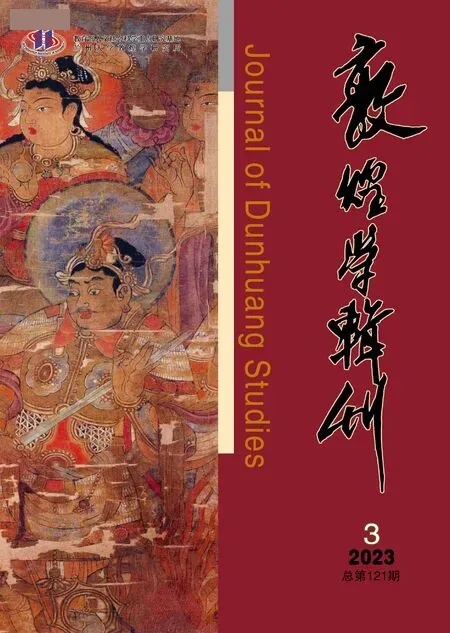汪宗翰與敦煌藏經洞文物的早期流散
陳雙印
(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
清末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隨著被譽為二十世紀初中國考古四大發現之一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偶然被發現,藏經洞文物外流也隨之開始。
《重修敦煌縣志》載,藏經洞發現后:“中藏經卷累累垛積,即時報知地方官。時縣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紳,大致翻閱一過,約數佛經二萬余卷。當時人亦不之重也,有攜回一二卷,亦有不攜回者。”(1)呂鐘修纂《重修敦煌縣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頁。總之,藏經洞文物被發現后的情形,正如王冀青所言:“實際上,自1900年藏經洞發現之初起,藏經洞文物便已經進入了四處流散的進程。”(2)王冀青《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頁。是不爭的事實。
“敦煌卷子最初的流傳,一般都以為是由于斯坦因的搜購,其實在他未到敦煌以前,這些卷子已經零星地傳布于世了。最初得到這些經卷和畫旌的,有葉昌熾、汪栗庵、恒介眉、張又履、張筱珊等人。”(3)蘇瑩輝《敦煌石室和敦煌千佛洞》,中國臺灣《“中央”日報》1965年3月31日(5)。以上蘇瑩輝所舉最早得到藏經洞經卷和畫旌的葉昌熾諸人,都是敦煌藏經洞文物發現之初,在甘肅任職的地方官員。這幾人當中,尤其是曾任敦煌知縣近四年之久的汪栗庵暨汪宗翰,因為近水樓臺的緣故,無疑是在斯坦因、伯希和等歐洲探險者成功盜買藏經洞文物,捆載西去之前,在甘肅地方官員當中,得到藏經洞文物數量最多的人物之一,并且因為藏經洞發現之初,一系列不負責任的行為和敷衍的封存,造成了洞內大量文物流散海外,汪宗翰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受葉昌熾之托搜集敦煌縣內碑拓簡牘等古物
汪宗翰,原名汪耀祖,“翰”一作“瀚”,字栗庵,湖北武昌府通山縣人。光緒己卯(1879)科舉人,庚寅(1890)恩科會試二甲第一百二十四名進士(4)朱鰲、宋苓珠《清代進士傳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第3冊,第1889頁。。中進士后先是被欽點主事簽分吏部,1893年授侍中,1896年調任甘肅鎮原知縣。此后便一直在甘肅做官,先后任鎮原縣令、華亭縣令、主管甘肅行省鄉試內簾考官,光緒二十八年(1902)農歷3月改任敦煌縣令。
1902年4月28日,汪宗翰從鄔緒棣手中接過知縣大印,成為新的敦煌縣令,直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二月九日卸任。汪宗翰擔任敦煌縣令近四年,不論是與其之前幾任陳問淦、嚴澤、吳緒棣,還是后來的黃萬春、王家彥相比,汪宗翰是任敦煌知縣時間最久的。
進士出身的汪宗翰,其文化水平自是不用懷疑的,關鍵是他還善詩文、懂金石、精通書法。汪宗翰曾為莫高窟千佛洞撰寫的楹帖:夏無酷暑冬不奇寒四季得中和景象,南倚雪山西連星海九州尋岳瀆根源,受到了曾擔任甘肅學政的著名金石學家、學者、藏書家,同樣是進士出身的葉昌熾“非俗吏之吐屬”(5)[清]葉昌熾著《緣督廬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第7冊,第4286頁。的較高評價。斯坦因“在著作中提到汪氏時,總是冠以‘有學者之風的’或‘博學的’一類形容詞”(6)金榮華著《敦煌文物外流關鍵人物探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第66頁。,可見其學識確實不賴。文人出身的汪宗翰,與一般俗吏不同之處,也從另一件事上表現出來,就是他更懂得歷史文化遺存對于彰顯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于是在光緒三十一年“刊立古陽關石碑,以志遺跡”(7)[清]佚名撰《敦煌縣鄉土志》卷2《歷代沿革·疆域》,甘肅省圖書館藏手抄本。,這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行為。
早在京城之時就曾得到過敦煌縣內石碑拓片的甘肅學政葉昌熾,托汪宗翰替其搜求敦煌轄境內的各類碑拓。葉氏不但是比汪宗翰早一年的進士,更是時任主管甘肅一省文教的學政,何況所請托搜集的碑拓,就在汪宗翰的轄境之內,汪知縣豈有不答應之理。汪知縣上任不久,就對葉氏的請托有了回報。葉昌熾在其所著《語石》里記載:“敦煌縣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丸泥,十余年前,土壁傾墮,豁然開朗,始顯于世。中藏碑版經象甚夥。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翰以名進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討,先后寄貽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畫象》,寫經卷子本、梵葉本各二,筆畫古拙,確為唐經生體,與東瀛海舶本無異。又諸墨拓中有斷碑僅存兩角。”(8)[清]葉昌熾著,姚文昌點校《語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0頁。
據《清史稿·職官志三·縣》載:“縣,知縣一人。正七品。……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都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9)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357頁。可見,作為一縣百姓父母官,知縣的權力是很大的,闔縣官民誰不巴結逢迎。
有文化修養,有收藏古物的喜好,又受人之托搜求碑拓之物,加之手中有權,汪知縣在敦煌縣境內搜求碑銘古物,可謂是如魚得水,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之便。
二、汪宗翰敦煌文物收藏品來源
早在汪宗翰出任敦煌縣令一年多以前的“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0)陳雙印《莫高窟王道士〈催募經款草丹〉再考》,《檔案》2022第9期,第32頁。有關藏經洞發現的時間,有1885年、1886年、1899年、1900年幾種說法,見王冀青《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第25-29頁。,藏經洞文物就已被偶然發現并開始外流(11)王冀青《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第25-29頁。。傳言王道士就曾送給時任敦煌縣令嚴澤一批藏經洞經卷,1900年12月7日卒于任上的嚴縣令,生前只“手存二卷”。由此看來王道士所贈經卷,嚴縣令“竟然沒看出手中經卷的歷史分量,根本沒當回事”(12)張翠萍《敦煌悲天》,《山西檔案》2001第6期,第33頁。,笑納的不是很多。繼任敦煌知縣的鄔緒棣,“似乎沒有收藏藏經洞文物的記錄”(13)王冀青《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第31頁。,但這并不能證明他手中沒有藏經洞文物,只是目前還沒有發現相關線索而已。
與前兩位不同的是,汪宗翰文學底子很好,懂得欣賞,自己收藏簡牘書畫等古物,又受葉氏請托搜求敦煌境內碑拓等。王道士結交這位同鄉知縣的得力之物,自然是藏經洞出土的佛經和絹畫等古物了。正如王冀青指出的,“汪宗翰和王圓祿是湖北同鄉,兩人多了一層關系,比較容易溝通。所以,王圓祿很快就將藏經洞發現之事告訴了汪宗翰,并不斷給汪宗翰選送藏經洞文物”(14)王冀青《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第32頁。。榮新江也指出:“他是王道士同鄉,所以王道士把一些很好的經卷和絹畫送給了他。”(15)榮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敦煌研究》2000第2期,第25頁。因此,汪宗翰手中的藏品來源之一,來自于王道士的多次饋贈。在汪宗翰長達近四年的任職時間里,王道士究竟贈送了多少藏經洞文物,已成為永遠無法搞清的謎,但是數量一定不少,這是毫無疑問的。
汪宗翰手中藏經洞藏品的另一來源,主要來自于敦煌地方官紳的饋贈。“王道士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但面對這么多古代的經本和畫卷,當然也知道它們的‘價值’。他不斷拿出一些書法精美的佛經寫卷和漂亮的絹畫,送給附近的官紳和過往的官僚士大夫們,以換取一些功德錢”(16)榮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第25頁。。因此,敦煌當地很多官紳手中或多或少都收藏有藏經洞文物。正如施萍婷所言:“自從藏經洞文物出土以后,至斯坦因、伯希和東來之前,王道士又是送給官府又是送給財主,‘自有不少流入達官貴人以及當地人士之手’(向達先生語)”(17)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廟寫本源自藏經洞》,《敦煌研究》1999第2期,第41頁。。而敦煌知縣汪宗翰,好古,又搜集碑拓簡牘繪畫等,“上好是物,下必有勝者矣”(18)[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禮記正義》卷55《緇衣第三十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576頁。,這就難免有人會投其所好。所以,汪宗翰的收藏,不排除其中的一部分來自于敦煌當地官紳的饋贈。
汪宗翰手中藏經洞藏品的第三個來源,應來自兩次莫高窟之行的拿取。第一次,徐珂《清稗類鈔》記載,壬寅(1902)許伯阮游敦煌,見“縣令某攜佛爐而去,又取經二百余卷”(19)[清]徐珂撰《清稗類鈔》第9冊《鑒賞類·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197頁。。王冀青指出許伯阮“提到的‘某縣令’,應指汪宗翰”(20)王冀青《藏經洞文物的發現與流散》,《文史知識》2016第16期,第16頁。。《重修敦煌縣志》收錄的《千佛洞古佛經發現記》一文記載,藏經洞發現后,王道士“即時報知地方官,時縣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紳,大致翻閱一過,約數佛經二萬余卷,當時人亦不之重也。有攜回一、二卷,也有不攜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為保存”(21)呂鐘修纂《重修敦煌縣志》,第40頁。。王冀青對此提出質疑并指出:若在藏經洞甫一發現的1900年即時報官,當時的敦煌知縣應是嚴澤,“汪宗翰是1902年四月才上任的,他第一次檢查藏經洞文物的時間,只能是上任后不久。但不管怎么說,這段記錄暗示,王圓祿在1902年肯定向汪宗翰報告過藏經洞之事。而第一個關注藏經洞發現之事,并對藏經洞文物進行全面檢查的敦煌縣知縣,還應該是汪宗翰”(22)王冀青《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第32頁。。另一次是光緒三十年(1904)汪宗翰負責檢點藏經洞時的順手牽羊(23)衛聚賢《敦煌石室》,《說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第65頁。。早期流散在外,后歸江西蔡氏收藏的一件藏經洞出土的《唐畫大士像》上,汪宗翰的親筆題識:“甘肅敦煌縣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畫大士像光緒卅年四月朔奉檄檢點經卷畫像畢迎歸署中供養信士敦煌知縣汪宗翰謹記”(24)汪宗翰的題識,系本文作者根據鄒安主編《藝術叢編1》第1至4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第345頁插圖上的文字釋讀。(圖1),證明衛聚賢因從王道士處取去若干寫經及畫像此說不誣,因此,借著檢點藏經洞文物的機會,以“迎歸署中供養”的名義,順手牽羊,汪宗翰又得了數量不少的藏經洞藏品。

圖1 汪宗翰藏《唐畫大士像》(采自鄒安主編《藝術叢編1》第1至4期,第345頁圖)
三、汪宗翰手中藏經洞文物知多少
汪宗翰在擔任敦煌知縣的近四年時間里,通過不斷接受王道士和敦煌地方官紳的饋贈,以及兩次檢點藏經洞文物時的肆意拿取,手中集聚了數量不少的藏經洞文物。
徐珂《清稗類鈔》一書中記錄:“壬寅,許伯阮游敦煌,得唐人手書藏經五卷,出而語人曰:‘石屋分內外,內屋因山而筑,有六十六穴,穴藏經四五卷,別無他物。外屋石床一,左鋪羊毛氈,尚完好,右鋪線氈,已成灰。床下僧履一雙,色深黃,白口,如新造者。中一幾甚大,金佛一尊,重約三百兩。金香爐大小各一,大者重百余兩,小者二三十兩。大石椅一,鋪極厚棕墊。縣令某攜佛爐而去,又取經二百余卷。后為大吏所知,遣員至敦煌,再啟石壁,盡取經卷而去。聞縣令取佛爐,悉熔為金條,以致唐代造像美術,未得流行于世,惜哉!’”(25)[清]徐珂撰《清稗類鈔》第9冊《鑒賞類·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第4198頁。
《清稗類鈔》中提到的許寶荃,字伯阮,為時任陜甘總督崧蕃幕僚。他在壬寅年(1902)游敦煌,親眼目睹“縣令某攜佛爐而去,又取經二百余卷”,許伯阮所說某縣令就是汪宗翰,他也得到了唐人手書藏經五卷。說明這次許伯阮游覽莫高窟千佛洞時有汪縣令陪同,僅汪宗翰一人,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從藏經洞拿走了數目驚人的200余卷經卷和佛爐等物。
《重修敦煌縣志》中“時縣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紳,大致翻閱一過,約數佛經二萬余卷”的記載,與《唐畫大士像》絹畫上汪宗翰的題識“甘肅敦煌縣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畫大士像光緒卅年四月朔奉檄檢點經卷畫像畢迎歸署中供養信士敦煌知縣汪宗翰謹記”,所述內容十分接近,故兩者所記應該指的是同一件事。依據《唐畫大士像》上的題識,汪宗翰檢點藏經洞的時間是光緒卅年四月朔日暨公歷1904年5月15日。汪宗翰此次莫高窟之行,究竟拿走了多少經卷和佛畫,我們已經沒法搞清。不過,《唐畫大士像》上的題識表明,汪知縣以“迎歸署中供養”的幌子,順手拿了一部分藏經洞文物卻是事實。
葉昌熾在壬寅年(1902)七月初二這一天的日記中寫到:“得敦煌令汪君宗翰第二函,穎芝蓮溪之友,以吏部改官作令,簽掣鎮原,調補邊缺,頗悒悒不得志。”(26)[清]葉昌熾著《緣督廬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第6冊,第3763頁。心情抑郁的汪宗翰到敦煌上任后,“欲通過葉昌熾改善自己‘悒悒不得志’的處境——‘調省’任事”(27)蔡副全《葉昌熾與敦煌文物補說》,《敦煌研究》2011第2期,第98頁。。衛聚賢指出:“葉昌熾(蘇州人,于民國二十五年左右病故)于光緒二十八年為甘肅學臺,對于古物亦好,托汪宗翰搜討。汪宗翰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象,寫經卷子本、梵頁本各二’送給葉昌熾了(見葉著語石卷一第二十九頁)。”(28)衛聚賢《敦煌石室》,《說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第67頁。從1902至1906年葉昌熾任甘肅學政期間,恰好也是汪宗翰任敦煌知縣的時間。汪宗翰除了數次寄信給葉昌熾外,還多次寄贈大量唐元石刻碑拓和敦煌經卷、佛畫。據蔡副全最新統計,汪宗翰只送給葉昌熾千佛洞藏經洞出土文物,就包括絹畫《水陸道場圖》《水月觀音象》各1副,《大般涅槃經》4卷,梵文寫經31葉等(29)汪宗翰所贈葉昌熾敦煌文物種類和數量,依據蔡副全發表在2011年第2期《敦煌研究》上的論文《葉昌熾與敦煌文物補說》中的數據統計得出,特此說明。。
羅振玉在《沙州石室文字記》里披露了一件汪宗翰送給同年陸季良的絹畫,“光緒戊申,同年陸季良示余甘肅敦煌縣令汪宗翰所遺后唐天成四年已丑歲五月廿九日樊宜信造《藥師琉璃光如來象》,絹本,長三尺許。筆意古拙,彩色鮮明。其所題記文皆右行,蓋千佛巖莫高窟物也”(30)羅振玉《沙州石室文字記》,羅振玉編纂《敦煌叢刊初集六·敦煌石室遺書百廿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341頁。。這件《藥師琉璃光如來像》絹畫,經榮新江考證,就是王惠民發表在《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日本白鶴美術館藏兩件敦煌絹畫》一文里介紹的第一件《藥師說法圖》(31)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8頁。。
在陜西省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考察中,發現了文物單位收藏的屬于藏經洞早期流散部分的21種敦煌寫經,根據題識可以辨認出其中的多數,是徐錫祺在1905年7月至1906年5月署任安肅道道臺時,為時任敦煌知縣汪宗翰贈送的精美長卷佛經。據王慶衛推測,汪宗翰任敦煌縣令時的送禮對象,除了葉昌熾、徐錫祺以外,應該還有在徐錫祺之前任安肅道道臺的和爾賡額、崇俊兩人。但他又引用王冀青的觀點,認為1904年在汪宗翰檢點藏經洞文物后,命令王道士將藏經洞文物封存并負責看守。王道士便在藏經洞門口安裝了一扇木門,加裝了鎖具,直至1907年斯坦因到來時一直如此。因此,從這種狀況來看,在1906年5月后署任安肅道道臺的崇俊基本沒有機會再從汪宗翰處得到敦煌寫卷(32)王慶衛《徐錫祺舊藏敦煌寫經簡述——以西安地區藏品為中心》,《敦煌研究》2019年第5期,第134-142頁。。其實汪宗翰早已通過接受王道士和敦煌官紳的饋贈以及檢點藏經洞文物時的恣意拿取,手中擁有了數量不少的藏經洞文物。藏經洞文物封不封存,都不會影響到汪宗翰用手中的藏品送禮。之所以沒有給崇俊贈送藏經洞文物的原因,是依據《重修敦煌縣志》記載,早在崇俊接任安肅道道臺的1906年5月之前的3月份(33)呂鐘修纂《重修敦煌縣志》,第40-42頁。,汪宗翰就已離開敦煌,調往省城蘭州任事了。
王冀青先生經過研究,認為:“可以推斷,汪宗翰為了同樣的目的,也應給其他‘大吏’或上級官員送過藏經洞文物。”(34)王冀青《藏經洞文物的發現與流散》,《文史知識》2016第16期,第17頁。從我們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可以確定汪宗翰僅在敦煌知縣任上,至少曾經給葉昌熾、陸季良、許寶荃、和爾賡額、徐錫祺等人贈送過藏經洞文物。不過,汪宗翰極有可能給何衍慶、侯葆文也有贈送。因為前者不但是1904年汪宗翰任敦煌知縣時的頂頭上司——安西直隸州知州,更是安肅道道臺和爾賡額派來敦煌復查采買糧事件(35)有關“敦煌采買糧事件”詳細情形,請參閱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與王圓祿及敦煌官員之間的交往》,《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3期,第60-76頁;郭勝利《敦煌抗糧事件與清末西北邊政之探討》,《中國邊疆學》2020年第2期,第163-186頁。的主官,而后者侯葆文是1905年10月至11月代表甘肅省府,被派往敦煌縣實地調查采買糧事件的主官。
邰惠莉轉引范耕球介紹自己收藏敦煌遺書的經過說:1947年春,在蘭州城隍廟附近范先生見一售賣敦煌寫經的人,“問是真的嗎?那人說:其祖父干過敦煌縣長,說這是寶物,叫子孫珍藏。……共購卅多卷。那人現才說,姓汪,祖上湖北人。其它不說”。后來,范耕球所購敦煌寫經,經馮國瑞、慕壽祺鑒定,確定為敦煌寫經,“出售經卷的汪姓年青人,自稱是1904年任敦煌知縣的汪宗翰的后人”(36)邰惠莉、范軍澍《蘭山范氏藏敦煌寫經目錄》,《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第80頁。。在藏經洞開啟四十多年后,范先生一人竟然就從那位自稱是汪宗翰后人的年青人手中,前后購得“卅多卷”,證明汪宗翰手中藏經洞藏品確實不少。
總之,汪宗翰手中究竟有多少藏經洞文物,具體數目已無從知曉。不過,從多次接受王道士和敦煌地方官紳饋贈,兩次從藏經洞拿取經卷,一次竟取走二百余卷經卷,一次不知具體數目,以及利用藏經洞文物饋贈多位上司和同年,其后人出賣藏經洞經卷數量十分龐大的事實判斷,汪宗翰手中擁有的藏經洞文物數量,一定不會少于數百卷!
四、誤報隱瞞,疏于管理,必須對早期藏經洞文物的大量外流負責
1.汪宗翰誤報瞞報藏經洞文物信息
王道士在藏經洞發現后,很快報知了時任敦煌縣令嚴澤,后來也應該報告了接任的吳緒棣,卻都沒有引起重視。傳言心有不甘的王道士,“私載經卷一箱至酒泉,獻于安肅道道臺滿人廷棟。廷棟不省,以為此經卷其書法乃出己下,無足重。王道士頗喪沮,棄之而去”(37)謝稚柳《敦煌石室記》,收入氏著《鑒余雜稿》,上海:上海美術出版社,1996年,第3頁;又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4頁。。而據王冀青考證,如果這件民間流傳的有關王道士赴肅州獻經一事屬實,“那這位道臺必定是和爾賡額,而不是廷棟”(38)王冀青《廷棟舊藏敦煌寫經入藏時間辨正》,《學習與探索》2008年第3期,第213頁;王冀青《關于敦煌寫本廷棟收藏品》,《敦煌學輯刊》2008第2期,第1-9頁。。不管如何,王道士辛苦奔波,其目的有邀功請賞之嫌外,無非就是希望官府知曉藏經洞藏品的事并接手管理。
1902年汪宗翰接任敦煌知縣,因為是湖北同鄉的緣故,易于交流,王道士也一定將藏經洞的消息報告了汪宗翰。也是在這一年,許伯阮游敦煌,親眼見汪宗翰從藏經洞拿走經卷二百余卷。不知為何,卻遲至癸卯(1903)十一月十二日,葉昌熾才收到汪宗翰贈送的唐元拓本和藏經洞出土的“絹色黯黕,丹黃陊剝,惟筆果出于俗工,尚不甚古,極早為明人之筆”,所繪系水陸道場圖的舊佛像一副,和“筆法遒古,確為唐經生派,紙色界畫與日本估舶者無毫厘之異”的《大般涅槃經》寫經四卷等(39)[清]葉昌熾著《緣督廬日記》,第7冊,第6285頁。。
有汪宗翰贈送的出自藏經洞的經卷畫像等實物,加上汪宗翰書信中對藏經洞以及洞內藏品的描述,葉昌熾“乃知唐人紙卷中,東同一流傳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盡。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剎,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門镕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幾石榻,榻上供藏經數百卷,即是物也”(40)[清]葉昌熾著《緣督廬日記》,第7冊,第6285頁。,可能才有了“建議藩臺衙門(甘肅省政府)將此古物運于省垣保存”(41)衛聚賢《敦煌石室》,《說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第89頁。的動議。事實絕非像任光宇引用《重修敦煌縣志》中“即時報知地方官,……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為保存”的記載,并說“這說明汪宗翰相當重視這個發現,在1902年內對藏經洞文物進行過初步核查。而且,其上司甘肅學政葉昌熾有日記證明,他很快就得到了汪氏的報告,并多次得到汪氏贈送的藏經洞珍貴文物”(42)任光宇《敦煌學術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與評議——兼論敦煌遺書發現人暨敦煌學的起始》,《唐都學刊》2021年第4期,第8頁。。不過葉昌熾可能因從汪宗翰的書信中得知,藏經洞內僅僅“榻上供藏經數百卷”,且石室打開之時,“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又見同僚“恒介眉都統,張又履、張筱珊所得皆不少”(43)[清]葉昌熾著《緣督廬日記》,第7冊,第2484-2485頁。,錯誤地估計可能藏經洞內所余經卷已不多,加之“估計運費要五六千兩,以運費無著,乃于光緒三十年三月下令敦煌縣長汪宗翰‘檢點經卷畫像’(原文云‘光緒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檢點經卷畫像,見藝術叢編第三冊’)乃為封存”(44)衛聚賢《敦煌石室》,《說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第66頁。,使得藏經洞文物失去了一次運往省城蘭州保存的絕佳機會。
如果說汪宗翰之前對藏經洞經卷數量的了解,只是出自王道士的一面之詞,尚好理解。可問題的關鍵是,壬寅年他陪許伯阮游敦煌,攜佛爐并取佛經二百余卷而去,肯定對洞內所藏經卷數量有了大概了解,為什么卻在給葉昌熾信中,依舊撒謊說藏經洞內僅有“藏經數百卷”,這就很有些令人費解了。
在甘肅省府要求檢點藏經洞經卷的檄文下至敦煌后,“時縣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紳,大致翻閱一過,約數佛經二萬余卷”(45)呂鐘修纂《重修敦煌縣志》,第40頁。。二萬余卷佛經,應是汪宗翰檢點藏經洞經卷后所得之數。但是,通檢從汪宗翰檢點藏經洞文物后的1904年農歷4月1日直至離任敦煌知縣的1906年農歷2月9日的近兩年時間內,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里的相關內容,反映出雖然其間兩人一直書信往來不斷,并且,為能盡快調離敦煌,汪宗翰不僅托人替自己在葉昌熾處說項,還數次附贈敦煌各地所出碑拓,其中有兩次附贈了藏經洞出土文物,但卻沒有只字片言談及二萬余卷經卷數量之事(46)通檢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第6、7、8、9、10、11、12冊中,凡涉及敦煌藏經洞文物的內容,卻沒有只字提及藏經洞有二萬余卷經卷。。這說明汪宗翰根本沒有將這一信息寫信告訴過葉昌熾,葉也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究竟。
1906年清政府廢黜科舉,學政改稱提學使,葉昌熾被免職,不久便離開甘肅,回了蘇州老家。被蒙在鼓里的葉昌熾,直至己酉年(1909)十月十六日才從張訚如口中獲知伯希和將石室大量寫經畫像捆載西去的消息,起初誤以為是敦煌莫高窟新開一石室中之物,表示惋惜的同時,還譴責了不知愛古的敦煌地方的俗吏邊甿和對汪宗翰“保護”石室所出之物的肯定。他在當天的日記里是如此描述的:“午后張訚如來言,敦煌又新開一石室,唐宋寫經畫象甚多,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載去,可惜也。俗吏邊甿,安知愛古,令人思汪栗庵。”(47)[清]葉昌熾著《緣督廬日記》,第10冊,第6284-6285頁。葉昌熾既說新開一石室,更證明其自始至終對藏經洞文物數量的不甚了了。
葉昌熾在其己酉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記里又寫道:“午后張訚如來,攜贈《鳴沙山石室秘錄》一冊,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間所藏經籍碑版釋氏經典文字,無所不有。其精者大半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圖書館,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國守土之吏,熟視無睹。鄙人行部至酒泉,雖未出嘉峪關,相距不過千里,已聞石室發見事,亦得畫象兩軸,寫經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寶藏,鞧軒奉使之為何?愧疚不暇,而敢責人哉!”(48)[清]葉昌熾著《緣督廬日記》,第10冊,第6326-6327頁。這段日記中的感慨之言,無疑是針對羅振玉《鳴沙山石室秘錄》一書中“(伯希和)亟往購得十巨篋,約居石室中全書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書及經卷之精好者,亦略盡矣”(49)羅振玉《鳴沙山石室秘錄》,宣統二年(1910)國粹學報社印,第1頁。的描述所發。只是不知道幡然夢醒,得知了藏經洞文物流散部分實情的葉昌熾,在自責“愧疚不暇”的同時,筆下對熟視無睹的“中國守土之吏”的譴責,是否也包含了汪宗翰在內?
華振之指出,在葉昌熾第一次收到汪宗翰寄來的出自藏經洞的寫經和畫像時,“葉氏為對考古素有研究學者,不知何以當時竟未深入查究,否則,這些藝術珍寶,也許可以幸免流徙異邦的劫運”(50)華振之《敦煌石室,國之瑰寶(下)》,《東方雜志》1976第8期,第42頁。。黃征也在《敦煌文獻的發現》一文中說:“在1902年3月的時候,汪宗翰當上了敦煌縣令,王道士不失時機地又送上一些樣品。汪宗翰是湖北省通山縣人,1890年考中進士,學識很好,對于古代文獻有較深的認識,當上敦煌縣令后曾在當地收集到一些漢簡。當王道士送來敦煌卷子時,他打開一看,十分稱賞,于是馬上就寫了報告交到甘肅學政葉昌熾那里,接到批復后又責令王道士暫將發現的文物和文獻放回洞中封存起來,等候處理。他是在1904年親自奉甘肅藩臺之命檢點封存藏經洞的。可是不幸得很,汪宗翰在1906年2月就被調離敦煌縣,以致未能將移送敦煌文物、文獻到公府之事辦妥。”(51)黃征《敦煌文獻的發現》,《嘉興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1期,第8頁。
歷史是無法假設的,事件發生了就是發生了。從后來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并最終導致大部分藏經洞文獻“流徙異邦”的結果來看,我們認為葉昌熾之所以沒有“深入查究”的原因,除了與其在官場上謹小慎微,抱著絕不越權的信條,在建議將藏經洞之物運到蘭州保存,遭到藩臺“運費無著”的婉拒后,便不再極力爭取,只是檄文汪宗翰“乃為封存”有關外,可能還因為相信了汪宗翰洞內僅“藏經數百卷”,初開之時眾人分取的謊言,又眼見同僚幾人手中也有不少藏經洞經卷,可能誤判藏經洞內文物已所剩無多,不值得再去爭取也有很大關系。
如果早在1902年汪宗翰陪同許伯阮游覽莫高窟,拿走二百余卷經卷和佛爐后,又或是在1904年檢點完藏經洞之后,將內藏“二萬余卷”經卷的消息,第一時間就毫無隱瞞地報告了葉昌熾。葉昌熾會不會再次積極運作,爭取甘肅藩臺采取措施,將藏經洞之物運往蘭州保存,我們不得而知。“過去學術界都傳說葉昌熾曾建議甘肅藩臺把所有藏經洞古物運到省垣蘭州保存,但因運費沒有著落,沒有成功。細檢近年廣陵古籍刻印刊行的《緣督廬日記》全本,沒有找到相關的記載,從葉昌熾當時不知有數萬本不被發現的情形來推測,這個傳說大概也是難以成立的”(52)榮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敦煌研究》2000第2期,第25頁。。葉昌熾之前應該有過向甘肅藩臺建議把藏經洞古物運到省垣蘭州保存的建議,否則,可能就不會有汪宗翰1904年奉檄檢點藏經洞之物的事。同樣的,如果葉昌熾得知依然有數萬卷的經卷躺在藏經洞內,是不是會如其日記中所言“鞧軒奉使”,“罄其寶藏”,運往蘭州保存也未可知!不過,汪宗翰幾年間刻意隱瞞藏經洞文物信息的行徑,是造成藏經洞文物沒有被運往蘭州保存的一個主要因素。
2.隨意拿取和饋贈,加速了藏經洞文物的外流
上文所揭,汪宗翰1902年陪同許伯阮游敦煌莫高窟,一次就拿走了多達二百余卷的藏經洞文物。1904年汪宗翰雖奉檄前往檢點藏經洞文物,但卻只是草草地“大致翻閱一過”,在其眼皮底下,隨從的文武官紳當場“有攜回一、二卷者”,汪縣令不但不予阻止,自己也以“迎歸署中供養”的名義,不知道私拿了多少經卷。依據第一次汪宗翰陪同許伯阮游莫高窟,拿走二百余卷藏經洞文物的行為推測,估計這次所拿經卷數量也一定不少。汪宗翰通過兩次莫高窟之行的隨意拿取和文武官紳的分取,無疑加速了藏經洞文物的外流。
為了搞好與上司的關系,同時為達到盡早調離敦煌的目的,汪宗翰不斷利用手中的藏經洞文物,給能夠替自己說項的同年及上司送禮。目前所知曾接受過汪宗翰贈送的至少一卷至數卷不等藏經洞文物的有葉昌熾、陸季良、許寶荃、和爾賡額、徐錫祺、何衍慶、侯葆文等數人。這樣,一批藏經洞文物經由汪宗翰之手,開始流向甘肅任職的一眾官員手中。正如王冀青所指出的,“1902年汪宗翰被任命為敦煌知縣后,加速了藏經洞文物的外流。汪宗翰任敦煌知縣期間(1902-1906),許多藏經洞寫本和繪畫品被送給了在蘭州的甘肅學政葉昌熾(1849-1917,1902-1906任職)和其他官員”(53)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與王圓祿及敦煌官員之間的交往》,《敦煌學輯刊》2007第3期,第66-67頁。。因此,汪宗翰就任敦煌知縣后,不但沒能阻止藏經洞文物的外流,相反,其隨意拿取、贈送藏經洞文物的行為,在客觀上加速了早期藏經洞文物的外流。
3.敷衍的“封存”,造成了藏經洞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盜買的結果
汪宗翰在奉檄檢點完藏經洞文物之后,沒有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只是輕描淡寫地“吩示王道人善為保存”,便不再過問,正如《敦煌學大辭典》中“汪宗翰”的詞條所描寫,“光緒三十年三月改命敦煌縣檢點封存,汪氏實主其事,但未嚴加保護,而是交由王道士就地保管”(54)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888頁。。檢點后藏經洞文物保管的情形,也依然如同后來斯坦因和王道士談判時,王道士抱怨的那樣沒有絲毫改觀:“官府甚至沒有對這批卷子如何處置作出任何安排”(55)[英]奧雷爾·斯坦因著,姜波、秦立彥譯《發現藏經洞》,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1頁。。藏經洞門口粗糙的木門和銅鎖,還是王道士事后自己安裝的,并且,“鎖的鑰匙由王圓祿親自保管。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訪時,情況一直如此”(56)王冀青《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第38頁。。
汪宗翰不負責任的檢點,名義上的封存,與掩耳盜鈴無異!后來的事實證明,王道士依然如故,不斷地從已“封存”的藏經洞內拿出一些精美的經卷和佛畫,送給敦煌當地的官紳和香客。小小的敦煌縣城,汪縣令不可能不有所耳聞,但對此卻充耳不聞,聽任王道士偷拿藏經洞文物贈送敦煌地方官紳,無疑助長了藏經洞文物的外流之風。
1907年斯坦因成功騙買走了大批藏經洞文物后不久,王道士擔心藏經洞內文物被官府收走,自己手中沒有了可以贈送和出賣以賺取香火錢的經卷,便和上寺、中寺的喇嘛一起,以轉經為名迷惑信眾,在莫高窟第351窟(伯希和編第160窟,張大千編第146窟)內建造了兩個封釘堅固,外表漆畫一新,實際上里面塞滿了大量從藏經洞內偷拿出來的大批經卷的所謂的轉經桶。
1909年10月,敦煌縣令陳澤藩奉命查驗藏經洞文物時,發現了轉經桶,但他并沒有將轉經桶內經卷收走,只在轉經桶上加貼了蓋官府印信的封條予以封存,并口頭“嚴諭”王道士將經桶嚴密看守,以免遺失,同時給繼任的知縣寫了一份有關轉經桶的移文。1910年10月20日又寫了第二封移文,交代了轉經桶之事,“嗣后,奉學部搜買。敝縣會同學廳,傳集紳民,盡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羅,護解省垣,其經桶原封未動”(57)衛聚賢《敦煌石室》,第89頁。。其后,繼任敦煌知縣申瑞元也有給民國第一任敦煌縣長黃金綬的移文。移文證明,“一直到清朝滅亡,轉經桶一直在王圓祿的看管之下”(58)王冀青《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第106頁。,未被拆封。
這說明,王道士還是很怕官的。在官府嚴令下,時間雖然過去了幾年,但轉經桶在王道士看管下依然完好如初。反過來說,假如當初汪宗翰稍稍用些心思,在檢點完藏經洞文物后的第一時間,命人在藏經洞門口安裝上木門并上鎖,再加貼上縣府的朱標印封,將鑰匙拿回縣衙保管,并且像申瑞元一樣,嚴諭“妥為保守毋再遺失私買,致干咎,切切”(59)衛聚賢《敦煌石室》,第89頁。,即使王道士膽大包天,也不敢私揭了縣府印封,破門撬鎖,偷拿藏經洞文物。因此,汪宗翰對藏經洞文物檢點后不負責任的敷衍封存,直接造成了日后王道士依然不斷拿取私賣贈送當地官紳,并最終將大批藏經洞文物盜賣給斯坦因、伯希和,流向歐洲的可悲結局。
五、結論
以前因為受資料限制,學界較少關注汪宗翰收藏藏經洞文物的情況,也很少注意到藏經洞文物流散之初,大量藏經洞文物的流散跟汪宗翰的關系。隨著更多與汪宗翰曾經有過交往官員的信件、日記以及收藏的藏經洞文物上的題識,汪宗翰曾經收藏的藏經洞文物上的鈐印、題識等信息的披露,我們對汪宗翰在藏經洞文物流散之初的所作所為,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擔任了敦煌知縣近四年時間的汪宗翰,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便利條件,即便不是藏經洞文物流散之初,攫取藏經洞文物最多的甘肅官員,但無疑是在清廷學部將藏經洞文物運往北京前,至少也能算得上是獲得藏經洞文物數量最多的人物之一。
2.汪宗翰隨意拿取藏經洞文物的行徑,一定程度上縱容了隨同文武官紳“各人分取”的行為,致使很多藏經洞文物流入敦煌官紳手中。同時,汪宗翰為了討得上司歡心和達到盡快調離敦煌的目的,不斷用手中的藏經洞文物,給葉昌熾等一眾官員送禮,導致在他任敦煌知縣期間,藏經洞文物流散數量增多,流散步伐加快。
3.汪宗翰刻意隱瞞藏經洞文物數量信息,致使葉昌熾沒有再盡力向甘肅官府爭取,從而錯失了將藏經洞文物運往省垣蘭州妥善保存的機會。
4.汪宗翰檢點完藏經洞文物后,單純為了應付上級官府,極不負責,徒具形式的“封存”,不僅沒能阻止王道士繼續偷拿藏經洞內文物贈送、私賣地方官紳的行為,并最終造成其將大批藏經洞文物盜賣給西方探險家,流失到歐洲的悲慘結局。
美籍獨立學者任光宇集各家之說,通過排比汪宗翰在藏經洞文物發現后的所作所為,做出芻議:“雖然有記載顯示汪氏頻頻向上級贈送遺書的目的,在于運動自己升遷和調回關內,但客觀上做到了及時上報、調查藏經洞發現,并協助葉昌熾正確鑒定了敦煌遺書。總的來說,汪宗翰在其任內有小功無大過,表現好于一般‘俗吏’”(60)任光宇《敦煌學術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與評議——兼論敦煌遺書發現人暨敦煌學的起始》,第8頁。。
縱觀汪宗翰在藏經洞文物早期流散過程中所扮演的各種角色,實在配不上任光宇對他這樣的謬評!
王慶衛指出:“在早期藏經洞文物的流散過程中,或多或少都和一個關鍵人物即汪宗翰有所關聯。”(61)王慶衛《徐錫祺舊藏敦煌寫經簡述——以西安地區藏品為中心》,第139頁。現在看來,不是或多或少的問題,而是直接和汪宗翰有很大關聯。如果汪宗翰在獲知藏經洞文物信息的第一時間,不隱匿,及時上報,又或者在“封存”藏經洞文物之時能盡職盡責,或許現在藏經洞文物的收藏會是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