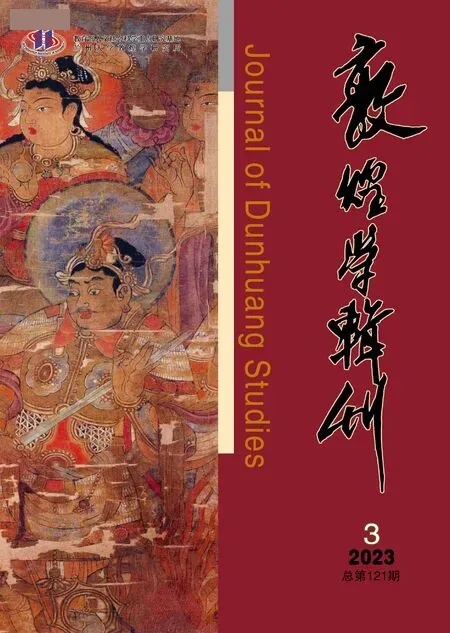王梵志詩的文學史意義
戴瑩瑩 鄒 知
(1.四川大學 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200;2.浙江大學 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0)
1925年,劉復先生的《敦煌掇瑣》出版,其中有三個從巴黎抄回的王梵志詩寫卷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至此,學界開始了漫漫百年的王梵志詩研究之路,研究主要集中在詩集的輯錄、校注、考訂和詩歌的語言、思想、藝術特征等方面。學界一般認為王梵志詩的文學史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從詩歌內部而言,王梵志詩主要用白描、敘述和議論方法再現和評價生活,彌補了文人詩的弱點(1)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29頁。;從詩歌外部而言,王梵志詩直接開創了唐代白話詩派(2)項楚等《唐代白話詩派研究》,北京:學習出版社,2007年,第125頁。,對唐代的通俗詩派產生了重要影響(3)張錫厚《論唐代通俗詩的興起及其歷史地位》,景生澤主編《唐代文學論叢》第9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4頁。。然而,作為文學作品的王梵志詩,在詩歌史、文學史上,是否有特殊的意義?它是如何一步步推動學界“構建”唐代詩歌流派、“重寫”文學史的?本文擬立足中國詩歌中“前人沒有注意的傳統”(4)陳致主編《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序言》第1頁。下同,不再出注。,探討王梵志詩的詩歌史、文學史意義,考察其對文學史、學術史產生的深遠影響。
中國詩歌具有悠久的創作傳統——敘事傳統和抒情傳統。陳致在《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中指出:
目前海內外關于詩歌抒情傳統的研究已形成一股熱潮,最近又有學者提出中國詩歌還有敘事傳統。這兩種傳統包含的范圍很廣,其概念也能為海內外學界普遍理解。但是我們認為創作傳統的內涵其實是多方面的,可以不限于這兩種思路。在中國詩歌批評史中,在審美觀照、體式格律、藝術表現、取題選材等許多方面都包含著對于前人創作傳統的許多思考和總結。同時,古代詩學的這類理論思考本身也形成了其特有的傳統。我們除了用現代學術思辨來闡釋和總結這些傳統以外,還可以從多種角度在古人的詩歌創作實踐中去發現前人沒有注意的傳統。(5)陳致主編《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序言》第1頁。
事實上,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今,敦煌學界都在持續挖掘這種“前人沒有注意的傳統”,遺憾的是尚未引起詩歌史、文學史及詩學批評領域學者足夠的重視。而王梵志詩的創作實踐正具備這種未被發現的傳統的特征——它在取材選題、藝術表現、體式格律、審美觀照等各方面不同于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傳統和敘事傳統,“王梵志詩正好是在文人詩歌最薄弱的環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6)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前言》第29頁。
一、底層暴露:取材選題、詩歌語言
(一)取材選題:“零距離”的唐代農村
王梵志詩以唐代民間生活為背景,著重描繪山野鄉間的村夫村婦及其瑣細日常、喜怒哀樂。不同于陶、謝、王、孟等文人筆下清靜幽美的田園風光、恬靜淡雅的隱居生活、自得其樂的農耕體驗,王梵志詩創造了一個迥然不同的唐代農村世界。王詩中的農村田園,丑惡、貧窮、骯臟、混亂,偏重展示中國封建農村中的各種人際關系——包括家庭關系、社會關系。人與人之間沒有半點溫情,互相傾軋,充滿了惡毒和怨恨。
家庭內部,父母、子女各為己利。父母抱怨兒女:“長大毛衣好,各自覓高飛。”(《人間養男女》)(7)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493頁。;甚至狠毒地咒罵親生骨肉:“腹中懷惡來,自生煞人子。”(《父母是怨家》)(8)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92頁。;兄弟聚族而居,卻勾心斗角、私聚家產:“當房作私產,共語覓嗔處。”“一日三場斗,自分不由父。”(《兄弟義居活》)(9)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215頁。。王詩常通過前后強烈的反差對比表現各種社會關系唯利是圖的本質,如:
父子相憐愛,千金不肯博。忽死賤如泥,遙看畏近著。(《父子相憐愛》)(10)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351頁。
前人敬吾重,吾敬前人深。……君看我莫落,還同陌路人。(《前人敬吾重》)(11)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17頁。
吾富有錢時,婦兒看我好。……邂逅暫時貧,看吾即貌哨。(《吾富有錢時》)(12)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12頁。
上述三首分別揭露父母子女、朋友、夫婦間人際交往的共性:趨炎附勢,虛與委蛇。富貴時相親相愛,沒落時恩斷義絕。
社會內部,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大多即可憐又可恨。如一些鄉村、州縣小吏,當其作為統治者時,他們以收受賄賂為生;當其作為被統治者時,又面臨重重壓力。如《村頭語戶主》:“在縣用紙多,從吾便相貸。”(13)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113頁。《佐史非臺補》:“錢多早發遣,物少被頡頏。”(14)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100頁。這些小官小吏往往負擔著沉重的賦稅和經濟壓力,有的甚至要向更貧窮的農民借貸;作為被統治者的農民間則貧富懸殊,《貧窮田舍漢》《富饒田舍兒》二詩以強烈的對比鮮明地揭露了這一巨大差異:
貧窮田舍漢,菴子極孤凄。……黃昏到家里,無米復無柴。男女空餓肚,狀似一食齋。里正追庸調,村頭共相催。幞頭巾子露,衫破肚皮開。體上無裈袴,足下復無鞋。……門前見債主,入戶見貧妻。舍漏兒啼哭,重重逢苦災。(《貧窮田舍漢》)(15)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58頁。
富饒田舍兒,論情實好事。廣種如屯田,宅舍青煙起。槽上飼肥馬,仍更買奴婢。牛羊共成群,滿圈養肫子。窖內多埋谷,尋常愿米貴。里政追役來,坐著南廳里。廣設好飲食,多酒勸遣醉。追車即與車,須馬即與馬。(《富饒田舍兒》)(16)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53頁。
窮者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負債累累,承擔著繁重的租稅;富者卻坐擁廣田、牛羊成群,享受著榮華富貴。壓在窮人身上沉重徭役負擔,富人只在推杯換盞間解決。巨大的貧富差距令人駭然不已。
王梵志詩中的農村世界,家庭內外、社會各級的人物形成了一個“閉環”系統。無論是個人的夫婦、父子、兄弟、奴主、朋友關系,還是社會的官吏、吏民、民民關系,人們多以自私自利為出發點來交際。王梵志詩無限深入地刻畫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血緣關系、夫妻關系、朋友關系、上下級關系,深刻展示人類精神的幽暗面。在現存的唐詩文獻中,這是絕無僅有的。王詩突破了詩歌“言志”“緣情”“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種種束縛,創造了新的敘事題材和敘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唐代詩歌的總體面貌。王詩中也有少量描寫閑適安逸的農村生活的詩歌,如《吾有十畝田》以農民的視角書寫“遨游自取足”(17)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348頁。的簡單樸素的躬耕生活。但這些作品并不作為王詩的主體出現,在文學史上也不具有特異性。
陶淵明、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都寫過農村生活,但他們在對客體世界觀物取象時,所采取的身份、立場、審美,及對待現實的態度與王梵志詩不同。陶詩、杜詩“通常是自上而下地俯視勞動人民的生活,并給予深厚的同情”(18)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前言》第24頁。,通過捕捉短暫的生活瞬間,藝術化地再現農村、表達情感。其詩歌既反映了部分現實,也變形了真實世界。而王梵志詩“則是從社會底層的內部觀察人民的生活,并作為人民的一員來唱出自己的痛苦,因此它比文人詩歌更真實,更具體,更深刻。”(19)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前言》第24頁。它即展現了封建農村世界,塑造了底層百姓人物群像,又展示了作者的精神和生活世界,折射出底層破落文人群體。兩重世界相互交織、以詩證史,不僅反映了那個世界的歷史真實和社會真實,更反映了“心靈真實”,展示了時人的內心世界(20)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前言》第26頁。。這既是“史”筆,更是“小說”之筆。
(二)詩歌語言:下層社會的語言系統
中國古典詩歌強調語言的簡約性、藝術性、象征性、音樂性等,但王梵志詩卻以口語、俗語、方言、“臟”語等白話語言為主,采用了俗字、俗音和口語語法,通俗直白、粗鄙丑陋。不同于文人的詩歌語言,王梵志詩還原了唐代下層社會的語言系統,展現了一種全新的語言風格。
王梵志詩中保存了大量的口語、俗語,包括當時人們常說的土語、流行語,如“方孔兄”“眼赫赤”“常展腳”“飯蓋”“兀硉”“土角”“肥沒忽”“遮莫”(21)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167、264、25、330、287、42、88、294頁。等;方言如“山鄣買物來,巧語能相和”(22)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164頁。的“和”,意為哄騙。“中心禳破氈,還將布作里”(23)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190頁。的“禳”,為“充填”之義,此二字至今都還存在于成都方言中;“臟”語,即不見容于文人詩的粗陋之語,如“糞尿”“老爛鬼”“臰穢”“糞塠”“膿血”(24)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08、496、499、519、52頁。等。詩人毫不避言“死”“尸”“臰”“穢”等詞,詞語雖然刺眼,卻極具沖擊力;通過梵志詩的用韻還可考察當時唐代民間口語俗音的真實面貌。都興宙以《王梵志詩校輯》收錄的三百余首五言白話詩為依據,歸納整理出25個韻部(25)都興宙《王梵志詩用韻考》,《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第121-126頁。,妥佳寧、何宗英在綜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27個韻部,較清晰地展現出當時中原真實的語音狀況(26)妥佳寧、何宗英《從王梵志詩韻看唐初中原方音》,《古籍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5-110頁。;語法上,王梵志詩大量采用口語語法,與文人詩的書面語法不同。比如“是誰……”“請看……”“饒你……”“得”“有”“不”(27)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273、275、279、283、318、279頁。等均是口語中常見的句法和用字,一般不用于詩歌書面語。
這些口語、俗語、方言、“臟”語,一方面具有重要的語料價值,豐富了漢語詞匯庫;另一方面表明了詩歌作者的社會身份和文化特質,展示了唐代下層文人詩歌的語詞、語意、語句、語法等語言形式之間的差異性。當詩人的社會、語言背景越趨于一致,語句、語詞的選擇范圍越相似,語意的表達、理解越接近,詩歌也越容易形成普遍性、關聯性和規范性。然而,王梵志詩使用的是唐代下層社會的語言,它具有特殊性、孤立性和不規范性,更依賴詩歌場域的建構,需要特殊性解讀。某種意義上說,這正是唐代詩歌語言的另一維度。
二、丑態展現:描寫技法、意象編聯
(一)描寫技法:重“形”不重“意”
不同于文人詩的重“神”取“意”,王梵志詩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以白描、寫形為主,重“形”不重“意”,注重對人物、事件進行白描式地刻畫敘寫。其詩以真實而精準的白描手法,勾勒出唐代民間底層百姓的“人物繪”。
文人詩即使是描寫社會底層平民,也仍然是以取“神”、取“意”為主。如白居易《新豐折臂翁》:“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須皆似雪。”(28)[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09頁。《賣炭翁》:“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29)[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1冊,第393頁。詩人截取人物面容的幾處典型細節,加以藝術化地描寫,刻畫了折臂翁、賣炭翁兩個老人形象。以小見大,字句精煉而內涵豐富,通過最具特征的細節傳神達意。同樣是描寫老人,王梵志詩則不同。如《心恒更愿取》描寫一個想娶年輕女子的糟老頭:“身體骨崖崖,面皮千道皺。行時頭即低,策杖共人語。眼中雙淚流,鼻涕垂入口。腰似就弦弓,引氣急喘嗽。口里無牙齒,強嫌寡婦丑。”(30)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48頁。詩人用白描手法,刻畫了一個骨瘦嶙峋、皺紋橫生、流淚垂涕、缺牙駝背的農村糟老頭。該詩以細致的筆觸摹寫了老叟的體格、臉面、姿態,眼、鼻、腰、口、齒,不遺余力地展現老翁形象的方方面面,淋漓盡致地寫形,而不傳言外之意。這是另一種敘事傳統。
古典詩歌中也有重“形”不重“意”的作品。如晉宋之際“巧構形似”“貴尚巧似”的山水詩,擅長細致描摹女性容貌的宮體詩等。不同的是,文人詩以“形似”為手段,實際上仍然以“傳神”為宗旨的,最終目的還在于表現“聲情神韻”,如來裕恂《漢文典注釋》所言:“文章之聲情神韻,全賴描寫摹擬以傳之,故其功用,悉在形容。”(31)來裕恂撰,高維國、張格注釋《漢文典注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45頁。王梵志詩雖也有夸張、比喻之語,但用意仍在真實地描寫、刻畫人物、事件,而非為對象注入“神韻”“靈趣”。
(二)意象編聯:審丑的逆光效應
中國傳統詩歌重視“意”“象”“境”的關系。以“象”達“意”,表達詩人的主觀情感和體驗;“意”“象”交融,建構“意境”,創造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的詩歌世界。因此,詩人選擇意象,往往具有一定的目的——情景交融,以達審美愉悅;虛實相生,增強詩歌表現力;新穎獨特,以悅人耳目等。但大部分王梵志詩取“象”、寓“意”、造“境”的美學基調是“審丑”而非“審美”,其敘事是“丑”的,語言是“丑”的,意象的選擇和編聯也是“丑”的。
首先,選擇“丑”的意象。寫女性,王梵志詩避開仙女、美女、少女,專意于懶婦、刁婦、妒婦、小家女、窮尼姑。如《讒臣亂人國》詩中,作者以刻薄的語言譏刺丑女:“丑皮不憂敵,面面卻憎花”(32)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300頁。,丑女若是簪花,則丑上加丑;寫官員,王梵志詩少寫清官、好官,卻對那些“天下惡官職”用筆甚勤,如顛倒黑白的三司長官、兇惡的御史臺、不知厭足的貪官等(33)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332、337、330頁。;梵志詩中面丑、心丑的人物形象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各個角落,除女性、官員外,還有心毒的浮逃人、不孝子、窮苦的農民、精明算計的奸商、貪婪自私的地紳等(34)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88、592、558、164、633頁。。人物之外,梵志詩中還充斥著大量“丑”的事物,如“椀鳴聲”“破氈”“黃檗皮”“積代骨”“白骨”“糞塠”“蟲蛆”“尸”“臰穢”“膿”“墳墓”等(35)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22、367、493、514、536、519、499、508、512頁。,幾無任何美感可言,反而陰冷、齷齪。
其次,“丑”意象的編聯。編聯多個意象構成一個完整的意境,王梵志詩通過大量的丑陋意象營造出荒蕪、恐怖、陰森的環境。如:“命絕拋坑里,狐狼恣意飡”“門前夜狐哭,屋上鵄梟鳴”“新墳影舊塚,相繼似魚鱗”“血流遍荒野,白骨在邊庭”(36)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21、321、514、536頁。等,舊塚新墳,狐鬼夜鷹,怪異瘆人。此外,作者還通過意象編聯構成簡單的敘事情節,奠定故事的基本格調。如《怨家煞人賊》:“怨家煞人賊,即是短命子。生兒擬替翁,長大拋我死”(37)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210頁。,子女長大不念養育恩情,卻想霸占父輩資產,父母怨恨子女,咒其短命。詩人以“煞人賊”“短命子”等意象編聯,揭露丑惡的人情和殘酷的現實。又如《天子與你官》:“飲饗不知足,貪婪得動手。每懷劫賊心,恒張餓狼口”(38)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330頁。,以“劫賊心”“餓狼口”等意象,夸張地表現官吏貪得無厭的丑相。
中國傳統詩歌重視“審美”,追求“盡善盡美”的境界,雖也有“審丑”現象,但其寫作動機與范圍都與王梵志詩明顯不同。如杜甫《負薪行》描寫了一群年近半百仍未出嫁的怪異、粗丑的“老姑娘”:“夔州處女發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并。”(39)[清]浦起龍撰《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95頁。這些夔州處女已半邊白發,卻猶結雙鬟,頭戴山花銀釵。但詩人沒有調侃和貶低這些丑女,而是表達了極大的悲憫與同情,這與王梵志詩鑒賞、把玩丑女形象迥然不同。
十九世紀西方象征派、現代主義,二十世紀的后現代主義將描寫和刻畫“丑”作為一個重要的創作命題,直到二十世紀才在中國美學、藝術界產生影響,而這種“反其道而行”的創作手法早在唐代王梵志詩中就已大量運用了。“丑”充斥王梵志詩歌,顛覆了讀者的閱讀經驗和期待視野,產生“審丑”的逆光效應。詩人對“丑”的對象進行審視、觀照、書寫和刻畫,詩歌的意、象、境因而粗俗、丑陋和畸形。
此外,王梵志詩大量運用不見于文人詩的獨特意象,極大地豐富了古代文學寶庫,對后世詩歌(尤其是宋詩)產生了重要影響。王梵志詩中大致有三類最富個性和創造性的意象:俗世意象、佛教意象和隱喻意象。俗世意象,包括俗世中的人物和事物(40)參考高國藩《論王梵志詩的藝術性》,《江蘇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第129-134頁。該文第二節比較詳細地論述了王梵志詩中的俗世意象,但舉例大多是人物形象。其實,王梵志詩中的俗世意象遠遠不止人物,還包括許多事物。。人物形象如村頭、貧農、土豪、懶婦、懶漢、奸商、工匠、浮逃人、鄉長、貪官、御史、守財奴、達官兒、府兵等(41)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113、367、553、132、126、167、172、588、109、330、337、170、161、158頁。,物象如私產、元寶、四合舍、百人齋、資產、三臺、故塚、破甕、山門、街巷、鬼樸、土孔籠、棺木、衾被、飯甕、食瓶、籍帳等(42)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215、207、201、199、193、191頁。,都是唐代底層平民生活中常見的物象。佛教意象如:三惡道、天堂、地獄、恒沙劫、五戒身、無常、業道、冥空、一隊風、菴羅、未來因、悉達、生路、四果等(43)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217、213、582頁。。這些晦澀的宗教術語在中國古典詩歌中難以見得,即使是在擅長用典、說理,受佛禪影響較深的宋詩中也是不見的;隱喻意象,如“饅頭”喻墳墓、“翻著襪”喻顛倒眾生,“鬼見拍手笑”以比喻諷刺守財奴等(44)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649、651、644頁。。隱喻意象多具諷刺性,想象大膽新奇,反映民間思維。
三、民間書寫:體式韻律、唐代民歌
(一)體式韻律:民間書寫的異質性
體式韻律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詩人的文化水平、文學素養和語言使用方式。文人詩是一種精致書寫,其體式韻律具有規范性。王梵志詩則是一種異質書寫,體式韻律具有不規范性。

用字方面,梵志詩毫不避諱使用重字。如“眾生眼盼盼,心路甚堂堂”“死時天遣死,活時天遣活”“生時不須歌,死時不須哭”“請看漢武帝,請看秦始皇”(48)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283、262、267、275頁。等,俯拾皆是。其詩常用疊詞或上下句采用相同的句式,僅改動個別字。相同的字詞在一首詩中可出現兩次、三次甚至更多。節奏方面,文人詩要求詩歌的節奏韻律、詞匯意象富于變化,有抑揚頓挫之感。而王梵志詩卻不受此限,許多詩歌意象少、句式單一、用詞重復、節奏平直。如《眾生眼盼盼》:“一種憐男女,一種逐耶娘。一種惜身命,一種憂死亡。”(49)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283頁。四句話首二字全同,且都是二、一、二式的結構,兩句之間、兩聯之間缺乏起伏變化。
(二)王梵志詩與唐代民歌
王梵志詩寫卷中還混雜著一些民間歌謠,包括歌詩和曲詞。根據胡懷琛《中國民歌研究》的定義:“流傳在平民口上的詩歌,純是歌詠平民生活,沒染著貴族的彩色;全是天籟,沒經過雕琢的工夫,謂之民歌。”(50)胡懷琛《中國民歌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第2頁。民歌是以平民生活為創作內容,以口耳相傳為傳播形式的詩歌,與文人詩和白話詩都有所區別。
民間歌詩,即下層民眾用于詠唱的詩篇。王梵志詩中的哪些詩歌曾經過百姓歌唱,如今難以詳考。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根據《敦煌掇瑣》考定二十八首王梵志詩為民歌。一方面,作者考定這些詩篇出于民間,而非佛教勸善歌。這是由于詩歌的內容反映世俗生活而不是宗教情緒,并且有些作品公然反對佛教、辱罵和尚;另一方面,作者考證這部分詩歌原本是口頭歌唱文學,而非最初就是書面文學。文章通過整理寫卷中大量的“音近形遠”的錯別字證實了這一觀點(51)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02-212頁。。本文以這二十八首詩歌為對象,分析王梵志詩寫卷中的歌詩對唐代民歌的貢獻和意義。
第一,繼承了民歌關注現實的傳統。《詩經》中的“風詩”是現存最早的民歌,開辟了民歌現實主義的傳統,區別于《九歌》等浪漫的楚地民歌。漢魏樂府民歌繼承了《詩經》關注現實的精神,其詩“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后代之人。”(元稹《樂府古題序》)(52)[唐]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92頁。北朝樂府民歌更以描寫的社會面廣泛著稱。王梵志歌詩是這一悠久傳統的延續,二十八首皆為現實主義佳作,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民生疾苦。如《二十充府兵》等六首(53)其余五首分別是:《生時同氈被》《患夜盲癥的老病卒》《兒大作兵夫》《窮漢村》《男女有亦好》,參考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該六首在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中分別題為:《你道生勝死》(第533頁)《知識相伴侶》(第613頁)《父母生兒身》(第502頁)《富兒少男女》(第566頁)《男女有亦好》(第606頁)《不見念佛聲》(第499頁)。揭露了唐代府兵制實行后期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富饒田舍兒》等七首(54)其余六首分別是:《貧窮田舍漢》《貧窮實可憐》《夫婦生五男》《人間養兒女》《父母是冤家》《門前見債主》,參考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該七首在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中分別題為:《富饒田舍兒》(第553頁)《貧窮田舍漢》(第558頁,前16句)《工匠莫學巧》(第172頁)《夫婦生五男》(第539頁)《人間養男女》(第493頁)《父母是怨家》(第592頁)《貧窮田舍漢》(第558頁,后4句)。反映了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土地兼并普遍、貧富分化加劇、農村經濟凋敝的社會現實。
第二,擴大了民歌的題材范圍。民歌的題材,以表現男女戀情最多,如《古詩十九首》《子夜歌》《鳳歸云》等。其次是反映風土人情、邊塞征戰、勞動生活等題材,如《竹枝詞》《戰城南》等。王梵志歌詩以廣大民眾為表現對象,深入細致地刻畫他們艱辛悲苦的生活,以冷靜的筆觸控訴黑暗政治和荒誕現實,字里行間充溢著批判和諷刺。如《心恒更愿取》(55)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548頁。盡情嘲諷“老夫少妻”,《世間慵懶人》《家中漸漸貧》(56)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第126、132頁。批判了那些好吃懶做的男女。王梵志歌詩對社會陰暗面的關注之廣、批判力度之大,都是那些仍受“溫柔敦厚”“風雅比興”影響的現實主義民歌無法相比的。
第三,以人物形象塑造為中心,增強了民歌的敘事性。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將二十八首王梵志歌詩分為六類,分別是:“府兵、戰爭”“地主、雇農、逃戶、貧農”“官與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其他(包括‘男二流子’‘女二流子’‘老夫少妻’‘家庭’‘后娘’)”(57)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目錄》第1-2頁。。這些作品絕大多數以人物為中心,按身份、職業屬性展開敘事。我國古代的民歌缺乏西方文學的史詩傳統,因而具有較強的抒情性,且多為短歌,像《孔雀東南飛》《木蘭詩》那樣的長篇紀事民歌很少。王梵志歌詩恰好彌補了這一空白,二十八首詩均以紀事見長,篇制短小。這表明我國古代民歌中存在不少“敘事短歌”這種體裁模式,部分作品具有很強的敘事性。
再論曲詞,王梵志詩寫卷中發現了一首《回波樂》、兩首《隱去來》詞。《回波樂》早在北魏時期就已出現,現存四首,均為六言四句的定格(58)參考劉尊明《詞起源于民間再闡釋》,《中國韻文學刊》1995年第1期,第61頁。四首《回波樂》分別為李景伯、沈佺期、楊廷玉及優人失名者所作。。王梵志詩寫卷《回波爾時大賊》為六言十二句,說明《回波樂》“創調之初并不受六言四句的限制,其形式遠為靈活”(59)張錫厚《整理〈王梵志詩集〉的新收獲——敦煌寫本L1456與S4277的重新綴合》,《文學遺產》1988年第6期,第128-129頁。。《隱去來》是敦煌曲,為凈土歌贊《歸去來》衍生之曲,用以歌頌期盼歸隱凈土的心聲(60)參考鄭阿財《敦煌凈土歌贊〈歸去來〉探析》,《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4期,第24頁。。《回波樂》《隱去來》曲詞的發現“更有力地表明詞的產生還可以上溯到唐代初年,它為詞學史研究提供了生動而又難得的材料。”(61)張錫厚《整理〈王梵志詩集〉的新收獲——敦煌寫本L1456與S4277的重新綴合》,第129頁。進一步為“詞起源于民間說”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四、結語
詩歌的審美價值和美學范式是考察文人詩歌藝術價值的重要維度,而當我們用傳統的詩歌審美范式去鑒賞王梵志詩時,得出的結論就是梵志詩沒有多少價值:“這些作品在詩歌的藝術價值上,自然是不高的”(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62)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00頁。“詩歌的藝術水平很低”(草莽《王梵志的詩歌價值不高》)“其詩歌的價值不是太高”(胡適《白話文學史》)(63)草莽《王梵志的詩歌價值不高》,《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第77頁。。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評價,原因在于我們始終用既有的學術批評話語和限定的詩歌傳統來闡釋王梵志詩,沒有從具體的詩歌創作實踐中去發現“前人沒有注意的傳統”,或者忽略了這種傳統的意義和價值。從具體的創作實踐出發,王梵志詩至少有兩大重要意義:
其一,文言之外,打開了詩歌史的多重維度。過去一百年的唐代詩歌研究,除輯佚、增補、證偽外,最重要的莫過于白話詩的提出和研究。從王梵志詩的研究,到敦煌詩歌、寒山詩、拾得詩、釋道詩歌的研究,學界一步步拓寬了詩歌史的書寫空間,為唐代詩歌文獻的整理、研究打開了多重視野。
其二,雅俗之外,打開了文學史的多重維度。在校錄、注釋王梵志、寒山等詩歌的過程中,學界逐漸認識到民間詩歌、俗文學的題材、語言、韻律、審美特征,并通過文學、文獻學、語言學、宗教學等學科的交叉綜合研究,充分認識到俗文學的特點、性質與研究對象,及其與俗語言、俗信仰、俗文化的融合貫通,從宏觀上建構唐代俗文學。此外,在研究王梵志詩和白話詩的基礎上,學者嘗試系統地將禪門僧人與僧人詩作納入詩歌史研究范疇,將唐代白話詩置于佛教詩歌的系統之中,將文學史與禪宗史交錯考察,凸顯文學的宗教特征與宗教的文學特征,提出白話詩派和佛教文學的關系。文學史和宗教史是交錯的,不能武斷分割。在鑒賞、研究白話詩、俗文學、佛教文學、道教文學時,亟需拋棄固有的批評體系,建立全新的研究和闡釋模式,拓寬文學史研究的領域,重寫中國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