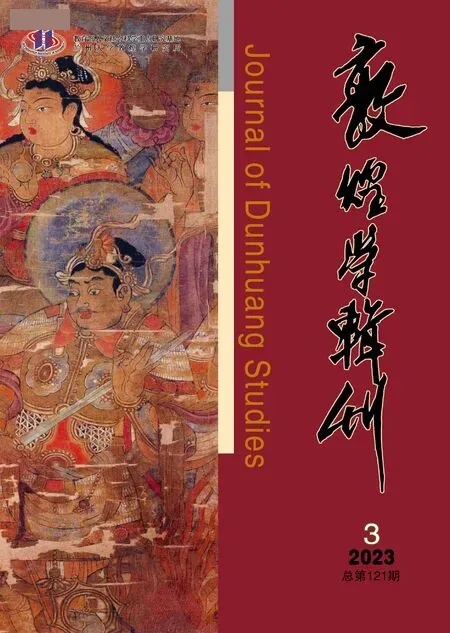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中國古代殘損佛像瘞埋是舍利瘞埋嗎?
——再論中國古代殘損佛像瘞埋的性質
張先堂
(敦煌研究院 人文研究部,甘肅 蘭州 730030)
一、引言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地不愛寶,在中國廣大地區持續不斷地發現了一批又一批古代佛教信徒在地下的土坑、窖穴,塔的地宮、天宮等處人為埋藏的古代佛教殘損造像。對于古代佛像瘞埋的現象,除了對各地出土佛像具體案例的考古報告和研究外,近10余年來已經有學者開始注意從宏觀的角度考察這些不同地區具體案例之間的聯系。崔峰先生曾梳理了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陜西、四川等省不同時期的20例重要佛像出土事件。(1)崔峰《佛像出土與北宋窖藏佛像行為》,《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第79-87頁。高繼習先生調查統計山東、河北、山西、陜西、四川、安徽、江蘇等地發現的殘損佛教造像群埋藏遺跡案例46例。(2)高繼習《宋代埋藏佛教殘損石造像群原因考——論“明道寺模式”》,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海岱考古》第8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488-514頁。黃盼女士收集了全國各地佛像集中埋藏的案例46例。(3)黃盼《中國中古時期佛像埋藏的考古學研究》,《華夏考古》2021年第5期,第74-84頁。筆者在2016年發表的論文中梳理中國百余年來的有關佛像瘞埋至少有48例,(4)張先堂《中國古代佛教三寶供養與“經像瘞埋”——兼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原因》,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0號,2016年3月,第253-273頁。此后近些年來筆者繼續搜集此類案例,已經增加到71例。
隨著此類考古材料的不斷積累,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在中國從北朝到唐代、宋代、金代、西夏乃至清代等不同時期,在山東、河北、山西、河南、陜西、四川、安徽、江蘇、寧夏、甘肅等不同地區,都曾經存在過將殘損佛教造像予以埋藏的現象,可以說是在中國古代相當長歷史時期內在廣大地區普遍存在過的現象。學者們將這種現象稱之為“佛像瘞埋”。瘞埋殘損佛教造像的性質是什么?學者們對此有許多不同的解說。其中有代表性的有2種:第一種是“佛像安葬說”,以李森先生的觀點為代表,他通過對山東臨朐明道寺、濟南開元寺和安徽亳縣咸平寺三處佛像埋葬情況的考察分析,認為青州龍興寺窖藏佛教造像的性質是在北宋時期山東地區流行的安葬佛像行為。(5)李森《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造像性質考》,《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12期,第147-149頁。第二種是“舍利瘞埋說”,持此說者較多,有杜斗城、崔峰、高繼習等諸位先生(詳下文論述)。目前學術界關于古代瘞埋殘損佛教造像性質的多種說法中,“舍利(法舍利)瘞埋說”為多位學者所贊同論證,成為比較流行的觀點。
筆者在2016年發表的論文中即已指出:“佛像等同舍利安葬說”似難以自圓其說。雖然舍利與佛像都與佛相關,但二者又各有所指。“舍利”專指佛以及高僧的遺骨,將佛像等同于舍利,既無典據支持,又有混淆名相之弊。其實從佛教史來看,舍利瘞埋與佛像瘞埋是互相相關而又各自不同的佛教歷史文化現象。(6)張先堂《中國古代佛教三寶供養與“經像瘞埋”——兼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原因》,第259頁。但當時筆者只是簡單提出觀點,未能予以深入論證。近幾年來筆者持續思考古代瘞埋殘損佛教造像的性質問題,在研究思路、論證證據方面獲得了新的進展。為此筆者特撰此文,對這一問題再予以申論。
二、從佛教義理和佛教典籍來看殘損佛像瘞埋不能視同于舍利瘞埋
中國古代佛像埋藏現象主要分為二類:一類是散亂埋藏,屬于對殘破佛像的隨意處置,可稱之為“佛像埋藏”;一類是對佛像恭敬的、有計劃的、禮儀性的瘞埋,可稱之為“佛像瘞埋”。后一類佛像瘞埋現象最值得關注。對于其性質,學者們曾有過不同的解說。
李森先生通過對山東臨朐明道寺、濟南開元寺和安徽亳縣咸平寺三處佛像埋葬情況的考察分析,認為青州龍興寺窖藏佛教造像的性質是在北宋時期山東地區流行的安葬佛像行為。
杜斗城先生認為山東出土的上述幾批造像,包括1979年山東高青、1996年山東昌邑的發現,皆為對廢棄的佛教造像的“舍利安葬”。(7)杜斗成《山東龍興寺等佛教造像“窖藏”皆為“葬舍利”說》,劉鳳君、李洪波主編《四門塔阿閦佛與山東佛像藝術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53頁。崔峰先生認為遍及山東、河南、河北、陜西、四川等省份的佛像埋藏行為不是“三武滅佛”時所為,而是一種護法之舉,殘損不齊的佛像被等同為舍利集中埋葬,并把殘件佛像稱為“感應舍利”。(8)崔峰《佛像出土與北宋窖藏佛像行為》,《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第79-87頁。高繼習先生更進而認為將殘損的石造像集中埋藏體現了“法舍利瘞埋”理念。(9)高繼習《宋代埋藏佛教殘損石造像群原因考——論“明道寺模式”》,第500頁。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擺脫了以“戰爭避難說”為代表的著重從外部社會歷史背景尋找佛像埋藏原因的研究思路的窠臼,注重從佛教歷史文化本身尋找根源,各有其合理之處,啟發我們以新的思路來探討佛像瘞埋現象的性質。但其中尚存一些不合理乃至誤解之處,有必要予以深入細致的辨析。
筆者認為,“安葬佛像行為說”僅僅說明了表象,尚未揭示出其內在實質:安葬佛像的目的是什么?性質是什么?“佛像等同舍利安葬說”“感應舍利瘞埋”“法舍利瘞埋”說表面上解釋了佛像瘞埋的性質。但此說存在理解的誤區,與佛教典籍和佛教義理不相吻合,難以自圓其說,有必要予以商榷、辨正。
從佛教義理上來說,雖然舍利與佛像都與佛相關,但二者又各有所指,不容混淆。在古代印度,舍利是梵語Saria的音譯,也作“設利羅”“室利羅”,意即身骨或尸骨,或曰“靈骨”,原指釋迦佛荼毗后燒出的特異結晶體。舍利也稱為“堅固子”,它的特點是堅固如石,形態各異,有舍利珠、舍利塊等。舍利對于佛教信眾來說,是在釋迦佛涅槃后留下的象征著“佛”的圣物。佛經中對舍利的來由、功用予以高度重視:“舍利者,乃是無量六波羅蜜功德所熏……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10)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卷第四》,《大正藏》,第16冊,第354頁。因此,它在印度被教徒們供養在覆缽形的舍利塔下,受到信徒們的禮拜。舍利、舍利塔和舍利信仰傳播到中國后也得到了中國佛教信徒的尊崇信仰。
在研究殘損佛像瘞埋現象時,多位學者將佛像等同于舍利,視之為“感應舍利”“法舍利”。這既無佛教典據支持,又有混淆名相之弊。“感應舍利”“法舍利”在古代佛教典籍中均有其特指,不應根據學者個人理解隨意解說,而應根據古代佛教典籍的記載,結合現代考古材料予以準確的理解和解說。
1.殘損佛像瘞埋是“感應舍利瘞埋”嗎?
“感應舍利”又名“影身舍利”“影骨舍利”,是歷史上佛教徒用七寶制作的仿真舍利。唐代不空譯《如意寶珠轉輪秘密現身成佛金輪咒王經·如意寶珠品》云:“若無舍利,以金、銀、琉璃、水精、馬腦、玻梨眾寶等造作舍利。珠如上所用。行者無力者,即至大海邊,拾清凈砂石即為舍利。亦用藥草、竹、木根節造為舍利。”(11)不空譯《如意寶珠轉輪秘密現身成佛金輪咒王經》,《大正藏》,第19冊,第332頁。此即為古代佛教徒用金銀珠寶、水晶瑪瑙甚至沙石竹木等物制作影身舍利即“感應舍利”的佛典依據。在我國歷次考古發掘的地宮舍利中,均有影骨舍利、感應舍利的出現。如法門寺出土的4節佛指骨舍利中有1節靈骨舍利、3節影骨舍利。
尚永琪先生曾精辟地將古代佛教舍利信仰概括為3個不同階段:(1)佛陀涅槃“荼毗”后“八王分舍利”的“靈骨供養”時期;(2)阿育王建塔的“塔供養”時期;(3)中原地區的“感應舍利”時期。(12)尚永琪《佛舍利崇拜的地理困境與感應舍利之起源——對佛教偶像崇拜歷史分流之認識》,《文史哲》2016年第4期,第77頁。“舍利供養”在由印度大陸經過中亞傳播到中國的歷程中,經歷了“紀念性供養”“塔供養”和“感應舍利供養”這樣三個具有不同內涵的發展階段。這個過程是隨著佛教傳播的地理范圍的擴大,釋迦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靈骨”的不斷被分,一直到了“分無可分”的地步,于是脫離了“八王分舍利”“阿育王再分舍利”的“靈骨”分流軌道,衍生出通過感應或祈請的方式得到舍利的方法。至此,“舍利崇拜”的內涵其實已經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由“紀念”“懷念”“崇拜”發展成“證明”佛教或佛法合理性的一種工具性手段。(13)尚永琪《佛舍利崇拜的地理困境與感應舍利之起源——對佛教偶像崇拜歷史分流之認識》,第83頁。這為我們理解佛教史上“感應舍利”的出現提供了頗具啟發性的思路。
用“感應舍利”一詞指稱佛及高僧舍利,至遲在五代時期即已見其例證。后梁洛陽僧人行堅撰《惠光和尚舍利銘記》載:慧光和尚于“乾化……五年歲次乙亥三月庚辰朔十二日壬申遷化,十四日焚燒,得感應舍利。京都人眾皆頂謁。”(14)[清]陸心源編《唐文拾遺》卷50,《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0939-10940頁。這是記載五代后梁乾化五年(915)高僧圓寂后火化時獲得“感應舍利”。《冊府元龜·帝王部·崇釋氏第二》載:“明宗天成……四年八月澤州盤亭山千峰禪寺僧洪密狀奏當院創感應舍利塔一所,乞賜塔額,乃賜號為圓空之塔。”(15)[北宋]王欽若主編《冊府元龜》卷52,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581頁。這是記載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創建感應舍利塔。
宋、遼時期“感應舍利”更是頻繁見載于僧傳、地方志、碑記等文獻。北宋贊寧撰《宋高僧傳》中“大宋臨淮普照王寺懷德傳”記載:“屬今上遣高品李神福赍旛華上供,并感應舍利至,葬于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軀供養……”當朝皇帝派員持幡花上供,并奉感應舍利瘞埋于臨淮普照王寺,該寺僧人懷德遂發愿自焚身軀以供養感應舍利。贊寧特意記載此事發生的時間“乃太平興國八年(983)四月八日也”,即佛誕日。“一城之人無不悲悼者……使臣回奏,上為之動容焉”。(16)[北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23,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603頁。僧人懷德自焚供佛的壯舉不僅令當地民眾悲悼,也讓皇帝感動。這條記載很簡略,但其中透露出的歷史信息很重要,據此可知,“今上”(當指贊寧撰寫此書的太平興國七年(982)至端拱元年(988)期間在位的宋太宗)曾下令派員持幡花供養,并奉感應舍利至臨淮普照王寺瘞埋于塔下地宮中。這是宋代佛教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
南宋羅濬撰《寶慶四明志》記載四明(今寧波)有古寺金繩院,“觀察推官關杞記院有韶國師所得隋文帝感應舍利一顆,主僧德昇建甎浮圖于院前以奉之。”(17)[南宋]羅濬撰《寶慶四明志》卷17,《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74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5303頁。所謂“隋文帝感應舍利”當指隋文帝于仁壽年間向全國三十州頒賜之舍利。遼代咸雍八年(1072)《特建葬舍利幢記》載,“涿州新城縣衣錦鄉曲堤里,邑眾……同去南北朝驛路上,設無遮之飯、濟求戒之人。益勵虔誠,潛膺多福。于設飯之所,遂復感應舍利一粒,不踰數日,大小自至二十余粒。……若起塔則止藏其舍利,功德惟一。建幢則兼銘其秘奧,利益頗多。況塵揚影覆,惡脫福增,豈不謂最勝者歟?于是同鳩凈賄,恪募良緣,石采瓌貞,匠徵郢俊,建尊勝幢葬□如來首于當村精舍內……”(18)向南編《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50-351頁這是記載遼代時涿州地方邑眾為瘞埋感應舍利而建尊勝佛幢。由上述可見,從五代至宋遼時期,均以“感應舍利”指稱佛及高僧舍利。
山東臨朐縣明道寺出土的宋代景德元年(1004)《沂山明道寺新創舍利塔壁記》是現存中國古代較早明確記載了瘞埋殘損佛像和“感應舍利”之事的一篇碑記文獻(圖1),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也被多位學者視為論證“佛像等同舍利安葬說”“感應舍利瘞埋”“法舍利瘞埋”說的最直接得力依據。其實在筆者看來,其中顯然存在理解的誤區。

圖1 《沂山明道寺新創舍利塔壁記》拓片(采自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
該碑記載:“今有講《法花經》僧覺融,本霸州人也,聽/學僧守宗,本莫州人也,早悟浮生,偶游斯地,睹石鐫壞像三百余/尊,收得感應舍利可及千錁(顆)。舍衣建塔,為過去之遺形;化詔□(有?)/緣,冀當來之佛會。此乃地穿及泉,甃若玉堅,壘成金藏,熔/寶作棺,固至地平,方命良工砌壘,塔形雖小,勝事甚多!……”(19)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附錄《沂山明道寺新創舍利塔壁記》,《文物》2002年第9期,第82-83頁。上引碑記提供的有價值信息至少有以下幾點:1.創建明道寺舍利塔的發起人是分別來自霸州、莫州的覺融、守宗2位僧人;2.覺融、守宗二僧在臨朐做了二件事:一是看見殘損佛像三百余尊(將其收集起來),又收集了感應舍利將近千錁(顆),二是帶頭捐資創建了佛塔;3.在地面以下挖掘、砌筑了堅固的地宮,在地面以上砌壘佛塔;4.將殘損佛像和感應舍利埋入塔的地宮,“熔寶作棺”提示是將感應舍利裝入用寶物制作的棺材形的容器中。有感于這是非同尋常的功德之舉,故碑記中贊嘆:“塔形雖小,勝事甚多!”
按照《沂山明道寺新創舍利塔壁記》的明確記載,該塔地宮中理應埋藏有殘損佛像和感應舍利。有關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清理結果,兩篇清理報告分別說明:“地宮內共清理出大小佛像碎塊1200余塊。”(20)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文物》2002年第9期,第65頁。“地宮內共清理出大小佛像碎塊600余塊,特別小的碎塊數百塊”(21)臨朐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石造像清理報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海岱考古》第9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83頁。。合計來看,與碑記中記載“睹石鐫壞像三百余尊”基本吻合。但令人遺憾和錯愕的是清理報告并未言及該塔地宮中是否有舍利瘞埋。據考古清理報告,明道寺舍利塔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還保存第一層塔室。該塔地宮1965年時曾被當地群眾打開取出部分埋藏物后又將其封堵。1982年春文物普查時發現。1984年春因村民建房地宮第二次被打開,同年10月由臨朐縣文化館對該塔地宮進行搶救性清理。(22)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第64頁;臨朐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石造像清理報告》,第281頁。所以有可能該塔地宮在清理前,“熔寶作棺”的舍利容器就已被人當做寶物取出盜走,故清理報告中只字未提舍利容器及舍利。
對于明道寺舍利塔碑記中“收得感應舍利可及千錁(顆)”一句話,學者們出現了不同的理解。崔峰先生以此句作為古人把殘件佛像作為“感應舍利”的依據,(23)崔峰《佛像出土與北宋窖藏佛像行為》,第86頁。顯然是一種誤解。筆者認為,明道寺舍利塔碑記中所記“收得感應舍利可及千錁(顆)”,是記載覺融、守宗2僧收集了佛的感應舍利將近千顆瘞埋于明道寺舍利塔地宮。其情形正類似于甘肅涇川大云寺遺址出土的銘文磚所記:“大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龍興寺曼殊院念《法花經》僧云江、智明同收諸佛舍利約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薩殿內葬之。”(2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涇川縣博物館《甘肅涇川佛教遺址2013年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4期,第73頁。考古專家在涇川大云寺遺址發現陶棺中漆盒內放置琉璃瓶3個,均為球形,長頸,其中一個琉璃瓶底部破裂,部分舍利散落,另外兩個琉璃瓶有裂紋。“目前清理出散落的舍利約1777粒,舍利大小如米粒,呈白色結晶狀,晶瑩剔透,質地為石英砂”(2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涇川縣博物館《甘肅涇川佛教遺址2013年發掘簡報》,第72頁。。(圖2)

圖2-1 甘肅涇川大云寺遺址出土舍利瓶 圖2-2 甘肅涇川大云寺遺址出土舍利子(采自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肅涇川佛教遺址2013年發掘簡報》)
甘肅涇川佛教遺址發現的宋代佛舍利是經過考古專家科學發掘出土的宋代“造作舍利”即“感應舍利”之實例,它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碑記中所記的“感應舍利”其實也是指造作的影身舍利。
太平興國八年,宋太宗派員到臨淮普照王寺瘞埋感應舍利于塔下地宮。21年后的景德元年,山東臨朐明道寺僧人覺融、守宗創建地宮瘞埋感應舍利。30年后的大中祥符六年,甘肅涇川龍興寺僧人云江、智明收集佛舍利瘞埋于寺院殿堂地下。在宋代諸如此類的舍利瘞埋事件尚有許多。由于宋太宗以皇帝之尊派員到地方供奉、瘞埋感應舍利,這對于宋代朝野重視感應舍利瘞埋、供養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流風所及,宋代各地僧人都熱衷于感應舍利瘞埋、供養,由此形成了宋代感應舍利瘞埋的熱潮。
2.殘損佛像瘞埋是“法舍利瘞埋”嗎?
在研究宋代殘損佛像群瘞埋現象的性質時,高繼習先生在“舍利瘞埋說”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法舍利瘞埋”的觀點。他認為現有證據表明,臨朐明道寺將殘損佛像瘞埋于地宮是有明確記載的出現最早的案例,將其稱之為“明道寺模式”,這是頗有創見的觀點。他又推理該模式產生的佛教義理依據是“法舍利瘞埋”,(26)高繼習《宋代埋藏佛教殘損石造像群原因考——論“明道寺模式”》,第500頁。其論證的主要依據是:“明道寺《舍利塔壁記》中‘偶游斯地,睹石鐫壞像三百余尊,收得感應舍利可及千錁’之語,似是說感應舍利是因殘損佛像而生的,從而更確定殘造像的法舍利性質。”(27)高繼習《宋代埋藏佛教殘損石造像群原因考——論“明道寺模式”》,第505頁。顯然,高先生在論述中采用了比較審慎的態度,“似是說感應舍利是因殘損佛像而生的”一句表明了推測而并非斷定的語氣。的確,筆者前文已經闡明《沂山明道寺新創舍利塔壁記》中“收得感應舍利可及千錁(顆)”是指瘞埋佛的感應舍利,并不是說把殘損佛像視作感應舍利。如同崔峰先生一樣,高先生將殘損佛像視作感應舍利的依據不存在,所以“感應舍利瘞埋說”難以成立。高先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的“法舍利瘞埋說”也同樣難以成立。
“法舍利”又稱“法身舍利”,特指佛經。《法華經·法師品》云:“若經卷所住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繒蓋、幢幡、伎樂、歌頌,供養恭敬,尊重贊嘆。若有人得見此塔,禮拜、供養,當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28)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花經》,《大正藏》,第9冊,第31頁。此即把佛經安置于佛塔等同于舍利供養的佛典依據。《大唐西域記》卷九載:“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于內,常修供養。”(29)[唐]玄奘述,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大正藏》,第51冊,第920頁。由此可見把佛經置于塔中作為“法舍利”,是源自印度佛教的一種供養行為。
據此可知,把殘損佛像瘞埋視作“法舍利瘞埋”是與佛教義理、佛教典籍不相吻合的。
三、從佛教史實看殘損佛像瘞埋是與舍利瘞埋既相關聯又各自獨立的兩種佛教供養活動
從中國古代佛教史來看,殘損佛像瘞埋與舍利瘞埋是被佛教信徒作為二種既相互關聯又各自獨立的佛教供養功德活動,是二種既互有交集關系又各自獨立發展的佛教歷史文化現象。
1.舍利瘞埋是中國古代一直流行、具有悠久歷史和不斷發展演變的一種佛教圣物崇拜活動。
我國舍利供奉自南北朝逐漸興起,隋唐時期達到鼎盛,這與當時的譯經盛行、寺塔興建、宗派興盛、朝野重視等相關。唐代皇家對法門寺佛舍利的多次迎奉供養,更是把舍利崇拜活動推向巔峰。至宋代時,舍利崇拜出現了中國化、世俗化、大眾化的趨勢。到元明清時期佛舍利崇拜活動依然存在,但總體上已趨于衰落,無復往昔之盛況。
關于中國古代舍利瘞埋,學者們已經做過深入的考察研究,發表過大量研究論著,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從本文研究所涉時代范圍來看,廖望春女士對宋代舍利“泛化”的研究值得關注。廖女士系統地整理和研究了發現于不同地域的宋代78座佛塔塔基中的舍利實物資料,探討了舍利信仰所依存的二種物質形態的變化,即舍利形態的演化和佛舍利塔的功能變化。由此提出了宋代舍利信仰的“泛化”問題。繼而通過對古代舍利遺物的形態變化分析,闡述了自宋代開始,舍利信仰已從原初以圣骨崇拜為核心的印度式信仰,泛化為具有象征意味的中國式的符號物信仰。進而指出了“泛化”的原因與晚唐至宋代佛教中國化與世俗化的時代背景直接相關。(30)廖望春《宋塔舍利發現與舍利信仰泛化的研究》,《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4期,第157頁。廖女士關于宋代舍利信仰泛化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宋代舍利信仰的發展變化趨勢。廖女士在其繪制的“舍利種類圖”中,將舍利分為“真身舍利”“法身舍利”二大類,在“法身舍利”后備注佛經、佛像,似乎有將佛像納入舍利“泛化”范圍的意圖,顯示出邏輯思考的某種搖擺性。但她在全文論述中卻只字未提佛像,她總結宋代舍利泛化說:“通過研究發掘于宋代佛塔中的舍利實物,發現源引自印度的佛祖舍利,已為大量其它物質形式的‘泛化舍利’所填充。這些物質形態的變化包括大德高僧的身骨舍利和駱駝骨、象牙骨、珠玉、石英砂石等不同類型的其它碎身舍利,也包括法身舍利(經卷)和全身舍利。”(31)廖望春《宋塔舍利發現與舍利信仰泛化的研究》,第161頁。顯示她終究遵循了古代佛教典籍對舍利概念的界定,尊重了古代佛教史實,并未將舍利瘞埋與佛像瘞埋混為一談。
2.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宋代、西夏、元代乃至清代曾出現過殘損佛像瘞埋與舍利瘞埋發生密切交集關系的現象,但只能說明二者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曾經在瘞埋方式上出現過重合、交集,并不能證明殘損佛像瘞埋就等同于舍利瘞埋。
殘損佛像瘞埋與舍利瘞埋發生密切的交集關系主要體現在下述兩個方面:
一是殘損佛像被瘞埋在以往慣常瘞埋舍利的佛塔的地基、塔室、天宮特別是地宮中。如濟南市縣西巷唐宋開元寺地宮遺址發現殘損的佛、菩薩、觀音、供養人等石刻像和泥塑近50尊,被有規律地排列在地宮中央“壇”的四周。(32)崔大庸、高繼習《濟南老城區發現地宮與佛像窖藏》,《文物天地》2004年第5期,第50-57頁。寧夏賀蘭縣西夏所建宏佛塔的天宮中發現西夏絹彩佛畫、泥塑佛頭像、羅漢頭像、西夏文佛經木雕版殘塊2000余塊、西夏文書殘頁等文物。(33)王瑞《宏佛塔建筑成就及出土文物價值探論》,《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第97-101頁。1910年王圓箓道士募資在莫高窟建造千像塔,將莫高窟洞窟中殘損的佛像瘞埋在塔中。(34)王慧慧、梁旭澍、蕭薇、張海博《〈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記〉、〈敦煌千佛山皇慶寺緣簿〉錄文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14年第5期,第64-70頁。
二是殘損佛像與舍利一同瘞埋于佛塔的地基、地宮中。如根據山東臨朐縣原明道寺舍利塔出土《沂山明道寺新創舍利塔壁記》可知于北宋初景德元年(1004)在塔的地宮內同時瘞埋了殘損佛像300余尊和感應舍利將近1000顆。安徽亳縣咸平寺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利用地宮之上的塔基空間埋藏殘造像碑和造像,該遺址出土《釋迦如來磚塔記》碑刻明確記載當時是將這批佛像“瘞諸基下”,地宮內石棺中存有數十枚宋代銅錢和一些五色石子(舍利子)。(35)韓自強《安徽亳縣咸平寺發現北齊石刻造像碑》,《文物》1980年第9期,第56-64頁。
上述案例表明,在古代某些時期,由于對殘損佛像瘞埋的高度重視,佛教僧俗信徒將殘損佛像瘞埋在慣常用于瘞埋佛舍利的佛塔中。特別是宋代時期集中出現了多個將殘損佛像與舍利一同瘞埋在佛塔地基、地宮的案例,由此造成當時人們將殘損佛像等同于舍利一同瘞埋的錯覺。其實這只是表明某些時期對殘損佛像和舍利瘞埋的方式上出現了重合的現象,但并不表明古代僧俗信徒就認為殘損佛像等同于舍利,將二者混為一體。
黃盼女士用考古學類型學的方法全面系統地研究了古代殘損佛像瘞埋現象,分為A、B、C三類,其中在對C2類即殘損佛像與舍利地宮相關的6個案例進行考察分析后得出結論:“C2類埋藏是佛教信徒發愿營造舍利塔或是寺院利用地宮現成的空間,將無法修復或不再修復的破損佛像置于塔下供養的行為,亦為佛像瘞埋,雖均與舍利地宮相關,但殘損佛像并不等同于舍利,是兩種瘞埋行為的結合,多發生于北宋以后。”(36)黃盼《中國中古時期佛像埋藏的考古學研究》,《華夏考古》2021年第5期,第82頁。黃女士的考察分析非常專業精準,筆者贊同她的觀點。
3.從長時段、廣區域的視野來看,殘損佛像瘞埋案例出現在山東、河北、山西、河南、陜西、四川、安徽、江蘇、寧夏、甘肅等不同省區,時代跨度從北朝晚期開始,歷經隋唐,到北宋時期達到高潮,直至西夏、元、明、清時期仍有其余緒,表明殘損佛像瘞埋是中國古代較長歷史時期內在廣大地區存在的現象。
根據筆者收集整理的殘損佛像瘞埋案例71例統計,其中在窖藏坑中瘞埋的占52例,占比高達73%,表明殘損佛像瘞埋是以埋入地下窖藏坑為主要形式,大多數是出現在寺院建筑之下、寺院附近的窖藏坑中。
其中幾次大規模的古代窖藏殘損佛像的發現尤為引入注目。如1954年、1955年在河北曲陽縣修德寺遺址發現地下窖藏坑,前后兩次發現的石刻造像共編號2659號。其中有紀年銘造像247軀,自北魏神龜三年(520)迄唐天寶九年(750),其間230年,歷經北魏、東魏、北齊、隋、唐5代,而以東魏、北齊和隋代造像居多。(37)羅福頤《河北省曲陽縣出土石像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5年第3期,第34-38頁;李錫經《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發掘紀》,《考古通訊》1955年第3期,第38-44頁。1957年,沁縣城東北30公里的南涅水村農民發現佛像造像窖藏,出土石刻造像1100余件,包括單體造像、造像石塔、造像碑銘三大類型,其中以造像塔為主,約400余件,單體造像近300尊。據造像題記和藝術風格判斷,雕刻年代為北魏太和年間至北宋天圣九年(477-1031),相繼延續北魏、東魏、北齊、隋、唐、宋六個朝代約500余年。(38)郭海林、李春蘭《南涅水石刻》,《文物世界》2001年第6期,第61-63頁;曹雪霞《山西省沁縣南涅水石刻館》,《文物世界》2012年第2期,第3-5頁。1996年,青州市故龍興寺遺址發現一東西長8.7、南北寬6.8米,面積近67平方米的大型窖藏坑,造像排放有序,大致按上、中、下三層排列擺放,出土佛頭像144件、菩薩頭像46件、帶造像身或半身造像頭36件、其他頭像10件、造像殘身200余件、殘經幢3件。從造像的時代分析,這批造像從北魏,歷經東魏、北齊、隋、唐、北宋,跨越時間長達500余年,其中尤以北魏、北齊時期的造像出土數量最多。(39)山東省青州市博物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簡報》,《文物》1998年第2期,第4-15頁。2012年在甘肅省涇川縣城關鎮共池村(古代大云寺遺址)發掘佛教造像窖藏坑2個,共出土造像260余件。其中有造像碑、造像塔(龕)、背屏式造像、單體圓雕造像等,其中單體圓雕造像數量較多。造像年代歷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時期,延續時代較長。(40)吳葒《甘肅涇川佛教遺存調查發掘獲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14年1月31日第8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涇川縣博物館《甘肅涇川佛教遺址2013年發掘簡報》,第54-78頁。上述表明,殘損佛像瘞埋是在中國古代廣大地區長期獨立存在的一種佛教供養活動。
四、結論:殘損佛像瘞埋不能視同于舍利瘞埋,殘損佛像瘞埋是與舍利瘞埋并行的佛教三寶供養活動
以上筆者根據佛教義理、佛教典籍,并結合考古材料論述證明,將殘損佛像視為“感應舍利”是對古代文獻資料的誤解,將殘損佛像瘞埋視同于舍利瘞埋,是對古代佛教歷史文化現象的錯誤解說。在古代人的概念中,顯然是將殘損佛像與舍利明確區分開來的,是把殘損佛像瘞埋與舍利瘞埋當做二種佛教供養活動區別對待的。
筆者又根據佛教史實來論述證明,舍利瘞埋與殘損佛像瘞埋是二種既相互關聯又各自獨立的佛教供養功德活動,是二種既互有交集關系又各自獨立發展的佛教歷史文化現象。佛舍利瘞埋是從南北朝時期開始、隋唐達到鼎盛、一直貫穿中國古代的佛教崇拜活動,而殘損佛像瘞埋是伴隨滅佛運動從北朝晚期開始,到宋代達到高潮、延續至元明清的佛教供養活動。在古代某些時期特別是宋代,由于朝野上下佛教信徒對歷經以往“三武一宗”滅佛運動后造成大量殘損佛像的處置特別重視,在全國許多地區特別是滅佛運動的重災區如山東、山西、河北等地組織實施了大規模的殘損佛像窖藏瘞埋活動,個別地方如山東臨朐明道寺、安徽亳縣咸平寺等處實施了將殘損佛像瘞埋在慣常瘞埋佛舍利的佛塔中,甚至與佛舍利一同埋入佛塔地宮這樣超常規的瘞埋活動,將殘損佛像瘞埋活動推向巔峰。但殘損佛像與佛舍利一同埋入地宮,只是表明這兩種瘞埋活動在瘞埋形式上出現重合,發生了密切的交集,并不意味著殘損佛像就等同于舍利。
總之,把殘損佛像視為“感應舍利”,把殘損佛像瘞埋等同于佛舍利瘞埋的觀點,既無佛典依據,也缺乏史實支持。
筆者認為,在有關殘損佛像瘞埋性質多種觀點中,以楊泓先生的說法最為接近史實并能深入揭示其本質。楊泓先生認為:北宋時期,青州地區寺院盛行一種隆重的法會,寺院僧人將早年滅佛活動中損壞佛像或經年累月破舊的佛像集中起來,然后舉行隆重的儀式,將它們埋葬起來,以積累功德。(41)楊泓在《梵音凈土之青州佛像之謎》電視節目中講述觀點,見《探索發現》欄目《考古中國》第五部,中央電視臺10頻道,2004年6月9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7411J7Ut/?p=19)。筆者贊同楊泓先生的觀點,認為在中國古代廣大地區普遍存在的將殘損的佛造像有意識地、有計劃地集中起來予以禮儀性瘞埋的行為其實屬于佛教徒的三寶供養行為之一——佛寶供養。對此筆者曾在2016年發表的《中國古代佛教三寶供養與“經像瘞埋”——兼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原因》(42)張先堂《中國古代佛教三寶供養與“經像瘞埋”——兼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原因》,第206頁。一文已予以論述,請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