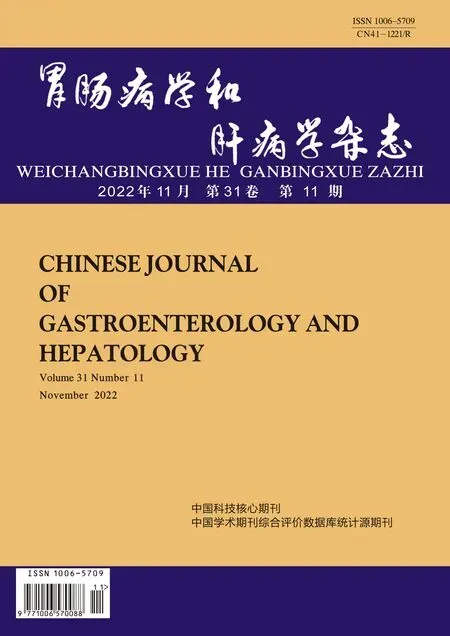FXR與腸黏膜炎癥在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發生發展中的作用
王廣祥, 崔立紅, 董昌昊, 冼 銳
1.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消化內科,北京 100853;2.南方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
腸易激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種以反復腹痛發作伴排便習慣改變為特征的最常見的功能性腸病之一。根據糞便性狀將IBS分為四型:腹瀉型IBS(IBS-diarrhea, IBS-D)、便秘型IBS(IBS-constipation, IBS-C)、混合型IBS(IBS-mixed type, IBS-M)、不定型IBS(IBS-unclassified, IBS-U)[1],此外,IBS還包括非特異性和感染后IBS(postinfectiou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PI-IBS)。根據最近一項由羅馬基金會專家組發布的關于功能性胃腸病的全球流行病學互聯網調查顯示,IBS的全球患病率為3.6%~4%,我國IBS的患病率約為2.3%,其中IBS-D仍是最常見的IBS亞型之一[2]。IBS的患者年齡范圍很廣,可以發生于任何年齡,其中以女性居多,男女比例約為1∶1.46[3-4]。據估計,與IBS相關的年度直接和間接成本在歐洲高達80億歐元,在我國則高達1 230億人民幣,在美國則超過100億美元。IBS目前主要是根據患者的主要癥狀進行診斷和治療[5]。然而,目前IBS的治療效果不佳,病情容易反復,導致患者的生活質量下降,嚴重影響了患者的學習與工作。因此,明確IBS的確切機制可為其更準確地診斷和更有效的治療帶來益處。
1 IBS與腸黏膜炎癥
目前,IBS的潛在病理生理學機制尚不清楚,考慮為多因素共同作用導致。本課題組前期對于IBS的臨床特點和發病機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表相關文章20余篇,包括腸道感染、腸黏膜低度炎癥、腸道通透性異常、腸道微生態失調、負性社會心理因素、飲食因素等[6-12]。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腸道動力異常和腦-腸軸功能異常。近年來不斷有研究者提出了腸道炎癥參與IBS病理機制的假設,并圍繞其做了大量研究[13]。
IBS與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顯微結腸炎(microscopic colitis, MC)有許多的癥狀重疊[14-15],并且一部分IBD臨床緩解期的患者常常有IBS樣癥狀出現[16]。這說明三者之間可能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機制。許多中藥在深入研究的過程中也被發現可以通過抗炎來緩解IBS[17]。本課題組前期研究結果也表明,腸道菌群失調與IBS-D發病密切相關,并發現調節腸道菌群可以通過抑制NF-κB信號通路的激活抑制IBS-D患者癥狀及腸黏膜炎癥[18]。本課題組前期IBS-D大鼠模型表明,TLR-4和NF-κB通路激活在IBS-D發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IBS-D大鼠腸黏膜中TLR-4、MyD88、NF-κB-TNF-α較對照組升高,IL-10較對照組降低,且IBS-D大鼠腸黏膜通透性較對照組升高。利用TLR-4-NF-κB通路抑制劑PDTC可下調炎癥因子的含量并緩解腸黏膜的破壞。腸道因每天都要與外界抗原、病原體接觸而保持“生理性炎癥”的狀態。但IBS患者相對健康對照組促炎細胞因子表達、黏膜中浸潤的免疫細胞數量和糞便鈣衛蛋白濃度均增加[19-21]。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未發現IBS腸黏膜固有層中免疫細胞增加[22]。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方面IBS是一種異質性疾病,另一方面這也與活檢部位的選擇有關。目前,胃腸道感染已經確定為IBS的強危險因素。約1/10的胃腸道感染患者在感染恢復后表現為IBS,這些患者在感染結束后仍存在慢性腹痛以及菌群失調,進一步研究發現其結腸黏膜通透性和結腸敏感性增加,并伴有腸黏膜低度炎癥。其中,90%的PI-IBS患者主要以混合型和腹瀉型為主[23-24]。
IBS患者腸道菌群的組成與健康人不同,表現為促炎的細菌相對豐度增加,而具有抗炎的細菌相對豐度降低。腸道菌群中也有一些特定的菌種與IBS癥狀有關,如產硫細菌被認為與患者的結腸敏感性增加有關。將這部分菌群移植至無菌動物中,也發現這些動物對結腸擴張的敏感性增加。另外,IBS的小鼠模型中發現普拉梭菌的相對豐度下降,而普拉梭菌不僅可以通過利用膳食纖維產生短鏈脂肪酸來維持腸道穩態,還具有抗炎和緩解結腸高敏感性的作用[25]。布拉氏酵母菌等益生菌也可以通過抗炎來緩解IBS-D[18, 26]。
近年來“腸漏”在IBS發病機制中所起的作用也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腸漏”是指腸上皮細胞間的細胞連接受損引起的腸道屏障功能障礙。它可以導致腸道中的細菌及其代謝產物、食物及毒素等進入穿過腸壁,激活腸黏膜上皮下的肥大細胞和巨噬細胞,促進細胞因子的產生并損傷腸神經或使其過度興奮[27]。IBS-D患者結腸組織中識別LPS 的TLR-4和識別鞭毛蛋白的TLR-5表達增加,是由于存在腸屏障功能受損和腸道通透性增加,增加了腸道細菌侵犯宿主的機會,從而導致患者處于慢性低度炎癥、內毒素血癥,和血液中促炎細胞因子如TNF-α、IL-1β和IL-6的水平增加[28]。在這個慢性腸道黏膜低度炎癥的過程中,由于免疫細胞與腸神經之間的密切聯系,導致神經與免疫之間的相互作用發生紊亂,從而引起IBS患者的腸道感覺及功能障礙相關癥狀。研究指出,日常飲食可通過促進腸道黏膜炎癥來引起IBS[29]。低FADMAP飲食,即低可發酵性寡糖、二糖、單糖和多元醇,可能通過抗炎來改善IBS[30]。
腸黏膜低度炎癥也可能是IBS的病理生理機制的基礎,即通過促進內臟高敏感性[31]和增加腸道通透性[32]來促進IBS的發生發展。有研究指出,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 CRF)-TLR-4-促炎細胞因子信號通路可以通過促進“腸漏”和內臟高敏感性從而在IBS的發病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33]。腸黏膜炎癥可以通過增加促炎細胞因子水平,進而誘導肌球蛋白輕鏈激酶的轉錄和激活,從而導致細胞骨架分解,Occludin和ZO-1的丟失。跨膜蛋白的降解和緊密連接疏松并形成間隙均導致了腸道上皮細胞通透性增加。利福昔明可以通過改善腸道中菌群的多樣性,防止菌群和病原體對腸道的粘附和入侵,從而減少上皮細胞炎癥,改善腸道屏障功能,并減少內臟痛覺過敏[34]。
關于腸黏膜炎癥相關分子機制的研究在近年來也有很多發現,為IBS的發病機制進一步提供了大量依據。研究表明,腫瘤壞死因子相關受體-6(TNF receptor associated factor 6,TRAF6)不僅可以通過依賴性MyD88通路激活NF-κB,進而誘導一系列促炎細胞因子、趨化因子、黏附因子的表達,從而參與誘導IBS-D低度炎癥的發生[35]。另外TRAF6表達的增加可以促進CBS(cystathionine β synthase)的表達從而參與慢性內臟疼痛[36]。熱休克蛋白HSP-27可通過抑制IκB-α的磷酸化進而抑制NF-κB的激活,從而抑制腸黏膜細胞的炎癥反應及凋亡[37]。色氨酸的代謝在腸道菌群與腸道免疫之間的聯系在近年來也受到廣泛關注。色氨酸可以通過腸道菌群分解為吲哚和吲哚衍生物,進而激活ArH受體表達,從而促進IL-22的表達、調節促炎細胞因子轉錄和腸上皮細胞之間的淋巴細胞和固有免疫細胞功能。而IDO1不僅是色氨酸代謝中犬尿氨酸途徑的限速酶,還可以調節T細胞,從而在腸道免疫中發揮重要作用。在消化道中,犬尿氨酸途徑中的產物也可能是促炎(興奮性毒性喹啉酸)和抗炎(神經保護性犬尿酸)之間平衡的基礎,通過改變神經元興奮性來影響腸道感覺和運動功能[38]。5-HT合成過多可導致腸黏膜低度炎癥、內臟高敏感性和胃腸動力增加,導致IBS-D的發生[39]。盡管目前關于腸黏膜炎癥機制的研究有很多,但其具體分子機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2 IBS-D與膽汁酸
膽汁酸在肝臟中利用膽固醇合成后儲存在膽囊,通過飲食過程刺激再從膽囊中釋放進入腸道,95%的未結合膽汁酸通過回腸末端重吸收進入門靜脈重新回到肝臟。膽汁酸在消化道中的主要功能是參與乳化脂質并促進其吸收的作用。不僅如此,膽汁酸本身還具有殺菌作用,從而起到調節腸道菌群的作用。
約有25%的IBS-D患者存在膽汁酸腹瀉(bile acid diarrhea, BAD),表現為糞便中膽汁酸總量及初級膽汁酸的比例增加[40]。初級膽汁酸中鵝脫氧膽酸(chenodeoxycholic acid, CDCA)可以促進腸道水和氯離子的分泌,而膽酸(cholic acid, CA)則不僅可以促進水和電解質分泌,還可以加速結腸傳輸。另外,有研究指出,IBS-D患者的血清中反映膽汁酸合成的血清C4(7-羥基-4-膽固酮-3-酮)水平升高,提示這部分IBS-D患者存在膽汁酸合成增加。回腸末端膽汁酸的攝取率隨著膽汁酸合成增加而存在代償性升高。這導致腸黏膜上皮細胞中的膽汁酸濃度升高,損傷腸黏膜上皮細胞,進而引起腸黏膜上皮炎癥[41]。腸黏膜炎癥削弱了腸黏膜對腸道中水和溶質的吸收能力,進而引起腹瀉的發生[42]。
此外,膽汁酸還是腸道免疫系統的重要調節劑。一方面膽汁酸可以直接激活Kupffer細胞釋放炎癥細胞因子。另一方面,膽汁酸還可以通過結合受體來抑制炎癥、防止病原入侵和保持細胞完整性,并進一步刺激產生激素包括FGF19、GLP-1和PYY來調節腸道穩態[43]。膽汁酸作為內源性配體結合其相關受體,包括法尼醇X受體(Farnesoid X receptor, FXR)、G蛋白偶聯膽汁酸受體5(takeda-G-protein receptor 5, TGR5)、孕烷X受體(pregnane X receptor, PXR)、維生素D3受體(vitamin D3 receptor, VDR)和組成性雄烷受體(constitutive androstane receptor, CAR)。其中,FXR作為最先發現的膽汁酸受體已有廣泛的研究。
3 膽汁酸與FXR在IBS-D中的作用
FXR又稱NR1H4/Nr1h4,是膽汁酸核受體之一,主要在肝臟和回腸表達。FXR在哺乳動物中包括兩個家族,FXRα和FXRβ,由于FXRβ在人類和靈長類動物均呈現假基因,因此在人體中發揮作用的是FXRα[44]。FXR在維持膽汁酸動態平衡、代謝性疾病、胃腸道及肝臟炎癥和癌癥的發生中具有重要影響[45]。肝細胞中膽汁酸的從頭合成途徑受到肝腸循環中膽汁酸池的直接反饋抑制,而FXR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主要作用。膽汁酸通過被動擴散或主動轉運的方式穿過細胞膜進入細胞并激活FXR。激活后的FXR轉移至細胞核中,并與類視黃醛受體(retinoid X receptor, RXR)結合形成異源二聚體,再結合相應DNA上的激素反應元件,從而調節基因表達[46]。肝細胞中,FXR通過誘導非典型核受體微小異源二聚體(smass heterodimer partner, SHP)的表達來抑制膽汁酸合成過程中的限速酶CYP7A1的轉錄。另外,膽汁酸在回腸中激活FXR后,刺激回腸分泌FGF19通過血液循環作用于肝細胞抑制膽汁酸的合成[47]。膽汁酸對FXR的激動效應也隨著其種類的不同而不同,具體表現為CDCA>DCA>LCA>CA[48]。除了抑制膽汁酸的合成,FXR在膽汁酸的運輸及重吸收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FXR不僅可以通過SHP抑制NTCP來抑制肝臟對膽汁酸的攝取,還可以上調BSEP和MDR3的基因表達來加速肝臟中的膽汁酸向膽管的排泄,從而防止膽汁淤積性肝病。腸道中膽汁酸含量增加可以導致腸道中電解質及液體的分泌增加、結腸傳輸加快和增大結腸收縮振幅,從而導致腹瀉癥狀的發生或加重[49]。FXR的激活除了可以調節膽汁酸代謝,還有抑制炎癥的作用[50]。根據動物實驗研究指出,FXR基因敲除小鼠隨著年齡的增長相對同源小鼠會更容易發展成亞臨床炎癥[51]。
4 FXR在炎癥反應中的作用
除此之外,FXR信號通路在機體的免疫調節中具有重要作用,參與多種器官的抗炎效應。GW4064(一種合成的FXR配體)可以通過抑制巨噬細胞的活化來緩解LPS誘導的肝炎[52],還可以通過上調FXR表達來改善LPS通過TLR4/p38 MAPK途徑介導的肝損傷[53]。在LPS誘導的急性腎損傷小鼠中,奧貝膽酸(obeticholic acid,OCA)預處理通過阻斷腎臟皮質中的腎小管上皮細胞中NF-κB的p65和p50亞基的核轉位,抑制了腎臟炎癥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表達[54]。在肺缺血/再灌注損傷的小鼠模型中發現,FXR可以通過抑制NF-κB的核易位,從而降低COX-2、IL-1β、IL-6、TNF-α的表達[55]。
FXR可以通過SHP依賴和非依賴的機制調節多個參與炎癥的基因的表達。SHP無DNA結合域,因此通常作為共抑制因子通過蛋白質-蛋白質相互作用來發揮其活性。SHP是通過穩定抑制復合物與趨化因子C-C基序配體2(chemokine C-C motif ligand 2, CCL2,又稱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啟動子的結合,從而抑制了NF-κB p65亞基的表達式和招募[51]。在LPS誘導的敗血癥動物模型中,巨噬細胞中的FXR通過激活下游靶基因SHP表達抑制NLRP3炎癥小體的活化,同時參與抑制CASP1的激活和招募核受體輔抑制因子1(nuclear receptor corepressor 1,NCOR1)復合體來抑制NF-κB,從而減少IL-1β、IL-18等細胞因子的產生[56]。NCOR1復合體在基礎狀態下可以通過結合這些基因的啟動子上,從而阻止NF-κB的結合,進而使它們處于轉錄失活狀態。另外,在巨噬細胞中,FXR還可以通過非依賴SHP機制抑制炎癥小體。炎癥小體是一類細胞質中的多蛋白復合體,包括NLRP1、NLRP3、NLRC4、AIM2家族,可以感知內源性和外源性病原相關分子模式或危險相關的分子模式(PAMPs和DAMP)。其中,NLRP3是最具特征性的炎性小體之一,它的過度激活在不同的炎癥性疾病中均被檢測到[51]。FXR可以通過抑制NLRP3炎癥小體誘導的炎癥改善抑郁模型小鼠的腦功能異常[57]。在小鼠模型實驗中,FXR的激活通過下調TNF-α的表達和減少腸道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的分化和激活來減輕結腸炎的嚴重程度。在急性肝炎的嚙齒動物模型中,INT-747(FXR的激活劑)抑制了NKT細胞的募集。綜上所述,FXR通過SHP依賴和非依賴的機制對單核/巨噬細胞、DC和NKT細胞發揮負調節作用,這些機制通常涉及對NF-κB通路的負調控[51]。
5 FXR與NF-κB的相互作用在IBS-D腸黏膜炎癥中的作用
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提示FXR對腸道免疫調節具有重要作用[58]。FXR抑制炎癥的機制最終很多是通過對NF-κB的抑制來實現的。FXR的激動劑可以抑制肝細胞和腸道中的NF-κB下游炎癥靶基因的表達,減少促炎因子如IL-1β、TNF-α的產生[59]。FXR還可通過抑制NF-κB與目的基因的結合和TLR-MyD88-NF-κB通路的激活,抑制腸道炎癥反應[35]。FXR不僅可以抑制炎癥,也是炎癥反應作用的目標。在DSS處理后的結腸炎小鼠中觀察到FXR的mRNA和表達顯著降低[60]。在急性炎癥反應中,LPS給藥后8 h就可以顯著降低小鼠肝臟中FXR的mRNA,并且通過EMSA表明,LPS處理顯著降低了DNA與FXR響應元件(IR1)的結合活性。除了細胞因子,還有研究觀察到NF-κB的激活在體外和體內均可抑制FXR介導的相關基因的表達[61]。因此,FXR與NF-κB信號通路之間存在相互抑制作用。一方面,FXR的激活通過減少NF-κB與其DNA結合序列的結合而特異性地抑制NF-κB誘導的炎癥反應。另一方面,FXR的轉錄活性被LPS誘導的NF-κB激活所拮抗[62]。NF-κB的異源二聚體p50/p65可以直接與FXR啟動子結合并抑制其轉錄[48]。
我們前期研究結果表明,IBS-D患者的FXR活性受到抑制,血清中FGF19含量低于正常人,即FXR-FGF19通路的激活受抑制。IBS-D患者血清中NF-κB表達增加[18]。FXR信號通路的抑制和促炎細胞因子的增加,破壞了腸道促炎與抗炎的平衡,從而參與觸發或維持腸黏膜低度炎癥和腸道免疫失調,對IBS-D的病理生理機制有廣泛的影響。動物模型研究表明,FXR敲除使機體促炎細胞因子表達的基線水平增加,伴隨著包括結腸固有層中炎癥細胞浸潤增加的慢性炎癥結構的變化。因此,FXR敲除不僅使體內膽汁酸池擴大,還會加重化學誘導的結腸炎癥,而激活FXR則可以通過改善腸道通透性和抑制NF-κB的途徑減少TNF-α、IL-1β等相關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63-64]。另一方面,NF-κB的關鍵功能就是在LPS或促炎細胞因子的刺激下快速活化,這是人類進化保存下來對抗感染的防御機制。LPS、TNF-α、雙鏈RNA和紫外線等均可以刺激NF-κB,使其形成p65(RelA)和p50異二聚體。有研究[53]發現,LPS通過結合TLR-4激活了NF-κB并刺激炎癥因子表達的關鍵通路p38/MAPK通路,成為肝臟損傷的主要決定因素。在IBS-D大鼠中也發現,TLR-4-MyD88-NF-κB通路明顯激活,大鼠血清中的IL-6和IL-1β水平明顯升高[65-66]。NF-κB的激活是導致腸道免疫失衡、增強促炎基因的表達和炎癥細胞的趨化作用的重要因素。其中,NF-κB對FXR的表達及活性的抑制還會反饋性加重腸道的炎癥反應,使炎癥和免疫失調慢性化、持續化[67]。
因此,IBS中的腸道低度炎癥狀態可能導致FXR的表達下降,減弱了對NF-κB的抑制,這個過程又進一步抑制了FXR的表達與活性,從而形成促進炎癥的惡性循環,導致腸道炎癥的反復與慢性化,為IBS-D提供了一種新發病機制的理論依據和未來治療策略的一種潛在的新方法。
6 討論
IBS-D病理生理機制的相關研究正在探索中。由于測序技術、免疫組織化學檢測和超微結構分析技術的進步,關于IBS的腸黏膜低度炎癥的假說在近幾年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本課題組前期針對腸道慢性低度炎癥機制的研究中發現了熱休克蛋白HSP-27可通過抑制IκB-α的磷酸化及NF-κB的激活進而抑制腸黏膜細胞的炎癥反應及凋亡[12,68]。但其復雜的分子機制仍待進一步研究來明確[69]。而IBS-D患者中存在一部分特發性BAD患者,并且這部分患者FXR的表達及活性下降,NF-κB的表達升高。FXR在其他器官組織中可以通過抑制NF-κB發揮抗炎效應。而NF-κB是調節炎癥的重要調節因子,在炎癥反應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促進炎癥因子、趨化因子及黏附因子等的表達,還對多種核因子具有抑制作用,包括FXR。因此,FXR與NF-κB信號通路之間存在相互抑制作用,并參與IBS-D的腸黏膜炎癥病理生理機制。而這種現象背后的分子機制仍待進一步研究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