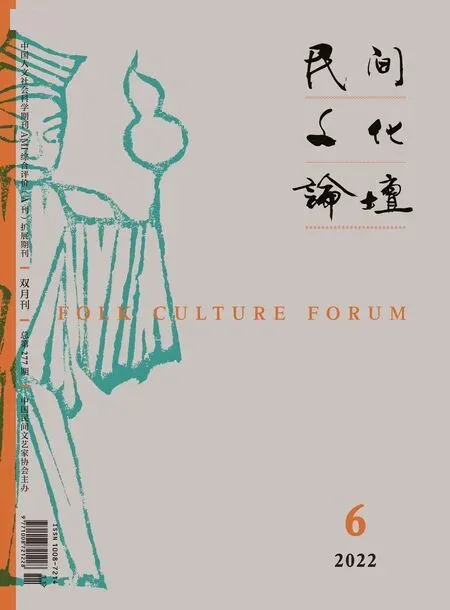劉錫誠《中國神話與民族精神》述評
邢 莉
《中國神話與民族精神》202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劉錫誠先生自1990年以來30篇神話論文的匯集,著作分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對于我國神話的研究,下篇是對于神話學者的評述。無論是上篇對各類神話的闡釋,還是下篇對于著名學者神話研究的梳理和評估,作者都是在力圖探究中華民族神話的特質及其民族精神。這也是他研究神話的目的與初衷。作者研究神話的目的充溢著對文明古國命運的人文關懷,洋溢著一位耄耋老人對中華民族自信、自強的信心和力量。
該論文集建構了研究中國神話的整體思維。①丁曉輝:《神話整體研究·神話學評論——劉錫誠的神話學研究》,《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9期。1987年10月23日,作者在中國神話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閉幕會上的總結發言中提出:中國神話要放到中國文化這一大背景上來討論,換句話說,中國神話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結構的相互影響和滲透,中國神話與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關系,似乎也挖掘得不夠。
從這里可以看出:其一,他認為神話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傳統文化不僅包括經史子集,而且還要眷顧民間文化,包括神話的民間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他突破了把神話視為文學想象和怪異敘事的窠臼,也不拘囿于用史學話語對神話的闡釋。他是位民間文化學家,以民間文化學者開闊的視域研究我國神話,力圖從文化史的角度解讀神話。其三,他認為,我國神話產生于黃土高原特殊的生態環境,形成了獨立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必然是區別于世界其他地域的人文創造。其四,我們談中華民族的認同,首先是文化的認同,而神話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標識之一。他之得以建構從民間文化學角度研究神話的整體思維,是與其學術功力分不開的。他撰寫了《中國原始藝術》和《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這兩部著作的寫作過程與其神話研究存在密切的關聯。可以說,這三部書是他成為民間文化學者的標識。
劉錫誠先生認為,我國不僅有一個龐大的帝系神話系統,而且也有一個豐富多樣的自然神話系統;不僅有一個宇宙和人類起源神話系統,也有一個創造文化英雄的神話系統。在本書的上篇,他研究了我國與世界各民族神話相通的各類神話,又針對我國各個民族豐富的神話呈現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分類。例如在人類起源的神話里,他劃分了肢體化生型、造人型、卵生型、感生型、石頭生人型及其他類型等,歸納出我國神話的豐富形態,突顯了我國神話的特色。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中國神話也有自己的譜系。盡管列出我國神話的譜系尚需要更大的功力和多學科成果的論證,但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在質疑和反思我國神話碎片化、歷史化、非體系化的結論。他對于中國神話譜系的提出,不僅是中國神話立足于世界民族神話之林的基石,也是探討中國神話民族精神的動力源。
為了探討中國神話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他不僅搜集了大量的漢族典籍資料,而且摒棄了漢族神話與少數民族神話二元論的敘事話語,把多個少數民族的神話包括北方民族的薩滿神話和南方各民族的神話納入了研究視域。在闡釋創世神話時,他運用了布依族的《力戛撐天》、壯族的《布洛陀》、布朗族的《顧米亞》、哈薩克族神話《迦薩甘創世》等豐富的資料。我國各個民族的神話產生于多樣的生態環境、不同的歷史形態與別樣風俗的情境之中。值得探討的是,我國多個民族都有盤古神話、女媧神話,如果起源于一地,廣泛傳播的路徑什么?傳播的動力何在?如果起源于多地,那么為什么多個地域會產生同樣的母題?這正是中華神話研究的整體觀要闡釋的問題。1907年,楊度發表了《金鐵主義說》一文,他認為中華民族與其說是一個種族融合體,不如說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文化的一體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①光緒三十三年 ( 1907)楊度在東京創辦《中國新報》月刊,任總編撰。《金鐵主義說》是他1903年發表在月刊上的一篇主題文章。中國神話整體觀的樹立,不僅有益于神話本體研究的拓展,而且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凝聚的標識之一。
神話是原始社會的遺響,其與原始社會的語言與宗教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在研究中,他涉獵原始社會的祭祀、巫術、占卜、預言等文化范疇。只有這樣,才能解開神話神秘的面紗,還原其歷史的真面與文化的真面,同時這也為探索中國神話的文化基因做好鋪墊。作者認為,祭壇就是神壇,神話往往是原始社會的人類在祭祀神祇時的語言表述。在分析鳥神話時候,作者談到鳥生神話與太陽崇拜的關聯,并且引用《尚書.堯典》“寅賓出日”之禮的記載說明神話于祭日儀式的存在。是時,關注神話與儀式的關系的學者尚少,作者憑借較為豐厚的學術積累,把神話的闡釋置于古代的儀式之中。這可以深刻闡釋神話在原始生活中的功能和價值。芬蘭民間文藝學家勞里·航柯于20世紀70年代在《神話界定問題》一文中談到界定神話的四條標準——形式、內容、功能、語境時說,除了語言的表達形式外,神話還“通過其他類型的媒介而不是用敘述來傳遞”,如祈禱文或神圣圖片、祭祀儀式等形式。②[芬蘭]勞里·航柯:《神話的界定問題》,載[美]阿蘭·鄧迪斯編:《西方神話學讀本》,朝戈金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2—65頁。神話不是講述的,而是肢體行為,具有渴望的情感并希冀得到可期的目的。劉先生對九尾狐神話的研究別出心裁,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把鄭州新通橋和山東嘉祥洪山村兩個地方出土的漢代畫像磚的九尾狐形象與文獻《汲郡竹書》《吳越春秋》的記載相對照,認為在西王母面前的九尾狐是一個溝通天地的巫師。這樣得出的結論非常新穎,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他在對我國神話母題研究的過程中,一方面尋求出世界不同生態環境中產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神話母題,另一方面努力分辨中國神話與他者的差異性。例如在闡釋創世神話、人類起源神話、取火神話、洪水神話時,都與其他地域的神話做了比較。在比較的過程中,尋求我國神話的特殊性和本源意義。在取火神話中,中國神話不是去天上盜火,而是鉆木取火。在分析洪水神話時,他認為,我國與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話有相似的避難母題,但還存在世界其他地域不存在的洪水之后再造人類的母題。他認為,兄妹(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話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洪水神話中別立一型的。這位民間文化學者在掌握豐富材料的基石上,往往使用國內外的大量材料進行比較研究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在這一點上,其與芮逸夫提出的“東南亞文化區”概念是相契合的。他認為,這種獨特的兄妹(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話極具東方特色,對認識亞洲文化史上的神話特征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揭示了我國原生態神話的本土知識和本土特征。
神話研究之所以被學術界認為是“迷思”,除了“迷思”是對myth的音譯,還因為神話敘事具有象征的意義。恩維特·卡西爾將神話定性為“表達符號形式”,他認為只有揭示神話的象征意義,才能理解神話的價值。劉錫誠認為象征不僅是一種研究方法,一種文化模式,還是一種思維方式。他有專著《象征——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問世。1996年在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民俗文化國際研討會”之后,他與游琪女士出版了論文集《葫蘆與象征》,討論的是中國葫蘆神話的象征意義,這本書具有廣泛的影響。得知美國召開了葫蘆神話研討的國際會議,東方文化研究會認為,中國作為歷史悠久的為世界文化做出貢獻的農耕大國,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與世界交流,顯揚自己神話的民族精神。在《禹啟出生神話及其他》這篇論文中,劉錫誠先生運用漢族的典籍,同時充分利用了佤族、哈尼族、壯族等民族的當代口承神話,闡釋了禹啟出生于石頭的神話背后的象征意義。他認為石頭是母體的象征,是生殖的象征,是在奇異的分娩之后已經失去了舊日權力的母系氏族的象征。卡西爾認為,在神話思維中,從人類意識最初萌芽之時起,我們就發現一種對生活的內向觀察伴隨著并補充著那種外向觀察。人類的文化越往后發展,這種內向觀察就變得越加顯著。①[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神話思維認為,人與自然萬物是一體的,主體和客體往往混淆為一。這屬于原始思維的范疇,也稱為互滲思維。石頭和葫蘆都是母體的象征,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但劉錫誠先生提出,石頭是已經失去了舊日權力的母系氏族的象征。雖然這一結論尚缺乏論證,可能會引起爭論,而爭論是更為接近真知的開啟。劉錫誠為白庚勝的《東巴神話象征之比較研究》撰寫了序言。他認為,白庚勝對于東巴神話的象征研究超越了民族志的記述和田野工作的簡單分析,促進了研究者對方法論的反省和批判。我們應該借鑒象征的理論,探索神話敘事背后的文化意義。
《中國神話與民族精神》的下篇是對于近代和當代中國神話研究的學術成果的評述,其對我國神話學大家的梳理和綜括具有學術史的價值,同時也書寫了他以探索神話為維度而尋求中華民族精神的初心。
早期涉獵神話學研究的顧頡剛、聞一多、黃石、丁山、茅盾、芮逸夫等前輩開啟了我國神話學建構性的研究。劉錫誠先生指出,中國神話與中國古史混雜在一起。一方面,他認可中國神話的史學特色的獨有;另一方面,史學特色又不是他唯一的研究維度。他站在神話學史的高度評述了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觀。顧先生認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若以建構的角度觀,恰恰就是將 “時序錯亂”“真偽混雜”的中國古代歷史,重新理順歸位——“我對于古史的主要觀點,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②顧頡剛:《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 273 頁。顧頡剛先生早期孜孜不倦地疑古、辨古,欲通過古史辨偽的工作推翻“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一以貫之的高度同一、統一的中國史觀,質疑“民族出于一統”“地域向來一統”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①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1923年7月1日),《古史辨》第一冊,第 96—101 頁。他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項標準: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第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第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②同上,第99—101頁。劉錫誠先生站在探究民族精神的高度評估了顧頡剛先生對我國神話學研究的重大貢獻。他認為,顧頡剛先生以淵博的學問在古史“辨偽”的名義下所進行的古史學術探索和論爭中,闡述了自己的完整的神話理論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創立了一套神話學學術體系,并在顧頡剛的帶動和影響下,逐漸形成了一個中國神話研究的學派——“古史辨派神話學”。
對茅盾先生關于神話研究的評述中,他指出,茅盾關于神話本質的論述,顯然有英國人類學派神話學的影子。這無疑應是“重構”中國神話學所要借鑒的。建立中國的神話學派可能要借鑒西方的神話,在接納、包容西方各個神話學派理論的同時,劉錫城強調不能完全套用西方學者研究的視域而探討中國神話。我國神話的產生有其獨特的生態環境、人文環境與文化特征,我國的神話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我國的神話學研究也完全可以稱為學派,因為近代中國神話研究的成果具有可供借鑒的獨特的研究視域、獨特的研究體系、獨特的研究方法,并為后學者提供寶貴的借鑒。當然我國的神話學研究能否構成學派要得到國內外的普遍認可,但是這是作者深慮的結果,也是為探究神話與民族精神所做的學術支撐。1990年以來,對于近代神話大家進行研究的論文有之,但對這批神話學大家做系列研究的成果卻少見。
論文集下篇還包括關于當代有成就的神話研究者的評述,包括張振犁、潛明茲、蕭兵、何新、葉舒憲、楊利慧等學者。劉錫誠給予張振犁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調查的“中原神話現象”及相關著作極高的評價,他為較為發達的中原地區保存至今的神話的古樸持久的生命力而拍案驚喜。同時,他充分肯定了蕭兵與葉舒憲的科研成果。他認為兩位的神話研究成果的思路都是以跨文化研究和原型解讀方式重構和復原失落了的古神話,這樣的思路與以往的考據法有別,開拓了我國神話研究的新思路。他還指出,葉舒憲與蕭兵的不同處在于并不停止在神話的重構(構擬)上,而是希圖溝通中西學術研究方法,并在中西方文化比較的背景上建立中國的比較神話學。
本書下篇的另外一組文章,包括《20世紀中國神話學概觀》《民俗學神話學:過去、現在和未來——2006年10月26日在中央民族大學的講座》《神話學百年與中華民族精神》等,都是對中國神話學歷程的梳理和研究。其研究的框架同樣具有宏闊的視野,其評述對象不僅包括中國百年神話學進程中具有卓越貢獻的大家,也包括近40年來中國神話學研究的后起之秀。通過對神話學百年研究歷程的概括,他在繼續探討中國本土神話的內容結構及文化特征。在這組文章中,他再三強調,研究中國神話的學者最終探索的目標是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而在民族精神的發掘與重構中, 神話無疑是極為重要的象征。民族精神是民族延續最根本的基因,民族基因是民族發展的原動力。
回顧百年神話研究的歷程,對于什么是民族精神他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認為:“中華民族是由多個族群融合而成的多民族國家。……從20年代夏曾佑到40年代徐旭生提出華夏民族是由古代華夏、苗蠻、東夷三大集團融合組成的以來,已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贊同。也就是說,華夏民族、或后來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體的文化……大量的中華古典神話和后來發掘采集的口傳神話都顯示,神話的文化精神或民族精神是生生不息的……我們的神話學者有責任闡明神話的這種生生不息精神。”我國神話的代表作女媧補天、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夸父追日都是生生不息精神的顯揚,其折射出在中國黃土地的特定的生態環境中生存的農耕大國民族精神和文化氣派。
神話學是一個涉獵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民俗學以及民間文學的交叉學科。為了闡釋和認知“迷思”(神話),學術界展開了“多重證據法”的討論。其源頭要追溯到大學者王國維。劉錫誠先生在研究神話的時候也采用了多重論證的方法。其中包括歷史典籍、筆記雜記、考古資料,包括漢代畫像磚、古老的巖畫、陶器的多種紋飾等,特別值得贊嘆的是,他還利用了自己調查或者他人調查的民族學田野調查資料。他把古典的與活態的、考古的與搜集的、紋飾的與記載的一覽盡收,經過分析、比較、質疑而后闡釋,盡力得出科學的結論。在研究“葫蘆生人”的神話意象時,他甚至運用了學術界對于很多學者感到生疏的滄源巖畫為佐證。在《世界樹神話》的闡釋中,作者運用了山東的畫像磚及三星堆出土的“神樹花果”的文物為佐證。這部成果重視民族志調查中所獲得的可貴的多個民族活形態的資料。葉舒憲認為,多重證據并重的過程,其內在的精神取向就是,破除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態度,以開放的心態大膽地溝通中西,從而“變單向的移植與嫁接為雙向的匯通與相互闡發”。①葉舒憲:《中國神話學百年回眸》,《學術交流》,2005年第1期。作者的目的是通過多重證據之間的“間性”,揭示被文字符號所遮蔽的文化之謎。
20世紀80年代以來,葉舒憲的著作《中國神話哲學》和《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以神話-原型理論為依據, 對于中國神話哲學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謝選駿的《神話與民族精神》和《空寂的神殿》也相繼登上神話研究的舞臺。前者探索了神話含蘊的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及民族精神,后者從文化哲學和神話哲學的角度開拓了研究中國神話與民族精神之關系的視野。在此基礎上,劉錫誠先生再次提出“中國神話與民族精神”的論題。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一直追問的就是“從哪種意義上來說,神話具有價值?”②[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第107頁。毫無疑問,這也是作者追問的問題。神話的價值在于民族精神的追問,追問的目的是尋找現代人建構精神家園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