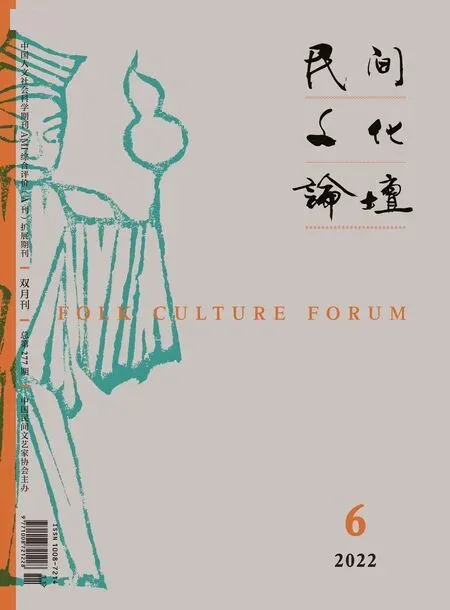民俗攝影的“當(dāng)下”立場(chǎng)和美學(xué)追求
鄧立峰
論者常常提及民俗攝影是特殊的攝影門類,因?yàn)樗鼉?nèi)含“學(xué)術(shù)性”和“知識(shí)性”,兼具“文獻(xiàn)價(jià)值”與“美學(xué)價(jià)值”,有人甚至稱其為“形象歷史檔案”或“圖像民俗學(xué)”“圖像歷史學(xué)”“圖像民俗學(xué)”。①董河?xùn)|主編:《民俗攝影》,北京:中國(guó)電力出版社,2018年,第84頁(yè)。類似為民俗攝影樹立特殊地位的論斷并不少見,按其重要價(jià)值,似乎民俗攝影應(yīng)當(dāng)成為藝術(shù)生產(chǎn)領(lǐng)域或民俗學(xué)研究中的“顯學(xué)”;然而讓人感到失落的是,當(dāng)今民俗攝影卻呈現(xiàn)出“熱鬧中的式微”,并產(chǎn)生了“種種與民俗文化相關(guān)的攝影異象”。②柴選:《民俗攝影的式微的現(xiàn)狀與“四化”異象》,那日松主編:《中國(guó)攝影批評(píng)選集》,北京:中國(guó)民族攝影藝術(shù)出版社,2013年,第442頁(yè)。
民俗攝影實(shí)踐的歷史可以追溯至現(xiàn)代攝影技術(shù)誕生之初,近二百年間也確實(shí)出現(xiàn)了一大批經(jīng)典作品,但作為一種經(jīng)過歸類、加以定義的攝影門類,“民俗攝影”還相對(duì)年輕——直至20世紀(jì)90年代,中國(guó)才開始出現(xiàn)“民俗攝影”的系統(tǒng)性論述,相關(guān)研究也在向前推進(jìn)。然而,在為其爭(zhēng)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民俗攝影被套上了來自“藝術(shù)”與“學(xué)術(shù)”的雙重枷鎖,至今仍然面臨著范疇界定模糊、拍攝取向不清、美學(xué)追求缺失等問題。
一、民俗攝影的范疇界定問題
“民俗攝影”成為學(xué)界認(rèn)可的專門攝影門類,是在1993年中國(guó)民俗攝影協(xié)會(huì)成立之后。冠以“民俗攝影”之名的攝影作品、關(guān)于民俗攝影的學(xué)術(shù)討論,也隨之多了起來。不過,以民俗為對(duì)象的拍攝行為卻并不是新鮮事物。早在19世紀(jì)40年代,英國(guó)攝影師大衛(wèi)·奧克塔維厄斯·希爾(David Octavius Hill)和羅伯特·亞當(dāng)森(Robert Adamson)就拍攝了一系列反映蘇格蘭地區(qū)日常生產(chǎn)生活的照片,算是最早的民俗影像之一。20世紀(jì)下半葉,人們更多將攝影技術(shù)看作記錄工具,廣泛應(yīng)用于對(duì)少數(shù)族裔、建筑、城市景觀及民間風(fēng)情等的拍攝記錄之中。1897年,英國(guó)伯明翰區(qū)議員班杰明·史東爵士(Sir Benjamin Stone)推動(dòng)創(chuàng)立了英國(guó)國(guó)家攝影記錄協(xié)會(huì)(the Naional Photographic RecordAssociation),“為未來記錄古跡、古代建筑、民間風(fēng)俗和其他歷史遺跡,形成一個(gè)國(guó)家記憶庫(kù)”①[英]凱利·懷爾德:《攝影與科學(xué)》,張悅譯,北京:中國(guó)攝影出版社,2016年,第79頁(yè)。。20世紀(jì)初,美國(guó)攝影師愛德華·柯蒂斯(Edward S.Curtis)完成了二十卷本的《北美印第安人》(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這是民俗攝影史上最常被提及的作品之一。之后的幾十年,西方民俗攝影活動(dòng)不再只聚焦于少數(shù)族裔和文化遺跡,開始越來越多地關(guān)注主流人群的生活狀態(tài),民俗攝影也達(dá)成了拍攝對(duì)象的“全覆蓋”。
在中國(guó),民俗影像的生產(chǎn)可以追溯到19世紀(jì)下半葉來華的西方商業(yè)攝影師、傳教士和殖民官員,如白斯德望(E?tienne Albrand)拍攝了貴州居民生活風(fēng)貌、方蘇雅(Auguste Franc?ois)拍攝了云南居民的城鎮(zhèn)生活。到了20世紀(jì)20年代,逐漸流行開來的大眾畫報(bào)催生了一批以民俗事象為呈現(xiàn)對(duì)象的作品——單單在1926年,《良友》畫報(bào)就刊載了《北京喪俗一瞥》《山西省小人戲》《福州之水嬉》等系列民俗照片,這說明,民俗事象此時(shí)已被納入社會(huì)視覺體系之中,成為視覺消費(fèi)的對(duì)象。與此同時(shí),一些國(guó)內(nèi)外研究者在中國(guó)中西部地區(qū)進(jìn)行人類學(xué)、建筑學(xué)等的考察,拍攝了不少反映當(dāng)?shù)孛耧L(fēng)的照片。而像莊學(xué)本、王小亭、孫明經(jīng)這樣有專業(yè)抱負(fù)的攝影師,也深入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拍攝了大量反映當(dāng)?shù)鼐用裆顮顟B(tài)、穿著服飾、節(jié)日習(xí)俗的照片……1993年,中國(guó)民俗攝影協(xié)會(huì)成立,“標(biāo)志著中國(guó)民俗攝影成為一個(gè)新的攝影門類并迅速被大眾接受”②馬有基、吳泳:《民俗攝影中的傳統(tǒng)文化及其表現(xiàn)》,《南京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年第4期。。
刊登于1995年第5期《新疆藝術(shù)》的《試論民俗攝影》,是最早對(duì)民俗攝影進(jìn)行專論的文章之一,作者將“民俗攝影”定義為“用攝影手段形象地表現(xiàn)民俗事象,它與風(fēng)光、人像、建筑等攝影一樣,都是由內(nèi)容來確定的一種專業(yè)性攝影門類”③雷茂奎:《試論民俗攝影》,《新疆藝術(shù)》,1995年第5期。。之后的研究者大多沿用這樣的界定,將“民俗攝影”視為民俗文化與攝影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是以民俗事象為題材進(jìn)行影像生產(chǎn)的攝影門類。
這樣的定義看似簡(jiǎn)單明了、有具體指向,實(shí)則蘊(yùn)含著范疇的邊界危機(jī)。當(dāng)下對(duì)“民俗攝影”的界定,混雜了作為獨(dú)立藝術(shù)門類的“民俗攝影”和作為民俗研究學(xué)科工具的“民俗學(xué)攝影”的邊界,使民俗攝影兼具藝術(shù)生產(chǎn)屬性和工具屬性,在科學(xué)取向、工具價(jià)值和藝術(shù)追求三個(gè)意義層次上產(chǎn)生了矛盾與交雜。具體來說,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
首先,當(dāng)下“民俗攝影”的主要呈現(xiàn)對(duì)象,是被視作“他者”的群體或具有文化遺產(chǎn)屬性的事物。一方面,說起民俗攝影,最常提到的是柯蒂斯、莊學(xué)本、王小亭等人的照片,而他們所表現(xiàn)的對(duì)象多是“我群”之外的“他者”;另一方面,人們也常常把“他者”的普通肖像——例如表現(xiàn)拍攝對(duì)象面部表情的照片及喝水、飲食等日常動(dòng)作的特寫——視作“民俗攝影”,這類僅僅因?yàn)閷?duì)方的“異域”長(zhǎng)相而被拍下來的照片,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民俗攝影的教材與攝影集中。為什么會(huì)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這還要從過往“民俗”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說起。高丙中指出,在民俗學(xué)確定其研究對(duì)象的時(shí)候,有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文化”作為參考,在工業(yè)時(shí)代,現(xiàn)代文化成為評(píng)價(jià)各種現(xiàn)象的標(biāo)準(zhǔn),而跟現(xiàn)代文化不盡相同的“古代或異域的文化遺留物”則成為民俗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雖然今天的民俗學(xué)研究同樣納入了主流人群的日常生活,但主流人群和“他者、異己”的二分形態(tài)“是民俗學(xué)興起之初就隱含著的內(nèi)在邏輯”,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xiàn)在不同時(shí)期、不同社會(huì)。④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來民俗學(xué)》,蕭放、朱霞主編:《民俗學(xué)前沿研究》,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8年,第162—163頁(yè)。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他者”影像更容易被看作民俗攝影了。
其次,民俗攝影常常被賦予“為歷史留存研究文獻(xiàn)”的學(xué)科屬性。一方面,民俗攝影被當(dāng)成記錄和保存文化遺產(chǎn)的工具。民俗攝影“一是可以幫助人類儲(chǔ)存民俗發(fā)展演變的形象資料,二是可以搶救那些瀕臨消失的民俗事象,作為現(xiàn)代化手段的形象‘化石’留給后人進(jìn)行研究。”①雷茂奎:《試論民俗攝影》,《新疆藝術(shù)》,1995年第5期。“民俗攝影所拍攝的大量的反映民俗文化的圖片,就是一個(gè)文化遺產(chǎn)的圖片庫(kù)。”②向先清:《民俗攝影: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俗記憶》,《柳州師專學(xué)報(bào)》,2010年第3期。另一方面,人們又將民俗攝影與其他學(xué)科聯(lián)系起來,為其賦予“學(xué)科邊沿性”。“民俗攝影既是民俗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組成部分,又與人類學(xué)、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等學(xué)科相聯(lián)系,有極強(qiáng)的學(xué)科邊沿性。”③譚巧勤:《關(guān)于民俗攝影的考察與研究》,《西華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社版),2004年第5期。這一點(diǎn)與其他攝影門類大不相同:眾所周知,現(xiàn)代攝影技術(shù)誕生之初就被用于記錄和存檔工作,其中包括以不同人種為拍攝對(duì)象的人類學(xué)攝影、記錄考古過程的考古攝影、用于拍攝罪犯或犯罪現(xiàn)場(chǎng)的司法攝影,等等。不過,這些攝影門類都有明確的功能邊界,媒介本身并沒有更多的意義指向;而被用來歸類一般攝影實(shí)踐的紀(jì)實(shí)攝影,對(duì)其界定雖然兼具行為過程和美學(xué)形式,但它并不會(huì)被視作工具,本身也不具“學(xué)科邊沿性”;只有民俗攝影與眾不同。
第三,民俗攝影被賦予了揭示“本質(zhì)”的科學(xué)要求。在相關(guān)論述中,經(jīng)常可以看到要求民俗攝影實(shí)踐者通過鏡頭揭示民俗“本質(zhì)”。有研究者寫道:“民俗攝影著重在于文化的體現(xiàn),樸實(shí)無(wú)華,甚至有些顯得毫無(wú)拍攝章法的民俗攝影作品所傳遞的文化信息更多。當(dāng)你以做學(xué)問的心情,以嚴(yán)謹(jǐn)?shù)目茖W(xué)態(tài)度,在面對(duì)即將消失的或正在消失的民俗事象時(shí),就已經(jīng)把攝影的技術(shù)‘忘記’了,不在乎用形象語(yǔ)言來塑造美的畫面,而關(guān)注的是民俗事物的演變、發(fā)展過程,希望自己拍攝的內(nèi)容具有知識(shí)性,學(xué)術(shù)性,希望畫面中的環(huán)境、人物能夠體現(xiàn)出民俗活動(dòng)的本質(zhì)意義,這樣攝影作品就能反映出稱作‘文化’的東西。”④同上。毫無(wú)疑問,這樣的要求混淆了“民俗攝影”與“民俗學(xué)攝影”的功能,也混淆了民俗攝影家和民俗學(xué)家的界限。
由此可見,當(dāng)今對(duì)“民俗攝影”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俗學(xué)攝影”。作為獨(dú)立藝術(shù)門類的“民俗攝影”,應(yīng)以審美屬性和藝術(shù)價(jià)值為根本追求;而具有學(xué)科屬性的“民俗學(xué)攝影”,則需要在文獻(xiàn)留存和研究?jī)r(jià)值的角度多做考慮。但在當(dāng)下的論述中,民俗攝影已成為民俗學(xué)與攝影藝術(shù)邊界不清、概念交融的地點(diǎn),而范疇界定的模糊,也導(dǎo)致了民俗攝影拍攝取向、美學(xué)追求的混亂與不定,影響了這一藝術(shù)生產(chǎn)形式存在的合法性。
本文認(rèn)為,應(yīng)將“民俗攝影”和“民俗學(xué)攝影”作清晰界定,并厘清作為影像藝術(shù)生產(chǎn)行為的民俗攝影所應(yīng)追求的美學(xué)原則。
二、本質(zhì)主義思維與民俗“景觀化”
如前所述,民俗攝影嘗試納入“文獻(xiàn)記錄”與“科學(xué)研究”等功能,來爭(zhēng)取作為獨(dú)立攝影門類的合法地位,并就此引入了揭示民俗“本質(zhì)”的科學(xué)要求。而在民俗攝影的實(shí)踐中,不少攝影師也確實(shí)抱著揭示“本質(zhì)”的目的進(jìn)行拍攝。
長(zhǎng)期在滇南地區(qū)考察的民間文化專家姜定忠,拍攝了大量具有文獻(xiàn)價(jià)值的少數(shù)民族照片。他在《民俗攝影的方法與理論》一書中提到了其拍攝理念:“對(duì)于民俗風(fēng)情攝影,擺拍比抓拍重要。如果不擺拍,不是有意識(shí)有準(zhǔn)備地把人物擺進(jìn)去,你去等幾天或者更長(zhǎng)時(shí)間,也不會(huì)有最佳環(huán)境、最佳景物、最佳光影、最佳人物同時(shí)在一個(gè)畫面中出現(xiàn)。”同時(shí),處理好民俗民情攝影,要“讓作品由表及里,透過表象而最生動(dòng)、最典型地反映民俗的本質(zhì)特征”①姜定忠:《民俗攝影的方法與理論》,昆明:云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8年,第5頁(yè)。。出于這樣的理念,他寫道:“在拍攝藏族民俗風(fēng)情時(shí),一定要跟那里的青藏高原結(jié)合起來……青山頂著藍(lán)天白云,濃厚的宗教氛圍,給喇嘛寺廟增加了高深之感,使那里的天、地、人都帶有神圣莫測(cè)的色彩……哈尼族居住于哀牢山層層梯田之中,形成了哈尼梯田生產(chǎn)、生活文化藝術(shù),其服飾、住房、婚俗、節(jié)日,所有一切都帶有梯田的神韻,沒有梯田的影子,就難以反映哈尼族民俗風(fēng)情的實(shí)質(zhì)。”②同上,第213頁(yè)。
不可否認(rèn)的是,作為資深的攝影實(shí)踐者,作者的確提供了一種快速入門、拍出讓人眼前一亮的攝影作品的方法。但是,這種以幾項(xiàng)“最佳”的組合來“反映本質(zhì)”的方式,僅僅是契合了拍攝者的“他者想象”——也只有在“他者想象”中,才會(huì)有對(duì)認(rèn)知對(duì)象“最佳組合”的判斷。追求“反映本質(zhì)”,更容易讓拍攝者陷入刻板印象和套式化認(rèn)知之中。
科學(xué)思維往往會(huì)為研究對(duì)象預(yù)設(shè)一個(gè)可加理解的“本質(zhì)”,并以研究活動(dòng)對(duì)其進(jìn)行揭示。民俗活動(dòng)中,這一“本質(zhì)”存在與否尚不清楚;而對(duì)于民俗攝影,對(duì)民俗“本質(zhì)”的追求,卻更容易跟拍攝者腦中的“本質(zhì)”交雜,產(chǎn)生認(rèn)知的混亂。致力于呈現(xiàn)民俗“本質(zhì)”的拍攝活動(dòng),的確造成了一些怪象的出現(xiàn)——拍攝者不再?gòu)娜粘I钪袑ふ颐袼滋卣鳎菫槊袼资孪蠛兔袼字黧w預(yù)設(shè)一個(gè)契合刻板印象的“本質(zhì)”。經(jīng)常可以在媒體上看到,在某“擺拍圣地”(如云南東川煙斗老人、福建楊家溪的老牛和農(nóng)村夫婦),“長(zhǎng)槍短炮”圍繞著一個(gè)孤零零的拍攝對(duì)象,這個(gè)拍攝對(duì)象及其所在的場(chǎng)景,契合了大眾對(duì)于農(nóng)民或其他勞作者的想象,可謂是“最佳環(huán)境”中的“最佳人物”。據(jù)媒體報(bào)道,江西婺源秋口鎮(zhèn)的“只撒網(wǎng)不打魚的漁夫模特”,光靠充當(dāng)被攝對(duì)象,每年就有近3萬(wàn)元的收入。③王國(guó)紅:《婺源:漁夫泛舟當(dāng)模特撒網(wǎng)擺拍忙創(chuàng)收》,《照相機(jī)》,2015年第1期。為了揭示民俗“本質(zhì)”,一些拍攝者“手動(dòng)”塑造景觀,自動(dòng)剔除與“本質(zhì)”不相關(guān)的民俗元素。而當(dāng)拍攝者“手動(dòng)”塑造的圖景契合于大眾對(duì)民俗的刻板印象時(shí),民俗攝影的景觀化就此完成。
居伊·德波對(duì)“景觀社會(huì)”的分析,為我們帶來了日常生活景觀化的啟示。在德波看來,建立在現(xiàn)代工業(yè)之上的社會(huì),本質(zhì)上就是景觀主義社會(huì)。④[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huì)》,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第7頁(yè)。由豐富的圖像構(gòu)成的社會(huì)圖景,使人們屈從于娛樂、消費(fèi)及意識(shí)形態(tài)等欲望客體,遮蔽了人們的本真生活和真實(shí)渴望。景觀具有其自足的“實(shí)證性”:“部分地看到的現(xiàn)實(shí)展開在其自身的普通統(tǒng)一性中,成為邊緣的偽世界,成為僅僅被凝視的客體。”⑤同上,第3頁(yè)。德波的景觀理論所反映的是人與生產(chǎn)方式、政治權(quán)力之間的系統(tǒng)性關(guān)系;不過,即使剝離開此一權(quán)力系統(tǒng)的運(yùn)作,我們?nèi)匀豢梢詮闹锌吹阶鳛樯鐣?huì)實(shí)踐的“景觀秩序”。這是一種對(duì)現(xiàn)實(shí)存在的景觀化建構(gòu),通過影響著大眾思維的本質(zhì)主義觀念,以影像生產(chǎn)的方式使表現(xiàn)對(duì)象“部分在場(chǎng)”,達(dá)致自足的“統(tǒng)一性”,以促成文化觀點(diǎn)或文化產(chǎn)品的流通。
我們熟悉的各類民俗表演,就是將民俗事象“景觀化”的重要形式。如今,民俗表演已非常普遍,“各地的攝影節(jié)慶活動(dòng)為吸引參與者,好像不安排點(diǎn)民俗表演就對(duì)不起四面八方的來賓;某些特色題材,已成為地方旅游推廣的重點(diǎn)項(xiàng)目天天上演,組織拉纖、套馬、放牧等‘大型場(chǎng)面’等也稱為攝影旅游景點(diǎn)的收費(fèi)項(xiàng)目之一。”①柴選:《民俗攝影的式微的現(xiàn)狀與“四化”異象》,那日松主編:《中國(guó)攝影批評(píng)選集》,第443頁(yè)。在民俗影展和相關(guān)影集中,經(jīng)常可以看到民俗表演的照片——一群穿戴少數(shù)民族服飾的人,在鋪好的紅毯或舞臺(tái)上,或神情莊重地站在祭品前念念有詞,或表演著獨(dú)具特色的民族舞蹈。拍攝者“巧妙地”抓住了“決定性瞬間”,展現(xiàn)了表演者虔誠(chéng)、投入的神情。
這樣的照片看似捕捉到了民俗活動(dòng)的“本質(zhì)”,也能滿足觀看者對(duì)民俗活動(dòng)的想象。但現(xiàn)實(shí)是,這類民俗表演本身就是一種“景觀化”的建構(gòu),依此拍攝的民俗照片更是對(duì)于景觀的再生產(chǎn)。在今天,這類表演往往由地方政府或商業(yè)組織主導(dǎo),具有強(qiáng)烈的政治屬性或娛樂屬性,與民俗本身所追求的社會(huì)功能相去甚遠(yuǎn)。不過,民俗表演往往能集合所有契合大眾想象的民俗元素,將獨(dú)一無(wú)二的民俗特征集中展現(xiàn)在一個(gè)完整的“舞臺(tái)”上,因此是民俗攝影中常出現(xiàn)的主題。然而,拍攝民俗表演照片時(shí),一些能改變民俗“本質(zhì)”的信息卻往往被有意無(wú)意地過濾掉——景觀化圖景賴以“自證”的合理性,首先就在于影像內(nèi)部話語(yǔ)系統(tǒng)的“統(tǒng)一性”,民俗是“民”之俗,表現(xiàn)為民間的自發(fā)性與自足性,在拍攝民俗表演場(chǎng)景時(shí),拍攝者會(huì)剔除其中象征政治性或商業(yè)性的“當(dāng)代”元素和“外在”元素,這在保證“民間”景觀純粹性的同時(shí),保持民俗的神話色彩。當(dāng)然,除了影像內(nèi)部系統(tǒng)的“統(tǒng)一性”,景觀化圖景存在的合理性,還依賴于影像語(yǔ)言與社會(huì)話語(yǔ)的連貫表達(dá),社會(huì)大眾對(duì)于民俗及民俗主體的套式化認(rèn)知和刻板印象,會(huì)使剔除了“當(dāng)代”元素和“外在”元素的民俗影像顯得毫不違和——當(dāng)身著特色服飾、投入地表演民俗節(jié)目的影像出現(xiàn)在大眾面前,對(duì)該民俗及民俗主體的生活化論述、“他者”想象,與影像本身相聯(lián)通,兩者相互印證,使民俗表演成為民俗“本質(zhì)”的證明。
基于本質(zhì)主義思維的景觀化生產(chǎn),使民俗影像成為拍攝者和觀看者合謀制造的片段圖景,它將被攝對(duì)象原本多樣的民俗元素和復(fù)雜的動(dòng)態(tài)變化簡(jiǎn)化為“想象-印證想象”的過程,而民俗攝影論者所期待的類似“影像民族志”的成果,往往會(huì)演變成民俗活動(dòng)的“偽民族志”。
三、基于民俗和民俗主體的美學(xué)追求
某種程度上講,本質(zhì)主義的追求和景觀化的塑造,暗合了對(duì)民俗“傳統(tǒng)”的推崇:將民俗視為“過去”的產(chǎn)物,在拍攝中選取象征“傳統(tǒng)”的元素——符合其生存與演變的歷史環(huán)境的意象,如“歷史的”服飾、“歷史的”儀式等,而忽視其基于“當(dāng)下”的動(dòng)態(tài)變化,這看起來更能體現(xiàn)民俗“本質(zhì)”,也更能契合觀者對(duì)民俗的歷史性想象。
“民俗”與“傳統(tǒng)”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一直決定著民俗認(rèn)知的發(fā)展,過往對(duì)民俗的定義也大多強(qiáng)調(diào)“傳統(tǒng)”,民俗學(xué)研究將“傳統(tǒng)”看作是界定“民俗”的特質(zhì)之一,在一些民俗學(xué)者看來,“傳統(tǒng)”甚至是“俗”的同義詞。②劉曉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傳承時(shí)代民俗學(xué)“日常生活”轉(zhuǎn)向的一種路徑》,《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但在“傳統(tǒng)”逐漸成為解構(gòu)對(duì)象的過程中,人們漸漸意識(shí)到,“傳統(tǒng)”與“當(dāng)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在英國(guó)歷史學(xué)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敘述的那些“被發(fā)明的”傳統(tǒng)中,“它們采取參照舊形勢(shì)的方式來回應(yīng)新形勢(shì),或是通過近乎強(qiáng)制性的重復(fù)來建立它們自己的過去。”①[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導(dǎo)論:發(fā)明傳統(tǒng)》,[英]霍布斯鮑姆、蘭格編:《傳統(tǒng)的發(fā)明》,顧杭、龐冠群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2頁(yè)。對(duì)傳統(tǒng)的闡釋和構(gòu)建離不開當(dāng)下的需求,傳統(tǒng)是“被發(fā)明的”。
民俗學(xué)發(fā)展過程中,對(duì)“傳統(tǒng)”的不斷拷問也改變著對(duì)“民俗”的界定。近年來,民俗學(xué)研究逐漸出現(xiàn)了“日常生活”轉(zhuǎn)向,“民俗”的定義逐漸從一種“實(shí)在”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過程”。當(dāng)這一轉(zhuǎn)變發(fā)生,民俗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從民俗現(xiàn)象轉(zhuǎn)向?qū)嵺`主體,“從靜止的、本質(zhì)化的共同體轉(zhuǎn)向流動(dòng)的、意向性建構(gòu)的‘共同體’”,不再將民俗視作“客觀的、本質(zhì)化的研究對(duì)象,而是一種為人們所意向性地建構(gòu)的社會(huì)文化事實(shí)”。②劉曉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傳承時(shí)代民俗學(xué)“日常生活”轉(zhuǎn)向的一種路徑》,《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
民俗學(xué)的“日常生活”轉(zhuǎn)向,為民俗攝影樹立“當(dāng)下”立場(chǎng)提供啟示:首先,民俗攝影應(yīng)突破民俗活動(dòng)的歷史性背景及頭腦中刻板印象的束縛,展現(xiàn)當(dāng)下的民俗場(chǎng)景,確立基于“當(dāng)下”的攝影語(yǔ)言;其次,民俗攝影應(yīng)將拍攝對(duì)象聚焦于作為民俗主體的群體或個(gè)人,突出主體與民俗之間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人在民俗活動(dòng)中的狀態(tài)。
我們以英國(guó)攝影家馬丁·帕爾(Martin Parr)的紀(jì)實(shí)作品為例。雖然以傳統(tǒng)的眼光看,帕爾很難被視為民俗攝影家,但他的作品中卻處處凸顯民俗元素。帕爾鏡頭中的民俗并不是帶有“傳統(tǒng)”印記的民族風(fēng)情,而是趣味盎然的“新民俗”。在異域題材系列作品《墨西哥》(Mexico)中,站在墨西哥的土地上,帕爾沒有刻意尋找典型民族元素,而是對(duì)墨西哥的街頭食物、帶有墨西哥元素的旅游商品、綠白紅三色的物品(綠白紅是墨西哥國(guó)旗的主色)、人們的街頭活動(dòng)等進(jìn)行拍攝,反映墨西哥的民風(fēng)民俗。這些影像顯然不具備揭示當(dāng)?shù)孛袼住氨举|(zhì)”的能力,卻直接地反映了墨西哥民俗文化的混雜性,正是對(duì)這一混雜特征的呈現(xiàn),將當(dāng)?shù)孛袼讖摹肮爬稀焙汀吧衩亍钡姆h中解救出來,彰顯了墨西哥文化的獨(dú)特精神內(nèi)核。
當(dāng)我們轉(zhuǎn)換觀看民俗的目光,將民俗視為“建構(gòu)的社會(huì)文化事實(shí)”的“過程”,就會(huì)發(fā)現(xiàn)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基因”,每個(gè)人都是民俗的承載者和參與者,人們從事著生產(chǎn)共同意義的群體性活動(dòng),民俗在此顯露輪廓。以“當(dāng)下”為本,以民俗中的人、生活為拍攝中心,而不是以追求“本質(zhì)”為目標(biāo)、以民俗形式為拍攝對(duì)象,這樣的民俗攝影更能展現(xiàn)民俗的動(dòng)態(tài)變化,也更能把握民俗主體的存在狀態(tài),抓住民俗流變中的精神內(nèi)核。
除了樹立“當(dāng)下”立場(chǎng),民俗攝影還應(yīng)具備美學(xué)追求,民俗攝影“合法地”成為獨(dú)立藝術(shù)門類,其最終依據(jù),不是揭示民俗“本質(zhì)”、保留歷史文獻(xiàn)的功能,而是對(duì)民俗活動(dòng)美學(xué)價(jià)值、民俗中個(gè)體生命力的充分表現(xiàn)。我們可以通過對(duì)比蒂娜·莫多蒂(TinaModotti)和路易斯·馬爾克斯·羅邁(Luis MárquezRomay)的墨西哥民俗主題攝影作品,來解釋這種美學(xué)追求。1923年至1930年間,來到墨西哥的莫多蒂用她的相機(jī)記錄下了當(dāng)?shù)氐拿袼罪L(fēng)情。女人頭頂陶罐出行是具有民間特色的風(fēng)景,莫多蒂拍攝了多張反映這一習(xí)俗的照片。當(dāng)我們看到這些照片,不僅可以看到頭頂陶罐的女人,還能看到女人開心的笑容、身邊赤裸身子的孩子、墨西哥細(xì)長(zhǎng)的街道及街道兩旁鋪有磚瓦的房子……莫多蒂很少切割與主題不相關(guān)的元素,她將人與環(huán)境悉數(shù)收入鏡頭,沒有迎合西方觀眾對(duì)于“他者”的刻板印象,而是在表現(xiàn)人與環(huán)境關(guān)系的和諧形式中凸顯人的生命力。相比之下,羅邁的一些墨西哥民俗照片就更體現(xiàn)文獻(xiàn)記錄的特性。1950年出版的《墨西哥民俗》(Mexican Folklore)刊登了100張展示墨西哥獨(dú)特民族服裝、裝飾配飾、儀式用具的照片,這些照片由羅邁拍攝,其中一部分是以定格肖像的特寫鏡頭呈現(xiàn),著重突出被攝主體,背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jì)。這類照片中,人的服裝、配飾、用具等是照片的主角,人成為模特。從中可以看出“拍攝者-被攝對(duì)象”的二元對(duì)立,人物“靈魂”缺失,使此類照片的藝術(shù)價(jià)值大大降低。兩相比較,羅邁的此類照片更可歸類為“民俗學(xué)攝影”,而莫多蒂的照片則更能體現(xiàn)民俗的美學(xué)價(jià)值。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這里所說的美學(xué)追求,并不是指風(fēng)格上“唯美”與“矯飾”,也不是單純追求構(gòu)圖、色彩搭配等的形式主義取向。攝影的機(jī)械特性和技術(shù)特點(diǎn),決定了它的強(qiáng)項(xiàng)在于即時(shí)抓住生活中的美感;過度追求“唯美”“矯飾”,會(huì)使其進(jìn)入到“想象”的美學(xué)感覺,這跟致力于凸顯“傳統(tǒng)”、塑造“遺存”之感的民俗攝影作品一樣,都會(huì)使攝影的紀(jì)實(shí)特質(zhì)喪失其本性。民俗攝影之美,要從基于當(dāng)下生活的民俗中尋找其美學(xué)價(jià)值,反映民俗之美、生活之美和生命力之美。
而要達(dá)到這個(gè)要求,就需要民俗攝影者具有“深描”的信念。我們?cè)诖私栌萌祟悓W(xué)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闡釋解釋人類學(xué)理念時(shí)所發(fā)展的“深描”概念。格爾茨認(rèn)為,面對(duì)結(jié)構(gòu)“層疊”或“交織在一起”的文化現(xiàn)象,“首先必須努力把握它們,然后加以翻譯”①[美]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2頁(yè)。。通過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深描”,可以建立抽象概念與具體知識(shí)之間的關(guān)系。其關(guān)鍵點(diǎn),就在于對(duì)研究對(duì)象進(jìn)行微觀分析,通過那些“在限定情景中長(zhǎng)期的、主要是定性的、高度參與性的、幾乎過于詳盡的田野研究所產(chǎn)生的資料”,可以實(shí)現(xiàn)對(duì)抽象概念的思考。②同上,第30頁(yè)。
雖然民俗攝影并不是一種研究行為,但其實(shí)踐者同樣需要以“深描”的信念與方法去理解復(fù)雜的民俗結(jié)構(gòu),建立對(duì)民俗更為全面的認(rèn)知,探求民俗事象背后的人為意義,這樣才能更深刻地把握民俗的動(dòng)態(tài)變化以及人在民俗中的位置。當(dāng)然,“深描”的價(jià)值不只在于“深”,也在于“描”,就像格爾茨所說的:“一部具體的民族志描述是否應(yīng)該引起注意,并非取決于它的作者能否捕捉遙遠(yuǎn)地方的原始事實(shí)……而是取決于它的作者能否說清在那些地方發(fā)生了什么,能否減少對(duì)鮮為人知的背景中的陌生行為自然要產(chǎn)生那種困惑。”③同上,第21頁(yè)。這樣的標(biāo)準(zhǔn)同樣適用于民俗攝影。民俗攝影實(shí)踐者不只是民俗的記錄者和展現(xiàn)者,還應(yīng)該理解民俗的動(dòng)態(tài)性和復(fù)雜性,用鏡頭把握民俗深刻的精神內(nèi)核。
當(dāng)下被公認(rèn)具有極高價(jià)值的民俗攝影作品,其拍攝者無(wú)不踐行著“長(zhǎng)期”“高度參與”的“深描”理念。無(wú)論是莊學(xué)本、王小亭拍攝于西部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影像,還是侯登科的“麥客”系列、陳錦的“茶客”系列等等,都可以看出拍攝者對(duì)民俗事象高度的理解和把握能力。為了拍攝四川人的茶習(xí)俗,攝影師陳錦把自己也變成了一個(gè)茶客,工作之余每天都泡在茶館里,和喝茶的人聊天。陳錦談到:“如果你僅僅作為一個(gè)拍攝者、一個(gè)獵奇者,那只能拍到茶館的表象,要真正深入茶館,必須進(jìn)入茶客的生活,被他們接納,融為一體,這時(shí)他們才不會(huì)把你當(dāng)外人,會(huì)跟你談家長(zhǎng)里短,談心里話,你拍照他也不覺得有什么,拍的畫面才真實(shí)自然,才能真正把握茶館文化的精髓。”④何瑞涓:《陳錦:四川茶館,品出生活變遷》,《中國(guó)藝術(shù)報(bào)》,2018年12月19日,第23版。更進(jìn)一步,近年來西方民俗攝影出現(xiàn)了當(dāng)代藝術(shù)取向——一些拍攝民俗主題的攝影師,開始在美學(xué)層面尋求與被攝對(duì)象的共鳴。例如,英國(guó)攝影師帕特里克·薩瑟蘭(PatrickSutherland)深入位于北印度的斯皮提(Spiti)地區(qū),拍攝當(dāng)?shù)孛袼孜幕嗄辏罱鼛啄辏淖兞藗鹘y(tǒng)紀(jì)實(shí)攝影的拍攝方式,讓拍攝對(duì)象擺出他們自己認(rèn)為“最佳”的拍照姿勢(shì)進(jìn)行拍攝,在此,民俗主體成為了可進(jìn)行文化交流、能在美學(xué)層面產(chǎn)生意義交融的對(duì)象,對(duì)民俗攝影實(shí)踐有極大的啟發(fā)意義。①鄧立峰:《薩瑟蘭與“他我同在”的影像創(chuàng)作》,《中國(guó)攝影報(bào)》,2022年6月3日,第3版。
與之相對(duì),當(dāng)下的民俗攝影實(shí)踐卻大多是“候鳥式”的拍攝,生產(chǎn)著景觀化的圖景。2021年3月,筆者由于工作原因前往位于新疆喀什地區(qū)的塔什庫(kù)爾干塔吉克自治縣,正趕上一家塔吉克人家舉辦婚禮,我們來到婚禮現(xiàn)場(chǎng),卻意想不到地看到了為數(shù)眾多的“長(zhǎng)槍短炮”來到現(xiàn)場(chǎng),在塔吉克人家里走進(jìn)走出進(jìn)行拍攝。打聽之后得知,因?yàn)闀r(shí)值塔吉克族傳統(tǒng)節(jié)日肖貢巴哈爾節(jié),很多攝影師、攝影愛好者專門從內(nèi)地飛到位于國(guó)境邊陲的塔縣進(jìn)行拍攝,正趕上塔吉克人的婚禮,所以一齊進(jìn)行了拍攝……我們完全可以將這種拍攝方式歸類為用以收集資料、保存文獻(xiàn)的“民俗學(xué)攝影”。但如果我們將其看作作為攝影藝術(shù)門類的“民俗攝影”,那這種“候鳥式”的拍攝方式能不能真正把握塔吉克婚俗的精神內(nèi)核?還是僅僅呈現(xiàn)一種“景觀化”的少數(shù)民族圖景生產(chǎn)?恐怕要打一個(gè)大大的問號(hào)。
結(jié) 語(yǔ)
當(dāng)今民俗影像生產(chǎn)面臨著一個(gè)奇怪的現(xiàn)象——打著“民俗攝影”名號(hào)的民俗影像,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傳統(tǒng)媒體和社交媒體上;但關(guān)于民俗攝影的研究卻呈逐年下降趨勢(shì),探討民俗攝影的立論也顯老套與空泛。
要使作為攝影藝術(shù)門類的民俗攝影更健康地發(fā)展,讓具有積攢資料、留存文獻(xiàn)功能的民俗學(xué)攝影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就要清晰厘定兩者的界限,并對(duì)其進(jìn)行體系性闡述。對(duì)于“民俗攝影”而言,要界定其邊界,首先要區(qū)分其與“民俗學(xué)攝影”的關(guān)系,“民俗攝影”應(yīng)與“民俗學(xué)攝影”有所區(qū)別,它具有獨(dú)立存在的藝術(shù)生產(chǎn)價(jià)值,不應(yīng)成為學(xué)術(shù)研究的工具。與此同時(shí),民俗攝影要放棄追求本質(zhì)和規(guī)律的科學(xué)式思維,更側(cè)重于通過鏡頭描述和呈現(xiàn)民俗活動(dòng)的多樣性及復(fù)雜性。在拍攝取向上,民俗攝影應(yīng)該脫離自身對(duì)拍攝對(duì)象的想象和價(jià)值預(yù)設(shè),擺脫“傳統(tǒng)”對(duì)認(rèn)知的束縛,以全面的、動(dòng)態(tài)的視野去觀察民俗活動(dòng)及民俗主體,嘗試?yán)斫猱?dāng)代生活對(duì)民俗的影響和滲透;要樹立以民俗中的人為本體的美學(xué)追求,通過鏡頭展現(xiàn)民俗之美、生命力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