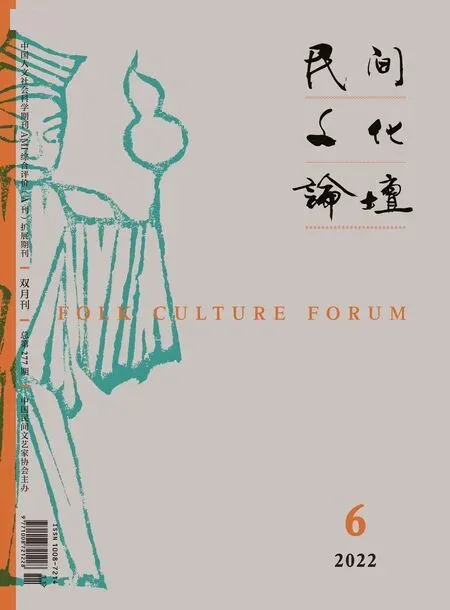清末民初“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的演變
王 蕊
“男主外,女主內(nèi)”是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形成的傳統(tǒng)性別習(xí)俗。它最早起源于儒家經(jīng)典《易經(jīng)》《詩經(jīng)》《禮記》中關(guān)于男女內(nèi)外有別思想的有關(guān)表述,其中包含男女在物理空間上的內(nèi)外之分和性別分工上的內(nèi)外之別。此后,“男外女內(nèi)”的儒家思想在歷代家訓(xùn)和女教書的闡釋下,經(jīng)過唐宋時(shí)期的平民化和明清時(shí)期的習(xí)俗化,逐漸內(nèi)化為女性自覺約束自己行為的民間習(xí)俗規(guī)范。時(shí)至今日,“男主外,女主內(nèi)”依然在日常生活中影響著女性在家庭和職業(yè)之間的抉擇,同時(shí)還影響著大眾輿論對(duì)女性的評(píng)價(jià)。
國內(nèi)外學(xué)者對(duì)中國古代社會(huì)的這一習(xí)俗多有討論,學(xué)者們主要持以下觀點(diǎn):一是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內(nèi)外之間的界限是相對(duì)的、動(dòng)態(tài)的、可以調(diào)適的;①[美]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美]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頁;[美]羅莎莉:《儒學(xué)與女性》,丁佳偉、曹秀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1頁。二是男女內(nèi)外之別象征著一種秩序、禮儀和文明;②高世瑜:《“內(nèi)外”之際與“秩序”格局:宋代婦女》,杜芳琴、王政主編:《中國歷史中的婦女與性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2頁;[美]羅莎莉:《儒學(xué)與女性》,于佳偉、曹秀娟譯,第84、85、86頁。三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中階級(jí)或階層之別是首要問題,性別之分一直是次要問題③[美]伊沛霞:《內(nèi)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胡志宏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頁;[美]許曼:《跨越門閭: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劉云軍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4頁。。這些相關(guān)研究為我們捋清了進(jìn)一步考察“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在近代社會(huì)的演變需要把握的幾個(gè)關(guān)鍵要素。
清末民初中國處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化、政治的諸多巨變之中,如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向工業(yè)社會(huì)轉(zhuǎn)變,傳統(tǒng)儒家文化被質(zhì)疑,帝制被推翻等,約束女性的“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性別習(xí)俗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開始發(fā)生顯著變化。這一時(shí)期相關(guān)的研究成果與之前相比不算多,代表性的觀點(diǎn)有:一是李長(zhǎng)莉認(rèn)為晚清上海開埠通商以后,鄉(xiāng)村女性紛紛進(jìn)入城市從事女傭、女工等職業(yè),她們脫離了對(duì)土地的依附,通過在社會(huì)上工作獲得經(jīng)濟(jì)收入,開始了由“男外女內(nèi)”向“男女并立”的轉(zhuǎn)變。④李長(zhǎng)莉:《從晚清上海看女性家庭角色的近代變遷——從“男外女內(nèi)”到“男女并立”》,張國剛主編:《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第401—422頁。二是程為坤通過對(duì)清末民初北京底層女性所從事的各種職業(yè)狀況的考察,認(rèn)為雖然很多底層女性打破性別分工和男性“并肩工作”,但是“女性在經(jīng)濟(jì)上的掙扎揭示出階層身份和性別身份的相互依存。在公共空間工作對(duì)提升他們的社會(huì)地位沒有什么幫助”。①[美]程為坤:《勞作的女人:20世紀(jì)初北京的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楊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第75頁。李長(zhǎng)莉和程為坤二人的研究對(duì)象都是城市中的底層女性,他們的觀點(diǎn)看似不同,但并沒有實(shí)質(zhì)上的分歧。李長(zhǎng)莉提出“男女并立”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程為坤考量的則是底層女性的社會(huì)地位。在此基礎(chǔ)上,筆者主要從習(xí)俗價(jià)值觀、性別權(quán)力關(guān)系變化以及區(qū)域差異的視角分析“男主外,女主內(nèi)”這一傳統(tǒng)習(xí)俗在清末民初的演變軌跡及其特點(diǎn)。
一、中上層女性社會(huì)角色的轉(zhuǎn)變——基于習(xí)俗價(jià)值觀的考察
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男女內(nèi)外之別無論是在空間上還是性別分工上是一個(gè)相對(duì)的、動(dòng)態(tài)的概念。但是這個(gè)時(shí)期女性沒有獨(dú)立的身份和人格,她們分別屬于父親或兒子所屬的身份或階層,在階層差異凌駕于性別差異之上的時(shí)代,不同階層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傳統(tǒng)習(xí)俗的約束也不相同。“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男女之別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中就是文明和野蠻之別、身份和階層之別②[美]羅莎莉:《儒學(xué)與女性》,2015年,第84—86頁。,它傳達(dá)的價(jià)值觀即是只有遵循男女之別的社會(huì)才是一個(gè)文明的社會(huì),只有“守內(nèi)”“主內(nèi)”的女性才是懂禮儀、身份尊貴的女性。
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中上層女性都認(rèn)同這種價(jià)值觀,“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習(xí)俗內(nèi)化于心,她們會(huì)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去踐行。明清時(shí)期出現(xiàn)了很多才華出眾的女性,通過寫詩、創(chuàng)辦詩社等活動(dòng),聲名和日常生活空間遠(yuǎn)遠(yuǎn)超越閨門③[加]方秀潔、[美]魏愛蓮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但是她們的活動(dòng)也僅限于此,社會(huì)上并未給她們提供一份同男性一樣能夠發(fā)揮才能的職業(yè)。明末清初出現(xiàn)的閨塾師也不是中上層女性所能從事的職業(yè),而是敗落貧窮的書香門第之家的女性迫不得已才從事的職業(yè)。④[美]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時(shí)至近代,一些中上層女性還是深受習(xí)俗約束不能自由外出,更不敢走出家門參加工作。1880年代,山東海邊縣城的女人一般是不能走出大門出去做事的,否則會(huì)遭到恥笑⑤[美]愛達(dá)·蒲露特:《蓬萊寧老太太的自傳》(四),賈祥久譯,《山東文獻(xiàn)》,1976年第4期。書中寧老太太出生于同治六年(1867)。;1890年代,山東海邊鄉(xiāng)村的女人一般也不去地里干農(nóng)活的,只有窮人家的女人才去地里勞動(dòng)⑥[美]艾達(dá)·普魯伊特:《在中國的童年》,載[美]安娜·普魯伊特、[美]艾達(dá)·普魯伊特:《美國母女中國情:一個(gè)傳教士家族的山東記憶》,程麻、程冰等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5、205頁。,傳統(tǒng)女性“除了家庭間的女紅外,如到外面去工作,那就以為失了體面”⑦顧綺仲:《婦女與職業(yè)的關(guān)系》,《婦女雜志》第12卷第12號(hào),1926年12月。。清末的北京城,如果上等人家的小姐沒有家人或傭人的陪伴在大街上拋頭露面會(huì)受到輿論的譴責(zé),林語堂的《京華煙云》詳細(xì)描述了這一狀況。京城豪富之家姚家的兩個(gè)女兒十四歲的木蘭和十二歲的莫愁被曾家邀請(qǐng)吃飯,從曾家回來時(shí)她們二人一起回家沒讓女仆陪同,結(jié)果在路上與大哥相遇后,木蘭不僅被大哥打了一巴掌,還被大哥指責(zé)道:“當(dāng)然我應(yīng)當(dāng)打你。你們女孩子家簡(jiǎn)直要成跑街的浪蕩娘兒們了。你一跑出了家門,就一點(diǎn)身份也不要了。”⑧林語堂:《京華煙云》(上),長(zhǎng)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73、74頁。可見1901年北京上層社會(huì)的女孩不能單獨(dú)外出是為了維護(hù)自己尊貴的身份,這正是“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傳統(tǒng)習(xí)俗的價(jià)值觀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呈現(xiàn)。
烏丙安認(rèn)為傳統(tǒng)習(xí)俗的改變?nèi)Q于三個(gè)重要因素:一個(gè)是習(xí)俗環(huán)境的重大變化,如社會(huì)的革命性變化和文明進(jìn)步,或外族實(shí)行侵略統(tǒng)治迫使原習(xí)俗做重大改變;另一個(gè)是個(gè)人置身于他民族文化習(xí)俗環(huán)境中生活日久的被迫改變;再一個(gè)是個(gè)人接受了文明進(jìn)步或革新的思想教育,主動(dòng)放棄并革除了原習(xí)俗的生活,自覺建立新的文明習(xí)俗規(guī)范。①烏丙安:《民俗學(xué)原理》,長(zhǎng)春:長(zhǎng)春出版社,2014年,第93頁。清末中國受到外來民族的入侵和西方文明的沖擊,這正具備了烏丙安提到的兩個(gè)重要因素,“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的變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fā)生的。
在資產(chǎn)階級(jí)維新派反省和審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并接受西方先進(jìn)文化的過程中,清末民初“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的價(jià)值觀逐漸發(fā)生轉(zhuǎn)變。清末光緒二十一年(1895),梁?jiǎn)⒊凇墩撆畬W(xué)》中提出國之“大治”,在于人人有職業(yè),而婦女有職業(yè)則是國富民強(qiáng)的關(guān)鍵,應(yīng)當(dāng)“國人無男無女,皆可各執(zhí)一業(yè)以自養(yǎng)”②梁?jiǎn)⒊骸墩撆畬W(xué)》,《變法通議附開明專制論》,揚(yáng)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第38、43頁。,婦女要有職業(yè)就要興辦女學(xué)。梁?jiǎn)⒊J(rèn)為女子應(yīng)當(dāng)接受教育、追求自立的言論在當(dāng)時(shí)影響很大,推動(dòng)了女子學(xué)堂的興辦。自此“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學(xué)識(shí)、能自養(yǎng)的女性才是這個(gè)時(shí)代的典范。
清末習(xí)俗價(jià)值觀的轉(zhuǎn)變以及女子學(xué)堂的興辦,使中上層女性拋棄舊習(xí)俗的偏見,開始到師范小學(xué)堂擔(dān)任教師。清末光緒三十年(1904),福州“在山兜尾開辦師范小學(xué)堂,招考八歲以上及十二歲以下幼童肄業(yè)其中,皆延通達(dá)文字之女師為之督課。……任斯席者,半多紳富家之婦”③《特延女師督課》,《教育雜志》,1905年第5期。;一些仕宦以及富紳之家開始送女兒到日本或歐美留學(xué)以接受新式教育,江寧婁慕蘭女士“負(fù)笈游學(xué)英國”,一些“儒家閨秀”留學(xué)日本“實(shí)效女學(xué)校”,“諸女史皆非常熱心于實(shí)業(yè),富于記憶力且精力強(qiáng)固,修業(yè)月余而進(jìn)步騰踴”④《婁女士留學(xué)西洋》《中國女留學(xué)生之名譽(yù)》,《教育雜志》,1905年第16期。。這些留學(xué)女生學(xué)成回國后推動(dòng)了女學(xué)堂的創(chuàng)辦和擴(kuò)充。留學(xué)女性不僅到女學(xué)堂任職,有的還獨(dú)立創(chuàng)辦女學(xué)堂,如1907年曾經(jīng)留學(xué)日本的秋瑾?jiǎng)?chuàng)辦大端女子學(xué)堂,1909年曾經(jīng)留學(xué)日本的劉青霞創(chuàng)辦華英女學(xué)堂等等。1907年,中國女學(xué)堂數(shù)量已達(dá)436所,女生人數(shù)為15676人。⑤謝長(zhǎng)法:《清末的留日女學(xué)生及其活動(dòng)與影響》,《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6年第4期。留學(xué)女性在接受了新教育和新思想之后,認(rèn)識(shí)也發(fā)生了改變,她們要做的不只是謀取一份職業(yè),而是準(zhǔn)備承擔(dān)起掃除千年惡習(xí)以改良社會(huì)的重任⑥林士英:《論女子當(dāng)具獨(dú)立性質(zhì)》,1911年5月,轉(zhuǎn)引自許力以等主編:《20世紀(jì)中國經(jīng)世文編》(清末卷),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8年,第579頁。。中上層新知識(shí)女性習(xí)俗價(jià)值觀及思想認(rèn)識(shí)的改變,又推動(dòng)了她們邁出家門走向社會(huì),逐步實(shí)現(xiàn)從家庭角色到社會(huì)角色的轉(zhuǎn)變。
從清末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的信件中我們可以切實(shí)地看到“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習(xí)俗在北京城上層社會(huì)女性中發(fā)生的變化。1907年9月,她在一封信中寫道:
現(xiàn)在的中國和五年前的中國大不相同了。處處都能感覺到變化,尤其是家庭中的女性,變化特別明顯。北京城內(nèi)現(xiàn)在有17所女子學(xué)校,均由中國女性資助和管理,她們之中有一些是宮眷。
……
我收到張夫人的來信,她在信中提到了她們學(xué)校的一些工作。她的小腳已經(jīng)不再受捆綁之苦,她能身心自由地隨意騎馬飛奔了。肅親王的第三個(gè)妹妹在北京擁有一所有八十多名學(xué)生的學(xué)校。她就待在學(xué)校里,教學(xué)工作每天從早上10點(diǎn)一直持續(xù)到下午3點(diǎn)。①[美]薩拉·康格:《北京信札——特別是關(guān)于慈禧太后和中國婦女》,沈春蕾、孫月玲、袁煜、綦亮譯,李菁審校,南京:南京出版社,第306、307頁。
薩拉·康格在信中所描述的這些京城女性基本上都是皇室貴族或朝中大臣的女性家庭成員,這些上層社會(huì)的女性不再遵循“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規(guī)范秩序,她們開始走出深宅大院,資助和管理女子學(xué)校,完成了從家庭角色到社會(huì)角色的轉(zhuǎn)變。北京城發(fā)生顯著變化的時(shí)間在1907年,而這一年正是清政府頒布《女子小學(xué)堂章程》《女子師范學(xué)堂章程》的時(shí)間,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女子教育納入學(xué)校教育制度的開始。教育和職業(yè)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接受新教育的中上層女性也擁有了選擇到社會(huì)上從事工作的機(jī)會(huì)和能力。可以說,“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對(duì)于中上層女性在空間和性別分工方面的規(guī)范與制約逐漸被打破。
民國成立之初,女子從事的職業(yè)種類已經(jīng)比較多樣,“女子職業(yè),上則教習(xí),下則傭媼,其間距離差太遠(yuǎn)。且教習(xí)非盡人可為,即保姆、產(chǎn)婆、看護(hù)婦,亦皆非普通之執(zhí)事,傭媼則奴隸之變相,不得認(rèn)為一職業(yè)。惟職工商業(yè),需人特眾,又非甚繁難,雖下材可以勉而為之。故為一般女子謀生計(jì),必先此二者。職工種類繁多,如前所稱,郵電、印刷、打字等,今日殆成女子之專利事業(yè)矣”②《〈江亢虎先生忠告女同胞書〉續(xù)》,《女子白話旬報(bào)》,1912年第6期。。有的知識(shí)分子認(rèn)為女性從事的最為高尚的職業(yè)就是做女紅、做教員、在醫(yī)院做看護(hù),女紅就是從事紡織、刺繡和縫紉工作,以中下層女性為主,教員和看護(hù)主要是中層女性在做。③朱文輝:《南昌婦女的現(xiàn)狀》,《婦女雜志》,1928年第14卷第1號(hào)。作者把職業(yè)分高低貴賤顯示了其時(shí)代局限性,但是在作者的認(rèn)識(shí)中,女性已經(jīng)是具有獨(dú)立身份的群體,她們不再附屬于男性所屬的階層,而是以女性所從事的職業(yè)來區(qū)分她們社會(huì)地位的高低,這一點(diǎn)已是很大的進(jìn)步。民國初年,正如程為坤所言,“女性加入勞動(dòng)力大軍慢慢被認(rèn)可”④[美]程為坤:《勞作的女人:20世紀(jì)初北京的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楊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第75頁。,中上層女性這一時(shí)期基本都在銀行、醫(yī)院、學(xué)校以及政府機(jī)關(guān)工作。
20世紀(jì)20年代新知識(shí)分子普遍認(rèn)為女子有相當(dāng)?shù)穆殬I(yè),通過勞動(dòng)能夠自食其力是一件光榮的事情,這樣的女子是值得尊敬的。⑤徐克嫻:《婦女職業(yè)問題》,《女學(xué)界》,1923年第15期,第3頁。這種價(jià)值觀念通過報(bào)紙雜志等媒體得到較為廣泛傳播。新知識(shí)分子對(duì)于上層女性不勞而獲的行為進(jìn)行批判,對(duì)于“無產(chǎn)階級(jí)”的婦女卻持有不同的態(tài)度,認(rèn)為她們除了“縫紉灑掃”、“撫育子女”之外還要到工廠做工,“那才是社會(huì)的生利者!我們要怎樣的尊敬啊。”⑥玖:《我的眼光中之煙臺(tái)婦女》,《婦女雜志》,1928年第14卷第1號(hào),第34頁。
二、從“男外女內(nèi)”到“女兼內(nèi)外”——基于性別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考察
清末民初,女性越來越多地到社會(huì)上工作是否意味著女性在社會(huì)和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顯然兩者之間并不等同。關(guān)于社會(huì)地位,筆者贊同程為坤的觀點(diǎn),即底層女性雖然想方設(shè)法出去工作以賺錢謀生,但是她們的社會(huì)地位并未提高。關(guān)于家庭地位,女性是否如李長(zhǎng)莉所說開始走向“男女并立”了呢?李長(zhǎng)莉認(rèn)為從鄉(xiāng)村來到城市的農(nóng)村家庭,實(shí)現(xiàn)了“家庭土地所有權(quán)與男人及其家庭的分離,使得男人和婦女在家庭中分擔(dān)的生產(chǎn)者角色,不再由土地所有權(quán)來決定,而是由市場(chǎng)需求來決定”,這樣使得男女“站在同等的地位”面對(duì)市場(chǎng),①李長(zhǎng)莉:《從晚清上海看女性家庭角色的近代變遷——從“男外女內(nèi)”到“男女并立”》,張國剛主編:《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第415頁。從而出現(xiàn)“男女并立”的局面。筆者對(duì)此持不同的看法。如果說脫離了對(duì)土地所有權(quán)的依賴,男女就能“站在同等的地位”,那么清末之前城市底層家庭基本處于無土地的狀態(tài),家庭中的女人都是出去做傭工、從事小商販或三姑六婆等職業(yè),那么她們是否可以說達(dá)到了“男女并立”呢?顯然沒有。男女是否“并立”不能只是從土地所有權(quán)和經(jīng)濟(jì)收入的高低來判斷,而是應(yīng)當(dāng)從男人和女人在家庭中享有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是否相同來看,也就是從性別權(quán)力關(guān)系來考察。
清末民初隨著近代男女平權(quán)思想的傳播,女性逐漸可以跨出家門去學(xué)校、醫(yī)院以及工廠等單位從事一份職業(yè)。“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分工模式被打破是社會(huì)的一大進(jìn)步,但是如果從男女雙方所處的性別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視角來看,女人遠(yuǎn)未獲得與男人“并立”的地位。“男女并立”應(yīng)當(dāng)是男女分工一樣,共同治理家事與外事,共同決定家庭重要事務(wù),共同擁有家庭財(cái)產(chǎn)的支配權(quán)。女性有了工作,有了經(jīng)濟(jì)收入,家庭地位開始提高,但并不代表著實(shí)現(xiàn)了“男女并立”。對(duì)于清末民初社會(huì)上“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的轉(zhuǎn)變,用“女兼內(nèi)外”來概括更為合適。
清末民初各階層女性有了參加工作的權(quán)利,但是男性并未發(fā)生相應(yīng)的改變,繁重的家務(wù)勞動(dòng)依然是由女性獨(dú)自承擔(dān),“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中只是女性發(fā)生了內(nèi)外兼顧的單向轉(zhuǎn)變。
民國初年,受過學(xué)校教育的女性的學(xué)識(shí)和能力逐漸在社會(huì)上得到認(rèn)可,“教育既遍施于男女,不特女子之聰明者,能駕男子而上之。即一般之女子,在學(xué)成績(jī),亦不見劣于男子”,既然如此,她們便可以從事與男子相同的職業(yè),“故今日之女子,不僅從事于家庭之職業(yè),更從事于社會(huì)之職業(yè),不止于良妻賢母之國民,更兼為良工巧匠、詩人、學(xué)士之國民,此職業(yè)發(fā)達(dá)之結(jié)果。女子活動(dòng)之范圍,殆于男子活動(dòng)之范圍相吻合,工場(chǎng)、市廛、學(xué)校、政府,無往不見其足跡也。”②陶履恭:《女子問題》,《新青年》,1918年第1號(hào)。該文雖然認(rèn)為女子享有同男子相同的工作權(quán)利,但是可以看出作者對(duì)于女性的要求是雙重的,即無論女子是否從事社會(huì)職業(yè),家事的職責(zé)都應(yīng)當(dāng)由女子承擔(dān)。民國初年社會(huì)輿論以及女性本身基本都持以上觀念。1926年太原的報(bào)紙《晉民快覽》發(fā)表的一篇關(guān)于男女性別分工的文章中,作者認(rèn)為理想的狀態(tài)是“婦女除治理家政外,兼作有益之工藝。如育蠶、種菜、刺繡、養(yǎng)蜂等,以其所得補(bǔ)助家計(jì)”;“農(nóng)工商業(yè)之家庭,婦女應(yīng)勉為男女同工之操作”;“軍警政教各界之家庭,婦人應(yīng)負(fù)做飯、縫衣及料理內(nèi)事之全責(zé)”。③《理想的家政》,《晉民快覽》,1927年五周年紀(jì)念號(hào)。直到1939年,關(guān)于婚后女子職業(yè)方面的調(diào)查顯示,被調(diào)查女性中,贊同女子應(yīng)該完全在社會(huì)上服務(wù)者只有11.45%,贊同女子應(yīng)該完全在家主持家務(wù)者占5.72%,贊同女子應(yīng)該社會(huì)與家庭兼顧者占69.79%。④劉臻瑞:《成都市婦女社會(huì)活動(dòng)調(diào)查》,李文海主編:《民國時(shí)期社會(huì)調(diào)查叢編》(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73頁。這項(xiàng)調(diào)查反映的只是女性的一種意愿,實(shí)際生活中,在家中主持家務(wù)和兩者兼顧的情況會(huì)更多。
在學(xué)校、行政單位以及工廠工作的女性對(duì)于來自家庭內(nèi)外的雙重壓力深有感觸。婚后繼續(xù)在天津某一學(xué)校工作的孫稚平認(rèn)為:“一個(gè)已出嫁的女子在外面做事同時(shí)還得撫育孩子,管理家政,比男子更多了一重任務(wù),在形體精神上所感到的困疲,可以不言而知。”①蔣逸霄:《津市的職業(yè)婦女生活(卅六續(xù)):教育局的女職員》,《大公報(bào)》,1930年5月3日,第9版。在天津行政機(jī)關(guān)從事文書工作的胡強(qiáng),也是兩個(gè)年幼孩子的媽媽,為照顧孩子雇著兩個(gè)奶媽,即便如此,回到家中照顧孩子的事情還是忙得不可開交。②蔣逸霄:《津市職業(yè)的婦女生活(八續(xù)):市黨部的兩位女職員》,《大公報(bào)》,1930年2月26日,第12版。對(duì)于這些繁雜忙碌的家庭事務(wù),她們的丈夫都是置身事外的。在工廠工作的女工在家庭中的狀況更是如此,在紗廠、絲廠、襪廠和布廠的女工,“住在家里的,還須忙著家務(wù)”③徐獨(dú)夫:《無錫婦女的勞工生活》,《婦女雜志》第14卷第1號(hào),1928年1月。,她們收入低,沒有經(jīng)濟(jì)能力雇傭保姆,因此更加忙碌和勞累。陳婉慈對(duì)男女在家庭中不平等的現(xiàn)實(shí)有十分透徹的觀察:“在現(xiàn)代的家庭組織下面,家庭工作,還是全歸女子負(fù)擔(dān)。所以她們?cè)诠S的勞動(dòng)時(shí)間,雖然與男工一樣,但是男工一經(jīng)出了工場(chǎng),就全然是休息的時(shí)間,而女工離了工場(chǎng),回到家里,還要料理茶飯,縫洗衣服,看管兒女,種種事情。所以她們的辛苦,自然比男工更甚。”④陳婉慈:《女工問題》,《農(nóng)工旬刊》,1928年第3期。總而言之,民國初年在夫妻二人和孩子組成的核心小家庭中,丈夫并沒有同妻子“并立”以共同面對(duì)家事,他們所治理的家事只是對(duì)于家庭重要事務(wù)的決定權(quán)而不是承擔(dān)起家務(wù)勞動(dòng)和照看兒女的責(zé)任。
女性從事職業(yè)分擔(dān)了男性的家庭負(fù)擔(dān),減輕了男性養(yǎng)家的壓力,但是男性并未因此與女性一起分擔(dān)家務(wù)和養(yǎng)育兒女,可以說“女兼內(nèi)外”是“男外女內(nèi)”習(xí)俗在清末民初呈現(xiàn)的一個(gè)顯著變化。“女兼內(nèi)外”制約著女性的職業(yè)發(fā)展,影響著女性的日常生活。人的精力有限,女性如果既要治理家事又要從事職業(yè),上層女性在傭人的幫助下也許能夠兩者兼顧,但是一般女性會(huì)出現(xiàn)家事和工作相沖突的情形,她們一般會(huì)選擇以一方為主。女性如果選擇以家事為主,那么工作只能是兼職,這樣導(dǎo)致女性的社會(huì)角色不受重視,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從家庭角色到社會(huì)角色的轉(zhuǎn)變。許多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工作的婦女一般處于這種境地。女性如果選擇以工作為主,為了能夠在職業(yè)上開辟新天地,許多選擇單身,這一現(xiàn)象在清末民初的職業(yè)女性中特別突出。中產(chǎn)階級(jí)以上的婦女,“她們的所以投身于職業(yè)界,完全因?yàn)橛X得受人豢養(yǎng),是一種喪失人格,非常可恥的事情,所以毅然決然的打破家庭的樊籠,要在職業(yè)界中自己開辟一個(gè)新天地”,“目前最顯著的現(xiàn)象,就是此等婦女,大多數(shù)是抱獨(dú)身主義者”,⑤晏始:《中國職業(yè)婦女的三型》,《婦女雜志》第10卷第6號(hào),1924年6月。女性獨(dú)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家庭中女性并未獲得與男性同等的地位。
三、區(qū)域差異——基于經(jīng)濟(jì)文化稟賦的考察
清末民初“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習(xí)俗發(fā)生了以上變化,但是社會(huì)上很多地方依然因循舊俗。1911年美國社會(huì)學(xué)家E.A.羅斯注意到中國社會(huì)中內(nèi)外之別與女性地位之間的關(guān)系,“那些女人——?jiǎng)澊摹⑻羲摹叩氐暮蜔鸬模杂傻卮┧笾5怯械匚坏呐藚s不能如此,她們只能坐在封閉的馬車?yán)锘蜾伾喜嫉囊巫由稀!雹轠美] E.A.羅斯:《變化中的中國人》,公茂虹,張皓譯,北京:時(shí)事出版社,1998年,第166頁。1928年,南昌大多數(shù)女性仍在“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舊俗規(guī)制下。“南昌的婦女,多半是靠男子吃飯的,自己很少生利,大家只有哺乳弄飯……的責(zé)任,這是受了‘男子治外’‘女子治內(nèi)’的教訓(xùn)的影響。”⑦朱文輝:《南昌婦女的現(xiàn)狀》,《婦女雜志》第14卷第1號(hào),1928年1月。舊俗與新俗同時(shí)并存的狀況正是清末民初這一過渡時(shí)期的特點(diǎn)。總的來說,清末民初城市與鄉(xiāng)村、南方與北方在“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的演變中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清末民初工廠一般建在城市,給城郊女性提供了到工廠做工的機(jī)會(huì),廣大農(nóng)村女性機(jī)會(huì)卻很少,這一城鄉(xiāng)差別使農(nóng)村女性依然處于以家事為主、農(nóng)事為輔的性別分工模式中,可以說“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習(xí)俗在農(nóng)村中變化不大。城市的工業(yè)化是導(dǎo)致城鄉(xiāng)女性在從事社會(huì)職業(yè)方面存在差異的原因之一,正如時(shí)人所云,“只以工廠設(shè)在城市方面,所招收的仍不過是一小部分的女子,而鄉(xiāng)村的一大部分的婦女,遂終身曠廢無所事事。”①炎:《鄉(xiāng)村婦女職業(yè)問題》,《興華》第23卷第37期,1926年9月。湖南黔陽“絕對(duì)尋不出一個(gè)婦女工廠,各商店、各機(jī)關(guān)、各學(xué)校,也都沒有婦女插足的地位,所以全縣的婦女,沒有一個(gè)有專門職業(yè)的。”②黃俊琬:《黔陽婦女的生活狀況》,《婦女雜志》第14卷第1號(hào),1928年1月。其次就是鄉(xiāng)村“求知識(shí),學(xué)技能”的女子太少③步毓芝:《我國鄉(xiāng)村婦女職業(yè)的范圍》,《農(nóng)民》第3卷第15期,1927年7月。,大多數(shù)鄉(xiāng)村女子都沒有能力去爭(zhēng)取在各種行業(yè)工作的機(jī)會(huì)。很多鄉(xiāng)鎮(zhèn)婦女都處在傳統(tǒng)的“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規(guī)制下,在社會(huì)上工作的人數(shù)極少。例如,20世紀(jì)30年代河北一個(gè)鄉(xiāng)鎮(zhèn)的民眾還持有這種男女內(nèi)外之別即是身份高低之別的習(xí)俗價(jià)值觀,家境好一點(diǎn)的人家,“便以為婦人趕集是一件很不體面的事”④潘玉林:《一個(gè)村鎮(zhèn)的農(nóng)婦》,《社會(huì)學(xué)界》1932年第6卷,1932年。,外出趕集都不被認(rèn)可,更不用說外出工作了。
清末民初南北方城市工業(yè)化程度不同導(dǎo)致女子工廠以及女工數(shù)量方面有著顯著差距,女工數(shù)量的不同使得南北方在“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變革的方式、廣度存在差異。1927年實(shí)業(yè)記事有云:“近來女子職業(yè)日益發(fā)展,如女子商店、女子工廠,南部各省已層見不窮,惟北部各埠尚稱缺乏。(天津)前數(shù)年女子商店雖設(shè)數(shù)處,而女子工廠實(shí)不多見。”⑤《國內(nèi)實(shí)業(yè)記事:天津貧民女工廠成立》,《實(shí)業(yè)鏡》,1927年第4期。天津與廣州相比,天津于1935年在女工人數(shù)較多的紡織工廠中有1454名女工⑥《國內(nèi)勞工消息——七月份》,《國際勞工通訊》,1935年第11號(hào)。,1929年廣州僅火柴業(yè)中就有女工1萬余人⑦梁鐵生:《廣州市婦女職業(yè)之調(diào)查》,《新建設(shè)》,1929年第6期工業(yè)號(hào)。。就北京和上海而言,北京工業(yè)落后于上海。清末民初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工業(yè)并不發(fā)達(dá)。1929年北京的工人總數(shù)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上海,1929年上海工人共有28萬余人,⑧[美]程為坤:《勞作的女人——20世紀(jì)初北京的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楊可譯,第40頁。北京工人總數(shù)僅7千余人⑨龔駿:《中國都市工業(yè)化程度之統(tǒng)計(jì)分析》,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3年,第193頁。,女工人數(shù)北京與上海相比會(huì)存在更大的落差。北方城市自下而上打破“男外女內(nèi)”性別分工的女工的力量十分薄弱,其“男外女內(nèi)”習(xí)俗觀念主要是在國家教育制度的變革和“男女平等”思想影響下自上而下逐步發(fā)生改變的。北方接受新思想和新教育的女性人數(shù)不如南方女工人數(shù)多,因此打破“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的女性人數(shù)南方比北方多,也可以說“女兼內(nèi)外”的現(xiàn)象在南方比在北方普遍。
結(jié) 語
“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傳統(tǒng)習(xí)俗是對(duì)中國社會(huì)影響極其深遠(yuǎn)的性別習(xí)俗之一。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化以及制度的變遷,清末接受新思想的知識(shí)女性開始突破“男主外,女主內(nèi)”空間分隔的性別規(guī)范,使內(nèi)與外徹底成為一個(gè)相對(duì)性的概念。從習(xí)俗傳遞的價(jià)值觀來看,傳統(tǒng)的“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傳遞的價(jià)值觀是遵循男女之別的社會(huì)才是一個(gè)文明的社會(huì),“守內(nèi)”“主內(nèi)”的女性是懂禮儀、身份尊貴的女性,至清末民初,這種價(jià)值觀被顛覆,新知識(shí)青年認(rèn)為有學(xué)識(shí)、能自養(yǎng)的女性才是值得尊敬的女性。價(jià)值觀念的轉(zhuǎn)變加之女子學(xué)校教育制度的實(shí)施,推動(dòng)了北方社會(huì)中上層女性逐步突破男女性別分工對(duì)于女性的規(guī)制,開始實(shí)現(xiàn)從家庭角色到社會(huì)角色的轉(zhuǎn)變。
清末民初,在“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變革過程中,女性雖然突破“內(nèi)”的束縛,但是男性并未突破“外”的規(guī)制,即社會(huì)輿論并未要求男人同女人一樣承擔(dān)家事,家事依然是女人的份內(nèi)之事,同時(shí)社會(huì)上也并未給予女人同男人一樣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和工資報(bào)酬。可以說,民國初年城市中“男主外,女主內(nèi)”習(xí)俗發(fā)展成為“女兼內(nèi)外”,而不是“男女并立”。
由于區(qū)域間經(jīng)濟(jì)文化特質(zhì)的不同,“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習(xí)俗在城市和鄉(xiāng)村、南方和北方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