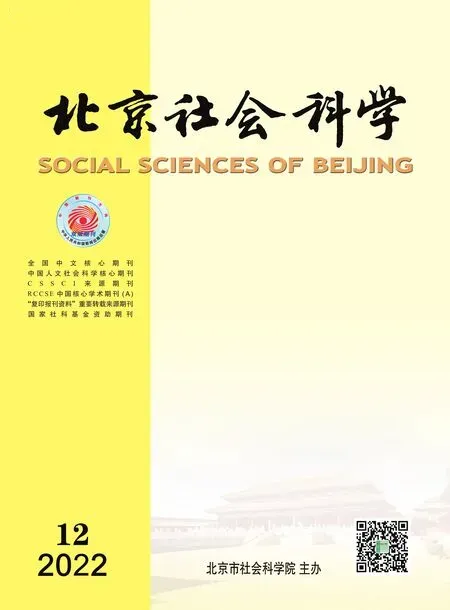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非洲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連 增 孫藝華
一、引言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斷深化合作,突出體現在對非洲直接投資呈迅猛增長趨勢。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20年,中國在非洲直接投資存量達434億美元,相較于2013年增加超過100億美元,其中,建筑業、采礦業和制造業為存量最多的三個行業,占比分別為34.9%、20.6%和14.1%。
中國在非洲國家日益增長的經濟活動引起了學術界和國際社會的關注與思考。西方學界用“西方大國殖民經驗”解讀中國對非投資,并時常與“對非掠奪”結合起來,認為中國對非投資本質上是要掠奪非洲的資源。[1-2]
中國在非經濟活動是否對非洲國家產生了消極影響?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以中國對非投資為切入點,試圖證明中國對非投資顯著促進了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升級。出口貿易結構在投資前后的變化客觀體現了東道國是否利用外資提升企業生產率進而提高其內生增長動力、[3]實現收入增長,[4]這是考察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之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駁中國對非投資是“對非掠奪”的觀點。在此基礎上,探究東道國體制對出口貿易結構的直接和間接效應,以駁斥“中國對非投資是腐敗的交易”的相關論調,并論證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原則,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貢獻提供實證支持。
二、文獻述評與理論闡釋
(一)文獻述評
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一直是備受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已有研究主要將投資和貿易的關系分為替代和互補兩大類。早期研究主要關注替代效應,關稅等壁壘會產生資本邊際產量的差異,進而導致資本的國際流動。[5]而且,對外投資使原本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進口替代部門得到發展,從而減少貿易量。費農提出的生命周期也說明投資和貿易是一種轉化關系,在產品的不同階段,廠商為實現利潤最大化,會在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中進行選擇,且隨著新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投資和貿易的轉化關系也會越來越明顯。[6]
另一部分研究認為,投資和貿易存在著互補效應,并從要素流和產品流的角度進行了解釋。其中的代表人物小島清(Kojima)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生產要素的總體轉移,可以使投資前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得以利用,從而生產出可以進行國際貿易的產品。[7]隨后的研究也從技術差別、規模經濟、關稅、不完全競爭市場和企業生產率等角度分析了貿易和投資之間存在著互補的關系。[8-9]相關的實證研究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顯著增加了東道國的出口貿易量。對外直接投資流入既提高了東道國的生產能力和出口供應潛力,又提供了更多出口市場信息和與母國供應鏈之間更緊密的聯系。[10]在以非洲為樣本的研究中,王嫚、閆黎麗實證檢驗了2003-2008年中國對46個非洲國家直接投資的進出口貿易效應,結果表明,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對貿易起促進作用。[11]也有文獻從貿易結構的角度刻畫了投資的貿易效應,并得到投資的流入提高了一國出口技術復雜度的結論。[12]在衡量貿易結構的指標選擇上,主要有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出口技術復雜度、出口產品質量、某類產品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例或市場份額四大類。[12-13]
綜上可見,當前國內外關于投資對東道國貿易效應的研究,由于研究區域、對象、樣本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到不同的結論。已有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的研究中更多以中國的出口為視角,[14]或者只使用國家層面的數據進行分析,[11]大多數研究使用引力模型解釋進出口貿易量的變化,但很少關注貿易結構,并經常與“對非援助”相結合。[15]此外,已有研究還缺少綜合非洲制度、官方語言和地理區位因素上的特點等方面的探討。
(二)理論闡釋
非洲仍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地區,自然稟賦、人口條件、氣候環境和政治文化等都在客觀上約束了非洲的經濟發展,盡管很多非洲國家大力發展民族工業,但資源和初級產品依舊占據著非洲出口產品的較大比重,在工業發展方面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單從東道國的角度來看,資本和技術流入能夠提高東道國的生產能力和出口供應潛力,使非洲國家的出口結構向更適宜本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方向轉換,比如中低端制造業產品。[15-16]同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也為非洲國家企業提供了更多出口市場信息,有利于減少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促進經濟主體之間的合作。[17]雖然對于非洲國家來說,融入國際分工可能是進入了發達國家“外包”出來的生產環節和生產階段,但相對于其現有水平來說是更為高端的環節和階段,[18]實現了出口貿易水平的提高。
從母國和東道國的互動角度來看,中國和非洲國家在產業結構上具有一定的互補性,中國現階段面臨的產能過剩問題可以與非洲的工業化進程有機結合。[19]相比于在經濟和技術上更有優勢的發達國家,非洲國家與中國的技術差距較小,在技術學習上相對容易,技術溢出效果會更加明顯。[20]在投資項目領域,中國在非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是道路、電力等,為非洲國家實現出口貿易結構升級提供基礎保障。此外,教育是技能和知識傳播的渠道,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的同時也注重培訓當地專業人才、向非洲當地派遣專家、為非洲學生提供來華留學的獎學金和建設教育基礎設施等,以“授人以漁”的方式幫助非洲國家提升生產能力。因此,中國對非洲投資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和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是實現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升級的渠道。
三、實證數據和模型
(一)計量模型構建
本文基準回歸模型設定為:
manui,t=β0+β1lnfdiflowi,t-1+β2Zi.t+γi+γt+εi.t
(1)
式(1)中,i、t分別表示國家和年份,被解釋變量manui,t為非洲國家i在t年制造業出口占商品總出口的比值;核心解釋變量lnfdiflowi,t-1為中國對非洲國家i在t-1年直接投資流量,Zi.t為其他控制變量,包括非洲國家人均GDP(lngdppppi,t)、勞動資源(lnlabori,t)、自然資源(lnnaturei,t)、匯率(lnexchangei,t)、制造業附加值(lnvalueadd)等,γi為國家固定效應,γ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二)樣本選擇、變量說明和數據來源
1.樣本選擇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54個非洲國家,樣本區間為2003-2017年,樣本類型為面板數據。考慮到群島國家的經濟不穩定性及國家內部動亂問題對數據造成的影響,剔除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爾、索馬里、南蘇丹4個國家;剔除了人均GDP、勞動力資源等基本數據缺失的國家和地區,[20-21]最終得到40個國家的數據。
2.被解釋變量
依據現有研究貿易結構的文獻做法及非洲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制造業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乘以100作為被解釋變量來反映一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利用manui,t表示。中國在非洲的制造業累計投資年增長在10%左右,2003年至2014年,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新建項目中,制造業占了最大的比重。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指標(WDI)數據庫。
3.核心解釋變量
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流量是本文的關鍵解釋變量,數據來自中國商務部發布的各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用fdiflowit表示中國對非洲i國t年的直接投資流量,單位是萬美元。為了不出現較大的方差差異,對fdiflow進行以下處理:
(2)
4.控制變量
參考相關文獻,控制變量包括非洲國家的人均GDP、自然資源、勞動資源、匯率和制造業附加值。所有的控制變量均取對數值,數據同樣來自WDI數據庫。一國的人均GDP可以反映其經濟發展水平,將人均GDP引入模型反映市場對投資和貿易的影響,按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用lngdpppp表示。自然資源用自然資源租金總額占GDP的百分比來衡量,自然資源租金總額是石油租金、天然氣租金、煤炭(硬煤和軟煤)租金、礦產租金和森林租金之和,用lnnature表示。勞動資源用一國的勞動力總數來衡量,是指包括所有年滿15周歲、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對從事經濟活動人口所作定義的群體,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用lnlabor表示。官方匯率指相當于1美元的本幣單位,是時期平均值,用lnexchange表示。制造業附加值是一個部門在總計了各項產值并減去了中間投入之后的凈產值,用lnmanup表示。
四、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基準回歸結果見表1所示。在控制國家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并加入其他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lnfdiflowi,t-1的系數均顯著為正,由此反映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非洲東道國制造業出口比例的增加,使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得到優化,意味著東道國工業化程度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均有所提高,內生增長動力增強。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在其他控制變量中,東道國經濟規模(lngdpppp)的系數為負,且除第(3)列外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對于較不發達的國家而言,中國投資的出口貿易結構優化作用更加明顯;東道國勞動力資源(lnlabor)、制造業附加值(lnvalueadd)和匯率(lnexchange)的系數均不顯著,表明勞動力資源的豐富程度和匯率對非洲國家出口貿易結構改善的作用不明顯;東道國的自然資源系數(lnnature)基本上顯著為負,反映了豐富的自然資源并不能促進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二)內生性問題:工具變量
基準回歸中通過控制年份和國家層面的固定效應,以及加入控制變量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在此基礎上,使用中國一般公共財政支出這一指標作為工具變量。[15]已有研究驗證了財政支出與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關系,[22]而中國的財政支出對非洲東道國的出口貿易結構不產生直接影響,滿足了工具變量外生性要求。中國的財政支出數據來自中國商務部,與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對應,財政支出的指標同樣取對數并用前一期數據進行IV-2SLS回歸。回歸結果見表2中第(1)列所示,核心解釋變量(lnfdiflowi,t-1)依舊顯著為正。Cragg-Donald Wald檢驗的F統計值為12.372,大于Stock-Yogo弱工具變量檢驗在15%水平的臨界值8.69,可以拒絕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
(三)穩健性檢驗
1.動態效應:系統GMM估計
由于東道國當期出口貿易可能會受到上一期出口情況的影響,本文加入了非洲國家制造業出口比例的前一期,采用系統GMM估計方法以考慮投資和貿易關系中存在的動態滯后性,模型設定為式(3)。估計結果為表2的第(2)列,使用系統GMM估計后的核心解釋變量(lnfdiflowi,t-1)的系數為正且依舊顯著,說明考慮了出口貿易結構的動態因素之后,中國對非洲投資依舊是促進了對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manui,t=β0+β1lnfdiflowi,t-1+β2manui,t-1+β3Zi.t+γi+γt+εi.t
(3)
2.Tobit估計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制造業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數值在0-1之間,乘以100后取值在0-100之間,本文使用Tobit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見表2第(3)列,核心解釋變量(lnfdiflowi,t-1)的系數為0.629且較為顯著,可以認為基準回歸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3.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另一種測算:出口技術復雜度
為了確保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采用另一種衡量出口貿易結構的指標,即出口技術復雜度(不包含服務貿易)。非洲i國t年的出口技術復雜度記為ESit,其計算公式為:[23]
(4)


表2 內生性問題處理和穩健性檢驗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分行業檢驗
中國對非直接投資流量促進了非洲東道國制造業出口比例的增加,體現了中國對非投資能夠提高非洲的出口能力,但使用對非直接投資流量這一指標并不能反映投資的具體類型和行業,本文繼續探究中國企業在不同行業投資對非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

(5)
國家層面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依舊來自《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投資企業數量則是在孫楚仁等①的基礎上,[25]整理了中國商務部發布的“境外投資企業(機構)名錄”中2003-2014年中國企業對非洲直接投資數據,并與WDI數據庫中10類②出口產品分類對應,得到中國在非洲投資企業920家,再對這些企業按照國家、年度、行業和企業個數進行匯總,得到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的行業數據。每年中國在非洲某國投資某一行業投資存量的前一期作為解釋變量,使用(1)式進行回歸,被解釋變量為每個行業產品的出口比例。
表3為分行業檢驗結果,(1)列為全行業回歸,(2)列至(4)列分別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③,除第(2)列外,其他各列回歸在控制了國家和年份固定效應的基礎上,還控制了行業固定效應。全行業的結果顯著為正,說明總體上支持中國對非直接投資促進非洲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升級的結論,并且從(2)列核心解釋變量顯著為負、(4)列顯著為正來看,在長期,中國對非投資正向著從第一、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升級。

表3 對外直接投資的分行業檢驗結果
五、擴展分析和機制探討
(一)基于制度質量的檢驗
非洲在經濟表現不佳的同時也在遭受著流血沖突,經濟學家保羅·克利爾認為,沖突本身是軟弱的制度帶來的。中國企業在非投資面臨著非洲國家政治風險,同時中國對非投資也被質疑存在著“腐敗的交易”和“透明度低”的問題,因此討論非洲國家的制度特征、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結構的關系,能夠為中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決策提供一些參考。
制度質量主要通過兩條路徑對投資的貿易效應產生影響:一是東道國制度質量自身影響其出口貿易的直接效應;二是制度質量與投資的交互效應,也可以認為是由制度質量傳導的間接效應。一個國家的制度質量通過影響其營商或投資環境,進而影響該國利用外資提升本國內生增長動力的能力。但已有研究因在樣本選擇上存在著差異,制度質量對貿易影響的作用方向上并沒有一致的結論。
為探究非洲國家制度質量的異質性是否對投資的貿易效應有不同的影響,首先在解釋變量加入衡量非洲國家制度的指標,以探究制度質量對出口貿易結構的直接效應。現有研究制度質量的文獻大多采用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治理指標數據庫中的6項國家治理評分,分別為政治穩定和不存在暴力或恐怖主義、政府效率、腐敗控制、監管質量、法制規則和話語權與責任,本文主要從腐敗的角度考察制度質量的影響,因此使用腐敗控制這一指標,取其對數,用lnCCi,t表示,數值越高表明國家腐敗控制的效果越好。為研究東道國制度質量與中國對外投資的交互效應對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引入腐敗控制和對外投資流量的交互項,模型設定為:
manui,t=β0+β1lnfdiflowi,t-1+β2lnCCi,t-1+β3lnfdiflowi,t-1×lnCCi,t-1+β2Zi.t+γi+γt+εi.t
(6)
結果見表4所示,(1)至(3)列直接加入腐敗控制的指標,第(4)列加入交互項且使用前一期(lnCCfdii,t-1)的數據進行回歸。由表4可以看出,在引入衡量東道國腐敗控制的指標之后,核心解釋變量對非直接投資流量(lnfdiflowi,t-1)的系數依舊顯著為正,但腐敗控制指標對出口貿易結構作用的符號并不確定,且都不顯著,說明東道國腐敗控制對其貿易結構沒有顯著的影響。然而,直接投資流量與腐敗控制質量交互項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可見,中國對非洲投資和東道國制度質量之間對促進優化非洲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有著顯著的交互效應,即較好的腐敗控制能夠更好地發揮投資對貿易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健全的制度建設對投資的貿易效應存在著放大作用,說明中國在非洲國家的投資并不是依靠“腐敗的交易”。

表4 基于制度質量的檢驗
(二)基于東道國官方語言的檢驗
非洲是世界上語言種類最多的大陸,獨立使用的語言約為800至1000種。由于歐洲殖民主義國家入侵,目前大多數非洲國家皆采用非洲以外的語言作為官方語言。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非洲主要有四種官方語言,分別為英語、法語、阿拉伯語和葡萄牙語。
語言障礙一方面直接影響到雙方溝通,從而影響經濟活動的進行,另一方面可能導致貿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進而增加交易成本。已有研究比較了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分別作為共同語言對貿易的影響,發現英語對貿易的影響最大。[26]對于沒有相同官方語言的國家,“通用語”或“第三方語言”(如英語)起到了一定的貿易效應。測算語言距離的研究發現,在非洲各國使用的語言中,漢語和英語的語言距離最小。[27]由此可見,現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洲國家不同的官方語言可能會影響中國對非直接投資與非洲國家出口貿易結構的關系。
將非洲國家按照官方語言分類后進行分組回歸,結果發現,四組的核心解釋變量(lnfdiflowi,t-1)的系數均為正,且官方語言為英語和法語的國家核心解釋變量(lnfdiflowi,t-1)的系數為顯著為正,而官方語言是阿拉伯語和葡萄牙語組的系數不顯著(表5)。

表5 基于官方語言的分組檢驗
其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英語和法語相對于阿拉伯語和葡萄牙語,使用范圍較廣,便于開展國際貿易;二是中國掌握英語和法語的人較多,便于中國企業在非洲當地進行調研、談判、合同簽訂等工作,能夠降低投資成本,也更利于投資促進東道國貿易結構升級;三是非洲官方語言的形成是由于殖民因素,非洲國家受宗主國的影響在當今也會體現在與宗主國有更緊密的經貿聯系上,反映出其在出口貿易結構上的差異。
(三)基于東道國地理區位的檢驗
地理區位也是影響一國貿易和投資的重要因素。地理區位影響投資的貿易效應有兩點原因:一是地理區位影響貿易成本,地理差異通過自然資源稟賦影響地區的生產率和生產成本,造成了各地區在專業化分工上的不同,地理距離也直接影響交通運輸成本。此外,地理邊界帶來的不同地區在制度和文化等因素上的差異在長期影響政策壁壘成本和交易成本。即使交通和互聯網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理距離的負向影響,但相鄰國家的貿易“組團”現象表明地理距離依舊對國際貿易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二是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知識和技術的流入存在地理溢出效應,地理位置上較為臨近的企業在學習新知識和技術時更容易形成集群而促進學習,而且這種溢出效應要在本地產業的知識基礎較為薄弱、新知識與本地產業有一定適配性的時候發生。[28]處于不同地理區位的非洲國家在自然資源、經濟發展程度和文化上存在著的差異可能影響投資的貿易效應。
為了探究地理區位的影響,采用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統計司的地理方案,將非洲國家按照地理區位劃分為北非、東非、西非、中非和南非。使用分組回歸的方式進行檢驗,回歸結果見表6,五個分組中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均為正,且中非、西非和南非分組的系數顯著為正。可見,中國投資對非洲國家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效應存在著地理分區上的差異。地理區位分組后,各組控制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相對于基準回歸也發生了變化。例如,在中非的分組里,人均GDP(lngdppppi,t)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對于中非國家,經濟發展程度對出口結構的優化起正向作用。同樣,在不同的分組中,勞動力資源(lnlabor)和自然資源(lnnature)的系數也發生改變,說明由于地理位置導致的自然資源稟賦、人口聚集和遷移等因素,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異質性。此外,截至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多的五個非洲國家分別為南非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贊比亞、尼日利亞和安哥拉,均位于南非、中非和西非,可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大國也對所在地理區位存在著一定的溢出效應。

表6 基于地理位置的分組檢驗
(四)作用機制
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是通過怎樣的作用機制來促進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升級呢?本文認為,中國對非洲投資能夠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和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從而使東道國從生產資源品和初級品轉向生產和出口更多的制造業產品。從WDI數據庫中選取非洲各國通電率(享有通電人口的百分比)指標和營養不良發生率作為中介變量,用通電率和營養不良發生率分別衡量一國基礎設施情況和人力資本水平,對上述傳遞路徑進行機制檢驗。模型設定為:
mediatori,t=β0+β1lnfdiflowi,t-1+β2Zi.t+γi+γt+εi.t
(7)
lnmanui,t=β0+β1lnfdiflowi,t-1+β2mediatori,t+β3Zi.t+γi+γt+εi.t
(8)
其中,mediatori,t表示非洲i國第t年的通電率或營養不良發生率,式(7)的解釋變量為中國對非直接投資流量滯后一期,通電率或營養不良發生率為被解釋變量,式(8)的解釋變量為中國對非直接投資流量滯后一期和通電率或營養不良發生率。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會顯著影響中介變量,并且中介變量和中國對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同時顯著影響非洲國家制造業出口比例,那么上述傳遞路徑就通過了機制檢驗。
表7第(1)列至(3)列為使用通電率為中介變量的結果,(4)至(6)列表示使用營養不良發生率作為中介變量的結果,(1)列和(4)列為模型(1)的回歸結果。第(2)列顯示,中國對非投資與非洲東道國的通電率回歸后,對非直接投資的系數顯著為正,對應了式(7),說明中國對非洲投資的增加會使得東道國享有通電的人口比例增加,即改善了基礎設施,而(5)列表示中國對非洲投資的增加降低了東道國的營養不良發生率,即提升了人力資本水平。第(3)和(6)列給出了核心解釋變量(lnfdiflowi,t-1)和中介變量(mediatori,t)對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結果表示,非洲東道國的通電率與非洲東道國制造業出口比例呈顯著正相關,說明隨著基礎設施水平的提升,出口貿易結構也在改善;營養不良發生率的系數依舊為負,說明從營養的角度衡量人力資本時,東道國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可以優化出口貿易結構,上文所述機制傳遞路徑通過了檢驗。

表7 機制檢驗
六、結論及啟示
近年來,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投資力度不斷增加,對非投資越來越受到關注,但是有關中國對非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大多聚焦于中國出口貿易情況和中非雙邊的貿易流量,少有關于中國對非投資與非洲東道國出口結構關系的研究。本文使用2003-2017年中國對非投資和非洲貿易數據,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和非洲國家出口貿易結構的關系,主要結論有以下四點。
第一,中國對非投資能夠促進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升級,體現在制造業出口占商品出口比例的增加和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提升,為非洲東道國帶來內生增長的動力。在長期,中國投資使非洲出口貿易結構從第一、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升級。
第二,東道國腐敗控制水平與中國對非直接投資的交互項對非洲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有著顯著的正向關系,因而東道國制度體系的完善能夠更好地發揮中國投資對貿易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
第三,對東道國官方語言和地理區位的異質性檢驗發現,中國對非直接投資對非洲國家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能力存在著地理差異,中國對官方語言為英語和法語的國家投資的貿易結構升級效應要更為顯著,中國在中非、南非和西非的直接投資促進制造業出口的效果也優于東非和北非。
第四,使用通電率和營養不良發生率作為中介變量進行機制檢驗發現,基礎設施的改善和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在中國投資優化非洲東道國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應。
本文為中國對非投資對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績效提供了一定的實證支撐,證明中國對非投資并非如西方社會所言是“對非掠奪”或“腐敗的交易”,而是可以促進非洲國家出口結構的改善,為其經濟發展提供內生動力,體現出中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望正在實現。面對西方社會對中國在非投資的負面態度,中國學者應多用量化的方法從非洲東道國的視角關注中國在非洲投資的績效問題。
注釋:
① 數據整理時參考來自孫楚仁等(2021),參見在《中國工業經濟》網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下載。
② 10類分別為:礦石和金屬、農業、制造業、食品、燃料、信息和通信技術、保險與金融服務、旅行服務、交通服務、計算機通信和其他服務。
③ 第一產業包括農業,第二產業包括礦石和金屬、制造業、食品、燃料、信息和通信技術,第三產業包括保險與金融服務、旅行服務、交通服務、計算機通信和其他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