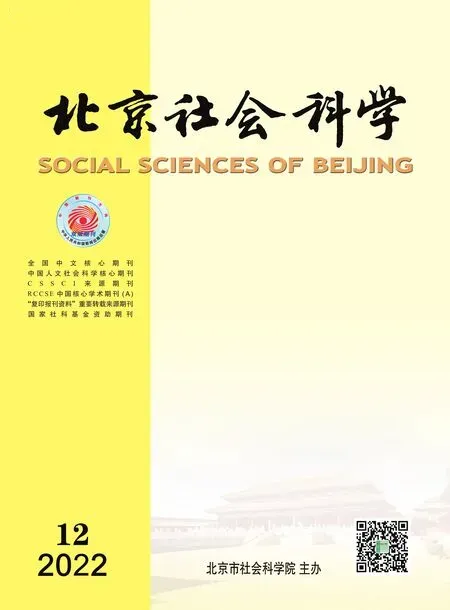元代京畿地區“說唱詞話”現象考略
李雪梅
一、引言
“說唱詞話”在元代之前的文獻中無跡可尋。因其民間表演活動的受眾群體主要是底層百姓,刊行的存世作品也多有亡佚,所以在明清文獻中,“說唱詞話”現象已極為模糊。這也導致民國以來傅惜華、趙景深、葉德均、鄭振鐸、孫楷第等俗文學大家對其考證闡釋差異頗大,更無法具體描繪出元代“說唱詞話”現象的原貌。
元代京畿地區的“說唱詞話”現象,主要包括民間表演活動與書坊文本刊行兩個方面,其表演活動也被稱為“面戲”,通常在冬至或其他傳統重要節令時以村社或家族為單位舉行。元至元十一年(1274),這種表演活動被官方嚴令禁止。到明代時,北方地區幾乎沒有“說唱詞話”表演活動留存,但在明成化年間,北京書林永順堂刊行13種“說唱詞話”,其中多有明代重刊的元代作品,這些作品有助于我們“通過它看到中國古代戲曲、說唱文學和小說相繼的發展過程,更加了解幾百年前元明間的‘詞話’究竟是什么”[1]。此外,元代時大運河交通便利,“經河道或海道北上的南方漕船經由通州溯流而上,直抵大都城內”[2]北方流民大批南移,“說唱詞話”現象因在北方受查禁而逐漸轉移到統治者關注度較低的南方偏遠地區。本文基于對現今安徽貴池儺戲的田野調查(2015年春節期間,筆者曾赴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地區實地觀摩儺戲表演),著力還原在古代說唱文學中已消失數百年的元代“說唱詞話”現象,并通過稽考相關史料,挖掘這一現象背后的深層意義。
二、元代京畿地區“說唱詞話”表演活動
《元史》《元典章》《大元通制條格》中出現了三則“說唱詞話”史料。
《元史·刑法志·刑法四·禁令》:“諸民間子弟,不務正業,輒于城市坊鎮,演唱詞話,教習雜戲,聚眾淫謔,并禁治之。”[3]
《元典章·刑部十九·雜禁·禁學散樂詞傳》:“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書兵刑部承奉中書省札付據大司農司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官申:順天路束鹿縣鎮頭店,見人家內聚約百人,自搬詞傳,動樂飲酒。為此,本縣官司取訖社長田秀井、田拗驢等各人招伏,不合縱令侄男等攢錢置面戲等物,量情斷罪外,本司看詳,除系籍正色樂人外,其余農民、市戶、良家子弟,若有不務本業,學習散樂、般說詞話人等,并行禁約,是為長便,乞照詳事。都省準呈,除已札付大司農禁約外,仰依上施行。”[4]
《大元通制條格·雜令·搬詞》:“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中書省大司農司呈河南河北道巡行勸農官申:順天路束鹿縣鎮頭店,聚約百人,般唱詞話。社長田秀井等約量斷罪外,本司看詳,除系籍正色樂人外,其余農民市戶良家子弟,若有不務正業,習學散樂,般唱詞話,并行禁約。都省準呈。”[5]
上述史料中出現了“演唱詞話”“自搬詞傳”“面戲”“般說詞話”“搬詞”“般唱詞話”等與“說唱詞話”相關的詞語,“搬”“般”即為“扮”,“自搬”“般說”“演唱”“般唱”說明這種表演活動有扮有唱有說,又名“面戲”,可知需戴著面具表演。但這種民間自發的表演活動因何招致官方懲戒?內中不乏深刻的時代背景與政治原因。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將國號改為“大元”,至元十一年六月,元世祖下詔攻打南宋,九月伯顏率軍出征。立國初期的元政權對京畿地區的聚眾活動十分敏感,《大元通制條格》卷十六“田令·農桑”載:“不得率領社眾非理動作聚集,以妨農時外,據其余聚眾做社者,并行禁斷。”[6]而至元十一年十一月的“說唱詞話”表演活動發生在順天路束鹿縣鎮頭店村,束鹿縣即今河北省辛集市。元代時期,河北、河南、山西、山東屬于中書省直接管轄的腹里地區,順天路治所在保定,確實是京畿要地,“聚約百人”的“說唱詞話”表演活動,自然會引起官方注意。
據《元史·本紀第七·世祖四》載,至元七年(1270)二月壬辰,元政府“立司農司,以參知政事張文謙為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司”[7],四道包括山東東西道、河東陜西道、山北東西道、河北河南道。隨著元代疆域的擴大,勸農使逐漸增多,同年“十二月丙申朔,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以御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8]。至元十二年(1275)四月,“罷隨路巡行勸農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9]。“提刑按察司”是元初才設立的一個機構,主管一省刑名、訴訟事務,也是中央監察機關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機構,對地方官員行使監察權,可見“巡行勸農司”官員的職責表面為勸農,實質是查訪維穩,權力相當大,可隨時處理突發事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元初統治者對官員處理公務的效率有嚴格的日期限定,“諸官司所受之事,各用日印,于當日付絕。事關急速,隨至即付……違者,量事大小,計日遠近,隨時決罰。其事應速行,當日可了者,即議須行”[10]。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農歷冬至日,由前述《元典章》史料可知,“中書兵刑部承奉中書省”札付“大司農司禁約”并布告統治區域“依上施行”的日期是“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考慮到元代官員對這類敏感事件的處理效率,順天路束鹿縣鎮頭店“說唱詞話”表演活動的發生時間應距“十一月二十六日”很近,當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冬至當日或之前不久。
為什么“說唱詞話”表演活動會在農歷冬至前后出現?這與冬至節令在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關,古代民間有“冬至大如年”的說法, 冬至與春節(正月初一)、寒食并稱三大節,被稱為“亞歲”。元代民間也保留著宋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的習俗。但元初京畿地區民間的冬至祭祀活動不免會涉及趙宋先祖,內容敏感,加之聚眾動樂會飲,引發的關注度高,導致元代官方對此類表演活動格外重視,一經告發,立刻在全國范圍內查禁。
三、元代“說唱詞話”的文本刊行情況
對元代“說唱詞話”文本內容及其刊行情況的追索,有賴于1967年上海嘉定墓葬中出土的13種“說唱詞話”。這些作品是“過去中國任何書上從來沒有著錄過的”[11],具體包括《花關索傳》(4集)《石郎駙馬傳》《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包待制出身傳》《包待制陳州糶米記》《仁宗認母傳》《包待制斷歪烏盆傳》《包龍圖斷曹國舅傳》《張文貴傳》《包龍圖斷白虎精傳》《師官受妻劉都賽上元十五夜看燈傳》《鶯哥行孝義傳》《開宗義富貴孝義傳》。全部為線裝竹紙刻本,封面和末頁有牌記、出版書坊名稱及出版年月,板框高約17.5厘米,寬約11.5厘米,粗黑口,每種“說唱詞話”正文15頁至43頁不等,“說”“唱”“贊”等字樣都用墨圍,且都附有插圖,共有上圖下文的兩節版插圖44幅,整面插圖104幅。
這13種“說唱詞話”作品大多刊行于明代成化年間,但《花關索傳》4集中之前集《花關索出身傳》與《唐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均系明代重刊的元代作品。其中,《花關索出身傳》末頁的長方形牌記上書“成化戊戌仲春永順書堂重刊”。趙景深曾就此點展開論述:“它的形式幾乎完全同《全相平話五種》(按:元至治年間刻)一樣,每半頁上端都有插圖,插圖約占三分之一,文字約占三分之二。圖刻得相當細致生動,刻字的形體風格也同《全相平話五種》一樣,每卷的頁數也相近。只是那五種是平話,而這種是說唱,文體殊異。因此我懷疑這部《花關索傳》是從元刊本翻印的,初刻的年代還可以推前一百多年。”[12]
汪慶正也認為:“成化本《花關索傳》是繼元刊《三國志平話》以后又一次發現的關于三國故事民間傳說的文學資料。當然,一些元雜劇本中也有這些材料,但內容都很少。這本《花關索傳》雖然是成化年間的刻本,但在《花關索出身傳》末刊有‘成化戊戌仲春重刻’字樣,說明原書的成書年代要更早。從該書上圖下文以及行格、版式看,與元刊五種平話基本相同,很可能是據元刻本重刊的。”[13]
再以《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為例,趙景深曾在《曲藝叢談》中談到:“講史第二種是《新刊全相唐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三十頁,半頁十三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半頁插圖十三幅,封面上端橫刻‘北京新刊’四字。卷末有‘成化辛卯永順堂刊’一行字。辛卯是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拿這本書同趙萬里從《永樂大典》第五四二二卷‘遼’字韻輯出的《薛仁貴征遼事略》對照,發現兩書開端幾行文字,幾乎完全相同,看來說唱詞話是根據‘評話’改編的唐統治者對外征伐的故事(趙萬里認為這評話可能是《永樂大典》所收二十六卷宋元評話當中的)。”[14]
“評話”《薛仁貴征遼事略》與“說唱詞話”《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這兩部作品,從開篇到“房玄齡杜如晦諫帝征遼東”,正文文字幾乎完全相同,“房玄齡杜如晦諫帝征遼東”后,故事情節也基本一致,但《薛仁貴征遼事略》行文詳細繁瑣,《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行文則簡潔明了,明顯是在前者的基礎上進行過刪減與改編。這一區別與“評話”和“說唱詞話”不同的表演特性有一定關系。
此外,縱觀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這13種作品,有一現象值得關注:所有作品的時代背景均為元代之前,而且宋代故事均為仁宗朝的包公斷案故事,其中也沒有出現稱宋代為“本朝”的現象,所以它們應是明代重刊的元代“說唱詞話”作品以及明成化年間新編刊行的“說唱詞話”作品。
四、安徽貴池儺戲是元代“說唱詞話”現象的基本再現
安徽貴池儺戲,是一種規模較大的群體性娛神娛人表演活動,其文本形式與表演程式基本上再現了元代京畿地區“說唱詞話”現象的原貌。
(一)安徽貴池儺戲的文本形式
1952年,戲曲家王兆乾在安徽貴池調研黃梅戲音樂時,發現九華山下周圍三四十個村莊每逢春節會通過演出儺戲來祭祀祖先、預祝來年,這一表演習俗可追溯至元代。如保存有儺戲劇本《章文選》的汪村:“由其七十一世汪開遷者于元至正時在汪村下首(今劉街鄉所在地的河對岸)修建了一座青山廟(毀于‘文革’前,尚有廟基存在),這座青山廟‘為九社祀典不絕’,各族儺戲演出前后都要將面具抬到此廟舉行請神儀式,謂之‘起圣’‘落圣’。”[15]
2015年2月28日(正月初十),筆者曾實地探訪2014年重建的青山廟并采訪當地村民。據了解,“文革”結束后的幾十年,劉街鄉汪、姚、劉諸姓儺戲會一直恪守元明舊習,演出前后依然會在廟前舉行“起圣”“落圣”儀式。
儺戲劇本中的《花關索》《宋仁宗不認母》《薛仁貴征東》《包公陳州放糧》等,其情節內容與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中同題材作品幾乎完全一致,另有一些劇本則不見于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如《章文選》《搖錢樹》《劉文龍趕考》等。


儺戲《薛仁貴征東》與明成化“說唱詞話”重刊的元代作品《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比較,前者多用七字句唱詞,而后者多用十字句唱詞,如前者第六出“托獅子”:“敬德聽說眉頭皺,不由煩惱在心頭。前唐不覺年年亂,六十四處起煙塵。李靖陰陽知禍福,老臣跨馬去征東。”[18]
后者第三段“宣敬德不伏老去征東”:“胡敬德,聽說罷,眉頭緊皺;不由人,添煩惱,暗里傷情。想前唐,自不巧,年成荒亂;有六十,單四處,各起煙塵。”[19]
“出土的成化刊本說唱詞話,已經有了十字句唱詞,刻本上注明‘攢十字’……而貴池儺戲所據之本,卻沒有一部運用‘攢十字’,全為七言句式。這證明儺戲所據的詞話本要比出土的成化本為早,當為‘攢十字’出現前的作品。”[20]王兆乾的這一論斷指的是他搜集到的所有安徽貴池儺戲劇本,并非單指《薛仁貴征東》這一部。“說唱詞話”的唱詞為詩贊體,句式結構以七字句為主,“攢十字”出現較晚,其“三三四”結構是在七字句“二二三”結構上每節加一個襯字而成,語言更通俗,敘述性也更強。這充分說明,儺戲劇本與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之間明顯具有前后承繼關系,唱詞純為七字句的儺戲劇本,其創作年代當早于已出現“攢十字”句式的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也就是說,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的創作年代晚于儺戲劇本。
(二)安徽貴池儺戲的表演程式
2015年正月,筆者在貴池實地觀摩了六場家族儺戲會,其中蕩里姚、茶溪汪、太和章、西華姚四家儺戲會的表演場地均為本族祠堂。田野調查顯示,安徽貴池儺戲的整套表演程式,包括置辦面戲、動樂飲酒、祭祀先祖,與前述史料中至元十一年順天路束鹿縣鎮頭店鎮的“說唱詞話”表演活動高度相似,具有很高的戲曲史研究價值。《元典章》中提及的“面戲”,在安徽貴池儺戲這里得到了充分的闡釋。“面具是儺事活動的核心,歷史證明,失落了面具,便意味著儺戲的消亡,儺事活動的全過程,都圍繞著面具進行。”[21]貴池當地每個村里的面具多少不一,種類均與“迎送神”及儺戲正戲中的人物有關,如宋仁宗、包公、章文選、蕭女、劉文龍、孟女、財神、土地、玉帝、觀音等。這些面具按一定規矩陳放在面具箱中,箱上分別書“日”“月”二字,故又名“日月箱”,正月十五儺戲演出結束后,再將其放入祠堂閣樓神幔中,待來年正月初七取下,開啟一年一度的儺事活動。
《薛仁貴征東》《花關索》《宋仁宗不認母》等劇目即是安徽貴池儺戲中的常見正戲。表演正戲的演員需在演出前一天沐浴凈身。演出當天,演員在后臺先沐手,穿好戲衣彩褲后,去“龍床”邊向面具行禮,待儺戲會里管面具的執事幫他們戴妥面具后,便在后臺等待“先生”來導引上場。
“先生”所指何人?正戲演出期間,“所有的舞臺或平地演出場合的后方,演員出場后都有兩位或一位‘先生’坐場,手捧劇本總稿進行指揮。他既擔任臺上的喊斷、提詞、幫唱、撿場、如搬桌椅、擺蒲墩等事務,也負責引戲上場……值得注意的是,姚姓演出《陳州放糧》《宋仁宗不認母》和曹姓演出的《劉文龍》,一位或兩位先生要坐在臺上,按照劇本從頭至尾高聲演唱。唱到哪個角色,哪個角色出場。角色若有唱詞或動作,則扮此角色的演員動作一下。”[22]
在這段介紹里,“先生”演唱的《劉文龍》劇本,在原始的“說唱詞話敘述體”底本基礎上稍加改動過,劇本中雖然出現了人物角色,但在演出過程中仍以第三人稱的“說唱詞話敘述體”形式演出,而不是讓演員用“戲劇代言體”形式演出。演員只是在后臺說書“先生”唱到某角色時,被牽引到臺前“動作一下”,再被牽引下場,整體看來,類似于雙簧表演,那些戴著面具的“角色”在臺上雖不發聲,但面具是神靈、祖先的媒介或載體,代表的是不忘先人,慎終追遠。
“區別戲劇與曲藝的標準還不能僅以是否代言體來衡量”[23],安徽貴池也有一些村社家族在進行儺戲表演活動時,后臺說書“先生”直接使用未加改動的“說唱詞話敘述體”底本,但每當他們提及某個角色時,那些戴面具的演員照樣被人牽引上場和下場。這也是宋元時期“說唱詞話敘述體”開始向“戲劇代言體”過渡的一個明顯標志。世易聲移,北化為南,這些留存在安徽貴池儺戲中的元代“說唱詞話”表演活動,是宋元時期促進南戲表演體式成熟的重要媒介,在中國戲曲的形成發展軌跡中應占一席之地。
五、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系“北京新刊”之考辨
明成化刊本13種“說唱詞話”中,《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扉頁中有半頁刻有“北京新刊”四個大字,所以趙景深、汪慶正均認為這批刻本是明代成化年間由北京永順堂刊行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印刷志》也將其定義為“北京永順堂”刊行,但相關著錄均未就此展開詳細論證。
近年來,學者劉理保撰文《上海出土明永順堂刻本為建陽刻本考辨》,認為這批刻本應為福建建陽書坊所刊。具體論據有四:其一,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包待制斷歪烏盆傳》末頁刻書牌記題“成化壬辰歲季秋書林永順堂刊行”,扉頁題“永順堂新刊”,此“書林”當指福建建陽崇化書林,因為明弘治本朝及以前,建陽崇化書坊善用“書林”之名。其二,部分明代刊印“書林”牌記的刻本中,弘治朝及前的刻本已被學界確定為建陽刻本,而嘉靖至萬歷朝的刻本,除絕大多數為建陽刻本外,另有金陵書林、揚州書林、建業書林、白門書林、常郡書林、金閶書林、杭城書林等,但未見北方尤其是北京書坊刊有“書林”二字。其三,“北京新刊”四字,應是“京本”之意,建陽書坊刻本自題“京本”的刻本不勝枚舉,如余氏雙峰堂明萬歷十六年(1588)刊《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等。其四,《花關索出身傳》版畫和元至治年間建安虞氏所刻《全相平話五種》版畫相比對,兩書都是上圖下文,圖右上角題寫版畫要說明的內容,版畫風格極為相似,明代前期北方未見有這樣兩節版的刻印方式。[24]
筆者通過稽考相關史料,認為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并非建陽刻本,而是刊刻于北京書林永順堂,具體剖析如下。
首先,明代時,福建建陽崇化書坊確有“書林”之稱,但在建陽崇化書坊中,并無永順堂這一書坊名。《包待制斷歪烏盆傳》末頁刻書牌記題“成化壬辰歲季秋書林永順堂刊行”,其中“書林”二字并非專指“建陽崇化書坊”或南方書坊,明代北京著名書坊之一金臺汪諒書鋪,又名金臺書院,刻印書籍數量大,傳世較多,如正德五年(1510)刻印《陳思王集》10卷、嘉靖元年(1522)刻《玉機微義》50卷、《文選注》60卷、《韓詩外傳》10卷、《太古遺音》不分卷、《潛夫論》10卷,嘉靖四年(1525)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130卷,嘉靖十六年(1537)刻《臞仙神奇密譜》3卷,萬歷元年(1573)刻《武經直解》23卷、《兵法附錄》1卷等。《北京印刷志》中明確著錄此書鋪曾于正德十四年(1519)刻《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25卷、《文》2卷,“在第25卷后刻有‘正德己卯正月吉旦金臺書林汪諒重刊’牌記”[25],此處“重刊”二字,說明汪諒刻印所用原版應早于正德年,而“金臺書林”四字則說明明代正德年間北京書坊也能自稱“書林”。
其次,明代金臺岳家書坊曾于弘治十一年(1498)刻印有《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5卷、《題詠》1卷、此本據王德信撰、關漢卿續的刊本重刻刊行,為上圖下文兩節本,半頁12行,一行18字,“卷末有‘弘治戊午季冬金臺岳家重刊印行’牌記,還有‘正陽門東大街東下小石橋第一巷岳家書坊’木記一行”[26],原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注釋西廂記》封面圖即為影印自原本的金臺岳家兩節版畫。[27]版畫中,人物線條簡潔疏朗,整體風格不同于徽派版畫的細膩繁縟,更接近閩派版畫的古樸質拙。由此可見,在明代前期,北京地區的書坊對閩派書坊的繪圖風格是有吸收借鑒的。
最后,金臺魯氏書坊也是明代北京著名書坊之一,臺灣省“國立中央圖書館”現藏有魯氏書坊成化年間刻印的四種小曲:《新編四季五更駐云飛》1卷、《新編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云飛》1卷、《新編太平時賽賽駐云飛》1卷、《新編寡婦烈女詩曲》1卷。[28]可見,北京金臺書坊在弘治、成化年間也出版有戲曲、小曲,與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13種作品題材非常類似。
建陽與北京,均是明代前期著名的書坊集中地,永順堂刻書至今未見有各家書目著錄,僅見于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筆者認為,封面的“北京新刊”與卷末的“成化戊戌仲春永順書堂重刊”“成化辛卯永順堂刊”等牌記,形成前后呼應,無須偽托,進一步指明了這13種“說唱詞話”的刊刻地是北京書坊永順堂。
六、結語
綜上所述,元代史料中最早記載了京畿地區的“說唱詞話”表演活動,明代成化年間北京書林永順堂又極為正規地刊行了13種“說唱詞話”,其中多有明代重刊的元代作品,這是目前為止國內外僅見存世的“說唱詞話”刻本。而自元代以來,安徽貴池儺戲劇本吸收元代“說唱詞話”文本內容并通過與其高度相似的表演活動代代傳承,至今鮮活。可以說,元代京畿地區“說唱詞話”現象,搭建了元代曲藝向戲曲過渡的橋梁,接續了中國古代說唱文學由宋至明的發展脈絡,為研究宋元以來說唱文學與民間戲劇相互滲透的關系提供了典型范例,是研究宋元南戲形成軌跡的重要視角。
——鄉村儺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