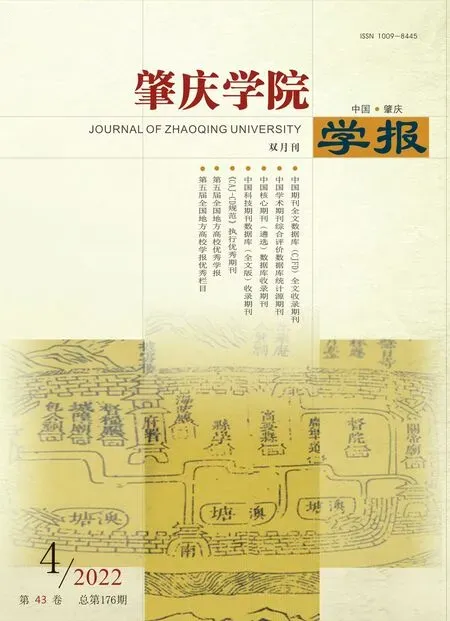關于刑法中盜竊行為的概念分析
李居全
(肇慶學院 政法學院,廣東 肇慶526061)
近幾年來,在我國刑法學界,關于盜竊行為方式的秘密性與公開性問題,受到普遍關注,爭論的焦點也很多。本文鑒于篇幅有限,不全面討論各個焦點問題,僅從盜竊行為概念這一個角度進行分析,以與學界同仁商榷。
一、概念的意義
(一)概念的統一性對于人類交流的意義
人是社會動物,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需求,人與人之間必須展開協作。而協作只能建立在相互交流的基礎之上。交流的本質是信息的傳遞。信息是人的大腦對于客觀對象的描述,是由各種相關概念所構成的。
概念是客觀對象在人腦中的反映,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都是先形成對該客觀事物的概念,然后再通過對概念的運用來進行判斷和推理。“概念是思維機體的細胞,是思維最基本的形式,因此,思維對自然界中到處盛行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就只能在形成概念的基礎上來進行。”[1]概念之所以是思維機體的細胞,是因為概念具有分類的功能,它是人腦將復雜而又籠統的客觀世界,劃分成若干類的客觀存在物。一個概念的外延所囊括的客觀事物,就是這個概念從完整的客觀世界中切割出來的一個類,即概念的對象物。概念的這一分類功能,正是信息傳遞的基礎。人對于客觀世界的改造不可能是整體進行的,只能是從局部開始逐漸進行,因而交流的內容也不是以整個客觀世界為對象,而只是以經過概念分類后的某個局部的、具體的事物為對象,也就是某個具體的概念所反映的對象。人類就某個客觀對象所進行的交流,只有通過相互傳遞與該對象相關的概念信息才得以實現。然而有效的概念信息交流的前提,必須是主體之間各概念的同一性,即各概念必須具有相同的外延——各參與交流的主體大腦中的同一概念所反映的對象必須相同。
法律是社會主體即公民的行為規范,其調整對象是普通公民的行為,而不只是法學專家的行為。法律的制定與頒布,其實也是一種交流,是立法者與公民之間的交流[2],尤其是在法治社會里,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立法者必須用法律的形式明確告訴公民什么事能為,什么事不能為。法律既然是立法者與公民之間的信息交流,那么立法者在法律中所使用的概念與社會普通公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概念,必須是相統一的,否則立法者就不能將其意志傳遞給公民,法律也就會失去法律的意義。
(二)不同語系人群之間的概念差異
在不同的人類群體中,因改造客觀世界的社會活動的經歷不同,其概念對于客觀對象的劃分也會有所不同,比如說“長度”這個概念,在社會歷史實踐中英語人群將長度劃分為英尺、英寸等概念,而漢語人群則將其劃分為市尺、市寸等概念。一個英國人與一個中國人就長度問題進行交流,要么都使用英制單位,要么都使用市制單位,否則雙方無法進行交流。
概念,作為大腦對客觀對象的反映,自身是不具備傳遞能力的,一個人大腦的想法是不可能自己跑到另一人的大腦里去的,它必須借助一種形式或者媒介才能傳遞,而這種形式或者媒介就是語詞。語詞是概念的語言表達形式[3],也是人類交流過程中概念信息的載體。大腦對客觀對象的反映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因此,概念的差異通常也表現為語詞意思上的差別。從一門語言中的外來語我們可以看出,不同語言人群中的概念發展是不平衡的。之所以使用外來語,是因為本語言中本身沒有該詞匯,因而也沒有該詞匯所表達的概念。例如,英文中的“romantic”(浪漫,羅曼蒂克)[4]779,860,漢語中本來是沒有的,而之所以沒有,是因為我們不曾有“浪漫”這個概念。再比如說“功夫”這個概念及其語詞,在英語人群中原本也是沒有的。因此,我們在做比較研究的時候,不能忽略不同語言中的語詞差異。
“盜竊”,在我國普通公民的意識中,就是“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4]268,不管我們對于“秘密”做何解釋,“自己認為秘密”也好,“他人認為秘密”也好,但絕不可能將其解釋為“以公開方式”,因為“秘密”與“公開”作為概念它們是矛盾關系,作為語詞它們互為反義詞。然而,漢語中的這種“盜竊”概念,在其他語系中是否存在?這個問題本文將在第二部分詳細論述。
二、“盜竊”概念比較研究
夏勇教授說:“沒有一部刑法不規定盜竊(竊盜、偷竊、偷盜)罪”[5]。這話未免說得太絕對了,至少不夠嚴謹。嚴格地說,英美法系刑法中基本沒有規定“盜竊(竊盜、偷竊、偷盜)罪”,德國刑法中也沒有規定。
英美法系刑法中沒有規定“盜竊罪”,主要是因為在英語中幾乎就沒有“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這一“盜竊”概念①在英語口語中,人們有時會用sneak或nick來表達“盜竊”的意思,但他們都不是正式用語。。如前所述,語詞是概念的載體,首先,我們來看看與漢語中“盜竊”概念最接近的幾個英文單詞。第一個,Larceny,準確意思是“以據為己用為目的將他人的財物取走且情節嚴重”的行為②“The felonious taking and carrying away of the personal goods of another with intent to convert them to the taker's use.”參見語言學會編輯的《牛津英語詞典》第6卷L-M(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VI L-M),牛津大學出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年版,第71頁。,完全不涉及“秘密”方式問題;第二個,Theft,意義是“將他人的財物拿走且情節嚴重”的行為③“The felonious taking away of the personal goods of another.”參見語言學會編輯的《牛津英語詞典》第11卷T-U(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VI L-M),牛津大學出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年版,第265頁。,與Larceny一樣不涉及“秘密”方式問題;第三個,Steal,意義是“不誠實地或者秘密地拿”④“To take dishonestly or secretly.”參見語言學會編輯的《牛津英語詞典》第10 卷Sole-Sz(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V Sole-Sz),牛津大學出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年版,第884頁。,“或者”是選擇關系,也就是說只要是“不誠實”即使是非秘密地拿也屬于Steal,因此,它與漢語中純“秘密地取得”這一“盜竊”概念的外延是不同的。然而在英漢詞典中,無論是Steal還是Larceny抑或Theft,都被譯成為“盜竊”。正是我國翻譯家們的這個不嚴謹的翻譯,導致了我國刑法學者們的誤解,誤以為英美法系中也有盜竊罪;誤以為在英美法系中“‘秘密性’并不成其為盜竊罪的一個問題”[5]。
基于以上英語語境,英美法系的刑法中不可能有“盜竊罪”。英國刑法中通常被我們翻譯成“盜竊罪”的犯罪實際上是Theft(侵占罪)。英國1968 年《侵占犯罪法》第1條第(1)款明確規定:以永久剝奪他人財物為目的,不誠實地侵占他人財物的,構成侵占罪(theft)⑤“A person is guilty of theft if he dishonestly appropriates property belonging to another with the intention of permanently depriving the other of it;and‘thief’and‘steal’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其中“appropriate”是指未經他人同意將他人之物據為己用,因而翻譯為“侵占”比較貼切,但應區別于我國刑法典中侵占罪中的侵占。。由此可見,英國法律對于Theft 罪的定義與該詞的普通含義基本一致,這說明其立法者與社會普通民眾所使用的概念是一致的。
德語中的盜竊概念是用“stehlen”⑥悄悄拿走別人的東西并據為己有(unbemerkt etw.nehmen,das einem anderen geh?ren,u.es behalten)(葉本度主編譯:《朗氏德漢雙解大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8頁。)一詞表達的。然而在德國刑法中卻沒有“盜竊(stehlen)”這個概念,《德國刑法典》中文版中的所謂“盜竊”,在德國刑法典原文中并非stehlen⑦如徐久生、莊敬華譯《德國刑法典》,將德國刑法第242條中的“Diebstahl”翻譯為“盜竊”。,而是Diebstahl。Dieb-stahl 是指“非法拿取(盜竊)別人的東西”①das verbotene Nehmen(Stehlen)von Dingen,die anderen geh?ren(葉本度主編譯:《朗氏德漢雙解大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1頁。),而“非法拿取”包括盜竊但不限于盜竊,也就是說“非法拿取”既包括秘密非法拿取,也包括公開非法拿取。“非法拿取”的外延大于盜竊,屬于盜竊的上位概念。因此德國刑法典中的Diebstahl 嚴格地說不是“盜竊罪”,而是“非法拿取罪”。由此,德國刑法對于Diebstahl罪的定義與該詞的普通含義也是基本一致的,說明德國的立法者與社會普通民眾所使用的概念事實上也是一致的。然而在日本和中國,刑法學者們都將Diebstahl 理解為“盜竊罪”,其原因仍在于翻譯家們的誤導,如日本人編寫的Grosses Deutsch-Japanisches W?rterbuch(《德日大辭典》)就是將Diebstahl翻譯為“盜み,竊盜,盜難,竊盜罪”[6],我國國內編寫的《德漢詞典》也是將Diebstahl翻譯為“偷竊,偷竊行為”[7]。這就造成了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德國刑法中也規定了盜竊罪的誤解。
我們知道,日本現行刑法典是于1907 年按照1871 年德意志刑法典制定的。日本現行刑法典第235 條規定:“竊取他人財物的,構成竊盜罪……”②日本刑法典第235條原文:“他人の財物を竊取した者は、竊盜の罪とし……”,其中行為方式為“竊取”。在日語中,“竊取”是指“以秘密的方法盜取”[8]。因此日本刑法中的“竊盜罪”實質上不同于德國刑法中的Diebstahl(非法拿取罪),日本刑法中的“竊盜罪”應該具備秘密性要素。然而日本刑法學界則普遍認為公然的行為也能構成盜竊罪,如西田典之認為:“竊取,本來是秘密取得的意思,但公然實行也可以成立本罪。”[9]日本刑法學之所以普遍認可“公然盜竊”,原因有二:一是翻譯家的誤導。如前所述,日本翻譯家將Diebstahl 翻譯成了“竊盜罪”,然而刑法學家在學習外國刑法之前都必須先學習外語,學習外語的工具書則都是翻譯家們所編寫的。眾所周知,在外語學習中越是簡單對應的詞匯越容易掌握,而翻譯家們又并非法學家,他們對概念的要求沒有那么嚴謹,因此,為了達到詞匯的簡單對應目的,通常會找一個最為接近的詞來翻譯,于是Diebstahl 理所當然地被翻譯成了“竊盜”。二是日本刑法乃至刑法學受德國刑法及刑法學影響太大。正如西原春夫所言,“本來日語中就沒有明確的有關法律關系的詞匯,而這些法律詞匯主要是從外語翻譯過來的。事實上,不僅‘法律用語’是如此,而且甚至日語不適宜于‘法的思考’。……如果極端地說,我認為在世界范圍內不符合法的思考的語言是日語, 而最符合法的思考的是德語。”[10]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刑法學者按照德國刑法對Diebstahl 的定義來理解“竊盜罪”則是情有可原的。
三、盜竊行為的主觀要素與盜竊罪的主觀要件的區別
(一)行為構造中主觀要素的意義
雖然犯罪即行為③也有少數學者提出告別“犯罪即行為”這個命題,告別的理由主要是因為行為的有意性在理論上不能解釋“過失行為”,在實踐中不能解決“汽車司機疲勞駕駛案”及“瓷器店暈倒”案。(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著,徐凌波、蔡桂生譯:“論犯罪構造的邏輯”,《中外法學》2014 年第1期)。事實上,“過失行為”這個概念是不存在的。所謂的“過失行為”,實際上是從行為的外部所作的一種評價,其所謂的“過失”并非行為的構成要素。很明顯“過失行為”一說是受過失犯罪的影響,認為犯罪是行為,既然有過失犯罪就應該有過失行為。這種說法混淆了犯罪與行為之間的差異。關于汽車司機疲勞駕駛案,汽車司機K為了能行駛更多的路程而在夜間疲勞駕駛。一段時間后他睡著了,車撞上了迎面開來的貨車,并導致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傷亡。金德霍伊澤爾將有意識的疲勞駕駛與無意識的夢中駕駛絕對分開,認為事故是夢中駕駛所致,與疲勞駕駛無關。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夢中駕駛只是因果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而且它不是原因,相對于疲勞駕駛而言它屬于結果,相當于槍擊事件中“子彈飛行”環節。如果我們不能說被害人不是被開槍的人打死的,而是被子彈打死的,那么我們也就不能說事故不是疲勞駕駛引起的,而是由夢中駕駛引起的。即使按照金德霍伊澤爾的避免義務違反說,也需要成立汽車司機的駕駛與事故發生之間的因果關系,否則不能歸責于汽車司機。汽車司機明知疲勞仍然繼續駕駛這一有意識的疲勞駕駛行為,正是導致夢中駕駛的原因。因此,應該非難的是汽車司機的有意識的疲勞駕駛行為,而不是無意識的夢中駕駛狀態。汽車司機在實施疲勞駕駛行為時對于事故的過失心理態度,并非包含在疲勞駕駛行為的意識之中,而是從行為外部對于行為所作的評價,屬于犯罪的主觀要件,而不是行為的主觀要素。同理,一個人在一家瓷器鋪突然暈倒并因此打碎了一只貴重的花瓶,由于不存在有意識的原因行為,因而在刑法上只能評價為意外事件。,但犯罪與行為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分別反映了兩種不同的事物。無論是根據哪一種犯罪構成模式,行為都是犯罪的構成要素之一,而不是犯罪的全部構成要素,僅此就可以說明犯罪與行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正因為犯罪與行為屬于不同的概念,因而它們各自的構造也不相同。在犯罪構成要件的劃分上,行為屬于客觀要件要素這是無爭議的。然而無論在哪個犯罪論體系中,目前處在通說地位的行為理論都認為行為的構造包含主、客觀兩個方面的要素,如大陸法系的有體性和有意性,英美法系的身體狀態和自覺性(Voluntariness)①英美刑法學中,無論何種行為理論,包括“行為自覺性的消極理論”,都不否定行為的自覺性要素的存在。(參見拙文“論英美刑法學中行為的構造”,《岳麓法學評論》2000年第1卷,第185-196頁。)。也就是說,犯罪客觀要件(行為)中也包含有主觀要素,這種主觀要素屬于客觀構成要件要素,而不屬于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
行為的主觀要素,無論是大陸法系的所謂有意性②有學者提出行為有意性不要說,認為“將有意性作為行為的特征并不具有現實意義”,從而主張將無意識的舉止也納入行為范疇之內(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五版,第143頁)。首先,在理論上,犯罪是行為這個命題所建立的理論基礎是:1、行為具有原因力,能引起客觀世界的變化,從而具有侵害的可能性;2、行為受意志支配,而意志則是可以通過對刑罰的權衡作出自由選擇的,權衡刑罰之苦大于犯罪之樂,那么行為人就會選擇放棄犯罪行為的意志。由此,行為又具有被威懾的可能性。而無意識的身體狀態因不具有被威懾的可能性,因而對于刑法來說是毫無意義的。其次,即使是使用三階層犯罪構成模式,無論何種情況下,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斷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不滿12歲的人殺人,至少因果關系的判斷是必須的,而因果關系的內容則屬于構成要件的內容,我們不可能繞過構成要件符合性而直接作責任判斷。最后,認為“知道自己患有癲癇病駕車肇事”與“不知道自己患有癲癇病駕車肇事”是“完全相同”的情形的觀點,與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所犯的是同樣的錯誤(參見上頁注釋③),忽略了因果過程中的原因與結果的關系。刑法非難的不是癲癇病發作時的所謂“駕駛”,而是明知自己患有癲癇病仍然駕車的行為,癲癇病發作只是這個有意識行為所引起的因果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如果不對明知自己患有癲癇病仍然駕車的行為作構成要件符合性判斷,何以對行為人對待結果的心理態度做責任判斷?,還是英美法系中的自覺性,都絕不是空洞無物的,而是應該有其實質內容的。在一定程度上行為的主觀要素決定了行為的性質。首先,根據目前通說的行為理論,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目的支配下的身體狀態。也就是說,人的身體無時無刻不是處在一種客觀狀態中的,但我們不能說人時時刻刻都在實施行為。那么,什么身體狀態(有體性)可以被界定為行為呢?這就只能看其身體狀態是否是由特定目的所支配的。從這個角度看,行為的主觀要素決定行為的存在。其次,在復雜的社會實踐中,人的行為種類繁多,為了交流上的方便,人類使用概念將人的行為劃分成各種不同的類型。可以這么說,一門語言中有多少個非同義的動詞,那么這個語言族群就將行為劃分為多少個行為概念,因為概念畢竟是用語詞來表達的,如殺人、傷害、強奸、詐騙、盜竊,等等。這么多的行為概念相互之間存在著質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行為的主觀要素。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行為實質上是人類基于對因果規律的認識,為達到特定目的而展開的一個因果過程。而這個過程不僅要以主觀認識為基礎,而且還需要先形成特定的主觀目的,更需要這種特定的主觀目的去支配身體的狀態。不同的主觀目的決定了行為的不同性質,如殺人行為與傷害行為,盡管身體狀態相似,也不管是否發生死亡結果,關鍵的區別在于支配身體狀態的主觀目的是希望行為對象死亡還是受到傷害。因此,行為的主觀要素不僅決定了行為本身的存在,而且還決定此行為與彼行為之間的區別。
(二)正確區分犯罪的主客觀要件
行為的主觀要素與犯罪的主觀要件都屬于犯罪行為人主觀方面的內容,但除了它們在犯罪構成中地位不同以外,他們的概念本身也各不相同。犯罪的主觀要件,實質上是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時對于犯罪結果的一種心理態度,這種態度除了追求該犯罪結果發生以外,還包括對犯罪結果的放任,漠不關心,不重視等態度,而這種放任,漠不關心或不重視等態度卻并不是行為的主觀心理要素。如在過失犯罪的情況下,行為的主觀要素必定是行為人追求各該過失犯罪的犯罪結果以外的其他結果,否則行為人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身體狀態就不能被評價為“行為”,因為無目的的身體狀態不是行為,因而也不能成為犯罪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行為的目的有時候比較簡單,但有時候卻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系統。行為目的本身也體現了行為人對結果的一種態度,即行為人對于犯罪結果的追求態度,而這種態度與犯罪構成主觀要件是競合關系,如殺人行為希望死亡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既是行為的目的,也是犯罪的直接故意。這種競合關系使得這種心理態度既是行為的構成要素即客觀構成要件要素,也是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不只是犯罪故意如此,就連部分犯罪目的也是如此。眾所周知,犯罪目的分為法定犯罪目的和非法定犯罪目的。所謂非法定犯罪目的,顧名思義,就是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犯罪目的。那么,這種非法定的犯罪目的從何而來?不能由學者或者法官主觀臆斷。事實上,非法定的犯罪目的就是從行為的主觀要素中提取的。盡管行為可能由各種動機所引起,但就單個行為概念而言,行為可分為單目的行為和復合目的行為,如殺人行為就是單目的行為,盡管殺人的動機可能各種各樣,但希望他人死亡這個目的足以滿足殺人行為的主觀要素。而盜竊行為則屬于復合目的行為,直接支配盜竊行為的意志是希望在不被他人察覺的情況下轉移他人的財產,然而僅希望在不被他人察覺的情況下轉移他人的財產尚不足以成其為盜竊行為,因為那也有可能是愚人節開玩笑的玩笑行為,因為以開玩笑為目的在不被他人察覺的情況下轉移他人財產的行為明顯是不具有盜竊性質的。因此,在不被他人察覺的情況下轉移他人財產的行為若要具備盜竊性質,其行為還必須受非法占有目的所支配。也正因為盜竊行為性質本身具備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素,刑法無需再為盜竊罪規定“非法占有目的”。這是非法定目的犯的犯罪目的存在的理論基礎①據此來看,我國刑法學中爭論的關于偽造貨幣罪是否目的犯問題不難解決。“偽造”并非復合目的行為,就偽造行為的性質而言,主觀要素除了意志以外并無其他目的,而我國刑法也并沒有為其犯罪構成規定一個目的。因此在我國,偽造貨幣罪不是目的犯。。
綜上,盜竊行為中行為人“自認為秘密”是行為的主觀要素,因而屬于犯罪構成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簡單地說,屬于客觀要件中的主觀要素。不僅如此,連盜竊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也屬于犯罪構成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因此,“自認為秘密”的說法,并沒有混淆犯罪構成中主觀要素與客觀要素的區別,而恰好是該要素在犯罪構成中的正確定位。
四、刑法中行為概念的意義
(一)簡單罪狀中的概念必須是眾所周知的概念
我們知道,刑事立法中對于部分犯罪構成要件的描述使用的是簡單罪狀。應該說,法律條文涉及到是非曲直,同時涉及到責任追究,因而在用語的使用上都是最為嚴謹的,對于罪狀的描述也應該是最為準確的,盡可能避免產生歧義。然而立法者之所以會使用簡單罪狀,是因為立法者確信簡單罪狀中所使用的語詞,既能夠精確地表達立法者所要表達的概念,也能夠精確地把立法者所要傳遞的法律信息傳遞給它的調整對象,不至于影響法律的實施。而能擔此重任的語詞及其概念,必定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眾所周知的,清晰的,不易產生歧義的語詞和概念,“只有在某一罪行是眾所周知而不需要在刑法分則條文中專門敘述其特征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簡單罪狀。”[11]54而盜竊則正是這種概念,所以刑事立法上對于盜竊罪使用了簡單罪狀[11]54②我國《刑法》第264條所規定的盜竊罪的罪狀雖然使用了較多的字數,即:“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但這只是為了符合刑法第13條關于犯罪的量的規定性而增加的情節要素而已,而在質的規定性上盜竊罪狀仍然是簡明的。。社會大眾對于生活中各種常見概念的認知,來源于他們所受的語文教育,而語文教育中各個概念的語詞含義則來源于各該國的通用詞典,如漢語教學中所通用的《現代漢語詞典》,因而我國一般社會民眾對于“盜竊”的理解應該是與《現代漢語詞典》一致的。
(二)公開盜竊論不利于刑法機能的實現
刑法具有行為規制機能(或稱規范[12]或規律[13]機能)。盡管學界對于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在刑法中的地位有不同的理解,但對于刑法具有這一機能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所謂行為規制機能,就是指刑法通過對犯罪的否定評價(評價機能),來影響公民的自由意志選擇,使之作出“不選擇犯罪”的意思決定(意思決定機能),其中評價機能是手段,決定機能是目的。然而,手段要能服務于目的,就必須保持刑法評價中的犯罪行為的概念與普通公民所認知的概念是一致的。如果刑法與公民的認知之間沒有共同的概念信息,就不能形成有效的交流。沒有有效的交流,公民就得不到正確的信息。沒有正確的信息,公民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意思決定,從而刑法的意思決定機能就不能實現。“公開盜竊”超出了公民的認識范圍,不利于刑法的意思決定機能的實現。
(三)公開盜竊論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重要意義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為了保障人民自由,刑法必須事先明確告訴人民什么是犯罪及犯罪后應該受到什么樣刑罰處罰。“不屬于刑法明文規定的行為,即便其法益侵害再嚴重,也不可能科處刑罰。”[14]56“國民通過刑法用語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為。在了解的過程中,國民當然會想到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14]51從而預測自己行為在刑法上的性質及其法律后果。對于“盜竊”,國民所能想到的當然是他們在語文學習中所學到的《現代漢語詞典》中所解釋的含義,即“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盡管語言在人們的生活和生產實踐中會不斷發展,但“盜竊”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該詞條被修訂之前,只能是“秘密地取得”,而不只是“其原本含義也是秘密竊取”[15]949。如果將國民根據刑法用語所預想不到的“公開盜竊”[15]949解釋為刑法用語“盜竊”所包含的內容,就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從而就會妨害國民的自由。
縱然刑法的適用是離不開解釋的,罪刑法定原則也不會完全排斥刑法的解釋,但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絕對不允許類推解釋,因為“類推解釋的結論,必然導致國民不能預測自己的行為性質后果,”[14]51國民面對刑法的類推解釋是沒有自由可言的①“法官一旦形成了她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其結果就會有人失去了自由、財產、孩子,甚至生命。”(Robert M.Cover:Violence and the Word,The Yale Law Journal,1986,Vol.95:1601)。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的解釋不能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判斷依據,則是“一般語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標準的語言用法。”[14]58如對于“盜竊”來說,若依一般語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標準的語言用法,則不能超過《現代漢語詞典》中的“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這一含義。將所要解釋的概念提升到更上位的概念作出的解釋,則是類推解釋,比如將“竊取”②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竊取”是偷竊的意思,而“偷竊”則是盜竊的意思。解釋為“違反被害人的意志,將他人占有的財物轉移為自己或第三人(包括單位)占有”[15]949,因為“違反他人意志將他人財物轉移為自己占有”的不只是竊取,幾乎所有財產犯罪行為都具有這一特征,尤其是搶奪行為。事實上“違反他人意志將他人財物轉移為自己占有”的行為就是各財產犯罪行為的上位概念,刑法正是根據財產轉移的方式不同才將財產犯罪行為區分為盜竊、詐騙、搶劫、搶奪等下位概念。同時,將“公開盜竊”解釋為盜竊,不只是讓一般國民感到特別意外,就連大多數中國刑法學者都感到意外,這也充分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由此也可以說這種解釋屬于類推解釋[14]59。中國已逐漸進入法治時代,即便不能將所謂“公開盜竊”的情形解釋為搶奪,那也不能用類推解釋的方法來填補“處罰上的空隙”[15]949,因為通過類推方法來填補的漏洞,屬于真正的刑法漏洞,而這種真正的刑法漏洞只能由立法機關通過修改刑法來填補[13]56。因為,在罪刑法定原則下,“不屬于刑法明文規定的行為,即便其法益侵害再嚴重,也不可能科處刑罰。”[14]56如果僅僅為了彌補刑法處罰上的空隙而適用類推解釋,那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違反,是對國民自由的侵害。將國民根據刑法用語所預想不到的事項解釋為刑法用語所包含的事項,會超出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從而導致國民實施原本不認為是犯罪的行為卻受到了刑罰處罰[14]51,這樣才會真正造成不公正現象。
五、結論
概念是人類在長期社會實踐中,對整個客觀世界進行切割、分類所形成的最基本的思維形式,是思維機體的細胞,是相互交流的基礎。概念的統一是有效交流的前提。法律的制定和頒布是立法者與調整對象之間的交流,因此,法律中所使用的概念必須與它所調整的對象之間保持統一,否則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地實施。不同語言的族群之間,因不同的社會歷史實踐經驗,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必然有所不同,所使用的概念也一定會有所差異,因此,我們在借鑒他國經驗時,必須要考慮這些差異,不能盲目吸收。中華文明中的“盜竊”概念,在有些國家是沒有的,翻譯家們的牽強附會,在法學研究中不能當然地接受。我國的刑事立法并沒有日本當時的時代背景,日本刑法學可以將錯就錯,而我們則不能盲從。
盡管行為是犯罪的基本構成要件要素,但行為與犯罪畢竟是兩個不同的事物,它們的構造也各不相同,不僅犯罪有其主觀構成要件,行為也有其主觀構成要素。行為在犯罪構成中屬于客觀要件,那么行為的主觀要素當然也隨之歸屬于客觀要件,不能因為行為的主觀要素與犯罪的主觀要件發生競合而否定行為的主觀要素在犯罪構成中的地位。區分行為的主觀要素與犯罪的主觀要件,不等于混淆犯罪構成中主觀要素與客觀要素的區別。
立法者為了與調整對象之間保持概念的統一,在語詞的選用上有較高的要求,確保能夠精確地把立法者所要傳遞的法律信息傳遞給它的調整對象。然而刑法中之所以使用簡單罪狀,是因為立法者確信簡單罪狀中所使用的語詞,既能夠精確地表達立法者所要表達的概念,也不至于影響法律的實施。能夠被用于簡單罪狀的行為概念,必定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眾所周知的,清晰的,不易產生歧義的概念,而“盜竊”則正是這種概念。由此,刑法學家對于盜竊行為的解釋,不能超越人們日常生活中眾所周知的內容,否則不僅會阻礙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的發揮,而且也違反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則。
(本文是許富仁博士生前與本人合作的一篇文章,由許博士提議,本人執筆完成的。許富仁博士是一位非常敬業的學者,退休后仍繼續從事刑法學研究,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個月里,躺在病床上也不時通過微信與我討論學術問題,其治學精神令我十分感動。今將本文獻給許富仁博士,以表達我對他的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