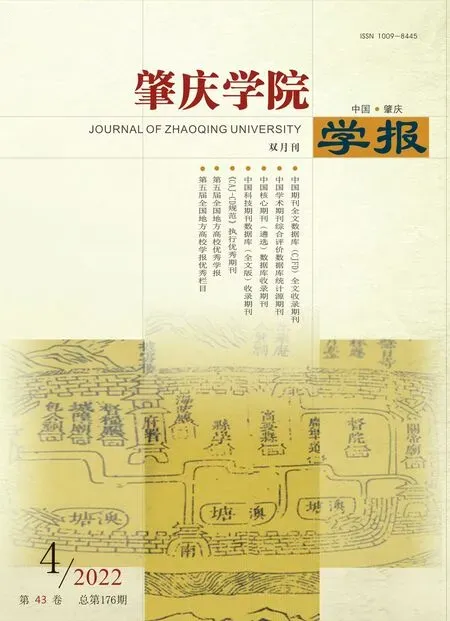論生態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與重構
王士榮
(江蘇商貿職業學院 會計與金融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1)
1968 年,法國五月運動過后,資本主義國家隨即進行政策性統治策略調整,在科技飛速發展的輔助下,資本迅速完成全球性空間再布局,重新構筑起以商品消費為主要“景觀”的全球化跨國資本積累機制。在資本的控制下,人們沉浸在消費狂歡之中,而完全意識不到被異化了的消費狂歡背后所隱藏著的意識形態控制,只能與資本主義形成更深層的依附關系。更嚴峻的是,在資本構建的消費狂歡背后,必然帶來對自然的索取無度和環境惡化,導致全人類籠罩在“生態危機”陰影下,直接威脅人類的生活和生存。但是,面對統治策略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的資本主義制度,西方馬克思主義卻束手無策,只能聽任危機蔓延。
在生態危機的威脅下,阿格爾、奧康納、福斯特、佩珀、高茲、萊斯、格倫德曼等歐美環境學者和思想家從異化消費、技術控制自然、現代性思想等揭露資本主義造成生態危機的必然性,通過建立生態社會主義探索生態政治的可能途徑,進而把改變的希望寄托在以綠色主義者、第三世界群眾、后工業無產階級為代表的被邊緣化群體,試圖重塑革命主體。生態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和方法,以“生態”維度切入資本主義制度批判,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能量,既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新的生長點”[1],也為我國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和參考維度。
一、“失敗的制度”:資本主義與生態危機根源
在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作為科學概念的“生態學”最初只是作為理論舞臺的背景出現,而不具有歷史動力功能。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在科技的助推下,資本主義實現了從生產到消費的轉變,消費成為資本主義實現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但是,為了緩解異化消費帶來的生態壓力,資本主義不得不向全球轉嫁生態矛盾,使得生態危機蔓延全球,“生態”逐漸成為揭露與批評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重要維度。生態馬克思主義發端于以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和方法,主要從異化消費、控制自然、生態殖民三個維度批判資本主義生態危機,以揭示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一)異化消費: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資本邏輯
隨著歷史的發展,借助于科技革命的助推,當代資本主義已經成功地突破了生產領域的危機,并無節制的生產出大量消費品。為了把商品的使用價值迅速轉化為交換價值,實現利潤最大化,資本主義致力于構建以消費為核心的生活觀和幸福價值觀,鼓勵人們把全部精力從生產轉向消費,營造狂歡氛圍以刺激消費,用“虛假需要”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錢利益,甚至“把人格在內的一切東西都貶低為追求利潤的手段”[2]148,導致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感受不到自由和幸福,只能沉湎于消費帶來的“虛假滿足”。在加拿大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本·阿格爾看來,這就是“異化消費”,即“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3]492。更重要的,生態馬克思主義把異化消費看做資本主義對社會實現深層控制的根本方式。由于資本主義的刻意鼓勵,不同階層人們被虛假消費抹平差異,進而被同質化,人們在消費價值觀和幸福觀的掩蓋下被高度集約的資本市場所左右,完全意識不到背后的資本在無形地操縱。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不與人的需求相聯系的異化消費,表面上看似使人們獲得了某種自由,但在本質上人們實際只是“受到抬舉的奴隸”[4]。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由于消費領域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最大的社會現實,因此,必須把傳統馬克思主義著重從生產領域批判工業資本主義危機拓展到消費領域。由于異化消費背后所追求的利潤最大化必然會導致大量廢棄進而對生態造成危害,而為了鞏固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又不得不強化這種異化消費,這就把異化消費和生態危機緊密捆綁在一起。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今天資本主義危機已經從生產領域轉移到異化消費所導致的生態危機,資本主義面臨的不僅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第一重矛盾”,更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第二重矛盾”[5]436,而“第二重矛盾”則是資本主義更迫切的危機。
(二)控制自然: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意識形態
面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諸多環境學家相信作為人類自我拯救的手段,技術的發展能夠增強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使人類解決生態危機,延續資本主義的統治。但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生態危機的根源之一恰是這種“控制自然”的現代意識形態,如果不突破這種現代意識形態的困囿,無論技術如何發展,都必將面對“杰文斯悖論”,進而導致自然對人類更嚴厲的報復。在這一點上,技術“只是減緩我們走向星球無法恢復的那一點的速度”[6]。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不在于技術,而在于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使用技術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放人的身體局限,而是為了最大程度地獲取利潤,而這只能導致對環境的進一步破壞。其結果,必然是技術愈益發達,人愈益化為馬克思意義上的“愚鈍的物質力量”[7]。受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性思想啟蒙、認為啟蒙理性已經走向技術理性的思想啟發,生態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在“二元論”這一“現代性”思想之源上批判人類通過技術試圖控制自然的迷思。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源于啟蒙運動的現代性原本是為了使人擺脫蒙昧的控制,脫離自然的局限,但隨著現代的發展,卻形成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二元對立,為人類“肆意掠奪自然資源(包括其他所有種類的生命)的行為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理由”[8]。在這種“控制自然”的現代意識形態的控制下,資本主義肆無忌憚地侵犯和剝奪自然,以滿足對高額利潤的占有,這就必然導致生態危機。
(三)生態殖民: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制度轉嫁
“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得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9],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把生產和消費變成世界性的。從這一維度出發,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通過生態殖民,把生態危機轉嫁到第三世界國家,通過建立“生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緩解了生態矛盾,延續了社會統治。為了緩解資本主義和生態危機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為高消費提供更豐富的商品,以維持更高水準的生活,同時避免生態進一步惡化,資本主義國家在把高污染、高消耗生產企業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的同時,更把有毒污染物直接傾銷到這些國家,通過污染轉移的形式來改善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和生態。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這種生態危機的轉嫁是對全球生態的殖民,通過這種“更高的不道德”和“窮國的饋贈”[10]52,資本主義國家得以維持富裕的生活,但全球生態危機卻進一步的加深,全人類都處于生態危機之下。
二、生態社會主義:通往生態政治的可能途徑
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作為一種失敗的制度,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全球生態危機,這也使得資本主義帶有“自我毀滅”的內在趨勢,因此,單純地從技術、環境、經濟等方面試圖解決全球生態危機,只能陷入強化資本主義統治的“現代性”牢籠。故而,要反抗資本主義對生態與人的異化,就只有走向生態社會主義,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生態馬克思主義主要從破滅消費價值觀、實行穩態經濟以可持續發展、通過基層民主實現生態社會主義三方面探尋實現生態政治的可能途徑。
(一)期望破滅的辯證法:抵抗消費控制
由于資本主義通過構建消費社會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望以消費異化實現社會統治,所以,人們的消費欲望不是基于生活本身的需要,消費所帶來的滿足不是基于勞動滿足帶來的幸福感,而是一種虛假的滿足,因此,愈加消費反而愈加強化了人們的不滿足感。資本主義很好地利用人們的這種消費期望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雖然給生態帶來更大的危機,卻強化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統治。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要解決生態危機,首先應破除的就是人們對異化消費的期望。在阿格爾看來,由于內在的生態危機,資本主義注定不可能源源不斷地給人們提供維持高消費的商品,所以人們應該打破對消費的這種期望,進而破除異化消費的控制,把自己對幸福生活的理解奠基在在一個并不完全豐裕的世界上,進而重新確立自己的消費觀和幸福觀。阿格爾把這一社會變革過程命名為“期望破滅的辯證法”,并強調在其中蘊含著“進行社會主義變革的有力的動力”[3]496。可見,阿格爾的“期望破滅的辯證法”旨在打破資本主義生產“多”與“好”之間的畸形關聯,以轉變人們的異化消費觀,實現從資本主義生產“多”到“少”的轉變,進而破除資本主義的消費控制,反抗資本主義以生態進行社會控制。與之類似,萊斯、福斯特、高茲等學者則進一步提出應該構建“較易于生存的社會”來取代當前高生產、高消耗的資本主義,使社會生產的目的以保障人、特別是窮人的基本需求為主,降低對商品的額外需求,把人們的幸福感從消費導引向勞動,進而把人均能源消耗降到最低限度,在他們看來,“這是我們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進行斗爭所要堅持的基本道義”[11]42。
(二)穩態經濟:緩和生態危機
與破除消費欲望相對應,生態馬克思主義主張應控制經濟增長的規模和速度,在保證社會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礎上,縮減大規模的技術應用,使生產過程小規模化和分散化,以抑制資本的逐利本性,把大規模的數量積累轉變為小規模的質量提升,從而緩和資本主義和生態危機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必須通過建立“穩態經濟模式”把“經濟理性”置換為“生態理性”,才能推動技術的“生態轉向”。如果不能推動這一轉向,即使是社會主義也同樣會陷入“經濟理性”的迷途之中,被“不增長就死亡”的狹隘價值觀所左右,盲目追求GDP的增長,給生態帶來巨大危險。印度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薩拉·薩卡通過對蘇聯生態問題的分析認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自然條件,完全有可能實現對生態更好保護,但由于蘇聯盲目追求GDP 高速增長,陷入“不斷增長”的發展邏輯中,反而給生態造成了更大的危機。所以,薩卡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應建立在“穩態經濟”的基礎上[10]28。針對對“穩態經濟”就是零增長會導致社會發展停滯的批判,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穩態經濟”不是不增長,而是改變對增長的極端追求,使經濟增長的規模和速度與人們的實際需求相適應。因此,生態馬克思主義推崇“小的是美好的”這一經濟觀點,認為其背后的“小規模技術”更符合生態,是更“具有人性的技術”,能夠推動經濟自然和諧發展,最終“把數量的積累轉變為質量的改進”[12]。
(三)基層民主:通向生態政治
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中,生態危機是內在于資本主義的,而資本主義也正是通過生態危機把人們牢牢地控制在社會統治體系之中,因此,要解決生態危機,其根本出路就是變革資本主義社會。但是,著名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福斯特認為,處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人類似于“籠子中踩腳踏輪的松鼠”,如果沒有外力的助推,人們“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從籠子中脫離”,所以,社會變革不可能自動完成,必須借助于社會主義才能完成,因此,“真正的生態革命必然是社會主義的”[11]37。福斯特、佩珀、高茲、阿格爾、萊斯、奧康納、克沃爾等眾多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認為,生態危機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走向生態社會主義,但是,在具體實施途徑上卻有所區別。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在未來的生態社會主義中,人與自然是和諧統一的,這就必然要求人與人之間的聯合是自由人的聯合,也就決定了生態社會主義必然是民主的,只有充分發展的基層民主,才能保證人的自由存在,進而抵抗資本主義以生態危機來阻礙社會變革。但是,要注意的是,隨著生態運動的興起而產生的“綠色運動”及其政黨組織“綠黨”,雖然對環境保護有重要貢獻,但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綠色政治”的政治理念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用市場經濟的機制來解決生態危機,試圖推動生態與資本主義共存,其結果只能是進一步強化資本主義制度,帶來更嚴重的生態危機。所以,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方向,通過激進社會變革才能實現社會正義以消除生態危機,到那時,“非人的自然將被改變而不是被破壞,并且,更加使人愉快的環境將被創造而不是被破壞”[2]356。
三、重塑主體:“后工業無產階級”與國際聯合體
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刻意淡化階級斗爭這一馬克思主義經典命題不同,生態馬克思主義重提這一經典命題,致力于建構生態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導力量。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雖然生態危機內在于資本主義且使資本主義帶有“自我毀滅”的趨勢,資本主義必然過渡為生態社會主義,但是,這種變革不是自動的歷史進程,必須依靠革命主體的革命能量方能實現。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傳統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兩種力量的劃分發生了發生了重大調整,特別是隨著女權運動、和平運動、綠色政治、同性運動等諸多政治派別的興起,使得諸多邊緣階層躍上歷史舞臺,成為時代政治的重要組成力量,這就為生態馬克思主義重塑革命主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工人階級:生態社會主義的依靠力量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資本主義改變統治策略,逐步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加之刻意營造的消費意識形態,逐步誘導工人階級沉湎于消費的虛假幸福之中,喪失了革命的主觀能動性,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的“肯定力量”。安德烈·高茲更是認為資本主義的成熟使得工人階級逐漸碎片化甚至和資產階級成為一體,工人階級再也無法控制生產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馬克思的工人階級理論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成為一封“沒有收信人的信”[13],工人階級已經喪失了革命的“主體”地位。但很多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卻堅持認為生態社會主義的實現必須依靠工人階級這一革命主體,致力于激發工人積極的革命覺悟。阿格爾在生態社會主義理論中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認為生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馬克思主義,正因為其“沒有忽視階級結構”。激進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佩珀則明確指出生態社會主義強大的變革力量是“潛藏的階級沖突”,只有工人階級才有對抗資本的“權力”。奧康納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生產仍然是階級關系,不依靠工人階級實現生態的社會變革是“烏托邦”,工人階級依然是變革的“主要依靠力量”[14]。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因遠離工人階級而產生革命悲觀情緒進而背離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這一經典命題不同,生態馬克思主義因致力于批判資本主義而重回馬克思階級理論的經典命題,并在階級沖突中尋求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力量,進而重構工人階級的主體地位,也使得生態社會主義更具有現實可能性。
(二)后工業無產階級:生態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
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以及社會運動的深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層越來越多元化,工人階級的構成也越來越復雜化,大量的勞動者被日常化的穩定工作排斥在外,不得不選擇從事間斷性的勞動,以短期工、臨時工、鐘點工,甚至是長期失業者的狀態從事勞動工作。同時,隨著科技的發展,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等處于穩定工作和間斷性勞動之間狀態的新的勞動階層迅速壯大,成為資本主義重要的階級構成。而且,隨著社會運動的深入,女權主義、綠色政治、和平運動、同性運動等眾多新社會運動團體也因脫離于工人階級而逐漸被邊緣化,這些被邊緣化的團體更易于遭受生態危機的威脅,其團體利益更易受威脅。在高茲看來,這些游移于工作與非工作邊緣的中間階層雖然身份模糊,沒有明確的工人階級意識,但卻因身份模糊而難以被資本主義用工作和消費誘惑,因而相對于被工作困囿的工人階級反而具有更大的優越性。因此,這些“后工業無產階級”應當成為生態社會主義可能的“社會主體”和“主要力量”[15]。佩珀和奧康納則堅持工人階級不應單獨行動,而應該加強與眾多被邊緣化的新社會運動力量的團結,與他們結成牢固聯盟,引領并促使他們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恢復和重構(從而重新界定)他們的生活世界的事業”[5]512。
(三)第三世界勞動群眾:生態社會主義的聯合力量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化,生態危機也被擴散到全球各個國家,由于在生產關系中的不平等,資本主義借助生產把生態危機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通過生態殖民,資本主義緩和了社會危機,但卻使第三世界國家的生態危機更加惡化。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環境威脅對每個國家中的個人并不是同等嚴重的,在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態殖民而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第三世界國家卻不得不承受生態危機的惡果。因此,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群眾作為生態危機最直接最嚴重的受害者,應成為生態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巴羅提出應特別把第三世界國家中被邊緣化的團體團結進反對生態危機的隊伍中,福斯特認為由于第三世界群眾在面臨生態災難時已經無可失去,所以他們堅決以激進措施反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佩珀則主張由于生態危機的全球化,第三世界國家勞動群眾應該是“反對全球資本主義根本斗爭的一部分”[2]284。由于生態危機的全球化,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爭取第三世界國家勞動群眾參與反抗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時,應“以19 世紀的方式做出反應”,團結更廣大范圍第三世界國家勞動群眾結成國際聯合體,“激發全球對抗帝國主義、阻止地球毀與遏制資本車輪的起義”[11]123。雖然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建設的設想具有一定的烏托邦色彩,但生態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和方法,以生態維度切入當代資本主義批判,論證生態危機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生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必然的變革。同時,生態馬克思主義把工人階級、后工業無產階級、邊緣群體、第三世界勞動群眾結成國際聯合體,試圖重塑革命主體。生態馬克思主義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工人領導、資本主義批判等經典命題,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深入到歷史的一個本質性維度中”[16]。“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17]。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倡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持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道路,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和生態保護措施,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思想,為解決全球生態危機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而這,也是眾多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贊譽“世界生態文明未來希望在中國”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