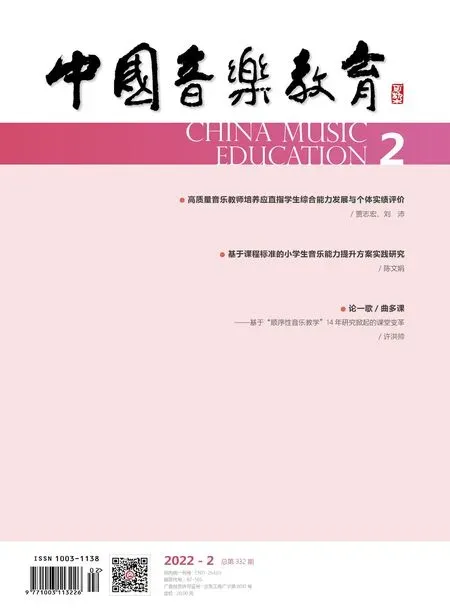借影視聲音探究音樂教育的生態格局
張漢超、胡 夏
音樂本就起源于人類對聲音的探索。無論是《禮記·樂記》中的“人心感于物”,抑或是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說”,都體現了東西方乃至全人類音樂的異派同源。但隨著千百年來人類音樂文化的不斷精進,音樂在教育中逐漸被物化、理化和神化,變成了少數人才能夠和應該具備的才能。尤其是在西方古典音樂體系的主導下,對于權威的膜拜,使得音樂教育潛移默化地被框定在有限的價值觀、語匯與方式中,形成了相對固化、精致的金字塔生態。盡管如此,在現象學倡導的“回歸事物本身”的理念下,20世紀后現代主義思潮及多元文化音樂教育觀還是重新意識到了音樂的聲音本體及其與人的天然關系,并在過程中不斷消解著那座“金字塔”。慢慢地,不僅西方古典音樂走下神壇,被視為眾多音樂文化之一,更重要的是,借助對噪音的重新審視與現代信息技術的進步,人類重燃的聲音探索熱情賦予了音樂新的定義。例如,美國實驗音樂的代表人物約翰·凱奇曾說過:“假如音樂這個詞是神圣的,是保留給十八九世紀的樂器的,那么我們可以用更有意義的術語代替:‘有組織的聲音’……”①這種觀點讓更多人有了親近音樂的動力,也賦予音樂在角色、形態和意義上的更多可能。
作為音樂的一門姊妹藝術,以影視聲音(或稱電影聲音)為代表的聲音藝術領域對于音樂的生態格局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影視聲音既是一門課程,也是一門交叉學科,它結合了影視、音樂、心理聲學等領域,與錄音藝術、音樂制作、聲音設計等專業有著密切的關聯。縱觀西方自19世紀末留聲機誕生以來的歷史脈絡可以發現,音樂作為最早的聽覺元素推動了默片的發展,而聲音技術、藝術理念的進步和視覺媒介的協同,又不斷為音樂的探索和呈現提供反哺。可以說,影視聲音與20世紀音樂的發展相輔相成,交相映射著人類對于聲音技術和藝術理念的探索。
一、影視聲音對音樂教育的生態關聯與問題折射
對于音樂教育而言,影視聲音不僅影響了人們記錄、欣賞和學習音樂的方式,還促進了音樂相關學科的拓展——即20世紀中葉以錄音藝術為代表的聲音藝術學科的確立,如德國教育體系中較早出現的“音響導演”(tonmeister)概念②。有趣的是,據史料記載,貝多芬喜歡稱自己為“音響藝術家”(tonkünstler)或“音響詩人”(tondichter),而非作曲家(komponist)。③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聲音藝術領域與音樂的天然關聯。
在我國,聲音藝術學科也是從設立影視聲音課程開始的。1951年,中央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學校《藝術系演員班教學計劃草案》中就出現了“電影錄音”課程。④不過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該類學科更傾向于工科領域。關于音樂科技的學科路線,則以80年代中期先后于上海音樂學院和中央音樂學院建設的計算機音樂實驗室為標志,⑤這從某種程度上也為我國的聲音藝術學科注入了更多的“音樂成分”。截至2019年的統計,包含北京電影學院聲音學院、中國傳媒大學音樂與錄音藝術學院、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工程系在內,全國已有至少41所大專院校開設了聲音藝術的相關專業⑥,而影視聲音也是這類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究其原因,不僅因為電影(影視)行業不斷繁榮,其藝術與工業體系對音樂、聲音人才有大量且復合的需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影視聲音強調的知識與能力結構,包括音樂技能與藝術素養、音頻剪輯與創作、電子與聲學基礎及視聽媒介的整合等,對于完善音樂、聲音人才的培養不可或缺。
從專業音樂教育來看,影視聲音領域與其關系密切。相關高校在選拔考生時會有較為全面的音樂能力考查,在培養階段,除了音樂科技類專業外,作曲、音樂學等傳統音樂學科也越來越多地關注到影視聲音。但與此同時,我國的音樂教育仍較為明顯地受制于傳統音樂教育生態觀,使得影視聲音乃至整個聲音藝術學科,因其交叉學科的特點,在學界的存在感尚顯微弱,更不要說涉足大眾普遍認知的領域。在2019年末于南京藝術學院舉辦的中國高校影視聲音藝術教學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和教師普遍認為當下的聲音人才培養標準不夠明確,考生的水平良莠不齊,缺乏規范的啟蒙教育,基本的聲音聽覺素養不足。我國音樂教育的另一個短板,即音樂創作問題,這在影視聲音領域也尤為突出。業界的優秀影視作曲家和聲音設計師長期處于緊缺狀態,以至于不少知名導演需要求助國外音樂家或聲音公司,這與我國音樂表演人才在國際上的強勢突破落差明顯。
當然,從另一個視角出發,影視聲音領域的問題與現狀,未嘗不是我們探究音樂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如果說傳統金字塔生態在短短幾十年間,依靠激烈的競爭與合力迅速確立了專業音樂教育體系的高度與權威性,那么未來隨著技術的跨越、音樂觀念的解放及音樂人才的多元需求,音樂教育將在與其他藝術、人文和科技的融合中涌現出更為廣闊的藍海,同時其核心定位也將與時俱進地發生變化。這是一個不斷向內自省和向外延展的過程,能夠使影視聲音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為音樂教育提供一些靈感。
二、小音樂,大生態
不可否認,音樂教育的概念在持續擴充,新的知識和學科讓我們感受到音樂教育的活力與潛能。但在相對閉環的音樂學科格局里,當這種擴充與膨脹超越了人們的學科認知屏障后,我們的音樂教育恐怕會面臨“到底應該教什么”的尷尬。當下,各類藝術院校圍繞聲音、音樂科技等跨學科領域所設置的培養計劃存在較大差異,就反映出這個問題。因此,共同營造一種適應當下與未來的生態格局不容忽視。
(一)聚焦音樂的聲音本質,關注多元音樂體驗
當今的中西方學者在談到音樂教育的生態格局時,都在強調“人—音樂—萬物”的關聯性和整體性,通過研究人作為生物的原始音樂沖動,以及音樂與人類世界的關系,探討一種開放式的系統。在人類的多元文化視野下,音樂無法被統一定性,甚至有越來越多的音樂現象超越了主流“科學理論”的解釋范疇。因此,如前所述,將音樂從整體上視為“有組織的聲音”,會有助于不同文化間的求同存異,并在剝去文化的非藝術性外殼后,還原音樂最初的形態——一種聲音的、流動的、抽象的“生命形式”。
從音樂到聲音,看似從簡到繁,實則是一種向內的“減負”,因為每個人幼年時都是通過細小的、不經意的聲音創意逐步形成音樂感知的。日本學者巖田忠彥(Tadahiko Imada)在關于“聲景”的理念中,倡導音樂教育應從臃腫的“大音樂”(big music)心態轉向“小音樂”(small music)——對體驗和加工原始聲音的關注。他認為,小音樂的理念在音樂教育中可以幫助學生感受到最早音樂的“神奇、不合邏輯及儀式的形式”⑦,并提供了將紙張用作音樂訓練的案例:通過讓學生對紙的充分接觸和傳遞配合,體會身體與紙張聲音的關系,然后引導學生用“吹紙”“撕紙”等多種方式,嘗試開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符號系統,并作為音樂創作的靈感來源。在后現代主義思潮下,音樂史無前例地凸顯著不確定性的特征,“小音樂”實則提醒我們的音樂教育需要滌清自身,保持對聲音的好奇,保持對世界的傾聽與互動,保持對原始創造力的呵護。這是音樂教育拓展的根基。正如國內學者謝嘉幸所言:“‘意’(音樂體驗)的豐富,必然導致‘言’(音樂符號系統)的豐富,而言的豐富性則體現了文化的延續性、整體性和開放性。”⑧可見,“小音樂”作為音樂教育的聚焦點,會輻射出廣袤的音樂文化與生態格局。
國內學者滕守堯和董云將“感知與體驗”與“創造與表現”、“反思與評價”視為音樂教育的生態聯結。⑨作為首當其沖的環節,充分的音樂體驗可被視為培養靈感與自發性創造力的“根莖”⑩。英國學者博伊斯-迪爾曼也強調完整、全方面的音樂體驗是構建健康音樂教育生態的重要途徑。?如今在科技的加持下,我們可以從更多角度為學生提供音樂體驗的機會,如聲音素材的多元化(各種自然界與人工合成的聲音)、感官知覺的多元化(視聽及觸覺、動覺的交互)、創作工具的多元化(樂譜、樂器、錄音設備或者midi設備)等。影視聲音領域具有較為豐富的相關經驗,我們的音樂教育可以適當援引其教學內容和方式來拓展體驗。比如,將影像世界作為現實世界的有效補充,引導學生在面對不同的影像世界時,去揣摩每個細微的聲音片段如何藝術性地表達,聲音的組織如何具備音樂架構,如何做到聲音既來自影像世界又對其升華,等等。關鍵是,這些手段能否結成有效的系統,是否圍繞創造力所需的核心素養,就需要音樂教育工作者的智慧了。
(二)突破音樂的概念邊界
既然音樂是有組織的聲音,那任何組織在一起的聲音都是音樂嗎?這涉及關于音樂教育內容核心的思辨。西方音樂學長久以來秉持的二元認識論,為已經客觀存在的音樂與一般意義上的聲音之間設定了清晰的邊界,如樂音與噪音的區分、和聲與曲式的規則等。就像提到影視聲音一樣,在大眾的認知中,不熟悉概念的人們往往會與影視音樂混淆,而在進一步了解后,也會很自然地把音樂、語言和音響這三個要素清晰地劃分開來,并認為音樂主要擔負著情感表達的藝術性。事實上,無論是如今的音樂人類學轉向,還是回顧中國傳統哲學,事物之間的所謂邊界并非絕對,更多的是一種“邊緣狀態”?,或者說交織狀態。早在默片時期,音樂就肩負了語言和音響的部分功能,那反過來,語言和音響這種傳統音樂理論所定義的噪音,也應具有一定的音樂意義。在如今的影視聲音理論中,三要素可以相互轉化已是共識,不僅是影視聲音,很多領域都在關注語言和音響的藝術性表達,二者在配樂中也正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甚至在熱門綜藝《這就是街舞》第二季中,還出現了一段完全由語言擔綱的配樂。另外,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美國還誕生了基于實驗音樂的“聲音藝術”(sound art)概念,雖然作為跨學科的當代藝術形式,部分學者認為它逐漸變為與音樂并置的概念,但其本質仍與音樂密切關聯。因此,回到“什么樣的聲音是音樂”這一問題,或許音樂作品的類型風格尚且有限,但任何聲音及其組織形式都可以具有藝術性,或者說音樂性,即人為賦予聲音的,凌駕于聲學認知和生理感知之上的情感體驗或藝術表達。而尊重和推崇聲音的音樂性,可以幫助人們解開音樂傳統概念的束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音樂教育也應兼具聽覺藝術教育或聲音藝術教育的職責。
在音樂教育中,嘗試不同的發聲材料,可視為突破邊界的最直接手段。“所有音樂都來自人體和環境的具體材料組成的組織”?,使用不同的材料會更容易幫助學生跳脫思維定式,發掘特色的節奏、音調、音色及創作方式。當然,發聲材料的嘗試離不開已有音樂所賦予的“藝術原型”或“原始意向”?,因此,需要輔以嚴謹的音樂訓練,才能使學生的音樂性不會在創新實踐中迷失。
除了材料之外,我們還需要意識到,在一個錄音技術成熟的時代,聲學空間也是構成音樂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圣詠的莊嚴感離不開教堂混響一樣,音樂的空間特性也體現著其與人和世界的緊密聯系。如今我們從事音樂活動的場所變得多元,而且錄音與還音技術可以通過對聲學空間的模擬,脫離音樂呈現的環境局限,更自如地服務于音樂自身的表達意圖。數字化音樂在經過音箱或耳機播放時,已經是經過混音浸染的非原始狀態,因此聲學設計也被越來越多地納入音樂評價的視角中。
隨之而來的,便是音樂理論也會被聲學、心理學和信息技術等知識擴充。正如加拿大音樂家莫里·沙費(R. Murray Schafer)曾說過的,在電聲中加入音樂被認為習以為常后,學生可能會被訓練用頻率、響度等術語來描述音高和力度,而非僅僅依靠傳統理論和直覺。?
(三)擺正視聽關系
雖然我們總在強調音樂是一門聽覺的藝術,并希望培養學生具備完善的聲音聽辨能力和想象力,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音樂的任何活動環節,不論是欣賞、表演還是創作,都無法擺脫視覺的干涉。根據中國傳媒大學高妍博士的報告,視覺和聽覺是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其中視覺約占83%,聽覺雖排第二位,但只有11%左右的占比。因此,在音樂教育中,我們容易陷入兩個誤區:一個是對視覺干擾的擔憂,比如在教學中控制影片、圖片等視覺媒介的使用,以使學生專注于傾聽。這種觀念有可取之處——對視覺媒介控制得當,可以提升學生的聽覺感知注意——但同時也容易減少教育的樂趣,以及知識獲取的途徑。另一個則是順應人的生理感受,大膽地“擁抱”視覺媒介,但這又會導致“馬太效應”,使聽覺認知更依賴于視覺。如今很多人在沒有視覺刺激的情況下,很難靜下心去欣賞一首較長時間或較為平靜的音樂,便是這種習慣所致。
影視聲音始終在探討如何將視聽置于平等的位置進行配合。法國聲音理論家米歇爾·希翁認為,視聽可以通過相互“增值”,即增加表現力和信息量的價值,來共同構建視聽幻覺(audiovisual illusion)。?音樂心理學中也認為視聽可以通過聯覺的機制,幫助增強對音樂的理解,包括對色彩的想象、情景的聯系及概念性的隱喻等。不論是幻覺還是聯覺,都論證了好的視聽結合絕非機械疊加,而是構建一種“一加一大于二”的關系,使得視聽二者相互輔助且相互成就。作為一種符合人類認知音樂的最樸素的方式,在音樂教育的生態視域下,我們應正視并重視視聽之間的有效鏈接,不僅是通過其引發和豐富音樂教育中的體驗、表現及創作,還應將視聽藝術(媒介)作為音樂教育的一個“出口”,不論在藝術層面還是應用層面,通過放大音樂教育的聽覺藝術教育屬性,讓音樂教育得以嵌入更多視聽領域。
(四)辨析音樂生態中的專業化與職業化
在傳統金字塔生態中,專業化被作為重要的考量標準,而對于音樂偶像和專家的過度聚焦,容易讓大眾忽視為一部作品、一場演出付出的大多數人,比如演奏員、錄音師、編曲師和編導策劃等。而這些“大多數人”,才是支撐音樂行業的基石。得益于工業化體系的推動,如今的音樂生態開始讓人們意識到了音樂的多元和音樂職業的多元,比如《中國好歌曲》《我是唱作人》等節目,將音樂的幕后制作流程和人才推到了臺前,又如《中國新說唱》《樂隊的夏天》等節目,不僅推廣了Hiphop、搖滾樂隊,并重新定義了它們。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普通人”獲得了過去只有偶像和專家才擁有的機會,有些甚至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音樂的細分領域也可以找到實現自我價值的舞臺。由此,我們的音樂教育不得不面對這種行情的改變:音樂的職業化日益凸顯,而如何重新定義專業化,則是亟待思考的問題。
在音樂教育中,項目制協作可能成為專業化與職業化的銜接點。經歷幾十年的電影工業進步,影視聲音已經成為音樂和聲音制作領域的團隊協作模式典范。今天的影視聲音教學不光是培養錄音師和理論人才,而是要把學生“下放”到聲音制作的整個流程中進行演練,切身感受完成一個聲音項目的方方面面,并在高素質人才與職業工種的碰撞中提升自身的專業性。美國學者克林特·蘭德斯也提出過類似觀點,即音樂教師可以參考導演或者制作人的角色定位來管理教學。在技術和知識唾手可得的今日,由教師為學生提供項目和一個“刺激的環境”,讓學生作為“藝術家”或從業者,在協作中體驗編曲、錄音、演唱、演奏和后期制作等不同職責,并想辦法實現他們的構思,最后由教師確保項目被很好地記錄和整合,?已成為現實。職業的多元體驗,可以讓學生找到更多看待音樂的視角,發現自己與音樂的最佳契合方式,并有效減輕過去單一專業化帶來的畏難情緒。隨著音樂生態的不斷擴大,音樂相關職業也在細化及增補,而關注每一個職業環節的細微創新與發展,也可視為“小音樂”理念的另一種詮釋。通過每一個職業的專業化實現音樂生態的整體繁榮,才是健康的發展路徑。畢竟音樂教育的責任不僅是培養音樂家,更是要幫助每個人融入音樂的生態。
三、小 結
倘若把音樂作為對待聲音的思維方式,那么與聲音關聯的廣闊生態格局將給予音樂教育無限的拓展空間。誠然,在聲音宇宙中的教育探索也絕非易事,需要始終秉持開放前瞻的眼界、扎實全面的技能,以及永恒的好奇心和創造力。影視聲音作為一個交叉領域,其已有的教育生態與行業生態可以從側面給予我們探索音樂教育發展的新思路,但也只能窺見一斑。音樂教育的生態構建需要更多領域的人們參與進來,以完善“人的生態”,只有這樣,音樂教育所謂“人的教育”才能得以實現。
注 釋
① 〔美〕約翰·凱奇著,李靜瀅譯《沉默》(五十周年紀念版),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② 姚國強、赫鐵龍、梁婧《創建與傳承:中國影視聲音學科及錄音專業的發展歷程與思考》,《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③ 〔德〕卡爾·達爾豪斯著,楊燕迪譯《音樂美學觀念史引論》,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頁。
④ 同注②。
⑤ 黃志鵬《我國音樂科技學科建設的理論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第94頁。
⑥ 姚國強、赫鐵龍《新中國電影聲音藝術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70年》,《電影評介》2019年第20期。
⑦ Tadahiko Imada,“Soundscape, Sound Education, and the Grain of the Music: Experiencing the Luminousness of Music Being What It Is,” inCreativity in Music Education, ed. Yukiko Tsubonou,Ai-Girl Tan and Mayumi Oie(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2019),p.40.
⑧ 謝嘉幸《關于當代中國音樂教育的文化思考》,《音樂研究》1994年第2期。
⑨ 董云《生態觀視野下的音樂教育》,南京師范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83頁。
⑩ Yu Wakao,“Toward Ecological Music Education: Thinking from the Batesonian-Deleuzian Views,” inCreativity in Music Education, ed. Yukiko Tsubonou, Ai-Girl Tan and Mayumi Oie(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2019),p.78.
? June Boyce-Tillman,“Towards an Ecology of Music Education,”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Review12,No.2(2004).
? 同注⑨,第85頁。
? 同注?,第104頁。
? 謝嘉幸《音樂的語境——一種音樂解釋學視域(下)》,《中國音樂》2005年第2期。
? 同注?,第106頁。
? R. Murray Schafer,The New Soundscape: A Handbook for the Modern Music Teacher(New York: Associated Music Publishers,1969),p.3.
? 〔法〕米歇爾·希翁著,黃英俠譯《視聽:幻覺的構建》,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5頁。
? Clint Randles,“Music Teacher as Writer and Producer,”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46,no.3(201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