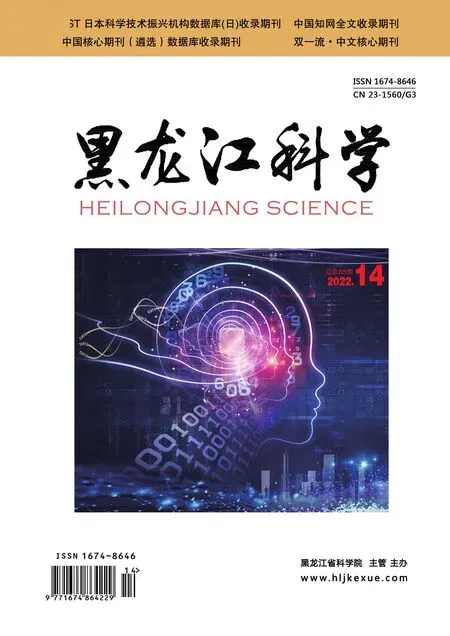抗體依賴性增強效應的作用機制及在人類冠狀病毒感染中的表現概述
2023-01-05 13:07:00尹海暢于天飛
黑龍江科學
2022年14期
關鍵詞:機制
李 靜,尹海暢,于天飛
(齊齊哈爾大學生命科學與農林學院,黑龍江 齊齊哈爾 161006)
0 引 言
病毒感染始于附著宿主細胞膜,在這個過程中病毒表面蛋白與宿主細胞上的特異性受體結合,為了阻斷病毒與靶細胞的黏附,宿主免疫系統通過分泌針對病毒表面蛋白的抗體來中和病毒,從而削弱病毒的感染能力。然而,在某些病毒中,特異性抗體與病毒表面蛋白的結合反而能促進病毒侵入某些類型的細胞,促進病毒感染,這樣的現象稱為抗體依賴性增強效應(ADE)[1]。
HAWKES等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報道稱ADE在埃博拉病毒(EBoV)、人類獲得性免疫缺陷病毒(HIV)、登革熱病毒(DENV)感染中常見[2]。1981年,WEISS等首次報道了冠狀病毒的ADE現象[3]。冠狀病毒家族成員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2(SARS-CoV-2)已被確定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病原體,它的出現和全球迅速傳播導致了大量的全球發病率和死亡率,造成了廣泛的社會性和經濟性破壞。SARS-CoV-2是一種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SARS-CoV)密切相關的β-冠狀病毒(序列同源性約為80%),也與馬蹄蝠中發現的冠狀病毒親緣關系密切[4]。SARS-CoV-2 纖突(S)蛋白由S1亞單位和S2亞單位組成,S1亞單位含有受體結合域(RBD),S2亞單位介導病毒與宿主細胞的膜融合。疫苗接種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產生中和抗體,通過阻斷受體-RBD相互結合作用或S蛋白介導的膜融合來阻止SARS-CoV-2進入宿主細胞。病毒疫苗及抗體相關免疫療法的一個潛在障礙是潛在的ADE可能加重COVID-19感染風險[5]。
1 ADE的作用機制
目前研究認為,ADE存在五種機制,不同病毒的ADE效應不一定由單一機制造成。……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四川勞動保障(2021年9期)2022-01-18 05:11:08
文苑(2018年21期)2018-11-09 01:23:06
當代陜西(2018年9期)2018-08-29 01:21:00
當代陜西(2017年12期)2018-01-19 01:42:33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9期)2017-01-15 13:52:00
中國衛生(2016年9期)2016-11-12 13:28:08
中國衛生(2015年9期)2015-11-10 03:11:12
醫學研究雜志(2015年12期)2015-06-10 06:57:46
中國衛生(2014年3期)2014-11-12 13:18:12
中國火炬(2014年4期)2014-07-24 14: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