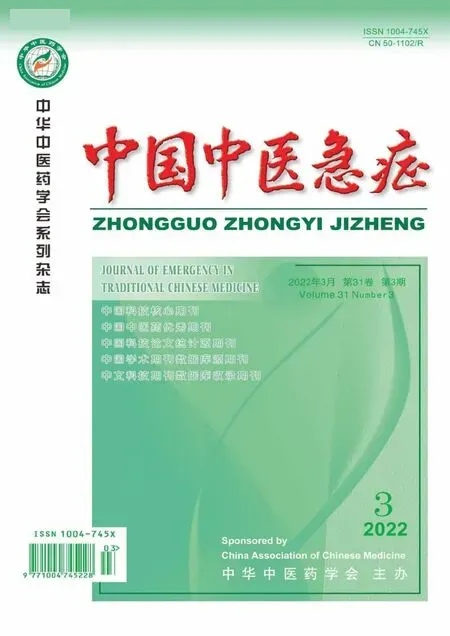僵蠶在瘟疫治療中的運用探析*
姬永寬 陳國森 梁錦娉 劉 果
(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105)
瘟疫,一稱“溫疫”,是一類由感受癘氣引起的具有強烈傳染性的溫病,發病急驟、傳變迅速、具有明顯的傳染性和流行性。明·吳又可《溫疫論》描述溫疫發病為“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瘟疫在治療上的復雜性,不僅由于疫癘的“病邪種類多樣”“病情深重”和“具有高度傳播性”,而且在于瘟疫發病時具有“表證難解”“多兼郁熱、痰濁”“伏邪難清”等致病特點,對應著《溫疫論》中的“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故為熱”“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郁,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為火”“先伏而后行者,所謂溫疫之邪”“伏邪蟠踞”等瘟疫發病機理。
僵蠶被專用于瘟疫治療,最早見于金·張子和《儒門事親·治大頭病兼治喉痹方》“人間治疫有仙方,一兩僵蠶二大黃,姜汁為丸如彈子,井花調蜜便清涼”[1],方中僅有4味:僵蠶、大黃、姜汁、蜂蜜,被溫病學家認為是后世瘟疫名方“升降散”的前身。張氏用此方治療當時的流行疫病“大頭天行”,明·朱橚《普濟方》稱此方為“治大頭病,兼治疫瘴方”[2];對于僵蠶治疫,清·楊栗山在《傷寒溫疫條辨》中稱“白僵蠶…于溫(瘟)病尤宜”,認為瘟疫“乃天地之雜氣為病,非四時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為病”,而僵蠶功能“升陽散火,祛風勝濕,清熱解毒”,用僵蠶治瘟疫“蓋以天地清化之氣,滌疵癘旱潦之氣”,故將其視為“溫(瘟)病之圣藥”。在楊氏所創制的著名治疫十五方中,均以白僵蠶、蟬蛻為君藥,其中升降散(僵蠶、蟬蛻、大黃、姜黃,以僵蠶為君),更被楊氏譽為“瘟疫正治諸方……而升降其主方也”。筆者從古今醫案中摘錄運用僵蠶治疫之典型文獻加以分析,以期對疫病治療有所助益。
1 僵蠶藥解
《神農本草經》中謂僵蠶“味咸平,生平澤。主小兒驚癇、夜啼,去三蟲,滅黑皯,令人面色好,男子陰癢病”。現代中藥學認為僵蠶功效為息風止痙,祛風止痛,化痰散結。清·楊栗山在《傷寒溫疫條辨》中稱“嘗考諸本草,而知僵蠶味辛苦氣薄,喜燥惡濕,得天地清化之氣,輕浮而升陽中之陽,故能勝風除濕,清熱解郁,從治膀胱相火,引清氣上朝于口,散逆濁結滯之痰也”,認為僵蠶在瘟疫治療中可以起到解郁熱、散表風、消痰濕的作用,并應用于瘟疫伏邪的治療。
1.1 疏解郁熱 關于瘟疫的發熱,《溫疫論·原病》解釋為“營衛運行之機,乃為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為熱”,表明了瘟疫發熱是由熱郁導致;《傷寒瘟疫條辨》亦稱“如溫病發熱,雜氣怫郁三焦,由血分發出氣分”,說明瘟疫發熱屬“里熱怫郁,浮越于外”的本質。僵蠶,味咸辛,性平,被溫病學派認為適用于清解熱郁,如《傷寒瘟疫條辨》稱僵蠶治“一切風熱腫毒,觀此則僵蠶之升陽散火,祛風勝濕,清熱解毒可知”,這一觀點在楊栗山所倡“升降散”方中得以進一步體現,楊氏善用升降散治療瘟疫發熱,如清·呂田所輯《寒瘟條辨摘要》中載有“在瘟病,乃里證郁結浮越于外也,宜升降(散)、雙解(散)”,即采楊氏之說。后世亦常用僵蠶治療郁熱內生,如趙紹琴教授治療爛喉丹痧誤經發汗所致火郁內閉證,用升降散去大黃以宣郁解熱[3]。
1.2 祛風透表 僵蠶之所以有祛風之效,清·徐大椿《神農本草經百種錄》解釋為“蠶,食桑之蟲也。桑能治風養血,故其性亦相近。僵蠶感風而僵,凡風氣之疾,皆能治之,蓋借其氣以相感也”,清·周巖《本草思辨錄》亦稱“蠶者食桑之蟲,桑能去風,蠶性故近之;且感風而僵,更于感風之病為宜”[4],即是說,僵蠶祛風因桑葉祛風、蠶食桑葉而成,且蠶感風氣而成僵蠶,故長于治療風疾。金·張元素《醫學啟源》稱僵蠶“氣味俱薄,體輕而浮升陽也,去皮膚間諸風”[5],以其作“祛風”之用;清·林慶銓《時疫辨》中載“僵蠶退熱,能散疫毒風淫”[6],謂僵蠶能治療瘟疫夾風所見表證。后世引申此義,應用僵蠶辨治“風溫”證屬風邪引動里熱所見之表證,近代蒲輔周在治療重癥小兒肺炎(風溫)時運用僵蠶以祛透在表之風邪,如《蒲輔周醫案》“風熱久羈,表氣郁閉,故法取清宣透表,用紫蘇葉、僵蠶、牛蒡子辛以散風,銀花、連翹、黃芩苦以清熱”[7]。
僵蠶“祛風”也適用于瘟疫“里熱結滯”的病機,“透表”以應用于瘟疫表證的治療。此處應說明,瘟疫的表證由于里邪的存在而區別于傷寒表證,吳又可在《溫疫論·內壅不汗》中解釋為瘟疫表證并非表邪,而是里邪郁阻內在氣機,陽氣不能敷布于外,表氣不充而見表證,因而禁用單純的辛溫發汗法;對此楊栗山《傷寒瘟疫條辨·表證》進一步闡述“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外,今里熱結滯,陽氣不能敷布于外……惟用升降、雙解,里熱一清,表氣自透,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者”。楊氏在《溫疫論》論述的基礎上,明確了在治療瘟疫表證時,針對“里熱結滯”的病機,升降散、雙解散等含有僵蠶的方劑具有“清里以透表”的作用,用以治療瘟疫發生過程中里熱郁閉、陽氣不布所見的發熱、畏寒等在表癥狀。
1.3 化痰除濕 僵蠶之所以化痰濕,西漢·劉安《淮南子·地形訓》有“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8],清·黃宮繡《本草求真》在解釋“蠶砂”時稱“緣蠶食多而不飲,其食出則氣燥,燥則可以勝濕祛風”[9],謂蠶不飲水而辛燥,因辛燥而治療濕濁,又清·盧之頤《本草乘雅本偈》中謂“蠶,昆蟲也。三眠三起,起如衛氣之出行陽道,眠如衛氣之入行陰道,三十日大眠,則衛道已周,周則變而化,吐絲為經矣”[10],以蠶能吐絲而稱僵蠶走經隧,明·倪朱謨《本草匯言》亦有“蟬飲不食,蠶食不飲,飲滋經氣,食益經隧,咸從任、督四布經絡”[11]。可見古人基于蠶的生活習性,進而認識其藥效“辛燥祛濕、清理經絡”,以之應用臨床而發揮“消痰濁、清伏邪”的作用。
痰濁作為病理產物,時常伴隨著溫疫的發生,如清·戴天章《瘟疫明辨》中有“飲入于胃,經蒸變而稠濁者為痰……時疫屬熱癥,故夾痰者更生其熱”,又有“(疫邪)夾風邪干肺者,脈兼浮,咳多痰沫……有夾水干肺者,不論表里,脈必兼緩,咳必多清痰”,表明痰濁在瘟疫發病中的影響作用。《寒瘟條辨摘要》亦稱瘟疫治法“以滌穢為第一”;據《傷寒瘟疫條辨》所載,僵蠶能“上治咽喉,取其清化之氣;從治相火,散濁逆結滯之痰”,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痰”區別于一般所講的“僵蠶消痰散結,治療瘰疬痰核”,而是溫熱病中的“痰濁”。如楊栗山在論述升降散主治病癥時,有“如咽喉腫痛,痰涎壅盛,滴水不能下咽者”,用其治療溫毒上攻,痰涎壅盛之證;明·倪朱謨《本草匯言》中集有“<勝金方>:治一切風痰喘嗽。用白僵蠶7個(直白者),姜汁調服”,用單味僵蠶治療風痰喘咳;清·劉奎《松峰說疫·瘟疫應用藥》中亦選用“僵蠶”作為“化痰”用藥[12];當代中醫名家朱良春教授稱僵蠶“其功能散風降火,化痰軟堅,解毒療瘡,故于風熱痰火為患之喉痹喉腫、風疹瘙癢、結核瘰疬等癥均適用之”[13];當代薛伯壽[14]、王鍵[15]等醫家亦使用僵蠶治療內傷病屬痰濕穢濁證者。
1.4 清透伏邪 伏邪作為瘟疫發病的內在病因,在溫疫治療中也被溫病諸家所重視,是瘟疫區別于一般外感“傷寒”的重要原因,如《溫疫論·行邪伏邪之別》中有“先伏而后行者,所謂瘟疫之邪,如鳥棲巢,如獸藏穴,營衛所不關,藥石所不及。至其發也,邪毒漸張,內侵于腑,外淫于經,營衛受傷,諸證漸顯,然后可得而治之”,對此,吳又可強調需在伏邪已發后,即里證凸顯時加以治療;在治療過程中,伏邪的消長與患者癥狀直接相關,如《溫疫論·原病》“伏邪未退,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漸通,熱亦暫減,逾時復熱”,即是說,由于伏邪的存在,患者雖然見到汗出而貌似表證已退,實則伏邪未去、里證未消,便會反復見到發熱。在伏邪治療上,吳又可創制名方“三甲散”,方中除養陰清熱除蒸藥以外,運用了“僵蠶、蟬蛻、山甲”等透邪出表的藥物。《溫疫論·主客交》談及三甲散的主治病癥時講道“所謂客邪膠固于血脈,主客交渾,最難得解,且愈久益固,治法當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敗,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明言其病證的復雜難愈與伏邪的膠著。后世楊栗山據吳氏之說立法“方其侵淫之際,邪毒尚在膜原,此時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創立治疫十五方皆以“僵蠶、蟬蛻”清解為用。
1.5 現代藥理研究 現代研究表明,僵蠶含有蛋白質、氨基酸、草酸銨、白僵菌素及多種微量元素、酶類、多糖等成分,具有抑菌、抗凝、抗血栓、抗驚厥、促纖溶、抗癌等藥理作用,可用于治療或預防癲癇、抽搐、咳嗽哮喘、外感發熱、過敏性鼻炎、神經性疼痛、頭痛、偏頭痛、牛皮癬等多種皮膚病、各種炎癥、高脂血癥、腦血栓形成、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舌下囊腫、息肉、痔瘡腫痛出血、多發性頑固性疔腫、肝炎、成人非胰島素依賴性糖尿病、腫瘤及失眠等[16]。基于僵蠶抑菌、抗驚厥、抗驚厥、抗血栓、改善微循環等作用,其可廣泛適用于心肺、血管、肝、腎系疾病,這也是臨床應用僵蠶治療多種感染性發熱的藥理學依據[17]。
2 實用方劑
在瘟疫治療中,有許多名家運用僵蠶的方劑,如金·李東垣《東垣試效方》治療“大頭天行”創制“普濟消毒飲”,用僵蠶“散腫消毒定喘”;朝鮮·許浚《東醫寶鑒》中有“僵黃丸”等[18],主治大頭病及喉閉;明·吳又可《溫疫論》創制“三甲散”,治瘟疫疫毒內陷;清·楊栗山《傷寒溫疫條辨》所創治疫十五方均以僵蠶、蟬蛻為君藥,著名的如“升降散”“增損雙解散”“加味涼膈散”等。其中的“升降散”被楊氏譽為“用治瘟病,百發百中,屢試屢驗,萬無一失”,至今仍被臨床應用于辨證為“邪毒郁閉,氣機升降失調”的諸多病癥。
3 驗案舉隅
3.1 風毒喉痧案 病者:傅君,年廿余歲,住上海塘山路。病名:風毒喉痧。原因:傳染而得,已有8天。前醫之方,皆是養陰清肺湯等類。證候:壯熱無汗,微有畏寒,痧麻隱約,布而不顯,面色紫暗,咽喉腫腐,滴水難咽,煩躁泛惡,日夜不安。診斷:脈郁數不揚,舌苔黃膩。余曰:此喉痧誤認白喉也。傅氏數房,僅此一子,老母少妻,哭泣求救。余對之曰:癥雖兇險,正氣未敗,尚可挽回。療法:隨投透痧解毒湯,加枳實、竹茹疏達開豁,兼刺少商出血,開閉泄火。處方:荊芥穗(錢半)凈蟬衣(八分)粉葛根(二錢)青連翹(二錢)紫背浮萍(三錢)炒牛蒡(二錢)炙僵蠶(三錢)淡香豉(三錢)嫩射干(一錢)輕馬勃(八分,包煎)小枳實(錢半)鮮竹茹(二錢)生甘草(五分)前胡(錢半)效果:一日夜服兩劑后即得暢汗,麻痧漸布,面色轉紅,咽喉腫腐亦減。連進數劑,三四日即愈。喉痧之證,有汗則生,驗之信然[19]。
按:本案系丁甘仁治療喉痧案,患者年二十余,因傳染而發病8天,癥見咽喉腫腐、壯熱無汗、微畏寒、痧麻隱約,辨證當屬風熱溫毒襲肺,肺熱郁閉,故見壯熱無汗、微畏寒,熱盛動血、散于肌表見痧疹隱隱,邪熱上攻咽喉見咽喉腐爛、滴水難咽;前醫誤認此為白喉,用甘寒養陰之養陰清肺湯反壓抑肺火、滋膩風熱,致熱透不暢、毒邪留戀,而見面色紫暗、脈郁數不揚、舌苔黃膩,痧疹不能透發而內陷,而見煩躁、泛惡、日夜不安。丁甘仁據此以透痧解毒湯加枳實、竹茹,用“荊芥穗、葛根、淡豆豉、牛蒡子、浮萍”引出在表之熱邪,透發痧疹,并刺少商出血,開郁閉、泄肺火,用“連翹、僵蠶、蟬蛻、枳實”疏散在里之郁熱,掃蕩毒邪,“僵蠶、前胡、竹茹、射干、馬勃、生甘草、牛蒡子”消咽喉局部之痰熱,利咽解毒。患者一日夜連服兩劑,汗出而表熱清退,疹暢而痧毒消散,面色轉紅系在里郁閉之熱毒得以宣透,咽喉腫腐減退系局部痰熱消散,原方又進數劑,4天而痊愈。此處僵蠶用量三錢為主藥,宣郁透邪而達表,對于本案屬誤用甘斂、閉熱于肺之證,效果卓然。
3.2 瘟毒郁遏,表里升降失調案 初診:患某,男性,14歲,2013年1月29日初診。癥見感染致鼻炎反復發作,鼻塞,張口呼吸,黃涕,咽痛,無咳嗽,口苦,肌肉關節無不適,平素怕冷,納少,二便正常。舌質紅,苔花剝,脈細滑。中醫診斷:溫毒,證屬瘟毒郁遏,表里升降失調。西醫診斷:EB病毒感染致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癥。治以疏風散邪,清熱解毒,升清降濁。處方:金銀花12 g,玄參8 g,荊芥穗6 g,牛蒡子8 g,白蒺藜8 g,蒼耳子 8 g,細辛 2 g,白芷 8 g,連翹 12 g,薄荷 10 g(后下),浙貝母8 g,蟬蛻5 g,僵蠶8 g,姜黃6 g,石斛10 g,生甘草8 g,玉竹10 g,炙麻黃5 g,防風6 g。14劑。3劑后熱退,后加減用藥病情平穩。隨訪藥后未再發熱,精神增加,飲食增加,惡心消失,鼻干緩解,二便正常,舌質淡紅苔薄白,脈沉細[20]。
按:本案系國醫大師薛伯壽治療傳染病驗案,患者始因發熱伴淋巴結腫大就診,西醫診斷為基因缺陷致EB病毒感染,行淋巴結剔除術;3年后上癥復發。患者反復出現發熱伴淋巴結腫大,鼻炎反復難愈,中醫辨證當屬“伏邪”范疇,系溫熱毒邪深伏于里,氣血為之壅遏,而見表陽不布之怕冷、鼻塞,里熱壅盛之發熱;熱邪不能外透,郁而后發,上侵清竅,同時伴有外邪“EB病毒”之引動,故癥見黃涕、咽痛、口苦、淋巴結腫大。薛氏診斷此為“溫毒之瘟毒郁遏,表里升降失調”,緊抓“伏邪壅遏氣血”之病機;方以“銀花、連翹、玄參、牛蒡子、荊芥穗、防風”為主,清熱解毒以去內在之邪熱,兼托里透表以引氣血達表;合升降散之“僵蠶、蟬蛻、姜黃”,升清降濁以行壅遏之氣血,清透伏邪以去里證之夙根。患者服3劑而熱退,服至30劑頸部、頜下、耳根腫大淋巴結均消退,繼服至70劑,諸恙悉愈,而收全功。此處僵蠶解郁熱以引熱出表,清伏邪兼可散結。
4 結 語
究其根本,僵蠶治疫,主要由于其適用于瘟疫中“疫癘怫郁于里,里熱外發,充斥表里”這一證型的病機特點。古人對其藥效的認識基于其來源于家蠶,以桑葉為主要食物,被白僵菌感染后蠶尸不腐等特點,因此在治療中具有“解郁熱,散表風,消痰濁,清伏邪”的作用,分別針對瘟疫發生過程中出現的發熱、表證、痰濁等癥狀與伏邪病因,在瘟疫的中醫藥治療中得以被廣泛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