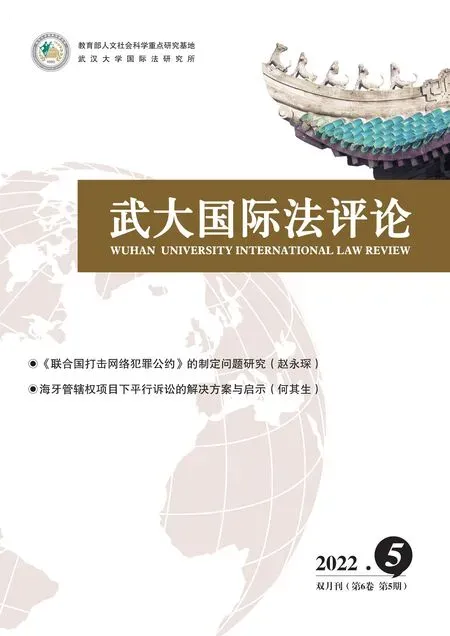中外雙邊投資協定中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分析
談譚 裴雷
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機制是雙邊投資條約(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的核心內容,其基本功能是在解釋和適用條約的基礎上確定國家責任,屬于國際公法性質的一種救濟方式,在保護投資者利益和維護東道國監管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目前生效的BIT有106個,①See 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China,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countries/42/china,visited on 3 May 2022.但現有中外BIT 中ISDS 機制存在一些問題,有的ISDS 機制內容較陳舊、條款原則化、缺乏制度化調解程序及上訴機制等。國際社會也對ISDS 機制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各種改革建議:歐盟提出建立常設投資法庭,實行初審法庭和上訴法庭兩級審裁制度;美國則主張在保留ISDS機制基礎上建立上訴機制;①參見王鵬:《中立、責任與參與:國際投資仲裁的多邊改革與中國對策》,《國際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8-119頁。以巴西為代表的少數國家反對投資者—東道國仲裁制度,主張提高替代性爭端解決程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中磋商、調解、調停在ISDS 機制中的作用,同時規定了爭端預防機制。②2020 年1 月,巴西與印度簽署的《投資合作和便利化協定》中詳細規定了投資爭端預防制度,并且將其與國家—國家間仲裁制度進行銜接。在中外BIT 中ISDS 機制需要升級完善和國際社會對ISDS 機制進行改革的背景下,本文從分析中外BIT 中ISDS 機制存在的問題出發,參考國內外ISDS 機制改革實踐,立足于中國當前資本輸入國和資本輸出國的雙重身份,提出完善中外BIT 中ISDS 機制的具體建議,包括確立爭端預防、制度化調解、上訴法庭這三項機制,旨在為國內打造良好營商環境和維護中國海外投資利益提供法律保障。
一、中外BIT中ISDS機制的爭端解決方式
1982 年,中國與瑞典締結了第一個中外BIT,其條款數量少且內容較原則,沒有導入ISDS 機制,僅針對“締約雙方在解釋或執行本協定中所發生的爭端”規定了解決機制——雙方政府談判后可根據締約任何一方的要求將爭端提交仲裁庭。③參見《中國—瑞典BIT》第6條。《中國—瑞典BIT》重視維護東道國主權、把國家利益放在優先位置。④2004年9月,中國和瑞典簽訂了《關于修改1982年中國—瑞典BIT的議定書》,該議定書規定:締約一方投資者在向投資東道國提出爭端書面通知3 個月后,雙方仍未能友好解決爭端的,投資者可以將有關投資的任何爭端提交國際仲裁解決。參見《關于修改1982年中國—瑞典BIT的議定書》,http://images.mofcom.gov.cn/tfs/202109/20210915103040598.pdf,2021年12月10日訪問。1990 年,中國正式簽署《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以下稱《ICSID 公約》)。此后,絕大部分中外BIT 中的ISDS 機制條款都提到“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仲裁和參照“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仲裁規則仲裁,并且采用單獨條款設置ISDS 機制,其中包括通過國際仲裁來解決投資爭端,但可提交國際仲裁的事項僅限于征收、國有化或類似措施的征收補償款爭端或雙方同意的其他投資爭端。1998 年,中國與巴巴多斯簽訂的BIT 規定:若經過雙方6 個月的友好協商仍未能解決爭端的,締約一方的投資者可以將其與締約另一方的任何投資爭端提交國際仲裁。《中國—巴巴多斯BIT》中ISDS 機制仲裁事項范圍超過了此前僅限于征收、國有化或類似措施的補償款爭端。⑤《中國—巴巴多斯BIT》第9 條規定:締約一方的投資者與締約另一方之間任何投資爭議,投資者有權選擇通過國際仲裁的方式解決。這種ISDS 機制的自由化轉向顯然與中國提出“走出去”戰略有關,即政府鼓勵和支持企業開展海外并購、有序向境外轉移產能、深化境外資源互利合作。
2012 年,以中國與加拿大簽訂涉及內容更廣泛的BIT 為標志,中國開始推進投資自由化并開始推廣“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方式,“強調東道國對公共利益保障的外資監管權”和“提升投資者—東道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正當性”。①王光、盧進勇:《中國雙邊投資協定:歷史演進與發展趨勢》,《國際經濟合作》2019年第2期,第53頁。中國嘗試改進中外BIT 的ISDS 機制,以求能夠平衡保護投資者利益和維護東道國監管權。②參見漆彤、聶晶晶:《論中國雙邊投資模式的變遷》,《武大國際法評論》2013 年第1 期,第228頁。2012 年《中國—加拿大BIT》中的ISDS 機制與此前相比更為詳細:明確將最惠國待遇條款排除出爭端解決機制,對國際仲裁的范圍、程序和提起仲裁的時效進行了具體規定。③參見《中國—加拿大BIT》第20條第1款、第21條、第三部分第21條附錄。2012 年《中國—日本—韓國BIT》和2015 年《中國—土耳其BIT》中的規定與2012 年《中國—加拿大BIT》規定類似。可見,最新的中外BIT 中ISDS 機制都在向平衡模式方向發展,其主要標志是:明確可訴請國際仲裁的爭端范圍;用盡東道國國內行政復議程序;規定明確的提請仲裁時效。這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11—2021 全球投資報告所指出的“從2013 年起中國資本輸入與輸出處于相對平衡狀態”的發展進程一致。
中國已經由資本輸入國向兼具資本輸入國與資本輸出國的雙重身份轉變,這種身份轉變成為中國完善和升級中外BIT 中ISDS 機制的內在動因。在討論完善或升級的具體措施之前,我們需要分析現有中外BIT中ISDS機制及其存在的問題。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統計,截至2022年5月,共有106個生效的中外BIT協定和4個附加議定書④這4 個附加議定書分別是:2004 年《中國—瑞典BIT 附加議定書》、2005 年《中國—斯洛伐克關于中國—捷克斯洛伐克BIT 附加議定書》、2007 年《中國—保加利亞BIT 附加議定書》、2007 年《中國—羅馬尼亞BIT附加議定書》。。目前生效的106個中外BIT普遍采取友好協商、東道國國內救濟和國際仲裁三種方式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間的投資爭端。
(一)友好協商
友好協商在中外BIT 中有磋商、談判、申訴等不同表述,它是指爭端雙方在提請國際仲裁前采取的一種爭端解決方式,同時也是提請仲裁的前置程序之一。通過梳理可以發現,大部分中外BIT 包含友好協商條款,友好協商的期限一般在3~12 個月(見表1)。這樣設置協商期限,主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時間過短不利于雙方充分交流和溝通,起不到解決爭端的目的;二是時間太長會增加爭端解決的時間和其他成本。同時,友好協商也是大多數中外BIT 中ISDS 機制規定的投資者提請仲裁的前置程序之一。

表1 中外BIT中“友好協商”條款規定一覽表
(二)東道國國內救濟
東道國國內救濟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向東道國國內有管轄權的法院提起訴訟;二是向東道國國內行政機構申請行政復議。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投資爭端,由于爭端一方為主權國家,將爭端提交國際仲裁涉及國家主權問題,而東道國國內救濟程序是東道國保護投資或對投資損失進行救濟的重要法律途徑,也是維護國家主權的體現。因此,中外BIT 中的ISDS 機制廣泛采用東道國國內救濟方式。
有關向東道國國內有管轄權的法院提起訴訟方面,除了19個中外BIT做出規定之外,①19 份中外BIT 具體包括與如下國家簽訂的BIT:保加利亞(1989)、瑞士(1986)、英國(1986)、奧地利(1985)、瑞典(1982)、加納(1989)、匈牙利(1991)、烏克蘭(1992)、白俄羅斯(1993)、烏茲別克斯坦(1992)、吉爾吉斯斯坦(1992)、亞美尼亞(1992)、菲律賓(1992)、土庫曼斯坦(1992)、哈薩克斯坦(1992)、塔吉克斯坦(1993)、以色列(1995)、德國(2003)、古巴(2007)。絕大部分中外BIT 都包含了這一規定,例如,《中國—馬其頓BIT》第9 條規定:“爭端任何一方(締約一方的投資者與締約另一方)有權將爭端提交東道國有管轄權的法院……”在法院管轄范圍上,不同BIT 雖在表述上略有差異,但規則內涵仍然是一致的,即允許投資者將在締約另一方領土內的投資所產生的任何爭端提交給締約另一方有管轄權的法院②參見《中國—馬其頓BIT》第9條。,或者“締約一方的投資者與締約另一方之間就在締約另一方領土內的投資所產生的任何爭端”,如未能協商解決,爭端任何一方有權將爭端提交接受投資的締約一方有管轄權的法院。①參見《中國—蘇丹BIT》第9條第1款、第2款。
有關申請東道國國內行政復議,總共30 個中外BIT 中的ISDS 機制條款包含相關規定。這些條款一般以兩種方式表述:一種是要求投資者將投資爭端提交國際仲裁前,用盡該締約方法律和法規所規定的國內行政復議程序,例如,《中國—緬甸BIT》第9 條第3 款第2 項規定:“(提交仲裁程序之前)作為爭端一方當事人的締約方可以要求有關投資者用盡該締約方的法律和法規所規定的國內行政復議程序”。另一種是規定投資者將投資爭端提交國際仲裁前,必須用盡東道國國內行政復議程序,例如,《中國—古巴BIT》第10 條第4 款第1 項規定:投資者只有用盡根據法律和法規規定的行政復議程序,才能提交仲裁請求。盡管《中國—緬甸BIT》的相關表述是“可以”,看似僅將行政復議作為可選項,但是出于維護主權的考慮,實踐中東道國往往會要求投資者先用盡東道國國內行政復議程序。
(三)國際仲裁
目前生效的106 個中外BIT,除1982 年《中國—瑞典BIT》外,其余105 個中外BIT 都規定了國際仲裁。首先,中外BIT 的ISDS 機制規定,提請仲裁的必要條件是雙方同意將爭端提交國際仲裁。除了雙方同意這個共有的前提條件外,可以將中外BIT 中提請仲裁的前提條件分為五種規定模式:第一種是除了雙方同意外,未規定任何其他條件。例如,1992 年《中國—烏茲別克斯坦BIT》第9 條規定爭端雙方可將任何有關征收補償款的爭端提交仲裁。第二種是協商、磋商、談判或向有關當局申訴未果的情況,比如,雙方訴諸本條友好協商的程序后6 個月內仍未解決爭端,可將爭端提交國際仲裁庭②參見《中國—新西蘭BIT》第13條第3款。。第三種是BIT 中規定協商未果或投資者用盡東道國行政復議程序之后提交仲裁,例如,2013 年《中國—坦桑尼亞BIT》第13 條第2 款規定,爭端未能通過協商解決的,締約另一方可以要求該投資者在提交國際仲裁之前,用盡締約另一方法律和法規所規定的國內行政復議程序。第四種是彼此協商未果且投資者用盡東道國國內行政復議程序的,在BIT 規定的提請仲裁時限內,可提請仲裁。第五種是2012 年《中國—加拿大BIT》模式,即專門單列一個條款(第21條、第21 條附錄)規定爭端投資者提請仲裁的前提條件,包括爭端各方首先進行磋商;引起訴請發生的事件至少已經過6 個月且投資者至少在4 個月前已書面通知東道國其提請仲裁的意向;未超過提請仲裁的3 年時效;投資者應當被要求用盡東道國國內行政復議程序。
其次,關于中外BIT中ISDS機制下可提交國際仲裁的事項范圍,按照ISDS機制的演進特征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ISDS 機制保守模式下,普遍規定可提交仲裁的爭端限于因征收、國有化或類似措施產生的補償款爭端;第二個階段是在ISDS 機制自由模式下可仲裁事項范圍擴大,任何投資爭端都可提交國際仲裁;第三個階段是在ISDS 機制平衡模式下,為平衡投資者利益與東道國監管權,通過ISDS機制條款細化國際仲裁事項范圍,例如,前述2013 年《中國—坦桑尼亞BIT》第13 條規定:締約一方投資者與締約另一方之間有關投資的任何法律爭端,應盡可能通過磋商友好解決,“違反本協定第2 條(促進和保護投資)至第9 條(代位),或者第14 條第2 款(信守以協議或合同形式作出的書面承諾)項下的義務而產生的爭端”,在滿足提請仲裁的條件后可提交仲裁。
再次,仲裁庭選擇分為依據《ICSID 公約》(締約雙方均是《ICSID 公約》締約國)進行仲裁或根據《ICSID 附加便利規則》(締約方僅有一方為《ICSID 公約》締約國)進行仲裁,或依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組建的專設仲裁庭,或爭端雙方同意的任何其他仲裁機構或專設仲裁庭,“根據作為爭端方的締約方包括其沖突規范在內的法律、本協定的規定和被普遍接受的國際法原則”,或雙方共同認定的仲裁規則做出裁決。1993 年中國正式批準《ICSID 公約》之前,大多數中外BIT 規定爭端雙方設立專設仲裁庭解決投資爭端。1993 年批準《ICSID 公約》后,有的中外BIT 規定只能將爭端提交專設仲裁庭;①《中國—埃及BIT》第9條第3款規定,可應任何一方的要求,將爭端提交專設仲裁庭。有的規定只能將爭端提交ICSID 仲裁庭;②《中國—加蓬BIT》第10條第2款規定,根據投資者的選擇,可將爭端提交ICSID仲裁。有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專設仲裁庭或ICSID 仲裁庭,這反映出作為爭端一方的投資者對于仲裁庭有選擇的權利。③《中國—芬蘭BIT》第9 條第2 款規定,仲裁可提交ICSID 仲裁,或提交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設立的專設仲裁庭仲裁。
此外,關于提請仲裁的時效,目前生效的106 個中外BIT 中,只有8 個晚近簽訂的BIT 規定了提請仲裁的時效,絕大多數中外BIT 沒有對此做出規定(見表2)。這可被視為中國正尋求建立一種平衡模式的ISDS 機制來調整投資者與東道國權益。

表2 中外BIT規定提請仲裁的時效一覽表
截至2022年8月,中國作為被申請人的國際投資仲裁案件共8起,都是依據中外BIT 中ISDS 機制條款提起的。這8 起案件中,除2 起已被提交常設仲裁庭(PCA)且具體信息未公開、1 起正在審理、1 起(Eugenio Montenero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正處于仲裁庭組建階段以外,已結案或終止仲裁程序的案件中,尚無中國在案件管轄權或實體問題裁決上敗訴的案件。從中國1993 年批準《ICSID 公約》到2021 年的28 年中,以中國為被申請人的案件共8 起,但近2 年這類案件就有4 起,這說明中國被投資者提起仲裁的幾率在增加。另一方面,中國投資者作為申請人提起了共14 起投資仲裁案件,其中10 起是依據中國簽訂的BIT 提起,近年來也呈現出明顯上升趨勢,而且大型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提起的案件占比高。14 起案件中,8 起已結案,其中4 起有利于東道國、3 起有利于投資者、1 起雙方和解,①參見池漫郊、任清:《中國國際投資仲裁年度觀察(2021)》,https://bjac.org.cn/news/view?id=4081&msclkid=407a4ab0cecb11eca5924447d8b5b4ae,2022年5月2日訪問。因此,中國應綜合平衡“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關系,特別是平衡保護投資者權益與維護東道國監管權的關系,同時借鑒國外ISDS 機制改革經驗,推動中外BIT 中ISDS 機制向平衡模式方向發展。
二、中外BIT中ISDS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外BIT 中ISDS 機制主要存在內容陳舊、條款模糊、缺乏調解程序、缺乏上訴機制等問題。
(一)大部分中外BIT中ISDS機制條款未經更新
目前生效的106 個中外BIT 中,大部分簽署時間較早,條款內容未經更新、顯得相對陳舊。僅17 個中外BIT 以重簽或議定書的方式進行了更新,其中14 個增加或更新了ISDS機制(見表3)。

表3 中外BIT中ISDS機制條款更新情況

續表
①“岔路口條款”是指國際投資協定通常規定,投資者可以在東道國法院訴訟和國際投資仲裁中選擇一種來解決投資爭端,且這種選擇具有終局性。也有一些投資協定規定,如果投資者已在東道國國內法院起訴,則需要撤回起訴后才可訴諸國際仲裁。2004 年《中國—瑞典BIT 附加議定書》增加了此前缺失的ISDS 機制,即在1982年《中國—瑞典BIT》第6 條基礎上增加了“新第6 條”——ISDS 機制條款。除此之外,其他三個議定書沒有對ISDS 機制進行更新,主要是因為2007 年1 月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加入歐盟以及2004 年5 月斯洛伐克加入歐盟,三個議定書所更新的主要條款是三國成為歐盟成員國后,“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條款不應適用于締約一方因作為關稅、經濟或者貨幣聯盟、統一市場或者自由貿易區的成員承擔義務而享受的優惠”。重簽的中外BIT 都更新了ISDS 機制條款,但除《中國—古巴BIT》與《中國—土耳其BIT》外,更新內容偏向ISDS 機制自由模式,未能體現中外BIT 趨向平衡模式的變化。
(二)部分中外BIT中ISDS機制條款模糊
ISDS 機制條款如果過于原則化,就會擴大仲裁庭的解釋空間,便利仲裁庭擴張仲裁管轄權,進而增加東道國被投資者申請仲裁的概率。關于最惠國條款是否適用于爭端解決(進而適用于ISDS 機制下仲裁程序)的分歧就是ISDS 機制條款模糊造成的。中外BIT 很少用明確的條款將最惠國待遇排除出爭端解決程序,僅4 個中外BIT 有明確排除規定,①4 個中外BIT 分別是2009 年《中國—烏茲別克斯坦BIT》、2011 年《中國—哥倫比亞BIT》、2012年《中國—加拿大BIT》、2013年《中國—坦桑尼亞BIT》。如2013 年《中國—坦桑尼亞BIT》第4 條第3 款規定:“本條(最惠國待遇)第一款(締約一方因建立自由貿易區等安排而產生的待遇、優惠或特權)不適用于本協定或其他締約一方簽署的類似國際協定中規定的爭端解決條款。”
透明度也是國際仲裁改革的熱點,但大量的中外BIT 沒有涉及仲裁透明度的規定,我們只檢索到2012年《中國—加拿大BIT》第27條規定了非爭端締約方獲取相關文件副本和陳述意見的權利;第28 條規定了仲裁裁定和仲裁庭庭審向公眾開放的相關條款;第29 條規定了在滿足相關條件后;仲裁庭可以接受非爭端方提交的書面陳述,這些都是對仲裁透明度做出的規定。
(三)大多數中外BIT缺乏制度化調解程序
調解制度是《ICSID 公約》下ISDS 機制一項重要的爭端解決方式,調解具有便捷、節約成本、維護爭端雙方友好關系等優點。《ICSID 公約》第3 章“調解”包括調解啟動、調解委員會組成、調解程序、調解規則、委員會制定調解報告。2020 年9 月生效的《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以下稱《新加坡調解公約》)為跨國執行國際調解協議提供了便利,使得“調解制度成為訴訟、商事仲裁之外具有獨立救濟功能的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方式”。②孔南翔:《〈新加坡調解公約〉在中國的批準與實施》,《法學研究》2021 年第2 期,第156 頁。《新加坡調解公約》2020年9月12日生效,中國2019年8月7日簽署該公約,但尚未批準。然而,目前僅11個中外BIT的ISDS 機制提到調解,③11 份中外BIT 分別是《中國—日本BIT》、《中國—捷克斯洛伐克BIT》《中國—希臘BIT》《中國—韓國BIT》《中國—以色列BIT》《中國—巴布新幾內亞BIT》《中國—荷蘭BIT》《中國—烏茲別克斯坦BIT》《中國—印度BIT》《中國—哥倫比亞BIT》《中國—坦桑尼亞BIT》。而且調解程序規定并不統一。這些規定大體可分為三類:其一,僅在ISDS 機制條款中提到爭端雙方可進行調解,沒有對調解程序做出具體規定,例如,2013年《中國—坦桑尼亞BIT》第13條規定:締約一方投資者與締約另一方之間有關締約另一方領土內的投資的任何爭端,應盡可能由爭端雙方當事人通過磋商友好解決,其中包括調解程序的應用。其二,參考《ICSID 公約》組成調解委員會或提交ICSID 進行調解,例如,1995 年《中國—以色列BIT》第8 條規定:征收補償款爭端可提交ICSID 調解或仲裁。其三,依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調解規則》進行調解或爭端雙方同意由ICSID 附設機構進行調解,2006 年《中國—印度BIT》采取此種模式。后面兩類雖然規定了參考或依照的國際公約或調解規則,但相較于國際仲裁,調解仍是輔助性的爭端解決方式,ISDS 機制中缺乏制度化調解程序,不利于在實踐中發揮調解制度的作用。
(四)中外BIT中缺乏ISDS上訴機制
ISDS 上訴機制有利于解決仲裁裁決不一致甚至裁決錯誤的問題,有利于提高國家間和區域間投資行為的可預見性。①參見丁曉雨:《ISDS上訴機制的構建問題研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頁。目前,歐盟在ISDS 機制改革中主張建立投資上訴法庭制度,即建立兩級審裁的多邊投資法院體系。2016 年10 月31 日歐盟與加拿大簽署的《歐盟—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2019 年6 月30 日歐盟與越南簽署的《歐盟—越南投資保護協定》和2020年4月28日簽署的《歐盟—墨西哥自由貿易協定》(EU-Mexico FTA)都包含上訴機制。②《歐盟—越南投資保護協定》第3.33條規定:如果締約一方投資者與締約另一方之間的爭端不能在提交協商請求后的6個月內解決,并且投資者向締約一方書面提交其爭端解決意向已至少超過3個月,投資者可將其訴求提交給依該協定第3.38 條成立的臨時投資法庭;投資者的訴求也可依《ICSID 公約》《ICSID附加便利規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或爭端方協議的其他規則提交給臨時投資法庭。該協定第3.39條規定:成立一個常設上訴法院(a permanent appeal tribunal)來審理對臨時投資法庭裁決的上訴,ICSID秘書長(負責管理爭端雙方付費的銀行賬戶)就是上訴法庭秘書長,并對上訴法院提供適當協助。2020 年7 月1 日正式生效的《美墨加協定》盡管沒有規定仲裁上訴機制,但是《美國2012 年BIT 范本》第28 條“仲裁行為”第10 款中提到上訴機制(an appellate mechanism),即締約雙方應考慮將來成立一個審查投資者—東道國仲裁庭裁決的上訴機制。③See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2870/download,visited on 10 May 2020.
目前生效的106 個中外BIT 都未規定正式的上訴機制,僅2003 年《中國—德國BIT》和2007 年《中國—古巴BIT》提及仲裁裁決的救濟方式。《中國—德國BIT》第9條第4 款規定,依據《ICSID 公約》做出的裁決,只受《ICSID 公約》規定的上訴或補救措施的影響。《中國—古巴BIT》第10 條第8 款規定,仲裁裁決的終局性約束力不影響雙方當事人向法院申請無效程序的權利。這些規定也可視為對仲裁裁決的救濟措施,但不是法律上的上訴程序。在ISDS 機制中引入上訴程序已基本成為共識,在此背景下,中國也可在升級和完善ISDS 機制時做同樣考慮,以進一步推動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三、完善中外BIT中ISDS機制的建議
中國兼具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的雙重身份,在中外BIT 中ISDS 機制的設置需要平衡保護投資者利益和維護東道國監管權。2020 年11 月,中國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并表示對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持積極開放態度。2020 年12 月,中國與歐盟原則上達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這些都表明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推動區域和雙邊貿易或投資協定談判的立場。CAI 中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最終文本仍需要進一步協商,不過,中國目前迫切需要解決中外BIT 中ISDS 機制存在的問題。借鑒歐盟等改革ISDS 機制的實踐,筆者建議在中外BIT 的ISDS 機制中導入爭端預防機制、規定制度化調解程序、增加上訴法庭機制。
(一)導入爭端預防機制
爭端預防機制的本質不是阻止爭端的產生,而是將潛在的分歧引導到問題解決上,避免爭端的沉積和升級。中國可借鑒巴西的投資合作與便利協定模式設立國家聯絡點(監察專員)制度安排,①巴西已與20 多個國家達成了投資合作與便利協定。See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Hub,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countries/27/brazil, visited on 3 November 2021.管理雙方投資爭端和避免爭端升級。它可以是具有強制性、嚴格按照程序操作的投訴渠道,也可以是靈活的、供投資者選擇使用的投訴渠道。國家聯絡點(監察專員)可以為投資者提供快捷、低成本和友好的爭端解決平臺。②See UNCTAD, Investor-State Disputes: Prevention and Alternatives to Arbitration, UNCTAD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o. E.10.II.D.11, New York, and Geneva, 2010,https://unctad.org/en/docs/diaeia200911_en.pdf,visited on 23 May 2022.東道國可通過該平臺及時獲得爭端信息或投資者訴求,進而分析爭端問題、評估爭端后果。目前,有部分中外BIT中已存在聯合委員會制度,如2012年《中國—日本—韓國BIT》(以下稱《中國—日韓BIT》)第24 條規定:締約各方設立聯合委員會,由締約各方政府代表組成,且可決定邀請政府之外具備必要專業知識的實體代表,聯合委員會任何決定都須一致合意做出,其職能是討論及審查投資協定的實施和運作,以及其他與協定相關的投資事項,聯合委員會在必要時可以向締約各方提出建議,以便推動協定的高效運作和目的實現。盡管2012 年《中國—日韓BIT》中的聯合委員會還不屬于ISDS 機制,缺乏處理投資者與東道國間爭端的職能,但它為中外BIT的ISDS機制增加爭端預防機制起到了示范作用。
具體來說,中外BIT 締約方政府應該成立專門機構作為該國國家聯絡點,接受和處理外商投資企業的相關投訴,向投訴方提供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信息,與有關部門協商及時處理投訴,并向雙方聯合委員會匯報。中國可根據2020 年1 月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以下稱《外商投資法》)第26 條規定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以下稱《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設立中央和地方兩個層級的國家聯絡點,中央層面的國家聯絡點由商務部主管,由設在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的全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中心承擔受理全國性重大投訴事項的職責;地方國家聯絡點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機構,比如,外商投資企業投訴中心,受理本行政區域的外商投訴事項,并將投訴處理結果及時反饋給中央層面的國家聯絡點。聯合委員會由締約雙方政府代表組成,除監督投資協議實施、擴大雙方相互投資機會、推動雙方合作議程外,還負責舉行正式會議進一步商討國家聯絡點沒有解決的投訴事項,制作關于爭端事項的報告,匯總投訴事項處理情況,為今后處理投資爭端提供參考。我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辦法》已于2020 年10 月1 日開始實施,為投資者申訴提供了制度安排。《外商投資法》中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辦法》使該投訴工作機制細化、透明化、便利化,起到了協調處理境外投資者與國內相關行政主體爭端的作用,在制度設計上具有爭端預防的功能。筆者建議將該機制設計為爭端預防機制,將其與中外BIT 現有的“磋商”或“協商”機制一道作為啟動ISDS 仲裁機制的前置條件。
此外,為提高工作效率、節約時間成本,雙方應在ISDS 機制條款中限定國家聯絡點處理投訴的期限,對聯合委員會會議時間和報告發布時間也須做出限制。同時,要求國家聯絡點在受理投資者投訴后,在規定的時間內向投資者提供與爭端事項有關的信息,并將處理情況反饋給投資者,投資者有權選擇提請聯合委員會舉行正式會議進一步討論或提交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如調解無果,再按程序提交國際仲裁。換言之,中外BIT的爭端預防機制不同于巴西《投資合作與便利化協定》(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on Investment Agreement, CFIA )的爭端預防機制,后者在國家聯絡點或聯合委員會未能解決爭端后,只能通過仲裁對爭端或事項進行審查,而中外BIT中投資者仍保留了可將爭端提交國際仲裁的權利。
有人批評巴西CFIA 范本中國家聯絡點和雙方聯合委員會這種爭端預防機制具有政治屬性,即通過規定投資者向這兩個機構尋求爭端解決,把國際投資保護倒退到傳統外交保護階段,并且國家聯絡點和聯合委員會的官方屬性,使其在處理爭端時可能會涉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博弈,進而影響爭端解決的效率和公正性,同時,這一方式也不符合國際社會多年來探尋的“去政治化”途徑保護外國投資者利益的努力。不過,也有意見認為,國家聯絡點和聯合委員會能夠使雙方在友好、互信的基礎上將爭端化解在最初階段,可預防風險并實現共贏。這種爭端預防機制具有靈活性,能夠促進爭端雙方溝通,提高信息在投資者與東道國間的流通,具有促進投資便利化、實現雙邊投資關系可持續發展的功用,“為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提供了一種預防爭端與國家仲裁相混合的創新模式”。①參見唐妍彥:《巴西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模式改革及對中國的啟示》,《拉丁美洲研究》2021 年第2期,第69-70、76-80頁。
(二)規定制度化調解程序
調解是當事各方自行約定爭端解決程序,并試圖通過第三方協助實現爭端友好解決的過程。②參見《新加坡調解公約》第2條第3款。調解具有靈活性、可量身定制、節約時間、節省國家司法行政成本等特點,一直是國際貿易或國際投資爭端的解決方式之一。國際實踐中,《歐盟—越南投資保護協定》和《歐盟—加拿大全面經濟與貿易協定》規定了制度化調解程序和措施。③《歐盟—越南投資保護協定》第三章第3.29 條“友好解決”規定:任何爭端在提交第3.30 條“磋商”前應盡可能通過談判和調解友好解決,且雙方在任何時候都可就此達成一致。第3.31 條“調解”規定:任何時候爭端方都可同意調解;調解是自愿的,不影響任何一方的法律地位;可按附件10 進行調解,其中的時間期限可由爭端雙方協議修改。第8.20條“調解”規定與上述規定基本一致。一些國際組織也積極推行和應用調解制度,比如,ICSID2018 年開始制定一套新的調解規則,作為ICSID 仲裁、調解和事實調查規則的補充。2020 年發布的ICSID 規則修正提案的第四份工作文件詳細規定了調解程序、調解適用規則、調解員行為準則、調解費用、保密規則等內容。2016 年,國際調解組織(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 IMI)發布的《國際調解組織調解員能力標準》(IMI Competency Criteria for Investor-State Mediators)對調解員的經驗和專業知識提出了全面具體的要求。④Se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 IMI Competency Criteria for Investor-State Mediators, https://imimediation.org/about/who-are-imi/ism-tf/,visited on 3 May 2021.2018 年修訂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調解示范法》第10 條確立了以保密為原則、以公開為例外的調解原則。⑤參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調解和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示范法》,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annex_ii_-_c.pdf,2020年11月20日訪問。2020 年9 月生效的《新加坡調解公約》主要是解決跨境執行調解產生的“和解協議”(settlement agreement)問題,其目標是賦予國際調解協議直接可執行性和約束力。《新加坡調解公約》有助于“建立公平、高效解決國際投資爭端的協調法律框架”,并為這一框架增添確定性和穩定性保證。⑥參見UNCITRAL:《〈新加坡調解公約〉介紹冊》,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zh/v1808433_chinese_revised.pdf,2019年10月7日訪問。
在中國國內實踐層面,中華文明“以和為貴”的思想既切合國際商事調解制度的內核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調解制度,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訴調對接、調解與仲裁相結合等制度在社會各領域糾紛解決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①參見明瑤華:《“一帶一路”投資爭端調解機制研究》,《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1期,第66頁。2018 年6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以下稱《意見》),提出支持“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糾紛通過調解、仲裁等方式解決,推動建立訴訟與調解、仲裁有效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國際商事法庭并牽頭組建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對當事人之間的跨境商事糾紛,根據當事人自愿原則先行調解,并制作調解書,由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經過司法確認獲得強制執行力,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務和保障。但是,目前中外BIT 雖提出用調解方式解決爭端,但沒有把調解制度化,未能發揮調解的實質性作用。對此,中國可借鑒國際社會調解制度實踐及其新經驗,在ISDS 機制中確立制度化調解程序,將東道國要求下的調解程序作為仲裁前置程序,即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投資爭端如果未能通過雙方友好協商解決,則在東道國提出要求時,須把爭端提交至該國主管當局或專門機構進行調解,還可參照CETA 模式在中外BIT 中以附件形式規定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爭端的調解制度、具體程序和規則。
其一,明確啟動調解程序和選任調解員的規則。任何爭端方可隨時以書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啟動調解程序,并對書面通知的內容作具體規定,另一方在收到調解請求后,應在規定的時間內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接受或拒絕調解請求。調解員由爭端當事方自主選任,爭端當事方可從締約雙方建立的專家庫中選任調解員,也可選任專家庫之外且爭端雙方都認可的人員擔任調解員。如果爭端雙方在規定的時間內沒有選出調解員,則提請聯合委員會從專家庫中選任。維護調解程序公正性的關鍵在于規范調解員行為,調解員的行為準則可單獨用一個附件進行規定。國際調解組織規定:如果調解不成功,調解員不得在其后就同一爭端進行的仲裁程序中擔任仲裁員,但當事人同意的除外。②Se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stitute,IMI Competency Criteria for Investor-State Mediators,https://imimediation.org/about/who-are-imi/ism-tf/,visited on 19 September 2019.如果調解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到中立、公正、勤勉義務,則由聯合委員會決定給予相應的懲罰。
其二,平衡調解的保密性與透明性。保密是調解的核心價值,從法理上講,因為調解的本質在于當事人的合意而非法官裁斷,從當事人的角度看,調解符合當事人的利益,當事人不希望自己的私事被公眾知曉。③參見李浩:《調解歸調解,審判歸審判: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中國法學》2013年第3期,第7頁。然而,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不同于商事爭端,前者往往涉及公共利益,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從東道國的角度看,政府行政行為的公開透明是建設法治政府和維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內容,民眾對于投資者與東道國涉及公共利益爭端的處理結果有知情權;投資股東對爭端的處理結果也有知情權。因此,考慮到平衡調解的保密性與透明性,中外BIT 設計調解規則時,可采取“一般+例外”模式,對于非必要公開事項一般維持保密性;對于必須公開事項要及時公開。當然,對于涉及調解工作的政府公職人員,應當要求他們在履職時公平、公正、公開。①See Catherine Kessedjian, et al., Mediation in Futur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Academic Forum on ISDS Concept Paper 2020/16,5 March 2020,p.13.同時,賦予非爭端第三方向調解委員會提交申請要求公開調解事項的權利,調解委員會收到申請要求公開的請求后,及時聯絡爭端雙方,確定是否公開調解事項。
其三,明確調解協議的執行。調解結果缺乏執行力是投資者與東道國不愿使用調解程序的重要原因。依據《新加坡調解公約》第3-5 條,締約方有義務建立執行調解協議的程序規則,明確本國可以調解解決的爭端事項范圍,以及表明主管機構可接受的證明調解存在的證據類型,即請求執行調解協議的一方應當向另一方主管機關出具各方當事人簽署的調解協議。②參見《新加坡調解公約》第3-5條。《新加坡調解公約》還確定了爭端執行層面的“岔路口”條款,即經由法院批準或在法院相關程序中訂立的協議,若可在該法院所在國作為判決或裁定執行,或協議已由仲裁機構記錄在案并可作為仲裁裁決執行,則不受《新加坡調解公約》調整。③參見《新加坡調解公約》第2條第3款。對此,中外BIT 可參照上述規定,確認并保障國際調解協議的可執行性。至于是否像《新加坡調解公約》那樣賦予調解協議以直接可執行性,當前國內主流觀點認為調解協議(包括國際調解協議)是被調解組織或機構認可的民事契約,須經過司法機關審查、確認后才有執行力。這種觀點與前文提及的2018 年《意見》中調解書須經有管轄權的法院司法確認才獲得強制執行力的規定一致。需要指出的是,ISDS 機制內的調解協議或仲裁裁決均不得違反東道國的公共利益,也不得侵犯調解協議或仲裁裁決案外人的合法權益,否則,該調解協議或仲裁裁決在東道國不具有可執行性。④參見孫南翔:《〈新加坡調解公約〉在中國的批準與實施》,《法學研究》2021 年第2 期,第169、172頁。
(三)增加上訴法庭機制
2018年《意見》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國際商事法庭,同時在深圳設立“第一國際商事法庭”,在西安設立“第二國際商事法庭”,受理當事人之間的跨境商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負責協調并指導兩個國際商事法庭工作。2019 年7月,中國政府向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第三工作組第三十八屆會議提交的《投資人與國家間爭端解決制度可能的改革的意見書》指出,“中國支持對常設上訴機制改革方案開展研究”,并且肯定“設立基于國際條約的常設上訴機制”對推動ISDS 機制法治化進程的重要作用。中國主張,既可嘗試在雙邊國際投資協定中對上訴機制做出規定,又可通過多邊規則規范上訴機制。①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https://undocs.org/en/A/CN.9/WG.III/WP.177,visited on 19 July 2021.中國考慮接納歐盟兩級審裁的投資機制上訴法庭機制,對中國—歐盟達成雙邊投資協定文本有重要意義。上訴法庭是ISDS 機制改革的關鍵,建立上訴法庭機制的目的是糾正錯誤裁決、維護裁決的一致性和公正性。
首先,明確上訴法庭組成及法庭審理范圍和期限。建議上訴法庭成員由雙方聯合委員會從締約雙方組建的專家庫中選任3 名,締約雙方各1 名,第三國1 名,都有固定任期限制。②CETA 第8.27 條規定:CETA 聯合委員會應任命15 位成員組成投資法庭,其中5 位是歐盟成員國國民、5 位加拿大國民、5 位第三方國民,5 年一個任期,可連任一次。聯合委員會可決定增加或減少法庭成員,增加或減少的數量應為3的倍數。上訴法庭成員行為準則可援引《國際律師協會關于國際仲裁中利益沖突的指南》,具體設定對上訴法庭成員獨立性、公正性、專業性、保密性等要求。③2021 年4 月19 日,ICSID 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聯合發布了《國際投資爭端解決裁判者行為守則草案(第2 版)》(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Version 2)。該行為守則將適用于國家—國家及ISDS 仲裁的仲裁員、特設委員會成員和常設機構法官等,主要涉及利益沖突時裁判者的披露義務、對裁判者同時擔任多種角色的限制、公開委任裁判者前的溝通等內容。See ICSID & UNCITRAL,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Adjudicator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Version Two,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draft_code_of_conduct_v2_en_final.pdf,visited on 19 April 2022.關于上訴法庭的審理范圍和期限,可借鑒CETA 第8.28 條,明確上訴法庭審理范圍既包括裁決解釋或適用法律錯誤、對事實理解的明顯錯誤,也涵蓋《ICSID 公約》第52 條規定的5 種撤銷裁決理由,即仲裁庭組成不當、仲裁庭明顯超越權限裁決、仲裁員貪污腐敗、仲裁庭嚴重違背仲裁程序規則、仲裁裁決未說明理由。爭端一方應在(涉及可提交上訴法庭的相關事項)裁決做出之日起的90 日內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應在爭端首次提交投資法庭的24 個月內做出最終裁決,如要延長審理期限,應通知爭端雙方延長的理由。上訴法庭裁決做出90 日后,如爭端雙方無上訴或上訴法庭未將該爭端事項發回初審法庭,裁決即生效。CETA 第8.29 條鼓勵締約雙方與其他貿易伙伴“建立解決投資爭端的多邊投資法庭和上訴機制”。這與中國“通過多邊規則規范上訴機制”的主張非常接近。中外BIT 也可借鑒CETA 有關上訴法庭審理期限的規定。
其次,規定上訴法庭的透明度規則和非爭端方參與規則。增加ISDS 機制下仲裁的透明度是國際社會改革ISDS 機制的重要內容之一,而非爭端方參與有助于增加ISDS 機制下仲裁的透明度,且非爭端方基于公眾知情權或公共利益,有參與爭端解決的權利。換言之,為了維護公共利益,私人利益有必要做適當讓渡。2022 年7月生效的修訂版《ICSID 條例和規則》(ICSID Regulations and Rules)的規則67(Rule 67)和規則68(Rule 68)分別規定了“提交非爭端方陳述”和“非爭端締約方參與”的條件、程序和方式。①2022 年《ICSID 條例和規則》規則67 規定:任何非爭端當事方的個人或實體都可向仲裁庭申請提交書面陳述。至于是否允許非爭端方提交書面陳述,仲裁庭應考慮陳述是否屬于爭端范圍內事項等相關因素,不再需要仲裁庭與爭端雙方協商。See ICSID, Proposals for Amendment of the ICSID Rules,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ule_amendment_proposals_convention.pdf,visited on 27 May 2022.2014 年3 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公布的《投資人與國家間基于條約仲裁透明度規則》第3 條詳細規定了仲裁文件公布規則,第4 條和第5 條分別規定了第三人提交材料和非爭端締約方提交材料規則,第7 條規定了機密信息或受保護信息和保障仲裁過程完整性的透明度例外情形。②該規則適用于依照2014 年4 月1 日及之后訂立的為投資或投資人提供保護的條約,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下提起的投資者與東道國的仲裁,除非該條約締約方另有約定依照2014 年4 月1 日之前訂立的條約提起仲裁的,由爭議各方同意適用或條約締約方同意適用。參見《投資人與國家間基于條約仲裁透明度規則》,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zh/rules-on-transparency-c.pdf,2019年3月20訪問。CETA 第8.36、8.38條詳細規定了透明度規則和非爭端方參與規則,并將其納入到第8.28 條上訴法庭機制中。因此,中外BIT上訴法庭機制可參考CETA和《投資人與國家間基于條約仲裁透明度規則》設計上訴法庭透明度和非爭端方參與仲裁的規則,包括規定東道國不得拒絕披露根據其相關國內法應當披露的信息;東道國采取的維護公共利益措施必須符合必要且適當的要求。③例如,《中國—日韓BIT》第19 條“臨時保障條款”規定:出現嚴重國際收支平衡或外部財政危機等金融問題時,締約方采取的措施不應超過必要的限度,應盡量避免對締約其他方的商業、經濟和金融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損害。
最后,上訴法庭裁決的執行。上訴法庭裁決是最終裁決,爭端各方要履行且不得就裁決再次提出撤銷、廢止等申請。同時,上訴法庭裁決的執行面臨與《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和《ICSID 公約》兼容的問題。一方面,《紐約公約》第5 條規定了締約方有權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五種理由,歐盟是《紐約公約》非締約方,歐盟通過條款回避《紐約公約》第5 條的審查,如,CETA 第8.41 條“裁決的執行”第3、4、5款的相關規定;另一方面,《ICSID 公約》第53條第1款規定仲裁裁決對爭端雙方都有約束力,除《ICSID 公約》規定的補救方法外,不得尋求任何上訴或其他補救措施。④參見唐海濤、鄧瑞平:《歐盟模式ISDS 上訴機制:革新與兼容性論析》,《湖北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第157、160頁。因此,中外BIT上訴法庭機制設計要注意與《ICSID公約》和《紐約公約》兼容。例如,解決執行上訴法庭裁決與《紐約公約》兼容問題時,可通過具體條款明確上訴法庭的裁決是最終裁決,不得用上訴、審查、撤銷等其他補救措施;上訴法庭裁決與《ICSID 公約》兼容方面,由于《ICSID 公約》排除爭端當事方提起上訴程序,因此,要使《ICSID 公約》締約國承認上訴法庭的裁決,存在巨大障礙,但中國可在中外BIT簽訂、升級和更新時,增加上訴法庭裁決等同于《ICSID公約》仲裁裁決的規定,解決兩者的兼容問題。
(四)三種機制應相互銜接
在對爭端預防機制、制度化調解程序和上訴法庭機制的具體設計后,中外BIT中ISDS 機制有必要對三者之間的銜接性進行明確規定。首先,爭端預防機制和制度化調解程序之間的銜接。爭端預防機制是預防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分歧升級為爭端的法律機制。國家聯絡點和聯合委員會在處理此類分歧時,一定程度上扮演著調解者的角色,雖然此時的調解不同于調解委員會制度化調解程序中的調解,但國家聯絡點和聯合委員會可以參考制度化調解程序規則,促使雙方消除分歧。如果分歧沒有消除,則可選擇啟動制度化調解程序,在調解委員會的主持下友好解決爭端。其次,爭端預防機制與上訴法庭機制的銜接。爭端預防機制先于上訴法庭機制運行,只有爭端雙方不能通過爭端預防機制化解分歧時,才能選擇國際仲裁,如果任何爭端方對國際仲裁裁決不滿,可依據ISDS 機制規定的上訴理由,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最后,制度化調解程序與上訴法庭機制的銜接。上訴法庭機制的啟動是在國際仲裁裁決之后,而制度化調解程序是與國際仲裁并行的爭端解決機制,換言之,制度化調解程序獨立于上訴法庭機制。上訴法庭機制運行期間,爭端雙方仍可參考制度化調解程序達成一致協議,即提起上訴的一方可主動選擇放棄上訴,與另一方共同決定再次啟動制度化調解程序,但此次選擇應具有終局性,如果爭端雙方仍不能達成一致,則上訴之前的國際仲裁裁決將作為此次爭端的最終解決方案。特別例外的情況,如雙方合意,則可提交上訴法庭決定是否再次開啟上訴程序。
四、結語
當前,中國已由側重資本輸入國轉為資本輸入國和資本輸出國身份兼具的國家。這種身份轉換必將影響中國國際投資政策和在投資者權益和東道國監管權之間維持平衡的ISDS 機制。國際社會也在探索和改革傳統的ISDS 機制。歐盟提出常設投資法庭和上訴法庭制度,把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間爭端的調解方式制度化,并在CETA 等投資協定中推行其改革后的制度。巴西在其CFIA 范本中設計了一個不包括締約一方投資者與締約另一方仲裁機制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新模式,即由(國家聯絡點和聯合委員會)爭端預防機制和締約方之間仲裁的混合模式組成的ISDS 機制,目的是將爭端解決的重心轉移至爭端預防,為投資者創造相對便利的爭端解決途徑。2018 年《意見》提出:推動建立訴訟與調解、訴訟與仲裁有效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2019 年7 月,中國政府提交的《投資人與國家間爭端解決制度可能的改革的意見書》再次肯定了“設立基于國際條約的常設上訴機制”。2020 年12月30 日,中國與歐盟原則上達成CAI,2022 年1 月1 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正式生效,但這兩個協定中的ISDS 機制還未最終形成,需要進一步談判。因此,更新或完善中外BIT 中ISDS 機制已很迫切,在中外BIT 中的ISDS 機制條款中創造性導入爭端預防機制、規定制度化調解程序、增加上訴法庭機制,不僅有利于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和CAI 中ISDS 機制的構建,而且有利于中國參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改革,促進建立完善的中外雙邊或多邊投資爭端解決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