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劇院?實驗劇團?小劇場戲劇?
◆倪 勝
本文主要想清理“實驗”和“戲劇”的歷史關系,讓我們先從國內戲劇界對實驗一詞的理解開始。
中國戲劇界的“實驗”命名
我國曾出現過一個非常有名的中央實驗話劇院,據2021年國家話劇院網站[1]介紹:
“1955年,歐陽予倩、沙可夫、李伯釗、孫維世、歐陽山尊等聯名向國務院倡議,以中央戲劇學院導演、表演兩個干部訓練班中的部分骨干為基礎,組建一個示范性的國家話劇院。五位戲劇家的倡議很快被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采納,1956年9月16日,中央實驗話劇院成立,首任院長是中國話劇事業奠基人之一、著名戲劇家和教育家歐陽予倩。
五位戲劇家聯名上書后,歐陽山尊在當年的《戲劇報》上發表了題為《我們需要一個新型的、示范性的國家話劇院》的文章,內容是關于創辦這個話劇院的一些設想,文章提到:“我們需要一個新型的、示范性的國家話劇院。首先,它必須是新型的才能起到示范的作用。它的新型應該表現在:它是一個嚴格地按照科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造方法,亦即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來進行創造的劇院。在文化水平上是整齊的;在創作方法上是一致的;在戲劇事業上是目標明確,信心充足,毫不動搖的。它的新型也應該表現在它的企業化而不是機關化的組織原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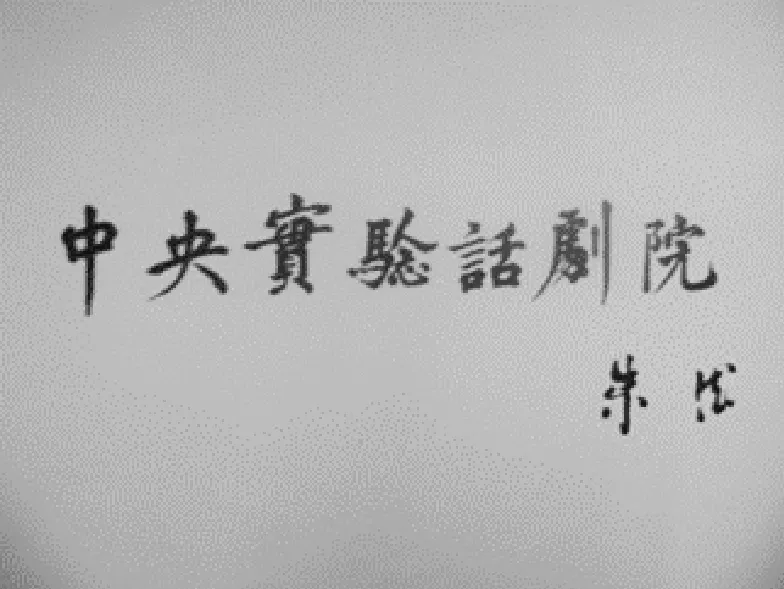
請注意,當時這些戲劇家們理解的實驗是“示范的”,而其要建設和示范的內容則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
這個劇院于2001年12月25日被改建的中國國家話劇院代替。當年文化部關于組建中國國家話劇院的決定中說:“根據中央關于‘改革劇團體制,集中力量辦好代表國家級藝術水平的劇團’的要求,為進一步深化文化部直屬藝術表演團體的體制改革,努力把中直院團建設成為在全國具有導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的國家級藝術表演團體,經國務院批準,現決定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和中央實驗話劇院的基礎上組建中國國家話劇院……為繼承和發揚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和中央實驗話劇院的優良傳統,保持歷史的延續性,國家話劇院的歷史包括上述兩個劇院的所有藝術實踐活動,并追溯到1941年延安青年藝術劇院時期……”
也就是說,無論是1956年建立的中央實驗話劇院還是幾經合并和分立之后,直到今天建立的中國國家話劇院,他們所理解的“實驗”始終是“示范”。
眾所周知,我國曾出現不少實驗中學,直到今天,這類中學也仍十分活躍。查詢這類學校的網站可以發現,他們對實驗的理解是一樣,即“示范”。比如山東省實驗中學[2]:
1950年7月,華東大學同山東大學合校,遷往青島。華東大學附屬中學于同年7月改為“山東省實驗中學”,擔負“進行中學教育工作中的實驗與改革”的使命,山東省實驗中學成為全國最早命名的“實驗中學”。
1956年山東省教育廳向全省推廣山東實驗實驗中學經驗。在這一時期,山東省實驗中學一系列的教學經驗在全省推廣。
六十年代,上級把縮短學制的實驗任務交給了山東省實驗中學。從1960—1965年,學校先后五次采用五年一貫制。
……
1980年,教學改革的浪潮在全國興起。山東省實驗中學接受了教育部新版中學教材實驗任務。1987年在北京舉行的新版教材實驗總結大會上,學校被評為教材科研一等獎,經驗在全國推廣。山東省實驗中學還是“新概念英語”最早的試用單位,這一實驗成果如今已在全國普遍采用。
……
2004年,隨著新課程改革的啟動,該校作為省教育廳確定的省級新課改重點實驗聯系校,責無旁貸地肩負起在全新的教育軌道上探索的使命。山東省實驗中學率先在全省開齊開全新課程八大領域的全部課程,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在全國起到引領和示范作用,以“基礎課程體系、校本課程體系、德育課程體系、國際課程體系”四大類課程為內容的多元課程體系已日趨完善,學校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辦學實踐被《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等中央媒體報道。
由上,我國實驗中學的任務就是中學教育的探索和研究,最后形成經驗,推廣全國。其中“實驗”的含義仍然是“示范”。
1956年中央戲劇學院以畢業生為主體成立了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并一直活躍在社會演出中。1962年附屬實驗話劇院獨立建制,改為隸屬于文化部的中央實驗話劇院。
2017年,為了加強學院的“雙一流”建設,按照學院一流學科建設方案要求,學院開始重新籌建實驗劇團,并于2019年4月正式恢復運營。[3]

中戲實驗劇團中“實驗”一詞的外文也是experimental。從中戲實驗劇團的演出實踐來看,主要屬于學生實習演出。因此,這是國內戲劇界對“實驗”的另一個理解:“實習”。
國外的戲劇實驗
以謝克納創建的遂行小組為例,他自稱為實驗戲劇團(experimental theatre company)[4]。隨后謝克納用實驗這個詞來解說先鋒,“‘先鋒’意味著‘某種先在的東西’——一種先驅、實驗性的原型,突破。”[5]
布萊希特有篇文章叫做《論實驗戲劇》(Ueber experimentelles Theater),他認為歐洲嚴肅戲劇的實驗已經歷經兩代人,他舉出的實驗導演有安托萬、布拉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克雷格、萊茵哈特、耶斯納、梅耶荷德、瓦赫坦戈夫和皮斯卡托等人。這些導演嘗試過很多方式,比如“瓦赫坦戈夫和梅耶荷德從亞洲舞蹈抽取出某些舞蹈形式而后為戲劇劇本(Drama)創作出完整的編舞。梅耶荷德用激進的構成主義進行導演,而萊因哈特使用所謂真正的觀演場所為舞臺:他在公共場所演出了《人人》和《浮士德》。在蘇聯人們嘗試過,在森林里的露天舞臺演出《仲夏夜之夢》,用阿芙樂爾戰艦再現攻打冬宮。舞臺和觀眾之間的障礙被拆除。在萊因哈特的《丹東》在柏林大劇院上演時,演員坐在觀眾席中間,而在莫斯科,奧赫洛普柯夫(Ochlopkow)則將觀眾安排到舞臺上。萊因哈特使用了中國戲劇的花道,并在馬戲團場地運用,以便于在人群中導戲。群眾場面導演方法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萊因哈特和耶斯納手里得以完善,后者曾以其階梯設計制造出一個三維舞臺。旋轉舞臺和圓拱頂舞臺被發明出來,燈光效果也被發現。聚光燈容許宏偉的照明效果。變化多端的光能幻化出‘倫勃朗式的氛圍’。人們可以將戲劇史上的某種燈光效果稱為‘萊因哈特式的’,就像人們在醫學史上看到的某種心臟手術稱為‘特蘭德林堡(Trendelenburg)式的手術’一樣。以舒夫坦方法為基礎,出現了一種新的投影方法,還出現了一種新的音效制作。為了演出藝術,卡巴萊和戲劇以及歌舞滑稽劇(Revue)和戲劇之間的界限被拆除。還有戴著面具、希臘悲劇的厚底靴和啞劇的實驗。大部分實驗都應用了古老的經典的劇目。莎士比亞的作品一再被改編和翻轉。這些經典被翻找過太多遍,以至于幾乎再沒有什么遺漏。人們體驗到哈姆雷特穿著晚禮服,凱撒穿著制服,那么至少晚禮服和制服就從這些戲中得益,并得到尊重。這些實驗有很多不同價值,而最引人注目的不再是最有價值的,但最沒有價值的也并不是完全無價值。例如穿著晚禮服的哈姆雷特所做的,比起慣常的穿著絲綢長襪的哈姆雷特來并非對莎士比亞更為褻瀆。人們絕對保持在服裝扮演的框架內行事。”[6]
以上譯文中,花道是日本戲劇特色舞臺設計,被布萊希特誤解為中國戲劇的了。舒夫坦又譯尤金·沙夫坦(Eugen Schuefftan),是著名的電影攝影師。服裝扮演,Kostuemstueck,即英文的costume play,簡稱cosplay,也譯角色扮演。
1916年出版的許家慶《西洋演劇史》中說:“俄國劇評向來評說劇本與舞臺藝術之高深,置演技于第二位,然而當時多數觀眾注重欣賞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技,于是對藝術劇院的反對之聲漸漸沉寂。”所以,可以說二十世紀的實驗戲劇的走向就是從重文學到輕文學的變化。“莫斯科藝術劇院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期,革除了舊劇場之陋習,集歐洲進步劇場之大成,帶來新的觀演風氣。”[7]這一段可以證實,當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也是非常具有實驗和探索性質的。
謝克納在《環境戲劇》中評價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帶給‘演員’這個詞以它以前從未獲得過的尊貴。他使演員成了一個人文主義者和心理學家,一個能理解和表達人類行為的情感、動機、行動和策略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強烈譴責那些允許自己被經理們剝削的演員。他痛斥懶惰、放縱、夸張、濫用才能、為喝彩而活著的演員。這個偉大的俄羅斯演員和導演堅持認為演員要生活‘在藝術中’——一種無論在不在舞臺上都有的,嚴格訓練的、自我監測的、高尚道德水平、精致的良好趣味的狀態。為做到這些,演員要學會在觀眾面前如何表現得‘自然’;這是一個復雜的、苛刻的任務。”[8]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James Roose-E-vans于1989年出版著作《Experimental Theatre:From Stanislavsky to Peter Brook》,標題為:《實驗戲劇: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彼得·布魯克》。
然而,我們又要看到,西方實驗戲劇從自然主義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而后,絕大多數戲劇家都是以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面目出現的。尤其是后現代思潮勃興之后,這一傾向非常明顯。
英國戲劇家克雷格(Edward Gordon Craig)是堅決反對自然主義戲劇的,他說:“我相信在某個時候,我們將會不要寫定的劇本,不用演員,就可以在劇院中創造出作品來;然而我也相信在今天我們擁有的條件下日常工作的必要性。”[9]
不少實驗藝術家們對傳統鏡框式舞臺總是不滿意,總在嘗試新的舞臺設計。比如梅耶荷德使用構成主義舞臺設計、德國導演皮斯卡托和現代主義建筑師格羅皮烏斯合作考慮過全景劇場的設計、布萊希特使用過半幕設計,而謝克納的車庫劇場也是非同尋常,生活劇團、面包與傀儡劇團都曾經在街頭演出。可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卻是以鏡框式舞臺為主。
小劇場戲劇?
什么是小劇場戲劇?
由于theatre有戲劇、劇場、劇團等各種含義,因此,要從歐美文字上將小劇場和小戲劇區分開不太容易。我查了一下資料,感覺和中國大陸所說的小劇場戲劇相關的材料有如下幾個:
1.歐洲自然主義風尚
在19世紀末,歐洲戲劇興起了以左拉為先行者的自然主義趨向,旗手包括易卜生、尼采、瓦格納和左拉等。由于這種戲劇經常遭到審查和禁止,“這些先驅竭力推行創建私人俱樂部或社團,由而可以擺脫審查而為志趣相同的擁護這些革命觀念的、精選過的觀眾來演出新型戲劇:自由劇院于1887年在巴黎開張;Otto Brahm于1889年在柏林創建自由舞臺(Freie Bühne),J.T.Grein于 1891年在倫敦創建獨立劇院(Independent Theatre),1888年創建莫斯科藝術和文學社團,隨后發展成莫斯科藝術劇院(the Moscow Art Theatre)。”[10]
法國戲劇家安德烈·安托萬1887年3月30日在一個不到400人的骯臟昏暗的小劇場(the dingy little theatre)上演了根據左拉中篇小說《雅克·達穆爾》改編的戲,標志著“自由劇院”的誕生。他取消了舞臺上的景片,而使用實在的三維的家具。[11]
這些劇團之所以小,一個是因為大劇場不接受他們的演出,另一個則恐怕是這些戲的觀眾并不多。
2.美國跟風
在美國也跟著興起了小劇場戲劇運動(The little theatre movement),這個詞譯成小戲院(或小劇院、小劇團)戲劇運動恐怕更為合適。“大約在1912年幾個‘小劇團’(little theatres)效仿歐洲獨立劇院而成立。其中最重要的有,波士頓的Toy劇團(1912年),芝加哥小劇院(1912年),普文斯鎮演藝團(馬薩諸塞州,1915年),紐約的鄰里演藝廳和華盛頓廣場演劇團(均成立于1915年),以及底特律藝術和技巧劇院(1916年)。到1917年有至少五十個這類劇團。一般說來這些劇團有全職導演但使用業余演員、設計師和職員。這是經濟上也是美學上的選擇。由于這些劇團正在培養新的觀眾,因此無法養活職業演員。但很多人也相信職業演員太過依賴于他們從商業戲劇里學到的情節劇技巧以至于不能有效地上演一出有挑戰性的輪演劇目,他們認為業余演員對新方法的態度會更為開放。小劇院每年為預定戲票的觀眾制作一系列戲劇,使用在歐洲已經被廣泛接受的技術。小劇院戲劇運動培養觀眾為接受新的戲劇和制作方式做好了準備,從而對1912年至1920年的戲劇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1920年以后,小劇院開始無法跟社區劇院相區分了。跟其對標的歐洲戲劇運動一樣,社區戲劇運動試圖復興古希臘戲劇精神,這個運動在美國大約從1905年開始。”[12]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小劇院是可以流動的,比如“1916年,普文斯鎮演藝團遷移到了紐約。”[13]這個事實表明,The little theatre movement不應該理解為小劇場戲劇運動,它跟劇場關系不大,準確的譯法是小劇院或小戲院戲劇運動。
小結一下,美國的小劇院戲劇運動具有業余性、非商業性、跟風歐洲自然主義等特點。這個運動興起于1912年,很快(1920年)就轉化成了社區戲劇運動進而商業化而消失了。
3.萊茵哈特(Max Reinhardt)的室內劇場
德國導演萊因哈特在德意志劇院擔任藝術指導的時候,曾開拓小劇場戲劇。“德意志劇院以前是一個大劇場,適合經典劇目的演出。但萊因哈特贊成斯特林堡的理念,認為探索微妙心理的戲劇需要更為親密的環境。在接管德意志劇院后,他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在那座老建筑旁建起第二個、更具親密性的場地——‘室內劇場’(Kammerspiele)。在這個場地中,通過對觀眾席進行建筑上的處理令它一直連接到舞臺上,且令舞臺僅只高出地板平面一小級臺階,從而打破了舞臺與觀眾之間生硬的區分。觀眾們——不超過400人——由此可以獲得一種與劇中人物似乎處于同一個空間的幻覺。”[14]這里所謂室內劇場,德語原文即Kammerspiele,英語為Chamber Theatre。2020年我曾在德意志劇院的大劇場和室內劇場分別看過一出戲,的確,大劇場舞臺要高出觀眾席一米左右,而室內劇場僅只高出觀眾席一級小臺階。
這個室內劇場曾被我國學者稱為小戲院。如宋春舫所撰《小戲院的意義由來及現狀》(1923年)介紹說:“還有一般劇本,不能在大戲臺上排演的,卻又不能因此而停演,來因赫特所以另造了小戲院(Kammerspiel)。”[15]
日本有筑地小劇場,“劇場在外形構造上參照德國著名導演萊茵哈特的室內劇場……筑地小劇場開場后的公演劇目中也有一批德國表現主義作品,如:《海戰》《從清晨到午夜》《煤氣》等。”[16]上海戲劇學院新空間劇場也可以算作小劇場,它甚至連這一小級臺階也沒有,舞臺平面就是觀眾席第一排的平面。
法國作家伏爾泰早就對這種親密的表演方式表示不滿,“巴黎劇院是一處裝飾趣味極為惡劣的舉行晚會的舞廳;人們都站著擁擠在一處骯臟的劇場里,這足以使他感到不快,尤其使他感到難堪的是,那種允許觀眾上舞臺的村野習慣,演員幾乎沒有足夠的場地來表演他們必須做的動作。……為了在這樣的劇院里進行演出,他創作了自己的《塞密拉米斯》。……首次演出時,觀眾還是坐在臺上的。后來在演出時,才改正了這種不適當的情況;演員把臺上的人請了下去;這在當時還是一個例外,純粹是為了照顧這樣一部非凡的作品,從那以后,舞臺才成為固定的設備。”[17]
因此,從劇場的小來看,它并不能造就一種獨特的戲劇藝術形式,只是有點小特點罷了。
4.科波(Jaques Copeau)
科波原是法國的一名評論家,1913年10月22日建立了自己的劇院——老鴿巢劇院。他最早推崇小劇團演出(the small-scale theatre),以戲劇藝術的探索來擺脫商業戲劇,后來他回顧自己的職業生涯,認為“那些小劇團(Those little theatres)只是技術實驗室,能令戲劇的最高貴傳統得以復活的藝術學校,但是不能被叫作真正的劇團,因為它們缺乏真正的觀眾。”[18]因此,所謂小劇場(戲院)戲劇并非這些戲劇人的主動選擇。
“即便如此,那些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迅猛生長的‘實驗室劇院’(laboratory theatres)正是出自科波的工作——耶日·格洛托夫斯基的‘波蘭實驗室劇院’,彼得·布魯克在巴黎創建的‘國際戲劇研究中心’,‘拉媽媽劇團’,理查·謝克納在紐約創建的‘遂行小組’——所有這些劇團都遵循科波的路線,回溯到戲劇的根本,去除了舞臺,復活了宗教儀式。”[19]這種情況的出現,應該是因為實驗戲劇本來觀眾就少,少有能在大劇場內演出的劇目,而小劇場的形制又比較靈活,有利于各種戲劇實驗的開展。
知識鏈知識資源的難以模仿性確保了知識鏈的知識優勢,并最終轉化為經濟利益;反之,如果知識鏈沒有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獨特的資源,其知識優勢就會慢慢喪失。所以,知識鏈管理的重心就是隱性知識的開發和利用——通過把員工頭腦中的創新思路、工作經驗、心智訣竅等意會知識變為知識鏈獨特的知識資源。除隱性知識外,知識鏈所擁有的專利、聲譽、渠道等往往也難以模仿,這些都保證了知識鏈知識優勢來源的穩定性。
我們應該看到,科波以及后來在小劇場工作的戲劇家,他們并不滿足于小劇場,他們一直希望能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觀眾。
5.日本地下演劇
日本隨著歐美的潮流,也出現了一些小劇場戲劇,“‘地下演劇’在中國多被翻譯為‘小劇場戲劇’。然而,這樣的譯法存有不少爭議,因為它極可能使人們誤認為‘地下演劇’的特征僅僅是‘小’而已。‘地下演劇’的劇場雖然小,但更主要的形態特征還是在于其多樣性和非傳統性,主要有以下幾大類:(1)小型劇場,指可用于演劇的規模較小空間;(2)臨時型劇場,大學演劇團體是‘地下演劇’的重要力量之一,用于演劇的大學教室等都屬于這一類型;(3)準劇場型劇場,比較典型的是‘藝術劇場·新宿文化’這一演劇空間,它原是一家用于放映藝術電影的影院,后來在電影放映結束之后增加了從晚上九點半開始的戲劇演出,這樣的演出空間契合了青年知識分子的欣賞需求,因此‘地下演劇’對這一空間頗為青睞;(4)流動型劇場;(5)再生型劇場。”[20]
“‘地下演劇’運動是在日本劇場資源已較為充裕的時期異軍突起的,卻同樣面臨著劇場‘貧困’。這主要是因為‘地下演劇’從演劇理念到具體表現形式,均排斥規整而有秩序的傳統劇場,認為那是對創造力的束縛,對激情的束縛,這使得他們熱衷于尋找符合其理念、適合其形態的非傳統演劇空間,甚至到沒有劇場的地方去‘創造’劇場,把不是劇場的場所變為劇場,因此劇場本身就具有了鮮明的身份——演劇創造的一部分。”[21]
據鈴木忠志回憶,“自1966年秋季至1976年3月為止的十年間,我所使用的表演劇場——位于新宿區戶塚町的早稻田小劇場,其舞臺空間寬三間半,縱深二間,而座位只有120個左右,整體而言是以后個箱型的小空間。近年來,使用這樣的小空間的舞臺發表作品,在一些熱愛戲劇的年輕人之間非常稀松平常,可是這在當年卻是很少見的。那時候,大家覺得只能在名為某某劇場的豪華建筑物內,才有機會接觸到所謂戲劇的東西。因此,當時還有人宣稱,在一些咖啡廳二樓的木造空間里演出的舞臺,不能被列入戲劇的范疇里。
“我之所以會在這類的場所做戲劇表演,并非一開始秉持著什么樣的理由。只是總覺得對于當時既有的戲劇表演感到厭倦,因此思考自己是否能創作一些非空間性的戲劇活動,因而不得不想辦法確保自己的演出場地,但又局限于經濟的因素而最后的結果成了這類的場地。但是,在這種可能連演員休息室或出入口都沒有的貧窮空間里,這十年來讓我學到的東西相當豐富。正因為空間狹小,我才能學到一個戲劇最重要的態度,那就是掌握對于戲劇而言最基本、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東西。
“觀眾的眼簾中央映照出演員的呼吸與汗水。而這樣的小劇場的空間會將劇中的一切裝飾要素無效化,也就是說,不論再怎么極小的事物,都能立即暴露出其真實或虛假的一面,而且也無法如同大劇場的戲劇,能夠提供那些借由機器道具所呈現的華麗幻影表現,因此只能憑著單方面演員的表演行為與身體動作的力量,傳達給觀眾。”[22]
鈴木先生明確指出,經濟因素是日本小劇場出現的主要原因。
6.美國外百老匯和外外百老匯Studio
“在二十世紀初‘小劇院’運動的目標是改革商業舞臺;它所推行的新風格或帶傾向性的主題后來被建制所采納。甚至阿爾托,這樣完全反對西方戲劇以及那個時代占支配地位的戲劇的人,仍然形成了標準戲劇事件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接下來的1960年代,探索實驗諸形式的外外百老匯戲劇以及‘戲劇實驗室’突現,一個不可彌合的裂隙開始出現了,這些劇院激進地與常規舞臺遂行不相容:環境戲劇、游擊隊戲劇和意象戲劇。”[23]
眾所周知,美國紐約百老匯大道(主要在41—53街)周圍有自然形成的一個商業劇院群,通常叫做百老匯戲劇,主要上演商業性質的音樂劇。而著名德國導演皮斯卡托在美國流亡期間,為對抗百老匯的商業性親手建立了外百老匯戲劇。
外百老匯戲劇的代表有公共劇院(Public Theatre),主要上演實驗戲劇。一些重要的獲獎劇作家如 Edward Albee(阿爾比)、Charles Gordone、Paul Zindel、Sam Shepard(謝潑德)、Lanford Wilson以及John Guare等其作品的首演都是在外百老匯。
1990年代接受采訪時,兩位美國著名劇作家都表示過對小劇場戲劇的同情。
米勒說:“現在我可以說,戲劇界有一種好現象,即目前有數目眾多的小型劇院,許多青年人在里面演出。我這里說的是美國,特別是紐約市。就是在洛杉磯,簡陋的小劇院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有的劇院只有百十個座位,有的只有五十個座位。新作品就在那里進行試驗演出。它的前途無量,我認為它現在作出的貢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24]
美國劇作家阿爾比說:“多數嚴肅的戲不在商業劇院里上演,而在小劇場里上演,在地方性劇場里上演。商業劇院主要是指百老匯區的劇院和夏季劇團。它們從不上演十分優秀的劇目。每一年里最多也只不過上演一兩個有分量的劇目,其余的全是商業性的。正是那些只有兩三百個座位的小劇院才上演嚴肅劇目。”[25]
隨著外百老匯不斷受到商業的侵蝕,紐約又出現了外外百老匯戲劇。外百老匯和外外百老匯戲劇基本上都是小劇團戲劇。
“到1990年代中葉,紐約大約有150個不同性質的外外百老匯劇院。它們大多通過組建于1972年的外外百老匯聯盟(the Off-Off-Broadway Alliance)相互聯合,這個聯盟主要幫助其成員處理共同的問題。”[26]外外百老匯劇院的代表有拉媽媽實驗戲劇公司(La Mama Experimental Theatre Company)、黑人劇團(The Negro Ensemble Company)、開放劇團(the Open Theatre)、曼哈頓戲劇俱樂部(Manhattan Theatre Club)、合成工作室劇團(Ensemble Studio Theatre)、晃來晃去劇團(Roundabout)等。
跟前述1920年代美國的小劇院戲劇運動一樣,此時出現的小劇團也是流動的,跟劇場關聯度不大,比如生活劇團,甚至常年往歐洲演出,很長時間里并沒有自己的固定劇場。
當然,演出和劇場無法完全分開。而紐約對百老匯和外百老匯的區分,也是按照劇場大小來的,“百老匯、外百老匯和外外百老匯劇院的差別主要是在契約上。根據演員權益協會的標準,百老匯劇院擁有座位500個或以上;外百老匯劇院座位在100到499個;外外百老匯則為99個及以下。紐約的大部分話劇都在外百老匯或外外百老匯劇院上演。”[27]
法國作家馬特爾也說,“除了地理位置不同,百老匯和外百老匯官方意義上的區別還在于劇院座位的數量,這個界限定在499,所以百老匯劇院必須提供499個以上的座位(平均為1,000個,有時在1,500到2,000個之間),而所有‘外百老匯’劇院必須提供100到499個座位。兩個除了風格不同——委實難以對這兩種風格進行定義——規模也不同。”[28]為什么說無法從風格上對百老匯和外百老匯戲劇進行區分呢?我們知道,當初外百老匯成立時的確有藝術風格上的考慮,皮斯卡托希望能對抗百老匯戲劇的商業性。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少外百老匯的戲劇也逐漸被百老匯戲劇吸收納入,也變得商業化起來,導致兩者開始趨同。
所以說,百老匯、外百老匯和外外百老匯用場地規模大小作為區分手段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辦法。當然也是一個不科學的辦法。
國外對小劇場戲劇(而非小劇團戲劇)的研究,資料比較少。我在德國特地查詢了相關資料,僅發現一部《Modernes Theater auf Kleinen Buehnen,Fotografie Renate von Mangoldt,Text Walter Hoellerer,Literarisches Colloquium Berlin》,大概是一次柏林召開的關于小型舞臺的文獻會議論文集,封面用的是生活劇團《禁閉室》的劇照。這一點進一步說明,the little Theatre指的并非小劇場(小舞臺),而是小劇團(劇院)。
小結一下:只是根據演員權益協會的規則,紐約戲劇界以座位多少來區分百老匯、外百老匯和外外百老匯戲劇,這并不是一個戲劇風格和學術上的區分標準。不能以這個標準來認定,小劇場戲劇為一種戲劇類型或風格。
中國學人提到小戲院戲劇運動
宋春舫在其《小戲院的意義由來及現狀》(1923年)中介紹了當時國外小劇院戲劇運動情況,他舉出的例子首先是安托萬(他寫成盎多安)的自由劇院,其次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莫斯科藝術劇院,英國格林的倫敦獨立戲院,萊因哈特(他譯為來因哈脫)的柏林小戲院(Fuchs)和慕尼黑(他譯為密興)的藝術戲院,美國1912年也出現了三個小戲院(芝加哥、波士頓和紐約),甚至在1923年左右美國已經有了50來個小戲院,隨后他提到戲劇實驗室(Dramatic Laboratory)以及卡內基技術學院(卡內基梅隆大學的一個學院,他譯為卡內奇工業學校)的實驗室戲院(Laboratory Theatre),哈佛大學的工作室戲院(Workshop Theatre)等。[29]
由于Theatre是個多義詞,因此這里需要區分劇場和劇團,我將劇場一詞理解為建筑空間,英語的表達是place,而劇團則是人的群體en-semble,我個人判斷,大學里的Theatre基本都是劇團,而安托萬自由戲院等則屬于場團合一的情況。
宋春舫總結說:“總而言之,這小戲院實在是近代戲院歷史里面一種最有意義的運動。他的特色,就是——(一)反對營利主義提高戲劇位置。(二)重實驗的精神,使戲劇可以容易進步。(三)容易舉辦,不比得大戲院要費很大的工程,及資本。”[30]
周作人在《中國戲劇的三條路》中提倡純粹新劇、純粹舊劇和改良舊劇三種,并解釋純粹新劇說:“第一種純粹新劇,當用小劇場辦法,由有志者組織團體,自作自譯自演自看,惟會員才得觀賞,并不公開,完全擺脫傳統,蔑視社會心理,一切以自己得趣味為斷,不受別的牽制。這種戲劇應該有兩樣特點,與別種演劇不同,便是非營業的,非教訓的。這全然是為有藝術趣味的少數而設,而且也不妨以其中的某種趣味為集合點,組成精選的小團體,將來同類的團體增多,可以互相提攜,卻不必歸并以雄厚勢力。……這個運動如見成功,小劇場可以隨處皆有,戲劇文學非常發達,但是享受者總限于少數,新的藝術決不能克服群眾,這是永遠的事實,只應承認而不必悲觀的。”[31]周作人這個建議,非常類似于歐洲的小劇場,然而比照前述安托萬的自由劇院的由來,是為應對當時歐洲各國政府審查制度而不得不實行會員制,強行搬入我國,似乎會水土不服。“第二種純粹舊劇,完全保存舊式,以供學者之研究。這也應用小劇場,也不公開,只附屬于一種學問藝術的機關,隨時開演,惟研究文化的學者、藝術家、或證明受過人文教育的人們,才有參觀的權利。在這種狀況之下,舊戲的各面相可以完全呈現,不但‘臉譜’不應廢止,便是裝‘蹺’與‘摔殼子’之類也當存在,甚至于我于光緒朝末年在北京戲臺上所見的Masturbado de la vigino的扮演似亦不妨保留,以見真相。”[32]這個建議類似于今天的非遺保護。
歐洲小劇院運動的發生原因已如上述。至于美國情況,汪義群《美國小劇場運動及其對美國現代戲劇的影響》(《戲劇藝術》,1982年第2期)指出,美國小劇場運動起源于對美國戲劇辛迪加的抵制。宋春舫書出版于1923年,他當然無法預見后現代戲劇的發展,其實當時布萊希特、皮斯卡托等人的獨特創作也尚未完全展開,而汪義群在1982年為小劇場運動補充了外百老匯劇場的興起和發展史,值得贊賞。
我國大概從1980年代,出現了一個小劇場戲劇運動。
我們知道,在這場延續幾十年的運動中,出現了林兆華(《絕對信號》)、牟森、孟京輝(《戀愛的犀牛》《我愛×××》)、田沁鑫、李六乙、賴聲川(《暗戀桃花源》)、王曉鷹(《掛在墻上的老 B》《哥本哈根》)等名導名作。而近幾年來,如北京鼓樓西劇場(2014年開張)這樣的小劇場也蓬勃出現,帶給中國戲劇界一股新風。
可惜我個人在這方面沒有多少觀賞經驗,更缺乏相關研究,僅讀過吳保和教授的《中國當代小劇場戲劇》等少數專著。根據個人一點微末的感受,我感覺中國的實驗戲劇,早年偏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改革開放后又偏重現代主義(荒誕派、意識流、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等,迷戀鏡框式舞臺等),直到今天,后現代主義的戲劇實驗仍屬少見。
簡單結論
1.小劇院戲劇在歐美國家因自然主義而興起。當時也并未成立為一個戲劇種類,于實驗戲劇有交叉,但不能等同于實驗戲劇。后來著名的實驗戲劇大師如萊因哈特、梅耶荷德、皮斯卡托乃至謝克納、生活劇團等都在大劇場和室外場地上演過實驗戲劇。
2.中國戲劇界小劇場戲劇運動僅取了little theatre小劇場戲劇的方面,強調劇場的小,而多少忽視了劇團的小。以劇場大小進行戲劇分類和研究,價值不大。建議改用實驗戲劇名稱。
3.中國話劇實踐,從開始就遭遇歐洲自然主義戲劇。到80年代受歐美現代主義戲劇影響而呈現新的發展。然而,至今仍少見后現代戲劇手段探索。
4.實驗戲劇是探索性的,嘗試性的,小眾的,關懷當代社會和人的戲劇。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當代歐美戲劇研究”(項目編號:19ZD10)階段性成果。
注釋:
[1]http://ntcc.com.cn/zggjhjy/lsyg/lmtt.shtml
[2]http://sdshiyan.jinan.cn/col/col5074/index.html
[3]http://web.zhongxi.cn/xyjg/jxkyjfbm/shiyanjutuan/
[4][5]THE FUTURE OF RITUAL:Writings on Culture and Performance,Richard Schechner,Routledge,1995,p.1-2,p.5.
[6]Bertolt Brecht Ausgewaehlte Werke in sechs Baen den,Sechster Band,Bertolt Brecht Schriften,Suhrkamp Verlag,1997,ss.404-405.
[7]姜濤:《斯氏體系在中國(修訂本)》,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6頁。
[8]【美】理查德·謝克納:《環境戲劇》,曹路生譯,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頁。
[9][10][11][14][18][19][23]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Theatre,Edited by John Russell Brow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62,p.343,p.343,p.368,p409,p409,p437.
[12][13][26][27]History of the Theatre,OscarG.Brockett,Franklin J.Hildy,Tenth Editi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4,pp.433-434,p.434,p.521,p.546.
[15][29][30]趙驥編著:《民國話劇史料匯編》第一輯3,學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頁,77-80頁,80頁。
[16][20][21]方軍:《日本現代劇場體系——從明治到平成劇場身份的變化與確認》,學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58頁,61頁,60—61頁。
[17]【德】萊辛:《漢堡劇評》,張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頁。
[22]【日】鈴木忠志:《文化就是身體》,林于并,劉守曜譯,國立中正文化中心2011年版,第95頁。
[24][25]郭繼德:《當代美國戲劇發展趨勢》,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頁,246頁。
[28]【法】弗里德里克·馬特爾:《戲劇在美國的衰落,又如何在法國得以生存》,傅楚楚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5頁。
[31][32]王元化顧問、翁思再主編:《京劇叢談百年錄》(增訂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9頁,9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