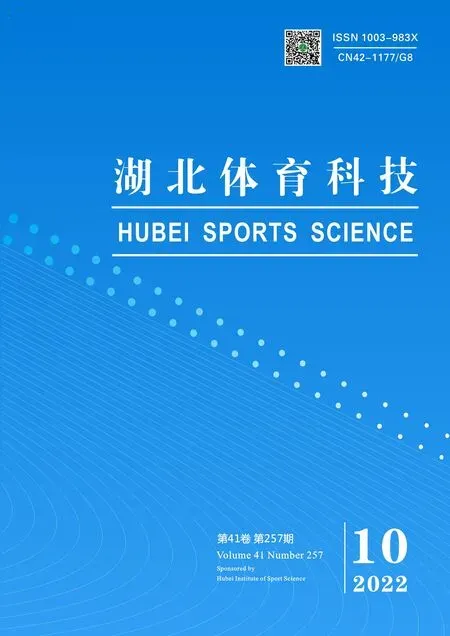體育情境中認知情緒調節對親社會—反社會行為的影響:道德認知的中介作用
馮泰熙,祝大鵬
(武漢體育學院 健康科學學院,湖北 武漢430079)
認知情緒調節策略(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是情緒管理的認知方式,是應對方式的認知成分[1-2]。 認知情緒調節是個體為了處理與之相關的情緒喚醒的信息而采取的基于認知性的且能被個體意識到的情緒調節方法, 是個體面對特定情境時有意識、有目的地努力調節情緒的過程[3]。 Garnefski 等[2]提 出 了 認 知 情 緒 調 節 策 略 的 9 種 成 分 :1)自 我 責備:個體為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想法和行為而感到內疚,譴責自己;2)責備他人:個體自己不承擔責任,反而把責任與錯誤歸咎他人,譴責他人;3)接受:個體接受自己所經歷的事情,接受已經發生的事情;4)重新關注計劃:個體重新思考采取什么措施處理和解決負性事件;5)積極重新關注:個體并不沉浸在負性事件中,而是思考愉快和快樂的的事情;6)沉思:個體不斷地回想與負性事件相關的感受和想法;7)積極重新評價:個體賦予自己成長中的事件以積極意義;8)正視現實:個體把當前的負性事件與其他事件相比,淡化負性事件的嚴重性;9)災難化:個體強調經歷的消極體驗。 這9 種成分可以分為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其中,接受、重新關注計劃、積極重新關注、積極重新評價和正視現實5 種成分屬于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而自我責備、責備他人、沉思和災難化屬于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
Vallerand 等[4-5]研究了 7 個不同的體育運動項目以界定體育道德(moral in sports)的內涵,認為體育道德包含5 個方面:1)運動員全身心投入體育運動:這種全身心投入是通過服從教練、在練習和比賽中努力表現出來,例如不讓球隊失望,總是提出最好的反對意見;2)社會規范:對運動中的社會規范的尊重,賽后握手,鼓勵隊友,做一個好的失敗者;3)規則和裁判: 對規則和裁判的尊重和關注, 即使對手作弊也要尊重規則,當裁判犯錯時不批評裁判,不報復對手的低級球,犯錯后保持冷靜;4)對手:對對手的真正尊重和關心,如將自己的設備借給對手,即使對手遲到也同意比賽而不是不戰而勝,以及拒絕欺負受傷的對手;5)對體育參與的消極態度:運動員對體育精神的態度是消極的, 其中運動員采取不惜一切代價取勝的方法,嘲笑對手,在輸掉比賽后發脾氣。 因而,我們可以把將體育道德定義為:運動員全身心投入體育運動中,并在體育運動中展現出的尊重、關心規則和裁判、社會規范、對手以及對體育運動的參與沒有消極的態度和行為。祝大鵬[6]總結前人對體育道德的研究,將體育道德定義為: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關注和尊重規則和裁判、社會規范、對手,對比賽全力以赴,對所有體育參與者沒有消極表現的原則規范的總和。 在運動心理學的研究中, 通常依據個體行為結果對他人造成的影響可以將運動員的體育道德行為劃分為運動親社會行為和運動反社會行為兩類[7]。運動親社會行為是運動員個體表現出的幫助他人或使他人受益的行為,如幫助跌倒的對手等[8];運動反社會行為指運動員個體表現出的傷害他人或對他人不利的行為,如傷害對手等[9]。
體育情境中道德認知與親社會行為和反社會行為也緊密相關。 祝大鵬[10]從道德結構發展的角度,將道德發展水平劃分為道德意向、道德判斷和道德行為3 個層面。 道德意向是指個體實施所表述的道德行為的可能性程度, 道德判斷是通過個體對實施反社會行為或拒絕親社會行為的認知來測量, 道德意向與道德判斷共同組成了個體的道德認知。 研究還發現,無論是一般情境還是體育情境,道德意向、道德判斷、道德行為均與親社會-反社會行為存在顯著相關。
目前,有研究發現情緒是影響個體道德認知水平的因素[11-14],情緒會影響個體的親社會行為[15-17],并且道德認知水平可能會影響個體的反社會行為[10,18]。 因此,道德認知可能在認知情緒調節與親社會-反社會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據此,將引入體育道德認知作為中介變量,將認知情緒調節作為自變量、親社會-反社會行為作為因變量,探討在體育情境中道德認知對親社會-反社會行為的作用。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1)認知情緒調節、體育道德認知與運動親社會-反社會行為之間存在顯著相關;2)體育道德認知在認知情緒調節與運動親社會-反社會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通過本研究,認識體育專業大學生的認知情緒調節方式,了解其道德認知發展水平狀況,探討其在體育競賽過程中親社會-反社會行為的產生機制。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本研究選取某體育高校500 名體育專業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431 份有效問卷,問卷的有效率為86.2%。 共有男性 332 人(77.03%),女性 99 人(22.97%)。 被試的平均年齡 19.78 歲(SD=1.21),平均運動年限 5.02 年(SD=2.78)。研究對象是來自于籃球、排球、羽毛球、啦啦操、武術、田徑等運動專項的體育專業大學生, 其中, 國內健將6 人(1.39%), 一級運動員 14 人 (3.25%), 二級運動員 74 人(17.17%),三級運動員18 人(4.18%),暫無運動員等級或運動等級已過期者319 人(74.01%)。
1.2 研究工具
1.2.1 認知情緒調節的測量
認知情緒調節的測量采用董光恒等[19]修訂的簡化版認知情緒調節問卷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適用于初高中生或大學生群體。 該問卷包含18 道題目,分為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分量表(PCER)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分量表(NCER)。 其中,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包括接受、重新關注計劃、積極重新關注、積極重新評價和正視現實5個維度,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包括自我責備、責備他人、沉思和災難化4 個維度。 該問卷采用Likert5 點計分,1 表示“從不”,5 表示“一直如此”,分量表的得分越高表示個體越傾向于采用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或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本次研究兩個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數為0.80 和0.75。
1.2.2 體育道德認知的測量
祝大鵬等[10]編制的道德意向、判斷和行為測量問卷,分為體育道德和一般道德兩種情境。 問卷的計分采用Likert7 點計分,總共24 個條目。 本研究僅采用體育情境中道德意向和道德判斷部分問卷來測量體育道德認知, 并將體育道德認知劃分為親社會道德認知和反社會道德認知兩個維度。 本次研究測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數為 0.52。
1.2.3 運動親社會-反社會行為的測量
體育競賽中親社會行為和反社會行為的測量采用祝大鵬[18]在中國文化背景下修訂的運動親社會行為與反社會行為(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Sport Scale,PABSS) 的中文版量表, 包括運動親社會行為與運動反社會行為兩個分量表,總共23 個條目。 該量表采用Likert5 點計分,1 表示“從來沒有”,5 表示“非常多”。 中文版 PABSS 總量表及 4 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系數)均在 0.78~0.89 之間,信度較好; 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4 個因子可以解釋方差總變異的62.53%,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該量表的擬合指數 (χ2/df =3.25,GFI=0.93,CFI=0.90,RMSEA=0.04,IFI=0.92,NNFI=0.92)較理想,結構效度較好。 本次研究測量的運動親社會行為與運動反社會行為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3、0.88。
1.3 研究程序
通過在班級上發放紙質問卷與收集問卷,由被試自愿、匿名填答。 研究使用SPSS 24.0 進行數據分析。 首先,使用SPSS 24.0 統計各變量的分布情況,進行差異檢驗與相關分析;然后使用SPSS 插件PROCESS 3.3 對研究假設中的中介作用進行檢驗。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自陳報告法收集數據,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 CMB)。 采用 Harman 單因子檢驗,即對所有變量的項目進行未旋轉的主成分因子分析。 結果表明,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6.89%,低于40%的臨界值。因此,本研究的數據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差異檢驗
為了檢驗體育專業大學生運動親社會-反社會行為的性別差異, 研究對不同性別體育專業大學生在運動親社會-反社會行為維度上的得分進行獨立樣本t 檢驗。 表1 結果表明,在運動親社會行為上, 體育專業男大學生的得分顯著高于女大學生(p<0.01);在運動反社會行為上,體育專業男大學生的得分也顯著高于女大學生(p<0.001)。

表1 不同性別體育專業大學生的運動親社會-反社會行為差異的 t 檢驗(n=431)
2.3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表2 列出了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矩陣。 結果顯示,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與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親社會道德認知、運動親社會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與反社會道德認知、運動親社會行為、運動反社會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親社會道德認知與反社會道德認知、運動反社會行為存在顯著負相關, 與運動親社會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反社會道德認知與運動反社會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運動親社會行為與運動反社會行為存在顯著負相關。 研究假設得到初步支持。

表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矩陣(n=431)
2.4 中介效應檢驗
2.4.1 親社會道德認知的中介作用
表3 結果表明, 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運動親社會行為的影響、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親社會道德認知、親社會道德認知對運動親社會行為的影響均顯著,并且,親社會道德認知在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與運動親社會行為之間可能起中介作用。

表3 親社會道德認知中介模型的回歸分析(標準化)
對中介效應進行Bootsrap 檢驗,重復取樣5 000 次,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及置信區間的估計, 若95%的置信區間不包括0,則表明間接效應顯著。 表4 結果表明,親社會道德認知在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運動親社會行為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模型見圖 1)。

表4 親社會道德認知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分析

圖1 親社會道德認知的中介作用
2.4.2 反社會道德認知的中介作用
表5 結果表明, 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運動反社會行為的影響、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反社會道德認知、反社會道德認知對運動反社會行為的影響均顯著,并且,反社會道德認知在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與運動反社會行為之間可能起中介作用。

表5 反社會道德認知中介模型的回歸分析(標準化)
對中介效應進行Bootsrap 檢驗,重復取樣5 000 次,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及置信區間的估計, 若95%的置信區間不包括0,則表明間接效應顯著。 表6 結果表明,反社會道德認知在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運動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模型見圖 2)。

表6 反社會道德認知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分析

圖2 反社會道德認知的中介作用
3 討論
3.1 運動親社會—反社會行為狀況
有研究表明[20-21],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程度的共情能力,表現出更多利他、匿名、情感上的親社會行為,但表現出更少公開的親社會行為,而男生表現出更多的公開的親社會行為。因而,在公開場合,如體育情境中發生摔倒、受傷等情況時,體育專業男大學生為了獲得他人認可,往往會給予他人幫助。 本研究結果仍舊印證了前人的理論基礎。
在運動反社會行為上, 體育專業男大學生的得分也顯著高于女大學生。 有研究發現[22],運動員在角色社會化過程中,男性表現出的粗野、 侵犯行為比女性更容易被他人和社會文化所接受。 在一般社會情境,無論是言語攻擊還是肢體攻擊,通常男性比女性的攻擊性與侵犯性更強; 而在處于體育競賽情境,雙方運動員具有很多肢體接觸,男性也更容易產生言語攻擊與肢體攻擊。
3.2 認知情緒調節、體育道德認知及運動親社會—反社會行為間的關系
研究結果表明,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親社會道德認知、運動親社會行為兩兩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反社會道德認知、運動反社會行為兩兩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前人研究[11,23]表明,個體的積極情緒能夠促進道德認知加工, 有利于提高道德判斷準則與決策, 進而提高道德認知水平,本研究結果與之相符。 因而,在體育情境中,運動員處于積極情緒狀態下,易于采取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進而啟動親社會道德認知加工方式;反之,運動員處于消極情緒狀態下,易于采取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 進而啟動反社會道德認知加工方式。
道德認知能力較高的個體會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16],道德判斷水平較低的個體表現出更多的反社會行為[17],本文研究也發現,在體育情境中的體育道德認知與親社會-反社會行為聯系密切。 因此,研究結果初步驗證了研究假設1。
3.3 體育道德認知在認知情緒調節對運動親社會—反社會行為間的中介作用
研究引入體育道德認知作為中介變量, 探討了認知情緒調節與運動親社會-反社會之間的作用。 通過PROCESS 檢驗可知:1)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正向預測親社會道德認知,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正向預測反社會道德認知;2) 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正向預測運動親社會行為, 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正向預測運動反社會行為;3) 親社會道德認知正向預測運動親社會行為,反社會道德認知正向預測運動反社會行為。 總言之, 親社會道德認知在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運動親社會行為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反社會道德認知在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運動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研究結果驗證了研究假設2。
由此可見, 傾向于采用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體育專業大學生,能夠更加積極地關注、評價與分析事件,對糟糕的事情接受度更高,更能夠妥善處理和改善自己的負性情緒,易于采取親社會道德認知加工方式, 在體育情境與體育競賽過程中,表現出諸如鼓勵隊友、幫助受傷的隊友或對手等親社會行為。 相反,傾向于采用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體育專業大學生,對待所發生的糟糕事件的態度更為消極,認知方式與應對方式較為被動、悲觀,甚至產生自我責難或是責難他人的想法,易于采取反社會道德認知加工方式,在體育情境與體育競賽過程中,表現出責難隊友、辱罵隊友或對手等反社會行為。
因此, 體育專業大學生應當學會積極的認知情緒調節與應對方式,提高自己的道德認知水平,在體育賽場上更多地鼓勵自己、鼓勵他人,幫助其他運動員,減少言語攻擊與肢體攻擊。
4 結論
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 親社會道德認知與運動親社會行為三者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 反社會道德認知與運動反社會行為三者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親社會道德認知在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運動親社會行為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反社會道德認知在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對運動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