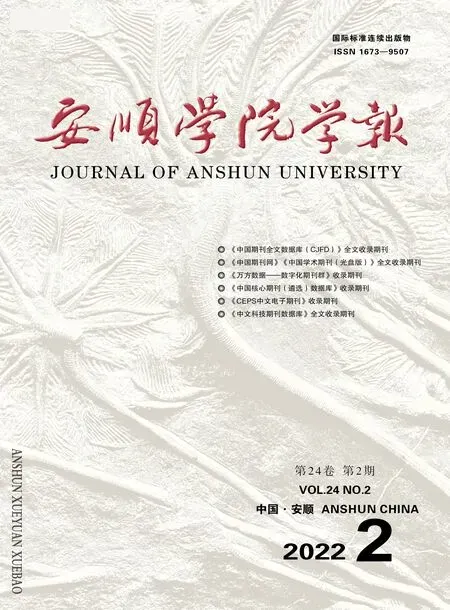何以顛覆
——對(duì)孫兆霞、張建論貴州屯田制度主要觀點(diǎn)的商榷
林 芊
(貴州大學(xué)歷史與民族文化學(xué)院 貴州 貴陽(yáng)550025)
孫兆霞、張建著《地方社會(huì)與國(guó)家歷史的長(zhǎng)時(shí)段型塑——〈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價(jià)值初識(shí)》一文,載《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年第5期。本文將其簡(jiǎn)稱(chēng)為“《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價(jià)值初識(shí)”,為行文敘述方便,再簡(jiǎn)稱(chēng)為孫文。
一、“《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價(jià)值初識(shí)”主要觀點(diǎn)
《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出版,在表現(xiàn)貴州明清時(shí)期契約文書(shū)的諸多文獻(xiàn)中,是僅次于《清水江文書(shū)》出版后的又一個(gè)文獻(xiàn)匯編,對(duì)于明清時(shí)期貴州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研究當(dāng)有重大意義。明史專(zhuān)家萬(wàn)明在為該書(shū)所寫(xiě)序言中指出了吉昌文書(shū)在研究屯堡社會(huì)的重要價(jià)值:“關(guān)于安順屯堡研究的突破性的發(fā)現(xiàn)和進(jìn)展”,“對(duì)于探討屯保社會(huì)實(shí)態(tài)具有重要價(jià)值”。[1]也如該匯編“前言”所說(shuō),吉昌契約文書(shū)的發(fā)現(xiàn)“填補(bǔ)了我國(guó)屯田制度地權(quán)變遷及影響的民間史料空白”[2]4。
在閱讀《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時(shí),對(duì)為何匯編將田地買(mǎi)賣(mài)契約以科田、秋田、水田/秧田、旱地/陸地等類(lèi)分進(jìn)行編排方式產(chǎn)生不解。當(dāng)時(shí)出版并影響很大的《清水江文書(shū)》(第一輯),是采取編戶(hù)為綱,再以時(shí)間為目,而《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卻是采用土地品質(zhì)為綱,不惜打亂作為史料的民間契約文書(shū)最珍貴的歸戶(hù)性進(jìn)行分類(lèi)編排的處理方式。當(dāng)再讀孫兆霞《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所寫(xiě)“前言”后,似乎感覺(jué)哪兒不對(duì)?于是找到孫兆霞、張建合著論文“《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價(jià)值初識(shí)”一文,閱讀后感覺(jué)似乎背后與有意識(shí)地定位以突出吉昌契約文書(shū)的屯田性質(zhì)有關(guān);同時(shí),又驚異于作者從學(xué)科和學(xué)理視角去認(rèn)識(shí)這批民間史料的重要價(jià)值初衷下,所論證的結(jié)論及終極評(píng)價(jià):“這意味著一個(gè)根本性的顛覆:至清末, 明代屯田制僅僅是政治、軍事功能的消解,而土地所有權(quán)制涉及的經(jīng)濟(jì)體制并未消解。對(duì)屯堡社區(qū)而言,明代屯田制僅僅是‘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①,這肯定是目前貴州軍屯史研究的一個(gè)新異觀點(diǎn)。
明代晚期,屯田開(kāi)始瓦解,至清康熙時(shí)改衛(wèi)為縣,軍屯制度已消失,與之相關(guān)系的屯田制度也隨之消解,是學(xué)界的基本觀點(diǎn)而成為共識(shí)。孫文提出的“一個(gè)根本性顛覆”的不同主張,主要反映在論文“《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價(jià)值初識(shí)”“填補(bǔ)了我國(guó)屯田制度地權(quán)變遷及影響的民間史料空白”一節(jié)。孫文對(duì)問(wèn)題的論證表述比較迂回復(fù)雜,但就其核心或者關(guān)鍵,不外是軍屯屯田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為此論證出兩個(gè)觀點(diǎn):第一,乾隆嘉慶以來(lái)的吉昌契約文書(shū)反映,以“屯田”名稱(chēng)存在的田產(chǎn)并非私田;第二,屯田并未進(jìn)入田地買(mǎi)賣(mài)市場(chǎng)而自由買(mǎi)賣(mài)。孫文的二個(gè)論點(diǎn)顯然是要顛覆“軍屯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是否如王毓銓等明代軍屯研究專(zhuān)家所說(shuō), 已經(jīng)從國(guó)有變?yōu)樗接小边@一史學(xué)界的基本共識(shí)。
就第一個(gè)論點(diǎn),孫文的舉證是征引道光七年安平縣縣令劉祖憲公文《安平縣田賦論》為重要論據(jù)。如孫文敘述道:“安平田有兩種:一曰屯田,每三畝八分科,納糧米一石;一曰科田,每畝應(yīng)納糧米五升四合。屯田由官所給,科田則民所自量,固賦之輕重懸殊至于如此也。又同文‘附錄前任徐升縣清理田賦稟稿’言:‘迄康熙二十六年, 改衛(wèi)設(shè)縣, 糧額仍依衛(wèi)制, 取足于屯軍百戶(hù)。而各百戶(hù)尚有所墾之余糧, 以輔足正額, 比歷來(lái)糧賦, 并無(wú)永久之緣由也’”。對(duì)此孫文的理解和結(jié)論是:“兩段文字皆透露出安平縣(平壩縣)原有屯田在賦稅量上‘仍依衛(wèi)制’;在土地所有權(quán)上,仍歸官田(國(guó)有),沒(méi)有發(fā)生實(shí)質(zhì)性的變化。吉昌文書(shū)‘迂回’證明此制度安排沿襲到民國(guó)”。
孫文第二個(gè)論點(diǎn)證據(jù)是:“‘汪公會(huì)記錄’中的 205塊田塊坐落地與吉昌村‘一等田’完全重合, 約 340畝或 410 畝,是原立主不可買(mǎi)賣(mài)田。”據(jù)此斷定“汪公會(huì)記錄”所載田地是明代以來(lái)的屯田:“光緒十年(1885)仍記錄在案于汪公會(huì)記錄中的‘屯田’在產(chǎn)權(quán)上仍屬‘官田’,‘戶(hù)主’與其為佃耕關(guān)系;此‘屯田’所載田賦仍按屯田一‘分’納糧四石的‘衛(wèi)制’施行”。
由于孫文認(rèn)為吉昌文書(shū)顯示出官田性質(zhì)的屯田存在,于是進(jìn)一步推論“意味著……至清末,明代屯田制僅僅是政治、軍事功能的消解, 而土地所有權(quán)制涉及的經(jīng)濟(jì)體制并未消解”,“明代屯田制僅僅是‘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概念成為孫文的又一個(gè)核心論點(diǎn)。
孫文的兩個(gè)論證過(guò)程及“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概念,否定了傳統(tǒng)研究“待清王朝將衛(wèi)所改為州縣時(shí),明代的軍屯在原屯堡區(qū)早已名存實(shí)亡”的結(jié)論。其實(shí),孫文的兩個(gè)論證得出的結(jié)論及“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概念,皆不成立②。
二、孫文征引論據(jù)不能證明“屯田”仍然公有與不可買(mǎi)賣(mài)
就第一個(gè)論證而言,孫文顯然是針對(duì)“軍屯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是否如王毓銓等明代軍屯研究專(zhuān)家所說(shuō), 已經(jīng)從國(guó)有變?yōu)樗接小薄5y于理解的是,孫文并沒(méi)有從《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找到證據(jù)去顛覆該論斷,而是征引安平縣(今平壩縣)縣令劉祖憲(道光元年至七年在任)公文《安平縣田賦論》為重要論據(jù),孫文引述道:“安平田有兩種:一曰屯田,每三畝八分科,納糧米一石;一曰科田,每畝應(yīng)納糧米五升四合。屯田由官所給,科田則民所自量,固賦之輕重懸殊至于如此也。又同文‘附錄前任徐升縣清理田賦稟稿’言:‘迄康熙二十六年, 改衛(wèi)設(shè)縣, 糧額仍依衛(wèi)制, 取足于屯軍百戶(hù)。而各百戶(hù)尚有所墾之余糧, 以輔足正額, 比歷來(lái)糧賦, 并無(wú)永久之緣由也’”。由此認(rèn)為劉祖憲所言,證明道光時(shí)還存在著屯田制度;而《徐升縣清理田賦稟稿》所講到“糧額仍依衛(wèi)制”,據(jù)此認(rèn)為在土地所有權(quán)上,屯田“仍歸官田(國(guó)有)”,沒(méi)有發(fā)生實(shí)質(zhì)性的變化。那么,兩位縣令公文就很關(guān)鍵了。兩縣令公文是怎樣闡述屯田制度的存在呢?
孫文所引劉祖憲《安平縣田賦論》及《附錄前任徐升縣清理田賦稟稿》兩公文,均收載于道光年間編纂成書(shū)的《安平縣志》卷之四《食貨志》。《安平縣田賦論》是道光七年(1827年)劉祖憲處理“黃大甫控告李上仁縮糧案”時(shí),引發(fā)出來(lái)的一個(gè)整治賦稅的報(bào)告;所謂“縮糧”,即是非法將原屯田田賦偷換成科田的“科則”繳納田賦。劉祖憲報(bào)告主要內(nèi)容是:首先指出這是長(zhǎng)期存在的混亂現(xiàn)象,尤其是“黠猾改屯作科”加深了這一社會(huì)矛盾,原因在于征收賦屯田與科田(民田)稅額不同:“安平田有二種:一曰屯田,每三畝八分科,納糧米一石;一曰科田,每畝應(yīng)糧米五升四合。屯田為官所給,科田則民所自墾,故賦之輕重懸殊至于如此也”。雖然自康熙九年(1670年)以來(lái)經(jīng)過(guò)多次清田整頓,形成了《田賦清冊(cè)》等規(guī)范文件,《田賦清冊(cè)》“只有柔(遠(yuǎn))東西民人尚存其半,而縣署及左、右、中、前、后五所無(wú)一存者”,造成解決問(wèn)題的困難。為此,劉祖憲認(rèn)為現(xiàn)在解決問(wèn)題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丈量計(jì)畝攤糧”,辦法是“其有未經(jīng)變改之田,各為清出。如此戶(hù)今年納屯糧若干,科糧若干,至明年減納若干,即追問(wèn)買(mǎi)主,令其過(guò)割入戶(hù)。是屯是科,各無(wú)混淆”,“著令戶(hù)書(shū)毋惜一時(shí)之勞,年為登記”。[3]
讀劉祖憲《安平縣田賦論》全文,其實(shí)是得不出孫文的結(jié)論的。劉祖憲報(bào)告核心是討論“平賦”(丈田均賦)問(wèn)題,就是針對(duì)在將屯田改為民田后,原屯田與科田(軍屯與民屯)在征收田賦上的差別所引發(fā)的紊亂。然后提出解決方案或思路。顯然,劉祖憲是在討論怎樣平賦問(wèn)題時(shí),為追索原因而回溯了明代田制中的屯田與科田的賦役制度,而非是說(shuō)道光時(shí)屯田制度還存在。孫文是將回憶過(guò)去的表述當(dāng)成了現(xiàn)在時(shí)。相反的是,在劉祖憲文稿中講到賦稅混亂原因時(shí),明確指出是“科田皆為屯田所改”“蓋從前改屯作科之田”;是“科田之價(jià)十?dāng)?shù)倍于屯田者,正以糧輕之故”。前者無(wú)異于表明屯田已科田化,或與民田一樣已“私有化”,后者則表明與“科田”(民田)一樣,屯田可合法地隨意買(mǎi)賣(mài)。劉祖憲報(bào)告本身對(duì)屯田早已買(mǎi)賣(mài)事實(shí)已有描述,如稱(chēng)“人經(jīng)五六代,田經(jīng)八九易手”。可見(jiàn),屯田買(mǎi)賣(mài)早在道光前,就盛行已久。
實(shí)際上,劉祖憲還留下了其他幾件公文,其中《捐設(shè)書(shū)院膏火并城鄉(xiāng)義學(xué)田租詳文》內(nèi)容明確表示屯田改為民田后,已可買(mǎi)賣(mài)。如他為給城鄉(xiāng)義學(xué)籌措資金,自己就指派相關(guān)人士購(gòu)置屯田:“派令素稱(chēng)誠(chéng)謹(jǐn)之生員帥鳳征、鄒凌云等作為首士,買(mǎi)得卑縣所屬之屯田,除全莊及田成一派不計(jì)丘數(shù)外,實(shí)買(mǎi)得田四百四十五丘。”[4]劉祖憲因?yàn)樵诼毱陂g平均賦稅,以解貧民困境,又親自購(gòu)置田產(chǎn)與鼓勵(lì)民間人士購(gòu)置田產(chǎn)資助義學(xué),成為地方敬愛(ài)的父母官,因此被譽(yù)為“縣第一賢宰”[5]。
至于孫文所提到的《附錄前任徐升縣清理田賦稟稿》,是指附錄于(道光)《安平縣志》卷之四《食貨志》一章“附錄”收載的《前任徐升縣清理田賦稟稿》[6]。稟稿作者是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任安平縣令的徐玉章,因政績(jī)有聲,旋升為興義府知府。徐玉章任職安平縣期間,面臨田賦征收中田賦不均社會(huì)問(wèn)題,在追索田賦混亂原因時(shí)講到:“迨康熙二十六年改衛(wèi)設(shè)縣,糧額仍依衛(wèi)制”,于是向上級(jí)部門(mén)提交《清理安平田賦稟》的公文。公文列出改制后田賦征收中出現(xiàn)的幾種弊端,如上田改為下則科田、改易地名混淆縮額、有將額糧佃與窮苗將租納糧而本名下雖田連阡陌卻“額糧無(wú)多”、有逃亡故絕而糧差及鄰族代為賠墊等現(xiàn)象。然后提出“丈田均賦,共樂(lè)輸將”的治理弊端政策,并請(qǐng)準(zhǔn)著手進(jìn)行的“魚(yú)鱗冊(cè)籍雇募算手造,給印單,并丈勘年限”等事務(wù)及經(jīng)費(fèi)開(kāi)支。
實(shí)際上,徐玉章稟稿基本意義與后來(lái)的劉縣令公文性質(zhì)基本相同。稟稿中所述“糧額仍依衛(wèi)制”,如同劉祖憲《安平縣田賦論》對(duì)明代屯田制度的回溯那樣,并不能視為屯田制度存在的依據(jù),只是說(shuō)改衛(wèi)為縣后,屯田改科田后還是按照原來(lái)的屯田稅率征收田賦,并指出這一方式易于為人所利用而帶來(lái)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混亂。因此徐玉章提出解決措施是:“而屯衛(wèi)既裁,似可裁去屯田名目,按照上、中、下三則計(jì)畝均攤。俾富戶(hù)不致詭寄,而貧民得以樂(lè)生,似以地方實(shí)有裨益”。《清理安平田賦稟》不僅直接講到屯田制度已改為民田事實(shí),還指出了屯田成為私產(chǎn)可以買(mǎi)賣(mài):“惟是改衛(wèi)設(shè)縣以后,屯科田畝均屬私業(yè),例得買(mǎi)賣(mài)。”屯田買(mǎi)賣(mài)已導(dǎo)致了“窮軍窮苗田園賣(mài)盡”現(xiàn)象。
清丈屯田科田,消除“改屯作科”及其他田賦征收出現(xiàn)的弊端,健全《田賦清冊(cè)》以絕后患,是劉、徐兩縣令公文的基本內(nèi)容。完全是針對(duì)屯田改制后遺留下來(lái)的田賦征收方面的差別現(xiàn)象,并未有孫文所謂制度上保存了賦役制度等事實(shí);屯田的私有化及法定的自由買(mǎi)賣(mài)事實(shí),屯田制度作為一種 “公有”經(jīng)濟(jì)制度,包括田賦征收制度在內(nèi),都已隨康熙時(shí)期衛(wèi)所撤銷(xiāo)而消失,關(guān)于這一事實(shí)在本文第四節(jié)的論述中將會(huì)提到。
三、屯田私有(民田化)可以買(mǎi)賣(mài)事實(shí)例證
就第二個(gè)論證而言,也難以成立。孫文的基本論證是以民間契約文書(shū)為證據(jù),主要是一件收入《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并命名為《汪公會(huì)記錄》的文書(shū),確信它“為明朝衛(wèi)所屯田制的承繼信息”,支撐起了孫文第二個(gè)論點(diǎn)。首先,以《汪公會(huì)記錄》80條田產(chǎn)中13條有“絕軍糧四石安佃”的記載[2]418-423,對(duì)應(yīng)著“一分”屯田的田賦,且田賦額與“屯田”四石子粒相對(duì)應(yīng),有暗示出“屯田”土地所有權(quán)仍歸官有,由此斷定80條田產(chǎn)是官田性質(zhì)的屯田;其次,80條田產(chǎn)記錄涉及205塊田,其坐落地與吉昌村“一等田”③完全重合,因“一等田”是屯田,是“原立主”不可買(mǎi)賣(mài)田。故至此時(shí)(至光緒朝)屯田不能買(mǎi)賣(mài)。
以《汪公會(huì)記錄》文書(shū)80條田產(chǎn)記錄“為明朝衛(wèi)所屯田制的承繼信息”作為仍然是“公有”屯田而不能買(mǎi)賣(mài)的證據(jù),是難以成立的。首先,《汪公會(huì)記錄》80項(xiàng)田產(chǎn)不是田地買(mǎi)賣(mài)契約,不能作為有無(wú)買(mǎi)賣(mài)關(guān)系的證據(jù)。《汪公會(huì)記錄》是在收集契約文書(shū)時(shí)從當(dāng)時(shí)吉昌村“汪公會(huì)”取得的一份文書(shū),從內(nèi)容看,原件絕非田地買(mǎi)賣(mài)契約,也無(wú)相關(guān)田地買(mǎi)賣(mài)的只言片語(yǔ),更像一件田產(chǎn)登記文書(shū)。其次,將《汪公會(huì)記錄》登記田產(chǎn)視為屯田,也無(wú)事實(shí)根據(jù)。如果視《汪公會(huì)記錄》為田產(chǎn)簿記冊(cè),除幾條“糧四石”可以斷定是屯田性質(zhì)的田產(chǎn)外,其余皆無(wú)判斷是屯田、還是科田或者秋田的信息,何以將其確定全是“官有”的屯 田?再次,“汪公會(huì)所承擔(dān)的由國(guó)家對(duì)官田實(shí)施基層管理的職能”僅是一個(gè)推測(cè),孫文寫(xiě)道:“吉昌契約文書(shū)中汪公會(huì)記錄中, 記錄了‘屯田’地塊、人戶(hù)、賦糧的內(nèi)容, 可將此理解為汪公會(huì)所承擔(dān)的由國(guó)家對(duì)官田實(shí)施基層管理的職能”。問(wèn)題是,汪公會(huì)是怎樣代理國(guó)家管理屯田的④,并無(wú)史事證實(shí),只是一個(gè)內(nèi)循環(huán)自證的邏輯推論——先入為主地視《汪公會(huì)記錄》所記之田為公田(屯田),由此派生出“汪公會(huì)所承擔(dān)的由國(guó)家對(duì)官田實(shí)施基層管理的職能”;如果進(jìn)行推論,那么《汪公會(huì)記錄》所記之田還有可能是“汪公會(huì)”本會(huì)田產(chǎn)。長(zhǎng)期研究屯堡社會(huì)的專(zhuān)家呂燕平就指出,汪公會(huì)“舊時(shí)曾經(jīng)有廟田”[7],作為會(huì)產(chǎn)的田地來(lái)源可以是接受社會(huì)捐贈(zèng),或者汪公會(huì)自行購(gòu)進(jìn),都是可能的。《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內(nèi)就收載有幾件涉及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等時(shí)期的汪公會(huì)買(mǎi)賣(mài)田產(chǎn)契約。最后,《汪公會(huì)記錄》登記田產(chǎn)戶(hù)主中的汪廷興、汪朝禮、汪朝賢、汪仲德等(僅以汪姓為例——引者注),在《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里就有田產(chǎn)買(mǎi)賣(mài)行為。就上述情形而言,將《汪公會(huì)記錄》作為官有而不能買(mǎi)賣(mài)的屯田證據(jù),嚴(yán)重缺乏公信力。
由于孫文基本論證是以民間契約文書(shū)為主體,本文也征引民間契約文書(shū)作出回應(yīng)。《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中沒(méi)有屯田買(mǎi)賣(mài)契約,不等于貴州明代軍屯其他地區(qū)沒(méi)有。清水江流域的田地買(mǎi)賣(mài)契約文書(shū)中,就夾雜著許多乾隆朝以來(lái)屯田買(mǎi)賣(mài)契約。如貴州東部三穗縣滾馬鄉(xiāng)上德明村楊家大院就遺存有許多屯田買(mǎi)賣(mài)契約,如下就是其中一件:
立賣(mài)田契人楊秀倫、子再鎰。情因空乏無(wú)銀使用,自愿將到先年得買(mǎi)堂堂兄歇?dú)馓淋娞锶龍w、外二坵,東抵河溝,南抵再立田,西抵秀成田,北抵再欽田;坎上長(zhǎng)田一坵,東抵秀成田,南抵再立田,西抵坎,北抵秀成與再欽田,四至分明。共花十纂,載軍糧二升一合五(勺),憑中出賣(mài)與族侄楊淳耀名下承買(mǎi)。議定價(jià)銀六十兩整,親手領(lǐng)晚。自賣(mài)之后任從買(mǎi)主子孫永遠(yuǎn)管業(yè),恐后無(wú)憑,立賣(mài)契一紙為據(jù)。
憑中堂兄再錢(qián)(花押)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十日立賣(mài)契人秀倫(花押),子再鎰?dòng)H筆(花押)[8]17
該次出售的“歇?dú)馓淋娞锶龍w”,顯然是屯田性質(zhì)。滾馬鄉(xiāng)上德明村在明代是得明堡,自明洪武時(shí)代起,又是湖廣鎮(zhèn)遠(yuǎn)衛(wèi)軍管地,在此駐軍屯田設(shè)得明堡,直到康熙十年(1671年)隨“改衛(wèi)入府”才裁撤得明堡,得明堡融入鎮(zhèn)遠(yuǎn)府邛水長(zhǎng)官司,屯田改為民田。上引契約即是屯田改民田后自由買(mǎi)賣(mài)的事例,而且從其中所述“先年得買(mǎi)堂堂兄歇?dú)馓淋娞锶龍w”一句,可知田權(quán)已經(jīng)是第二次轉(zhuǎn)讓?zhuān)砻髟诖未宿D(zhuǎn)賣(mài)之前屯田就已在自由買(mǎi)賣(mài),之后一如既往地自由買(mǎi)賣(mài),如下一件文書(shū)所述:
立賣(mài)田契人楊秀倫、子再欽。情因生理缺少本艮,父子商議自愿將到欽受他名下歇?dú)馓量蚕萝娞镆粓w,載糧二升一合五勺,計(jì)花七十五纂,將來(lái)出賣(mài),上門(mén)問(wèn)到族孫政彰弟兄名下承買(mǎi)。三面議定賣(mài)價(jià)艮(銀)五十兩整,當(dāng)日艮(銀)契兩交,并無(wú)少欠。其田界至東抵河溝,南抵本買(mǎi)主田,西抵再傳田,北抵坡,四至分明。自賣(mài)之后任從買(mǎi)主永遠(yuǎn)管業(yè),恐后人心不古,立賣(mài)契一紙為據(jù)。
內(nèi)涂一字天一字
堂弟再錢(qián)(花押)
憑中 胞弟再銘(花押)、再益(花押)
子再欽親筆(花押)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立賣(mài)契人秀倫(花押)[8]19
從上德明楊氏家族遺存契約文書(shū)中看到,其田產(chǎn)集中所在地之一除歇?dú)馓镣猓硪惶幗凶鳌拔彘g”的田壩,分為上五間、中五間和下五間,契約文書(shū)中皆稱(chēng)其田地為軍田(屯田)。同治十二年(1873年)楊昌燕編制家庭田產(chǎn)簿冊(cè)時(shí),就將一部分田產(chǎn)契約文書(shū)匯集取名《軍田契薄》[9]。德明村清代屯田買(mǎi)賣(mài)并非個(gè)案,在清水江流域土地買(mǎi)賣(mài)契約文書(shū)中都會(huì)看到。
同樣,民間文獻(xiàn)也看到,康熙時(shí)屯田已改制為民田。《迪光錄》是今天黎平縣亮寨司村龍氏家族族譜,編纂于康熙時(shí)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印。《迪光錄》記載其家族祭祀時(shí),內(nèi)中就有“前所,胡世芳注一斗二升,朱克林注一斗;化所,龍秀一注一斗五升”[10]104。今天亮司村轄地,明代設(shè)置有亮司所,緊臨新化所。文中的前所、化所,即是軍屯。康熙以來(lái)“所田”已列在“家族祭祀田”內(nèi),可見(jiàn)此時(shí)屯田早已化為私田。類(lèi)似的記載還有同治三年(1864年)修訂的《迪光錄》內(nèi)“附諸屯”條,記敘龍池屯等13屯在明末改為民田事:“原額屯軍四千五百七十名,永樂(lè)間存七百六十三名,嘉靖間存三百五十名。明未載革,而屯軍皆為土人矣。”[10]348而在龍池屯買(mǎi)賣(mài)契約中,契約多載有“府糧”,標(biāo)志著屯田完全民田化。
綜上所述,作為孫文中心論斷吉昌文書(shū)所顯示出來(lái)的屯田性質(zhì)與不可買(mǎi)賣(mài),顯然是經(jīng)不住史實(shí)驗(yàn)證的論點(diǎn)。只是不解,殊不論貴州其他軍屯地區(qū)歷史文獻(xiàn),為何孫文引征的嘉慶、道光時(shí)期安平縣徐、劉二縣令文稿已講得很明白了,孫文卻認(rèn)定是屯田存在的論據(jù)?
四、 屯堡社區(qū)“(屯田)經(jīng)濟(jì)體制并未消解——明代屯田制僅僅是‘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僅僅是一個(gè)預(yù)設(shè)
孫文將契約文書(shū)研究上升到理解國(guó)家制度安排的高度,無(wú)疑是歷史研究的一項(xiàng)基本任務(wù),其中對(duì)屯田制度的評(píng)價(jià)涉及經(jīng)濟(jì)制度安排。明代屯田制僅僅是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概念,成為孫文又一個(gè)核心觀點(diǎn)。
事與愿違的是,孫文所引征資料皆與其制度安排的預(yù)設(shè)不相符。事實(shí)與邏輯是:作為經(jīng)濟(jì)制度的田制,明代田制是:府縣代國(guó)家(王朝)管理民田,農(nóng)民世有耕作其田;衛(wèi)所代國(guó)家(王朝)管理屯田、科田,屯戶(hù)(旗軍或軍余)世有其田,百戶(hù)代為收納屯籽糧,民屯納衛(wèi)所科糧。清康熙十年(1671年)以及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分別對(duì)貴州衛(wèi)所進(jìn)行改制,原屯田主體旗軍或軍余身份已轉(zhuǎn)化為府縣民人;屯田改為府縣民私有,軍屯屯糧變更為府縣征收田糧。這樣,作為國(guó)家制度,衛(wèi)所政治經(jīng)濟(jì)職能已為府縣取代。因此,從邏輯上看,社會(huì)變革致衛(wèi)所原有政治經(jīng)濟(jì)皆已發(fā)生質(zhì)變。衛(wèi)所無(wú)存,何來(lái)土地所有權(quán)制涉及的經(jīng)濟(jì)體制并未消解?反之,如果屯田經(jīng)濟(jì)體制并未消解,那向誰(shuí)繳納田賦?世有耕作其田者又是什么身份?
梳理史籍及文獻(xiàn),清楚地顯示出清初以來(lái)屯田制度消解的路徑軌跡。簡(jiǎn)而言之,先是從政策上承認(rèn)屯改科(或民)行為,然后從法律文書(shū)上給予確定,最后從國(guó)家制度上確定原屯田私有。從國(guó)家制度安排事實(shí)看,康熙時(shí)期貴州衛(wèi)所改制變更為縣,屯田變更為民田,即是重大的“制度設(shè)計(jì)”。貴州巡撫衛(wèi)既濟(jì)主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編纂成書(shū)的《貴州通志》,就有屯田改制的“路線(xiàn)圖”。從該書(shū)“卷之第五·大事記”便可看到,凡康熙四年(1665)之前,統(tǒng)計(jì)每年新增開(kāi)墾田地時(shí),“題報(bào)”用語(yǔ)往往是“各府縣衛(wèi)新墾荒民屯科田共XX畝”或“民屯田地共XX畝”,而康熙五年(1666年)之后的“題報(bào)”,則一律改寫(xiě)為“各府縣衛(wèi)新墾荒田共XX畝”,取消了屯田或屯田、科田的名目。“題報(bào)”是官文書(shū),“題報(bào)”用語(yǔ)變化,實(shí)際上是屯田變?yōu)槊裉镌谥贫壬弦怨俜轿墨I(xiàn)表現(xiàn)出來(lái),并且還表明,在康熙十年(1671年)改衛(wèi)為縣之前,“題報(bào)”就已對(duì)發(fā)生屯田為民田的事實(shí)予以承認(rèn)。
屯田民田化的改制行為,最突出的事件是編制于康熙四年(1665年)的貴州《賦役全書(shū)》。貴州《賦役全書(shū)》是最權(quán)威的“土地所有權(quán)制涉及的經(jīng)濟(jì)體制”的官方文件,成為解釋和描述貴州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的原則和根據(jù)。所以康熙《貴州通志》在記敘稅田名稱(chēng)時(shí),尊《賦役全書(shū)》為準(zhǔn)則,對(duì)發(fā)生于康熙四年(1665年)之前的新增田地統(tǒng)計(jì)的題報(bào)是“民屯科田”,之后則只記為“新墾荒田”。關(guān)鍵詞的變化,本質(zhì)上是對(duì)屯田改為民田的反映,康熙四年(1665年)貴州《賦役全書(shū)》確定了整個(gè)經(jīng)濟(jì)制度的新變化。
制度新變化更重要的行動(dòng)是康熙十年(1671年)十月貴州巡撫曹申吉疏請(qǐng)裁龍里、平越、都勻、普定、清平衛(wèi),各分別改府縣治。此次改衛(wèi)為縣,吉昌村所在的普定衛(wèi)改制普定縣。在得到批復(fù)后,巡撫曹申吉又疏請(qǐng)新置縣的賦稅征收,由知縣管理“永遠(yuǎn)可行”。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辛亥日“戶(hù)部議應(yīng)如所請(qǐng),從之”[11]。屯田賦稅改為府縣征收,實(shí)際上已完成了田賦征收形式的轉(zhuǎn)換。消解屯田制度的最后一擊發(fā)生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當(dāng)年裁撤了平壩等衛(wèi)所,平壩衛(wèi)改置為安平縣,宣告了屯田制度的消解。乾隆六年(1741年)編纂成書(shū)的《貴州通志》之“食貨志序”對(duì)此言之鑿鑿:“我朝……貴州軍伍屯田,許民間占為永業(yè),不取其值。”[12]軍伍屯田許民間占為永業(yè),這是從國(guó)家制度上明確申明屯田已私有化(民田化)。
綜上所述,從制度上而言,“明代屯田制”在康熙時(shí)代就已經(jīng)廢止。軍戶(hù)的社會(huì)身份由軍衛(wèi)變?yōu)楦h民人,經(jīng)濟(jì)制度上田制由屯田變?yōu)槊裉铮镔x征收主體由衛(wèi)所轉(zhuǎn)變?yōu)楦h,這是一體性的社會(huì)變改。不存在著只是軍衛(wèi)政治、軍事職能變化,其經(jīng)濟(jì)職能還保持著并持續(xù)的屯田公有和不可買(mǎi)賣(mài)。因此,孫文所謂“意味著……至清末,明代屯田制僅僅是政治、軍事功能的消解, 而土地所有權(quán)制涉及的經(jīng)濟(jì)體制并未消解”是不切實(shí)際的推論,因而也不存在“明代屯田制僅僅是‘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
孫文重視制度設(shè)計(jì)對(duì)吉昌文書(shū)進(jìn)行整理與研究是有貢獻(xiàn)的,其中如分析了吉昌文書(shū)史料在型塑屯堡社會(huì)有多重價(jià)值。但一些論點(diǎn)也可商榷。如科田契約與秋田契約都是該文重要論題,但對(duì)其歷史意義作出的解釋?zhuān)埔膊惶N切。譬如孫文分析指出:吉昌契約文書(shū)共 438份,其中土地買(mǎi)賣(mài)、典當(dāng)契約277份,占總數(shù)的 63.2%,而“科田”又有86份,占土地買(mǎi)賣(mài)的31%。因此,“科田”契約的意義在于記錄了其從明朝沒(méi)有買(mǎi)賣(mài)記錄到清雍正以后普遍流轉(zhuǎn)的制度變遷情況。收入進(jìn)《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科田契約最早也只是產(chǎn)生于乾隆朝。實(shí)際上,早在萬(wàn)歷時(shí)期,科田已民田化。這一點(diǎn)萬(wàn)明在為《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所著序言中已明確指出:屯堡社會(huì)存在的“大量科田,在明代已是民田的一種稱(chēng)呼,而曾為明代國(guó)有土地的屯田,到此時(shí)業(yè)已私有化,可以自由買(mǎi)賣(mài)。”[3]乾隆時(shí)期屯田制度壽終正寢已歷五十幾年,而作為民屯的科田,則早在萬(wàn)歷時(shí)已民田化。因而這些契約文書(shū)失去見(jiàn)證屯田變化過(guò)渡時(shí)期的歷史文獻(xiàn)價(jià)值。
五、對(duì)貴州屯田制度消解問(wèn)題的一點(diǎn)思考
如上分析所顯示,無(wú)論是官方文書(shū)如康熙四年(1665年)編制的《賦役全書(shū)》,還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官方編纂的《貴州通志》,已將屯田制度消解過(guò)程揭示出來(lái)。問(wèn)題是,孫文何以仍然持有“土地所有權(quán)制涉及的經(jīng)濟(jì)體制并未消解”的認(rèn)識(shí)呢。閱讀孫文,可以作出判斷的信息是,其問(wèn)題意識(shí)直接針對(duì)“王毓銓等研究軍屯制度”的結(jié)論。王毓銓在《明代的軍屯》一書(shū)中,一個(gè)論證方式是依據(jù)屯田賦稅名稱(chēng)變化邏輯,即從征收方式論證屯田照民田例起科,屯田轉(zhuǎn)變成民田⑤。而孫文則發(fā)現(xiàn)《汪公會(huì)記錄》中13條有“糧四石”屬于屯糧田賦的記錄,似乎可認(rèn)對(duì)王毓銓《明代的軍屯》一書(shū)結(jié)論作出反向回應(yīng),如孫文所分析:《汪公會(huì)記錄》有“‘絕軍糧四石安佃’的內(nèi)容,暗示出‘屯田’土地所有權(quán)仍歸官有”。
實(shí)際上,如上一節(jié)所述,孫文所引《汪公會(huì)記錄》中包含13條“糧四石”在內(nèi)的80條田地視為屯田,嚴(yán)重缺乏公信度,因此建立在其上的推論——“土地所有權(quán)制涉及的經(jīng)濟(jì)體制并未消解”肯定也不可靠。但孫文卻有一個(gè)很重要的貢獻(xiàn),即“潛意識(shí)”地提出了一個(gè)啟示性的問(wèn)題:貴州自明至清屯田制度的消解,制度設(shè)計(jì)上的變化只是一個(gè)方面,還應(yīng)當(dāng)從王毓銓軍屯轉(zhuǎn)化為民田的基本標(biāo)志——屯田“照民田例起科”的關(guān)鍵思路出發(fā),觀察貴州自明至清屯田制度的消解。
據(jù)王毓銓《明代軍屯研究》分析,自嘉靖起,佃種屯田的承種者,其佃種屯田永為己業(yè)這一點(diǎn)已很明確,并推論“軍屯授民記為己業(yè)和屯田子粒改作民糧可能同時(shí)并行……早晚也要改依‘民田’例起科的民糧”[13]368。歷史發(fā)展事實(shí)證明“無(wú)論軍種民種一律照民田例起科”,并得到了崇禎皇帝的批準(zhǔn)。“后來(lái)清皇朝建立,遂廢衛(wèi)所屯田,改隸州縣(即改為‘民田’),就是這個(gè)發(fā)展趨勢(shì)的結(jié)果。”[13]369
《明代軍屯研究》重點(diǎn)是對(duì)北方和腹里軍屯研究,極少著眼貴州軍屯。但貴州軍屯制度變化,實(shí)際上也大致經(jīng)歷著與全國(guó)同步發(fā)生的變化,并且更鮮明地體現(xiàn)出是從屯田改科田的征收方式上開(kāi)辟了消解屯田制度的道路。最早的記錄在嘉靖年間編纂的《貴州通志》中:“因軍數(shù)逃故,田地多荒,而糧仍舊,有司議以軍舍余會(huì)計(jì)認(rèn)種之。后各衛(wèi)所屯田同此。”[14]144表明至少?gòu)募尉笗r(shí)起,貴州各衛(wèi)屯田已層出不窮地發(fā)生“屯改科”事件。嘉靖十三年(1534年)巡按貴州監(jiān)察御史王杏,針對(duì)屯田制度、田賦制度設(shè)計(jì)、屯田制度遭到破壞和解決方案等一攬子問(wèn)題捐,提出了《清理屯田事議》。
《清理屯田事議》可以視為貴州屯田制度的一個(gè)綱領(lǐng)性文件,同時(shí)也是記錄屯田消解的歷史文獻(xiàn)。作為綱領(lǐng)性文件,它概括了貴州屯田的制度規(guī)定:“貴州屯種額例,總旗一名種田二十四畝,小旗一名種田二十二畝,軍人一名種田一十八畝。內(nèi)各以八畝納糧四石,余外皆為會(huì)計(jì)糧田,以給助口食等用。……每分除田八畝招佃,軍余認(rèn)納額糧”。作為記錄屯田消解的歷史文獻(xiàn),首先指出了消解屯田的力量,是從軍余會(huì)計(jì)田上,為改屯為科打開(kāi)缺口;其次,指出了導(dǎo)致會(huì)計(jì)田改科田的產(chǎn)生,一方面是屯軍戶(hù)“殆以逃亡者”,另一方面是“管千、百戶(hù)軍吏、屯頭人等自占耕種,擅行佃典,名為公用,實(shí)歸私囊等因”,兩種現(xiàn)象將本來(lái)是屯田出現(xiàn)困境的一種補(bǔ)救方式的會(huì)計(jì)田,侵占為科田性質(zhì)一樣的私田;再者,以“是皇上浩蕩之仁”為借口,對(duì)侵占屯田為私的行為網(wǎng)開(kāi)一面:“蒙乞戶(hù)部查議,將前項(xiàng)經(jīng)手官員遵依恩詔,悉免治罪”,實(shí)際上從政策上默認(rèn)了改屯為科的合法性。[14]484-485
20年后的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主管屯政的貴州提學(xué)謝東山,面對(duì)軍屯出現(xiàn)的問(wèn)題,幾乎重蹈王杏《清理屯田事議》覆轍。一方面,他面臨著王杏時(shí)屯田破壞的處境:
貴州各衛(wèi)旗軍,上糧屯田俱各八畝。會(huì)計(jì)口食則總旗十六畝,小旗十四畝,軍人一十畝,皆得計(jì)其子粒之輸,以充月糧之入。故旗軍缺一名,則一名之分田有在,屯田遺一分,則一分之花利猶存。往以逃亡者雖缺而解發(fā)者當(dāng)補(bǔ)故,遂忽而置之。及今逃亡益多,解發(fā)益寡,而遺田益眾,管屯人等遂有歲收常貨以致家成鉅積者矣。侵占田土,律有明禁,侵漁之盜可不亟懲?[14]369
另一方面,他隨后在《勘處地方議》的解決方案中的又肯定和承襲了王杏默認(rèn)屯改科做法:
各衛(wèi)正軍雖有逃絕,而余丁尚多,屯田雖多僻遠(yuǎn),而佃戶(hù)頗眾。動(dòng)謂軍伍缺乏、屯田荒蕪者,偽也。大抵余丁多于舊時(shí),而籍口于逃絕;屯田廣于舊額,而籍口于荒蕪。于是丁口為實(shí)閑之資,田糧為私莊之蓄。此各衛(wèi)影射之弊,守巡該道尤宜留心情理者也。[14]360-361
貴州巡撫劉大直則在行政上實(shí)施了謝東山的提議。他主政期間,“查屯荒田,招集軍民商諸人芟穢耕種,許以三年成熟,照數(shù)納糧。則所謂會(huì)計(jì)人役者”[14]147。改屯為科大勢(shì)所趨,軍屯田賦制度的走向是改為科田方式征收。
實(shí)際上,民間文獻(xiàn)也見(jiàn)證了侵吞屯田,再將屯科轉(zhuǎn)為民田后,照民田例起科的事實(shí)。如下列成化二年的契約文書(shū):
永安鄉(xiāng)□□□□□□□細(xì)仔□會(huì)洪武二十二年□□衛(wèi)當(dāng)軍隨營(yíng)住坐,田地拋棄。至□□(天順)六年回籍尋認(rèn)產(chǎn)業(yè)。有□□里□□□□□□□遺丁口甫后至□□□邦禮、覃心亮,備情具告本縣,□□差里長(zhǎng)粟天隆、老人梁漢方,□憑本甲人等詣田□□□等,當(dāng)官退出前后田地與□□□□□白。就憑里老鄰右人等,立寫(xiě)合同傳批與本管里長(zhǎng)粟文海、江耕種。秋糧米一石六斗七升□□□送納。立寫(xiě)合同二紙,在后再不許□□。□田開(kāi)寫(xiě)土名于后。
(后略)
注:錄文中“□”字符為文書(shū)原件中缺損字的指代。
這是一份內(nèi)容較為復(fù)雜的合同書(shū)⑥,但一個(gè)明確的事實(shí)是,原田主人身份為洪武時(shí)期隨營(yíng)坐住;“坐住”是軍人身份,故其田是一份屯田。該屯田在后來(lái)長(zhǎng)期被他人蠶食侵占,最后在成化二年經(jīng)官府“斷案”后,屯田“轉(zhuǎn)批”民人耕種,以民田的形式繳納國(guó)家賦稅:“秋糧米一石六斗七升□□□”。該次事件表明,它不僅是一次屯田殘破后被他人蠶食侵占事件,也在屯田轉(zhuǎn)化為民田過(guò)程中,完成了賦稅照民田例起科的轉(zhuǎn)換。以此為例,表明至少在成化時(shí)期,屯田已有向民田轉(zhuǎn)化事實(shí),并在賦稅征收照民田例起科。
清代賦稅征收屯田照民田例起科,在康熙四年貴州《賦役全書(shū)》中體現(xiàn)出來(lái)。據(jù)《賦役全書(shū)》的規(guī)范,田賦稱(chēng)呼皆一律照統(tǒng)一口徑書(shū)寫(xiě)。因此,康熙《貴州通志》在“卷之第十一 田賦”一節(jié)中,已無(wú)屯田屯糧之名目,全書(shū)寫(xiě)為原額田多少,實(shí)在征米谷多少。如安順府親轄和各州縣原額田共429,740.5畝,糧原額本色米谷64,058.6石。在具體到各州縣的統(tǒng)計(jì)口徑,如普定縣原額田57,312畝,原額本色米。安平縣原額田27,063畝,原額本色米谷6,507.6石。均無(wú)民田、屯田、科田的區(qū)分。后來(lái)在咸豐年間編纂成書(shū)的《安順府志》也記載:康熙十年(1671年)十二月裁普定衛(wèi),設(shè)普定縣與府同城,知府將錢(qián)糧征收之權(quán)下放給普定縣。畝征銀1錢(qián)1分,米1斗1升;原糧為銀2錢(qián),米2斗。此“原糧”,即是未改衛(wèi)前的屯田賦稅額度,將原糧銀2錢(qián)、米2斗改為1錢(qián)1分、米1斗1升,可見(jiàn)已對(duì)屯田民田化的改革,是伴隨著賦稅征收照民田例起科同步進(jìn)行。
從“照民田例起科”思路觀察貴州自明至清屯田制度的消解,有一個(gè)問(wèn)題就不得不加以正視視,就是康熙時(shí)期廢除了屯田制度,照民田例起科,但起科田地卻保留了原屯田稅率,于是在后來(lái)征收田賦時(shí),民田按民田稅率征收田賦,而耕種已經(jīng)私有化了的原屯田者,則仍須按照過(guò)去屯田稅率上糧。這樣,在各地方志食貸志田賦規(guī)定中,往往記為屯田“每畝起科本色秋米二斗六升四合……”,科田“每畝起科本色米一斗兩升二合……”,民田“每畝起科本色米五升三合六勺……”等[16]72-73,出現(xiàn)田賦征收稅率雙軌制現(xiàn)象。
原屯田稅重,科田(民田)稅輕的田賦征收稅率雙軌制,不久便出現(xiàn)了嚴(yán)重問(wèn)題。不法分子利用差率,通過(guò)買(mǎi)賣(mài)將屯田改為民田,以“偷漏”田賦,造成賦稅不均現(xiàn)象,引發(fā)社會(huì)矛盾。直至道光初年的安平縣,由于“邑屯田糧重,鬻田之家貪重價(jià)改屯作科者近豐年矣。此秒不再為清理,則歷年愈久,弊混愈多。”[16]75針對(duì)此弊端,基本解決方式就是查“清丈屯科田畝”,查出“偷漏”田賦。早在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都進(jìn)行了清丈田畝的行動(dòng),但問(wèn)題似乎不曾好轉(zhuǎn),到雍正時(shí)也引發(fā)了雍正七年(1729年)云貴廣西總督鄂爾泰與工部侍郎申大成就此問(wèn)題開(kāi)展的一場(chǎng)討論。先是申大成建議“黔省軍田許照民田一體買(mǎi)賣(mài),每畝上稅銀五錢(qián),給契為業(yè)”,以過(guò)“九卿議復(fù)”,雍正皇帝指示準(zhǔn)行。但在七月,鄂爾泰對(duì)此提出異議,認(rèn)為:“黔省軍田一畝之價(jià)可買(mǎi)民田二畝,應(yīng)納糧賦一畝亦可抵民田二畝,若再征銀五錢(qián),于民生無(wú)益,仰一請(qǐng)豁免。嗣后凡有軍田授受,悉照常例報(bào)稅。”最后雍正皇帝采納了鄂爾泰意見(jiàn):“應(yīng)如所請(qǐng)”。[11]91-92
這次事關(guān)原屯田賦征收政策的調(diào)整,鄂爾泰也僅是提出契稅上優(yōu)惠。不征契稅,只解決了田地買(mǎi)賣(mài)的困境,從政策上鼓勵(lì)了原屯田進(jìn)入市場(chǎng),但并沒(méi)有消除屯稅與民稅雙軌制引發(fā)的弊端問(wèn)題。原屯田自由買(mǎi)賣(mài)不可抗拒,如何調(diào)整田賦稅差,只待后來(lái)的實(shí)踐。雙軌制導(dǎo)致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問(wèn)題積重難返,到嘉慶道光時(shí)期,仍然是讓縣令們頭疼的事情,故出現(xiàn)了上引徐令和劉令“清田均賦”的主張,為此徐提出了“而屯衛(wèi)既裁,似可裁去屯田名目,按照上、中、下三則計(jì)畝均攤”的方案。但是,無(wú)論何種方案旨在針對(duì)“偷漏”田賦或者均田賦問(wèn)題,絕非保護(hù)屯田制度。以至于誤導(dǎo)了孫文“土地所有權(quán)制涉及的經(jīng)濟(jì)體制并未消解”,“明代屯田制僅僅是‘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的認(rèn)識(shí)。
最后,回到本文開(kāi)頭來(lái),對(duì)為何《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以“科田”“秋田”“水田”“旱地”等田地品質(zhì)屬性進(jìn)行分類(lèi)編排方式產(chǎn)生不解,以及“《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價(jià)值初識(shí)”一文的論證過(guò)程中的許多令人不解之處,已有了答案。如果我們理解了孫文寫(xiě)作動(dòng)機(jī)是源于發(fā)現(xiàn)吉昌文書(shū)尤其是《汪公會(huì)記錄》,便立即與軍屯制度研究原有結(jié)論聯(lián)系,如孫文所述“吉昌進(jìn)入地權(quán)交易和未進(jìn)入地權(quán)交易的土地,‘屯田’,田賦額與‘屯田’相對(duì)應(yīng);可交易田則賦額與‘科田’、‘民田’相對(duì)應(yīng)”,就好理解原來(lái)死死盯盯住了吉昌文書(shū)的屯田性質(zhì),其背后意圖就是要“顛覆”舊說(shuō)的沖動(dòng),如《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前言”所表述那樣“使屯田性質(zhì)特征在此初步研究中,有所表現(xiàn)和貢獻(xiàn)”[2]3,于是論證出至清末“國(guó)有”性質(zhì)的屯田而一直存在,且不能買(mǎi)賣(mài)的大問(wèn)題,是與私有的田產(chǎn)如科田等形成鮮明對(duì)比。故在對(duì)契約文書(shū)編排時(shí),為突出這一差異選擇了科田、秋田、水田/秧田與旱地的劃分。
可以說(shuō),孫文是在關(guān)懷屯田制度研究突破性思維下,希望在契約文書(shū)中看到突破性的歷史內(nèi)涵,故產(chǎn)生了“顛覆”舊說(shuō)的眼前一亮之快或者驚喜,從而忽略了首先得對(duì)貴州屯田制度本身的歷史進(jìn)程進(jìn)行周詳梳理與研究,不至于否定了自己的另一個(gè)“直到清朝還出現(xiàn)標(biāo)明‘科田’……或者只是一個(gè)習(xí)慣性的稱(chēng)呼”[2]7的明智判斷。
注 釋?zhuān)?/p>
①孫兆霞、張建:《地方社會(huì)與國(guó)家歷史的長(zhǎng)時(shí)段型塑——〈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價(jià)值初識(shí)》一文載《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年第5期第43頁(yè)。該論文載《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年第5期,第41-46頁(yè),本文以下凡引孫兆霞、張建論文,不再注明引文出處與頁(yè)碼。
②閱讀一些研究吉昌契約文書(shū)的論文,也常引述孫文,對(duì)其顯然不成立的觀點(diǎn)也有察覺(jué),但都沒(méi)有去正面反駁而是采取回避態(tài)度,唯一的商榷對(duì)話(huà)是在毛亦可著《清代衛(wèi)所歸并州縣研究》一書(shū)第三章第二節(jié)“評(píng)孫兆霞等人對(duì)貴州省吉昌屯土地交易的研究”,對(duì)孫文觀點(diǎn)提出三個(gè)方面的質(zhì)疑,但只是從作了簡(jiǎn)約分析(參見(jiàn)毛亦可:《清代衛(wèi)所歸并州縣研究》,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8年版,第169-171頁(yè)),故尚有進(jìn)一步探討之必要。
③此處“一等田”,在《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附錄中解釋為屯田。吉昌屯在1913年前,屬于行政區(qū)劃屬普定縣。據(jù)乾隆時(shí)貴州巡撫愛(ài)必達(dá)編著《黔南識(shí)略》“普定縣”條所載:“田有三等,科糧田為上,秋糧田為中,屯糧田為下。”(羅麗麗點(diǎn)校:《黔南識(shí)略》,載貴州省文史館編《黔南叢書(shū)》第二輯,上,第52頁(yè)。)這里的“上等田”是否與“一等田”對(duì)應(yīng),如果是,那么將一等田屯田視為屯田,顯然有錯(cuò)。
④《吉昌契約文書(shū)匯編》收集契約文書(shū)中,出現(xiàn)“汪王會(huì)”有 3 次,“汪公會(huì)會(huì)首、會(huì)眾”有 4次。表明“汪王會(huì)”會(huì)田參與買(mǎi)賣(mài)行為。
⑤有關(guān)“屯田照民田例起科”問(wèn)題的研究,參見(jiàn)王毓銓《明代軍屯研究》“下篇:明代軍屯上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 九 屯田(軍屯)的‘民田’化”。載《明代軍屯研究》,中華書(shū)局2009年版,第356-369頁(yè)。
⑥文書(shū)來(lái)源于天柱縣檔案館藏。文書(shū)檔案號(hào):全宗號(hào)WS目錄號(hào)TZ持有人覃獻(xiàn)忠 盒號(hào)53。持有人所在地:天柱縣坌處鎮(zhèn)抱塘村二組。對(duì)文書(shū)內(nèi)容的分析,參見(jiàn)林芊:《從明代民間文書(shū)探索苗侗地區(qū)的土地制度———明代清水江文書(shū)研究之三》,載《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