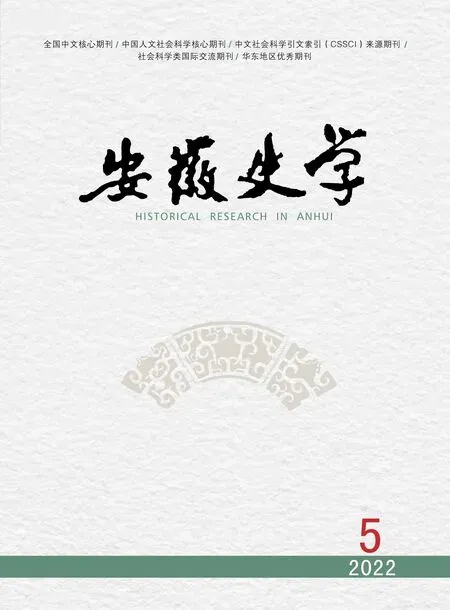走出神話:民國時期高等教育成就的歷史審視
劉 巍
(安徽財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民國時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早期發展階段,在接近半個世紀的動蕩歲月中,高等教育受到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毅然曲折前行。特別是抗戰之際,淪陷區師生跋山涉水,遠赴邊陲,賡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這種可歌可泣的家國情懷值得后人感佩和銘記。
進入21世紀,隨著社會轉型加劇,追憶民國逐漸成為一種頗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在一些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描述中,民國是一個大師輩出的璀璨時代,也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在上述語境里,人們往往懷有一種今昔對比的態度,隱含了對高等教育的現實關懷。誠如當代學者所言:“民國大學熱之所以出現,反映了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發展問題的熱切關心,對高等教育改革的殷切希望,希冀中國高等教育盡快躋身世界一流,期盼中國大學人才輩出、大師紛繁涌現。”(1)寧波:《民國大學絕非都是美好》,《博覽群書》2017年第5期,第29頁。
相對于民間的過分美化,學術界的看法較為謹慎。近年來,不少學者對民國時期的學術水平進行了評判,考察對象側重于人文學科的知識精英。應當說,上述研究對于客觀定位民國學術,具有正本清源的功效。但是,知識精英的學術水平只是衡量高等教育成就的一個維度,無法形成整體觀照;更何況對于學術水平的評價,也往往由于評價者的價值取向和參照對象的不同,極易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情形。例如,葛劍雄認為:“除了個別杰出人物外,總體上遠沒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總體學術水平,已經大大超越了民國時期。”(2)葛劍雄:《被高估的民國學術》,《文匯報》2014年10月17日,第T03版。相反,姜萌則認為:“對清代學術而言,可謂全面超越,對當代學術而言,可謂篳路藍縷,對中國學術而言,可謂承前啟后。”(3)姜萌:《評判民國學術的維度與態度》,《光明日報》2016年3月19日,第11版。歐陽哲生的看法又不相同:“民國學術確不如清代乾嘉漢學,但與后來身陷傳統文化斷裂層的新一代學人相比,其古典遺傳又要豐厚。”(4)歐陽哲生、左玉河、閻書欽、李帆、鄭大華:《多維度視閾下的民國學術發展》,《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1期,第6頁。相比之下,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辦學水平和人才產出等指標,更適合用于評判高等教育的整體成就。有鑒于此,本文擬從上述層面入手,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民國高等教育展開全方位、多角度的祛魅工作,力爭走出神話,揭示真相。
一、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
(一)學校分布失衡
民國初年,高等院校的數量在沿襲清末的基礎上,略有增設,這一時期的高等院校分為大學、專門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從北洋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數據來看,當時高等院校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大學數量少。國立大學僅有北京大學、北洋大學和山西大學,私立大學僅有朝陽大學、中國大學和中華大學。其二,分布不平衡。6所大學中,3所分布在北京,剩下3所分屬天津、太原和武漢。(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教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190、199—203頁。在現代交通工具未能充分發展和普及的情況下,學校分布格局的失衡會加大異地求學的難度。
進入1920年代,高等院校的數量持續增加,尤以大學為主。根據1926年7月的數據,全國共有高等院校92所。其中,大學超過40所,占比接近半數。(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教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190、199—203頁。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降低了大學的設置門檻,引發了“高師改大”和私人辦學的熱潮。但是,這些新增大學多在北平和上海,對于高等院校分布失衡的格局并沒有起到改善作用。(7)《京滬之新大學》,《中華教育界》1924年第14卷第3期,第15—17頁。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等院校分為大學、獨立學院和專科學校。1931年,全國共有高等院校105所。(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教育”(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271、246—247頁。但是,失衡狀態仍然延續,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從高等院校的位置來看,以北平(8所)、上海(9所)為多。其二,從大學生的籍貫來看,以江蘇(6647人)、廣東(5844人)為最。相比之下,青海、西康等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甚至不足10人。(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教育”(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271、246—247頁。有鑒于此,國民政府決定為邊疆學子提供優待政策,將他們引入內地接受高等教育;但是,由于基礎知識薄弱、冒籍現象嚴重和保送名額有限等因素的制約,邊疆地區的高等教育并沒有獲得實質性的進步。(10)劉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邊疆大學生優待政策研究》,《高教探索》2018年第10期,第97—102頁。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東南半壁江山在短期內淪于敵手。大批的東部高校陸續內遷,從而改變了這一時期高等院校的分布格局。1941年,遷往四川的有18所,包括著名的國立中央大學和武漢大學,以及私立復旦大學和金陵大學;云南則擁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和同濟大學。(1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教育”(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5—749、790頁。與此同時,高校的數量也有增長:從全面抗戰爆發前(1936學年度)的108所,增加到抗戰勝利時(1945學年度)的141所,增幅超過30%。(1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教育”(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5—749、790頁。
客觀地看,抗戰時期的高校內遷對于教育資源分布失衡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國立昆明師范學院(今云南師范大學的前身)就是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范學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成華大學、川北大學、中央工校等也是在類似的背景下誕生的。(13)余子俠:《抗戰時期高校內遷及其歷史意義》,《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67—200頁。然而,受制于社會經濟水平的落后,西部地區無法為高等教育提供充分的發展空間。因此,抗戰勝利后不久,內遷高校就開展了大規模的復員工作,高等院校的分布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回歸到抗戰之前的情形。從1947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數據來看,全國高等院校的數量增加到210所,仍以上海(35所)、北平(13所)、廣州(15所)、南京(11所)、天津(9所)等院轄市為主。(1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教育”(一),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24—625頁。
由上可見,民國時期高校數量在整體上呈現出遞增的趨勢,即使在全面抗戰的艱苦年代,也沒有陷入停滯,這是難得可貴的。然而,在分布格局方面,除了全面抗戰時期以外,則始終未能改變失衡的狀態。高教資源長期集中在經濟發達的省(市),中西部地區(特別是邊疆省份)嚴重缺乏,制約了高等教育的普及。
(二)受教人數不足
民國初年,由于高校數量較少,學科單一,招生規模自然受到限制。即使辦學規模最大、學科最為齊全的北京大學,在校生也不足2000人,而且預科生占比過半。至于私立大學和專門學校,招生規模更小,均不足千人(含預科生)。其中,安徽、甘肅、云南等省的法政專門學校在校生僅為數十人,私立朝陽大學和明德大學更是因為經費問題停止招生。(1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教育”,第176—190頁。
此后,隨著高校數量的增加,總體招生規模逐步提升。但是,與同時期的歐美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1931年,中國大學生只有4.4萬余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還不及萬分之一。而人口剛剛過億的美國,大學生數量已經接近百萬,大學生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是中國的70多倍。德國的人口只有中國13.3%,但是大學生的數量已經超過15萬,接近中國的3.5倍。加拿大、英國、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國的大學生數量雖然和中國相仿,但由于這些國家人口少,致使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仍然遠超中國數倍至數十倍之多。(1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教育”(一),第242—245頁。
進入1940年代,高等教育的總體招生規模持續擴大。抗戰勝利時,中國在校大學生人數已經達到80646人,與1936學年度的41922人相比,幾乎翻番。(1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教育”(一),第794—795頁。然而,從普及高等教育的角度而言,這樣的增幅仍然是杯水車薪。1948年,留美歸國的教育家陳炳權慨嘆:“美國大學現有一千七百間,大學生有二百五十萬人以上,而中國的大學只有一百八十余間,大學生只有十三萬人,如果再以美國的一億五千萬人口與中國四億人口比較,我們中國人受教育的機會實在太少了。”(18)吳樺:《訪問陳炳權博士》,《廣州大學校刊》1948年第43期,第10頁。
平心論之,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受教人數不足,并不能僅僅歸咎于高教資源的稀缺,根源在于基礎教育的嚴重落后。科舉制度廢除之后,“無如新教育需費太多,國家富力又極薄弱,斷不能供給這種教育費。中學以上不必說了,單就強迫四年小學教育而論,各省均無力負擔。”(19)方惇頤:《中國教育必須改革的我見》,《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專刊》1933年第1期,第270頁。在這種情況下,“應當作為全部教育樓閣的基礎的小學,論質論量,都是很殘缺。究竟從六歲到十二歲的幼童幾分之幾入學,無從知道。充其量,平均不過百分之二十;在較好的省市或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僻遠區域,幾至全無入學的。入學的幼童之中,許多在學時期太短,不能收時效。中學分初高兩級,共六年,在許多地方,讀畢六年的似乎很少。……因為中等教育之不良,許多大學學生實不能接受大學教育之益。”(20)R.H.Tawney著、蔣廷黻譯:《中國的教育》,《獨立評論》1933年第38期,第12—13頁。由于基礎教育尚且不能惠及更多人,高等教育更加遙不可及。1934年,時任上海市長吳鐵城在圣約翰大學演講時就坦言,“中國教育未普及,文盲遍全國,能受大學教育機會的,已屬萬幸。”(21)吳鐵城:《中國大學生之時代的使命(二)》,《新聞報》1934年7月3日,第19版。教育部也明確表態,“在人人尚不能受國民教育之現在,而欲普及高等教育,事實上尚不可能,因專科以上學校為人才教育。”(22)《此時欲普及高等教育,事實上尚不可能》,《新聞報》1947年9月21日,第7版。
與科舉時代相比,新式教育不僅辦學成本過高,上學費用也顯著增加。(23)羅志田:《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后果》,《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第191—204頁。在政府缺位的情況下,一名學齡兒童在未來求學道路上的發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庭經濟條件。1931年,時任中央大學教授陶希圣指出,“今日的教育仍然是最惠的社會階層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的幾層等級,逐漸把貧苦子弟剔除下來。最貧苦的工農兒童沒有受初級小學教育的機會。”(24)陶希圣:《中國現代教育之定性分析》,《社會與教育》1931年第20期,第306頁。教育家古楳以中山大學及其附屬學校為例,估算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平均開支:小學階段(6年)606元,附中階段(4年)1121.6元,預科階段(2年)830.8元,大學階段(4年)1828元,合計4386.4元。(25)古楳:《中山大學暨附校學生用費的調查(續前期)》,《中華教育界》1930年第18卷第11期,第121頁。對于普通家庭而言,如此規模的教育開銷是難以承受的。盡管官方在高等教育階段采取了一系列獎助學措施,試圖減輕寒門學子的經濟壓力,但覆蓋面和資助力度終究有限。(26)方偉:《南京國民政府前期高等學校獎助學政策(1927—1937)》,《高教探索》2016年第5期,第73—77頁。更何況絕大多數的學齡青年早在少年甚至童年階段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權利,對于他們而言,高等教育資助政策根本沒有實際意義。那些被今人推崇備至的“民國大師”,大多家境殷實,這樣的家庭條件為他們日后的求學深造提供了有力的財力保障。
二、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辦學水平
(一)經費投入有限
作為教育事業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教育經費的投入水平直接關系到辦學機構的正常運轉。遺憾的是,民國時期教育經費的總體投入長期在低水平徘徊。從中央預算來看,北洋政府時期軍閥混戰,軍費開支龐大,教育經費僅占財政支出的1%左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教育經費的比重有所增加,在1929—1936年之間,平均占比為2.62%。全面抗戰爆發后,由于稅源喪失和軍事開支的激增,教育預算再度削減,在1937—1945年之間,平均占比降至2.44%。抗戰勝利后,教育經費短缺問題仍然存在。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教育科學文化經費占比不得低于15%。但從實際預算來看,最高年份(1948年)也不過10.89%,最低年份(1947年)僅有2.92%。由于這一數據中包含了科學和文化支出,教育經費所占比重其實更低。(27)項懷誠主編、劉孝誠著:《中國財政通史(中華民國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203頁。
因此,在教育經費總體投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高等教育的支出規模自然難以滿足實際需要,以至于很多高校連最基本的硬件設施都無法齊備。根據時人觀察,“在八一三以前,各國立大學的圖書儀器,比較普遍地完備的,只有清華大學。”(28)王以中:《高等教育管見(二)》,《民主》1945年第12期,第287—288頁。1933年,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委員會在向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提交的改革高等教育提案中,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因教育經費困難,使各公立大學獨立學院之設備,甚為簡陋,或竟最低限度之設備亦不可能。公立者如此,私立者更不待言。學校數量雖日見增加,而其質量反日形低劣。”(29)《中央黨部組織委員會向三全會提議改革高等教育案》,《云南教育行政周刊》1933年第2卷第38期,第28頁。
客觀地看,私立高校的教學設備之所以更為落后,主要是因為其經費水平遠較公立大學為遜。大夏大學創辦人歐元懷就對當時各類高校的生均經費進行了分析:“私立大學每生歲占經費最高額為七〇〇元,恰好和國立大學每生歲占經費的最低額相等。而國立大學每生歲占費最高額比私立大學每生歲占費的最高額多四倍,比私立大學的最低額多十六倍。”(30)歐元懷:《十年來之中國高等教育》,《大夏》1934年第1卷第5期,第25頁。上述數據并不意味著國立大學的辦學經費很高,只不過表明私立大學的辦學經費更低而已。1934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每年給予全國私立高校72萬元補助費,用于擴充設備和添設教席,該年度申請補助的高校共有32所。(31)劉巍:《民國時期私立大學財政補助研究》,《高教探索》2021年第11期,第100—108頁。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這樣的補貼力度無異于杯水車薪。民國時期,許多私立高校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走向“國立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教育經費的實際支出還常常受到政局動蕩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受害最深的便是依靠薪酬度日的教職員工。1920年代初,在軍閥混戰的大背景下,各地高校遭遇了嚴重的經費危機,不僅高校教師生計無著,甚至連教育部工作人員也被欠薪數月。北京八所國立高校的教職員工在赴總統府請愿的過程中,還遭到軍警毆打,釀成血案。(32)吳惠齡、李壑編:《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1輯,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頁。全面抗戰爆發后,情況愈加艱難。根據經濟學家何廉回憶:“珍珠港事件后,中國進入了另一個通貨膨脹的階段。南開同事的生活條件越來越糟……人們可以看到大學教職員工的妻子在路邊去賣個人的物品——鐘表和衣服等。”(33)何廉著、朱佑慈等譯:《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頁。抗戰勝利后,內戰接踵而至,各地高校教師生活再度陷入絕境。根據當時的報道,“北平糧價,高于全國,北大、清華等國立大學及燕京、輔仁等私立大學教授生活,尤為清苦。北大、清華等校教授因入不敷出,多向校方透支,據謂北大一百八十余教授,透支已達四億元。”(34)《薪俸難維生活,北大教授透支,燕大經濟亦臨危境》,《燕京新聞》1947年5月12日,第1版。至于河南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更是出現了罷教風潮。(35)《物價狂漲生活益艱,各地大學紛紛罷教》,《燕京新聞》1947年5月12日,第1版。
(二)優秀師資短缺
民國處于新舊轉換的時代,傳統教育與新式教育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服務于近代高等教育戰略的師資儲備體系未能及時建立。1934年,時任教育部長王世杰應首都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之約,在中央廣播電臺講演《中國教育的現狀》時坦言:“現在多數的大學,均感優良師資的不足,而現時國內大學因研究所的缺乏,復尚難自植大學師資。”(36)王世杰:《中國教育的現狀》,《中華教育界》1934年第22卷第5期,第98頁。
由于優秀師資短缺,兼課現象十分嚴重。1931年,時任中央大學教授陶希圣在山東全省教育局長會議上指出:“大都市里的大學(如北平,如上海),教員大體上是共通的。各大學在教員上并沒有獨立性。一個教員兼任兩校的系主任及和第三第四校的專任教授并第五第六校的講師,這并不是沒有的。”(37)陶希圣:《現在中國教育上幾個問題——在山東全省教育局長會議席上第二次演講》,《社會與教育》1931年第23期,第3頁。1935年,教育部調查北京師范大學時發現,“該校教員共一百三十八名,專任者僅四十四人,其中在外兼課兼職者仍有二十八人之多,即系主任亦有在外兼課者,合計兼任性質之教員實數,當在一百以上。”(3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教育”(一),第211—212頁。這一現象固然與教師追求經濟利益的主觀動機有關,但各大高校優秀師資短缺的現實更是不容忽視的客觀原因。
全面抗戰爆發后,師資流散嚴重。隨著高校數量和招生規模的增加,即使是普通師資也不敷使用。1941年,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秘書長程滄波談到,“戰前教育界所恐慌的是超等人才之不易吸收,而今日的問題,竟成平均人才亦無法招聘。”(39)程滄波:《教育界的才荒問題》,《中央日報(重慶)》1941年3月31日,第2版。為了填充缺額,官方被迫放寬了師資選聘標準。(40)李艷莉:《民國時期大學教師準入制度的演變及啟示》,《教師教育論壇》2014年第2期,第92—96頁。在這種情況下,師資水平進一步下降。對此,輿論指出,“戰前校數較少,師資勉夠分配,戰后校數增多,原有師資紛紛改業,新師資出產又少,因此大學師資極感貧乏,因為合格者貧乏,又造成了不合格者濫竽充數的普遍現象,這當然要影響到高等教育的素質上去。”(41)徐中玉:《對目前高等教育上幾個問題的意見》,《教育通訊旬刊》1943年第6卷第4期,第10頁。
由于國內可供選擇的優秀師資太少,許多高校便將目光投向留學歸國者。理由在于,“因本國高深學術,尚未發達,如缺乏完全之實驗設備,博學多才之教授,使學者欲求高深之學識,不得不遠涉重洋,求助他國。”(42)《吾國留學政策之商榷》,《大學季刊》1941年第2卷第2期,第421頁。客觀地看,民國時期許多知名教授確有海外留學背景,他們也為現代科學的引入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這類人才終究是少數,才不堪用的“海歸”可能為數更多。1924年,私立南開大學的學生就在《南大周刊》發表文章,將混學歷的留學生回國教書,教出來的學生再依樣畫葫蘆的行為,諷刺為“輪回教育”。此舉引發了南開教員的強烈不滿,以至于釀成罷教風潮。(43)春蕃:《教員與輪回教育——評南開大學風潮》,《民國日報·覺悟》1925年第1卷第27期,第2—4頁。在輿論看來,“一留學生出國,先有一二年之時間為語言及生活方面之困難所占去,文字方面總不若本國之能運用自如,等到語言文字熟練之后,則又將返國。……留學生到外國留學四五年,其實時間并不算短,實在也學不到多少東西,如此回國便為人師,平心說實在無此資格。”(44)錦生:《關于中國派遣留學生問題的商榷》,《國訊》1939年第199期,第10頁。
由上可見,優秀師資短缺成為制約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發展的嚴重障礙。在這種情況下,高等院校的辦學水平得不到保證,也不利于人才培養工作的有效開展。誠如時人所論,“大學教育雖亦有改善之必要,然阻礙頗多,欲進不前,其因子雖多,而大學師資之數量缺乏,與品質低下為其主要因素。”(45)何錦明:《論我國大學師資問題》,《建設研究》1941年第6卷第2期,第61—65頁。
(三)學生水準低下
民國時期高等院校的整體辦學水平欠佳,關于大學生水準低落的報道屢屢見諸報端。根據1934年10月31日《申報》報道,中央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實驗所在測試了南北各省著名大學大一新生的英語成績之后得出結論:“我國大學一年級英語理解及速率程度之最佳者,僅及美國初中二年級。”(46)《艾險舟測驗萬人結果:大學一年級英語程度僅及美國初中二年級》,《申報》1934年10月31日,第14版。如果說大學生的英文水平不佳,尚可歸咎于語言環境和文化差異;那么,社科常識甚至國文水平的低下,則無可推諉。這一點可以通過第二次中央高等考試看出:在200份國文試卷中,文字通順的只有35%,根本文不成章的有55%,差強人意的有8%,優等的不過2%;在140份憲法試卷中,及格的只有6個人。北平某機關招收書記,有北平高校學生120余人應考,在4項考試科目中,國文及格12人,英文及格9人,寫字及格30人,常識及格22人。(47)靈囿:《高等教育改革問題》,《每周評論》1934年第52期,第7—8頁。全面抗戰爆發后,許多高校內遷,生源所在地也發生了變化。由于西部地區基礎教育落后,各大學被迫降低了錄取標準,這也導致大學生的水準更差。1946年9月13日《中央日報》報道,在抗戰后舉行的首次留學考試中,全國共有6000余人參加。根據普通科目(含國文、英文和史地)閱卷者的普遍看法,應考者的水平與戰前參加庚款留學考試的學生相比,降低了很多。(48)漢璍:《由留學考試看大學生們的水準》,《中央日報》1946年9月13日,第4版。
學生水準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高校數量增加導致辦學質量下降,正如國聯教育考察團所言,“大學發達之速度,超過其組織,無穩定基礎之大學,遂相繼以起,因而高等教育所必要之經費及合格教師之供給,均感不足。”(49)國聯教育考察團:《中國教育之改進》,國立編譯館1932年版,第159頁。與公立高校相比,私立高校的問題更為嚴重。1924年,劉景云等38位參議員向政府痛陳:“查京畿私立大學,兩年以來,陡增數十校,其中除少數差強人意之外,類皆藉辦學之名,行牟利之實,視教育為圖利事業,視學校為營私機關。”(50)《議員質問政府放任私立大學》,《新聞報》1924年8月15日,第3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教育部頒布法令,要求私立高校限期立案,對于不合規的學校,“或勒令停辦,或限期結束,或立予封閉”。(51)《私立大學獎勵取締法》,《新聞報》1930年8月22日,第8版。然而,從實際情形來看,私立高校的辦學亂象并沒有徹底解除。1932年,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傅斯年直言不諱地批評道:“私立大學除辦南開大學的張伯苓先生幾個少數以外,有幾個真正存心在教育事業呢?”(52)孟真:《教育崩潰之原因》,《獨立評論》1932年第9期,第2—6頁。根據1939年的新聞報道,上海某“野雞大學”竟然只有兩名學生。(53)《上海某野雞大學學生僅二名》,《電聲》1939年快樂周刊,第139頁。
學生水準低下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中等教育落后,制約了大學階段的學習。1934年,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周上,做了題為《中國大學教育之危機》的演講,對中學教育的落后給大學教育造成的不良影響進行了批評:“這幾年來,國內中學大部分實在辦得很有缺陷,而大學直接與中學相銜接,因之也受到很密切的影響。”(5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教育”(一),第287頁。國聯教育考察團也指出:“入學之大學生,多數缺乏適當之準備是已。中國有多數高級中學,成績極為不良,至投考大學之學生,有多數毫無相當之資格,可受益于大學教育者。”(55)國聯教育考察團:《中國教育之改進》,第174頁。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入學之后,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補習高中課程,這種做法又會壓縮大學課程的學時,導致高校的課程設置陷入兩難的境地。時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就感慨道,“中國大學的課程多而又雜,一年級學生所讀的東西,除了一二門專門功課之外,大半是高中所應該知道的。”(56)薩孟武:《從法律系的條文教育說到中國的大學》,《時代公論》1934年第114期,第6頁。時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黃建中也無奈地表示,“據最近數年大學招生統計,中學程度尚未見提高,如大學本科課程專門太早,高深過甚,則學生程度恐瞠乎莫及;如先多設普通課目以補高中程度之不足,則大學一二年級不啻為從前預科,而三四年級學生且難得研究高深學術之門徑。”(57)黃建中:《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關聯》,《播音教育月刊》1937年第1卷第10期,第95頁。
三、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人才產出
(一)失業現象嚴重
民國時期,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一個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人才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原本屬于稀缺資源的大學畢業生卻大量淪為失業人群,從而產生了人才缺乏和大學畢業生過剩的悖論。1931年,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就認為:“大學畢業生如此之多,至于沒有出路,論到真真做起事來,處處感覺到專門人材的缺乏,因此有很多人主張少辦幾個大學。我國大學畢業生的過剩,雖然是社會事業的不發達,需用大學畢業生的機會太少,但專門人材的缺乏,便不能不說是大學教育的失敗。”(58)朱家驊:《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及應行注意各點》,《云南教育周刊》1931年第1卷第29期,第1頁。
為了解決大學畢業生的失業問題,官方采取了一系列舉措。1930年,教育部針對“國內外大學專門學校畢業生,亦多陷于失業狀態中,而釀成種種墮落、卑污現象,且亦埋沒國家人才”的現狀,擬定了救濟方法8條,包括組織各學科榮譽學會、給予優秀學生獎學金、為大學畢業生提供試用崗位等。(59)《教育部擬救大學生失業辦法》,《中央周報》1930年第110期,第12頁。但是,這些舉措并沒有起到實際作用,1933年和1934年兩年度,全國專科以上失業畢業生人數高達9622人。(60)《失業大學畢業生人數》,《國際勞工通訊》1936年第21期,第88—89頁。在這種情況下,北平各大學畢業生憤而組成“職業運動大同盟”,向政府請愿。失業學生在宣言中痛陳,“三十年來,政府及社會人士,但知廣設學校,造就人才,而如何安插統計,則無人過問,甚有以教育為營業,視學生為商品,濫加制造,不計銷路,以致人浮于事,學失所用,用非所學,槁項黃馘,老死窗牖者,不可勝數。……‘大學畢業即失業’,在今日實為至慘痛之口語,極普遍之情形。”(61)《民二三北平各大學畢業生職業運動大同盟宣言》,《民生》1934年第2卷第23期,第12—13頁。面對輿論壓力,官方不得不再度提出解決方案,最重要的舉措就是成立學術工作咨詢處,作為人才調劑機構。然而,這一機構的業務范圍僅僅限于登記、調查和介紹等方面,無法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因此,成立兩年來,雖有2025名大學畢業生前來登記,但只有195人獲得了工作機會。(62)茹心:《大學畢業生之就業問題》,《青年月刊》1936年第2卷第4期,第1—2頁。在這種情況下,失業大學生的不滿情緒再一次爆發。1936年,北平大學生又成立了“服務運動大同盟”,作為兩年前請愿運動的延續,他們明確表示:“我們要求解決的,不是口頭允諾的咨詢處和介紹所的成立,而是分發任用,給予工作,要求畢業文憑兌現。”(63)《北平各大學畢業生服務運動大同盟告畢業同學書》,《中國學生》1936年第2卷第21期,第26頁。鑒于嚴重的失業危機,教育部決定在南京創辦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訓導班,招收最近三年的大學畢業生1000名進行短期訓練,實習考驗合格后按照成績分配工作。(64)《教廳牌告大學生就業訓導班簡章及招收學員辦法》,《四川月報》1936年第9卷第2期,第385—389頁。結果,報名者高達4000人,超出原定名額的三倍,其中還包括留學生200余人。(65)《大學畢業生就業訓練報名竟達四千人》,《圣公會報》1936年第29卷第18期,第30頁。
綜合地看,民國時期出現的大學生失業現象,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與高等教育的發展速度脫節,無法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其二,高等院校的人才培養質量有待提高,大學畢業生的工作能力和就業意向無法滿足社會的現實需要。其三,人才選拔和任用機制不健全,難以為年輕學子開辟廣闊的就業渠道。正如歷史學家鄭鶴聲所言,“數年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破產,失業問題,形成最嚴重之社會問題。身受高等教育之大學畢業生,自亦不能例外,所謂‘大學畢業即失業’一語,已成為極普遍之口號,考其原因,除社會經濟破產,教育本身不良外,則政治機關之未臻完善,人才登庸之未循正軌,要亦使大學畢業生無出路,而使職業問題日趨嚴重化。”(66)鄭鶴聲:《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關于高等教育之理論與實施》,《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10期,第30頁。
(二)應用人才匱乏
民國時期,就在大學畢業生為失業問題叫苦不迭的同時,社會上又為應用人才的嚴重匱乏而焦慮不安,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高校招生存在專業結構失衡問題。在很多年份,文科生占比都超過70%,其中又以文、法兩科為主。(6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教育”(一),第334—337頁。上述問題的存在,對于中國工業化進程極為不利,國聯教育考察團就指出:“若自然科學與工科萎縮過度,法科,文科,政治科學發達過度,則不論由學生個人或國家全體之觀點而論,皆為極不幸之現象。”(68)國聯教育考察團:《中國教育之改進》,第165頁。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矯正文法教之畸形發展,注重造就多數之實科人才”(69)《教部規定二十三年度各校院招生辦法》,《國立同濟大學旬刊》1934年第23期,第2頁。,官方進行了三個方面的政策調整:其一,增設實科學校及院系。主要包括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牙醫專科學校等國立院校,勷勤工學院、四川農學院等省立院校,以及一些私立實科院校。同時,安徽大學、東北大學、光華大學等高校也陸續增設了實科院系。其二,限制文法科院校及招生規模。這種做法使文理科之間的招生差距逐漸縮小,1935年度,實科新生的人數首次超過文科,占比51.2%。其三,增加實科留學生比重。自1933年度起,實科留學生的比重連續三年維持在50%左右。如果僅就公費生而言,實科留學生占比更高,1933年度為87%,此后兩年也都在七成以上。(70)黃龍先:《兩年來之高等教育》,《中國新論》1937年第3卷第4—5期,第137—146頁。
但是,理工科招生規模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培養質量也能得到同步提升。如前所述,民國時期大學經費普遍不足,以至于硬件設施都難以齊備,加之優秀師資短缺,導致辦學水平不盡人意,這些問題對于理科生的影響尤其嚴重。根據當時的報道,著名國立大學航空工程系畢業生在飛機工廠居然做不好鍍煉工作。(71)陶家澂:《論工程人材之培植》,《新工程》1947年第1卷第1期,第1—4頁。時任南開大學教授張純明就指出:“所怕的不是文法學生太多,而是文法科粗造濫制。……我們的問題是不患多而患不精。不精,不但文法科是問題,就是‘實科’也何嘗不是問題呢?”(72)張純明:《我國之高等教育問題》,《國聞周報》1937年第14卷第23期,第57頁。上述觀點并非杞人憂天,在1933年度和1934年度將近1萬人的失業大學生中,就包括工、農、醫、理各科學生2000余人。(73)甫:《論大學生的失業》,《時代青年》1936年第1卷第2期,第3—4頁。
由上可見,民國時期的高等教育并沒有為社會培養出足質足量的應用人才。今人耳熟能詳的“民國大師”,大多來自于人文學科。他們出生于耕讀或官宦之家,童年時代就接受了嚴格的私塾教育,打下了扎實的國學功底。無論是從生活年代還是求學經歷來看,他們的學術成就似乎更應歸功于傳統教育。至于少數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獲得成功的學者,如錢學森(物理學)、李政道(物理學)、楊振寧(物理學)、侯德榜(化學)、陳省身(數學)、茅以升(土木工程學)、童第周(生物學)、竺可楨(氣象學)、梁思成(建筑學)、張培剛(經濟學)和費孝通(社會學)等,雖然在年輕的時候接受了國內教育,但學術生涯卻始于留學西方以后,重要的學術成就也大多是在國外取得的。退一步而言,即使有少數人成功也不意味著整體進步,并不能扭轉民國時期應用人才匱乏的局面。
余 論
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在艱難的環境中曲折前行,其開拓進取的時代精神和為國育才的歷史功績不容抹殺。民國時期屬于近代高等教育的早期發展階段,在社會各界的努力下,不僅誕生了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等享譽中外的高等學府,也涌現出一批才華橫溢的精英學人,這些都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寶貴財富。
但是,民國時期戰亂不斷,各項現代化事業的開展極為艱難。在政局動蕩和經濟凋敝的大環境下,高等教育不可能一枝獨秀。從整體上看,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成就并不應該被過分拔高:對于國家而言,受制于有限的普及程度和低下的培養質量,沒有為工業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輸送充足的優質人才;對于個人而言,受制于昂貴的收費標準和極高的文盲比例,也未能向廣大底層青年提供“讀書改變命運”的機會。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少數精英之所以能夠成為本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不僅僅在于他們本身優秀,更是由于上述學科在中國剛剛起步。因此,他們的盛名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他們的學術貢獻固然值得稱道,但也只是寒冬之際的一抹春色,并不能代表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水平。綜合來看,民國時期的高等教育在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科技進步、文化繁榮和國家安全等方面,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卻沒有發揮出質變的功效。
相比之下,新中國的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和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實現了從“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轉變,中國也實現了從文盲半文盲大國向教育大國的歷史性跨越:2020年,全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為95.2%,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 54.4%。(74)《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地質教育》2021年第3期,第106—110頁。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與新中國分別處于高等教育的不同發展階段,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一脈相承而非相互對立。新中國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夠取得佳績,離不開民國時期的開拓之功。因此,當后人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征程上闊步前行之時,不僅應當對先賢的曲折探索報以“了解之同情”,更應當對他們篳路藍縷的奮斗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