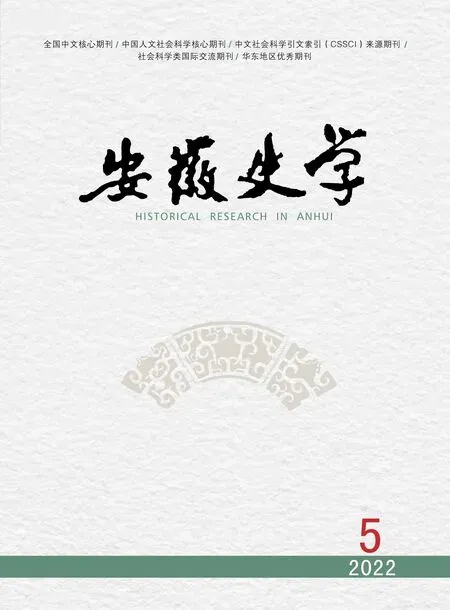“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與新中國初期城市街道治理
尹紅群 張 敏
(1.湖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2.中央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 100081)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新中國婦女運動史上定格了不少經典女性形象,例如:“鐵姑娘”和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jiedao dama with red armband)(也稱為居委會大媽、胡同大媽等)。“鐵姑娘”類型(與之類似的還有“女拖拉機手”“女扶犁手”“女機車手”等)主要是國家對女性個體的勞動形象塑造,體現了中國勞動分工的“去性別化”,即“男女都一樣”,形成女性不斷擴大其職業領域、與男性勞動相融匯混合的特點。(1)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相較而言,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的形象則更多反映了在基層治理層面國家對女性的同構化塑造——如果說街道大媽的“紅袖章”體現了國家的管治權力和身份認同,“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則體現了街道治理的“賦性別化”特點,原本居家的家庭女性被吸納入公共領域并成為一個城市基層治理的形象。這和新中國初期大量的以男性為樣本的對女性新形象的“去性別化”的時代性(2)崔菲菲、文紅玉:《新中國婦女新形象的塑造——以《人民日報》的典型形象為例(1949—1956)》,《前沿》2013年第17期。形成明顯差異。這種女性積極分子的形象建構機制和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新中國成立以來婦女解放成就舉世矚目,具有世界性意義,也一直是學術界積極關注的主題。在中國大陸學術主流是基于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延續革命話語,結合歷史事件(包括政治運動、社會政策),展現婦女解放的成就。(3)李從娜:《近10年來建國初期中國婦女史研究綜述》,《北京黨史》2006年第2期。社會性別理論引入中國后對婦女史研究產生了積極影響,“社會性別主流化”的理念被中國共產黨接受并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的實踐。(4)耿化敏:《中國共產黨婦女工作史(1949—197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98頁。從學術角度看,“社會性別”立足“真問題”(5)宋少鵬:《立足問題,無關中西:在歷史的內在脈絡中建構的學科——對中國“婦女/性別研究”的思想史考察》,《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第5期。,拓寬了歷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性別視角與階級、地域、族群等共同成為歷史研究的角度或范疇,婦女/性別史學科“從邊緣走向多元”。(6)高世瑜:《從婦女史到婦女/性別史——新世紀婦女史學科的新發展》,《婦女研究論叢》2015年第3期。高小賢的“銀花賽”(7)高小賢:《“銀花賽”:20世紀50年代農村婦女的性別分工》,《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4期。、金一虹的“鐵姑娘”、美國學者賀蕭關于“女勞模”的性別記憶(8)Gail Hershatter,“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Chinese Women and the 1950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002,Vol.28,No.1.,都是使用社會性別理論研究新中國成立后女性群體的典范,有力地推進了社會性別理論在中國的運用。通過社會性別視角,新中國的女性形象更加豐富多樣,對于新中國婦女形象的理解也更為深入。
本文立足于社會性別視角,探討“街道大媽”——即城市基層社會的女性積極分子在城市政權建設的歷史性變革中如何被建構,并成為城市基層治理的代表性符號。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本文主要使用有關湖南省長沙市的婦女檔案資料。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長沙市是一個中等商業城市,在城市規模上可以代表更多二線城市的一般情況,體現出地域差異性和某些共性,能夠在學理層面提供“理想類型”的分析,進一步探究在新中國歷史上女性形象建構的復雜機制。
二、婦聯“發現”和組織街道婦女:歷史背景
正確理解“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離不開對歷史背景的詳盡考察。新中國成立初期,新興的政權初掌城市,開始了“人民的城市”的改造和建設進程,作為城市基層的街道是民主建政的重點領域。“三年多來雖然經歷了各項運動,覺悟有所提高,但還沒有深入系統地發動,街道組織不純潔不健全,民主生活缺乏,基層政權未打下堅實的基礎”(9)中共長沙市委:《市委關于完成民主建政工作的指示》,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28-3-79。,如何在城市社會展開治理成為一個新命題。(10)郭圣莉:《城市社會重構與新生國家政權建設》,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作為中國共產黨重要群眾組織之一的婦聯(時稱民主婦聯)積極地向下延伸建設地方組織,街道婦代會是婦聯的城市基層組織。新政權向城市基層擴展中,婦聯創建基層婦代會,體現了婦聯組織的性別意識和發展策略。(11)Wang Zheng,“State Feminism?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Feminist Studies,Vol.31,No.3(Fall,2005),pp.519-551.在新城市“三大”民主改革運動之一的街道民主建政中,街道婦代會積極參與,發揮了生力軍的作用。(12)尹紅群:《新中國成立初期街道婦代會與基層民主建政——以湖南長沙為例》,《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6期。“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的經典形象即可上溯至此。(13)可作佐證的經典案例是北京的“西城大媽”,往上追溯,自新中國成立起,這個比鄰紅墻的社區,就有了戴紅袖標的志愿者,只是名稱不同,過去被京城百姓親切地稱為“小腳偵緝隊”。參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4月12日,第5版。
初入城市的婦聯并沒有成熟的城市街道婦女工作經驗,最初領導的城市婦女組織工作并不順利,革命時代農村婦女工作的經驗顯然不能照搬到城市來。最初的組織工作是非常艱難的,但是很快找到了組織的方法:與區政府、派出所、居民委員、居民小組長及當地有組織的婦女聯系,通過他們的協助,婦聯干部下去召開婦女代表會,作動員工作,不斷地發現積極分子、培養積極分子推動工作。(14)長沙市婦聯:《組織部一、二、三月工作計劃(1951)》,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15。婦女的組織發動工作逐漸打開局面。
1951年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和抗美援朝運動對婦女運動影響深遠。在各種紀念活動和游行示威中,婦女的組織得到擴大和健全,原來沒有建立婦女組織的,也建立了起來,特別是街道婦女群眾。各地婦女游行隊伍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無組織的勞動婦女與家庭婦女特別多。“三八”節上海30萬婦女的游行隊伍中,無組織的婦女占60—70%。重慶市區8萬婦女的游行隊伍中街道婦女占50%。經過這次紀念活動,各方面對婦女工作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婦女的力量和作用有了正確的估計與認識,改變了輕視婦女工作與婦女力量的看法。婦女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因此大大提高,有的婦女干部說:“通過這次工作,才認識到婦女工作的重要。”(15)《全國各地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工作的綜合報告》,中國婦女管理干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匯編》第2冊,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01頁。
正是在社會政治活動中,婦女群眾的自我認識發生重大轉變,新的積極分子大量涌現,婦女組織的積極性也大大提升。到1951年11月,長沙市婦聯在情況報告中指出:“本市各區婦代會是從今年‘三八’節后,通過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民主建政等中心工作建立起來的,現在已成立婦女代表委員會18個,婦女代表會156個,代表共2100人,聯系了家務婦女41414人。”(16)長沙市婦聯:《街道婦女代表會議報告(1951.11.3)》,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5。婦女代表認識到“婦女只有以積極參加勞動生產、社會活動來爭取參政,和求得男女真正的平等”;男性也認識到了婦女的作用,“由于婦女的覺悟提高推動了工作,也轉變了男居民對婦女的看法,大家認為沒有婦女的力量,居民工作就作不好,群眾也發動不起來,任務就完不成。”(17)長沙市婦聯:《組織部十、十一月的工作總結(1951)》,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15。
總體來看,“街道大媽”的出現是時代的產物,只有把“組織起來”的城市家庭婦女和底層婦女放置于人民政權在城市的推進、城市基層政權建設和城市社會秩序重構背景下,才能更深刻理解“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為什么能出現在城市街道,及其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三、參與民主建政:“街道大媽”崛起
在國家推進的街道民主建政這項中心工作中,家庭婦女和一些街道底層婦女在政治運動中被“發現”、挖掘和凸顯出來,逐漸走向公共參與,走進街道政權建設和社會治理之中。在城市街道民主建政運動中,“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的形象及內涵逐漸明朗——她們就是一群翻身的勞動婦女、治街如治家的女性積極分子。“街道大媽”的崛起,融匯了“訴苦”機制和“同構”機制的共同作用,是城市婦女解放的標志成果,體現著黨政機關與婦聯組織的共謀共建。
(一)“訴苦”機制:革命化建構
“訴苦”是“街道大媽”形象建構的起點,是婦女個體受革命話語體系指引完成革命化的方式;也是發現和培養女性積極分子的機制。處于城市社會最底層的受壓迫婦女成為“苦主”,婦女“受苦”和反壓迫的訴求成為街道民主建政運動的重要戰線。
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召開城市工作與工礦工作會議,討論了工廠、行業和街道開展民主改革運動的問題。10月,長沙市按照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確定深入開展街道民主建政運動,“深入發動群眾,提高覺悟,肅清街道中殘余封建反動勢力;發揚民主,整頓組織,召開街道人民代表會議;如此在街道中進行一次系統的社會改革,了解社會情況與政治情況,完成基層建政工作,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18)中共長沙市委:《關于完成民主建政工作的指示(1952.8.28)》,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28-3-79。改造舊城市基層社會,就要發動群眾和控訴斗爭,這是革命運動的基礎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婦女成為控訴斗爭的主力軍。中共長沙市委經過對街道的了解和重點街道試辦民主建政的經驗,強調街道民主建政的關鍵在于全面發動群眾,要始終堅持“男女一起發動”的方針,特別提出要重視發動婦女工作。(19)長沙市婦聯:《民主建政中第一階段發動婦女參加運動總結(1952.10.8)》,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7。在客觀上,街道居民中男人多有組織,而居家的大多是職工家屬、家庭勞動婦女,她們受封建統治的殘害壓迫、污辱的程度更深,因此斗爭性更強、更堅決。長沙市婦聯指出:“如南區觀音閣楊娭毑,她控訴丈夫被迫害,槐樹巷何錦純控訴被強奸,東區劉玉英在舊社會受苦很深,她們的控訴對發動群眾斗爭地方惡霸起了很大作用,是運動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因此不能忽視婦女的發動。只有充分的發動婦女群眾,才能壯大勞動人民的隊伍,集中力量,打倒敵人,否則運動便不全面和不徹底。”(20)長沙市婦聯:《關于如何發動婦女參加民主建政的初步意見》,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7。
正是由于動員組織了婦女群眾,把婦女個人的苦,引導到共同的敵人,提高到階級的仇恨,婦女們才敢于發聲、勇于斗爭,成為控訴論理的主要力量,“街道民主建政時,多半是婦女供給材料,斗爭時,大多是婦女訴苦,控訴論理,帶動了群眾,斗倒了敵人”。(21)長沙市婦聯:《長沙市街道婦女代表會議總結報告(1952.9.5)》,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7。街道婦女的“訴苦”,為更深入的城市街道民主建政運動奠定了基礎。據4個區統計,街道民主建政運動中,婦女參加各種會議學習占總數的80%:如南區參加各種會議人數51261人中,婦女占41088人;西區239753人中,婦女占101824人。積極分子中婦女占60%以上:南區積極分子1485人中婦女880人,占59%強;西區2135人中婦女1281人,超過60%;各個區民主建政籌備委員中婦女占50%。(22)長沙市婦聯:《民主建政中第一階段發動婦女參加運動總結(1952.10.8)》,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7。
新中國成立后,新政權迅速掃清城市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凈化和純化城市街道社會關系。這本身就是一場深入的反封建的階級斗爭。和農村地區土改過程中的“訴苦”技術類似,城市居民也需要從道德化的個體轉化為意識形態化的階級成員的機制而存在。(23)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中國學術》2002年第4輯。對于城市街道婦女而言,這種建構更被打上了性別化的色彩,婦女個人的受辱——抗爭,具有社會性別意義上的抗爭意蘊,抗爭的對象就是這些男性化的封建勢力。階級斗爭通過社會性別進行表述,社會性別滲透在革命話語體系中,婦女成為衡量政治立場和革命斗爭的尺度。
(二)同構機制:國家化建構
“同構”機制是指在運動中街道婦代會的階級化機制,是形象建構的關鍵環節。從“苦主”到街道治理的參與者和“管家”角色的轉變,中間經歷一個關鍵變動,即“同構”:婦女組織國家化建構。國家政權和婦聯組織都有政治上的訴求把街道婦代會改造成以工人家屬和勞動婦女為領導層的組織,實現階級同化和國家性質的同構,造就國家政權的社會基礎。
街道婦代會的內部整頓就是按國家政權的模樣重塑自己的一個縮影。街道婦代會成立之初,代表成份比較復雜,“最初群眾的覺悟不高,一般職工家屬和勞動婦女認為自己沒有文化,說不得累不得做不得,而不敢出來,一天也沒有閑不愿出來,而愿意出來的是些會說會道的工商界婦女家庭知識分子,以及一些作風不正派家庭或丈夫有問題的反革命份子家屬官僚太太之類形成婦代會,非常不健全,代表成份不純不起作用,因而組織流于形式。”因此,婦聯明確提出:“自上而下的要掌握與貫徹明確的階級路線與組織路線,必須是依靠職工家屬與勞動婦女,團結各階層的婦女,防止壞份子鉆進來。”(24)長沙市婦聯:《長沙市街道婦代會的組織情況(1952.10)》,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7。在民主建政運動中,群眾檢舉揭發了不少存在問題的婦女代表,如北區星子橋(已經過民主建政)婦女代表委員會共有123人,其中反革命分子家屬及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家屬25人,占總數20.3%,幫會大姐又是妓女的1人;又如南區天心閣婦代會所屬朗公街代表會有29個代表,有2人丈夫有問題,8人工作不積極,4人作風不正派,因此,他們在群眾中威信不高,不能體貼廣大勞動婦女的痛苦,更不能代表勞動婦女的利益。(25)長沙市婦聯:《長沙市街道婦代會的組織情況(1952.10)》,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7。結合民主建政,婦代會清除了隱藏的不良婦女代表,在新的選舉中做到婦代會代表成份中職工家屬和勞動婦女占2/3,其他階層占1/3。(26)長沙市婦聯:《長沙市婦委關于如何發動婦女參加民主建政的初步意見》,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7。經過組織整頓,街道婦代會保持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本質,始終與國家政權站在一起,成為國家政權堅實的社會基礎。
與國家“同構”之后的街道婦代會更加廣泛地參與到基層政權。長沙市街道民主建政運動順利完成,先召開了街道人民代表會議,成立了街道人民代表會議辦事處(簡稱街道辦事處),在此基礎上又召開了區人民代表會議,代行區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選舉產生區政府,在群眾中提拔產生的副區長4人當中,有3個婦女當選(2個系家庭婦女)。(27)中共長沙市委:《區委三個月來工作匯報摘要》,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28-3-79。從民主建政運動的主旨來看,婦女組織不僅積極參加斗爭,而且深入制度層面,是新中國街道政權建設的參與者。
四、參與街道治理:傳統性別角色嵌入
傳統性別角色嵌入,是國家對女性積極分子的角色職能定位和形象建構調整機制。在使用革命話語發動婦女“訴苦”,走出家庭的同時,婦女發揮街道治理角色職能的邏輯也在悄然生變——傳統中國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邏輯,即婦女在家庭中家務“管家”的地位延伸到了街道治理。
長期以來,革命話語強調婦女要走出家庭,打破封建家庭的束縛。但是在新中國的街道治理中,舊的觀念被有意識地運用于新秩序的建構。治街如治家,婦女和女性化的治理方式在街道占據主流。街道是家庭的延伸,中國傳統的女性當家,以及家庭內部的溫馨氛圍的營建等在街道上也得以運用。正如瓊·斯科特所言:“大的政治動亂摧毀舊秩序,建立新秩序。在尋求新的合法性形式時,這個過程可能會修改社會性別的術語和組織方式。但是也可能是另外的結果:舊的觀念也許反過來幫助確立新的政權。”(28)Joan Wallach 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5.December 1986,pp.1053-1075.本文參考了鄭巖芳譯、王政校對的中文版本。
城市街道治理面對的問題有兩大類,一類是敵我矛盾,一是人民內部問題。在敵我矛盾方面,經過鎮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等之后,大的罪惡深重的封建反動分子基本上被鎮壓,剩下的主要是封建殘余勢力和其它次要反動分子。在此背景下,人民內部問題逐漸成為街道治理中的主要問題。在處理人民內部問題時,街道治理側重教育、說服、調解的方法和手段,婦女和婦女組織——街道婦代會使得街道治理方法、手段更柔性。在民主建政中,婦女代表向婦女宣傳,把傳單念給大家聽,動員參加討論和選舉。比如,東區政府發動婦女代表大膽向候選人提意見,帶動了其他婦女;南區麻園塘居民愛國公約,就是居民委員和婦女代表共同領導訂立的,并選舉婦女代表湛麗清作為居民愛國公約檢查員。(29)長沙市婦聯:《街道婦女代表情況報告(1951.11.3)》,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15。
在解決家庭和婚姻問題等這些“家務事”上,女性積極分子更是功不可沒。街道婦代會大力宣傳婚姻法,婦聯召開婚姻法擴大座談會議,婦女代表均積極學習和宣傳,并抓住各種群眾會議,她們在居民大會、小組會、學習班、反革命分子家屬座談會上,就結合宣傳,在讀報組中堅持必談婚姻問題。婦女代表更是重要的基層調解工作者,較正確地處理了一些婚姻案件,解決不了的,就反映到婦聯;制止了一些虐待婦女的事件,如東區紫荊園居民彭楚容,經常打妻子,宣傳婚姻法后,婦女代表批評了他,后來就不打了。西園一個婦代會一個月內調解5件虐待婦女、夫妻不和的案子。支持婚姻自由,如北區姚家巷一個鰥夫與寡婦戀愛,她兒子阻止,婦女代表極力支持他們結婚,也支持有正當理由的婦女離婚。婦女代表大都不怕麻煩,耐心細致地調解問題,解決好了,群眾反映婚姻法真好。(30)長沙市婦聯:《街道婦女代表情況報告(1951.11.3)》,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15。
女性積極分子及街道婦代會充當了街道政權“賢內助”的角色。街道婦代會的婦女干部主要結合中心工作,做好政府的助手,搞好街道和家庭衛生,宣傳婦嬰衛生育兒,推廣新法接生;維護婦女權益,協助街道調解委員會調解夫妻不和、家庭糾紛,培養民主和睦、勞動生產的新家庭。(31)長沙市婦聯:《關于街道婦女工作的報告(1953.8.25)》,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34。
至此,經過婦聯組織和國家的共謀與共建,在新中國人民的城市街道上,管這管那而又親切的熱心大媽形象躍然而出,既體現出敢于反抗、勇于斗爭的革命精神,新社會的主人翁精神,也能體現出傳統中國女性的吃苦耐勞、甘于奉獻的美德,這是構建美好大家庭的基礎。“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既有古道熱腸,更有家國情懷,從而演變為性別政治的經典符號。
五、治理角色的爭議與調整
“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成為街道工作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她是基層權力角色嗎?或者僅僅是一個被授權的治理形象?在新中國城市政權創建和完善過程中,這個爭議是客觀存在的,特別是婦聯基層組織和婦女積極分子對如何參與基層政權及參與程度并沒有明確的認識,黨政機關與婦聯組織的協調和妥協不可避免。
(一)黨政機關與婦聯組織的差異化訴求
在城市基層政權初創之時,黨政機關與婦聯組織之間存在差異化訴求:一方面,婦聯組織領導城市婦女群眾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各項運動中,特別是在街道民主建政運動中有著突出表現,在新基層政權組織未健全之前,“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行使了一些基層權力,基層婦代會具有一定的行政化色彩,婦聯組織發現、培養和領導這些“街道大媽”,在街道治理中發揮方方面面的作用,從而強化了婦聯組織的增權意識。另一方面,黨政機關內部對基層婦代會的看法有所變化,“自從若干城市先后建立居民委員會之后,在某些男女干部中產生了取消基層婦女代表會議的想法”。(32)章蘊:《國家過渡時期城市婦女工作的任務和當前幾項具體工作的報告》,中國婦女管理干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匯編》第2冊,第216頁。
婦聯的增權意識與“取消婦代會”的想法,本質上體現了治理形象(身份)和制度建構的內在張力。這種體制內張力在長沙市婦聯向中共長沙市委的一系列報告、請示,以及中共長沙市委的回復往來中得到體現。彼此的訴求差異必須在更高層次的組織制度層面進行協調和妥協。
從長沙市婦聯的相關文件看,婦聯組織的增權意識和行為有三個表現:
第一,在街道婦代會的組織職責上,強調了婦女的特殊利益,突出了性別意識:“代表廣大婦女群眾,特別是勞動婦女的切身利益,為婦女爭取一切合法權利,如:人身自由權;土地財產權;婚姻自由權;參加社會活動的自由權;參政權。”(33)長沙市婦聯:《為什么要成立街道婦代會組織?》,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15。在基層政權的工作機制上,長沙市婦聯提出:在基層婦代會與作為基層政權組織的街道辦事處之間,應“明確不是領導關系,而是互相聯系,互相配合、分工的問題”(34)長沙市婦聯:《關于街道婦女工作的報告(1953.8.25)》,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34。,“做到互相參加會議商量工作,重視婦女組織;街道辦事處工作計劃和總結要有婦女工作;調婦代會常委以上干部要通過區婦聯;等”。(35)長沙市婦聯:《市婦聯就街道婦女工作向市委的請示(1953.6.16)》,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28-3-79。
第二,在民主建政和選舉工作中,婦聯組織因勢利導,強調了婦女的平等參政權。長沙市婦聯在街道民主建政運動開展之初召開婦女代表會議,提出“婦女群眾要支持婦女領袖人物,支持他們,幫助他們出來”(36)長沙市婦聯:《長沙市街道婦女代表會議總結報告(1952.9.5)》,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7。,防止兩種錯誤傾向:其一是忽視婦女的發動,認為婦女不頂事或受封建思想束縛,不敢培養積極分子;其二是防止使用觀點,只吸收婦女參加斗爭控訴,忽視婦女參政。(37)長沙市婦委:《關于如何發動婦女參加民主建政的初步意見》,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27。
第三,擴大婦聯組織權利的要求。1953年長沙市婦聯主任羅秋月以市婦聯名義向中共長沙市委遞交請示,要求和建議:(1)請求市委吸收羅秋月同志參加生產改革辦公室的會議,以便及時了解領導意圖,通過婦聯干部及組織貫徹工作;(2)要求市委指示各部門注意發揮婦女組織的作用;(3)要求市委派一婦委副書記到市總工會當女工部部長,建議市總工會健全女工部,配齊7個干部的編制,國營工廠配齊女工委員,調動女干部要經女工部同意。(38)長沙市婦聯:《市婦聯向市委的幾點要求和請示(1953.7.2)》,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28-3-79。
婦聯組織的增權意圖很快得到中共長沙市委的回復,但并不是婦聯組織所希望的方向。中共長沙市委似乎比較滿意其婦聯組織和女性積極分子目前所承擔的角色和職責:
第一,市委在回復時明確了基層婦代會的“群眾組織”性質,認為:“提出婦代會和街道辦事處的關系是分工配合關系,似乎不妥當,因街道辦事處是區政府派出機關,婦代會是群眾組織,這樣提可能使街婦代會代替行政,街辦事處貫徹上級政府法令執行區政府區人代會的指示和決議,街婦代會應動員婦女擁護執行,街道辦事處應吸收婦代會干部參加工作。”(39)《市委曾直政委回復(1963.9.2)》,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28-3-79。
第二,否定了婦聯組織提出的加強街道婦女工作的意見。市委不希望婦聯脫離黨和國家既定的婦女工作方針,另辟新路線。中共長沙市委向市婦聯指出:“目前提出加強街道婦女工作(以分散的職工家屬、獨立生產婦女及貧苦勞動婦女為對象)是十分必要的,因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很差。但仍應堅持‘以生產為中心,以女工工作為基礎’的方針,在繼續加強女工工作及集中的工人家屬工作的基礎上,注意加強街道勞動婦女的工作。不提‘以街道婦女為主’的方針。(據說有這樣的意見)。”(40)《市委曾直政委回復(1963.9.2)》,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28-3-79。
第三,有關市婦聯主任參加市委會議以及有關婦女組織人事問題,也沒有采取如婦聯所愿的改革。中共長沙市委副書記劉晴波在回復市婦聯的函件中談到了婦女積極分子事:“街道積極分子工作上的問題,區委開會時加以研究解決。”(41)《市委副書記劉晴波回復函(1953.9.3)》,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28-3-79。也就是說,婦女積極分子的人事問題是繞開街道婦代會的。
凡此種種,均說明婦聯組織的這些努力沒有得到相應的回應,顯示出了婦聯組織在政權結構中存在的困境。一個后果是基層婦代會的地位明顯下降,婦代會一位常委在常委會上抱怨說:“我們婦代會干部在中心運動過了便失了業,平時也只搞搞困難戶包干,反正婦代會做不了什么,看不到成績。”(42)長沙市婦聯:《荷花池四管區婦代會在糧食中心運動發動家屬情況》,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32。這種現狀與女性積極分子充分參與街道治理的認識形成了較大的落差,體現了婦聯基層組織及女性積極分子在城市街道政權結構與社會治理中地位與作用的不穩定性和困境。
(二)街道治理角色的調整
長沙市婦女工作中的困境并非個案——幾乎在同一時期,有關街道婦代會的存廢問題也在全國婦聯引起了討論。婦聯組織內部經過討論,重申基層婦代會去行政化,回歸群眾組織的定位,對于活躍在街道上的女性積極分子也進行治理身份的調整,即“街道大媽”側重在街道治理的參與。
1955年4月19日全國婦聯召開第一次城市婦女工作會議,全國婦聯副主席章蘊作工作報告,報告花了相當大的篇幅談城市基層婦代會及基層婦女工作問題,強調不僅不能取消基層婦代會的組織,而且應當加強基層婦代會的工作,健全基層婦代會的經常工作機構,建立經常工作;并就基層婦代會的組織問題、基層婦代會與街道辦事處以及居民委員會的關系問題、基層婦女干部和積極分子的培養教育和使用問題進行了說明和界定:“一般來說,基層婦女代表會議應設立在居民委員會的轄區內……便于同城市街道基層組織相適應,互相配合工作”;“在工作上,基層婦女代表會議必須同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取得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工作”,“又應努力幫助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作婦女工作的干部,了解婦女工作的情況,熟悉婦女工作的業務,供給她們必要的業務資料,吸收她們參加必要的會議,同她們共同研究婦女工作中的問題,共同開展工作;但不能依靠她們來代替婦女代表會議的工作。”(43)章蘊:《國家過渡時期城市婦女工作的任務和當前幾項具體工作的報告》,中國婦女管理干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匯編》第2冊,第216—217頁。
從全國婦聯的報告中可見,城市基層婦代會進一步明確了自身的地位與作用,它并非基層政權結構的組成,但應積極參與街道工作,是街道治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沙市婦聯在培訓基層婦女干部和積極分子時強調:“我們應該明確婦代會是群眾組織,街辦事處是半政權性質的組織,我們主要是發動婦女群眾完成街道各項中心工作,而且這兩個組織可以建立適當與可能的工作聯系制度,可以做到互相參加會議、互相了解工作情況(事實上已有這樣作的),互相研究工作。”(44)長沙市婦聯:《街道婦代會基層干部輪訓班學習總結報告(1954.4)》,長沙市檔案館藏,檔號:120-1-64。
另一方面,全國婦聯特別強調了基層婦女干部和積極分子的問題,“近幾年來,在基層工作中,培養了大批的婦女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她們是婦聯聯系廣大婦女的橋梁,是婦聯進行基層工作的骨干,是群眾中的新生力量,必須注意教育培養和愛護。”(45)章蘊:《國家過渡時期城市婦女工作的任務和當前幾項具體工作的報告》,中國婦女管理干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匯編》第2冊,第216—217頁。城市的市、區婦聯利用城市的有利條件,有計劃地分批地短期輪訓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成為城市婦女工作的重點之一。表現優秀的婦女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大量被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吸收,據統計,到了1957年,在城市基層的居委會中,婦女干部在其中占到80%左右。(46)《更充分地發揮婦女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人民日報》1957年3月8日,第1版。婦聯組織真正成為輸送優秀婦女干部的“娘家”。“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治理形象深入人心,是基層婦代會對城市街道治理工作的一份突出貢獻。
結 論
“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的崛起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市基層婦女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新事物新現象,這種新形象建構是新中國革命女性形象建構的案例之一。它是中國特色性別政治的體現,無疑是比較成功的和獨特的。“街道大媽”的治理形象建構,在生成機制上是國家與婦聯組織圍繞“中心工作”的共謀和共建,訴苦機制與同構機制具有強烈的革命化建構,在街道治理實踐中又強化了傳統性別角色的嵌入,賦予了性別政治色彩。黨政機關與婦聯組織之間的差異化訴求需要彼此的協調,婦聯組織作為黨的群眾組織,需要服從服務于黨的領導,而黨組織同樣要照顧婦女工作的特殊性,彼此要處理好關系。婦聯組織更深刻意識到自身的定位是“娘家”,“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逐漸成為街道治理形象的代名詞。
在不同的性別理論與話語體系中,“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或許有不同解讀,西方語境中的研究往往強調中國革命與婦女、國家與婦女組織之間的二元對立,側重于考察中國革命對婦女的改造以及國家對女權主義的抑制,忽視了婦女組織與國家建構間可能存在的復雜機制。在中國革命話語體系中,婦女解放是在國家建構的語境中展開的。國家建構絕非簡單地排棄社會性別,而是通過對社會性別策略性應用強化國家建構。從社會性別的視角看,街道婦女和婦女組織的崛起出乎意外但又合乎情理。新掌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在進行“人民的城市”建設時,一方面是要強力地排除舊社會殘留在街道的“污泥濁水”,另一方面是要建構新的基于社會性別的權力關系:當廠礦和政府部門成為男性化的組織機構時,家庭、街道成為婦女的主場,街道是家庭的延伸,管理家庭的婦女延伸為街道的管理者,社會角色和功能自然延伸;街道事務處理是家庭事務處理的延伸。這一切符合“家國一體”的傳統社會心理結構,凝結在“治街如治家”的表述中。從這個角度看,“戴紅袖章的街道大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內涵豐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