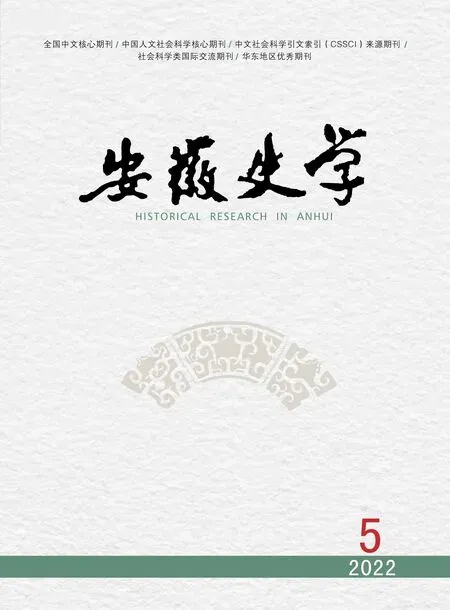陸寶忠日記與晚清史研究補論
李細珠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2488)
陸寶忠(1850—1908),字伯葵,號定廬,江蘇太倉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職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南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署禮部尚書等職,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并曾任湖南學政、順天學政及多次兼鄉、會試考官、閱卷大臣等學差、考差,是晚清時期典型的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官僚。陸寶忠存世文字不多。在他去世之后,其門人唐文治等人便刊印《陸文慎公墨跡》(宣統元年,1909)和《陸文慎公奏議》(宣統三年,1911)各一冊。民國十二年(1923),有《陸文慎公年譜》上下兩卷問世,自道光三十年(1850)陸氏出生到光緒二十年(1894)以前為上卷,系陸寶忠自訂;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后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陸氏去世為下卷,乃其門人陳宗彝續編。這個年譜記載了陸寶忠主要的生平事跡,也是研究相關史事的重要資料。
陸寶忠勤于寫日記,惜乎大多散失,現存未刊稿本八種十四冊由收藏家陳桂海先生珍藏,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所存日記僅是其中一部分,但內容豐富,是研究晚清政局與社會變遷難得的珍貴史料。對于陸寶忠的家世、生平及其未刊稿本日記的基本情況與史料價值,馬忠文先生已經撰文做過介紹(1)馬忠文:《陸寶忠未刊日記的史料價值》,《江漢論壇》2016年第6期。,讀者可以參考。本文擬在簡要介紹陸寶忠日記的基礎上就馬忠文先生未及注意的幾個方面做些補充說明,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這部寶貴的日記史料,并有助于推進晚清史研究。
一、陸寶忠日記簡介
現存陸寶忠日記稿本共八種十四冊,按時序大致如下:
(一)《湘游日記》五冊,即督學湖南日記,起于光緒十一年(1885)八月初一日奉旨簡放湖南學政,迄于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二十五日等待后任接任期間,尚缺最后在湖南的約50天時間。這部分日記是較完整的學政日記,詳細地記載了陸寶忠從受命出任湖南學政,準備、赴任、接任及在湖南各府、直隸州衡文校士的全過程,非常清晰地呈現了一個學政三年兩考的路線圖。關于歲考、科考的基本程式,科場舞弊及其處置的種種情形,陸寶忠與湖南巡撫、司、道、府、廳、州、縣官員及地方紳士的交往,湖南的官紳關系與士習民風,以及陸寶忠自己的日常生活與生命感悟,均有較為詳盡而鮮活的記載,是研究晚清學政與科舉制度及湖南地方史的重要資料。對此,筆者曾撰有專文研究(2)李細珠:《晚清學政的日常事務與生活世界——陸寶忠督學湖南日記稿本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6期。,可以參閱。
(二)《使東日記》一冊,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初八日至九月初八日,任山東鄉試主考官日記。這部分日記較詳細地記載了一個鄉試主考官從受命、上任到監考、閱卷、錄取的全過程,也涉及陸寶忠與山東巡撫李秉衡及一些地方官員的交往事跡。
(三)《讀禮日記》二冊,分記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初十日,因丁母憂賦閑在京之日常生活。這部分日記涉及戊戌變法時期及政變之后京師官場動態,所記雖然簡略,但其透露的蛛絲馬跡對于了解相關史事不無補益之助。
(四)《己亥庚子日記》一冊,記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十一日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三日,服闋之后重回南書房,并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的公務活動。這部分日記涉及己亥建儲冊立大阿哥及大阿哥教育等相關史事。
(五)《燕軺日記》一冊,記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十二日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三月三十日,任順天學政赴大名、河間等府主持歲考、科考事務。這是陸寶忠第二次出任學政的部分日記。
(六)《監臨日記》一冊,記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十六日,赴河南開封監臨順天鄉試。其時,因庚子事變京師貢院被毀,順天鄉試借闈河南省城開封補考。這部分日記記載陸寶忠以順天學政在開封監臨順天鄉試的歷程,也涉及其與當時河南前后任巡撫錫良、張人駿及其他地方官員的交往事跡。
(七)《丙午日記》二冊,記光緒三十二年(1906)全年(缺十月初九日至十一月初二日)京官生活。當時陸寶忠任職都察院左都御史(官制改革后任都御史),并在戴鴻慈出洋期間兼署禮部尚書之職。這部分日記涉及丙午官制改革時的官場動態及陸寶忠的反應與政治取向。
(八)《丁未日記》一冊,記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京官生活。可惜該年上半年日記缺失。其時發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凱勢力擊敗瞿鴻禨、岑春煊等人,陸寶忠明顯同情瞿、岑而不滿奕、袁。隨后,袁世凱進京入樞,陸寶忠被勒令停職限期戒煙。因政敵借故傾軋,陸寶忠內心非常郁悶。這部分日記反映丁未政潮之后官場變動及陸寶忠晚年失意憤激的艱難處境。
關于陸寶忠日記的史料價值,前揭馬忠文先生一文已做重點論述,提示了幾點重要內容:一是對戊戌政變后滿洲權貴的批評,二是反對袁世凱和丙午官制改革,三是袒護趙啟霖、奏請嚴禁黨援,四是戒煙與黨爭,五是有關科舉制度的珍貴資料,六是其他如南書房翰林享受的優厚待遇等。以下再做幾點補充。
二、對晚清政局的觀感
陸寶忠所處的時代,是近代中國動蕩與變革的時代。他長期任職南書房、內閣、禮部、都察院等衙門,有較多接近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及當朝王公重臣的機會,可謂天子近臣、朝中顯貴。作為晚清官僚體制中的重要成員,他對時局的觀察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時代的縮影。
陸寶忠現存部分日記涉及晚清歷史上戊戌變法、己亥建儲、庚子事變、丙午預備立憲與官制改革、丁未政潮等牽動清朝政局變動的重大政治事件。盡管他可以近距離觀察這些政治變動,但他非常謹慎,在日記中惜墨如金,只是有所涉及而并沒有太多的記載。對此,陸寶忠自己曾經吐露了心聲。光緒二十六年(1900)二月初一日,陸寶忠記載給好友張曾敭(小帆)寫信時有謂:“寫小帆信,中多傷時語,此后亦宜謹慎,末世人心,不可不防也。(小帆乃素心人,屬其閱后即焚。)”(3)本文征引陸寶忠日記為未刊稿本,無頁碼,文中直接寫明年月日,全文同,不再一一說明。可見陸寶忠并非漠然無視一切,其實毋寧說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只因其對時局的判斷不容樂觀,深感人心莫測而不得不謹小慎微。正因為陸寶忠相關記載的文字不多,可知其下筆時是如何字斟句酌、左右權衡,如此發自肺腑地慎重表達,其所透露出來的蛛絲馬跡,或許可謂其內心觀感的真實寫照,因而益顯珍貴。
關于戊戌變法。當時陸寶忠丁母憂賦閑居京,其日記幾乎沒有記載變法的舉措,有少許涉及政變的文字,都是用小字寫在每天日記正文中間或后面,顯然是事后補記。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本日慈圣自園還西苑。”初六日,“本日拿康有為,已先日出京矣。”初九日,“本日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拿問,電旨拿梁啟超。”十三日,“本日康廣仁、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正法。”只是簡單記事,沒有任何評論。盡管如此,但陸寶忠對于變法之事并非無動于衷。有兩則日記可見其對變法的憂心:一是當年七月十八日所記看湯壽潛《危言》的感受,有謂:“午后,看湯蟄仙《危言》,可采處多,然亦有書生之見,能說不能行者。世變至今,真五千余年第一創格,天殆將混一全球乎?然中華民智未開,人心太壞,浩劫將臨,其慘殆不忍言,不知我生能免見之否?”二是七月二十三日閱讀《宋史》王安石變法的感受,有謂:“閱《宋史》荊公變法,引用小人,卒釀徽欽之禍,其時宋尚承平,且有正人與之爭論,荊公雖執拗,而其學問甚辨博,貽禍且然,況遠不如彼者乎?”顯然是針對時事有感而發,而且對康梁變法并不滿意。后來還有一些日記,也可見陸寶忠對于康梁變法是持反對態度。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三日,“看湘人所刻《翼教叢編》,彼康梁固罪不容誅,而刻書者事后自居正士,仍是一派求名求利之心,未可為真君子也。”十月二十八日,“在稚夔處借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閱之,令人憤憤。”十一月二十九日,“訪燮老……去夏參康片引喻切當,臨遞時抽去,不免有觀望之心,殊可惜耳。”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六日,“季樵來答,憶戊戌初變法時,見其熱中,即屢規之,今罷官以山長自活,亦可憐已。”說康梁“罪不容誅”,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很氣憤,惋惜孫家鼐(燮臣)當年參劾康有為臨陣退卻,屢阻王錫蕃(季樵)參與變法,均表明陸寶忠與康梁不是同路人。
關于己亥建儲。陸寶忠服闋之后重回南書房不久,近距離觀察了冊立大阿哥儀式。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記載:“晨起。先祭神畢,入直。辰正初刻,偕同事至瀛秀門外伺候。巳初叫起,同詣儀鸞殿東暖閣。太后、皇上并在南窗北向坐,阿哥侍立在太后旁。諸臣齊跪。太后玉音甚低,聽不分晰。上親遞紅絨結頂帽,令阿哥換戴,免冠碰頭后,太后命:‘先與我叩頭。’阿哥叩頭畢,復向上叩頭,隨侍立在旁。太后將朱諭交慶邸,令諸臣同閱。即出,在外略待,同至軍機聽起屋內恭閱畢,復同至書房吃飯,散。瞻仰天顏,清瘦已甚,不禁泫然。歸后料理瑣事,寫劬庵信。竟日如醉如癡,國運至此,后憂方大,何生不逢辰耶。”這則日記透露出三個重要信息:一是慈禧太后非常強勢,冊立大阿哥是其強勢所為;二是光緒皇帝很可憐,陸氏深表同情;三是陸寶忠對朝政非常擔憂,暗自慨嘆前景不妙。陸寶忠還有關于大阿哥教育的看法。光緒二十六年(1900)正月二十一日記載:“謁蔭軒師,適錫聘之在座,談及大阿哥功課。蔭老謂以講貫為第一義,而文山師以為須熟讀,理自明,兩人意見似不合。帝王之學與呫嗶異,且年已十六,尚不趁早講明道理,異日何以出治。蔭老之見,高于崇師多矣,所談頗暢達。東海究有見地,道光末年即在工部當差,所見先朝規矩較多,舉朝無出其壽,精神尚健。祝其期頤,尚可補救于無形也。”此中蔭軒師、蔭老、東海均指徐桐,文山師、崇師即崇綺,兩位都是大阿哥師傅,也是陸寶忠中進士時的座師。徐桐以固守程朱理學著稱,是守舊派代表。陸氏把大阿哥教育寄希望于徐桐,還是著眼于傳統正學教育。
關于庚子事變。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年)二月二十七日,陸寶忠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現存該年五月十三日以前日記,沒有關于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華事件的任何記載。光緒二十八年(1902)三月二十六日,陸寶忠日記載:“閱《畿輔通志》,教匪起事在大名,毗連齊豫一帶,近畿如固安、黃村亦多。嘉慶年間,禍發數次。拳匪起時,猶不知防范,且引用之,可謂顛倒錯亂。”此所謂“拳匪”就是義和團。可見陸寶忠對當年朝廷處置義和團不當并不滿意。
關于丙午預備立憲與官制改革。陸寶忠日記記載非常簡略: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讀預備立憲上諭。”十四日,“今日有上諭派編纂官制各堂官,都察院派壽子年,余可藏拙,乃幸事也。”當時朝廷宣布預備立憲,從官制改革入手,并隨即選派編纂官制館官員,陸寶忠以未能參與為“幸事”。兩個多月后,清廷公布新的官制,仍然保留都察院,陸寶忠為都御史。其九月二十一日記載:“八鐘起,見昨實行厘定官制上諭。……午間,小趙來,知仍留察院,埜秋調郵傳部尚書,燮鈞調禮左,隨即擬謝恩折。四鐘,始見上諭:都察院都御史仍著陸補授,副都御史仍著伊克坦、陳名侃補授,欽此。署中人來,知已辦公折,明晨赴園謝恩,自擬之稿,可不用矣。”官制改革涉及人事安排與權力分配,各派政治勢力明爭暗斗。陸寶忠深為憂慮,其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記載:“適徐菊人來,談東三省情形甚悉,俄之魄力最大,日之心志最齊,吾則事事腐敗,受制于兩大,已無自強之望,而京中士大夫不知公益,不思國恥,專為蝸角之爭,可為嘆息痛恨!”
關于丁未政潮之后的政局。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發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凱勢力擊敗瞿鴻禨、岑春煊等人,進而牢固掌握清朝中央政權。陸寶忠站在同情瞿、岑的角度,對奕、袁勢力頗為不滿。其七月二十日記載:“傍晚,馬景山軍門(玉崑)來拜,談時事,亦知當國者無主宰,用人不當,專以張皇無據之言哃喝兩宮,大局殊為可慮云云。武夫所見如此,則政府之不愜人望可想矣。”在此他借馬玉崑之口,批評“政府之不愜人望”。七月二十六日,陸寶忠從邸抄看到大學士張之洞、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均補授軍機大臣,便發出“從此朝局將大變矣”的感慨。陸寶忠擔心袁世凱入樞之后與首席軍機大臣奕劻狼狽為奸。七月二十八日記載:“北洋楊士驤署,川督放陳小石,鄂督趙次珊調,張小帆調蘇撫,馮汝骙驟得浙撫。此皆項城之措置也。時局至此,專用私人,所謂勵精圖亂,破格用己,甫執政柄,即毅然為之,勢不至亡天下不止,可為痛哭!”袁世凱甫入樞,便在督撫中安插私人,使陸寶忠頗感政局可危。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陸寶忠日記還不時透露出一種強烈的“末世”感,這是其親身經歷與近距離觀察政局變動及社會變遷的深刻而痛苦的體驗。治近代史者往往津津樂道同治六年(1867)兩江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之間那段著名對話(4)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與趙烈文閑聊,“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良久,再問:“然則當南遷乎?”趙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樊昕整理:《趙烈文日記》第3冊,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1479頁。),并驚嘆趙烈文對清朝國運驚人的預測。其實,在晚清時期,清朝統治在內憂外患之中風雨飄搖,有識之士對國家前途與命運深感憂慮不足為怪。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張之洞就曾致書守舊派首領人物大學士徐桐大發警世危言:“若不急謀自強,恐有再圖十年之安亦不可得。”(5)《致徐蔭軒中堂》,《張文襄公函牘未刊稿》第3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張之洞檔案”,檔號:甲182—393。陸寶忠日記則有多處表露清朝國運將盡、已到“末造”“末世”的悲憫心態。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1899年1月15日),“閱《甲申傳信錄》(抄本,嘉善錢士馨稚農談國初人,中有違礙之言,故世不多見),當時食祿之臣良心喪盡,末造人心先死,而后家國隨之,千古一轍,能無愾嘆?”光緒二十五年(1899)九月二十六日,“連日看《北盟會編》。午后,又看《崇禎朝記事》,江陰李遜之膚公(李忠毅公應昇之子)撰。從古亡國破家,皆由于賢否混淆,君子難進,小人易進,營私罔上,而宗社淪亡,可不懼哉?歷觀往事,以驗今時,宋南渡時,人才尚盛,即崇禎時,如熊廷弼、孫承宗、文震孟、黃道周諸人,皆才德可用,如烈皇信而任之不猜,終不偏執,不用奄寺,猶可支危局。今環顧諸公卿,果孰能遺大投艱乎?人才消乏,至期已極,可為憂嘆。”十月十二日,“飯后,赴郝琴軒云山別墅約,同座為趙寅臣、徐花農、何潤甫、李伯屏及西賈二三人。……言及臺州教案,皆府縣釀成,致殺人如麻,害及無辜,民心不服,近有罷考之事。噫!近時吏治不講,小民受累,害及國家,從古末造覆轍相循,可勝浩嘆。”十一月二十七日,“燈下,仍看《政書》(引者注:《胡文忠公政書》),不禁感慨系之。當咸豐末年,粵匪蹂躪半天下,繼以庚申木蘭之狩,大局岌岌可危,然卒能力持危局,馴致中興者,以外有胡、曾諸公(文忠為首功,惜年不永,然規模宏遠,志慮忠純,勘定東南,皆基于此,是為不世出之杰。曾尚亞之,左以下無論矣),內有恭邸及李文清、文文忠皆力主公道,不掣將帥之肘。今時局日非,設胡文忠生此時,恐未必能行其志,況顛倒錯亂乎?當日人心吏治已日非,亦尚未落今之甚,今糜潰至不可收拾矣。外患內憂,相逼而來,必至內訌由外患而起,外患即乘內訌而來,瓜分豆剖之局成矣。中原兆姓將為人之魚肉,為人之奴隸,為人之狗彘,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劫也。欲挽回之,非改弦更張,力持定見,齊心協力,濟以猛毅不可。先節國用,求將才,清吏治,結民心,庶有支撐之望。生非其時,體又日弱,此恨殆付之終古矣。漫記于此,以寄吾悲憫之心。”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初十日,“得王紫翔信,謂吾婁三百年來,以京官躋一品者,惟王顓菴一人,今繼其躅,務善自樹立云云。顓翁當康熙盛時,雖以建儲觸怒,而天下想望豐采。今當末造,內憂外患,相逼而來,自問既無學問,又乏經濟,浮沉其間,徒速官謗,可愧可愧!”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8年1月27日),“傍晚,夢陶來談,亦述陳瑤圃之言,與鳳老所云適合,斷無再出之理。宦海風波,古今人經此者不少,惟須心有把握耳。所述蘇省公呈,請親貴出了路事,聞之可嗤。末世人心如此,焉得不敗?”陸寶忠晚年“以朝局日壞,益形憂憤”(6)陸寶忠自訂、陳宗彝續編:《陸文慎公(寶忠)年譜》,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8輯(575),臺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96頁。,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四月病逝,其時距清朝覆亡僅三年多時間。應該說,其多年來“末世”感的準確度并不亞于趙烈文隨口一說之預測。
三、對晚清人物的臧否
陸寶忠日記涉及人物眾多,不少是晚清歷史上的要角。與對政局變動的記載較為謹慎的情形略有不同,陸寶忠對所見人物則時有評騭,甚至任意臧否,雖三言兩語,不免一孔之見,但這些文字對相關人物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
早在湖南學政時期,陸寶忠與當時湖南巡撫卞寶第及繼任巡撫王文韶、前任湖南學政曹鴻勛、道員莊賡良、永順知府張曾敭等人交往密切,其日記有不少相關記載。前揭拙文有詳細介紹,此不贅述。陸寶忠日記對李秉衡、盛宣懷、袁世凱、孫家鼐、劉坤一、徐琪、錫良、周馥、梁敦彥、唐紹儀、趙爾巽、徐世昌等人的品評,也頗值得玩味。
李秉衡(鑒堂)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由山東巡撫升任四川總督時,陸寶忠正任山東鄉試主考官,其九月初三日記載:“午后,聞鑒堂升蜀都之信。此公清廉,當今第一,但自用之性已甚。深慮其過于操切,以治山左之法行之,必致生事,交淺未可言深,聽之而已。”
盛宣懷(杏蓀)與陸寶忠以江蘇同鄉交往頗密。在陸寶忠看來,盛宣懷是洋務專家。有兩則日記可證:光緒二十五年(1899)九月初六日,“盛杏蓀來,長談時局,西伯利亞路成時將不堪設想,論大局甚透徹,可為嘆息痛恨。”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月十六日,“盛杏蓀信謂:新政以改科舉、改學校為先,沿江沿海少年高興,若使根底不清,十年之內不知如何變局,故講求西學轉當以宋學為本,小學堂所以端蒙養之本,課本亟宜預定,師范亦宜講求。公視學畿輔,若能勸諭各府州縣先立小學堂,便是第一入手功夫。其言極可味。杏蓀乃講洋務者,而所言如此,亦見近日浮躁少年專思以新學為進身之捷徑,防其流弊,故立論甚平正。”
袁世凱(項城)與陸寶忠不在同一戰線,陸寶忠對袁頗有微詞。有兩則日記:一是陸寶忠不愿意推薦朋友蕭紹庭入袁世凱幕府。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十四日,“得紹庭信,求薦本初(袁紹字,代指袁世凱——引者注)幕,乃無聊之極思也,即復之。”二是丁未政潮之后,紹英(越千)勸陸寶忠暫時避開與袁世凱的矛盾。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08年1月25日),“午間,紹越千來長談,亦以項城既齟齬,以暫避其鋒為是。此人手辣心狠,國事亦日益糟,其名譽亦日益損,但大權在握,不值再受其侮,務愛惜此身,以為他日報效地步而已。噫!未來事不可知,聽之而已。”
孫家鼐(燮臣)與陸寶忠是親家,官至大學士,兼光緒皇帝師傅。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九日,“訪燮老,年逾懸車,官至師相,奉身以迎恩禮,始終不得,謂非人生之榮遇,所惜者逢時不偶,無補世艱耳。然此老涵養深純,中有所主,不隨人轉移,與常熟共事時,甘心退讓,及其蹉跎,不為所累,相幾而退,絕不游移,亦有不可及處。”此處涉及孫家鼐與翁同龢(常熟)的關系,顯示孫氏圓熟老練的政治定力。
劉坤一(硯莊)在己亥建儲時的忠直建言頗為時論稱許,陸寶忠也不例外。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月初五日,“午初,劉硯莊制軍來長談,召對時語及時事,頗多忠直之言。此老尚有見地,非專事揣摩迎合者,惜年老體衰,不能振作有為耳。”
徐琪(花農)是陸寶忠南書房同事,其為人處世被陸氏所不齒。有三則日記: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902年1月26日),“午后,寫徐東甫信,為領本任俸銀米事,秋季俸銀未領著米事,徐花農設法領去,此人可謂貪鄙無恥。”十二月二十五日,“閱《京報》,知花農褫職,咎由自取。”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二十七日,“徐花農之夫人廿三沒,今日其次媳又沒,斯人家運太壞,況又極窘,深憫其暮境頹唐也。”
錫良(清弼)任河南巡撫時,陸寶忠以順天學政在開封任順天鄉試監臨。起初,陸寶忠對錫良并無好感。光緒二十八年(1902)八月初四日記載,“汲令鄭克昌借洋教士之勢,不畏上司,不恤民事,可惡已極,而錫中丞并不敢參撤,可謂外強中干。”后來,通過較長時間接觸了解,陸寶忠改變了對錫良的看法。其當年九月二十三日記載:“巳正,出門拜客。晤清弼,長談。……飯后,會客,清弼來,又長談,此人清正可佩。”當時張人駿(安圃)接替錫良任河南巡撫,陸寶忠正好與錫良一起離開河南省城開封。其九月二十五日記載:“九鐘二刻行,至北門外官廳,錫中丞先在,略坐。安老率屬跪安,予與清弼并立,答以回京轉奏,即行。沿途送者絡繹,行不數里即下輿周旋,皆送錫帥者。十一鐘二刻至河干,偕錫帥在棚略坐。曼伯、何紹軒及道府數人周旋畢,即祭河,登舟。東寅、謹菴皆依依,恩均、徐思勤、郭其章皆到船送,乃為予來者。棟甫送至道口。舟行約三刻,即登北岸。過新店,首府、縣在道旁送。錫帥今日住新店,明日停一日,讓予先行。”十月初九日,“夜飯后,錫清弼來長談,此公見識卓越,其清風亮節,令人欽佩,與余頗相得,真畏友也。”
周馥(玉山)與陸寶忠交往不詳,或許因為陸氏以周乃袁世凱私人而不滿。光緒二十八年(1902)陸寶忠從開封回京途經山東時,與友人談及時任山東巡撫周馥,頗為不屑。其十月初七日記載:“黎明起,請惺伯(送阿膠、掛面)登舟,談良久,述周玉山種種乖張,專事諂媚外人,剝削百姓,可為嘆恨!朝廷如此用人,其何能淑?”
陸寶忠還在日記中對比品評留美幼童出身的梁敦彥與唐紹儀(少川),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五日記載:“梁崧生星使(敦彥)來答,談良久。此君安詳靜穆,議論平正,絕無洋學生出身習氣,較唐少川有靜躁之別。”又與卸任盛京將軍趙爾巽(次珊)閑談,痛斥新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菊人)“庸妄”,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初十日記載:“趙次珊來談,以徐菊人參財政局各員,憤憤不平。徐菊人到任后,一無展布,徒知媚外,經人彈劾,轉疑前任運動,用此辣手,可謂庸妄。朝廷如此用人,焉得不壞?”對唐紹儀與徐世昌的批評,實際上又一次發泄了對奕劻、袁世凱勢力的不滿。
四、晚清變局中的個體角色定位與生命感悟
陸寶忠日記里有許多關于個人日常生活的鮮活史料。無論古今中外,所謂宏大敘事式的大歷史書寫都很少涉及個人生命史。私人日記作為深具個性特質的私密性史料,則是這方面無可比擬的獨特材料,但一般都比較零碎,個人生命史不會在日記中自然呈現出來。如何從日記重建個人生命史,是值得探討的新課題。
關于陸寶忠家庭生活狀況與日常生活情趣,前揭拙文曾利用其督學湖南日記做過詳細介紹,可以參考。這里再就其個體角色定位與生命感悟提示兩點:
一是陸寶忠政治立場保守,但并不守舊。一方面,陸寶忠并不是一個頑固守舊的人,對近代新事物不但不一味排拒,而且能夠積極接納。日記中有不少陸寶忠閱讀翻譯新書及新式報刊的記載。比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五日,“數日看《泰西新史攬要》。”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二十二日,“閱上海譯書公會所譯各種,亦足增見聞。”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902年1月23日),“閱《萬國通史》前編。”光緒二十八年(1902)二月初四日,“午前,閱各報。飯后,略睡。補寫杏蓀信,計十三紙,索南洋公學堂已譯書。”陸寶忠與晚清著名翻譯小說家林紓(琴南)過從甚密,喜歡閱讀林譯小說。如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二日,“閱林琴南所譯《紅礁畫槳錄》,此君言情之作皆勝,惟太幽折,不及《茶花女》《迦茵小傳》之明媚。”日記中還有陸寶忠喝洋酒、咖啡的記載,這在晚清高官中應該算是很時髦的了。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907年1月26日),力軒舉給陸寶忠診脈看病,建議他“酒不必戒,可服勃蘭地(白蘭地——引者注)及葡萄酒,加非(咖啡——引者注)亦可常飲(每飯后服之,茶宜少飲)。”陸寶忠還把其第三、四兩個兒子送到日本、美國留學。光緒三十二年(1906)三月初九日,“三、四兒赴東洋游學,慕周送之,同行附日本使署參贊鄭永邦伴。伊兄弟根底太淺,志氣未定,余本不愿其遠離,乃其念甚堅,當此過渡時代,亦未便強抑之,只得令其東游。付學費川資九百十五元,大約可敷一年之用,幸有柯亭、亮儕在彼,尚得所因依,至成否則仍在自為,父兄不能操其柄也。送其登車時,老人不無眷念,而伊輩自若。”其三、四兒從日本留學一年回來后,陸寶忠又通過熊希齡(秉三)聯系兩江總督端方(午橋),為三兒謀求南洋官費生(并帶四兒自費),隨駐美公使梁敦彥(崧生)赴美。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五日,“熊秉三來,托其發電午帥,為三兒謀官費生,如得成,則四為自費生,于九月中隨同梁松生赴美。”后因梁敦彥改署外務部侍郎,伍廷芳(秩庸)任駐美公使,陸寶忠又把三兒托付給伍廷芳赴美,四兒則再赴日本留學。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以四兒今日重游日本,手書一紙告誡之。……十一鐘,四兒行,叩別時,含淚諭之,乃母淚出如涌,而伊不甚眷戀,此乃年幼輕別離之常態,不足責也。”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間,三兒進見,勖勉之,以明日起程赴滬,隨伍公使赴美游學,此去至少六、七年,能否學成,其學費敷用否,皆不可知,可謂冒險,然業已成局,只得聽之。”陸寶忠認定其所處“過渡時代”,故在新舊之間不難取舍。
另一方面,陸寶忠也主張變法,屬于比較溫和穩健的改革派。他在戊戌時期反對康梁變法,在新政時期站在袁世凱官制改革的對立面,可能與變法的路線有關,或者說與政治派系利益有關。戊戌政變之后,在維新變法與清末新政之間的低谷時期,陸寶忠從友人處聽說日本向西方學習的進步狀況,表示了對變法的認同。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初一日,“柯亭到京,述東瀛諸事整齊,步武泰西,三十年來日增月盛,其人皆勤,無一游手好閑者,可見法之不可不變也。”庚子事變之后,清末新政展開,興辦新式學堂是其重要舉措。陸寶忠任順天學政,在從開封監臨回京途經各府、州、縣時,對各地興辦新式學堂很重視。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月初九日,“七鐘起,船已行四十里至泊頭,屬南皮。縣令王樹泰(號岳生,湖南人)來見,人尚老成。詢以學堂事,現已捐富戶書院,屋尚敷用,大約冬春可以開辦。”十月十一日,“九鐘至靜海縣(四十里),縣令沈葆恒來見。詢以學堂事,知已開辦,靜海風氣先開,教習尚易延。”后來,當他的好友張仁黼(字劭予)在學部受到排擠時禁不住慨嘆:“劭予之不容于學部者,以不能附和蜀黨之故。學部尚書中無定識,而疑忌性成,將來必貽笑話。學務不能整飭,中國更無振興之望矣,可為浩嘆!”(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廢科舉之后,有人向陸寶忠建議復科舉,他不以為然。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八日,“王子祥來信,意欲予請復科舉,可謂舊矣,置之一笑。”陸寶忠對新政是贊成的,但反對做表面文章。他在琉璃廠看到新設巡捕的功效,“惟設有巡捕,車馬并不擁擠,行人亦不紛擾,此乃從前所無也。”(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他在京師大學堂看運動會,引發對學習外人的感慨:“至大學堂觀運動會。所謂體操者,乃練習筋骸,為衛生之助,而競走一場,竟有爭先暈倒者,是不特無以衛生,且因之傷生矣,殊非所宜。中國性質習慣皆幼,與外人殊,乃不學外人之堅卓忍耐,而獨學外人之表面,且表面亦不能似,甚無謂也。”(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陸寶忠與出洋五大臣端方、戴鴻慈多有聯系,對預備立憲和官制改革,不同意袁世凱等人的激進舉措,主張穩健改革。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初二日,“夜飯后,看立憲新書(書名《憲法啟源》,陳澹然著),似有見地。國民程度太低,非遲至十數年來不可,目下只有養其萌芽耳。”陸寶忠主張把都察院改造為國議會,作為立憲政體之議院的基礎,曾領銜上奏《請改都察院為國議會以立下議院基礎而符立憲政體折》。八月十八日記載:“所上請改都察院為國議會以立下議院基礎而符立憲政體折,奉旨交會議政務處議奏。飯后,赴臺。路遇孫壽州,約三鐘到寓。趕赴臺中,匆匆即歸。壽州已坐待,以折稿示之,極以為然,謂必贊成,與資政院雙峰并峙,冀于國事略有補救。吾輩皆一心為國,絕無絲毫私見于其間也。”可見,陸寶忠為推動實現“改都察院為國議會以立下議院基礎而符立憲政體”的主張,還曾與大學士兼資政院總裁孫家鼐(壽州)極力謀劃,雖然并無結果,但其溫和穩健的改革路線,與袁世凱一派甚至有廢除都察院的激進主張顯然不同。
二是陸寶忠對生命的感悟,發人深省。陸寶忠一生基本上還算順風順水,尤其早年從科舉正途入仕,長期入直南書房,為天子近臣,深受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恩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1900年1月10日),五十歲的陸寶忠在丁母憂二十七個月服闋之際,決計復出之后勉力報效朝廷。其當天日記載:“巳初,上祭,巳正,易吉服,親朋來者將二十人。傍晚,恭請神主,至后照房中間,升祔先光祿公神龕之右。率家人行禮畢,撤靈座,從此事親禮畢。十七日詣闕,當勉力報效,以答特達之知。時局雖難,人心雖壞,自有應盡之職,不必矯激以沽名,亦斷不可淟涊以負國,中立不倚,不植黨援,不通聲氣。倘萬不可為,則引身以去,葆吾清白家風。人生如夢幻泡影,功名富貴,何足系戀,惟事事持正,不為威愒,不為利疚,可以自主,子孫能自立與否,亦不能預籌,聽之而已。燈下志此,務隨時警醒,勿墜先大夫遺訓,及先慈鞠育教誨之苦心,至要至要。”隨后,陸寶忠重回南書房,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兼署禮部尚書。只是丙午官制改革與丁未政潮時,陸寶忠因站在奕劻、袁世凱勢力的對立面而受到排擠,晚年頗為失意憤懣。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三日,他在日記中自我反省有謂:“予胸襟向本灑落,五十歲前不甚知愁,自庚子遭患難,忽變為多愁多病之身,然前數年尚有自尋娛樂之時,今年則體日衰,心日窄,覺凡事不足解吾憂,時時悲天憫人,觸處皆增感慨。靜定思之,國事之壞,關乎氣數,斷非少數人所能挽回,即假吾事權,亦自問無此才力。至家事亦尚粗安,且向于生計亦不甚關心,垂暮之年何苦自尋煩惱?從明日起,務割棄一切思想,或獨坐以筆墨自娛,或出門訪友,于無味中覓有味,養此余年。若再沾滯,大病將至矣。燈下書此,以冀醒悟。”陸寶忠在回憶與張百熙(埜秋)、王懿榮(廉生)、黃紹箕(仲弢)、陳冕(冠生)同試南書房及五人不同命運時感慨頗深。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1月29日)記載:“噫!人生如夢耳,何必沾滯?以福命論,自以文達為第一。文敏之死至慘,而殺身成仁,自足千古。仲弢文采學問皆好,而遽至此。冠生福最薄,而家計尚裕。予矯矯自好,惟語言憨直,為世不容,家累太重,后顧茫茫,真不知作何結束也。”其時陸寶忠正因被朝廷勒令停職戒煙而身心備受煎熬。這與其說是陸寶忠感慨各位老友命途多舛,不如說是其對自己現實處境的悲觀寫照,同時也是對其所處時代前景黯淡的悲鳴。對照幾乎同時代的晚清重臣張之洞在宣統元年(1909)病危之際所寫的絕命詩“誠感人心心乃歸,君臣末世自乖離;不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喻詩”(7)陳曾壽:《讀廣雅堂詩隨筆節錄》,許同莘存《廣雅遺事及趙鳳昌來函等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許同莘檔案”,檔號:甲622—4。,以此便可理解陸寶忠多年來“末世”感的深刻意蘊與歷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