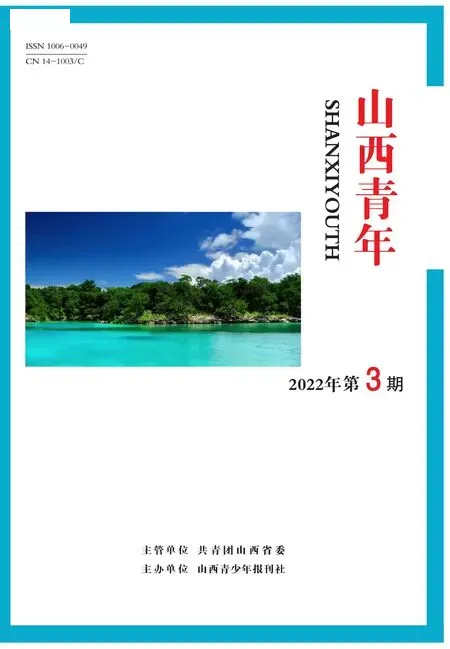我國古代服飾顏色詞的英譯探究
——以《紅樓夢》為例
劉 暢 李怡玲 陳 婕
南京工程學院,江蘇 南京 211167
《紅樓夢》[1]由清代小說家曹雪芹所著,被譽為我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全人類社會的文化瑰寶。作為一部兼具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偉大文學作品,《紅樓夢》對貴族家庭飲食起居等生活細節都進行了真實細致的刻畫,而對于人物的穿著服飾,作者也極盡筆墨。
《紅樓夢》中描寫的明清服飾蘊含我國傳統文化幾千年來的沉浮變遷,在書中也作為人物審美形態的重要表現形式,成為這部經典之作中不可忽視的亮點之一。同時,色彩作為人們認識世界的領域之一,與人類生活緊密聯系[2]。在文學作品中,顏色詞往往承載著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內涵,使得語言具有藝術性。作為語言和文化的研究課題,顏色詞也成為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因此,本文旨在通過具體分析《紅樓夢》中服飾顏色詞的英譯情況,進一步探究顏色詞的英譯策略。
一、顏色詞定義與分類
在顏色詞的分類研究中,最普遍的分類原則是將顏色詞分為基本顏色詞和復合顏色詞。
(一)基本顏色詞
目前對于基本顏色詞的數量問題依然沒有標準答案。比較著名的論斷如美國學者柏林(Berlin)和凱伊(Kay)在其聯合發表的專著中提出了基本顏色詞的理論[3]。該書共總結了十一種基本顏色詞:white(白),black(黑),red(紅),green(綠),yellow(黃),blue(藍),brown(褐),purple(紫),pink(粉),orange(橙),gray(灰)。此外,詹人鳳先生采用三條標準界定現代漢語的基本顏色詞,分別為專門性、概括性及非派生性。根據這三條標準,現在更為普遍接受的基本顏色詞有白、黑、紅、綠、黃、藍共6個[4]。
(二)復合顏色詞
復合顏色詞的分析可以從詞義和詞形兩個角度進行,本文主要從詞形角度進行分析。
從詞形的角度分析,復合顏色詞可以分為復合式、附加式、重疊式共三類。本文重點分析附加式復合顏色詞。附加式又分為前附加式和后附加式,前附加式多見于書面語中,后附加式則具有鮮明的口語特點。前附加式由表示色彩義的構詞語素前添加修飾性成分構成,如鮮紅。后附加式顏色詞則由表示色彩義的語素后添加修飾性成分構成,并以重疊的形式出現,有較強的感染力,如綠油油[5]。
(三)紅樓夢顏色詞使用概況
在運用顏色詞的精準性與創造性方面,《紅樓夢》在我國整個文學史中無出其右。通過對1982年紅校本《紅樓夢》[6]中顏色詞使用情況的全面分析,發現《紅樓夢》共使用顏色詞228條[7]。曹莉亞關于顏色詞使用頻率的數據表明,《紅樓夢》全文中顏色詞共出現了1845次(人名、地名等專名中的顏色詞未計其中)[8]。
二、服飾顏色詞英譯實例分析
本文選擇了楊憲益、戴乃迭版本[9]與霍克斯版本[10]的英譯《紅樓夢》為參考,從基本顏色詞、實物顏色詞及其他復合顏色詞三個方面具體分析服飾顏色詞的使用與英譯技巧。
(一)基本顏色詞的英譯
本文從《紅樓夢》中使用的諸多基本顏色詞中選取“青”為代表,進行實例的分析。
“青”色的翻譯對于中外譯者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據《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11],“青”有藍色、綠色、黑色等多種意思,因此,在翻譯中,“青”色的翻譯需要根據實際使用情況作出適當的選擇。
《紅樓夢》第三回中,作者在描寫賈寶玉與賈府一丫鬟的著裝時,均使用了“青緞”一詞。賈寶玉“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而丫鬟則是“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在第四十二回中,作者又以“青皺綢一斗珠”來形容賈母所著的“羊皮褂子”。在以上三個例子中,楊憲益分別將“青”色譯為“blue”“black”和“blue”,而霍克斯則均將其譯為“black”。
從以上翻譯對比中不難看出,楊傾向于將“青”譯為“blue”,即藍色,而霍則更傾向于將“青”譯為“black”,即黑色。在《紅樓夢》中,“青緞”是丫鬟常穿的上衣布料,除上文所舉例子外,作者對鴛鴦(第二十四回、第四十六回)、襲人(第二十六回)都曾有著青緞背心的描寫。
在第四十回中,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布料“軟煙羅”,據賈母稱:“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匹,做一個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里子,做些夾背心給丫頭們穿,白收著霉壞了”。
從賈母的話中可以看出,軟煙羅中的雨過天青色布料常用于丫鬟們背心的縫制,而這種布料可能正是“青緞”的來源。而賈寶玉、賈母等地位較高的人物所著的服飾與丫鬟們背心的“青”色極大可能并不是一種青色。因此,在翻譯丫鬟們所著背心顏色時,宜將“青”譯為“blue”,即藍色;而在翻譯地位較高人物所著服飾時,則宜譯為“black”,即黑色。此外,賈母稱需用雨過天青色軟煙羅“做一個帳子我掛”,如帳子為黑色,則并不符合傳統,也為“青”色的翻譯提供了依據。盡管如此,在實際翻譯過程中,譯者仍需根據實際情況與色彩搭配仔細斟酌,進行顏色詞的選擇。
(二)實物顏色詞的翻譯
《紅樓夢》中的實物顏色詞如“蜜合”“藕合”“秋香”等絢麗多彩,體現了高度的藝術美感。本文選擇“松花色”“月白色”與“石青色”,進行實例分析,力求在英譯過程中追求真實,還原其美感。
1.“松花色”的英譯
第三十五回中,賈寶玉在詢問鶯兒(薛寶釵的丫鬟)梅花絡的配色時,曾有這樣的對話:寶玉道:“松花色配什么?”鶯兒道:“松花配桃紅。”;而在第九十一回中,寶蟾(夏金桂的陪房丫頭)在設計勾引薛蟠時,則“上面系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在以上兩個例子中,楊憲益分別將“松花色”和“松花綠”譯為“light green”和“dark green”,而霍克斯則均將其譯為“viridian”。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霍克斯在翻譯時將“松花色”與“松花綠”認定為一種顏色,即“viridian”,意為“鉻綠色,青綠色”。而楊憲益則認為,“松花色”為“light green”,即淺綠色;“松綠色”則為“dark green”,即深綠色。顯然,兩名譯者在翻譯時均偏向于將“松花色”歸為綠色系一類,只是在深淺上有所不同。
針對“松花色”,唐《新修本草》[12]中記載道:“松花名松黃,拂取似蒲黃正爾。”唐代王建《設酒寄獨孤少府》[13]中也寫道:“自看和釀一依方,緣看松花色較黃。”據此,筆者認為,松花色與松綠色很可能是同一植物不同發展階段呈現出的不同顏色,松花色更偏向黃色,而松綠色更偏向綠色。因此,筆者傾向于將“松花色”譯為“greenish-yellow”,即“帶綠的嫩黃色”。但與此同時,由于詞匯翻譯的與時俱進性,將“松花色”歸為綠色系也并不意味著完全錯誤。
2.“月白色”“石青色”的英譯
第六十八回中,作者以尤二姐的視角描寫了王熙鳳“身上月白緞襖”;而在第三回,對于王熙鳳服飾的初次描寫中,她“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在以上兩個例子中,楊憲益與霍克斯分別將“月白”譯為“pale blue”和“the palest of pale blue”;而將“石青”譯為“turquoise”和“slateblue”。
“月白”和“石青”均屬于藍色系顏色詞。需要注意的是,“月白”并不是指白色。據《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月白”指淡藍色。因此,此處兩位譯者對“月白”的翻譯均比較準確。
第三回中的“石青”色,作為清代乾隆年間的流行色,往往為大家富室所著,用于較為莊重的場合[14]。楊憲益將“石青”譯為“turquoise”,意為“a greenish-blue colour”,即“綠松石色,青綠色”,雖然就漢語層面來看,楊的翻譯指向了綠色,但就“turquoise”一詞的英文釋義來看,該翻譯可供參考。霍克斯則將“石青”按字面義譯為了“slate-blue”,意為“石藍色”。就石青色本義來看,其顏色與深藍色較為接近,甚至接近黑色,而與綠色并無太大關系。因此,筆者認為,霍克斯的翻譯更加符合原義。
(三)其他復合顏色詞的英譯
作為《紅樓夢》中經常出現的復合顏色詞,“大紅”的翻譯需要譯者特別注意,以傳達出原文的神韻。
第四十九回中,出現了多處對復合顏色詞“大紅”的使用。例如對林黛玉“罩了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貍皮里鶴氅”與史湘云“頭上戴著一頂挖云鵝黃片金里大紅猩猩氈昭君套”的描寫。
在翻譯“大紅”時,兩位譯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在翻譯“大紅羽紗面白狐貍皮里鶴氅”時,楊憲益將“大紅”譯為“crimson”,意為“dark red in colour”,即“深紅色的,暗紅色的”;而在翻譯“大紅猩猩氈昭君套”時,他則將“大紅”譯為“scarlet”,意為“bright red in colour”,即“猩紅的,鮮紅的”。筆者認為,此處的轉變主要受后文“猩猩氈”影響,以“scarlet”同時譯出“大紅”“猩猩氈”兩種意思。與之相比,霍克斯的翻譯則更加直白,直接將“大紅”譯為“darkred”,與“crimson”意思相近,而在“大紅猩猩氈昭君套”的翻譯上失去了“猩紅”的意味。
三、結語
《紅樓夢》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經典著作,而豐富多彩的顏色詞被運用于服飾刻畫與細節描寫中,對于推動情節發展與展現文化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基于顏色詞的分類標準,以實例的形式具體分析了《紅樓夢》中服飾顏色詞的使用情況與英譯技巧。由于語言環境與文化背景的限制,譯者要在了解語言文化差異的基礎上選擇適當的翻譯方法,結合不同國家特有的文化和語言表達習慣,體會其深刻內涵,綜合使用不同的翻譯策略,更為精準地展現我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與魅力,讓我國古典藝術進一步為英語讀者理解和接受,推動我國文化對外發展,提高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