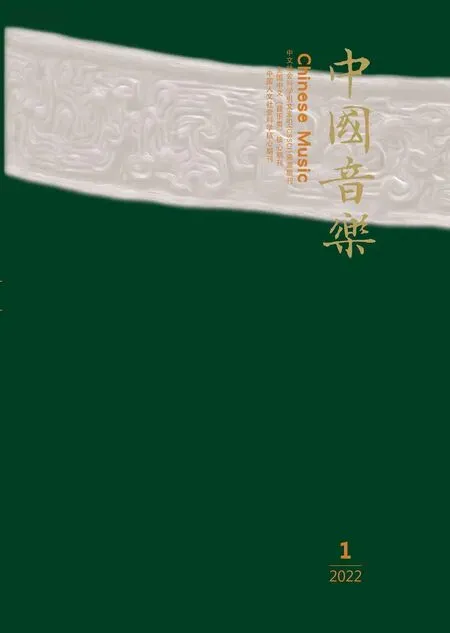風起于青萍之末
——從音樂與語言的關系看中國音樂的旋律學建設意義
○ 孟凡玉
人們常說“旋律是音樂的靈魂”,旋律對全世界的音樂表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是大家的一個共識。筆者認為,旋律對于中國音樂的意義更為重要,旋律學建設對“中國樂派”構建也具有更加特殊的意義。
一、語言是音樂的基礎
《尚書·舜典》說:“詩言志,歌永言”,道出了歌唱是語言的藝術化,即詠唱表達的真諦。追根求源,從音樂發展的歷程來看,器樂是在聲樂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盡管器樂作品擺脫聲樂的束縛之后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有了獨立的藝術品格,但是,水流千里終有源,樹高千丈須有根,從根本上講,器樂源于聲樂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毋庸置疑。而歌唱又是源于語言的藝術形式。《毛詩序》:“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十分生動形象地描繪了人類因情感激動,由語言到歌唱、由歌唱到器樂、舞蹈的發展歷程。由此,“語言—歌唱—器樂—樂舞”的發展脈絡清晰可見。
語言是音樂藝術的根源,語言的聲調、韻律、節奏之中孕育著音樂的胚芽。正如近代學者王光祈所說:“中國語言因其兼有四聲,忽升忽降,忽平忽止之故,其自身業已形成一種歌調。再加以平聲之字,既長且重,參雜其間,于是更造成一種輕重緩急之節奏。故中國語言自身,實具有音樂上各種元素。”①王光祈:《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頁。中國音樂的旋律深深植根于中國語言之中,所謂“風起于青萍之末”,所有的音樂之“風”,都起于語言這個“青萍之末”。
近些年來,中國音樂界提出建設“中國樂派”構想,多個項目以及眾多研究不斷取得成果,成為近幾年中國音樂界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中國樂派的音樂作品,旋律具有更為重要的表現意義。
語言是音樂的基礎。中國的語言是一種有聲調的語言,漢語語言的聲調具有表意功能,受母語的長期熏染,中國人不但善于表達語言聲調的升降起伏,而且,中國人的耳朵也非常善于捕捉聲調的起伏及其細微的差別,對旋律的感受能力也是特別強的。
二、漢語四聲中的音樂元素
中國的漢語是一種有聲調的語言,漢語語言的聲調具有表意功能。普通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聲調,很多方言還有更多的聲調,有五聲、六聲、七聲、八聲、九聲等不同情況。在中國的語言系統里,比如“媽、麻、馬、罵”四個字,其聲調不同,意義也隨之不同,聲調具有明確的表意功能。這些不同字調間的平行、上行、下行以及它們的各種復雜的組合形式,是形成歌唱旋律的基本依據,也是進而形成器樂旋律的主要根源。
關于中國語言的聲調與音樂的關系,早就有中國的先賢討論過。比如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在《詩論》里面就詳細討論了四聲的長短、高低、輕重問題,這三者與音樂的音高、節奏、節拍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不僅是詩的問題,也是音樂的基本問題。
在四聲的長短方面,朱光潛先生認為“四聲顯然有長短的分別”。他引顧炎武《音論》說法:“平聲最長,上去次之,入則詘然而止,無余音矣”,指出“近人多持此說”;還引錢玄同:“平上去入,因一音之留聲有長短而分為四”,吳敬恒:“聲為長短… …長短者音同而留聲之時間不同”,易作霖:“四聲是什么?… …它是‘拍子關系’,譬如奏1音(筆者注:簡譜do),奏一拍便像‘都’,奏拍便像‘篤’,就時間上分出四種不同的聲音,就是平上去入的四聲”②朱光潛:《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145頁。等諸家觀點,進一步論證四聲的長短關系。四聲有長短的差別,這是確定無疑的,不同的聲調有長短之別,組合起來就是節奏的胚芽。但各地四聲長短之間的具體差異又千差萬別。不同區域之間、同一區域的不同個人之間、同一個人不同情況下的發音,四聲時值都有可能存在一些差異,其差異無法準確定量,而這些差異,不僅是方言,也是音樂地方風格的形成原因之一。
在四聲的高低方面,各聲調的絕對及相對調值有很大不同,有高有低。據趙元任《國音新詩韻》:“陰聲高而平。陽聲從中音起,很快地揚起來,尾部的高音和陰聲一樣。上聲從低音起,微微再下降些,在最低音停留些時間,到末了高起來片刻就完。去聲從高音起,一順盡往下降。入聲和陰聲音高一樣,就是時間只有它一半或三分之一那么長。”③趙元任:《國音新詩韻》,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4頁。音與音連接,從而產生音的高低運動與不同走向的組合,恰似旋律運動的起伏軌跡,它是孕育音樂旋律線條及展開、發展的基礎。中國傳統聲樂中所謂“依字行腔”,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在四聲的輕重方面,四聲有輕有重,輕重的交替可以形成節律,和音樂的節拍、節奏有著密切的關系。一般認為,上聲、去聲較重,發音較為費力,平聲較輕,發音較為省力。如唐代《元和韻譜》說:“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④引文見朱光潛:《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147頁。《元和韻譜》今佚,〔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所附沙門神珙撰《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之序中的引文中保留了這段話,文字略有不同,各句第三字有一“者”字,意義完全相同。〔梁〕顧野王撰:《大廣益會玉篇》,呂浩校點,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1024頁。明末清初顧炎武的《音論》說:“五方之音,有遲疾輕重之不同… …其重其疾,則為入、為去、為上;其輕其遲,則為平。遲之又遲,則一字而為二字,‘茨’為‘蒺藜’,‘椎’為‘終葵’是也。”⑤〔明末清初〕顧炎武:《音學五書·音論卷(中)》,載《顧炎武全集》(第二冊),劉永翔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0頁。《康熙字典》引明朝真空和尚《玉鑰匙歌訣》:“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⑥《分四聲法》,載《康熙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字母切音要法”第4頁。這些輕重強弱的關系,反映在音樂上就是節奏、節拍的律動關系,它也會直接影響旋律的高低、長短、強弱等具體音樂形態,如曲家所指出的那樣,“凡曲,上聲當低唱,平入聲又當酌其高低,不可令混”⑦〔明〕沈寵綏:《度曲須知》,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五),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200頁。。可見,語言對音樂旋律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以詩傳樂是中國音樂的一個重要傳統。自古以來,在唱歌、聽書、唱戲、唱曲兒等各種音樂生活中,中國人的樂感受到詩樂傳統的巨大影響,在聽懂唱詞的前提下,唱腔音樂做各種潤腔,旋律線條豐富多彩,并進而滲透在器樂的旋律之中,形成中國音樂中獨具特色的以“三音環繞”為基礎的旋律發展衍進。例如,京劇《上天臺》中劉秀所唱“金鐘響玉兔歸王登九重”一段唱腔,其中第一句最后一個唱詞“重”字,就有長達18拍58個音符的拖腔(譜例略),旋律起伏跌宕、曲折婉轉。類似的旋律形態在中國戲曲、曲藝、民歌、器樂中也常可見到,并不是個例。如此變化多端的旋律形態,是中國音樂中獨有的。旋律自身的信息極為豐富,甚至不怎么需要和聲的補充,即可自成體系。
王光祈和他的導師霍恩波斯特爾曾經把世界音樂分為中國樂系、希臘樂系、波斯阿拉伯樂系等三大樂系。其中,中國樂系的音樂特征被歸納為“樂音的帶腔性”“織體的單聲性”“彈性節拍與彈性節奏”“旋法的五聲性”等,獲得較為廣泛的認同。可以說這幾個特點就是中國音樂元素、中國音樂風格中最基礎性的要素。而這些特點,帶腔性、單聲性、彈性節拍、五聲性旋法,基本上都是指向旋律本身的。由此可見,旋律對于中國音樂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的。
三、旋律寫作的誤區與旋律學建設意義
筆者曾經有過幾次現場聆聽不同的專業音樂學院作曲專業學生新作品音樂會的體驗,發現追求新奇(甚至怪誕)的音響成為一種時髦,而能夠讓人記住的旋律卻難得一現,甚至有些人對寫旋律很鄙視,不屑一顧。這種傾向值得深思。
近些年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在音樂學院作曲專業舉辦的新作品音樂會上,動聽的旋律成為稀缺物品、難得一聞了。有很多人都在追求的怪誕的音響,寫出很多連自己都聽不懂、識別不出、不知所云的作品。對聽眾更是一種聽覺的嚴峻考驗與痛苦煎熬。這種風氣愈演愈烈,發展成為一種趨勢、一種時髦兒。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深層次的文化心理究竟如何?我們在不否認很多有益探索價值的前提下,對那些偏離正確發展軌道現象的原因以及旋律學的建設意義作一些探討。
我認為形成這種現象,有以下幾點原因值得重視:
第一,音樂才能枯竭,無法寫出感人的旋律。一些天分不高的作曲者,缺乏音樂靈感,無法寫出動人的旋律,無可奈何之下,反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干脆不寫旋律,只寫一些難聽的“聲響”。筆者多次現場去聽所謂的新作品音樂會,無法忍受那些毫無音樂感覺的噪音,基本都是提前退場。本人認為那些難以卒聽、無法入耳、更難以入心的“聲響”,是稱不上“音樂”的,只能用“聲響”稱之。按照中國經典樂論文獻《樂記》的說法,“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如果那種無任何旋律、只配稱之為“聲響”的東西聽多了,人的品格就會降低,自甘沉淪到和只憑動物本能感知物理層面之“聲”的禽獸為伍,豈不是十分可悲、可憐!
創作這種音樂,還可以和畫不成人就去畫鬼相提并論。俗話說,畫鬼容易畫人難,因為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要畫得像需要很高的技巧、很深厚的功力,那是很難的。而畫鬼卻可以隨便畫,只要夠丑、夠難看,誰也不知道畫的是對是錯,因為那是一個沒有標準、人人都不知道的形象,無從判斷是非對錯。
第二,受一種盲從的文化心理裹挾,身不由己寫出這種作品,裝模作樣欣賞這種作品。創作這種作品,近一段時期,已經儼然成為一種時髦的趨勢,并且愈演愈烈,不斷蔓延,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如果不這樣就會被認為是落伍、不高級、低檔的一種認識上的誤區。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被裹挾,身不由己加入其中,一些本不愿如此的學生、老師,尤其是初學者,尚未形成自己穩定的音樂價值觀、審美觀,很容易隨波逐流,受到裹挾,迎合時髦,而去寫一些這樣的東西,偶爾寫出一兩句旋律,有可能遭到身邊人的恥笑,甚至自己也非常不自信,覺得自己怎么寫出旋律來了,十分害怕被人恥笑。
這個情況和大家熟知的《皇帝的新衣》寓言故事非常相似,面對鬼畜一樣的所謂音樂,人人都說“好”,生怕說不好,會被人恥笑,會被人說沒有品味、不懂欣賞,就像寓言故事中人們面對那位沒穿衣服的皇帝,因為騙子預設了一個前提—只有聰明人才能欣賞皇帝的新衣,傻瓜是看不到的—眾人才異口同聲夸贊皇帝的新衣服好看,其實什么也沒有看到,人們被裹挾著,都不敢、不愿意去捅破這層窗戶紙。
第三,片面的音樂價值觀、扭曲的音樂審美觀影響的結果。也有一些人本來具有很高的音樂素養、音樂技術能力,但是由于音樂的價值觀念扭曲,對音樂的本質、音樂服務大眾之基本功能與價值定位認識不足,而一味地追求新奇,追求怪誕,沉溺于個人的自我表達,而寫出這樣的作品,實在令人惋惜。
以上幾點可以說是存在于那些一味追求怪誕的作曲者們身上的痼疾,只有徹底破除這些心魔,才能走出誤區,回歸正道,返璞歸真,寫出具有人性光芒的真正的藝術作品,而不是依靠某種公式、某種模板計算出來的機械、死板、缺乏人性之光、沒有“人味”的所謂“音樂”作品。
本人呼吁作曲者應該回歸正道,努力寫出動人的旋律,讓作品“說人話”,表達人的真實情感,退一步說,至少要讓可聽性強的旋律在作品中占據重要地位,而不能都是那種無法留下鮮明記憶的東西。
音樂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譜寫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是必須堅持的創作方向。不管是“頂天立地”,還是“鋪天蓋地”,能夠得以傳承,才算是成功的作品。
在“中國樂派”建設的諸多要求之中,“以中國音樂元素為依托,以中國風格為基調”⑧王黎光:《堅守根本 與時俱進—建設“中國樂派”系列思考》,《中國音樂》,2020年,第3期,第5頁。是基礎性的前提條件。這就要求必須高度重視中國音樂以旋律見長的藝術特點,深入研究旋律構成的規律,在源自西方作曲技術理論“四大件”的和聲學、對位法、曲式學、配器法之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旋律學,深入研究旋律寫作的內在規律,提供音樂方面的中國經驗,做出中國音樂對世界樂壇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