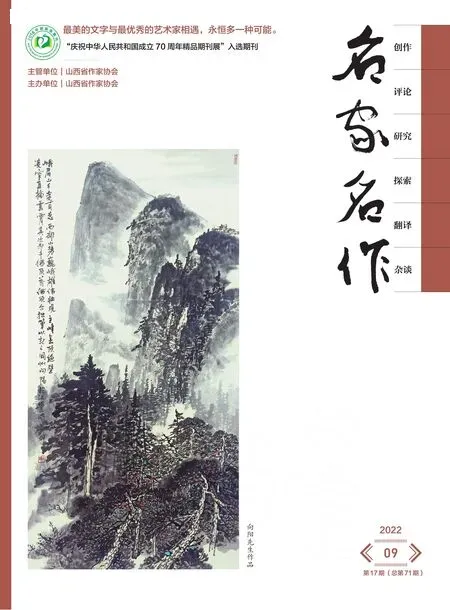歷來關于“思無邪”重要解釋梳理與淺析
徐 悅
“思無邪”語出自《詩經·魯頌·駉》,后被孔子用作《詩三百》的總評,《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此,“思無邪”成為《詩經》乃至詩學的一個重要命題。而歷來學界對“思無邪”的解釋頗有爭議,各家之言百花齊放。本文試從《詩經》和《論語》的源頭出發,以《四庫全書總目·詩經》為中心、不同注疏版本和出土文獻為研究對象,結合各時代的發展背景進行對比分析,探究“思無邪”的重要解釋,進而談談個人的淺見。
一、源頭:《詩經·魯頌·駉》中“思無邪”的本義表達
《魯頌·駉》位于《魯頌》第一篇,《毛詩序》認為該詩當為贊頌僖公“《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史克作是頌”。從具體文本來看,全詩的主體顯然是馬。全詩末尾連用八“思”:
思無疆,思馬斯臧。思無期,思馬斯才。
思無斁,思馬斯作。思無邪,思馬斯徂。
通過“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和“思無邪”等描述來吟詠馬的雄壯威猛和神態溢于言表。結合《毛詩序》及鄭玄箋,通過贊美馬來表達對魯侯的贊美,以此歌頌僖公養馬眾多,注重國家長遠發展的遠大格局。理解全詩主旨后再從語詞本義探討“思無邪”的具體解釋,這里的關鍵是“思”和“邪”的釋義。文中的八“思”作何用法,說法不一。每章末句的“思”字為句首語氣詞(簡稱:語詞),歷來并無爭議。但前一句的“思”字則有兩種說法,一說亦語詞,一說即思想、思考之思。
全詩三十二句,四章的開頭三句都是“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接著各列舉四種具體的馬,講馬的特點,最后是贊美之詞。綜合全詩,“思無邪”與前面的“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呈現出一種并列關系。其中的“疆”“期”“斁”和“邪”四字,意思大同小異,都有偏于一端之義,“無疆”“無期”“無斁”和“無邪”都指向表達馬的狀態俱佳。再看“思”,既然前三者中的“思”為語詞,那么“思無邪”中的“思”也當為語詞,而“思無邪”就是使馬兒沿著大道不偏斜。楊伯峻在《論語釋注》中認為,“思”字在《駉》篇本是無義的語首詞,是忠實于《詩經》文本的本義表達。然而經學家解讀《詩經》過程中,受到以孔子為代表的詩論及時代發展的影響,對“思無邪”的解釋多有不同,實際上偏離了《魯頌·駉》的文本。
二、身份轉換:《論語·為政》中的“斷章取義”之“思無邪”
“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斷章取義”是春秋時期重要的用詩方法,孔子用“思無邪”論《詩》,也屬于這一類。因此,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里的“思無邪”之解釋相比《駉》中的本義相差甚遠。結合前文文本解讀,孔子借用“思無邪”并非完全脫離文本,而是基于文本解讀的深度延伸。“思無邪,思馬斯徂”寫馬匹一致,孔子以此喻指《詩經》的詩也能不偏離中心軌道,忠實于儒學的中庸思想。
結合史料分析,從《詩經·駉》到孔子評詩,“思無邪”應該實現了華麗轉身,一定意義上是發生了身份的轉換。在《詩經·駉》中,“思”作為語詞,是無實義的虛詞。孔子“斷章取義”時大可刪去“思”,直接說“詩三百無邪”,但孔子用三字并列的形式闡釋對詩的評價,即“詩三百,思無邪”,這里可否理解成“詩”對應“思”,“三百”對應“無邪”,如此解釋,此處的“思”當作實詞,以此來表達孔子對《詩經》的看法。“思”到底指什么呢?“思無邪”又是指什么呢?這是孔圣人遺留下來的千古難題,歷朝歷代學者一邊忙著“注疏立言”,一邊忙著辨別真偽。俗話說,真理越“辨”越明,但經書之辨偽,卻難以撥云霧見青天。自漢儒以來,學者們各執一詞,既有揭示圣道王功者,又有“拿來主義”之“為我所用”者,總之各抒己見,將《駉》與《論語·為政》中的“思無邪”混為一談,難辨真假。
三、考究流變:辨析漢唐宋乃清儒之“思無邪”重要闡釋
《四庫全書總目》小序中寫道:“《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后則眾說爭矣。”基本反映了《詩經》的演變過程,同時四庫學者將清以前的《詩經》研究匯總為漢學和宋學之爭,指出古學者是在不同話語體系下的歷史語境表達。而“思無邪”作為評價《詩經》的總結性評語,其闡釋的流變也同樣反映了這種變化。
漢代《詩經》學是在圣人話語體系下的政治學說。漢儒鄭玄箋“思無邪,思馬斯徂”句曰:“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認為“思無邪”中的“思”作“思想、思考之思”解釋,而唐初經學家孔穎達注疏時也認同鄭玄的說法。由此,漢唐經學大家一致認為,《駉》乃“美僖公之頌”的“牧馬”之詩,表達執政者“盛德為政”。而“思無邪”,就以“思想純正”作解。后人多有認同,如邢昺《論語注疏》解曰:“‘思無邪’者,《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歸于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楊伯峻《論語譯注》譯作“《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就是‘思想純正’”。承襲了以上觀點。是以,漢學的《駉》“思無邪”解讀蒙上了政教意味的面紗,成為君臣情志的抒發。
宋儒所言經義,大都是將他們自己的學說套在古經上,無論好壞,總之十有七八非古經所本有。宋學釋《詩經》體現了儒學話語體系下的君子學說,自我修養之學。關于“思無邪”的解讀,“二蘇”和朱熹的闡釋體現了新的時代美學理念。以程朱為代表的宋儒關注“思無邪”義理的闡發,將《駉》中的“思無邪”與儒家的誠意正心、溫柔敦厚、性情之正、中和之美等附加意逐漸融合在了一起。由此,宋代理學家將“思無邪”中的“邪”理解成了“正”或“誠”的意思。而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認為,《三百篇》“不皆出于情性之正”,把孔子“思無邪”理解為“讀之者”“思無邪”,強調“思無邪”在于“讀詩之人”,把“思無邪”的主語作了置換。此外,朱熹還把《詩經》中的“鄭聲淫”合理化,認為“好底詩”能“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也能“起人羞惡之心”,達到“思無邪”之目的。“思無邪”不僅對儒家思想有傳播作用,對讀者自身的心性也有塑造作用。“二蘇”對“思無邪”的理解頗有獨創性,蘇軾的《論語說》和蘇轍的《論語拾遺》《詩集傳》皆從心性角度出發,融匯了儒釋道思想,提出了“無思之思”和“思其無所思”的概念,帶上了他們自身的文化符號。漢儒基于《詩經》本身審美意蘊和孔子的美學理念,融合其時代儒釋道審美精神,各有側重,但又互補,不失為將“思無邪”闡釋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漢學復興,清學者對于“思無邪”的解釋開始凌駕于歷時性注疏文本之上,逐漸回歸《詩經》文本。清儒方玉潤指出“思無邪”,“此一言也,實作詩者之真樞”。陳奐、鄭浩和姚際恒等學者從語言學的角度給出了不同的解釋,鄭浩提出“思無徐”“無邪猶無斁”,實為一種突破前人桎梏的壯舉。《四庫提要》則兼收漢學、宋學之長,構建了文本詮釋的新模式。此等發展說明學者開始跳出歷史語境的束縛。
四、回歸本義:基于出土文獻的開枝散葉
近些年,出土文獻的問世又給“思無邪”的闡釋帶來了許多生機。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楚竹書《詩論》中的《語叢三》有“思無紿”和“思無邪”,強調“思”出自人的自我誠意,同時“思”還是個人的主動行為。而于省吾先生結合文字學考釋法,將“思無邪”的“邪”讀作圄,通“圉”。那么“無邪”即“無圉”,猶言無邊,無邊指牧馬之繁多言之。根據《詩論》核心,有學者認為孔子以“思無邪”概言《詩三百》,乃是指三百篇之蘊藏既富且廣、無所不包。
還有學者猜測郭店簡《語叢三》簡48—49是一種祝詞的套話,大意為“愿福壽無邊,愿福壽無窮,愿福壽無數,愿萬事如我意”。結合上文對《魯頌·駉》“疆”“期”“斁”和“邪”的并列關系,“思無邪”“思無疆”“思無朝”都可理解為意思相近的吉祥語,均表示一種美好的祝愿。更有學者從倫理學的角度探討“思無邪”的闡釋。將“思無邪”與“興于詩,立于禮,成于禮”相結合,建構出適應個體道德修養同社會治理和發展相結合的倫理思想體系。
至此,基于出土文獻研究的關于“思無邪”的闡釋呈現一種開枝散葉的狀態,大部分闡釋逐漸回歸《詩經》本義,同時又有從不同視域、不同范疇體系等方面做進一步的闡釋。
五、結語
理解和闡釋是關于兩種不同的視域,理解關于文本本身,而闡釋則更多是理解闡釋者的當下。伽達默爾認為,任何一個傳承物在每一個新的時代都面臨新的問題和具有新的意義,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理解,重新加以解釋。同時,理解是具有應用與實踐的功能的,“研討某種流傳物的解釋者就是試圖把這種流傳物應用于自身”,而闡釋者“為了理解這種東西,他一定不能無視自己和自己所處的具體詮釋學境況”。不同時期對同一定義或概念就會因所處的大背景而產生微妙的變化,闡釋者會賦予更多復雜的內涵。因此,歷來關于“思無邪”的不同闡釋也反映了文學的發展其實很難脫離時代的影子,尤其是古代的政教作用如影隨形。圣人話語下的漢學政教思想實乃“權威”,宋學能挑戰權威,朱子“情詩”的審美表達,“二蘇”的從“心”出發,皆為創新與突破之舉,后人解讀時卻要小心辨別真偽。除了對文本本身進行解讀外,對不同的闡釋者也要做更深入的對比研究,從共時與歷時的角度去看待文本的推演,更有助于“撥開云霧見月明”。
文獻的考據因為出土文獻變得更具流動性,加上學科之間的壁壘逐漸打破,跨學科思維逐漸顯現,因現今對“思無邪”的解釋變得開枝散葉。我們肯定每一個時代對經書的闡釋有其特殊的歷史價值,對反映詮釋者的時代背景和自身的文化符號有幫助,但我們不能忘記“具體詮釋學”境況,避免落入詭辯論的藩籬。
總之,“思無邪”的解釋,應該區分《詩經·魯頌·駉》中的“思無邪”和孔子的“思無邪”是不同的語境表達。前者是贊頌詩,而后者放在《論語》中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意義。孔子的“思無邪”或許本身就包含了多重含義,內容上借喻《詩三百》包羅萬象;情感上指向真情的詩性表達;抒情方式上又符合儒家文化的中和之美。因此,孔子將千言萬語歸結為“詩三百,思無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