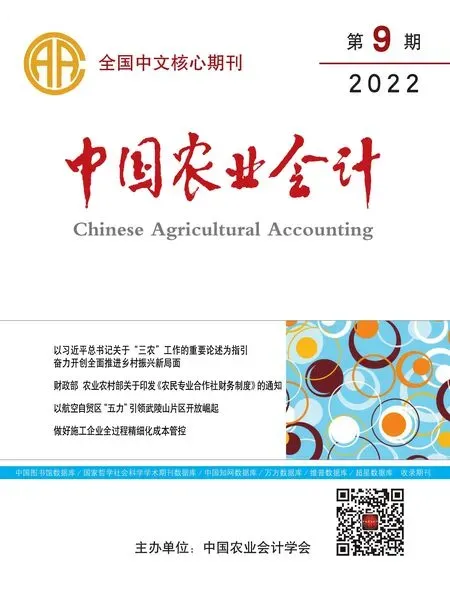外資持股、兩職合一與企業風險承擔
李 軍 石德金 陳龍飛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斷引進外資資本。2019年末外資持有A股市值突破2萬億元人民幣,據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實際使用外資9 999.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2%,規模創歷史新高,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國A股上市公司中累計外資投資過的公司為3 163家。與此同時,我國不斷完善外資進入準入相關法律法規,2020年我國公布的最新《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0年版)》,從2019年版的1 108條增加到1 235條,增幅超過10%。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境外資本的流入,各省區市始終將招商引資作為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可以看出,境外資本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有研究已開始關注外來資本對企業實體產生的影響,已有文獻表明,外資持股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步丹璐等,2021),公司價值(曲麗清,汪紅麗,2007),股價同步性(何佩勵,2015),研發投入(王宇峰,李怡婷,2016),公司績效(吳杰,孫毅,2017)等方面會產生重要影響。但外資對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風險承擔究竟有何影響?在什么情況下影響的作用更強?做好上述問題的回答,對于我國設立與完善外資股東相關管理法規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使用2007—2020年中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采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研究外資持股對于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第一,在其他條件一定的前提下,外資持股比例越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越高;第二,兩職合一對于外資持股所產生的風險承擔效應具有向下調節的作用,即外資持股比例對于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提升作用會受到CEO兩職合一削弱。
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理論方面,本文豐富了外資持股與企業風險承擔的理論研究。在上市公司類型上,現有研究中關于外資持股與風險承擔關系的研究上大多關注金融類企業樣本,由于金融企業的特殊性質,所得出的結論對于非金融類企業可能存在不適用的情況。例如,楊敏和梁銀鶴(2021)基于153家商業銀行非平衡面板數據研究得出引入外資降低了中國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外資股東在入股中國商業銀行時并不存在選擇效應;尹莉婭(2018)基于76家商業銀行非平衡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得出,外資持股同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及資產風險之間為U型關系。本文采用全樣本分析得到,外資股東對企業風險承擔具有積極促進作用,而且在進一步區分CEO兩職合一的情況下,研究發現在CEO與董事長兩職分離的公司內部,外資持股才能對我國上市公司的風險承擔產生積極的正向影響關系;而當CEO與董事長兩職合一時,外資持股對于公司的風險承擔作用并不顯著。本文提供了非金融上市公司外資持股風險承擔的經驗研究證據,研究對于上市公司引入外資持股后的CEO權利分配具有啟示作用。其次,豐富了關于股權結構與風險承擔水平的研究文獻,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股東股權性質,股權集中度(王飛和葉志秀,2017),股東增持減持,金字塔層級(蘇坤,2016),管理層持股(梁權熙和詹學斯,2016)以及股東控制權、現金流權分離等方面,而本文則基于中國放寬境外資本準入背景,為研究外資股東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提供了新的視角。最后,在當前持續推進改革開放、外資準入門檻不斷降低、減少外商投資比例限制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推進等國家政策與戰略背景下,上市公司成為外資的重要投資目標,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上市公司降低引入境外資本的顧慮,提高其風險承擔水平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二、文獻綜述
(一)風險承擔
風險承擔反映了企業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對投資項目的選擇,更高的風險承擔水平意味著管理者更少放棄高風險但預期凈現值大于0的投資項目(李文貴和余明桂,2012)。已有研究表明,投資更高風險項目能夠加快社會資本流動,促進經濟增長與企業技術的進步,適度的風險承擔還可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加股東財富,提高企業績效,增強創新能力。截至目前,關于風險承擔的研究,主要包括風險承擔的影響因素、風險承擔的影響效果等內容。
風險承擔的影響因素主要集中在企業內部微觀層面與企業外部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上,李文貴和余明桂(2012)認為,不同性質的企業有不同的風險偏好程度,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由于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具有更低的高風險投資偏好。Cheng(2008),Wang(2012)等學者認為,董事會規模的增加會降低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而Nakano和Nguyen(2012)基于日本企業數據研究發現,董事會規模的擴大有助于提高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進一步來講,也有學者研究獨立董事比例對于公司風險承擔的影響,Beasley(1996)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比例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王凱、范合君、薛坤坤等(2019)基于董事會成員的行業經驗與連鎖董事關系,分別衡量董事會人力資本與董事會社會資本,發現董事會資本通過影響上市公司設立分層董事會條款,從而降低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也有學者研究股權激勵對于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Chen和Steiner(1999)研究發現,股權激勵可以提高公司的風險承擔水平。邱強等(2018)研究發現,在控制管理層風險偏好變量情況下,股票期權激勵仍然具有風險激勵效應,而限制性股票則沒有風險激勵效應。
在風險承擔的影響效果上,已有研究較多關注風險承擔與企業績效,企業價值與資本配置效率。余明桂等(2013)研究發現,更高的風險承擔有助于提升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和企業價值。李新麗等(2021)研究發現,制度脆弱性弱化了風險承擔水平對企業價值和資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響。Palmcr和Wiscman(1999)在研究中則發現風險承擔較高時,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投資持保守態度,導致企業績效降低。也有學者關注風險承擔水平與企業內部資源配置的具體關系,李文貴、余明桂(2012)發現高風險承擔下,企業會進行更多的債權性融資,提升財務杠桿,而非進行股權融資。Djembissi(2011)研究發現,高風險承擔將導致企業進行更多的短期融資。劉華等(2018)研究發現,適度的風險承擔有助于企業創新,而過度的風險承擔則對創新產生負向影響。
(二)外資持股與風險承擔
在中國境內進行投資的外商股東大多來自歐洲與北美洲等發達地區,相對具有更高的現代公司治理能力與經驗,當外資股東進入到中國上市公司后,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會更多地對公司內部治理結構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此外,由于西方主流思想的冒險精神,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使企業投資更多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步丹璐等(2021)研究發現,外資股東的進入對于國內被投資企業具有“示范作用”與“溢出作用”。上述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提高企業對于未來利潤的預期,從而提高企業風險承擔能力,進行更多高風險項目的投資。并且當外資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時,進行高風險項目投資所獲得的利潤也就越高。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外資持股提高了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
(三)外資持股、兩職合一與風險承擔
由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上市公司內部存在委托代理問題,管理者為了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選擇犧牲股東利益的情況廣泛存在。為緩解委托代理問題,現代企業不斷完善公司內部治理制度以解決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問題。管理層出于個人利益與職位的考慮,為了維持現有薪酬水平與職業聲譽,不愿意去冒險而選擇風險更低的投資項目,從而違背了股東對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意愿。因此可以看出,管理層個人利益函數與股東利益函數分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風險承擔水平。
中國上市公司內部廣泛存在兩職合一的情況,此種模式下,CEO相對具有更高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導致董事會的監督作用下降。根據已有研究,在兩職合一情況下,管理層地位更加穩固、權力更加集中,不僅加大了管理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也提高了其實施機會主義行為的動機(董屹宇等,2019),在進行風險項目選擇時更多從自身利益角度衡量其成本與收益。具體來講,第一,按照理性經紀人假說,CEO作為一個理性的主體,在進行公司內部事務決策時會在完成與股東協議的前提下盡可能維護個人利益。當面臨眾多不同類型的風險項目時,由于CEO出于維護自身聲譽與維持現有薪酬水平的目的,CEO更偏愛于風險小、投資回報快的項目,而選擇規避風險較大、收益回收慢的項目(鐘熙等,2020)。第二,兩職兼任情況下,董事會對CEO的監管作用將降低。如果CEO既擁有公司的決策執行權,又擁有公司的決策控制權,顯然就是CEO自己監督自己(謝永珍等,2006)。在兩職分離情況下,當CEO出現與股東利益相悖的行為或違背公司章程的行為時,董事會可以及時對CEO的行為進行阻止,防止其行為造成進一步的危害。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相比于非兩職合一的企業,外資持股對于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效果更弱。
三、研究設計
(一)實證數據
為驗證本文所提假設,這里選擇2007—2020年非金融類A股上市公司數據,對初始樣本進行如下處理:(1)刪除ST、PT、ST*、PT*樣本;(2)刪除存在嚴重缺漏值的數據樣本;(3)刪除金融業、保險業、證券行業等上市公司樣本。通過上述篩選步驟,由于企業風險承擔變量以五年為一個計算滾動周期,故實際參與回歸樣本區間為2009-2018年,本文最后共獲得16 283個觀測樣本。
本文的企業特征數據主要來自RESSET銳思數據庫及WIND數據庫。此外文章對涉及的連續型變量均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
(二)變量度量與模型設定
1.變量定義。被解釋變量風險承擔,目前基于業績評價度量風險承擔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樣本期間內企業盈利波動性,第二種是股票收益的年度波動率,第三種是ROA的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基于本文研究內容,選擇樣本期間內連續五年的盈利波動性度量風險承擔水平。此外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ROA的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對風險承擔進行度量。
解釋變量外資持股。本文使用外資持股比例作為解釋變量。外資持股比例參考鐘熙等(2020)及孫芳城等(2021)研究采用年度內所有外資股東持股比例之和來衡量外資持股比例。
調節變量兩職合一。CEO兼任董事長,取值為1,否則為0。
其他控制變量,參照李小榮等(2014)、王海妹等(2014)學者關于風險承擔和外資持股的研究,本文將影響公司風險承擔的控制變量分為公司內部治理變量(具體包括獨立董事占比indr,兩職合一dual、股權集中度first、最終控制人性質state、內部控制質量ici),公司特征變量(資產收益率roa、資產負債率lev、公司規模size、總資產周轉率asset、權益報酬率roe、企業成長growth、股權集中度con_10、固定資產比率ppe),外部宏觀變量(市場化進程指數market)以及行業虛擬變量IND(制造業細分)和年度虛擬變量Year。變量具體定義如表1。

表1 變量說明
2.模型構建。為驗證假設1,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為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iskit),i代表企業,t代表時間,解釋變量為外資持股(forp)與兩職合一(dual),α為截距項,β1為對應的變量估計系數,X代表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
為驗證假設2,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在模型(2)中dual代表CEO兩職合一,兩職合一取1,否則取0,其他符號定義與模型(1)相同。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由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是否具有外資持股比例forpdum的均值為17.5%,說明境內上市公司在2007—2020年間僅有17.5%的公司接受過外商資本投資,具有外資持股的上市公司的比例仍然很小。外資持股比例forp的均值為0.03,最大值為0.653,說明外資持股比例仍然很低。企業風險承擔變量RiskT從0.004到0.693,說明我國非金融業上市公司風險承擔能力仍然存在較大差異。
由相關性分析表中可以看出,風險承擔水平RiskT與forp外資持股存在正向的相關關系,且在5%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內部控制質量ici與風險承擔水平RiskT為負向相關關系,與之前學者研究符號一致。由于篇幅限制,未匯報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結果,備索。
(二)回歸結果分析
1.外資持股與風險承擔。表2是對模型分析的結果,本文通過逐步加入控制變量、年度固定效應和行業固定效應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第(1)列為未加入任何控制變量的結果,第(2)列為加入控制變量和年度固定效應后的結果,從結果來看,forp對risk的作用均為正向,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第(3)列為加入控制變量、行業固定效應和年度固定效應后的結果,從結果來看,forp系數為正且在5%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外資持股對風險承擔具有正向作用,具有外商投資的企業在投資選擇時會具有更高的風險承擔傾向,假設1得到驗證。
表2第(4)列與第(5)列所示為分企業規模進行回歸的結果,第(4)列為大規模組,第(5)列為小規模組。結果表明,相比于大規模企業,小規模企業組的forp系數雖然為正,但并不具有統計意義,而大規模企業組forp系數顯著為正,且在5%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外資持股對于企業風險承擔的增強作用僅在大規模企業中存在,這可能是由于較小規模企業外資持股比例相對較低,在進行投資項目選擇時,受外資股東影響較小,且受限于企業規模而無法進行較大風險的投資。

表2 外資持股與風險承擔
2.外資持股、兩職合一與風險承擔。表3列示了不同兩職合一情況下外資持股對于風險承擔的影響,第(1)列為總體樣本情況下的外資持股對風險承擔的影響,從結果來看,交乘項forp*dual為-0.0348且在10%顯著性水平上具有統計意義。第(2)列為兩職合一情況下外資持股的風險承擔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回歸系數為負,且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這說明當CEO兩職合一的情況下,外資持股的風險承擔效應并不存在。第(3)列為非兩職合一組,可以看出forp系數為0.0437,且在5%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由此支持了假設2。即當CEO具有較大權力的情況下,作為理性人的CEO會更傾向于具有更低的風險承擔傾向。實際運作中,即使董事會對兩職合一的CEO所做決定存在不同意見,也由于CEO兼任董事長而無法完全發揮董事會的決策監督權。

表3 外資持股、兩職合一與風險承擔
(三)穩健性檢驗
1.重新定義被解釋變量。參照Boubar等(2013)研究,使用ROA的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對風險承擔水平進行變量替換(即Maxroa-Minroa)。在使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且控制年度與行業固定效應后外資持股forp的系數為0.0736,在5%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對應的t值為2.21),且兩職合一對于外資持股的風險承擔效應仍具有調節作用,與上文檢驗基本一致。
2.解釋變量滯后一期。考慮到內生性問題,將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均作滯后一期處理,檢驗外資持股與風險承擔之間關系,結果表明外資持股的系數為0.0395,且在1%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對應t值為2.61),支持上文檢驗結果。由于篇幅限制,穩健性檢驗結果未匯報,備索。
五、結論
本文基于2009—2018年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研究外資持股與風險承擔的關系。研究發現,外資持股對于提升公司的風險承擔水平具有積極作用,但外資持股所產生的風險承擔效應在不同的CEO權力安排下不同。具體而言,相比于兩職合一的上市公司,非兩職合一的上市公司可以更好地發揮外資持股的風險承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