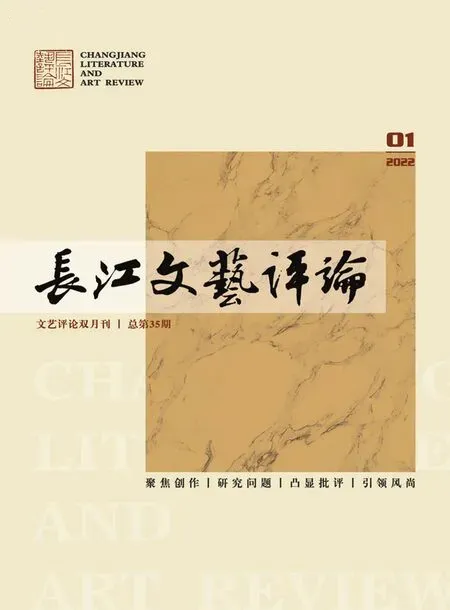歷史激蕩中的家國(guó)情懷
——陳繼明長(zhǎng)篇小說(shuō)《平安批》讀解
◆曾 攀
縱觀近現(xiàn)代中國(guó)歷史,“感時(shí)憂(yōu)國(guó)”的敘事形態(tài)成為了自19世紀(jì)中期遭受外來(lái)侵略以來(lái),直至1949年新中國(guó)成立,現(xiàn)代文學(xué)最重要的一種情感結(jié)構(gòu)與精神倫理。需要指出的是,“家國(guó)情懷”并不是一種固化的概念,也不是不言自明的所在,在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歷程中,這樣的情懷是流動(dòng)的、開(kāi)放的,經(jīng)歷了政治的、文化的補(bǔ)益,以及美學(xué)的與修辭的建構(gòu),甚至在歷史的動(dòng)蕩中遭受了沉重的沖擊,也經(jīng)歷了自身的危機(jī),最終通過(guò)內(nèi)外的裂變和重建,呈現(xiàn)出一個(gè)民族牢固而生輝的精神抱負(fù)、抒情形態(tài)以及價(jià)值關(guān)切。
陳繼明長(zhǎng)篇小說(shuō)《平安批》寫(xiě)的是潮汕人民“下南洋”的百年跌宕,以鄭夢(mèng)梅為主要人物的掙扎、奮斗和堅(jiān)守,以及以潮汕人民為代表的世界想象與實(shí)踐,尤其是在生活、事功、革命等若干層面中,展現(xiàn)中華民族濃郁的家風(fēng)民俗與國(guó)族意識(shí)。在這其中,“平安批”既是深情厚誼的家書(shū),更是關(guān)于家庭觀念與家族意識(shí)的重要象征。小說(shuō)以“平安批”為切入點(diǎn),撬動(dòng)一個(gè)多世紀(jì)以來(lái)潮汕人民的奮斗史、家族史與革命史,將之置于19世紀(jì)末以降的革命歷史之中,歷經(jīng)戰(zhàn)火洗禮,呈現(xiàn)出波瀾壯闊的歷史激蕩,以及其中難能可貴且熠熠生輝的家國(guó)情懷。
一
《平安批》首先以主人公鄭夢(mèng)梅為視角,觸及到的是中國(guó)南方的一種獨(dú)特的地域性書(shū)寫(xiě),更確切地說(shuō),其集中敘寫(xiě)了潮汕地區(qū)的家族生活,展開(kāi)同時(shí)具備地方性與世界性的生活場(chǎng)景,并以此為基點(diǎn),對(duì)潮汕人民“下南洋”的辛酸史與發(fā)家史進(jìn)行了鋪展,并將之拋入近現(xiàn)代中國(guó)的變革歷史之中,后者同時(shí)是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以來(lái)中國(guó)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融入世界的歷史。而正是在這樣的跨文化書(shū)寫(xiě)中,人物內(nèi)在的家國(guó)情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蘊(yùn)蓄。正如陳繼明本人在創(chuàng)作談中所言,“把故事放在二十世紀(jì)前五十年。那是中國(guó)社會(huì)由封建走向現(xiàn)代、由混亂走向治理的重要時(shí)期,也是東西方文化開(kāi)始接觸、試探和融合的重要時(shí)期,讓那個(gè)時(shí)代的主調(diào),像空氣一樣始終彌漫于故事的縫隙。”在一個(gè)跨文化的歷史語(yǔ)境中,如何重新廓清中國(guó)視野中的世界,以及世界意識(shí)范疇里的中國(guó),這事實(shí)上不僅代表了潮汕人民“下南洋”的生命走向,而且意味著現(xiàn)代中國(guó)勾連并融入世界的一種重要嘗試。如果從這個(gè)層面來(lái)看問(wèn)題,“平安批”的存在便提示了更為深刻也更為闊遠(yuǎn)的內(nèi)涵。
小說(shuō)圍繞著“溪前”與“溪后”展開(kāi)了潮汕地區(qū)的家族關(guān)系史,“時(shí)光里,平安里,單單從這兩個(gè)名字就能看出溪前、溪后的不同,溪前子弟多才情,講義氣,喜歡讀圣賢書(shū),不切實(shí)際,好高騖遠(yuǎn),‘等閑談笑見(jiàn)心肝’;溪后子弟剛好相反,個(gè)個(gè)冷靜務(wù)實(shí),長(zhǎng)于運(yùn)籌帷幄,善于做生意搞經(jīng)營(yíng)。另外,溪前輩輩乏丁少口,好不容易生出個(gè)兒子,往往又年壽不永,很難活過(guò)五十歲,這一點(diǎn)溪后也相反,不愁女,也不愁男,每一代都人丁興旺。所以,溪前、溪后,當(dāng)人們這樣稱(chēng)呼雙方時(shí),意味相當(dāng)豐富,一言難盡。但有一點(diǎn)是顯而易見(jiàn)的,溪前、溪后,強(qiáng)調(diào)了兩種大不相同的秉性和時(shí)運(yùn)。”家族之間微妙的關(guān)系,以及彼此血液般的內(nèi)在牽連,在小說(shuō)中體現(xiàn)得尤為顯著,這也是人物早期的主體形成的關(guān)鍵因素,并且影響波及成年后以至到世界中去時(shí)的性格、性情甚而是精神格調(diào)的養(yǎng)成。更為重要的是,伴隨著20世紀(jì)前后中國(guó)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興衰中的跌宕,潮汕文化對(duì)家庭以及家族觀念的倚重,一方面承傳的是傳統(tǒng)中國(guó)的價(jià)值倫理,這一層級(jí)的文化形態(tài),支撐著小說(shuō)人物的內(nèi)在認(rèn)同以及彼此之間的精神紐帶;另一方面則是傳統(tǒng)中國(guó)在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guò)程中,勢(shì)必會(huì)經(jīng)受的歷史沖擊,以及在時(shí)間的滌蕩后留存下來(lái)的精神余緒。前者成為了傳統(tǒng)中國(guó)文化理念的現(xiàn)代衍變,而后者則直接決定著家族本身的存續(xù)。值得一提的是,小說(shuō)最后,在國(guó)—家的價(jià)值體系中,“國(guó)”的問(wèn)題得以很好地處置之后,“家”的困境同樣得以解決,原本分崩離析的溪前與溪后的家族內(nèi)訌得以緩解,“溪前鄭不僅挽回了聲譽(yù),而且實(shí)力和影響力漸漸超過(guò)溪后鄭,溪前溪后也擯棄前嫌,重新成為鄭氏雙雄。溪后為什么總是躲著溪前?謎題也終于解開(kāi)了。原因不過(guò)是一點(diǎn)迷信而已:溪后怕沾上溪前的晦氣和霉運(yùn)。現(xiàn)在好了,溪前不僅晦氣霉運(yùn)一掃而光,反而如日中天,不光生意做得很大,人也好好的……”縱觀整個(gè)小說(shuō),家庭與家族構(gòu)成了人物情感結(jié)構(gòu)的基座或曰底色,在此基礎(chǔ)上,生活得以展現(xiàn)出穩(wěn)固的整體性特質(zhì),并且以此為中心,生發(fā)出新的精神支脈。而由于強(qiáng)烈的家庭與家族意識(shí),生活的“日常”即為傳統(tǒng)之倫理,并在新的可能與未知的境況中,輻射出豐沛的精神能量。
在小說(shuō)中,鄭夢(mèng)梅和他的子嗣乃誠(chéng)兩代人共同堅(jiān)守著批局的發(fā)展,乃誠(chéng)與父親有著相似的經(jīng)歷。乃誠(chéng)少時(shí)不愿離開(kāi)時(shí)光里,被夢(mèng)梅責(zé)備之后才勉強(qiáng)跟去,“乃誠(chéng)從來(lái)不和別人對(duì)視,偶爾看一眼別人,馬上就閃開(kāi),目光軟得像驕陽(yáng)下的薯秧,也不敢離開(kāi)夢(mèng)梅半步,走路總是躲在夢(mèng)梅身后,常常還要拉著夢(mèng)梅的衣服。夢(mèng)梅無(wú)論如何都想不通,小時(shí)候那么討人喜愛(ài)的一個(gè)孩子,一個(gè)已經(jīng)當(dāng)上了父親的人,怎么竟是此等模樣。”但是到了后來(lái),乃誠(chéng)得到了成長(zhǎng),與父親歷盡艱辛,恢復(fù)番批業(yè)務(wù),并且成為了能夠獨(dú)當(dāng)一面的人,足以繼承父親的事業(yè)。由于歷史的時(shí)間流動(dòng),以及其中的革命與戰(zhàn)爭(zhēng)的沖刷,小說(shuō)的人物往往能在其中得到成長(zhǎng),也避免了臉譜化的傾向,更重要的,如是這般的精神成長(zhǎng)與衍變不是一處空談,而是沉落入人物生活的言行舉止與起伏跌宕之中,在于人情交往以及家庭婚姻里,并延伸至追索事業(yè)與報(bào)效國(guó)家的更高的價(jià)值序列。
可以說(shuō),從整個(gè)小說(shuō)而言,“平安批”更像是一種隱喻,其不僅在現(xiàn)實(shí)層面對(duì)應(yīng)著潮汕人民走向世界過(guò)程中的頻頻回望及其中極為可貴的守護(hù),更代表著傳統(tǒng)價(jià)值倫理序列中的道德秉持,甚至關(guān)乎整個(gè)現(xiàn)代中國(guó)的家國(guó)情思,如是這般的精神寄寓并不是憑空懸置的,其既停留在一封封情真意摯的信件、錢(qián)財(cái)及其包裹的精神形態(tài),同時(shí)落位于“平安批”兩頭的生活現(xiàn)場(chǎng),那里包孕著最本原的同時(shí)也是最真切的情感境況,同時(shí)人物對(duì)家庭的思念和幫助,人們情感間磊落光明的扶持,以及在面對(duì)家國(guó)困頓時(shí)展現(xiàn)出來(lái)的靈魂恪守。
值得注意的地方還在于,盡管在革命歷史中經(jīng)歷苦難和波折,但人物的情感卻始終沒(méi)有被架空,鄭夢(mèng)梅們內(nèi)心如火焰般燃燒的熱情與溫情同樣沒(méi)有被嚴(yán)酷的斗爭(zhēng)淡化,他們自身寶貴且備受珍視的情思也在此過(guò)程中絲毫沒(méi)有潰散,反而在生活現(xiàn)場(chǎng)和情感交互中歷久彌新,并不斷得到增益。如鄭夢(mèng)梅與藺采兒盡管早有情愫,但始終相敬如賓,直至藺采兒之夫林阿為意外殞命,鄭夢(mèng)梅意識(shí)到她的可憐及需要照顧,“采兒用當(dāng)?shù)卦?huà)報(bào)案的樣子可憐極了,不像原來(lái)那個(gè)采兒。像紙做的一個(gè)人。全身發(fā)抖,聲音也發(fā)抖,整個(gè)人薄薄的,又薄又脆,不用費(fèi)力就能撕破的樣子。這樣的采兒,任何事情,哪怕針尖大的事情,都做不了,更別說(shuō)保護(hù)自己。這個(gè)情景讓夢(mèng)梅大為吃驚,也才意識(shí)到,一個(gè)雅姿娘真的很脆弱,比所有人都脆弱。”正是出于這樣的情與義的緣由,當(dāng)然也包裹著自身對(duì)藺采兒念念不忘的情感,才讓鄭夢(mèng)梅真正顯露出對(duì)她的關(guān)懷,并最終堂堂正正與之相處相愛(ài)。不得不說(shuō),小說(shuō)無(wú)論在生活、情感、德性等方面,都傳達(dá)出人物身上有情有義的倫理?yè)?dān)當(dāng)。這于當(dāng)下的文學(xué)書(shū)寫(xiě)是何其的重要,尤其在后現(xiàn)代宏大整全的情感和精神不斷處于被消解的境況中,小說(shuō)敘事如何通過(guò)德、情、義等觀念的抒發(fā),重新凝聚既是傳統(tǒng)中國(guó)的同時(shí)也是當(dāng)下稀缺的文化狀態(tài),從而使得《平安批》這一小說(shuō)能夠透露出真正的歷史意識(shí),特別是在數(shù)十年激蕩的革命情勢(shì)下,將濃得化不開(kāi)的家國(guó)懷抱加以延續(xù)與傳承,無(wú)疑具有富于當(dāng)代性的價(jià)值探詢(xún)。
二
事實(shí)上,小說(shuō)開(kāi)始時(shí),鄭夢(mèng)梅原本對(duì)“下南洋”不感興趣甚至不無(wú)排斥,但是鬼使神差,他在冥冥中遇到了一位“高手”老貨郎,得到后者指點(diǎn)如何破除“活不過(guò)五十歲”的短命之讖,“唯一的辦法就是遠(yuǎn)離祖居之地”,這或許也屬因緣際會(huì),同時(shí)也與小說(shuō)所要展現(xiàn)的潮汕地區(qū)的民間氣息緊密相關(guān)。鄭夢(mèng)梅從一個(gè)庸庸碌碌、不思進(jìn)取的柔弱子弟,到走出國(guó)門(mén)“下南洋”,再到商海激蕩所向披靡,這其中可以見(jiàn)出小說(shuō)在處理人物時(shí)所注重的對(duì)人物性格與德性的關(guān)注,并且將其游至于現(xiàn)實(shí)的事功層面,也就是說(shuō),主要人物鄭夢(mèng)梅是通過(guò)他的事業(yè)建立起自身威望的,而且他所經(jīng)營(yíng)的批局,事實(shí)上牽連甚廣,貫穿起整個(gè)小說(shuō)的枝枝葉葉。事實(shí)上,鄭夢(mèng)梅下南洋之后的運(yùn)氣并不賴(lài),“夢(mèng)梅在海上漂到了四十歲。接著又漂到了五十歲。接近五十歲的那幾年幾乎全年在海上,一年十二個(gè)月,有十個(gè)月在海上。生意順風(fēng)順?biāo)瞬毁嵎e惡錢(qián),別的錢(qián)能賺則賺,種子公司、電燈公司、抽紗公司、女子學(xué)校、批局、醫(yī)院、錢(qián)莊、義莊,絕對(duì)是遍地開(kāi)花,蒸蒸日上。”在暹羅義山亭,他被宋萬(wàn)昌視為批局事業(yè)的繼承人,與此同時(shí)還結(jié)識(shí)了若干志同道合的友人。需要指出的是,鄭夢(mèng)梅備受青睞的背后,是他內(nèi)心所秉持的傳統(tǒng)中國(guó)的價(jià)值倫理,這樣的內(nèi)在品格與德性,在一個(gè)動(dòng)亂的風(fēng)雨飄零的年代是何其的難能可貴,而更重要之處還在于,在鄭夢(mèng)梅身上,實(shí)際上寄寓著堅(jiān)如磐石的文化佑護(hù),他的靈魂如一座大山矗立于世間紛擾之間。正如鄭夢(mèng)梅、陳光遠(yuǎn)和喬治在結(jié)拜兄弟時(shí),前者所提及的在遭遇禍和福、生和死涉及立場(chǎng)、事關(guān)原則時(shí),所應(yīng)護(hù)衛(wèi)的關(guān)于“義”之精髓所在:
結(jié)義結(jié)義,因義而結(jié),義,自古以來(lái)都有明確的含義,比如,義不容辭、見(jiàn)義勇為、義無(wú)反顧、仗義疏財(cái)、義薄云天,這幾個(gè)詞中的“義”,都是同一個(gè)意思,即道義、正義、公義、大義,中國(guó)古代文獻(xiàn)里更是有很多關(guān)于“義”的進(jìn)一步說(shuō)明,比如,“度義而后動(dòng)”“義固不殺人”“義不殺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值得一提的是,《平安批》事實(shí)上刻畫(huà)了一組人物群像,他們?cè)跉v史的動(dòng)蕩中左突右沖,面對(duì)戰(zhàn)爭(zhēng)與革命帶來(lái)的生存危殆,卻始終秉持內(nèi)心的道德律。而小說(shuō)中的每一個(gè)人,只要一出場(chǎng),便不再是虛空的,其必然往有血有肉的方向發(fā)展,對(duì)于這點(diǎn),作者也有所意識(shí),“重視人物,寫(xiě)好幾個(gè)人物。無(wú)論舊小說(shuō)新小說(shuō),無(wú)論傳統(tǒng)還是現(xiàn)代,都必需重視人物,離開(kāi)活生生的人物,離開(kāi)具體困境、實(shí)際交往和情感聯(lián)系,一切都是空談。每一個(gè)人,是寫(xiě)作過(guò)程中的一道道窄門(mén),過(guò)不了這些窄門(mén),小說(shuō)就不存在。無(wú)論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只要有名字,只要出場(chǎng)了,就必需寫(xiě)好,必需有血有肉。”不僅如此,人物還需要有棱有角,否則必然會(huì)顯得空洞,尤其在革命與戰(zhàn)爭(zhēng)的情形下,很容易會(huì)外在地洗刷磨滅性格的硬度。可以說(shuō),在小說(shuō)中,作者所刻畫(huà)的每一個(gè)體都有著自身的個(gè)性、命運(yùn)甚至是使命,他們存活于文本世界之中,與現(xiàn)實(shí)歷史發(fā)生著種種不可磨滅的勾連,因而其必定是可信的與可靠的,以此反過(guò)來(lái)推敲小說(shuō)所試圖觸及的現(xiàn)實(shí)歷史的可能性,盡管個(gè)別人物的書(shū)寫(xiě)略顯臉譜化或沒(méi)有得到很好的延續(xù),但總體而言,小說(shuō)中涉及的諸多人物,如果以細(xì)讀的方式展開(kāi),可以發(fā)現(xiàn),除去前面所提及的宋萬(wàn)昌、陳光遠(yuǎn)、喬治,以及陳阿端、林阿為、藺采兒等,都成為了同一種精神序列中不可忽略的人物形象。鄭夢(mèng)梅正是遇上了他們,與他們結(jié)成某種價(jià)值共同體,才得以在生命的衍變中披荊斬棘,成就自身;而鄭夢(mèng)梅在發(fā)跡之后,也沒(méi)有忘本,其中之情誼與情義,可見(jiàn)一斑。“夢(mèng)梅發(fā)家之后,在汕頭置地?cái)?shù)百畝,創(chuàng)辦了純公益的萬(wàn)昌義莊,專(zhuān)門(mén)寄厝無(wú)主尸體或暫時(shí)不能入土為安的靈柩。義莊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了整整一艘大火輪,把曼谷義山亭內(nèi)有意愿遷回國(guó)內(nèi)的靈柩,和一些無(wú)主遺骨無(wú)償遷葬至萬(wàn)昌義莊。”不僅如此,鄭夢(mèng)梅還感念宋萬(wàn)昌對(duì)自己的知遇之恩,“為了感謝和紀(jì)念宋萬(wàn)昌,所有的公司仍然以萬(wàn)昌命名。宋萬(wàn)昌先生已于多年前病故,兩個(gè)兒子在每一家名叫萬(wàn)昌的公司里都持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很多人認(rèn)為不必這樣,夢(mèng)梅則毫不動(dòng)搖,堅(jiān)持如此。”不得不說(shuō),在鄭夢(mèng)梅身上,作者寄寓了對(duì)潮汕人民的精神美德甚而是整個(gè)中華民族的德性倫理的深度認(rèn)同。
不僅如此,在小說(shuō)末尾,1958年6月29日,身在曼谷的夢(mèng)梅仍心系“抗戰(zhàn)時(shí)期沉批博物館”的建立,且頗費(fèi)周折之后,終于如愿以?xún)敚皦?mèng)梅收到興寧中國(guó)銀行從國(guó)內(nèi)寄來(lái)的匯款,以港幣一元兌人民幣六千三百七十五元的標(biāo)準(zhǔn)結(jié)算,共計(jì)人民幣五億一千萬(wàn)元。收到這筆匯款后,萬(wàn)昌批局逐一征求了所有能找到的寄批人的意見(jiàn),大部分寄批人都無(wú)心收回批款及其利息,愿意交給萬(wàn)昌批局,創(chuàng)建抗戰(zhàn)時(shí)期沉批博物館。”而實(shí)際上,鄭夢(mèng)梅建立沉批博物館的目的,是“以為日軍侵犯我國(guó)之間接證據(jù),并警示后人勿忘國(guó)恥,居安思危,振興中華。”不僅如此,鄭夢(mèng)梅更是打算回國(guó)之后捐出自己的一棟洋樓,創(chuàng)建沉批博物館,隨后此一計(jì)劃亦得以成就,“建成后,晚年的夢(mèng)梅不再出門(mén)遠(yuǎn)行,要么整天待在博物館里,守著成千上萬(wàn)封沉批死批發(fā)呆,要么仍然抱著一線希望,以一個(gè)最最普通的批腳的樣子繼續(xù)走鄉(xiāng)串戶(hù),或步行或騎自行車(chē),四處尋訪,又有不少原以為毫無(wú)辦法的沉批、死批到底被救活了。”應(yīng)該說(shuō),關(guān)于平安批的博物館建立,不僅關(guān)系著一代代華僑的感念情思和精神寄托,同樣代表著潮汕人民乃至中華民族流脈的文化守持。這樣的事功不是空中樓閣,也不僅存留于簡(jiǎn)單的形式概念之中,而是切切實(shí)實(shí)建筑于物質(zhì)與現(xiàn)實(shí)之上的,是潮汕人民的務(wù)實(shí)之風(fēng)與愛(ài)國(guó)之情使然,是秉持著真摯濃郁的家國(guó)情懷而尋求的精神寄寓。
三
回過(guò)頭來(lái)看,鄭夢(mèng)梅等人的個(gè)體成長(zhǎng)史與奮斗史,以及溪前與溪后剪不斷理還亂的家族史,始終是與近現(xiàn)代中國(guó)的國(guó)族史相互勾連,這個(gè)過(guò)程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其所牽引出來(lái)的現(xiàn)代中國(guó)始終纏繞的革命歷史。
對(duì)于鄭夢(mèng)梅而言,其出生于遭受著千年變革的晚清,這是近現(xiàn)代中國(guó)的一個(gè)重要的過(guò)渡時(shí)期,同時(shí)也是舊的價(jià)值系統(tǒng)的坍塌與新的文化觀念構(gòu)建的過(guò)程。而與思想的迭變相呼應(yīng)的,是20世紀(jì)作為一個(gè)革命世紀(jì),其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歷史的直接作用力,如何理解隨著革命歷史和文學(xué)的美學(xué)流變而發(fā)生衍化的家國(guó)情懷,又如何在“感時(shí)憂(yōu)國(guó)”的精神框架下對(duì)國(guó)族意識(shí)進(jìn)行更為深化的辨析,并對(duì)其澤被于當(dāng)代中國(guó)的精神脈絡(luò)進(jìn)行梳理呈示,這樣的命題在《平安批》中都得到深刻的反映。
對(duì)于整個(gè)小說(shuō)而言,鄭夢(mèng)梅所牽涉到的,是關(guān)于潮汕人民對(duì)于家庭與家族、遷徙與事功、革命與奉獻(xiàn)的理解,除了形而下的關(guān)于生活、生存、致富等意義的探詢(xún),還在于自身的“事功”層面,也即在個(gè)體/群體奮斗過(guò)程中,有著自身的經(jīng)濟(jì)抱負(fù),是關(guān)乎經(jīng)營(yíng)的與事業(yè)的內(nèi)心秉持。不僅如此,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以鄭夢(mèng)梅為代表的潮汕人民,對(duì)于整個(gè)中華民族的革命史與戰(zhàn)爭(zhēng)史,都有著突出的貢獻(xiàn),其身上透露出來(lái)的顯豁的家國(guó)情懷,激蕩在百年來(lái)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歷史。具體而言,在小說(shuō)中,以鄭夢(mèng)梅和“平安批”為中心的人—物雙重交疊,在一種歷史的長(zhǎng)時(shí)段延展中,呈現(xiàn)出非常豐富立體的文化形態(tài)。從辛亥革命開(kāi)始,到逆反復(fù)辟與軍閥混戰(zhàn),再到抗日戰(zhàn)爭(zhēng)與解放戰(zhàn)爭(zhēng),甚至歷經(jīng)20世紀(jì)中期以來(lái)當(dāng)代中國(guó)的種種變革與更迭,最為難能可貴之處在于,鄭夢(mèng)梅內(nèi)心是如此的堅(jiān)定,他對(duì)自身所守衛(wèi)的價(jià)值意義是那么的篤定,當(dāng)然,歷盡劫難的他,時(shí)間的玫瑰也給予了其最為豐厚的饋贈(zèng)。鄭夢(mèng)梅也得以在跌宕起伏的革命甚至戰(zhàn)爭(zhēng)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于歷史的長(zhǎng)河之中,從而也使得他所秉持的精神理念和倫理道德在其間熠熠生輝。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shù)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一段歷程,鄭夢(mèng)梅不僅當(dāng)“日本領(lǐng)事館的富田書(shū)記官帶著一個(gè)臺(tái)灣籍的翻譯官前來(lái)求見(jiàn)時(shí)”,婉言拒絕其來(lái)訪,且告知其壽宴取消,以此下逐客令。甚至于,當(dāng)國(guó)內(nèi)的父親來(lái)信希望鄭夢(mèng)梅幫助購(gòu)買(mǎi)軍火以抗擊日本侵略,鄭趕忙找到老朋友陳光遠(yuǎn)、陳阿端、林阿為、藺采兒等人。其中,林阿為可以弄到五百支最新款的毛瑟長(zhǎng)槍?zhuān)A采兒負(fù)責(zé)聯(lián)系她剛剛承包了一艘火船的堂弟協(xié)助躲過(guò)檢查,陳阿端則提議“先把槍支彈藥裝進(jìn)不透水的箱子,再把箱子用鎖鏈穿起來(lái),掛在船尾,沉入海底,等出了港再撈上去。”就這樣,在愛(ài)國(guó)華僑們的群策群力中,抗日的軍火得以運(yùn)往汕頭。然而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林阿為被漢奸所害,獻(xiàn)出了自己的生命,藺采兒的內(nèi)心也因此遭受了沉重打擊。鄭夢(mèng)梅與他的友人之間,無(wú)不成為了生死之交,而在他們背后,則是整個(gè)家國(guó)歷史的動(dòng)蕩和變遷,個(gè)人的命運(yùn)與國(guó)族的沉浮自始至終緊密牽連在了一起,這便使得《平安批》這部小說(shuō)具備了某種歷史的縱深度,與此同時(shí),又能傳遞出現(xiàn)世的情感與情懷。
這就是小說(shuō)頗具意味之處,整個(gè)文本以“平安批”為核心,然而卻處處充滿(mǎn)了險(xiǎn)境與危機(jī),平安的對(duì)立面則往往是革命戰(zhàn)爭(zhēng)歷史境況中的深深的威脅,死亡與平安之間的張力在人物的精神操練中,淬煉出了感人至深的家國(guó)情懷。小說(shuō)既然名為“平安批”,那么關(guān)于“平安批”以及圍繞此進(jìn)行的敘事便是中心所在。在這其中,“平安”自然是人物內(nèi)在的一種愿景,與此同時(shí),“平安”同樣意味著廣大華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實(shí)踐,特別是在動(dòng)蕩的中國(guó)近現(xiàn)代史,“平安”二字時(shí)常顯得難得甚至奢侈,不僅如此,“平安”還凸顯出革命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個(gè)體的激憤、勇毅,是不畏險(xiǎn)阻與艱辛的不屈不撓的拼搏。譬如在戰(zhàn)爭(zhēng)情勢(shì)下,鄭夢(mèng)梅的小兒子乃誠(chéng)從畏事膽怯,到最后不斷成長(zhǎng),便是通過(guò)“平安批”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lái)的,下面是乃誠(chéng)代寫(xiě)的第一封批:
母親大人尊前:
敬稟者,近聞倭寇向我國(guó)不宣而戰(zhàn),北平天津上海廣州均已失陷,又聞吾地南澳島幾番易主,終陷敵手,日軍飛機(jī)每日在韓江兩岸低空偵察,炸橋毀路,同胞死傷無(wú)數(shù),我料來(lái)者不善,敵進(jìn)犯潮汕為期不遠(yuǎn)。前日接吾母回批曰,我妻剛生一子,母子平安,鄉(xiāng)里仍顯平靜,諸事如常,去年稻谷收獲甚豐,米價(jià)甚昂,家中尚有積蓄,囑兒不必省食儉用,精神皆在家中。兒讀之不禁目汁如雨,夜不能寐,幾乎成疾。茍一時(shí)戰(zhàn)事發(fā)生,汝等婦孺,手無(wú)縛雞之力,苦狀可知,宜須鎮(zhèn)靜,無(wú)得驚慌,并望囤些錢(qián)物,以防困厄。
茲付國(guó)幣五十元,順致妝安!
兒 得全敬上
民國(guó)二十六年十二月四日
此批從語(yǔ)言之精煉、感情之抒發(fā)等層面而言,都能見(jiàn)出寫(xiě)批的功力,特別是其中的情感流瀉,夾雜著對(duì)家庭的深情厚誼,以及對(duì)國(guó)家民族的深切關(guān)懷。可以說(shuō),整個(gè)小說(shuō)中所刻畫(huà)的以潮汕人民為代表的華僑群像,無(wú)不具有如是這般的精神質(zhì)地,他們經(jīng)歷時(shí)間的沖刷而始終如礁石般矗立,在海洋的跌宕沉浮中始終屹立不倒。不得不說(shuō),以鄭夢(mèng)梅為代表的潮汕人民,即便他們離開(kāi)了故土,在“南洋”摸爬滾打,等著他們的是不可預(yù)知的未來(lái),是無(wú)有確定的現(xiàn)實(shí),然而他們內(nèi)心的家國(guó)情懷未曾削減,反而日益增強(qiáng),他們舍生忘死,參與到國(guó)內(nèi)幾乎每一次的革命與戰(zhàn)爭(zhēng)之中,為國(guó)分憂(yōu)、為民請(qǐng)命。那種家國(guó)情懷所涂抹而生的精神底色,已然成為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可動(dòng)搖的律例。
四
縱觀陳繼明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平安批》,以鄭夢(mèng)梅等人物為代表的個(gè)體命運(yùn),展現(xiàn)潮汕家庭/家族的生活狀態(tài)與情感結(jié)構(gòu),被置于20世紀(jì)前后的近現(xiàn)代中國(guó)歷史,而且將之投入一種世界性的視野之中,對(duì)潮汕地區(qū)甚至是整個(gè)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倫理進(jìn)行一種歷史性的書(shū)寫(xiě)。陳繼明自己對(duì)這部小說(shuō)的寫(xiě)法事實(shí)上有著深刻的自覺(jué),他認(rèn)為,寫(xiě)潮汕不能只寫(xiě)潮汕,而要“跳出潮汕看潮汕,把潮汕故事當(dāng)中國(guó)故事去寫(xiě),甚至當(dāng)人類(lèi)故事去寫(xiě)。遷徙、流落、求生、逃亡、土地、回歸、家國(guó),這些命題,事實(shí)上的確不是中國(guó)人特有的,但在中國(guó)人身上表現(xiàn)得的確更強(qiáng)烈,更極端,更有意味。”不得不說(shuō),“平安批”這個(gè)題材非常有意味,一看就是有故事有內(nèi)涵的寫(xiě)法,加之在結(jié)構(gòu)上采取的是歷史性的敘事,通過(guò)一種核心之“物”左牽右引,鋪陳出龐雜的內(nèi)蘊(yùn)。“《平安批》這個(gè)名字是從一開(kāi)始就定下來(lái)的。平安批,僑批中的一種,是在南洋上岸后寄回家的第一封批(同時(shí)至少寄兩塊銀圓)。‘平安’二字不可小覷。”可以說(shuō),小說(shuō)不僅在于表述百余年來(lái)的歷史沉浮所帶來(lái)的諸多人物的精神困頓及解脫,而且“平安批”自身的內(nèi)在蘊(yùn)藉同樣傳達(dá)出豐富的歷史與人文涵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鄭夢(mèng)梅們的身上,寄寓了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的中華民族的家國(guó)情懷,尤其以“感時(shí)憂(yōu)國(guó)”的敘事姿態(tài),刻寫(xiě)了一代又一代的潮汕民眾的事功追求及精神守持。可以說(shuō),《平安批》代表著當(dāng)代中國(guó)文學(xué)主題創(chuàng)作的新形態(tài),其以“平安批”為核心,甚至將其作為方法,牽引出新的國(guó)族敘事,而以“僑批”為中心的主題創(chuàng)作,也提示著當(dāng)代中國(guó)紅色文藝的創(chuàng)新性表達(d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