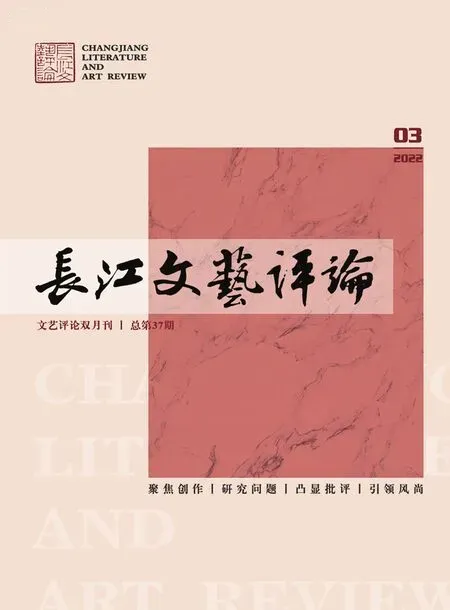延安、榆林地區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的融合互動
◆賈振鑫
陜北說書是全國具有較大影響的地方曲種,一般由說書人自彈三弦(或琵琶)坐唱或多人組合演出,主要流行于陜北的延安、榆林及周邊的甘肅、寧夏等地區。2006年5月入選首批國家級非遺曲藝類名錄。
一直以來,陜北說書的主要演出陣地都在農村,為了保持與聽書人的平視、親切,勢必“在內容上表現農民生活,在追求上反映農民理想,在形式上符合農民審美情趣”,確保藝術傳達到位,完成愉悅民眾、調節生活、道德教化、情感補償、思想啟迪的功能。同時,藝人在流動作藝中會觀察聽書人的欣賞反應來調整說書內容和表達方式,以求更加符合聽書人的“口味”,還會把所見所聞的民間故事、生活趣聞、社會新聞、家長里短充實到書文之中亦或形成新作,從而完成陜北說書對外部生存發展環境的適應。由此,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循環往復地融合互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生相長,鄉村文化與藝人的說書技藝乃至陜北說書的整體都獲得了發展。
根據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融合互動的發展實際,可從1945年前的純粹民間存活階段、“改造說書”創高峰、改革開放后的再出發、國家非遺展新姿、前景展望五個維度論述這一生態現象,分析其意義價值及存在問題與解決方式。
一、1945年前的純粹民間存活階段
陜北說書的演出傳統,是該曲種與陜北區域文化融合互動的結果,而陜北區域文化的形成與其獨特的自然環境又多有關聯。
延安、榆林地區北接毛烏素沙漠,地處黃土高原腹地,自然條件惡劣,高原起伏、溝壑縱橫、干旱少雨、自然災害頻發。而且該地區交通嚴重不便,“千里頑石,四圍重阻,商家難以至其地,行旅難以出其鄉”。這種與外界相對隔離的自然環境,勢必造成當地文化的保守性、獨特性、傳統性。正如著名民俗學者鐘敬文所言,“民俗是起源于人類社會群體生活的需要。”歷史上,靠天吃飯的陜北農民囿于知識認知,無法參透大自然的奧秘而獲取突破環境限制的生存法則,處在社會最底層的他們感受更多的是惡劣自然環境下生活的無奈與無助,只能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現實的希望寄托于神靈的庇護,從而造就了該地理區域相對封閉環境下巫風盛行的獨立民俗文化特點。在人們心目中忠肝義膽、無所不能的關公、主管施雨的龍王、送子送福的觀音等都成為修廟供奉的信仰對象。民國初期,僅榆林城內東山就有庵觀寺廟51處,農村地區更是分布著各類龍王廟、觀音廟、娘娘廟、關帝廟等廟宇,甚至“有時一個村落就有二至三個”。
民俗文化是地方曲藝生存發展的外部環境,與環境互動而參與民俗是民間曲藝最重要的民間存活方式,陜北說書亦是如此。原本是依賴乞食討生活的陜北說書,依靠既能愉悅又能教化的綜合優勢,在個體農民求子、祛病、消災的還愿中以“口愿書”的形式取代了“巫醫”,在農家的院落、炕頭進行演出,有設壇、請神、參神、安神、送神等祭祀儀式,并在參神環節后按“場”計(“場”是演出的基本單位,每場90至120分鐘,分書帽、正本、結束套語)表演書文,整本書會連演數天甚至二十幾天。口愿書“儀式中,請神、送神位于‘口愿書’的始末,一個‘口愿書’僅請神一次、送神一次;而參神、安神則位于‘場’或中間休息的頭尾,每場書或每次間隔后都必須有此儀式。”再就是每年3至0月在各個廟會演出的“廟會書”,一般演3至7天,和口愿書一樣每場書也有請神、參神、安神、送神的儀式程序,說書人有套詞可用,參神后的演出和口愿書演出內容大體相同,由書帽、小段、正本、結束語組成,常演書目有百余部,包括公案書、脂粉書、俠義傳奇、歷史演義、民間故事等內容,如《金鐲玉環記》《五女興唐傳》《雙頭馬》《小八義》《珍珠汗衫記》《羅成破孟州》《劈山救母》《花柳記》《萬化記》等。據相關資料,廟會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興盛,說明陜北說書作為廟會書必備項目的傳統已很久遠。
及至民國年間,廟會書、口愿書已成為根深蒂固的鄉村文化傳統,是陜北說書最為重要的演出形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俗信仰的文化背景需要,另一方面是盲藝人享有的“特權”。“在陜北的民間觀念中,說書始終被認為是上天賜給盲人的飯碗,具有神圣的不可剝奪性。”當時的明眼人是不能進入說書行業的。陜北說書盲藝人,雖然由于視力缺陷喪失了勞動力,但良好的聽覺與記憶力為從事說書提供了優勢條件。而且,當時說書人因演出的高臺教化而被稱為先生,受到人們尊敬。古人囿于認知偏頗,迷信地認為掌握音樂的“瞽矇”能通神、知天道,所以會選擇他們出現在祈禱祭祀儀式之中。再就是限于當時貧窮的經濟條件,陜北說書具有一人表演且“一專多能”的性價比優勢,既參與宗教儀式充當“巫”的角色,還能通過“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的說書教化、愉悅民眾,讓主辦方以較少的經濟投入便可獲取民俗信仰儀式以及愉悅民眾的高綜合效應回報,也是被選擇的內在原因之一。另外,辯證地分析,當時“口愿書”“廟會書”是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互動的主要媒介,這些演出形式具有推動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互動的功能,也有著推動陜北說書發展的積極意義。
口愿書、廟會書的受眾面廣泛、影響大,是陜北說書藝人獲取經濟收入的主要途徑。再就是,平安書也是陜北說書常見的演出形式,其稱謂具有說書保平安的含義,以愉悅身心為第一目的,演出內容自由,說書人現場抓哏、即興發揮較多,更能體現陜北說書的藝術創造,可視為舞臺說書的雛形,也是我們認為的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融合互動的理想模式。此外,類似于“撂地”的地攤書,演出于集市,多為老弱藝人所為,且摻雜有乞食文化成分,較為少見。還有“社書”的形式也比較少見,形式介于廟會書和口愿書之間,主要是增加了公雞和上山的儀式環節。
通過上述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融合互動的傳統形式與內容,可知陜北說書植根于歷史主義傳統,以普通百姓最感興趣的“未知過去”為切入點,向他們展示曾經世界的精彩,以書目中人物所作所為、人生經歷來預知自己的命運結局獲得心理的調節補償,從而在一段段陜北說書的精彩演繹中找到精神的家園。這些充滿忠奸善惡斗爭的故事,總是以“好”的一方勝利為結局,宣揚了善惡有報的思想。這些書目中男女愛情的題材占了絕大部分,那些一對對青年男女經歷磨難終成眷屬的美好愛情故事,反映出人們對愛情的珍視與期待。常見的公案書,表明當時深受壓迫的農民只能在陜北說書表述的清官之公平正義中找到精神安慰,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此時陜北說書面對的聽書群體,文化教育程度低下,聽書是他們了解未知世界、學習人生道理、得到思想升華的重要途徑,從而賦予了陜北說書文化傳承功能。至于,陜北說書曾經的傳統中多有封建迷信的糟粕,考慮到時代環境、文化背景的作用,也就容易理解個中原因了。
二、“改造說書”創高峰
從上世紀40年代持續到70年代的“改造說書”運動屬于紅色文化范疇,是政治因子作用的結果。基于當時農耕文化的時代背景,自然表現為鄉村文化與陜北說書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
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成立,給予了這片土地紅色文化的背景。1938年5月《陜甘寧邊區民眾娛樂改進會宣言》指出:“我們要愛我們的歌謠、小調、大鼓、蓮花落、花鼓、戲曲等,差不多像愛吃、愛喝、愛抽香煙、愛自己要愛的人一樣。”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拉開了延安革命根據地文藝整風運動的序幕。1944年10月11日召開的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總結了文藝運動取得階段性成果,會議閉幕式上通過了《關于發展群眾藝術的決議》,提出了發展創編新唱本、故事、鼓書,教育改造舊說書人、故事家、小調家、練子嘴家為新生活、新思想服務的目標任務。這些政治因子促進了“說書改造”運動的順利開展。
大約1944年夏秋之際,由于賀敬之發現、引薦,韓起祥受邀到魯藝演出,由此進入了邊區文協的視野。1945年4月,陜甘寧邊區文協“說書組”成立,由程士榮、柯藍、陳明、林珊、高民富、王崇元等幫助韓起祥編新、創新、改造說書。一方面改造藝人“半書半卦”“半書半巫”的身份,促進移風易俗的開展,更重要的是利用“舊瓶裝新酒”創新陜北說書的內容,使其更加契合當時意識形態宣傳的需要。
韓起祥是“說書改造”運動的旗幟性人物,編演新書560余篇,編演新書多有農村題材,演出受眾亦是以農民為主,體現出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的特點。他常年深入農村演出,長期與農民同吃同住,善于觀察體驗農村的鮮活生活并提練成藝術作品。他創作的《紅鞋女妖精》來自延安蟠龍發生的一個二流子和巫神相互勾結危害鄉里的故事,是他深入故事發生地的村莊邊演出邊采風后創作完成的。為了編演《張玉蘭參加選舉會》,他反復深入農村聽取老鄉的意見,編了演、演了改,如此反復終得定稿。《大翻身記》的一至十回也是住在農村和村民反復聊天編寫完成的。此外,他的代表作《劉巧團圓》是反對農村買賣婚姻、提倡婚姻自主的,《反巫神》是反對農村巫神裝神弄鬼、哄人騙人的,《二流子轉變》則反映了農村好逸惡勞行為的轉變,《張家莊祈雨》主要針對農村封建迷信活動的害人害己,等等,莫不滲透著鄉村文化的基因。
正如韓起祥所說:“我的創作主要是靠長期的無條件的全心全意地到農村去體驗生活。人家有些是走馬觀花、下馬觀花,我做不到,我最好是安家落戶。”實際上,他編演新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親近農民群眾的做法,因為熟知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情感愿望、思想動態,所以能用老百姓的話講老百姓的事,講老百姓愿意聽、聽得懂的事,并且愿意把作品置于老百姓的評判之中,把“自己編、文人改、百姓評”有機結合起來,調動發揮各方的能動性,最后才有了一部部作品的成功。他在解放后編演的《合作化好》《麻雀記》也是長期和農民同吃同住后完成的。
除了內容的創新,韓起祥還在大家的幫助下,汲取了信天游、民歌小調、秦腔、眉戶、晉劇、二人臺、榆林小曲、道情的曲調充實到演唱之中,大大豐富提升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受到了農民群眾的熱愛,并集中體現在《劉巧團圓》的藝術表現方面。而在新書改造之前,韓起祥對陜北說書表現手法改革,如添了小镲、發明螞蚱蚱、加了個板以及聲音分男、女、老、少等,不僅豐富了陜北說書的藝術手法,促進了藝術表現的生動形象,而且也為編演新書做了良好準備。
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韓起祥在走遍陜北縣、鄉、村落演出的同時,在延安、榆林、橫山、延長、清澗、米脂等地舉辦了9個新書培訓班,受訓藝人達273人,讓演唱新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讓更多說書藝人加入到了說新唱新的行列,極大推進了說書改造的進程。而且,隨著說唱新書藝人的增多,韓起祥進行了發揮人員優勢的表現形式革新,把原有的一人演唱,改進為每人各執樂器的多人分角色坐唱形式,相對具象化的表演受到了群眾歡迎。上世紀60年代,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之下盲藝人三五人一組下鄉演出,多人坐唱的形式發展為演出常態。
以韓起祥為代表的說書改造運動,創造了陜北說書社會影響力的空前高度,加速了這一偏居一隅的地方曲種走向更廣闊天地的步伐。這種做法無疑是陜北說書對外部生存發展環境能量的一次成功轉化,在陜北說書的歷史主義傳統基礎之上開辟了現實主義的一片新天地,極大擴展了陜北說書的藝術表現力,使之既能表現金戈鐵馬、公案傳奇、才子佳人的古代故事,也能說演現實生活中英雄的先進事跡和普通百姓的家長里短。這些采用傳統說書的程式、手法表現新生活、新內容的做法,無疑加速了陜北說書轉化社會生活為藝術作品的效率,在當時產生極大社會影響亦為自然。
韓起祥的這些新書在藝術上、政治上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他擔任過中國曲協副主席等職務,亦是享譽全國的說書大家,曾經為毛澤東、朱德等開國元勛演出。他常年堅持走進鄉村服務百姓的演出、創作,提速了當時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的融合互動,促進了陜北說書的發展。
受“改造說書”運動的影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安塞、延川、子長、清澗、甘泉等縣,成立了主要演出陜北說書的曲藝隊,1961年延安縣還成立了曲藝館。1978年4月延安地區曲藝館掛牌成立,鄧穎超親自題寫館名,這是全國首家依托單一曲種成立的地市級曲藝部門。這些平臺的建立,為陜北說書更好地服務百姓、增強與鄉村文化的互動,乃至走向更高的平臺奠定了堅實基礎。并且,說書改造運動的影響力持續至今,說唱、編演新生活儼然已為陜北說書的新傳統。
總之,說書改造運動彰顯了曲藝“文藝輕騎兵”的功能作用,政治傾向突出,給農民宣傳了新思想、新意識,傳遞了新信息,鼓舞了革命熱情,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同時愉悅了老百姓的生活,推動了陜北說書的舞臺化進程。同時,改造說書為陜北說書注入的紅色文化基因,為這一曲種的后續發展贏得了更多機會。
三、改革開放后的再出發
改革開放后,延安、榆林地區農村經濟得到極大發展,農村生活展現出嶄新氣象,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極大改變。80年代,石油開采的進入為延安、榆林地區的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及至90年代,進城務工農民逐漸增多,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人們開始從窯洞遷到磚房,電視也在農村大量普及,普通民眾的文化娛樂方式開始有了新的選擇。另一方面,“村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各地重修、新修寺廟之風盛行,廟會活動悄然復興”,意味著傳統民俗的回流。
如此,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工業化大生產和現代傳媒尚未對陜北農村相對獨立的文化生態構成大的影響,外來文化元素和陜北說書還沒有構成競爭關系,陜北說書在百姓文化娛樂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得到了保持。在傳統文化回歸的背景下,藝人進入廟會和村莊演出漸成為常態,促進了廟會書、口愿書在當時的相對活躍。
這一時期,韓起祥繼續扛起陜北說書說新唱新的大旗。1978年延安地區曲藝館成立后,他招收了四女一男學徒,均為明眼藝人,標志著女性藝人開始進入陜北說書的行列。韓起祥教徒弟“是帶他(她)們到農村去,一邊學習、一邊排練、演出,一邊參加勞動。”表演的書目有《劉巧團圓》等新書,還有根據改革開放后農村新發展編寫的《新臨門》《一只老母雞》《老兩口趕會》等。這說明了陜北說書的說新唱新在改革開放后的再發展,與鄉村文化的融合亦是繼續前行,表現內容、形式以及人員組成呈現出新的時代特征。
張俊功是稍晚于韓起祥的著名陜北說書藝人,因1979年在電影《北斗》中的配唱而蜚聲陜北,1978年成立甘泉曲藝隊,收徒七十余人,常年深入農村演出,保持著民間藝人的存活方式。他的最大貢獻是在上世紀80年代創新了陜北說書的表現形式,改原來的坐唱為一人持四頁板表演、眾人伴奏(唱)的走唱。演員由“坐唱”到“走唱”解放了雙腳和形體身段,基本不需要再演奏樂器而解放了雙手,充分釋放了演員的自主表演能力。而且伴奏人員不時以角色化的身份參與表演,有著一唱眾和的生動、熱鬧,也有一人一角色的生動、形象、鮮活,一經推出便大受歡迎。較之傳統說書,張俊功強化了“白口”的比重,突出了表演的即興特點,所演書目有著極富個人魅力的自由發揮,彰顯了說書的代入感、親切感、形象感,特別是體現了曲藝即興的智慧。他的說書在“豐富的精彩”與“簡單的親切”之間找到了平衡,所謂豐富表現為:源于民間生活的“象聲詞”多,揉進的“孩子啼哭、馬的嘶鳴、雞叫”等口技模擬多,運用三弦、二胡、板胡、笛子、揚琴等伴奏樂器多,借鑒陜北民歌、道情、快板等姊妹藝術多,增強戲劇效果的“笑料”多;所謂簡單表現為:在廣泛吸收不同流派唱腔、迷糊音樂基礎上,統一于個性鮮明的“迷花調”,而更加突出表演的重要性。這些改革措施大獲成功,獲得擁躉眾多,在延安、榆林及周邊地區影響很大,多有演出一票難求及觀眾圍觀以致街巷交通擁堵的現象出現。
我們說,只有表現形式受到了老百姓喜愛,才能確保內容的傳達到位。張俊功的改革滿足了觀眾新奇感的需求,演出畫面感強,藝術形象更為直觀具體,而且手法豐富、形式靈活生動,令人應接不暇;再就是加強了陜北說書的娛樂性,把原來看似平淡的內容也能說得絢麗繽紛、奪人耳目,從而受到老百姓的喜愛。這些做法無形中加速了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的融合互動,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陜北說書在鄉村文化娛樂中的主導地位。
當時光挪移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電視在鄉村生活中的普及,以港臺流行歌曲、電視劇為代表的多種文化元素的持續發力,對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互動生態的負面影響開始凸顯。首先,電視為陜北農民了解外面的世界打開了窗口,陜北文化由于地理環境封閉造就的文化獨立性、保守性,因為農民接受新觀念、新思想、新鮮事物的增多而發生改變,人們的一些傳統文化觀念悄然淡化,隨之“口愿書”的數量大幅減少。在發展經濟已為百姓生活主旋律的時代背景下,“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是當時文化與經濟結合的流行模式,傳統廟會的宗教信仰氛圍被商品集散交易的商賈云集取代,廟會書的娛樂功能隨之加強。從生態學分析,陜北說書生態環境的改變,必然要導致陜北說書生態系統的升級或顛覆式的重建。此時陜北說書的表現內容在繼續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同時做出的積極變革符合這種形勢。比如為了適應娛樂的需要而增加了演出的戲劇性、喜劇性以及與觀眾互動的即興成分,為了適應快節奏生活簡短化了說書的篇幅內容。陜北說書的這種活態傳承的流變,符合人們在緊張的勞動生產之余放松心情、宣泄情感的時代要求,也是張俊功改革受到歡迎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認,當時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的積極互動中卻也出現了一些商業化演出中為了迎合觀眾的“三俗”內容,這也是曲藝應對外部生存發展環境變化的尷尬與無奈的表現。
要強調的是,這一時期陜北說書盲藝人一統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明目藝人成為演出主體,而且多有女藝人的參與。同時,陜北說書面對面的演出模式被改變,錄音磁帶、電視、互聯網成為民眾接受陜北說書的新傳播媒介。從1984年至2005年,先后有安塞縣黃土情深說唱藝術團、橫山縣王獅子說唱團、延安市滿多說唱團、子長縣賀四曲藝說唱團、定邊牧彩云曲藝說唱隊等十家主要服務農村的國有或民營的曲藝團體成立。這些新現象的出現,是陜北說書適應生態環境變化的必要之舉,顯現了陜北說書的生命活力,促進了陜北說書的提升進步,為陜北說書鋪平了“舞臺化”的道路。
隨之,陜北說書走向了全國展演、比賽的舞臺,在央視等各大電視臺精彩亮相成為常態。這些看似陜北說書城市化的內容,實則是對鄉村文化的“反哺”。當電視等大眾媒體已成為鄉村接受信息的主體,藝人們在現代媒體中的精彩表現,對于提升藝術形象和社會影響力多有裨益,能引領民眾的“從眾心理”而增加欣賞陜北說書的意愿。同時,陜北說書的形式改造依然在進行著,鄉村題材的陜北說書劇《王二村長》《珍嫂》《村官罷免》分別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亮相,斬獲了包括國家級賽事在內的獎項。當然,陜北說書的戲劇化只能是探索與點綴,并不能代表陜北說書的發展方向。
總之,這一時期的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的互動,繼續行走在傳統與現代相互交織、平行并進的道路之上。陜北說書在面臨工業化的生產、生活方式變化以及電視等大眾媒體迅猛普及的多元文化競爭中,進行了“適應”生態環境的必要改良,“改革創新”是這個時代最為“搶眼”的標識,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融合互動生態的平穩運行得到保持。
四、國家非遺展新姿
此一時期,陜北說書的外部生存發展環境呈現出新的變化。一方面,陜北說書入選首批國家非遺曲藝類名錄,標志著其傳承發展納入了政府工作范疇,延安曲藝館作為責任單位要更加全面、具體地統籌相關工作的開展。而且,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黨和國家“支持農村地區優秀戲曲曲藝、少數民族文化、民間文化等傳承發展。”“支持‘三農’題材文藝創作生產,鼓勵文藝工作者不斷推出反映農民生產生活尤其是鄉村振興實踐的優秀文藝作品,充分展示新時代農村農民的精神風貌。”而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立給陜北說書提供了新的臺口。這一切都表明陜北說書生態環境的向好。另一方面,融媒體發展超乎想象,接收終端的小型化實現了信息傳播的無縫隙覆蓋,民眾接收信息的方式更為便捷,陜北說書與姊妹藝術的競爭更趨激烈。同時,農村文化生態繼續發生著改變,生態環境對陜北說書的限制作用開始凸顯。集中表現在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更多青壯勞力離開鄉村走入城市,使得陜北說書觀眾群體逐年流失萎縮,老年觀眾占有絕大多數的現象普遍。
而且,隨著人們思想觀念的持續更新,“口愿書”已經幾無市場空間。傳統的廟會書在原來服務經貿物流的基礎上繼續流變,陜北說書雖憑借儀式中的不可缺少性尚保留有一席之位,但主體地位已經喪失。究其原因,一是主辦方的經濟條件得到改善,戲曲、道情、小品、小戲的演出團體亦在邀請范圍之內,陜北說書不再是唯一選擇;二是陜北說書相對單一的演出形式、嚴肅的主題、較長的篇幅,在當下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下,很難再讓民眾“穩下心來”聽書。還有廟會原屬的傳統信仰觀念遭到淡化,體現出的更多是一種村莊外出務工人員與村莊的嶄新“情感鏈接點”功能。這樣,一些原本主要演出陜北說書的團體,根據客戶需要在陜北說書、小品、小戲等多個藝術門類之間“穿越”。為了增加說書吸引力,陜北說書與觀眾的即興互動愈加強化,說書的娛樂性更為突出,藝人們隨口而出的吉利話、祝福話、場面話占據了顯要的演出地位。由于陜北說書表現形式的機動靈活以及把點開活的演出針對性,容易契合觀眾的興趣點、興奮點,再加上語言親切、主題傳統教化的優勢,在下鄉演出中反倒比一些姊妹藝術更容易攏住觀眾。
陜北說書在與鄉村文化的融合互動中,形式也更為豐富多樣,圍繞大局、服務大局的意識更加突出。除了服務婚、喪、嫁、娶等人生禮儀的傳統演出之外,業務拓展到了開業慶典、廣告宣傳、同學聚會、普法宣傳、政策宣傳等諸多方面。如《婚姻法》《交通法》《國家保密法》、公益訴訟、道路安全的宣傳,掃黑除惡、鄉村振興、精準扶貧、扶貧扶志、“三變”改革、減稅降費、十九大政策進鄉村的宣傳等。這些演出以下鄉惠民的形式在農村大隊部、文化廣場等地點出現,對于鄉村文化的正面引領作用極其明顯。表現農村現實生活的《山里回來些年輕人》《那道道峁梁那道道川》《爭書記》《蘋果滿山上紅》《常賴娃脫貧記》等大量作品涌現,有的在當地電視臺演出,有的榮膺國家大獎之于鄉村文化的貢獻顯而易見。
更重要的是,陜北說書入選國家非遺名錄的“紅利”得到釋放,迎來了新的傳承發展機遇。一方面,延安曲藝館作為責任單位深入鄉村采訪藝人、錄制傳統書目,圍繞挖掘、整理、研究、傳承、保護、宣傳、展示做了大量的工作,且成績顯著。先后出版的《曹伯植文集》系列、《韓起祥文集》系列以及連續七屆說書培訓班等可茲佐證。另一方面,陜北說書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得到進一步彰顯,在重要媒體、重大活動中亮相的機會大大增多,參與“反哺”鄉村文化的功能得到加強。2018年春節,粗獷、豪放、樸實的關中漢子們唱著充滿“黃土味”的陜北說書和操著吳儂軟語、溫婉秀氣的江南女子們演唱的蘇州評彈“混搭”,組成了《看今朝》的強大演出陣容,在人民大會堂的春節團拜會為國家領導人演出后,又在央視元宵晚會給全國人民進行了精彩展示。這一事件,隨著媒體擴大效應的持續發酵,在陜北乃至全國曲藝界都影響很大,進一步增強了陜北說書在鄉村文化中的親和力、影響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專業文化工作者的倡導下,陜北說書原本不著演出服、演出中隨意喝水甚至吐痰的現象得到改善,演出的舞臺美感得到進一步增強。此外,從2006年到2012年間,國家專業團體志丹縣民間說唱藝術團、安塞縣民間藝術培訓中心曲藝隊以及民間曲藝班社綏德耿曉飛說書藝術團、子洲縣郝飛說書隊、吳起縣洛河源說唱藝術團、安塞張安平曲藝團、安塞縣招安鎮光勝說唱藝術團、子州喬仰文說唱藝術團、榆陽區駝峰民間說唱團等相繼成立,他們主要以農村為服務對象,這說明陜北說書在鄉村文化建設中的重要功能作用繼續得到了有效發揮。
個體藝人主動應對生態環境變化的適應性改良也在繼續之中。一些富有創新意識的藝人,積極利用融媒體受眾面廣、影響力大的特點,基于抖音、快手APP進行陜北說書直播,僅子長縣說書藝人賀四就在“抖音”擁有近四十萬的粉絲,累計觀看量達到千萬次以上,子洲縣說書藝人喬仰文、橫山縣說書藝人熊竹英等在此方面也具有較大影響。
總之,這一階段國家非遺的“背書”給陜北說書營造了更加有利的生態環境,陜北說書基于生態環境變化的持續改良創新,保護了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的融合。陜北說書在愉悅民眾、調節生活、道德教化、情感補償、思想啟迪的過程中,娛樂功能得到強化,舞臺化進程進一步加速,藝人服務大局、與時俱進、服務百姓的意識進一步增強,與鄉村文化融合互動的方式更為豐富,內容也更為廣泛。但不可忽視的是,青年觀眾參與度乃至參與熱情的降低,導致了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融合互動能量轉化關系的弱化。
五、前景展望
展望延安、榆林地區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融合互動的前景,有必要分析成就這一生態現象特點及各組成要素的功能作用,以便為分析提供啟示作用。
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的融合互動在不同時期發揮了愉悅民眾、文化傳承、道德教化、宣傳普及政策知識的功能作用,對促進民眾心理健康、和諧家庭及鄰里關系、維護社會穩定有著積極意義。這一生態現象,呈現出經常、動態的特點,由古至今傳承延續且富有活力,雖然在融合方式、融合內容、融合特點上有一定流變,但都是為了適應生態環境做出的必要改良,最終維護了這一生態系統的平穩運行。之所以如此,延安、榆林地區相對封閉、惡劣的自然環境下,人們形成的文化傳統起到了支撐性作用,這種文化的獨特性根深蒂固,即使各種外來文化與現代媒體持續沖擊,仍未撼動陜北說書在鄉村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陜北說書融進了當地普通民眾的生活,擁有著平行于區域文化傳統的觀眾群體,是陜北說書發展的最大源動力。從藝術主體看,陜北說書1330余人的龐大演出群體,大多為半農半藝或專于說書的農民,他們為了生計在藝術上自強不息、勇于攀登,能夠圍繞服務百姓,主動適應包括人們生活方式的外部生存發展環境的改變,對說書內容、表現形式、表達方式、傳播方式、藝術風格、藝術手法等進行持續變革,與之保持常態化和諧互動的能量轉化關系,是這一生態現象得以延續的又一根本要素。而國家、地方各種利于陜北說書發展政策的落實實施,對藝人的幫扶、輔導、推介,對創作創新的持續推進,是這一生態現象繼續的保障。
基于上述思維,將來的陜北說書要繼續維系與鄉村文化的互動,繼續保持百姓生活內容的有機組成是生存發展的根本,放棄百姓生活的融入就等于沒有了持久的動力來源。
目前看,延安、榆林地區與外界交流的持續深入,現代媒體信息傳播必然影響到原有文化傳統的獨立性,陜北說書的廟會書、口愿書的說書傳統會面臨更多的挑戰。陜北說書在與姊妹藝術的競爭中,能否保持地位不被撼動,或者只是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存在,極大弱化其藝術價值和儀式價值,將會是一個問題。
更嚴峻的是,陜北說書的藝人隊伍逐年萎縮,傳承形勢不容樂觀。工業化背景下,有著更多就業選擇的年輕人不再把陜北說書當作生計。目前二十幾歲或更小的陜北說書從業者亦或學習者屈指可數,后續藝人力量不足將成為困擾陜北說書發展的又一難題。縱觀延安曲藝館、安塞曲藝隊、志丹縣民間說唱團等國有專業單位,以曹伯炎、甄三梅為代表的專業演員隊伍,也存在年輕人占比明顯虧缺的現象,較之民間藝人與鄉村文化的融合力度亦有提升空間。而且,隨著城鎮化的加劇,“二八定律”在村民留村居住與遷居城市方面得到集中體現,而留守農村的20%又大部分為老年人。農村觀眾群體的迅速滑落,必然導致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的融合互動生態受到影響,陜北說書的新發展已然站在了選擇的“十字路口”。現在,作為進城村民“鄉愁”情結的體現,陜北說書出現在一些城市家庭、朋友聚會的現場,可視為與鄉村文化互動的延伸,亦可視為陜北說書城市化進程的初級階段。今后陜北說書究竟如何走好城市化道路,利用進城村民的生活方式留存,鏈接、轉化陜北說書傳統的后續發展模式,值得深入探討。
如果,陜北說書藝人和觀眾群體都出現了問題,那么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融合互動的生態平衡將被打破,陜北說書生態系統的升級改造、顛覆性的重建亦或陷入運行停頓都存在可能。
毋容置疑,陜北說書和全國地方曲種的狀況類似,存在培養傳承人、培養觀眾群體的雙重難題。目前看,加大陜北說書“文教結合”“文旅結合”的力度尤為必要。文教結合,可藉以陜北說書國家非遺的政策優勢,一是大力施行“進得去、留得住、出成果”的陜北說書進校園工程,以傳承家鄉文化為落腳點,編寫符合當地教學實際的陜北說書地方文化教材、校本教材,將陜北說書教學納入中小學日常課程教學體系,邀請國有曲藝單位職工或陜北說書藝人進入課堂,從根本上解決陜北說書培養人才、培養觀眾的雙重問題;二是在已具陜北說書教學、研究基礎的延安大學進行以培養傳承人為目標的高校人才教育,為增加學生報考意愿,可協調相關部門進行訂單化培養,解決學生就業的后顧之憂,并以此培養模式構成的專業隊伍實現對陜北說書的行業引領。文旅結合,應將陜北說書的紅色文化基因、獨特地理標識的藝術價值在現代旅游業得到有效轉化,積極融入延安紅色旅游、陜北文化旅游,在展示陜北文化魅力的同時提升陜北說書的影響力。此外,為適應現代觀眾欣賞需求,陜北說書在表現內容方面要體現時代特點,表現(達)形式要契合觀眾審美,傳播方式要堅持舞臺主體,除此之外,還要積極利用現代媒體,藝術手法要有更多的豐富與借鑒,從而更為突出時代特征,創造性轉化陜北說書傳統藝術,與時代共舞。由此,開啟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融合互動的新時代步伐,推動陜北說書生態系統的全面升級。
綜上所述,延安、榆林地區陜北說書與鄉村文化的融合互動的前景,呈現出需要適應生態環境變化而不斷變革的特點,具有向現代城市生活延伸的發展趨勢。推動這一國家非遺項目的傳承發展和與鄉村文化的融合互動,應“居安思危”及時發現當今存在的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為陜北說書服務民眾的可持續積蓄能量。
注釋:
[1][9]曹伯植:《陜北說書概論》,陜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頁,22頁。
[2]清延州知府許瑤奏折。轉引自呂靜:《陜北文化研究》,學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
[3]鐘敬文:《民俗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4][22]孫宏亮:《陜北農村廟會書調查與思考》,《社會科學論壇》,2009年第2期。
[5]呂波:《陜北農村神廟活動探析》,《榆林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4期。
[6]“口愿書分仕途口愿、訴訟口愿、消災口愿、治病口愿、生育口愿、婚姻口愿,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生活口愿。”摘自曹伯植:《陜北說書概論》,陜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頁。
[7]長篇大書稱“本”,陜北說書有“短為段,長為本”的說法。
[8]孫鴻亮:《儀式和說唱:陜北農村口愿書田野調查》,《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11月第11卷4期。
[10][13]孫宏亮:《彈起三弦定準音:陜北說書考察》,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頁,61頁。
[11]臧立:《試論我國說唱藝術的起源》,《曲藝論叢》第四輯,中國曲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頁。
[12]又稱打閑書。
[14]柯仲平:《陜甘寧邊區民眾娛樂改進會宣言》,《新中華報》,1938年5月25日。
[15]參見胡孟祥:《韓起祥評傳》,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頁。
[16]1937年11月陜甘寧邊區文協成立。
[17]韓起祥(1914—1989年),陜西橫山人,著名陜北說書表演藝術家,原中國曲協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原延安曲藝館館長、書記。一生致力編演新書、推廣新書,創作改編新書560余篇。代表作有《大翻身記》《張玉蘭參加選舉會》《劉巧團圓》等,多次受到國家獎勵。
[18][23]曹振乾:《韓起祥文集》,中國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頁,491頁。
[19]參見韓起祥口述、孫宏亮編:《紅色說書人:韓起祥陜北說書口述史》,中國致公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第45頁。
[20]參見曹伯植:《陜北說書音樂探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390頁。
[21]張國全編著:《陜北文化通覽》,陜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頁。
[24]這一時期延安、榆林地區縣屬曲藝隊下鄉演出繼續進行,直到本世紀初還保留有藝人在文化部門安排下到各村流動作藝、藝人從中獲取一定酬金的演出模式。
[25]《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頁。
[26][27]《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頁,18頁。“三變改革”指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
[28]受訪人:韓應蓮,女,62歲。訪談人:賈振鑫,訪談時間:2019年5月17日。訪談地點:西安竹韻齋分部。
[29]據曹伯植:《陜北說書音樂探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402頁,“目前陜北說書尚有民間藝人2000余人”,參照該書出版年度,隨著王學師、白旭章、吳錫忠等盲老藝人的故去,當下藝人規模已有所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