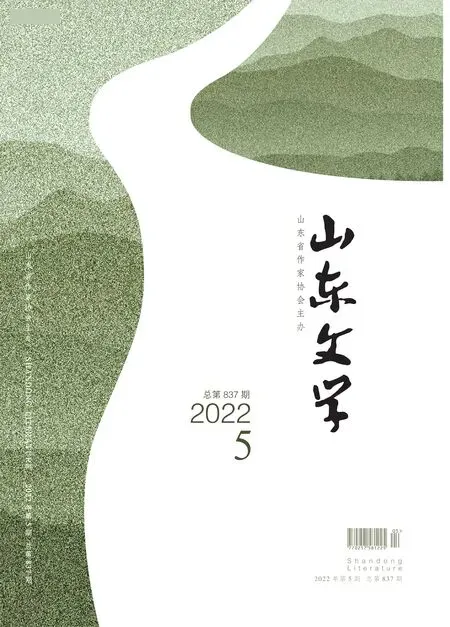在海岬上鉤沉
——漫議楊機臣的紀實文學寫作
張洪浩
在中國北方大陸的東端,有一個海濱城市叫威海。在威海市區最東端的岬角,有一個人常常站在這里向東方眺望。這里是他辦公的地方,海近在咫尺,在幾步遠的崖下。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枕浪聽濤的所在,正前方碧波萬頃,目光稍稍右移,兩千多米外便是著名的清代北洋海軍基地劉公島。他為自己所處的位置而自豪,在他看來,這逼仄的海岬乃是觀察世界的絕好的立足點。威海灣的遠處是黃海,黃海的遠處是太平洋,站在這里向前看去,既是看東方也是看西方;他在向前看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向后看。他希望自己的目光能深遠些,再深遠些。
這個喜歡眺望的人是一位作家,他叫楊機臣。他的目光常常在打撈記憶,鉤沉歷史。
有作家曾經如此說過:對于一個具備基本文字能力的人來說,寫作是正常的,不寫作才是不正常的和不應當的。這種說法,乍一聽會為之驚訝,細思則深以為然。是的,寫作不過是一種表達,與說話類似,它是所思所想的釋放,是獨自一人時的傾吐。一個有基本的寫作能力而又善于思考的人,很容易在某一天忽然要寫點什么,就像一個健談者難以抑制他的侃侃而談。
楊機臣的寫作正是這樣,他在“不學藝”的中年開始的寫作,是人生走到這一步的必然:大半輩子的生命體驗和對生活的認知感悟,讓他不吐不快。早年供職于機關,他曾從事過文字工作,對于寫作并不陌生。他又是一個特別勤奮特別用心的人,立志寫作以來,他苦心經營,孜孜不倦,很快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國內最有影響的散文雜志諸如《中華散文》《散文》《美文》等時常可見其作品發表,《雨季心思》《海灣悠悠》等篇什還被各種選刊、教科書和學生課外閱讀材料選載過,散文集《海隅印記》獲得過冰心散文獎。
讀過楊機臣許多散文作品。他的散文有短有長,短的千八百字,長的數萬言,所寫多與記憶有關,與故鄉的歷史、風物、人與事有關。無論是短章還是長制,讀來感覺都頗有內容,也富有靈氣。他的寫作是平常心的寫作,不故作矜持和高深,文筆有行云流水般的明快灑脫,而無矯飾和滯澀之感。他的文字明朗坦誠,始終保有純樸的民間情懷;在他那些拉家常般的敘說中,樂觀、幽默和自我解嘲隨處可見。豐富的知識、不俗的見解和俊逸的文采,是其散文的特色,更重要的還有飽經歷練者樸素率真的生活態度和游刃有余的人生智慧。他似乎天生具備點石成金的本領,寫作素材在他可謂俯拾即是,似乎從來沒有匱乏過,永遠也不會枯竭。然而,在我們為其散文創作的強勁勢頭而驚訝之時,他又悄悄地來了一個華麗轉身,長篇大論地寫起了紀實文學。
中年人的寫作往往有“向后看”的傾向,而紀實文學主要是一種“向后看”的文體,所以,楊機臣由散文而紀實文學,是順理成章的過渡。他從挖掘記憶、追溯個體生命歷程開始,逐漸擴大題材領域,在紀實寫作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于是,廣闊的寫作前景在他面前迅速展開。近年來,《中國作家(紀實版)》《中國報告文學》等大型刊物先后推出了他多部長達數萬字的中篇紀實文學作品。不僅如此,他還接二連三地出版了好幾本紀實文學作品集。
持有現實主義寫作觀的作家,會知道筆下的題材離不開腳下的土地,自己的寫作對本土負有責任。楊機臣的寫作正是如此,他的散文和紀實文學主要是對本土歷史文化的記錄和挖掘,是源于故土情結的一種自覺選擇。故鄉威海是突出于中國北方大陸東端的一個岬角,位置獨特,因而有著很不一般的歷史文化:道教全真教留下的諸多遺跡和傳說,清朝北洋水師覆滅的沉痛記憶,英租三十年的殖民地歷史……這一切,在他的散文中已有不少敘述,具有明顯的紀實色彩。他在近年轉向紀實文學的寫作,應該是碰上素材富礦之后的必然選擇。
楊機臣最初的紀實文學作品,其中多篇的主題可用他的一個題目來概括——拯救威海的記憶。這些作品的產生有一個共同的契機,即突然冒出來的檔案資料。前些年,威海市檔案局積極聯系英國方面,獲得了大量英租期間的檔案。正是在這些檔案中,楊機臣獲取了極其豐富的威海史料,在此基礎上進行一系列的發掘、梳理、調研和想象,讓僵死、枯燥的資料復活、生動起來,變成了一幕幕可視可感的活劇。
《拯救威海的記憶》是他首部中篇紀實文學作品,記述的正是威海市檔案局赴英查檔的復雜、動人的故事。檔案是以文字和實物的方式留下的記憶,我們知道,大到民族,小到個人,失憶都是可怕的,是令人惶恐不安的。威海因為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缺失近百年的檔案,是一個記憶殘缺的城市。“拯救威海的記憶”乃是一個迫不及待的、充滿了懸念的事情,因而,異域查檔的故事顯得分外迷人。楊機臣的敘述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現實的記述中穿插了歷史的回溯,使得讀者在閱讀中愈來愈強烈地感受到找回一個城市的記憶的焦灼。文章所記錄的不僅是威海檔案人員一次次赴英查檔的行動,還有英國民間人士對查檔的熱烈回應。由此,我們可以感知到中西方人共同的懷舊情結。
關于記憶的拯救是成功的,關于拯救的記述也是成功的。正是在這一篇的基礎上,又衍生出另外一部紀實文學作品:《一個蘇格蘭家庭的威海探族之旅》。這是赴英查檔故事的后續,記述的是蘇格蘭商人鄧肯·克拉克的孫子、年逾七旬的小鄧肯在闊別威海66年之后故地重游,追尋祖輩和父輩記憶的故事。鄧肯·克拉克是英租時期在威最重要的蘇格蘭商人,“兩代人40多年的奮斗,鄧肯家族在威海建起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王國。他的投資涉及旅游、市政、交通、地產、農業和教育領域,是近百年來威海最大的外資商行,對當時當地經濟和社會生活以至相當長的時期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樣一個家族,對英租時期的威海有著巨大的貢獻。兩代人幾十年苦心經營的歷史記憶,使得家族長輩多年來一直處于深深的懷舊情感之中,對異國他鄉的威海可謂魂牽夢縈。小鄧肯的威海探祖之旅,旨在追尋家族五代人的記憶,釋解他們濃重的威海情結,因此是一次意義非凡的跨國尋跡行動。善于捕捉題材的作者,敏銳地意識到機會的難得,以攝影師的身份作了全程陪同,和小鄧肯一道追溯歷史,探查鄧肯·克拉克家族在威海留下的建筑遺跡,尋訪祖輩一百多年的過往歷程。這樣切近而親密的接觸,使得作者成功地掌握了全部素材,并順利寫下了這樣一篇長文。作者詳盡地記錄了小鄧肯探祖過程的諸多細節,又以頻頻閃回的筆法貫通了百年記憶,梳理了鄧肯家族在威海的歷史脈絡,講述了兩代人在威海的故事,以及他們回國后對威海的懷念之情。文章氣韻飽滿,令人感動又令人回味。
《被遺忘的15萬“一戰”華工》同樣是一部來源于英方檔案的紀實文學作品。作品告訴我們,一戰中,中國共有15萬華工赴歐參戰。正因如此,中國北洋政府成為了協約國的一員,在戰后也終于享受到一次久違的戰勝國的滋味。然而,赴歐參戰的15萬中國勞工是付出了慘重代價和犧牲的。如此重大的舊聞,如此沉重的題目,對于作者來說,所激起的不僅僅是探究來龍去脈的興趣,更重要的是一種鉤沉歷史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作者在查閱大量英方檔案的同時,還查證了中方文史資料,采訪了本地民間人士,故而所寫逼近真實,又做到了具體生動。這部作品題材宏大,背景復雜,但作者敢于直面挑戰,其宏觀把握頗具氣勢,敘述大開大合,遒勁有力。如此這般記寫中國勞工的紀實文學作品,在大陸當數首篇。這是一次了卻沉重心愿的寫作,作者煞費苦心地寫下它,體現了自己的良知,也實現了駕馭題材上的某種超越。
威海這塊土地需要拯救的記憶很多。四萬多字的《威海衛人與香港警察》,是對沉潛的威海記憶的又一次打撈:“威海素有僑鄉之稱,據不完全統計,僅香港僑胞就有五六萬之眾。不僅如此,以香港為跳板,他們的子孫及親朋好友走向世界各地不計其數,而且綿延近百年生生不息,圈子越滾越大,未來其必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海外華人勢力。尋本溯源,九九歸一,這支人群的根始于1922年起赴港從警的威海先人。他們雖然早已逝去,卻不愧為威海人乃至中華人融入國際化的先軀與探索者。”對這一題材的重視和執著挖掘,難能可貴,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楊機臣本人就是一個香港警察的后代,兒時爺爺發黃的老照片是一個懸念式的存在,誘惑他在幾十年后去破解歷史之謎。因為有感情上的維系,其工作有了非凡的熱情和巨大的沖動。于是,難以考據的資料浮出水面,蒙塵的記憶被漸漸拭亮,僵死的歷史復活和流動了。在此,作者的眼光是宏闊的,他追尋的是一個時代的故事,一個史實的流變。“我爺只是滄海之一粟,似流星一閃即逝。然而,他的人生因此而飽滿豐厚。”這句話說得好。其實,那數百名遠赴香港當警察的威海人,哪個不是如此?還有他們的后裔,都因這一歷史機遇改變了人生軌跡。在寫到威海籍香港警察的后裔、消防界精英宋修民的時候,作者說:“如果說我的人生可窺我爺以及眾多還鄉香港警察回鄉后人生及家庭的軌跡,那么宋先生的人生則典型地反映了香港警察從警及遷居香港后漫漫人生路上的悲歡離合……”是的,正是在宋家兩代人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比較完整的、浸染著血淚的喬遷史和奮斗史,也更加清楚了這部紀實作品的內涵。作品中,值得特別重視的一個人,是蜚聲香港政壇及海內外的政界人士梁振英,這個威海人的根苗,不僅是威海港督后裔中的翹楚,還是香港市民所推崇和追慕的榜樣;他靠底層打拼終至脫穎而出,顯示的不僅僅是威海人可貴品質的傳承,還有更加耐人尋味的東西在其中。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移民已成平常事的今天,作者對這一題材的追尋,是特別新穎別致而且深具現實意義的。
長篇紀實文學《膠東人家》是作者迄今篇幅最長的作品,達10萬余字。作品從清乾隆四十八年寫起,一直寫到新中國解放前夕,時間跨度漫長,出場人物眾多,既有居高臨下的歷史俯瞰,又有細致入微的現實描寫。它記述的是吳姓人家自濰萊平原逃難東遷來到榮成沿海村莊后,幾代人持家、經商、辦學、報國的故事,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家族史記。素材是塵封已久的,故事是繁復錯雜的,所以寫起來難度很大。然而作者不辱使命,經由深入采訪和合理想象,將一部漫長的血淚家族史寫得異常扎實飽滿,可讀性強又可堪回味。三代頂梁柱的創業守業,整個家族的沉浮掙扎,通過舒卷有致的敘述和描寫,演繹成為一幕幕鮮活的戲劇,復活了一個家族的百年記憶:生與死,成與敗,困頓與順遂,挫折與磨礪……民間底層人物的榮辱悲歡,被描畫得波瀾起伏,風云激蕩:逃難東遷,扎根菜園;修路種菜,禁毒御敵;傳宗接代,教育孩孫;訂立家訓,授業解惑;襄助村民,義舉頻仍;家勢衰微,晚景凄涼;青樓失足,收養孤女;氣死老婆,搶得媳婦;兒郎中魔,戀人殉情;冰船搶險,酒宴散伙;老來信佛,出任校董;暗度陳倉,勇赴國難……透過具體的故事,我們看到的是豐富廣博的內涵: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沿海地區農民和漁民所經受的深重苦難,儒家文化熏染下形成的道德準則,膠東人所秉持的堅韌頑強的生存信念,位卑未敢忘憂國式的民族大義,等等。可以說,這是一部具有史詩氣質的作品,是《百年孤獨》式的大跨度的歷史敘寫。作品中的膠東漁村猶如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而吳姓家族也恰似布恩蒂亞家族。人物的沉浮掙扎,世事的消長興衰,命運的跌宕起伏,一切都歷歷在目,卻又恍惚如夢。一股悲愴的暗流,始終涌動在文本深處,時時引發讀者深長的慨嘆。作品的可貴之處在于,雖然多有細節上的演義,但其全部故事都是有據可查的,因而特別具有啟示意義,并能引發讀者的思考。這也正是作品的紀實屬性的魅力所在。更為重要的是,作品的著力點不僅僅在于敘述家族歷史和人物命運,還特別注重了對于膠東沿海地區特定歷史風物及民俗風情的描寫。人物、故事與人文歷史背景等諸多信息元素的水乳交融,使得文本具有一定的百科全書性質。這就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文化含量,豐富了作品的價值內涵,等于以點帶面地書寫了一部膠東沿海區域文化的百年歷史。這里透露的信息是異常豐富的,比如說膠東在過去曾經有過怎樣的移民史,沿海漁民是如何經商發家的,他們為什么重視教育,為什么特別注重互幫互助、友善待人,為什么會出大批的經商、從政人才,等等。許多人文方面的問題,都可在作品中找到說明,找到印證,找到歷史淵源和發展脈絡。
曾經奇怪作者為什么會起意寫這樣一部書。這部長篇的寫作沖動,是讀者所不容易看出來的;它不是突發事件,沒有新聞性,也不是某種意外發現所導致的發掘,更沒有個人自述的成分在其中。就文體傾向來看,作品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另類的、具有散文風格的長篇小說。它是真正的“大塊文章”,雖以一個家族為視域,但本質上寫的是大地和大地上的事情。它并不需要一個貫穿始終的邏輯線索,也并不特別凸顯某個人物。它的主題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如果非得要有一個主人公的話,那么只能說主人公是沿海地區的膠東人。作品的題材是厚實、穩定的,因而在寫作上必然體現為內斂、沉著的風格。這是難度很大的寫作,作者之所以敢于迎難而上,耗費很多精力寫它,其中必有深意存焉。
在通讀了作者近年全部作品之后,我忽然明白了他創作這部作品的動力和心勁之所在。作者了解自己的優勢,了解自己的能力。對于本土歷史文化的來龍去脈,對于當地人性格的形成,他有很深的理解,并且已經寫了許多;但可能,他覺得自己并沒有寫透,沒有寫到過癮的程度。而要寫得透,寫得過癮,必須要有一個大的框架結構。正因如此,他最終選擇了這樣一個題目,用了一本書的篇幅來寫。我相信這是他酣暢淋漓的一次寫作,猶如胸膽開張的疾呼,一醉方休的暢飲,日行千里的狂奔。這一次寫作可能很累,但很痛快,作者實現了很久以來的愿望,成功地抵達了預期的目標。
一部寫民間生存故事的作品,能夠忠實地再現民間歷史脈絡,又能表現出命運和人性的內涵,表現出草根民眾的生機與活力,其價值自不待言。《威海衛一家人》就是這樣一部中篇紀實文學作品。這其實是作者的父系家族史,內中飽含充足的創作原動力。
作品從太爺爺輩的奮斗寫起,時段在二十世紀前二十年,也就是英國人強租威海衛的大背景下。太爺爺是位典型的膠東漢子,老實木訥,肯于吃苦,為了給四個兒子置辦宅基地,他跑到北京干挑水生意,一直干了十幾年,先后掙下幾十畝土地。這是民國時期外出打工者的代表,作品中太爺爺的這段歷史,包含了一定的民間史料價值;更重要的是,因為有這一鋪墊,才可以講述后面的故事:分家。
分家的故事是一個核心的故事,因為在國人的傳統觀念中,三世乃至四室同堂,才意味著家庭和睦、祖孫幸福。所以,爺爺輩的老大鬧分家,和太爺爺的外出打工一樣,表現的是這個家族的勤苦老實人不肯安于現狀、反叛的一面。這里面其實有相當多的文化內涵與人性內涵,也可以說代表了膠東人血脈中的某種東西。爺爺輩的兄弟四人,性格各異,在分家問題上態度也各各不同。分家的故事,分家后老大為蓋房子經歷的酸甜苦辣,是作品工筆描寫的內容,許多細節是耐人尋味的。比如四個兒子為分家而抓閹,想分家的、勤苦的老大和厚道肯干的老三抓到的都是宅基地,但他們真要蓋房的話,又覺得力量不足;游手好閑的老二和體弱的老四,命運的安排是讓他們擁有現成的房子。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還有,老三在蓋房上對老大施以援手,感人至深;多年以后,老三的兒子蓋房面臨困境,老大的兒子又代父輩做了傾力回報。這些仗義之舉,是民間傳統風尚和道德倫理的所在,也是文章中溫暖人心的所在。
置地,蓋房,對于農民來說,都是一生中的大事,為此常常要傾盡積蓄,竭盡全力。也正是在這樣的人生重要關節,農民的艱辛和堅韌,一代人乃至一個家族的命運軌跡,都得到了充分顯現。這些事情,雖然并無大的波瀾起伏,但對于植根于土地的農民來說卻是特別重要的,經由作者一筆一筆寫來,感覺特別真實,其中的人生況味值得咀嚼,常常讓人感到辛酸,為之嘆息。作者以小說家的耐心,啟動想象,把兩代人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前后表現,寫得細致入微,生動可讀,所謂“紀實文學”的文學性由此凸顯。
什么叫命運?命運既包括了天意,又在于人為;前者如抓閹,后者如蓋房。二者的緊密結合,符合天地大道的運行法則,也使得熙攘人間活力永存。
在寫民間生存和命運的大主題上,有著豐富人生閱歷的楊機臣顯得非常老到。他善于抓住要緊的核心故事,提綱挈領、簡潔有力地表現主題。寫爺爺輩的兄弟分家如此,寫自己女兒的擇業也是如此。《我與女兒》一篇可看作紀實散文,它的敘述分為兩個層面:表層故事是女兒的就業問題,以及這一問題帶給全家人的焦慮、思考,和最終的抉擇;深層的東西,是作者大半輩子的人生經歷和人生感悟,以及這一切導致的人生決斷。作品采用了回旋的結構,以女兒的就業問題為引子,頻頻擴展敘述幅面,把鏡頭探向自己生命歷史的縱深處,使得故事愈來愈豐富,思想愈來愈厚實,意蘊愈來愈深邃。讀后首先會覺得,這是一部作者的回憶錄或者家庭史;其次,會認為它包含的東西很多,主題在深化中又有升華,并逐漸超越了具體的個人,具體的家庭,上升為對中國普通百姓命運的思考。作品的涵蓋變得廣闊起來,它反映的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普遍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狀態,是億萬個普通百姓家庭共有的生存困惑,因此具有一種特別感人的力量,能夠引發讀者強烈的共鳴,不少地方可謂催人淚下。
楊機臣“向后看”的民間寫作不僅體現在寫塵封已久的歷史,還體現在寫正在流動著的現實。比如在《老村·老街·小區》中,他分別寫了威海的一條百年老街、一個有著四百多年歷史的老村、一個小區(過去是故土的一道山崖)。擁有作家、攝影家雙重藝術身份的作者,往返穿梭于歷史和現實間,不倦地游走、拍攝、記錄。他作了許多歷史追溯和客觀記述,并沒有再多說什么,但一切盡在不言中,我們還是能看到他對歷史遺跡的眷戀,看到他文字和鏡頭之外的不舍之情。在回憶故土山崖的原始舊貌時,他的筆致變得多情起來。經過與父親的一番追憶,他甚至將此地原來地塊的名字按位置一一編排了一遍。這些地名恰如一個個情感密碼,可以還他一個久違的原初。
懷舊,關注民間文化,考查歷史的陳跡遺影,體現的乃是有文化素養和浪漫情懷的人的共同情感。楊機臣了解本土歷史和文化,而且由衷地喜歡做這方面的工作,可謂難能可貴。他以不倦的激情和辛勤的勞作,捧出這樣一些散發著濃郁的本土氣息的作品,是對地域文化的卓越貢獻。記錄歷史的他,應該被歷史記錄。
綜觀作家的憶舊散文和紀實文學寫作,可見目光是深遠的,其對地域性歷史題材的探究、發掘和思考,觸及的是關乎人類生存的大命題,因此作品往往具有某種文化上的意蘊,等待我們用心省察和感悟。他“向后看”的尋根,總是帶有“向前看”的現實意義。他的寫作還常常呈現出可貴的原生態性質,不可多得。他家族的、私人的故事,并不僅僅屬于家族和私人。他故鄉的村莊楊家灘,一旦出現在作品中,就超越了地理意義上的楊家灘,所表達的一切可能涵蓋了膠東,山東,乃至中國。文章從具體、個人的位置上寫起,是不會錯的,這可以接底氣,可以避免大而無當,可以避免情感的匱乏和虛假。而情感,是寫作的原動力,是緣起,同時也標示著文章的方向,感召著自己的讀者群,它指向的正是作品的歸宿。在我看來,作家寫作題材的區域,正是他情感抵達的區域;他作品的高度,正是他情感抵達的高度。
多年來,楊機臣始終在勤奮地耕耘,執著地尋找,不倦地探索。作為一個業余寫作者,他所取得的成績,他對故土的貢獻,是難能可貴和值得珍視的。對于文學寫作而言,地域的所謂中心和邊緣并不重要,寫好腳下的土地,寫好熟悉的生活,就有可能寫出好的和重要的東西,而以地方的發現為中心的表達,常常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相信不久的將來,在散文和紀實文學的寫作中,楊機臣必會有更加豐厚、更加令人矚目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