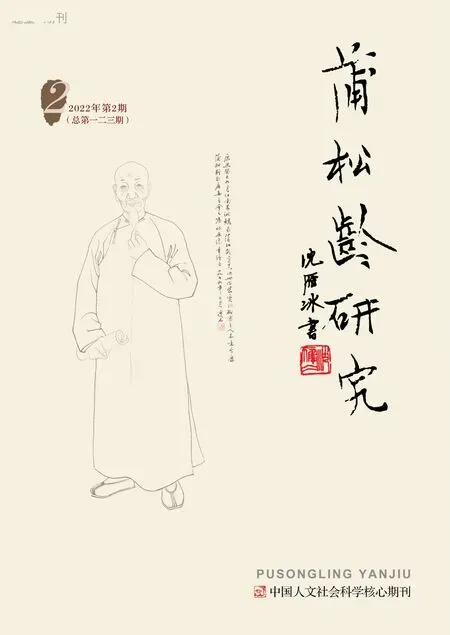《品花寶鑒》中異化的才子佳人模式
李雨薇 舒 乙
(1.青島港灣職業技術學院,山東 青島 266580;2.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品花寶鑒》成書于清中葉男風大盛的時期,狎優成為雅好龍陽者的時尚。在此背景下,作者陳森以士族公子梅子玉與男優杜琴言的同性戀情為中心,反映了京師的梨園生活和盛行于社會各階層的男風現象。在這一時期,雖然發軔于明末,盛行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有所衰落,但《品花寶鑒》的創作依舊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響。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一方面將《品花寶鑒》歸類為狹邪小說;另一方面也指出其未脫才子佳人模式之舊套。因為其中的“伶如佳人,客為才子,溫情軟語,累牘不休”依舊是才子佳人小說的思想內容。但魯迅也承認其中的“佳人非女”是“他書所未寫者”。這涉及到品花寶鑒以士優同性戀情為主體的思想內容。才子佳人模式限制了《品花寶鑒》對于同性戀情的現實描寫,但同性戀情在書寫的過程中也不斷地沖擊著才子佳人模式,形成了異化的才子佳人模式。以梅杜戀情為例,梅子玉與杜琴言的戀情從最初的品評色相、一見鐘情的才子佳人模式到最后發展為趨于友情雙方平等的知己之交,這一變化過程就展示了一種異化的才子佳人模式。
一、性別倒錯下的“才子佳人”
才子佳人小說在明末清初大量涌現,其最大特點就是具有明顯結構特征的固定模式。盡管這種被曹雪芹稱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的小說受到了歷代文人的批判,正統文人認為其“淫蕩人心,敗壞世道”,非正統文人則從小說藝術價值的角度對其進行批判,但它依舊在文壇上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繁榮趨勢。從明末清初到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模仿者紛起。盡管《品花寶鑒》是以清代士優之間的同性戀情為題材,但陳森在寫作《品花寶鑒》時也不可避免的陷入到才子佳人的小說模式中。
對于貫穿于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固定情節模式,許多人都對其做過闡述與界定。魯迅是最早對才子佳人小說進行系統研究的,他在對才子佳人小說進行了明確界定的基礎上,初步闡釋了才子佳人小說共同具備的情節特點,“至所敘述,則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為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范煙橋對此進行了更明確的界定,“大多以才子佳人為經,以功名利祿為緯,且往往‘否極泰來’,以快其意”。在此基礎上,郭昌鶴總結了才子佳人模式通備的五個特點“一、有一個真才子必生一個真佳人;二、姻緣是天注的,而結合的形式是不違禮教的真戀愛;三、初會多在后花園或廟宇中;四、好事多磨;五、結果是大團圓”。從歷屆學者對其的界定可以看出,固定的角色模式、戀情發展的千篇一律以及最后的大圓滿結局是才子佳人模式的三個主要特點。由于《品花寶鑒》中有一種奇異的性別倒錯,使得其中士優戀情的發展都體現了這三個特點,從而造就了《品花寶鑒》中的士優戀情與才子佳人模式的契合。
首先是名士與才子、優伶與佳人角色的完美契合。在士優的同性戀情中,士子群體作為戀情的一方,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才子,其中多數都家世顯貴,這符合一貫對才子的定義;而戀情的另一方優伶雖是男身,他們身上卻出現了一種性別倒錯現象,表現出更多的女性特質,相對于男性身份而言,他們在小說中的形象反而更加貼近才子佳人模式中的“佳人”形象。
從小說的描寫可以看出,《品花寶鑒》中處于被動一方的伶人都被刻意強化女性氣質,這具體體現在他們的容貌、姓名和氣質性格上。以梅杜戀情中的男優杜琴言為例,子玉第一次看到琴言時,他眼中的琴言是“以玉為骨,以月為魂,以花為情,以珠光寶氣為精神”,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女性化的審美描寫。作者不僅讓琴言在容顏儼若女子,在心理與思想上也賦予了琴言女性的特質。在小說第二十一回中,杜琴言因魏聘才惡意誹謗子玉而心神不安,在短短的半天里他的情緒幾度起伏,并且動不動就“滴下淚來”。據統計,這段并不長的情節敘述,杜琴言總計六次落淚。相對于男子身份而言,杜琴言的表現更符合中國古代對于女子“柔弱”“溫順”的要求。
在梅杜戀情中,杜琴言在性別倒錯下填補了“佳人”角色的空白,再加上梅子玉的才子身份,從而形成了才子佳人的角色模式,梅杜戀情也順勢陷入了才子佳人小說的慣常套路。梅子玉為才子,杜琴言為佳人,二人一見傾心,繼而徐子云以假琴言試探,證明梅子玉非“狹邪人”,二人始正式定交,情投意合。但此后便聚少離多,中又有小人誹謗,遭遇諸多煎熬。細究梅杜戀情的發展過程,其中所體現的依舊是一見鐘情、小人挑撥、好事多磨等才子佳人模式的典型特征。
在小說的最后,盡管梅子玉需要遵循傳統的倫理道德娶妻生子,但作者為其安排的妻子瓊花小姐的面貌卻又與杜琴言十分相似。琴言與瓊華小姐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組特殊的“鏡像”:
皇天可憐子玉一片苦心,因琴言是個男子,雖與子玉有些情分,究竟不能配偶,故將此模樣,又生個瓊華小姐出來,與琴言上妝時一樣,豈不是個奇事?
梅子玉娶面貌酷似琴言的瓊華小姐為妻,這也可以看做瓊華小姐代替琴言與子玉達成了傳統意義上的大團圓結局,從而完成了才子佳人模式上的最后一環。這一情節在另一位名士田春航和男優蘇惠芳之間也出現過,田春航在金榜題名后所娶的妻子蘇浣蘭不僅與蘇惠芳有“九分相似”,連姓氏都一樣。這種“鏡像”在本質上是小說中男旦們性別倒錯的隱喻,小姐們是男旦們身上女性特質的具現化。
在以梅杜戀情為中心的名士群體與男旦群體的戀情中,男旦們身上體現的性別倒錯貫穿于戀情發展的始終,引導著小說情節向才子佳人模式發展。這種奇異的性別倒錯并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作者陳森精心設定的,對此他甚至借小說中的人物之口直接發聲:
只有相公如時花卻非草木,如美玉不假鉛華,如皎月纖云,卻又可接可玩,如奇書名畫,卻又能羽而非言,如極精極美的玩好,卻又有千嬌百媚的變態出來。
從作者的敘述中可以看到,他試圖用一種唯美主義的論調調和男女性別的天然差異,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顛覆了傳統的倫理觀。但這種審美主義的論調,本質上依舊體現著男權中心主義的思想,是將男旦與美人和花草放在一起,用一種鑒賞的態度來進行品評和玩味。《品花寶鑒》中的“花”指的是在作者有意的性別倒錯下,如花一般美麗的名旦,而“品”則指的是名士們對男旦物化后的品評鑒賞。
在傳統的情愛結構中,只有女性處于被把玩鑒賞的地位,進而成為男性情欲寄存的對象。因此在士優交往的過程中,那些被迫承擔著女性角色的男旦,是被視為與女人并列的第二性,逃脫不了被窺視,被展示的命運。男旦們的男性身份被忽略,其所扮演的女性化角色被追捧,他們展示出的女性化魅力甚至成為了男男戀情中激發情欲的關鍵性要素。即使“風骨高絕”的梅子玉,初見琴言時的動心,也是由于其“驚艷絕倫”的女性化容顏。這種對于男旦身上女性特質的追求,展現著士子們在同性戀情中對于感官刺激下“欲”的追求。
二、不穩定的“佳人”角色與“愛情”的消失
《品花寶鑒》中的士優戀情雖然沒有脫離才子佳人的模式,但這其中也出現了一定的僭越。一方面,小說中的“佳人”角色并不是由男旦們的性別決定的,而是由其職業的特殊性及其低下的社會地位造成的,當男旦們的身份地位出現變化時,“佳人”的角色也就呈現出消解的狀態;另一方面,如果說才子佳人模式下的小說結局是“愛情的勝利”,那《品花寶鑒》的最后結局則表現的是愛情的消失,或者說愛情在潛移默化之間轉變為友情。
關于佳人角色的消解,可以梅杜戀情中的杜琴言身份變化為例。杜琴言的身份變化經歷了從常人到賤民,再從賤民到常人,最后從凡人到紳耆子弟的三重變化。
從常人到賤民的階段,指的是琴言因父母雙亡,被其嬸嬸賣入梨園,琴言從此由常人變為賤民,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在梨園從業時,琴言與梅子玉相戀。但在梅杜戀情的初始,琴言是被賣身的男旦,在性別關系和社會結構中都處于被支配的低下地位;而梅子玉則是出身官宦人家的名門子弟,且滿腹經綸,不僅在等級制度中占據上層地位,而且在性別關系結構中占有霸權地位,這就導致了在才子佳人模式下的梅杜戀情中,作為主動方的梅子玉占據了才子的角色,作為被動方的琴言被迫承擔起“佳人”的角色。從賤民到常人的轉變指的是徐子云為琴言贖身,琴言脫離梨園從而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和等級可變性。最后,琴言實現社會等級的提升,從常人到縉紳子弟的轉變則是通過扶乩認父的這一事件來實現的。怡園扶乩,上仙斷出琴言與屈道翁有前世的父女淵源,徐子云又進行說和,琴言拜屈道翁為義父,改名屈勤先。此事之后,琴言也成為官宦子弟。此時,杜琴言與梅子玉社會等級身份已基本相同,這使得梅杜二人在戀情中的角色模式也趨于平等,在這種情況下,琴言在梅杜戀情中所承擔的女性化的“佳人”角色也就轉變為更平等純摯的“知己”角色。
從杜琴言到屈勤先的變化過程反映的正是杜琴言社會等級地位的變化,這種變化導致了他在性別結構關系中的變化。杜琴言所承擔的“佳人”角色就在這種變化中逐步的消解了。
“佳人”角色在戀情中的不穩定性,體現出《品花寶鑒》對于才子佳人模式的僭越,除此之外,這種僭越還體現在對于士優戀情大圓滿結局的處理上。
在一般的才子佳人模式中,主人公們都會為愛情而奮力抗爭,最后達成“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圓滿結局。但以梅杜戀情為代表的士優戀情卻呈現出“愛情消失”的結局。當梅子玉考中翰林進入仕途徹底地融入正統的人生軌道,他與杜琴言之間的同性戀情就開始被逐漸地消解、淡化,這種同性戀情逐漸向著友情轉變。在杜琴言成為屈道翁的義子后,他又輾轉變成梅子玉的伴讀,子玉本人也有了品貌雙全的妻室。梅杜二人之間很明顯隱藏著愛情的種子,但當這種愛情受到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婚姻制度的制約時,它在潛移默化之中轉變為友情。
梅杜戀情的變化體現著作者貫穿于小說中的“主情克欲”的原則。“情”指的是符合封建倫理道德的情,當同性戀情與士人的道德追求相違背時,它便轉化為君子之交的知己之情。需要克制的“欲”,一方面指的是肉欲,另一方面指的是士人受男旦們女性化特質的吸引而衍生出的情欲。在梅杜戀情的初期,子玉還受到琴言容貌的吸引,用一種女性化的視角看待琴言,稱贊其溫順柔弱、貞潔自守的品質;但在梅杜戀情的后期,作者通過一次扶乩認父,使得琴言進入士族的行列,梅杜二人的關系由才子佳人的戀情變為君子之交的知己之情。在清代社會,縱欲思想蓬勃發展,男風的盛行對傳統的家庭倫理道德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品花寶鑒》中的梅杜戀情從摻雜有情欲因素的同性戀情發展為更為平等純潔的知己之情,實際上就是儒家“克己復禮”思想的體現,反映了作者思想中的儒學痕跡。
三、情與欲的沖突———作者矛盾的書寫狀態
在小說中,梅杜二人的相戀情節作為小說中的主線,具有串聯起其他名士與男旦們戀情的作用,集中體現了《品花寶鑒》士優戀情的特點。因此,對梅杜戀情進行分析,可以透析作者對于《品花寶鑒》中士優戀情的書寫心態。
從梅杜戀情展現的異化的才子佳人模式中可以看到,作者在書寫《品花寶鑒》的士優戀情時體現出一種矛盾的狀態,這種矛盾主要集中在“情”與“欲”的沖突上。作者對于“欲”的渴求,主要體現在小說花費大量筆墨來實現男旦們的性別倒錯,對于男旦女性化特質的大力刻畫與追捧。在將男旦轉換為“佳人”后,其女性化的容貌和溫順的特質使得人們獲得視覺上的感官刺激與男性霸權心理的滿足,進而成為投射情欲的載體。而作者所追求的“情”,在小說的第一回就可見一斑。他將縉紳子弟和名旦分為十種,皆是一個情字,最推崇的就是梅杜二人的“情中正”與“情中至”。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及:“《品花寶鑒》中的人物,大抵實有,就其姓名而言,推之可知。惟梅杜二人皆假設,字以‘玉’與‘言’,則‘寓言’之謂,蓋著者以為高絕,而已無人足供影射者矣。”這表明梅杜二人的戀情是作為一種寓言存在的,寄寓著作者理想化的同性戀情模式。這種理想化的同性戀情,作者在小說的最后將其轉化為一種符合禮教與倫理道德的“戀情”模式,細究這種戀情的本質,可以看到,比起戀情,作者所追求的這種情實際上更偏向于同性之間互相欣賞的知己之情,而作者在這種對于同性戀情的處理過程中無意間實現了對于才子佳人模式的僭越。一方面,作者追求符合禮教倫理的同性戀情;另一方面,作者又投注大量筆墨對于男旦的女性特質進行重復的描寫與細致的刻畫,暴露了其對于美色帶來的感官刺激的戀戀不舍,這兩者體現出作者矛盾的創作心態。
這種矛盾的創作心態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清代的狎優風氣和“主情”“重情”的文藝創作思潮都對作者的創作產生了影響。而作為主流的儒家文化對于男風的態度以及中國男風傳統所獨具的一些特點也影響了作者對于士優戀情的態度。
中國古代的男風傳統源遠流長,受時代的更替和地域的差異的影響,呈現出盛衰變化的跡象。在明清之際,中國古代的男風文化達到了頂峰。相對于前代而言,清代男風呈現出的最大的特點就是狎優風氣的盛行。此時的士人們多好歌童而不好名妓。咸同年間的士人黃均宰在《金壺遁墨》中曾描繪過這種景象:
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館者,眾皆訕之。結納雛伶,則揚揚得意,自鳴于人,以為某郎負盛名,乃獨厚我。
以描寫士優戀情為主要內容的《品花寶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清代狎優風氣的興起,需要從明末社會強調個性解放與肯定人欲的風潮中追溯其源流。在晚明時期,王陽明的心學興起,反對宋明理學對人性的戕害,強調人欲和個性解放。但當文化思潮過度強調人欲時,整個社會都彌漫著縱欲的氣息,人們道德觀念開放的同時,性愛觀也呈現出極其復雜的狀態,這種背景下男風應運興起。晚明男風的興盛一直延續到清末。同時由于明清二代禁止官吏狎妓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官宦們不得不在男性優僮身上尋找替代性出路。隨著清代戲曲的發展,大量伶人自乾隆時期開始匯聚京城。在當時的男風背景下,戲劇的興盛帶動了狎優文化的興起。男旦們所獨有的“兒女英雄一身兼”“名士傾城合一身”雌雄同體的性質受到了當時好男風人士的追捧。對此,梁紹壬有詩為證:“軟紅十丈春風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婉轉歌喉裊金縷,美男妝成如美女。”但在受追捧的同時,戲子由于自身卑賤的社會地位和職業的娛樂性質,也常常成為身份比自己高的觀眾的狎玩對象,甚至被以“倡優”待之。
士人們對于男風的追捧,展現的是一種恣意縱欲的心態。在狎優風氣盛行的男風背景下,男旦們由于其出眾的容貌與低賤的社會地位從而成為士子們情欲寄托的對象。而陳森在寫作《品花寶鑒》時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這一時代風氣的影響。
關于陳森的重情思想,小說的第一回就有具體的體現,“事不出于理之所無,人盡于情之所有”“先將搢紳中的子弟分作十種,皆是一個‘情’字”“再將梨園中名旦分作十種,也是一個‘情’字”。在小說的初始,作者便將“情”作為評判標準,而在小說的最后作者盡力擯除了梅杜戀情中的狎昵成分,使其變為“至純”“至正”的知己之情。陳森在小說中始終體現著對于“情”的探索與追求。這種創作思想一定程度上受當時“主情”“重情”的文藝創作思潮的影響。清初在詩文領域出現了性靈文學思潮。性靈派文學要求詩人在寫作詩歌時要具有“真性情”。這一理論在達到極盛之后,也影響了小說的創作,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提及《品花寶鑒》的思想內容深受《紅樓夢》的影響,而這一時期出現的峰巔之作《紅樓夢》,所秉持的正是“大旨言情”的創作主張。無論陳森所追求的“情”與性靈派文學所追求的“情”是否一致,他“重情”的理念貫徹于小說的始終,在小說中借梅杜戀情展現了自己理想中的同性戀情。
除了時代背景的影響外,作者矛盾的創作心態與還與中國古代男風的特點以及儒家主流文化對于男風的態度有極大關系。
施曄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中對中國古代男風的特點進行了概括,認為:
中國古代同性戀者之間存在著固定、鮮明的權力架構,年長、富有、權高者充當主動方,反之則為被動方,絕少角色互換的例子。中國的男風組合大多是異性戀組合的戲擬,是一種‘亞異性戀’,是男尊女卑現象在男人內部的復制,同性愛不過是異性愛的模仿,缺乏獨特性和自足性。
而陳森在處理士優戀情時,不自覺地將被極力強化了女性特質的男旦們作為士子們情欲寄托的對象,正是基于中國古代同性戀者之間存在的固定、鮮明的權力架構。在士優戀情中,士子們是霸權男性的代表,是主動方;男旦們則處于被動方的地位,是被雌化了的男性,性特權不僅存在于男性對女性中,還存在于霸權男性對被雌化的男性中。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士子們是將男旦們視為與女子無異的情欲寄托對象。
《品花寶鑒》以士優戀情為題材,一方面對“用情守禮的君子”與“潔身自好的優伶”之間的同性戀情極力描摹,表現出贊賞推崇的態度;另一方面,小說的結局卻又極力淡化同性戀情的痕跡,將士優戀情轉變為更符合傳統禮教的知己之情。這一矛盾的表現形式也與占據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密切相關。
儒家主流文化對男風一直持一種溫和的反對態度,這主要歸因于儒家文化中始終貫徹的中庸之道。子曰:“中庸之為德也,甚至已乎!民鮮久矣。”儒家的中庸之道具有包容、理性、穩健的特色,強調寬納包容、和而不同。施曄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中闡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對于中國古代男風的影響:
首先,儒家主流文化這種接近中立的溫和反對態度,為同性戀者創造了一個寬松的生存環境。同時,中國古代同性戀也以中庸之道行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摒棄完全逆轉的性取向,不排斥異性戀,在性生活中陰陽同體、雙性皆可。
儒家主流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男風溫和的態度,是陳森對于士優同性戀情推崇贊賞的思想基礎。但由于社會和宗族的壓力,絕對的同性戀在中國古代沒有生存空間。《品花寶鑒》中也只是將同性戀情作為夫妻敦倫、男女性愛的補充。因此,在小說最后,作者讓梅子玉、田春航等士人在功成名就后娶妻生子,男旦們也出了“旦黨”,以普通人的身份做起了生意,士優之間的同性戀情向純潔的友情轉變。一方面可以認為作者所追求的理想的同性戀情正是這種純潔無欲念的感情,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作者在小說中所安排的結局也體現著對現實倫理道德的妥協。儒家主流文化對于男風所持的溫和的反對態度極大地影響了陳森的創作觀。
《品花寶鑒》異化的才子佳人模式反映了陳森在小說書寫過程中的思想矛盾。他在《品花寶鑒》中力圖呈現一種用情守禮的同性戀情,但又不可避免的受清代男風文化中最典型的狎優風氣和女性化審美影響。在追求純摯的“情”的過程中,小說中的士優戀情呈現出一種雅正的君子之交,體現著儒家克己復禮的思想。然而,作者又難以割舍美色下“欲”的感官刺激,不斷強化小說中男伶們的女性特質,用一種奇妙的性別倒錯,消解男旦們的男性特質,將其轉化為可供士子們進行情欲投射的“第二性”。陳森的這種思想矛盾既受時代風氣的影響,也受根植于其思想中的儒家文化的影響。“透過情欲沖突的表層,異化的才子佳人模式中隱藏的是小說作者面對男色時既躲閃又渴望的矛盾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