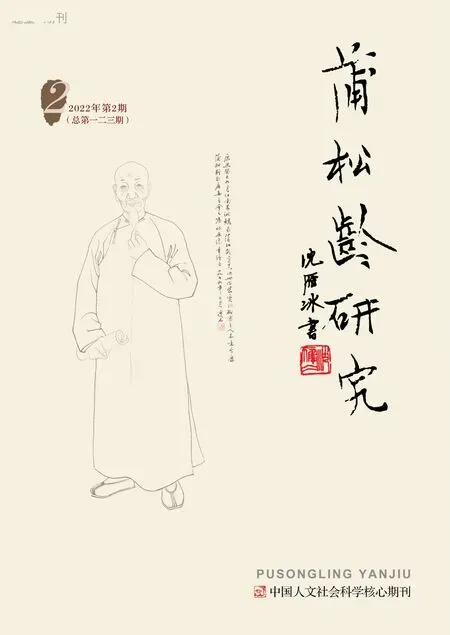《聊齋志異》在西班牙語世界的翻譯與傳播
李翠蓉 趙智利
(貴州財經大學 外語學院拉美研究中心,貴州 貴陽 550025)
一、《聊齋志異》的西譯版圖
根據羅一凡《創造中國怪異:Rafael de Rojas y Román首譯〈聊齋志異〉西班牙語譯本研究》一文,《聊齋志異》的首個西譯本為西班牙翻譯家Rafael de Rojas y Román 所譯《志異故事》(Cuentos extra?os,1941),距今,西譯史已達八十年。已有數十個譯本,包括改編畫冊、選譯本、節譯本;英語、法語、德語等歐洲語言轉譯本與漢語直譯本交互,西班牙語世界譯入與中國譯出并進。
(一)西班牙持續譯入
西班牙對《聊齋志異》的翻譯始于巴塞羅那,Rafael de Rojas y Román翻譯的插圖版《志異故事》包括10篇:《龍飛相公》《畫壁》《西湖主》《勞山道士》《書癡》《宦娘》《聶小倩》《汪士秀》《紅玉》以及《恒娘》,26幅插圖,由加泰羅尼亞20世紀最重要的插圖畫家Joan d’Ivori繪制。同年,也在巴塞羅那,佚名譯者翻譯彩色插圖西譯本《中國故事》(Cuentos chinos),選譯《宦娘》與《書癡》等5篇,這個版本1951年再版。
20世紀80年代共4個譯本:1個選譯與3個節譯,均在馬德里出版。選譯本為Isabel Cardona與博爾赫斯從英語轉譯的《報恩虎》(El invitado tigre,1985),共16篇,其中14篇選自《聊齋志異》;第一個節譯本是Carmen Salvador轉譯《羅剎海市》(Los fantasmas del mar,1982),選譯 4篇;第二個節譯本是Laura A.Rovetta與Laureano Ramírez從漢語直譯的《聊齋志異》(Cuentos de Liaozhai,1984);第三個節譯本是 Kim En-Ching 與 Ku Song-Keng 從漢語直譯的《聊齋志異:真正的中國經典故事》(Extra?os cuentos de Liao Chai:auténticos y clásicos cuentos chinos,1987)。
Rovetta為烏拉圭籍專業譯者,除母語西班牙文之外,還通曉中文、英文及法文,曾任職于墨西哥駐華使館,口、筆譯經驗豐富。Ramírez為西班牙著名漢學家,目前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翻譯學院任教,譯作豐富且皆為經典文本。他們合譯的《聊齋志異》遵循乾隆十六年的鑄雪齋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版;譯本的插畫則取自1866年的廣百宋齋版本;選譯105篇,附引言、腳注與三篇附錄:科舉制度、中央政府及地方的行政工作分配與中國傳統文學作品。2004年5月與10月重印兩次。
譯者將中國古典故事的發展(《聊齋志異》之前)分為四個階段:產生、童年、成熟與沒落。“產生”對應秦漢,寓言與傳說極為豐富,故事創作基于現實、寓言、傳說,融入想象,甚至夸張元素;“童年”對應東漢北魏六朝,故事創作范圍擴大,普通大眾以及非正統文人都融入其中,鬼魅、超自然事件也被納入其中;“成熟”對應唐朝,故事創作的文學含金量逐漸增加,唐傳奇篇幅增長,描述更加細化,結構更加縝密,語言更加精良;宋明時期對應“沒落”階段,因為話本對古典故事的沖擊,唐傳奇故事主題的無限重復,導致中國古典故事的衰退。譯者在此基礎上定位《聊齋志異》,認為它是“短篇故事”的扛鼎之作,原因有二:一是蒲松齡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描繪:封建主義最后階段的社會沖突與明清過渡階段的社會動蕩、變革。二是從蒲松齡個人的角度闡述,他作為一個社會個體,作品反映了他個人的生活狀態,他也通過文學來實現了宣泄與傾訴。
譯者清楚地交代翻譯策略以流暢易懂為原則,根據古孟玄在《〈聊齋志異〉西譯本與中西文化差異》中的論述,此譯本是從溝通的角度去翻譯,“西方文化在文字游戲、單位詞、神話、傳說、文化遺產等方面,和中華文化落差極大,《聊齋志異》譯者 Rovetta及 Ramírez靈活應用西語讀者的文化背景和習慣,搭起兩文化間的溝通平臺”。
20世紀90年代,西班牙有一個節譯本、一個選譯本。1992年,Imelda Huang Wang與Enrique P.Gatón從漢語直譯《一位愛藝者的神奇故事》(Historias fantásticas de un diletante),選譯 31 篇《聊齋志異》故事,在馬德里出版;德國著名傳教士漢學家衛禮賢著有《中國故事》(Chinesische M?rchen),1958年在慕尼黑出版。此譯本由Paz Ortega Montes轉譯為西語:《中國故事I——〈柳毅傳〉與其他中國神話傳說》(Cuentos chinos I.La princesa repudiada y otros relatos de la mitología china,1997)與《中國故事II——〈嬰寧或笑美人〉與其他中國民間故事與傳奇故事》(Cuentos chinos II.Yingning o la belleza sonriente y otros cuentos populares y fantásticos,1998),在巴塞羅那出版,共 100 個故事,選譯有《勞山道士》《種梨》《畫皮》《嬌娜》《小獵犬》《蟄龍》《白蓮教》等 15篇聊齋故事。這個譯本在西語世界影響頗大,在西班牙分集、合集、選集反復出版,2009年、2012年在巴塞羅那合集再版;2019年在馬德里分四集出版;2020年在馬德里節選再版。
2003 年,RolandoSánchez-Mejías從漢語直譯《中國神奇故事選集》(Antología del cuento chino maravilloso),選入部分《聊齋志異》故事,在巴塞羅那出版。2009年,Clara Alonso從英語轉譯《中國微型小說》,選譯41篇微型小說,以現代小說為主,但選譯3個古典篇目,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蒲松齡的《申氏》與干寶的《李寄斬蛇》,在馬德里出版。
(二)西班牙語美洲分散譯入
相對于西班牙的持續譯入,西班牙語美洲對《聊齋志異》的譯入則較為分散,體現在時間上的斷代與空間上的零零星星。從時間上來看,早在20世紀40年代,西語美洲便產生相關選譯本,但此后直到21世紀,才重新出現新的譯本;空間上則主要是阿根廷與墨西哥有相關譯入文本。
西班牙著名漢學家黃瑪賽(Marcela de Juan,1905-1981)是首位從漢語直譯中國古典文學的譯者,她的譯作豐富,譯風精準,在西語世界影響深遠。1948年,黃瑪賽譯《中國古代傳統故事》(Cuentos chinos de tradición antigua),在阿根廷出版,選譯宋元明清四個朝代共9個故事,《聊齋志異》最為突出,共4篇:《羅剎海市》《促織》《成仙》《嬌娜》。黃瑪賽簡述蒲松齡的生平、作品以及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與《聊齋志異》的重要地位,“《聊齋志異》毫無疑問是最被中國人珍視的書,也是認識、了解中國民俗習慣與生活方式的最佳向導”。
黃瑪賽的翻譯質量是值得信賴的,但她也闡述了自己認為翻譯過程中所丟失的一些元素:“顯然,它們(聊齋故事)風格迥異且語言類型豐富,古文,白話文,俗語甚至口語盡囊其中,遺憾的是,這些細節在翻譯的過程中已經遺失。”這個譯本頗受歡迎,首版是1948年3月31日出版,在同年的9月18日就又刊行了第二版,相隔時間還不到半年。而黃瑪賽對《聊齋志異》的偏愛也在后續的譯作中得到沿承,比如,1954年黃瑪賽再譯《〈古鏡記〉與其他中國故事》(El espejo antiguo y otros cuentos chinos),共 8個故事,再次選譯《促織》《嬌娜》與《羅剎海市》三篇。
《中國古代傳統故事》后,西語美洲對《聊齋志異》的譯入開始斷代,直到21世紀,才又出現新的譯本。墨西哥學院的亞非研究中心成立于上個世紀60年代,是西語美洲成立時間最早、研究成果最多、學術水準最高的有關中國的研究中心。他們的西班牙語學術期刊《亞非研究》(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1966年1月始發,至今,已不間斷發行近200期。期刊的主要板塊為書評、論文與譯作。《亞非研究》2012年第1期載《嬌娜》(Jiao Na)西語譯文,Radina Dimitrova與Pan Lien-Tan從漢語直譯。2014年第2期兩位譯者再譯三篇:《瑞云》(Ruiyun)、《書癡》(El lector obsesionado)與《丑狐》(La zorra fea)。
關于《聊齋志異》最為新近的一個節譯本在阿根廷出版。2014年,Julio Miranda譯《中國魔幻故事》(Cuentos mágicos chinos),共 18篇,全部選自《聊齋志異》,如《洞庭主》《瑞云》《勞山道士》《書癡》《恒娘》《林四娘》與《紅玉》等,此譯本無前言,無注釋,無附錄,也未點名蒲松齡與《聊齋志異》這兩個關鍵詞,大概是譯者希望讀者更多地從文學欣賞的角度去看待這部故事集。
(三)中國集中譯出
中國對《聊齋志異》的譯出呈現“集中”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出版社集中,主要是外文出版社與朝華出版社;二是均從屬于某一些出版系列。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就注重向世界表達自我,開啟主動譯出的歷程,早期的譯介以文學作品改編為主,連環畫、兒童畫冊最為常見,民間故事與經典文學作品是改編的重要對象。從西班牙語譯本來觀照,《西游記》畫冊最多,《聊齋志異》次之。20世紀80年代,外文出版社與朝華出版社發行西語版彩圖畫冊共8本:《仙人島》《白練秋》《紅玉》《勞山道士》《阿寶》《促織》《蓮花公主》《嬰寧》。裝幀精良、繪圖優美、故事簡潔。畫冊署名編者、繪畫者、裝幀設計者,但并無譯者,這在一定程度上無法保障翻譯質量,翻譯水平且不談,拼寫錯誤就常見,比如,在《嬰寧》的封里,“Extran os Cuentos de Liaozhai”中的“Extran?os”就拼寫錯誤。
《大中華文庫》致力于系統、準確地將中華民族的文化經典譯成外文,編輯出版,介紹給全世界,1994年開啟,選擇110種圖書,是一項國家層面推動的大型系統出版工程。得到季羨林、任繼愈、葉水夫、袁行霈、丁往道、韓素音等多位學者和翻譯家的支持與指導,已有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等18家出版社參與該項目圖書的編輯與出版工作。《大中華文庫》涉及兩種類型的翻譯,一種是語內翻譯,即將古代漢語翻譯成現代漢語;另一種是語際翻譯,即將漢語翻譯為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俄語、阿拉伯語、日語和朝鮮語共8種外語。其中,漢語——西班牙語對照本的出版計劃分三批,共25冊,《聊齋志異》屬于第二批。
2014年,《大中華文庫》系列的西語版《聊齋志異選》(Selecciones de Extra? os Cuentos del Estudio Liaozhai),外文出版社發行,譯者為古巴翻譯家María Teresa Ortega與Olga Marta Pérez,采用張友鶴輯校本,共選譯216個故事,漢西對照,分四冊,近2000頁。前言稱“《聊齋志異》成為一部馳想幻域而映射人間、諷喻現實、表現世情的‘孤憤之書’”。并將這些故事大致分為兩類:“這些多姿多彩的奇幻表意之作,又可大致分為兩類:美情小說與諷喻小說。前者歌贊人性的善、人情的美,特別是愛情之美;后者針砭社會的丑,世態的惡,特別是官場的丑和惡。”
二、《聊齋志異》的西譯風格
在橫向地大致勾勒《聊齋志異》的西譯版圖之后,縱深地通過對比譯本來觀照譯風。《嬌娜》是各個譯本選譯較多的篇目,以此為例。袁行霈《中國文學史》認為《嬌娜》帶有對兩性關系的思索性內涵,“玩味小說情節和夫子自道,可以認為作者是用了并不確當的語言,表達了他感覺到的一個人生問題:得到‘艷妻’不算美滿,更重要的是‘膩友’般的心靈、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滿應是兩者的統一”。袁行霈認為蒲松齡在《嬌娜》中描述了理想的男女關系,或者是男人對女人的完美幻想:“艷妻”與“膩友”統一,但他點到即止,并未深入探討。
在《〈聊齋志異·嬌娜〉中的第四種關系》中,葉潤青立足文本分析,體悟作者意圖,定位孔生與嬌娜之間是第四種關系,即“膩友”關系,他認為,在兩性關系的范疇中,文學中的描繪不外乎三種主要類型:純潔至真的友情、靈肉結合的愛情和血肉相連的親情。“這種關系可以說是前三種關系的交叉、臨界和邊緣,既復雜又純粹。而維系第四種關系的重心是兩人之間心心相照的‘知契’感應。因此這種情愫的微妙、多義和潛在的力量賦予了其獨特的美學內涵與永恒的審美價值”。
其實,《嬌娜》中關于兩性關系的總述主要體現在最后的“異史氏曰”:“余于孔生,不羨其得艷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饑,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神與’,尤勝于‘顛倒衣裳’矣。”我們比較三個漢語直譯本對此段的翻譯:
Rovetta譯本(2004):
En lo que a mí respecta,admiro más a la maravillosa amiga de Kong que a su bella mujer.Dicen que a uno se le quitaba el hambre nada más verla y que oír su voz era una bendición para los oídos.No me cabe duda de que charlar y comer en compa ía de una amiga así,sintiéndose compenetrado en todo,supone un placer mucho mayor que el mantener con ella unas simples relaciones carnales!
Dimitrova譯本(2012):
No envidio a Kong Xueli por tener una bella esposa,sino por encontrar una cordial amiga.Al ver la cara de un amigo,uno se olvida del hambre;al escuchar su voz,la sonrisa sale sola en el rostro.Al tener un amigo tan próximo con quien de vez en cuando conversar o comer juntos,el espíritu se regocija frente a la faz querida!Y aquellos líos que acaban con la ropa de ambos en desorden ni de lejos se pueden comparar con la verdadera amistad.
Ortega譯本(2014):
Lo que admiro del erudito Kong no es que se casara con una mujer bella,sino que también tuviera un buen amigo cuyo rostro pudiera hacerle olvidar el hambre y cuya voz le trajera dicha y deleite.Tener un buen amigo como ése con quien hablar y comer y beber significa un flujo y una fusión en la esfera espiritual.Una amistad tal supera al amor entre esposo y esposa.
首先,觀照“得艷妻”與“得膩友”兩者之間的關系。雖然從表面看兩者是“非此即彼”的并列關系,但根據后文的“色授”可知,“膩友”是在“艷妻”的基礎上增進了“魂與”,即“膩友”首先也是美麗的,其次還是能夠成為知己,類似于現代的“紅顏知己”,首先要保證顏值。所以,從內涵上講兩者是遞進的。觀照三個譯本的翻譯:Rovetta譯本譯作遞進關系,相比艷妻,更加“傾慕”膩友,遞進關系恰當,但直接“傾慕”,而不是羨慕孔生“得”,意義的準確度上有所欠缺;Dimitrova譯本與原文亦步亦趨,用的是“不是……而是……”的并列關系;Ortega譯本用了強調的并列關系:“我羨慕孔生的不是……,而是……。”
其次,我們觀照“膩友”的翻譯,“膩友”在文中是有具體指射的,即嬌娜,即使將孔生與嬌娜的關系抽象出來,也是獨特的男女關系,在西語中仍然應該用女性朋友“amiga”,Rovetta譯本在整段中均用“amiga”,翻譯貼切;Dimitrova譯本在“而羨其得膩友也”采用“amiga”,但后文所有關于“膩友”的指射都抽象為“朋友”(amigo),突出友情,忽略男女之間的特殊關系;Ortega更是從頭至尾都用“朋友”(amigo),將“第四種關系”狹隘地解讀為友情。
三、《聊齋志異》在西語世界的傳播緣由
由上可知,《聊齋志異》西譯本眾多,蒲松齡在西語世界也頗有影響。2001年,José Manuel Pedrosa Bartolomé作《口述與書寫——亞瑟王傳奇與蒲松齡對博爾赫斯與胡安·戈伊蒂索羅的影響與交匯》(Oralidad y escritura:Influencias y convergencias〈de la literatura artúrica y Pu Songling a Borges y a Juan Goytisolo〉),論述“口述”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但以西方的文論、作家為主,涉及蒲松齡之處,僅短短三段。引用《聊齋自志》:“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借此分析《聊齋志異》的“口述”源頭,但并未將蒲松齡和兩位作家聯系起來,所以,更多地是借作一個噱頭,但也能側面揭示蒲松齡與《聊齋志異》在西班牙語世界的名氣。
博爾赫斯在《報恩虎》(1985)西譯本的前言指出:“《聊齋志異》在中國的地位就等同于《一千零一夜》在西方的地位。”這個比較看似無意,其實道明了《聊齋志異》在西語世界廣泛傳播的兩個原因:一是靈活的短篇形式;二是無窮想象力。短篇故事是西方文學的重要形式之一,西班牙語文學也不例外,古有《盧卡諾爾伯爵》,與蒲松齡時代接近的有Juan Pérez de Montalbán,Chen Xinyi在《中國文學與西班牙文學的比較研究:17世紀的胡安·佩雷斯·德·蒙塔爾班與蒲松齡的短篇故事》(Estudio Comparativo entre la literatura espa?ola y la china:relatos cortos del siglo XVII de Juan Pérez de Montalbán y Pu Songling)中將兩者作比,但研究并不深入也不具體,不過作者在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博士論文是涉獵這兩個作家的比較研究,有待以后深入梳理。西班牙語美洲近現代文學的短篇故事佳作更是數不勝數:Juan Rulfo《烈火平原》、Horacio Quiroga《愛情、瘋狂和死亡的故事》、Juan José Arlt《寓言集》等,西語讀者對短篇故事的接受度高。從翻譯實踐來看,短篇故事靈活,易于選擇,從上述譯入譯出的作品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到,《聊齋志異》各類西譯本從一個、幾個、十幾個再到百來個、兩百余個的選譯都具有可操作性。
《聊齋志異》承志怪與傳奇,袁行霈論道:“《聊齋志異》……就文體來說,其中有簡約記述奇聞異事如同六朝志怪小說的短章,也有故事委婉、記述曲微如同唐人傳奇的篇章。……《聊齋志異》里絕大部分篇章敘寫的是神仙狐鬼精魅故事,有的是人入幻境幻域,有的是異類化入人間,也有人、物互變的內容,具有超現實的虛幻性、奇異性,即便是寫現實生活的篇章,如《張誠》《田七郎》《王桂庵》等,也往往添加些虛幻之筆,在現實人生的圖畫中涂抹上奇異的色彩。”[
《聊齋志異》的無窮想象力是它在西語世界受到青睞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僅從書名的翻譯便可見一二,有一些譯本會刪減“聊齋”,或者直接用音譯,但“異”字從來都是譯者刻意突顯的重要因素:黃瑪賽用了“extra?o”;Imelda Huang Wang 用了“fantástico”;Rolando Sánchez-Mejías 用了“maravilloso”;Julio Miranda用了“mágicos”,均突出了《聊齋志異》的無垠想象力。
不光是題目,在各個譯本的前言中,也不無突出作品想象力的。《聊齋志異選》就在前言中厘清了關于女性人物塑造的無窮想象力:“蒲松齡筆下的狐女形象甚多,嬰寧、青鳳、嬌娜、小翠、蓮香、青梅、鳳仙、紅玉……,鬼女(連瑣、宦娘、晚霞、小謝、巧娘、聶小倩、伍秋月、公孫九娘、辛十四娘)、花女(葛巾、香玉、黃英、荷花三娘子)、仙女(嫦娥、翩翩、蕙芳、蕓蘿公主)、鳥女(竹青、阿英)、蜂女(綠衣女)、龍女(織成)、蛙女(十娘)、鼠女(阿纖)、獐女(花姑子)、揚子鱷女(西湖主)、白鰭豚女(白秋練)……”
其實,想象力豐富只是表層,內里是幻象、幻境的敘述方式,不少評論都認為蒲松齡營造的世界,幻象與真實界限淡化,兩者交叉互融。Rovetta就認為,“當他給我們講述怪物或狐女時,并不將其作為一種文學手段,而是真實地相信它們的存在”。其實,對于這種用“平常口吻”敘述“奇像”的獨特敘事方式,并非蒲松齡獨有。善于講故事的拉美作家也深諳此道,比如墨西哥作家Juan Rulfo在《佩德羅·巴拉莫》中用平靜的口吻講述鬼魂故事,又比如1982年諾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他在驚世之作《百年孤獨》中,用尋常的口吻講述人物飛升空中、持續四年的雨季、豬尾巴嬰兒等一系列奇怪的故事,這與《聊齋志異》敘事口吻相映成趣。
除了短篇形式與無限想象力,《聊齋志異》在西語世界受到青睞的第三個原因則是它對彼時“中國現實”的呈現與批判。從文學作品中去“見中國之像”一直都是西方讀者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尤其是離我們遙遠的古代社會現實,中國古典文學為此提供了合適的窗口。蒲松齡收集民間故事,在此基礎上創作《聊齋志異》,所以它經歷過采集民間聲音的過程,使得它對現實的反映增加了不少“可信度”。也是因此,《聊齋志異》中人物眾多,有訪仙道士,奇異鬼魅,嚴肅公務員,可怖惡魔,佛家和尚與花妖狐女等,蒲松齡以不同層次、不同生活圈的人之口、非人之口,以及他們的生活經歷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主要描繪兩種“社會之像”:一是他自身的感悟與體會;二是對社會的觀察與深入。大部分篇章的故事與書生、文人的生活境遇休戚相關,“聯系作者蒲松齡一生的境遇和他言志抒情的詩篇,則不難感知他筆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由他個人的生活感受生發出來,凝聚著他大半生的苦樂,表現著他對社會人生的思考和憧憬。就這一點來說,蒲松齡作《聊齋志異》,像他作詩填詞一樣是言志抒情的”。但是,蒲松齡寫自己,但并不局限于自己,“在那個時代,官貪吏虐,鄉紳為富不仁,壓榨、欺凌百姓,是普遍的現象。位賤家貧的蒲松齡,有一副關心世道、關懷民苦的熱心腸,又秉性伉直,勇于仗義執言。抒發公憤,刺貪刺虐,也成為《聊齋志異》的一大主題”。
Rovetta也認為,蒲松齡的文學創作價值就在于他的批判精神。秘魯著名漢學家吉葉墨(Guillermo Da?ino,1929-)在西班牙語版的《中國文化百科》中如此解釋《聊齋志異》的現實指射:“這部作品也是對當時某些社會現實的一種揭露與批判:賄賂、專政、科舉的不公正、官員的腐敗、地主階層的專橫。每一個故事的夫子自道也揭示了這種批判與控訴意圖,他同農民共同生活過多年,他自己也曾艱難度日,所以深知那個時代的各種不公,所以他的很多故事都描述了統治階級對民眾的剝削。”Chen Xinyi在《中國文學與西班牙文學的比較研究》中具化了三個批判對象:一是官員;二是科舉制度;三是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道德體系。總之,《聊齋志異》以其靈活的短篇形式、無限的想象元素以及深刻的批判精神,受到西班牙語世界譯者、讀者的青睞與喜愛,傳播深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