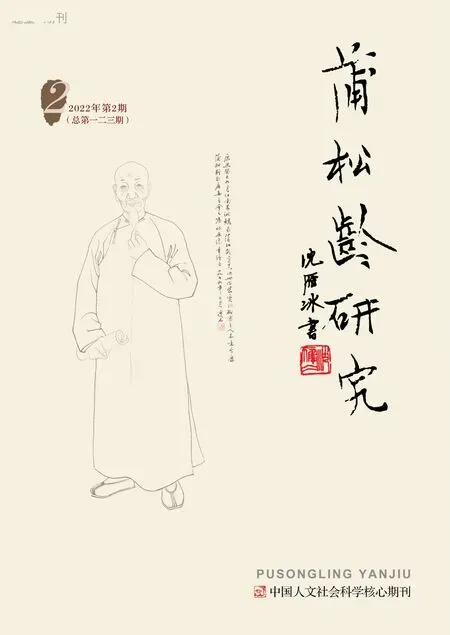對《聊齋志異·席方平》的重讀及其創作啟示的探討
陳國學
(云南民族大學 文學與傳媒學院,云南 昆明 650031)
《席方平》作為《聊齋志異》中的名篇,過去往往被當作揭露封建社會黑暗的標桿,這固然沒錯,但筆者在反復閱讀該文和教學過程中,對這篇杰作有了很多的思考。在此文中,我就想根據這些思考,從人物形象及思想淵源、題材來源、文體淵源等角度對它進行更深入地審視,并探討由此產生的有關創作啟示的問題。
一、《席方平》的人物形象及思想淵源
《席方平》描寫的是席方平出生入死、死而復生、生而又死地去為父親鳴冤昭雪的故事,作者在文后總結席方平是“……死而又死,生而復生……忠孝志定,萬劫不移”。這一曲折經歷和作者的定論首先讓我們想到的是《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以及湯顯祖給她的定性:“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而席方平顯然也可以說是個至情之人,只不過,這種至情不是男女之情,而是兒子對父親的感情。為此,我們需要明白,至情之情如何從男女之情擴展到了父子之情。在這一點上,我們很容易就能想到馮夢龍在《情史》序言中所寫的《情偈》:“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虛假。有情疏者親,無情親者疏。無情與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種種相,俱作如是觀。”蒲松齡有沒有受到馮夢龍這段話的影響我們不知道,但他所寫的《席方平》可以說就是在為《情史》所倡導的的“情教”觀中“子有情于父”這一說法在做形象的演繹。
晚明人馮夢龍看到了湯顯祖“至情說”的巨大意義,但可能覺得他的至情有點狹隘,于是把這種情擴大到人類的一切感情,主張用這種包容一切的情教來教化百姓。在此,我們不論其局限性,而應該看到它對“至情說”的挽救。應該說,蒲松齡塑造席方平形象時,受到了湯顯祖“至情說”與馮夢龍“情教說”兩方面的影響,方有那個下地上天為父申冤的錚錚鐵漢席方平的形象。
臨淄蔡支者,為縣吏。曾奉書謁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見如城郭,遂入致書。見一官,儀衛甚嚴,具如太守。乃盛設酒肴,畢付一書。謂曰:“掾為我致此書與外孫也。”吏答曰:“明府外孫為誰?”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孫天帝也。”吏方驚,乃知所至非人間耳。掾出門,乘馬所之。有頃,忽達天帝座太微宮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書訖,帝命坐,賜酒食。仍勞問之曰:“掾家屬幾人。”對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經幾年矣?”吏曰:“三年。”帝曰:“君欲見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戶曹尚書,敕司命輟蔡支婦籍于生錄中,遂命與支相隨而去。乃蘇歸家,因發妻冢,視其形骸,果有生驗,須臾起坐,語遂如舊。
蔡支開始來到的地方顯然是泰山府君(即文中的“太山神”)之所在,府君讓他帶一封信給天帝,結果他乘著馬就到了天帝之所在,顯然是泰山府君的神力所致。這里并沒有人間、死后世界及后來所謂上界之間的劃分。《席方平》中作為凡人的卻能穿越三界的構思與此極為類似,如果是這樣,那說明蒲松齡的思路沒有被明清時期已定型的人間、地府、天界這三界的劃分所限制,而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和不拘一格的汲取能力。
二、《席方平》的題材來源
《席方平》的整個結構框架表明其題材來源于傳統的“入冥——復活”類型的故事,這一點筆者在《“舊瓶裝新酒”:〈聊齋志異〉對傳統冥游題材小說的繼承與創新》一文中已有解說,在此簡單概括一下。席方平冥游地府,不是因為鬼差的勾招,而是出于為父申冤的自由意志,而他也因此經受了地獄的種種酷刑,最后到達天帝處告狀,天帝殿下九王子命二郎神審理此案,將地府各級官員及為富不仁的仇家羊某一網打盡,然后席方平蘇醒過來。顯然,作者借用了傳統的“入冥——復活”題材,卻不是簡單地為佛教的地獄思想做傳聲筒,因為地獄里原來用以懲罰惡人、壞人的種種酷刑現在卻被用來對付良善之輩,所以本文是在影射人間官府的官官相衛、只認錢財、貪酷無比。
《席方平》一文中還雜糅了離魂、投胎轉世等傳統題材,這是顯而易見的。而它對于封建社會黑暗的揭示之深,令人嘆為觀止。這讓我們想到,借用精怪鬼神、宗教題材竟也可以寫出如此杰出的有思想深度的文章。
三、《席方平》的中的判案文:公案文體與斷案文的杰作
《席方平》又可以看作一篇公案小說,要說它表達了封建社會底層人民對于所謂清官的期盼也是可以的,其中的二郎神顯然類似于公案戲中常見的包公形象。不過這里筆者更想賞析其中那篇犀利無比的斷案文,如其中諷刺冥王的“繁纓棨戟,徒夸品秩之尊;羊狠狼貪,竟玷人臣之節”,可謂將貪官的面目揭示得無比形象。二郎神判決詞中對他的懲罰則是“當掬西江之水,為爾湔腸;即燒東壁之床,請君入甕”,簡直大快人心。接下來譴責城隍、郡司官員收受賄賂后“上下其鷹鷙之手,既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獪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贓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對于為虎作倀的下層差役,則批判其“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最后,對以金錢買通官府的羊某,也不忘指責他“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這里其實更多地還是隱含著對官府黑暗的揭露。通觀這篇斷案文,可以說表現了蒲松齡高度的文言文修養,其對現實社會犀利尖銳的揭露以及對用典、對偶、比喻等等修辭手法的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這樣的作者卻一輩子考不上科舉,真正是冤哉枉哉!
由此想到作為“文備眾體”的小說的文體淵源。在小說中雜入公文,自然不始自《聊齋志異》。在《金瓶梅詞話》第48回即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彈劾山東提刑所正副千戶夏壽、西門慶的奏折,文中說正千戶夏壽:“葺茸之材,貪鄙之行,久于物議,有玷班行……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群下有木偶之誚。”又批判西門慶“本系市井棍徒,夤緣升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為之不清;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為掩飾,而贓跡顯著”。之后總批二人“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這篇奏折就很類似《席方平》一文中的斷案文。《醒世姻緣傳》第13回則正式出現了斷案文,該回在描寫東昌府理刑褚推官對晁源的妾施珍哥誹謗正妻計氏與和尚通奸、致使計氏上吊自盡一案后,發布斷案文,文中說施珍哥:“惑主工于九尾,殺人毒于兩頭。倚新間舊,蛾眉翻妒于入宮;欲賤凌尊,狡計反行以逐室。乘計氏無自防之智,窺晁源有可炫之昏,鹿馬得以混陳,強師姑為男道;雌雄可從互指,捏婆塞為優夷。桑濮之穢德以加主母,帷簿之丑行以激夫君。劍鋒自斂,片舌利于干將;拘票深藏,柔曼捷于急腳。若不誅心而論,周伯仁之死無由;第惟據跡以觀,吳伯之奸有辨。合律文威逼之條,絞無所枉;抵匹婦含冤之縊,死有余辜。”說晁源“升斗之器易盈,轆軸之心輒變。盟山誓海,夷鳳鳴于脫屣之輕;折柳攀花,埒烏合于挾山之重。因野鶩而逐家雞,植繁花而推蒯草。奪寵先為棄置,聽讒又欲休離。以致計氏涉淇之枉不可居,覆水之慚何以受?無聊自盡,雖妾之由;為從加功,擬徒匪枉”。后文還批判差役伍圣道、邵強仁“鼠共貓眠,擒縱惟憑指使;狽因狼突,金錢悉任箕攢。二百兩自認無虛,五年徒薄從寬擬”。就更加類似于《席方平》一文了。
由上引文可知,明代小說中引入公文甚至更具體的判案文已經是并不罕見的情況,蒲松齡先生應該是對此非常了解,才在《席方平》一文中創作了一篇絕佳的斷案文,顯示了他高超的文言造詣。該文的雜入雖不無炫才的特點,但簡潔地顯示了二郎神對冥府各級官吏及行使賄賂以報私仇的羊某的一網打盡,有大快人心的效果,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四、結語
以上從人物形象及思想淵源、題材來源、文體淵源等角度探討了《席方平》可能的靈感來源,探討顯示出該篇是有著多處的源頭的:其思想淵源是明代中后期從湯顯祖到馮夢龍的的主情思潮;題材淵源則是《太平廣記》中大量存在的佛教的“入冥——復活”小說;文體淵源還與公案小說中雜入的判案公文有關。而蒲松齡先生對這些源頭進行了富有創造性的融會貫通,表現出杰出的鍛造本領。其創作啟示至少有二:其一,利用宗教題材卻不拘于宗教宣教意識的創作宗旨,這表明,宗教題材是可以用來表現非宗教內容的,而且可以表現得相當成功。其二,突破固有觀念的想象力,正是這一點,使作者突破了宗教題材的限制,例如席方平可以自由地擺脫肉體的束縛,魂靈自主地來到陰曹地府為父申冤。而以往的入冥題材中,入冥者一般都是被陰間使者(即所謂黑白無常)帶入地府的,席方平投胎為嬰兒后,三天不吃奶氣絕身亡,死后靈魂再次獲得自由,在去尋找灌口二郎神的路上遇到天帝殿下九王子,告狀成功。這里沒有明確地講席方平的靈魂是到了天上,但按固有觀念應該是來到了天界,而一般而言,凡人的靈魂是難以到達天界的。所以說,文中的席方平是自由出入三界,才得以表現他為父申冤的堅定意志,這是蒲松齡追求法制公正思想的表現,但是呈現為突破三界不可隨意穿越的固有觀念的自由意志。偉大作家利用宗教又突破宗教觀念,簡直達到了“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地步,令人贊嘆不已。而這顯然是充沛的創造力的體現,可謂“元氣淋漓,真宰上訴”。
當然,《席方平》一文本身還是首重對儒家思想中孝道的表達,結尾處壞人被一網打盡、好人獲得好報仍然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傳統觀念。可見什么時候需要遵守傳統,什么時候需要突破固有觀念,在偉大作家那里是有衡量的。也許可以說,在道德觀念上遵循中華民族的基本思想、不作隨意大膽的逾越,而在想象力上盡可以天馬行空,是《席方平》一文給我們的總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