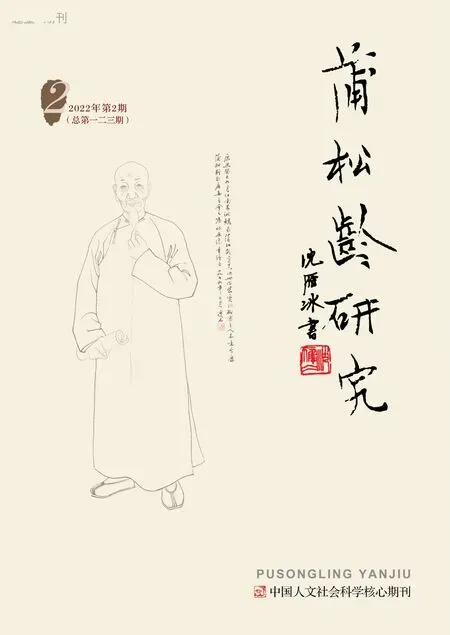《聊齋志異》中的重商意識及其深層意蘊探析
楊士欽
(淄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人文學院,山東 淄博 255130)
《聊齋志異》作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的最高峰,其成就遠遠超越了其前的諸志怪傳奇及其后的諸仿作,正如馮鎮巒所說:“是書傳后,效顰者紛如牛毛,真不自分量矣。”從中可以看出后人對《聊齋志異》的推崇!《聊齋志異》之所以會取得如許高的地位,固然源于其“化工賦物,人格面目”的高超藝術成就,也得益于其思想方面的諸多真知灼見,重商意識即是其重要思想之一。
一、《聊齋志異》重商意識之表現
(一)對商業的重視
在《聊齋志異》490多篇小說中,涉商題材或有商人出現的小說有近80篇,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在蒲松齡的筆下,商人的數量多門類廣涉及到眾多的商業領域,既有行商又有坐賈。前者像《夜叉國》中泛海為賈的交州徐姓,《羅剎海市》中“浮海為生”的馬駿,《任秀》中販賣氈裘的商人仁建之,《黃英》中販菊的商人陶生等;后者像《王通》篇中開典當鋪的王通,《小二》中開琉璃鋪的小二,《阿秀》中開雜貨鋪的阿繡,《鴉頭》中開酒肆的王文。所營行業更是遍及當時社會中的各行各業,有梨商(《種梨》)、胡餅商(《二商》)、糧商(《阿纖》)、布商(《布客》)、面商(《蕙芳》)、雜貨商(《阿秀》)、氈裘商(《任秀》)、花商(《黃英》)、琉璃商(《小二》)、帛商(《恒娘》)、行旅商(《王成》)、雜負販商(《金和尚》)、鹽商(《王十》)及典商(《王通》)等。在一部“以傳奇而志怪”的文言短篇小說中,出現如此多與商人有關的小說,這絕對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
更難能可貴的是,不同于時人對商業的輕視,蒲松齡重視商業,在其創作的小說中多次為商業和商人鼓而呼。這典型地體現在《細柳》《黃英》與《賭符》諸篇中。在《細柳》篇中,當次子高怙“游閑憚于作苦”時,細柳則以“四民各有本業”來規誡他,可見在細柳看來士農工商都是“本”業,即都是正業,很顯然此處蒲翁是借細柳之口表達自己對商業的肯定。對商業和商人的肯定更明顯地體現在《黃英》篇中,當陶生以馬子才“固不豐,仆日以口腹累知交”,準備賣菊為生時,馬子才則以“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矣”相譏,而陶生的回答卻是“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茍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可謂振聾發聵!寥寥幾句話就寫出了從商的正當性。可見,在蒲松齡看來通過正當的商業經營來獲取財富沒有任何可以指責的,這和農業生產勞動沒甚兩樣。
在某種意義上蒲松齡對商業的重視甚至還超越了農業生產,這典型地體現在《賭符》篇中,針對賭博的危害,蒲松齡在文末異史氏曰中發表了一大段議論,其中有這樣幾句:“夫商農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在這里蒲松齡在談到人的寄生本業時,不同于一般人口中常說的“農商”而改為“商農”,把商業排在農業之前,更可看出其對商業的極端重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聊齋志異》中商業題材篇章的數量之大,還是蒲松齡對商業與商人的高度評價都體現了其濃厚的重商意識。
(二)獨特商人群體的塑造
在《聊齋志異》中有兩個獨特的商人群體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即儒商群體和女性商人群體。
首先看第一類儒商群體。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由于統治階級采取的是“重本抑末”的經濟政策。由此衍生了“士農工商”四大職業,所謂“士農工商”,《漢書·食貨志》曾做出過解釋:“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士”無疑居于四民之首。正所謂“學而優則仕”,讀書的終極目的毫無疑問是“出仕”。而在《聊齋志異》中卻出現了一類獨特的現象,就是“去儒而賈”,這些商人本來都是讀書人卻由于種種原因最終走上了經商的道路。或出于父命,像《白秋練》中的慕蟾宮,因為“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成為了商人,再如《羅剎海市》中的馬駿因為父親的“數卷書,饑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最終走上了從商之路。有的則因為有外界其他力量的推動,像《劉夫人》中的廉生,“少篤學”,后來遇到鬼婦劉夫人,勸其從商,并以“讀書之計,先于謀生”,對其進行開導,最終使其成為一代巨賈。
如果說前兩類儒士成為商人都是由于外力的推動,那第三類儒商則完全是出于自身的覺悟,最杰出的代表當屬《雷曹》中的樂云鶴。樂云鶴因“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受到啟發,認為“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遂看破了科舉,棄儒從商。
另一類則是女性商人形象的塑造。在《聊齋志異》中還塑造了一類女性商人形象,這在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她們或頗有經商才能或宅心仁厚富有遠見。前者如《黃英》篇中的黃英,在陶生不在家時,獨自在家“課仆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其不但沒有廢棄家中的花商事業,反而更勝前昔,可見其過人的經商才能。后者的代表為《小二》篇中的小二。其先和丈夫避居于山陰里,結果因“里人共嫉之,群首于官,以為鴻儒余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女認為:“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于益都之西鄙。”從而使家中避免了禍殃可見其識見之先。后來在益都經營琉璃廠,作者對其描寫到“女為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于男子”。同樣也體現了其非同一般的經商才能。在其經濟實力強大即“財益稱雄”之后,其沒有只顧自己的小家而是主動出資幫助村人共同致富。即“村中二百余家,凡貧者俱量給資本,鄉以此無游惰。”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幫助家庭脫離困厄,真可謂巾幗不讓須眉。這些女性商人形象,很好地詮釋了女子在商業上的獨特才能,為中國古代的小說畫廊增添了一抹罕見的亮色。
儒商及女性商人形象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即便以描寫商人為重要題材的“三言二拍”也未出現,獨特商業群體的塑造,無疑體現了蒲松齡對商人的極度關注與獨特思考,體現了其重商意識。
(三)商人形象的著力刻畫
在《聊齋志異》中,作者塑造了很多鮮活生動的商人主人公形象。對于這些人物形象,作者或抓住其某一性格特質著力刻畫,或抓住其本來面目大力渲染,造就了一系列典型的商人畫像,令人過目難忘。
前者的代表是《王成》篇中的王成,在篇中作者抓住了其“性介”這一特質,緊緊圍繞這一特質來構造文章。其先是家中“惟剩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可見家中貧困之至,但當其拾到金釵一股,有一老嫗來尋時,王成“遽出授之”,家中貧窮到如此地步卻絲毫沒有貪念,可見其性格之“介”。后來在逆旅中,鬻貨將歸,銀兩被盜,當別人“勸鳴官,責主人償”時,他的回答是“此我數也,于主人何尤?”此處,王成雖把失金歸結為數,但不違背良心誣賴主人,可見其“介”之至!無怪乎但明倫評到“歸之于數,不尤乎人,何等器量,何等耿介!”
對商人形象的著力刻畫,還體現在異類商人的塑造上。其代表當為《黃英》篇中菊精幻化的商人黃英與陶生。蒲松齡塑造黃英和陶生人物形象的最大成功之處,就是抓住了其物性、人性與神性三性合一的特點,既寫的精警傳神又顯得合情合理。文中的黃英與陶生姐弟很多地方與常人無異,像其中黃英與馬子才的婚戀以及陶生的經商販賣等等,跟普通的婚戀與商人負販沒啥區別,這體現了其所具有的人性。但是當看到“見荒庭半畝皆菊畦,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盡皆向所拔棄也”。馬子才所不要的劣根殘種卻都在陶生的手中培育成“罔不佳妙”的蓓蕾,卻能夠讓人覺得黃英姐弟有點與眾不同,在陶生喝醉酒幻化成菊,黃英“覆以衣”幫其重新幻化為人,已顯示出二者的身份是菊精,又體現了其神性。但當我們閱讀文章卻發現黃英姐弟由人到神的轉變絲毫不給人突兀之感,其原因就在于蒲松齡在此之前早就做好了鋪墊,對其物性進行了合理描摹,即“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兩句話暗含了菊花不擇環境但蘗生能力強的植物特點。
此類精彩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了魯迅先生極高的評價:
《聊齋志異》獨于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
真是鞭辟入里,恰切之至。
對當時社會地位不高商人形象的著力刻畫,這無疑體現了蒲松齡對商人這個群體的看重,凸顯了其重商意識。
二、重商意識背后深層意蘊探析
《聊齋志異》中商人形象的塑造背后有其深刻的勸懲意蘊。作為一部“以傳奇而志怪”的文言短篇小說,《聊齋志異》主旨卻不在于搜奇記異,其所創造的一個個曲折動人的傳奇故事背后往往都蘊含著深刻的內涵,勸懲思想即是其一。對于《聊齋志異》所蘊含的勸懲思想前人早已有所注意。像唐夢賚就曾經對本書的意旨進行過評論:“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于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體現了其對《聊齋志異》“賞善罰淫”主旨的肯定。對這一點《聊齋志異》評論家馮鎮巒則有更深刻的認識,他在《讀聊齋雜說》中曾評論到“多言狐鬼,款款多情;間及孝悌,俱見血性,較之水滸、西廂,體大思精,文奇義正,為當世不易見之筆墨,深足寶貴”。此處,馮鎮巒不但肯定了其“間及孝悌,俱見血性”的勸懲意蘊,還肯定了其“款款多情”“體大思精”的高超藝術成就。這種勸懲思想在商業小說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其勸懲思想簡而言之即勸善懲惡。
在蒲翁筆下的商人,盡管行業不同、大小不一,但都脫離不了兩個范疇:善商與惡商。在《聊齋志異》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善商形象,他們往往誠實正直、樂善好施,在作者筆下這些善商最終的結局都是美好的。前者的代表像《劉夫人》中的廉生、《蕙芳》中的馬二混及《王成》中的王成,后者的代表則有《雷曹》中的樂云鶴、《布商》中的布客與《張不量》中的張不量等。家綦貧的廉生,當被劉夫人托以重任,讓其攜資經商時,面對這難得的機遇,他并沒有像一般人一樣欣喜若狂,反而以“少年書癡,恐負重托”來推辭,可見其誠篤,后經商累至巨萬,面對劉夫人“堆金案上,瓜分為五,自取其二”的做法,廉生堅辭不受,在劉夫人“強納之”的情況下,才勉強“止受其半”,處處可見其誠實不貪的高尚品格。而在故事的最后,作者為其設計了這樣一個結局,“生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再如《王成》篇中的王成,“性最懶”,最終卻“起屋作器,居然世家”。王成之懶可以說是一以貫之,故事一開始“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就是對其懶惰的最好注腳,即便后來奉狐祖之命去販葛,也因“中途遇雨暫休旅舍”,即因懶而錯失良機,即便后來暴富后也沒有改變其懶惰的本質,還得靠狐祖的督促勞作,這樣的一個懶漢在作者的筆下卻能發家致富,令人不能不嘖嘖稱奇。對此,但明倫曾經給出了一個很好的解釋:
拾釵而不取,亡金而任數,所謂‘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者,非耶?其惰也,殆亦有說矣。老嫗、主人贈金,皆出諸意外,而卒以此致富,謂非天之報狷介士哉?
可見,在但明倫看來王成之所以能發家致富其根源就在于其狷介,亦即正直。再如《蕙芳》中的馬二混家貧,與母相依為命,以貨面為生。仙女蕙芳主動下嫁,從此錦衣玉食,生活幸福。凡所需無不立至,用文中的話說就是“馬自得婦,頓更舊業,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著”,真是幸福到了家。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其誠篤”。正如文末異史氏評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褻,蕙芳奚取哉?于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
再看后者的代表《雷曹》中的樂云鶴,在好友夏平子去世后其竭力幫助好友妻兒,“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后來晝寢,夢到夏平子來投胎報恩,正如原文所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攜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后果得佳子,十六歲,及進士第。再如《布客》中的布商長清某,以販布為業,本當命盡,后逢冥中隸胥,“屢市餐飲,呼與共啜”,使隸胥深受感動,并告知其命當盡,后來因其“鳩工建橋”,被冥間延壽。
可見在作者的筆下,正直善良、樂善好施的商人不但能夠獲得巨大財富、娶得美妻甚至能獲得嘉兒延長生命,可見蒲松齡對為善行商的肯定與褒揚。
相反,對于那些貪婪自私、冷酷無情、吝嗇之極的惡商,蒲松齡則為其設計了截然相反的結局。
《任秀》中的任建之在赴陜經商途中碰到了一個商人申竹亭,因言語投機兩人“盟為弟昆,行止與俱”。到陜西后任建之一病不起,臨終留下遺言:
吾家故無恒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謝異域。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 囊金二百馀,一半君自取之,為我小備殮具,剩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櫬而歸。如肯攜殘骸旋故里,則裝資勿計矣。
此遺言字字血淚,讀來令人傷痛不已。安排中以一百金給申竹亭也可謂不薄,沒想到申竹亭竟然只用五六兩銀子為任建之買了口薄棺就卷款而去,可謂薄情之至!對于這個忘恩負義之人,在文章最后作者為其安排了一個人鬼賭局,其昧心賺走的二百兩銀子一文不少得回到了仁建之兒子任秀手中,而申竹亭作賭局賺取的銀子則化為灰帛,為鬼所戲,真是報應不爽。《云翠仙》中“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的梁有才,娶了云翠仙后,“由此坐溫飽”,但是由于沉迷于賭博,后來為獲取賭資竟然要賣云翠仙,又因“貨為媵,金可得百;為妓,可得千”。為了獲取更多的賭資竟然準備把妻子賣做妓女,真是可惡之極!其結局則先是被云家暴揍,渾身“腫潰為癩”,為人所不齒,后被囚死獄中。《金陵乙》中的賣酒人金陵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飲者,不過數盞,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最終這個喪心病狂的惡商卻在作者筆下化為狐貍,數日尋斃。《聊齋志異》中其他的惡商也都得到了類似的報應,不一而足。
總之,在蒲翁的筆下,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商人或獲得巨富或娶得美妻或誕得麟兒或易死為生,而那些或奸詐或貪婪或冷酷的商人,則或為鬼神所戲或身陷囹圄或化為異物,正所謂果報不爽,體現了蒲翁勸善懲惡的救世婆心。
三、蒲松齡重商原因淺探
(一)外在環境的影響。
首先從時代背景來看。蒲松齡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大致生活在明末清初時期。我們知道明朝中后期是中國封建時代商業經濟發展的黃金期,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使得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其實在清初雍正實行閉關鎖國之前,商業依然得到了較大發展。當時的山東作為北方經濟重鎮,其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就在《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五談到山東風俗時說:
大較濟南省會之地,民物繁聚,兗東二郡,瀕河招商,舟車輳集,民習奢華,其俗也文若勝質;青、登、萊三 郡,憑負山海,民殖魚鹽以自利,道里僻阻,商旅不通,其俗也質若勝乎文……其小民力于耕桑,不賤商賈。
可見其時山東商業經濟的繁榮。
就蒲松齡的家鄉淄川來說更是歷來都有經商重商的傳統,唐夢賚曾在《濟南府志》中曾這樣描述淄川:
人勤稼穡,家鮮蓋藏,農儉嗇,三時既盡,輒出將車以謀食,或緯蕭為業,商賈治絲帛,業香屑,工則梓匠圬墁,并以巧聞。
應該說明末清初商品經濟的發展及蒲松齡家鄉淄川的重商傳統對其重商意識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家庭環境的影響。
蒲松齡出生在一個亦儒亦商的家庭,其父蒲槃的人生經歷了先儒后商復儒的歷程。這在《述劉氏行實》中有很好的描述:
初,松齡父處士公敏吾,少慧肯研讀,文效陶鄧,而操童子業,苦不售。家貧甚,遂去而學賈,積二十余年,稱素封。然四十余無一丈夫子。不欲復居積,因閉戶讀,無釋卷時,以是宿儒無其淵博……每十余齡,輒自教讀;而為寡食眾,家以日落。
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蒲槃先是苦讀但是連個秀才也沒考中,后因家庭貧困去讀而賈,家稱素封。“素封”一詞見于《史記·貨殖列傳》:“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指無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蒲松齡父親蒲槃經商二十多年稱素封,可見其卓越的經商才能。后又因四十多了還沒有兒子,再次去賈而讀,并親自指導兒子們讀書。在這種家庭環境的熏陶下,蒲松齡的重商意識自是應有之義,其對商人特別是儒商飽蘸感情的描寫也就不難理解了。《白秋練》中“乘父出,則執卷哦詩”的慕蟾宮,《劉夫人》中的廉生巨富后復去賈而讀,從中幾乎都可以看到蒲槃的影子。
(三)個人經歷的影響。
蒲松齡少小聰慧,十九歲參加縣府道考試連取三個第一,“名藉藉諸生間”,從此終其一生不廢科舉,冀博一第,但都名落孫山,直到七十二歲才援例成為貢生。在此期間因為“食指日繁”,蒲松齡從康熙五年開啟了設帳生涯,一直到七十歲才撤帳歸家,這在蒲箬《柳泉公行述》中有明確的記載,即“迨撤帳歸來,年七十矣”。人生七十古來稀,七十才撤帳歸家,固然由于其與館東畢氏父子相交莫逆、賓主合和相關,但經濟貧困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原因。這在其《子笏》詩中可見一斑:
我為糊口耘人田,任爾嬌惰實堪憐。
幾時能儲十石粟,與爾共讀蓬窗前。
作者為了糊口而只能替別人教育孩子內心何其沉痛,其親自教育自己孩子的愿望又何其迫切!但貧困影響了他的愿望,從詩中看出連“儲十石粟”這樣低微的愿望都難以實現,可見貧困之至。關于自身貧困的描述多見于其詩文,這在《除日祭窮神文》表現得尤為集中突出。我們不妨看一下:
窮神,窮神,我與你有何親,興騰騰的門兒你不去尋,偏把我的門兒進?難道說,這是你的衙門,居住不動身?你就是世襲在此,也該別處權權印;我就是你貼身的家丁、護駕的將軍,也該放假寬限施施恩。你為何步步把我跟,時時不離身,鰾粘膠合,卻像個纏熱了的情人……
窮神!自從你進了我的門,我受盡無限窘,萬般不如意,百事不趁心,朋友不上門,居住在鬧市無人問。我縱有通天的手段,滿腹的經綸,腰里無錢難撐棍。你著我包內無絲毫,你著我囊中無半文,你著我斷困絕糧,衣服俱當盡,你著我客 來難留飯,不覺的遍體生津,人情往往耽誤,假裝不知不聞。
文中作者用幽默詼諧的語調對窮神進行質問,初讀令人捧腹,深思令人淚垂,直可謂字字血淚,寫盡滿腹的心酸無奈。面對如此窘境如何改變呢?正所謂“學而優則仕”,蒲松齡開始是寄希望于科舉的,但是隨著科舉失利的打擊接踵而來,其對科舉也由熱忱變得失望起來,這從《聊齋志異》中《葉生》《賈奉雉》等篇可以得到明證。此情此景下從商無疑是改變窘境的一種快捷方法,雖然沒有確切資料證明蒲松齡有從商的念頭和打算,但是考慮其家庭困境、其父從商的經歷及從商給家庭帶來的變化,其對商業的肯定自是應有之義,其重商意識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