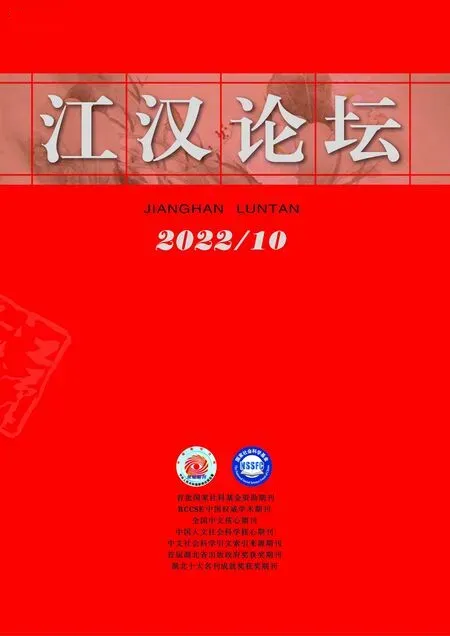湖廣民變與晚明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
方 興
從萬歷二十四年(1596)開始,明神宗朱翊鈞以“助大工”為名,陸續向南、北兩直隸和除貴州之外的12個布政司及遼東地區派出宦官,或為礦監,或為稅使(又稱稅監),或礦監兼稅使、稅使兼礦監,統稱“礦監稅使”或“礦監稅監”。礦監稅使在各地開礦并額外課稅,所至之處,幾乎都引發了程度不同的社會動蕩,臨清、蘇州及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多個城市,更發生了被稱為“市民運動”的民變。其中,湖廣民變在多個中心城市及城鎮發生,持續時間長、牽涉人員廣,情況尤為復雜。
一、萬歷時期的湖廣民變
從萬歷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丁酉)到三月七日(丙戌),在短短的50天里,先后有10位礦監稅使奉命前往云南、湖廣、山西、福建、江西、四川、陜西、遼東等處采礦、征稅,另有4位礦監稅使被賦予更大的權力。這是萬歷皇帝派遣礦監稅使過程中力度最大的一輪,當時的記載是:“諸弁馮綱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可。”在所有已經派出的近20位礦監稅使中,以御馬監奉御(正六品)前往湖廣荊州征稅的陳奉品級較低。
或許是為了向急于看到經濟效益的皇帝表現自己的能力,在受命后的第三個月,萬歷二十七年閏四月十七日,陳奉進獻的第一批稅銀就運抵北京。為了不讓稅銀旁落,陳奉提出和長江下游的江西稅使明確稅界的請求。萬歷皇帝顯然欣賞陳奉的雷厲風行,命江西稅使李道、潘相不得越過省界征稅,以保證陳奉在湖廣的征稅業績。得到鼓勵的陳奉,加大了課稅的力度,并且受命在湖廣各地開礦,由“稅使”而為“礦監稅使”。
但是,陳奉在湖廣的活動從一開始就受到當地民眾及官員的抵制,并且在多個城市引發了一系列民變。這些民變,一度被有關學者稱為“市民運動”。
(一)襄陽民變。萬歷二十七年夏,陳奉委官在湖廣西北部中心城市襄陽課稅。開征未久,“商人三百六十行聚眾鼓噪,知府李商耕治其參隨”。
(二)荊州民變。萬歷二十七年夏秋之交,陳奉由省城武昌抵荊州,征收“店稅”。當地“商民鼓噪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莫可御。道府諸臣……殫力防護”,保障陳奉安全。荊州府推官華鈺多方阻止當地吏員為陳奉供役,并裭奪陳奉委官吳應瑞等人冠帶。
(三)武昌及漢陽民變。萬歷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湖廣巡撫支可大奏稱,有積棍劉之良、宋大工等,自稱為稅監陳奉所遣,恫嚇民眾,致使湖廣省城武昌及漢陽“士民”數百人,齊赴巡撫、巡按衙門,擊鼓聲冤。接著,人群又往陳奉稅署鼓噪。自辰時至酉時,經撫、按的反復勸諭,人群逐漸散去,但騷亂延續多日,才勉強平息。而據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都御史李化龍所言,當時聚集在撫按及及前往稅署的民眾,并非巡撫支可大所說的數百人,實有上千人。
(四)蘄州民變。萬歷二十八年夏,陳奉在黃州府所屬蘄州攤派礦稅,知州鄭夢禎不從。陳奉繼遣委官王金吾開蘄州迎山礦,并索取賄賂。鄭夢禎憤而乞休,蘄州民眾群毆王金吾、挽留鄭夢禎。
(五)承天民變。萬歷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承天守備內官監少監杜茂、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立賢的奏疏同日抵京。杜茂稱,有生員沈希孟等、縣民劉正舉等,聚眾毆打稅監陳奉所遣差人,“鼓噪倡亂”;王立賢則直指陳奉“貪縱暴虐、激變地方”,請召回陳奉,嚴懲陳奉委官孟學等10人、土民李二生等9人。
(六)武昌再度民變。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省城武昌發生更大規模的民變。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奏稱:由于陳奉在武昌作威作福,僭稱“千歲”,其黨肆意橫行,或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將民女掠入稅監署中,肆意蹂躪。王姓生員之女、沈姓生員之妻,皆被逼辱,訴于官府,“市民從者萬余,哭聲動地”。民眾包圍稅署,“甘與奉同死”。湖廣撫、按及三司官員守護數日,人群逐漸散去。有記載說,巡撫支可大曲為陳奉蒙蔽,兵備僉事馮應京則捕治其爪牙、上陳奉十大罪,陳奉亦反訐馮應京“故違明旨、阻撓稅務……凌辱欽使”。
(七)武昌持續民變。因陳奉的參奏,萬歷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萬歷皇帝下“圣諭”,命錦衣衛派得力緹騎前往湖廣,將湖廣兵備僉事馮應京及棗陽知縣王之翰、襄陽通判邸宅,一并“扭解來京究問”。馮應京為湖廣按察司僉事一年,備兵武昌、漢陽、黃州三府,善待民眾、深得民心,被捕之日,“百姓”群聚呼號,欲驅逐陳奉。陳奉盛陳兵衛,招搖都市,殺死市民李廷玉等二人,又命護衛300人,驅逐百姓,射殺數人,傷者多人。馮應京被押離武昌,陳奉命人開列其罪,榜于道路,激起更大的民憤,數萬人日夜聚集,誓殺陳奉。陳奉躲在楚王府中,逾月不敢出門。憤怒的民眾將陳奉參隨耿文登等6人投入長江(或漢水),又怒巡撫支可大曲護陳奉,縱火燒了巡撫衙門。
襄陽民變、荊州民變、漢陽民變、承天民變、蘄州民變,特別是持續不斷的武昌民變,在當時引起廣泛關注,多種史料都有記載。但據萬歷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內閣大學士沈一貫的題本,內引陳奉所云,民變還發生在東部中心城市黃州、東北部中心城市德安,以及今屬湖南的中心城市寶慶(今邵陽)、湘潭,以及襄陽府之光化縣、黃岡縣之陽邏鎮、武昌縣之仙桃鎮、蘄水縣之巴河鎮等處。
就在湖廣各地城市頻頻發生民變的同時或前后,山東臨清,南直蘇州、儀征,江西景德鎮、湖口、上饒,廣東合浦、新會,遼東山海關、開原,浙江杭州等地,也發生了由于類似原因而引發的城市民變。
和包括明朝在內的中國歷史上不斷發生的以失去土地或逃避兵役、徭役的農民為主體的民變、以礦徒或教徒為主體的有組織的民變不同,上述萬歷二十七至二十九年湖廣承天、武昌、荊州等地及臨清、蘇州等地民變,都是發生在中心城市并以城市居民為主體的自發性民變,并且不同程度得到當地官府及官員的同情和支持,城市居民和當地官員共同抗衡皇帝派出的“欽使”。這不僅僅在明朝,即使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屬罕見。
二、湖廣民變中的各類“角色”
短時期內在湖廣及各地城市頻發的“民變”,毫無疑問是因為礦稅陳奉及相關地區礦監稅使的“激變”。《明史·宦官傳》概括性地描述了陳奉初至湖廣的作為:“奉兼領數使,恣行威虐,每托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對于湖廣民變,當時所有的批評首先都是針對陳奉,將其與山東陳增、遼東高淮,并稱為所有礦監稅使中的“最橫者”。陳奉撤回北京之后,代行其職的承天守備太監杜茂也批評陳奉在湖廣的作為:“自陳奉不能體德意,額外苛求,以致商賈罷市、行旅罷途,人人自危,在在思亂。”
但是,圍繞著陳奉們的“激變”和各地的“民變”,可以明顯看出:“激變”的陳奉及各地礦監稅使,都并非一個人在“戰斗”。陳奉和各地的礦監稅使一樣,他們的開礦課稅,由于沒有納入國家“正課”,所以雖然出自皇帝委派,主要依靠的卻不是當地官府,而是從北京帶來的隨行人員,特別是在當地招募的各色人等。陳奉到湖廣之后不久,獲準在每個府招募“廉干舍人”15名,給與冠帶。這些有“冠帶”的“廉干舍人”,和陳奉從北京帶來的隨行人員一道,多被陳奉委以采礦課稅之責,成了“委官”。而在當地招募的各色人等,則成了陳奉及“委官”們的“參隨”及“爪牙”。所以后來繼任湖廣巡撫的趙可懷說:“夫(陳)奉固一虎耳,委官之為虎者又百數十人,參隨各役之為虎者又千數百人。”據都御史溫純所言,包括陳奉在內的各地礦監稅使,都在當地招募數量不等的“護衛”,其中又以陳奉所募最多:“(湖廣)陳奉以千計,(遼東)高淮、(山東)陳增、(臨清)馬堂以百計。”
這些委官、參隨及爪牙、護衛等,代表著陳奉及其他礦監稅使,直面民眾及當地官府,他們和陳奉們一道,在湖廣及各地激發了一次又一次城市及城鎮民變。我們以湖廣“青山礦”開采引發的承天民變為例。“承天民變”源于萬歷二十七年九月。時有“武功衛百戶”韓應桂上疏,奏稱“湖廣德安府(今湖北安陸、隨州)等處產真礦銀砂及大青銅錫等物”;十二月,據“土民夏國瑚”提供的信息,“湖廣京山具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經過陳奉及當地官府的實地查勘,韓應桂提供的信息并不可靠,故被撤回,但陳奉根據另外一位“原奏”“武功右衛百戶”謝應魁的信息,將開礦地點選擇在“青山”。
“青山”位于明代襄陽府棗陽縣西南約60里處,南距承天府治所鐘祥縣東北的“顯陵”百余里。“顯陵”埋葬著嘉靖皇帝的父親、萬歷皇帝的曾祖“獻皇帝”朱佑杬。所以,當地官員及民眾為了阻止在青山開礦,皆以驚動顯陵“龍脈”為由。他們認為,非此不足以打動萬歷皇帝、不足以讓其制止陳奉。萬歷二十八年三月,鄖陽巡撫鄭國仕上疏,指責謝應魁等人“誑惑圣聽,擅掘祖陵龍脈,乞免棗陽、京山二縣之開采”。等候了三個月,萬歷皇帝沒有回復,鄭國仕再次上疏,請求“致仕”,希望撇清日后可能要承擔的責任。棗陽知縣王之翰及襄陽府通判邸宅、推官何如棟,則通過各種方式對青山礦的開采進行阻撓。
但是,萬歷皇帝相信的是礦稅使陳奉。根據陳奉的報告,萬歷皇帝明確表態:“湖廣附近皇陵地方,山場連絡龍脈,不許擅行開采……棗陽等縣既查隔遠,準你會議開采,銀兩解進。”青山既屬棗陽,以驚動顯陵作為反對或阻撓開礦的理由,并不成立。在皇帝的支持,陳奉派出“委官”韋夢麟、戴燁、李茂春等人,招募河南等地方“礦徒”數千人,在青山破土動工。有陳奉撐腰,韋夢麟等人在招募礦徒及開礦的過程中,“擁兵操練,所過地方,舳櫓數里,旌旗蔽江,炮鼓連天,亡命罪棍,悉為爪牙,鄉官士民,悉遭魚肉”。
陳奉親自前往承天府治所在地鐘祥縣坐鎮。開礦現場雖然在襄陽府棗陽縣的青山,反對的呼聲更多發生在“顯陵”所在地承天府、鐘祥縣。陳奉坐鎮鐘祥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推動在承天、襄陽兩府課稅。南京監察御史朱吾弼在奏疏中指稱陳奉到承天的情狀:“衣大紅蟒袍謁顯陵,而杜茂不敢問;行牌提鐘祥縣官,而撫按不敢問;用夾杖加生員且辱生員妻女,而提學官不敢問。”為了打動皇帝,朱吾弼指責陳奉的所作所為是真正的“無主、無官、無士、無民”,為有明建國以來聞所未聞。
朱吾弼把矛頭對準陳奉,但具體辦事的則是陳奉的“參隨”李二生(至)、薛長兒等人。萬歷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民變發生,為首者是承天府學生員沈希孟、唐三登、張奕業等,以及縣民劉正舉等,李二生被憤怒的人群所殺。
在此期間,又有陳奉“參隨”陳文經等九人,在承天府暗訪富戶,被參與民變的人群抓獲,一位名叫孫國棟的參隨被打死。人們從陳九經的袖中搜出開列的富戶名單,共有50多家,遂將陳文經等人扭送到承天府衙,要求府衙處置。陳九經等人尚未處置,陳奉的鈞牌卻到了承天府:由于青山、京山等地未開采到有價值的金銀礦,承天府每年需上繳礦銀5000兩,即強行攤派“礦”銀;追究參隨孫國棟死于街頭的原因,要求承天府緝捕兇手。
陳奉此舉引發了更大騷動。五月十八日晚,周邊大批鄉民擁入承天府城,聲援城內的生員與縣民。此后兩天,參與民變的人們,先“揭竿”于岳王廟,再“盟誓”于報恩寺,聲討礦監及委官參隨。經過當地官方的反復勸說,這些“聚囂”的人群先后散去。
隨后一個不知真假的消息迅速傳開,說是錦衣衛“緹騎”將來承天,追究“揭竿”“盟誓”的首犯,致使“士民洶洶”。六月十七、十八日,“解散之眾,號召復聚”。六月二十二日夜,人們抓獲了陳奉的“養馬人”俞三,要求俞三提供陳奉疏內“誣陷”士民的名單。俞三說名單應該就在鐘祥縣,人們遂蜂擁至鐘祥縣衙。主事者表示不知情,說如果真有名單,應該在“司房”藺榮處。于是人們又云集至藺榮宅,對其進行毆打,逼其交出名單。
承天守備太監杜茂本來對陳奉的所作所為有些不滿,故一直靜觀事態的發展。但事情鬧大了,守備就得負責任,于是命承天衛指揮周之屏、胡效忠、秦上等,統兵殺奔領頭鬧事的生員沈希孟、唐登三等人之家,接著殺向承天府學,砍傷、打傷生員40余人。人們將受傷生員抬到承天府衙,要求懲治兇手。承天知府王禹聲驗明傷勢,命人將傷者抬往“守道”衙門,建議緝捕兇手。當時的荊西道副使為萬振孫,表示將為受傷生員主持公道。
杜茂則采納被毆打的“司房”藺榮的策劃:一是稱沈希孟等“士民”因私怨倡亂;二是假傳“圣旨”,將沈希孟等人拘捕并囚禁于承天衛獄;三是命人在沈希孟等人家中搜獲兵器,并讓當地地保文科等人出面作證,坐實其“蓄謀已久”的證據。但是,從沈希孟等人家中搜出的“斬馬刀”,是和沈希孟有嫌隙的鄰居、另一“司房”劉可立提供;搜出的刀、槍,則是逼迫“屠戶”劉桂、“鐵匠”李榮提供;對于出面作假證的“地保”文科等人,各給官田50畝以行封口;而所有的文字證據,則出于“司房”王南皋之手。
“承天民變”從萬歷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到六月二十日,前后延續了一個多月。事發之后,承天守備太監杜茂、湖廣巡按御史杜立賢,針鋒相對,分別上疏,杜茂聲稱沈希孟等人“倡亂”,杜立賢堅稱陳奉及其參隨“激變”。
在承天府發生的民變中,“激變”方是湖廣稅監及其委官、參隨、爪牙,以及承天守備太監及其調遣的承天衛官軍,承天府、鐘祥縣的司房,被卷入的有鐘祥地保及屠戶、鐵匠等。“民變”方是承天府、鐘祥縣的生員、富戶、縣民,被卷入的有鄉民,在他們的身后,是阻撓開礦及對民變持同情態度的道、府、縣官員。
在襄陽、荊州、武昌、漢陽等地,民變的“激變”方是稅監及其委官、參隨、護衛、爪牙、錦衣衛“旗番”等;“民變”方,“士”即生員及其他身份的讀書人一直是主要成分,而在城市經濟相對發達的襄陽、荊州、武昌等地的民變,以商人為主體的市民占有很大比重,被卷入的有當地其他身份的民眾,同情并支持他們的部分當地官員。武昌民變之后,有“耆老”李之用等人代表武昌、漢陽、黃州三府民眾,為馮應京鳴冤,要求懲治陳奉。
朱吾弼在向“朝廷”上疏陳述承天民變時,對“委官”韋夢麟等人的作為用了16個字的概括:“亡命罪棍,悉為爪牙;鄉官士民,悉遭魚肉。”這十六個字也可以視為湖廣民變對立雙方的基本分野:投奔陳奉及其委官為參隨、為“爪牙”者,大抵被視為“亡命罪棍”者;受其欺凌、被其魚肉并參與民變者,多為“鄉官士民”。
三、民變中不同“角色”的社會屬性和利益訴求
在湖廣城市及集鎮發生的民變,就“民變”方而言,無論是生員、富戶、商民、商人、士民,還是縣民、鄉民、耆老,以及同情與支持他們的當地官員,身份有高低、財富有多寡,但在當時或當地,大抵生活相對安定或曰“有恒產者”,對現有秩序相對比較維護。蘇州、臨清及江西、廣東等地城市民變的參與者,主要也是這些人群。可以說,生活相對安定者、現有秩序的維護者,成為晚明湖廣及其他各地城市民變者的主體,是這一輪民變與以往任何時期民變的最大區別。當然,不排除無業游民及其他成分的人群在其中起作用。
相對于“民變”的參與者,“激變”方的身份顯得多元并復雜得多。
(一)礦監稅使。在湖廣民變中,稅監陳奉是“激變”的第一責任人;在承天府民變的過程中,給陳奉“助力”的是承天守備杜茂,陳奉召回之后由他代行礦稅之職。他們分別代表全部47位礦監稅使的兩種類型:其一,直接由京師派遣到地方,這是礦監稅使中的主體;其二,本為當地守備太監或織造太監,奉命兼收礦稅銀兩。
礦監稅使具有三種社會屬性,因而也代表著三個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一是代表皇室。《明史·食貨志》稱:“自(萬歷)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珰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這是礦監稅使們對皇室的貢獻,他們代表著皇室的利益。二是代表內府宦官衙門。礦監稅使們上納的“礦稅銀兩”,皇室和內府各衙門之間,有達成默契的分成比例,礦稅銀兩越多,宦官各衙門所得利益也就越豐厚。正是因為有這樣的默契,使萬歷三十年發生的一件奇怪的事情就容易理解:這年二月十六日(己卯),萬歷皇帝因病發布“臨終遺言”,第一條即“罷礦稅”。但是第二天下午,“罷礦稅”的“上諭”尚未來得及落實,已經“病愈”的萬歷皇帝便派文書房宦官來到內閣,索取前日“上諭”,并且傳達新的“上諭”:礦、稅皆不可罷。據記載,除了“奉旨”前來的“文書房”宦官,前后另有20多名各衙門宦官自發來到內閣,索取“上諭”。沈一貫和內閣同僚堅持不給,宦官們一擁而上,將大學士們“搏顙幾流血”。這是各宦官衙門因為利益攸關而表現出來的“整體性”態度。三是代表自己的家庭、家族。明朝前期的宦官多來自朝鮮、安南及女真、苗、瑤、僮、回等少數民族,和原有的家庭、家族幾乎隔絕。但是,隨著對外擴張及國內對少數民族戰爭的減少,明代中后期的宦官,多出自京畿農家,主要是貧苦農家,他們肩負著家庭、家族“脫貧”乃至“富貴”的責任。
(二)委官。陳奉在湖廣的“委官”,主要有兩種人員構成:一是從北京帶來或從北京差遣而來的錦衣衛及各京衛、邊衛的中下級軍官;二是當地衛所的軍官及“冠帶”舍人余丁。見于記載的陳奉委官有:韓應柱、韋夢麟、仇世亨、謝應魁、戴燁、李茂春、吳應瑞、王體仁、王指揮、王金吾、孟學等。身份比較明確的有9人。9人之中,有錦衣、武功、騰驤等衛“百戶”5人、千戶1人、原任守備1人、現任指揮1人、冠帶舍人1人。
“土木之變”后,明朝軍制多次變化,總的趨勢是衛所精銳不斷被抽調,另立兵營,成為“營兵”,專事“鎮戍”;留下的老弱及舍人余丁,從事屯田。營兵為戰斗之兵,“衛所徒存老家之名”。韋夢麟等九名身份比較明確的陳奉“委官”的共同特點,都是中下級軍官。而且,或者是衛所“老家”的屯田序列軍官,或者是被戰斗序列革除“回衛”的軍官,他們的地位,與“營兵”軍官不可同日而語。9人之中,除荊州衛“王指揮”是當地衛所軍官、吳應瑞是當地衛所的“冠帶舍人”外,其他七人都是來自“京衛”及“邊衛”非戰斗序列的中下級軍官,以及被免職的戰斗序列軍官。其中,韓應柱、韋夢麟、戴燁、仇世亨、王體仁、謝應魁6人,是提供了在湖廣開礦或課稅信息的“原奏官”,派遣到湖廣,由“原奏官”轉化為“委官”。9人之中,身份相對較高的是“革任回衛”的原任守備戴燁。革職不久,戴燁就提供了湖廣有“羨余銀兩”億萬兩的信息,并以“原奏官”的身份來到湖廣,和韋夢麟等人一道成為陳奉的“委官”,往河南招募礦徒并在青山開礦。但是,由于戴燁是“革職回衛”的軍官,所以不能直接上疏,而是需要通過“騰驤衛百戶”仇世亨代為請奏。9人之中,身份最低的是吳應瑞,本為荊州衛所的“舍人余丁”,被陳奉給予冠帶、成為“委官”。可以看出,在“營兵”序列中革職或“回衛”的軍官,和在“老家”衛所中的軍官,都是“礦監稅使”事件中也是湖廣民變及其他各地民變中“原奏官”及“委官”的重要構成。至于“委官孟學等十人”,沒有發現能夠證明他們身份的材料,但從上述例證看,他們應該是兩種來源:或者是從北京來的陳奉參隨,或者和吳應瑞一樣,為當地衛所的“冠帶舍人”。
(三)參隨。陳奉在湖廣的參隨,主要由三類人構成:一是當地衛所的“舍人余丁”;二是在當地招募的“亡命罪棍”;三是陳奉從北京帶來的宦官、原奏官們的親戚及朋友。
文秉《定陵注略》載:萬歷三十年正月,命逮京師西城兵馬戴文龍,原因是山西礦監張忠劾其“捏報鋪戶”。張忠屬下有一參隨,名叫張國紀,是從京師帶來的。萬歷皇帝“逮治”戴文龍的“圣旨”說:“參隨張國紀,系題奏欽派人役,鋪戶準優免。戴文龍違旨輒地申報,好生可惡。”這道“圣旨”說明:其一,張國紀是張忠從京師帶到山西來,否則京師的“西城兵馬”管不著;其二,一旦被礦稅申報為“參隨”,便是“欽派”人役,可以免除在原籍的徭役,各地官府不得輕易處置。而作為“參隨”的張國紀,很可能就是山西礦監張忠的一位同宗的兄弟或伯叔、甥侄。更為典型的例子是,陜西稅監梁永屬下有一參隨名叫戴勛,為梁永家的“舍人”,也就是家丁;而另一位參隨呂四,則是梁永的侄子。由此也可以推測,陳奉等礦監稅使從北京帶來的“參隨”,不乏其親戚朋友。
見于記載的與湖廣民變有關的陳奉及其委官的參隨人員,有李二生、薛長兒等9人,陳文經、孫國棟等9人,劉之良、宋大工等人,耿文登等6人(《明史》說是16人),荊州衛王指揮參隨多人,陳奉護衛300人,以及在各地的“爪牙”。
李二生、薛長兒等9人,是稅監陳奉或委官韋夢麟等人的“參隨”,為承天民變的直接激發者。南京監察御史朱吾弼在奏疏中稱之為“奸民”:“蓋其士民初變,則五月十五日以陳奉聽奸民李二生、薛長兒等,牌提縣令、夾打生員,拆人屋、擄人財、奸人婦,用銅鉤鉤人肉、銅拶拶人乳,所在驚恐,公憤聚眾,期殺李二生輩,無知犯法,實非得已。”時任湖廣巡按御史的王立賢,稱李、薛為“土民”:“委官孟學等十人,與土民李二至(生)等九人,均之大奸極惡、召亂起釁,行臣等提究正罪。”后任湖廣巡按御史的史學遷則稱之為“郢人故讎”:“參隨薛長兒、李二生,皆郢人故讎,報郢人獨憯。”同治《蘇州府志》在為承天知府王禹聲立傳時記有薛長兒、李二生等人的出身及事跡:“奸民薛長兒、李二生皆承天人,為奉爪牙……二生等嘗以罪為鐘祥令案治,至是圖雪其私,遂以阻撓,下檄捕令,士民相聚揭竿。”從這些記載看,李二生、薛長兒等人是陳奉或韋夢麟等在當地招募的“土民”,由于各種原因和當地的富民、生員產生嫌隙,又因事曾被縣衙處置,當屬不愿從事正當職業的“不安分”者,時稱“奸民”或“游棍”,投奔陳奉及其委官,成為稅監之參隨。李二生死于承天民變中,薛長兒隨陳奉到武昌后,與其他參隨一道,“魚肉楚民,商賈不行”。武昌府推官胡嘉棟在分巡道馮應京的支持下,“盡逮群校薛長兒等,置之死”。
參隨陳文經、孫國棟等“九人”,除了南京御史朱吾弼的奏疏外,未見其他記載,或許和李二生、薛長兒等“九人”本是一伙,被重復說到,但并不影響他們的身份。既然能夠搜羅富民的名單,陳文經等人應該和李二生等人一樣,也屬當地的“土民”,也是土民中不安分守己的“游棍”“奸民”之類。
劉之良、宋大工等人的被提及,是在武昌、漢陽民變之后。萬歷二十八年正月,湖廣巡撫支可大上疏:“楚地遼闊,民情獷悍,易動難安。近自采木派餉,又益抽稅開礦,追取黃金,搜括積羨。小民賠累不堪,囂然思亂。乃有積棍,指稱稅監,嚇詐噬人,如劉之良、宋大工等,遂致武昌、漢陽土民數百,奔赴撫按,擊鼓聲冤。”支可大一直被指責為懼怕稅監、隱瞞真情,此疏將激發民變的劉之良、宋大工稱為“積棍”,當是他們的真實身份。二人及其同伙和李二生、薛長兒等人一樣,也是當地無正當職業者或不愿從事正當職業者,投靠陳奉為參隨。但支可大說劉之良、宋大工二人“指稱稅監”,而不直說“參隨”,則是為陳奉開脫。
在陳奉的所有委官、參隨之中,最為著名的是耿文登,幾乎所有關于湖廣民變乃至萬歷時期“市民運動”的文獻,都要提及這位“耿文登”。《明神宗實錄》載湖廣巡撫支可大疏:“應京既被逮,奉大書應京之名,榜其罪狀懸于通衢。眾群聚,欲殺奉。奉逃匿楚府,逾月不出。又執奉左右耿文登等六人,投之江。”《明史·馮應京傳》:“緹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相率痛哭。奉乃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奉窘,逃匿楚王府。遂執其爪牙六人,投之江,并傷緹騎;詈可大助虐,焚其府門,可大不敢出。”《明史·陳奉傳》:“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送之。奉又榜列應京罪狀于衢。民切齒恨,復相聚圍奉署,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眾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于江。”除了《明史》有“六人”與“十六人”之分歧外,各種記載皆同。但身份最不明確的,也是這位“耿文登”,或稱之為陳奉之“左右”,或稱之為“奉黨”,竟然不明其為“委官”還是“參隨”,或者是一般的“爪牙”或“護衛”。

如此看來,耿文登的身份有三種可能:其一,和劉之良、宋大工等一樣,為武昌或湖廣某地的“積棍”“奸民”,投靠陳奉而為“參隨”“護衛”;其二,從北京追隨陳奉來到湖廣的參隨,或許是某宦官或陳奉本人的親戚或朋友;其三,“奉旨”由東廠或錦衣衛派遣而來的“旗番”“官旗”,即錦衣衛緹騎,他們同樣是湖廣激變中的一股因素。和“耿文登”一并被民眾投入江中的“六人”,則三種身份皆有可能。

當然,無論是在湖廣的承天、武昌、襄陽、荊州、黃州,還是在南直隸的蘇州、山東的臨清及江西、廣東等地,民變的激變者固然是陳奉等礦監稅使及其委官、參隨、護衛、爪牙,但整個事件的真正推手——卻是皇城內的萬歷皇帝,他才是各地民變激變的真正“主角”,是“礦監稅使”事件發動者和堅持者。否則,無法解釋這場事件發生十分迅猛,而在萬歷皇帝病死后,又立即宣告終結。所以,當人們就湖廣的事件指責陳奉、就山東的事件指責陳增、就遼東的事件指責高淮的同時,又將所有的批評指向萬歷皇帝。

皇帝一面持續為陳奉在湖廣的行為撐腰并排除障礙,一面在“原奏官民”們的推動下,不斷給陳奉等礦監稅使更大的權力、施加更大的壓力,而“原奏官民”所提供的信息,多屬捕風捉影,有些更是天方夜譚。如仇世亨、戴燁所說的湖廣全省各府州縣有積貯銀“億萬余兩”,錦衣衛百戶王守仁說祖上“定遠侯”王弼留存在楚王府的莊田86處、田租累計800多萬兩,另有黃金6萬余兩、白銀260余萬兩等。
筆者從《明神宗實錄》《定陵注略》《明史紀事本末》《明史》及其他文獻中,輯錄“原奏官民”138人,其中,有明確身份的約100人,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其一,錦衣衛等在京各衛的中下級軍官,共71人,其中“百戶”為多,約40人。他們和前文所說的陳奉“委官”韋夢麟等人一樣,大體上為軍中的閑散人員。其二,京師文官機構的下級官員或吏員,約10人,也有個別地方官署的下級官員,特點都是“雜職”,類似于前文所說的“司房”藺榮等,沒有一位進士出身的官員。這兩類屬“原奏官”。“原奏民”約20人,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他們之中,有省祭官、門官、革職的軍官等,以及被稱為“奸民”“土棍”“竊棍”之類的當地無業游民,他們的身份,與陳奉參隨李二生、薛長兒等相似,多為當地的無業人員及失去土地的破產農民。也就是說,他們也是各種成分的“無恒產”者。

萬歷皇帝的心機,當時的人們也是洞若觀火,兵科給事中田大益直指萬歷皇帝的內心:


四、“白銀”刺激下的利益共同體


萬歷皇帝對財貨的追逐,固然與自身性格有關,更有不可忽視的兩大因素:(一)延續10多年的“國本”之爭,這是直接的“家計”因素;(二)“百年承平”帶來的社會財富積累、特別是大量白銀的進入中國并在市場流通,則是強大的“社會”因素。
由于受制于太后和文官,萬歷皇帝雖然喜歡鄭貴妃卻無法將其立為皇后,雖然喜歡鄭貴妃的兒子常洵卻無法將其立為太子。萬歷皇帝認為母親乃至整個官場都在和自己作對,所以,以腳疾為借口,不上朝、不理政,并且希望在經濟上對鄭貴妃和兒子常洵進行補償。從這個角度上說,礦監稅使派出,又是在給鄭貴妃和常洵置辦家業,這就是田大益所說的“家計”。


無論是數以億兩計(高位)還是數以千萬兩計(低位)的白銀輸入,這些白銀皆為民間貿易或者說是海上“走私”的結果,雖然對于國內市場的繁榮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但大抵與明朝朝廷無關。明朝后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一方面是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繁榮、財富的積累,各階層的社會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從明太祖建國,到明朝滅亡,財政稅收體制幾乎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國家財政卻仍然以農為本,對外禁海、對內禁礦,喪失了大量財源。巨量白銀的流入,一方面激發了全社會對白銀的追逐,另一方面,也激發了朝廷和皇室對白銀的占有欲。可以認為,正是在大量白銀輸入和城市高消費的刺激下,導致了礦監稅使的出現。
問題現在應該清晰起來。湖廣及其他地區所發生的城市居民的“民變”,是在社會財富日漸積累、城市經濟日益繁榮,特別是大量白銀通過走私貿易進入國內市場的形勢下,由多種力量的“合力”所激發的。以御馬監為代表的具有“破壞性”的宦官,被“邊緣化”的中下級賦閑軍官及部分“書吏”,被稱為“亡命罪棍”的地方閑雜人員,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無恒產”者,在皇帝吹響的“集結號”中,結成了松散但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對天下的“有恒產”“有恒心”的“鄉官士民”進行的剝奪。在這個利益共同體中,最高統治者皇帝和最底層市井無賴一樣,幾乎全然沒有行為準則和道德底線,他們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上下互動,最終形成了聲勢浩大向民間掠奪白銀的行動。
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怪異而罕見的現象,其后果也極為嚴重。

①因為大學士沈一貫的奏請,貴州稅監已經委派而未行。
②關于明朝萬歷時期的“礦監稅使”問題,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各地民變,學界有過持續的研究(參見方興:《明代萬歷年間“礦監稅使”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江漢論壇》2014年第2期)。其中,劉志琴教授《試論晚明民變》(《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影響巨大,萬明教授關于海外白銀輸入的系列研究,更有利于揭示問題的本質。這些成果,對本文寫作具有重要啟示。


⑥?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65《礦稅之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12、1013頁。
⑦?《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88冊,《溫恭毅集》卷6《仰體圣明宥過至意懇乞恩憐被逮微臣以光圣德疏》,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519、521頁。
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29冊,《福建通志》卷43《人物·鄭夢禎》,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版,第476頁。

?《明神宗實錄》,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6409頁;《續修四庫全書》卷479《史部·敬事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第322頁。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31冊,《湖廣通志》卷10,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96頁。
????《續修四庫全書》卷467《史部·皇明留臺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629、630、629頁。
?方興:《明朝萬歷年間“礦稅銀兩”的定額與分成》,《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陸容:《菽園雜記》卷2:“京畿民家,羨慕內宮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陸容:《菽園雜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9頁。山東巡撫黃克纘對山東稅監陳增的個人財產進行清算:山東徐州的大小二庫,存有白銀10萬余兩、玉帶等物約值1200兩,另有貓睛寶石等一箱;北直保定府新安縣的老家有大宅一所,貯銀30余萬兩,另有金寶無數;京師有大宅一所,貯銀30余萬兩,玉帶10余條及各色金銀器皿等。黃克纘:《數馬集》卷2《乞籍沒稅監停免採榷疏》,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66頁。
?陳子龍:《明經世文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420頁。
?文秉:《定陵注略》,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12頁。
?《中國地方志集成》,《同治蘇州府志三》卷80《人物七·王禹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頁。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32冊,《湖廣通志》卷43,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