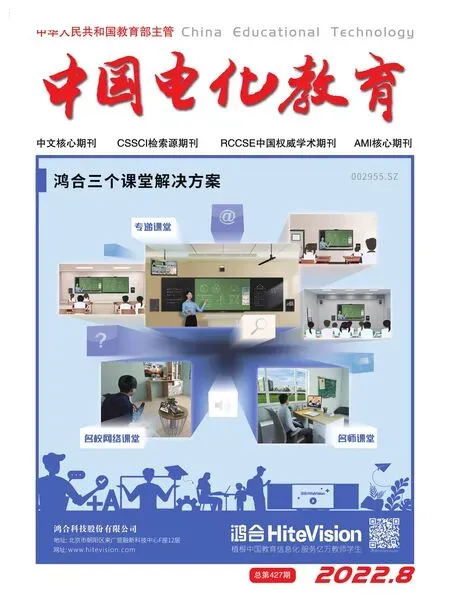數(shù)字教學法:一種數(shù)字時代的教學法及一種教學法的數(shù)字教材 *
郭文革,楊 璐,唐秀忠,李海潮
(1.北京大學 教育學院 教育技術系,北京 100871;2.普洱學院,云南 普洱 665000;3.北京大學第一醫(yī)院,北京 100035)
一、引言:教學法的數(shù)字化變革
2020年的大規(guī)模在線教育實驗,大大加快了全世界教育數(shù)字化轉型的步伐。在“十四五”期間,中國政府和教育部也頒布了一系列文件,推動教育“新基建”工程、啟動關鍵領域新型教材的建設、頒布2022新課程標準等,積極推進中國教育的數(shù)字化轉型。
教學法的數(shù)字化變革是教育數(shù)字化轉型的核心。在教育學的諸門課程中,如果要選一門最具特色的代表性課程,一定是教學法。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經濟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管理學等都是其他學科視角和方法在教育學領域的投射,唯獨教學法,不僅屬于教育學獨門所有,而且還輸出到其他學科,成為所有學科教書育人的一套原則和方法。
《辭海》對教學法的解釋是:實施教學共同遵循的一套原則和“方法”。維基百科“教學法”詞條的解釋是:教學法是學習的理論和實踐。教學過程既影響著社會、政治和學習者的心理發(fā)展;也被社會、政治和學習者的心理發(fā)展所影響[1]。綜合這兩種解釋,從教學的外在環(huán)境來看,教學法受到社會、政治和學生心理狀態(tài)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從教學的內在過程來看,教學法涉及對教學(內容)資源、教學工具的選擇、教學活動的安排,以及對學生學習過程提供反饋與評價等一系列行為。因此,瑞典于默奧大學教育學院前院長大衛(wèi)·漢密爾頓(David Hamilton)提出,教學法“牽涉到一種教育實踐體系的創(chuàng)造”,“大約在1450到1650年間,教學大綱、班級、課程、學科、教學法等一系列詞匯開始出現(xiàn)在歐洲教育詞典上,并逐漸發(fā)展到美國的南北部地區(qū)”,這是現(xiàn)代學校教育的開端[2],它濫觴于15—16世紀的印刷技術變革時期。
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教育實踐體系的外在環(huán)境和內在要素都在發(fā)生變化。無論社會、政治和學生心理等教學的外在生態(tài)環(huán)境;還是資源、教學、平臺和教學活動等教學的內在構成因素,都處于變革之中。在數(shù)字資源、數(shù)字工具和數(shù)字平臺等構成的數(shù)字化教學生態(tài)環(huán)境下,教師應該怎樣選擇資源、工具、平臺和活動等要素,組織教學?學生如何學會以新的方式思考和合作?
針對以上問題,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組織數(shù)百名數(shù)字人文研究者,以Twitter和Github等數(shù)字共享平臺為中介,開展了長期的研究和討論,他們形成了一個共識:“在今天這個數(shù)字化時代,不使用‘數(shù)字教學法’的教師是不負責任的”[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際,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正式以在線出版的方式,發(fā)布了這“部”《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數(shù)字教材[4],不僅帶來了一種新型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內容體系,也展示了一種數(shù)字環(huán)境下新型教學法的“教材”形態(tài)。
二、數(shù)字教學法釋義
關于什么是“數(shù)字教學法”,目前還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定義。但是,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的數(shù)字人文學者們清醒地認識到:數(shù)字教學法不等于教學技術!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Paul Fyfe教授專門撰寫了《“不插電的”數(shù)字教學法》[5]一文,用4個“不插電”的數(shù)字人文教學案例,闡述兩者的區(qū)別。
怎樣理解“數(shù)字教學法”與“教學技術”之間的差別?本文用圖1的四個象限,解釋兩者的不同涵義。

圖1 教學法的四個象限
如前所述,教學法是為了滿足特定生態(tài)環(huán)境下社會對人才的需要,逐漸形成的一套“教學實踐體系”。外部環(huán)境與教學內在的要素和過程,是定義教學法的兩個關鍵要素。圖1以“印刷生態(tài)環(huán)境-數(shù)字生態(tài)環(huán)境”為橫坐標;以“傳統(tǒng)教學法-數(shù)字教學法”為縱坐標,將技術變革過程中的“教學法”分列入4個不同的象限。
其中,象限I為“數(shù)字生態(tài)環(huán)境-數(shù)字教學法”,即采用數(shù)字教學法,培養(yǎng)數(shù)字時代所需要的,具備編程、計算思維能力、人工智能等數(shù)字素養(yǎng)能力的人才。象限II為“印刷生態(tài)環(huán)境-教學技術”,指采用多媒體、網(wǎng)絡等“教學技術”,培養(yǎng)印刷生態(tài)環(huán)境下所需要的,具有書面讀寫算素養(yǎng)的“印刷人”。象限III為“傳統(tǒng)教學法-印刷生態(tài)環(huán)境”,即采用傳統(tǒng)的“班級授課制”教學法,培養(yǎng)印刷環(huán)境下所需要的,具有讀寫算能力的人才。象限IV為“傳統(tǒng)教學法-數(shù)字生態(tài)環(huán)境”,即在傳統(tǒng)課堂教學環(huán)境下,培養(yǎng)數(shù)字時代所需要的具備編程、內容標注、人工智能等素養(yǎng)能力的人才。
四個象限的分析表明,“數(shù)字教學法”與“教學技術”最大的差別在于:前者用數(shù)字技術培養(yǎng)數(shù)字素養(yǎng)(Digital Literacy)能力;后者則是用數(shù)字技術提高傳統(tǒng)教學法的效率或效果,培養(yǎng)具有印刷讀寫素養(yǎng)(Literacy)的人才。
關于數(shù)字素養(yǎng)和印刷素養(yǎng)的差別,數(shù)字人文研究者比其他人更為敏感。人文學科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著為社會和文化發(fā)展制定語法、話語規(guī)則的使命。不僅人與人的社會交往建立在語言、話語交流的基礎上,學術研究和學習也同樣離不開概念、文法和修辭等技藝(Art)。人文學科的英文表述Liberal Arts,指的就是這種通用“技藝”。一個人無論學習哪一門學科的知識,他/她首先都需要學會閱讀,理解文字和概念的意義。所以,當短視頻、可視化表達等大行其道的時候,傳統(tǒng)人文學科的選課學生人數(shù)和資助金額雙雙下滑,學科發(fā)展受到嚴重威脅。2021年奈飛(Netflix)制作并播放了一部6集電視劇《英語系主任(Chair)》就描述了美國人文學科目前面臨的困境。因此,人文學者總是比其他人更早感受到新媒介技術的挑戰(zhàn)。16世紀“印刷技術時代的教育改革先鋒”彼得·拉米斯就是一位人文主義哲學家,他從改革文法、修辭和邏輯等文科課程入手,開啟了印刷時代的教育改革[6]。20世紀末,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崛起,最早討論新型教學法的也是一批人文學者。1994—1995年,來自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的10位人文學者①其中包括游戲化學習之父詹姆斯·保羅·吉(James Paul Gee)。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新倫敦市(New London City)召開研討會,討論新型教學法的問題,他們的討論結果以《一種多元素養(yǎng)教學法:設計社會的未來(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7]為題,發(fā)表在《哈佛大學教育評論》1996年第1期。這是“數(shù)字教學法”領域最早的原創(chuàng)文獻,20多年來引用高達5000多次。
二十多年來,人文學科一直被數(shù)字技術改造,也不斷貢獻著新的修辭和表達方式。隨著大型文獻數(shù)據(jù)庫的建立,數(shù)字人文學者創(chuàng)造了遠讀(Distant Reading)、歷史動力學(Cliodynamics)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圍繞教學的數(shù)字化轉型,也出現(xiàn)了MIT OCW開放課件運動、視頻精品課、開放存期(Open Access)、慕課等大量新的探索。這些變革匯聚在一起,從數(shù)字素養(yǎng)目標、教學的外部生態(tài)環(huán)境、教學法內在的資源、工具和平臺等各個方面,逐漸打造出一種新型的“教育實踐體系”——數(shù)字教學法。
三、《數(shù)字教學法》:新理念和新的數(shù)字出版
教學法雖然是教育學科的核心內容,但它本質上是一個交叉學科研究領域。教學法的研究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教育學科從事教學法研究的專業(yè)人員,他們采用觀察、訪談等研究方法,通過發(fā)表教學法的相關論文和著作,提供“用理論包裝”的二手的、反思性的課程“經驗”。二是各專業(yè)領域的任課教師。這支隊伍人數(shù)眾多,但他們“以學科研究”為主,發(fā)表的教學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少而且不成體系。結果,大量以“實踐”為表征的教學法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未能得到應有的表達和重視。
紙質出版形態(tài)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塑造了傳統(tǒng)教學法的知識體系。期刊論文的篇幅有限,紙質教材則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封閉的、自成體系的內容實體,形成了“重理論、輕實踐”的傳統(tǒng)教學法知識結構。這種“重理論、輕實踐”的傳統(tǒng)教學法教材傾向于告訴教師,好的教學具有哪些共性特征、“你應該怎么做”等一系列原則性內容,但很少提供可直接“再利用”的有效教學實踐“構件”。結果,在全球教育面臨數(shù)字化轉型挑戰(zhàn)時,以傳統(tǒng)教學法為指導的大規(guī)模教師培訓雖然投資巨大,但實際的效果卻是“海市蜃樓”[8]。
數(shù)字技術為大量傳播瑣碎的教學實踐“構件”,重構教學法的知識體系,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工具。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出版的這部《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合集就充分發(fā)揮了數(shù)字技術的優(yōu)勢,將大量來自數(shù)字人文教學實踐的優(yōu)秀案例用“超鏈接”結構組織在一起,放大了“教學實踐”的聲音,突出了教學法的實踐特色。
(一)“數(shù)字教學法”的三個關鍵詞:教學構件、分叉和重混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認為,“好的教學往往來自于改編或借用他人的優(yōu)秀作業(yè)、課堂活動、教學大綱,甚至是講義”[9]。為了落實這一理念,《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提出了三個具有實踐導向的核心概念:教學構件(Pedagogical Artifacts)、分叉(Fork)和重混(Remix)。
教學構件是指一門課程的構成要素,《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提供了24類教學構件,包括數(shù)字教學資源、教學大綱、教學活動、評價、數(shù)字工具等幾大類。借用知識圖譜中“實體”的概念來說,這24類教學構件相當是一個包含24類“實體”的教學法的知識圖譜“元數(shù)據(jù)”,是一組可重用(Reusable)的教學實踐“單元”。教學構件是《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編寫的基本單元,也是分叉和重混的可重用“部件”。
分叉這個術語來自軟件開發(fā)行業(yè),原來指軟件工程師從一個軟件包中獲取源代碼的副本,對其進行獨立二次開發(fā),創(chuàng)建一個新軟件的行為。《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借用“分叉”描述一位教師通過借用或修改另一位教師的教學資源、教學大綱、教學活動、教學評價等“教學構件”,設計自己的課程和教學的行為。
重混的英文單詞是Remix,原意是“混音”,指通過增刪改等操作,對音樂進行編輯的行為。隨著多模態(tài)表達和數(shù)字素養(yǎng)的發(fā)展,重混(Remix)的涵義擴大了,指通過修改現(xiàn)有的網(wǎng)絡多模態(tài)資源,創(chuàng)建新內容的數(shù)字化創(chuàng)作行為。在美國政府資助的“開放教材”項目中,還出現(xiàn)了一種新型的教材編輯器Remixer,可以通過選擇、修改和重組開放教學資源,編輯形成一本新教材或者創(chuàng)建一門新課程。《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用“重混”這一概念,表達以“教學構件”為基礎的,可重用的、“迭代式”的課程設計和創(chuàng)新理念。
教學構件、分叉和重混這三個核心概念,即體現(xiàn)了數(shù)字生態(tài)環(huán)境所具有的開放、協(xié)作、自由探索、實踐、學生自主性和個人身份等特征,同時也是落實“數(shù)字教學法”這六大特征的具體策略。
(二)建構數(shù)字出版的學術基礎設施
從以概念、原則為主的教學法紙質教材,到支持“教學構件”分叉和重混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轉型,不僅是對傳統(tǒng)教學法理念的變革,同時也是對教材編寫、出版“范式”的數(shù)字化變革。如何把豐富的“教學構件”組織在一起,形成一種教師可以分叉、重混使用的新型教學法數(shù)字教材?這不是簡單地把紙版教材、教學視頻等搬到網(wǎng)上的問題,它依賴一套全新的數(shù)字出版“學術基礎設施”的支持。
1.公開、協(xié)作的開放編輯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數(shù)字教材采用了開放編輯、公開評審的寫作方式;最后成果在網(wǎng)上以數(shù)字形態(tài)出版,免費提供給社會公眾。不僅提供了一種新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知識體系”,也帶來了一種新型的教學法“教材”形態(tài)。
編寫《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想法是在2010年提出的,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的數(shù)字人文學者們最初利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網(wǎng)絡開展關于“數(shù)字教學法”的對話。2014年正式立項,決定編寫這部《數(shù)字教學法》合集。2014—2020年的六年間,項目團隊使用開源平臺Github作為開放編輯、公開評審的工具。Github是一個開源共享平臺,所有人都可以訪問,因此,這部《數(shù)字教學法》合集在編寫的過程中,就已經得到大量使用,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這部開放、大規(guī)模協(xié)作編寫的《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合集的作者人數(shù)近800人,包括:4位編輯、84位關鍵詞策劃人,以及700多位來自計算機、數(shù)字人文、數(shù)字修辭、數(shù)字古典學、語言學、媒體研究、藝術、音樂、地理學、在線教學、開放教育和歷史等領域的學者,為這部合集貢獻了573個“教學構件”優(yōu)秀案例,建成了一個人文學科教師可分叉、重混使用的“教學工具箱”[10]。
2.創(chuàng)建數(shù)字教材出版的基礎設施
要把573個優(yōu)秀的“教學構件”組織成一個數(shù)字教學法新型教材,就必須探索新的教材組織結構和出版形態(tài)。為此,美國現(xiàn)代語言學會聘請多模態(tài)新型學術出版專家凱瑟琳·菲茨帕特里克(Kathleen Fitzpatrick)擔任項目顧問。凱瑟琳·菲茨帕特里克是《計劃過時:出版、技術和學術的未來(Planned Obsolescence: Publishing,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Academy)》[11]一書的作者,也是MediaCommons①MediaCommons是一個由圖書未來研究所、紐約大學和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共同支持創(chuàng)辦的全電子學術出版網(wǎng)絡。網(wǎng)址為: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diaCommons。的共同發(fā)起人之一。
在菲茨帕特里克的指導下,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創(chuàng)辦了Humanities Commons平臺,為19,000多位數(shù)字人文學者提供了一個開源的服務網(wǎng)絡;并利用代碼共享網(wǎng)站Github作為協(xié)作編輯平臺;還為“關鍵詞”設計了Markdown寫作模板;最后,創(chuàng)辦了一個WordPress網(wǎng)站,作為內容公開評審和發(fā)布的平臺。
3.版權許可與永久訪問
教材作為一種特定出版物,必須要保證所有內容的穩(wěn)定、永久可訪問性。紙質教材的穩(wěn)定、永久可訪問性是依靠讀者對圖書的“物理”占有來保證的。網(wǎng)絡教材的穩(wěn)定、永久可訪問性還缺乏有效的保障機制。早年學術期刊曾禁止引用網(wǎng)絡文獻,原因就是很多文獻在1年、2年后就無法訪問,甚至有4年后失蹤60%的極端情況[12]。現(xiàn)在,通過建立大型論文數(shù)據(jù)庫等措施,期刊引用的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當教材變成網(wǎng)上的數(shù)字出版物時,如何保證一個網(wǎng)頁超鏈接合集的穩(wěn)定、永久可訪問性?這是教材的數(shù)字出版面臨的一大難題,也是數(shù)字出版業(yè)急需解決的問題。MediaCommons、Creative Commons(知識共享)等公共平臺的創(chuàng)辦就是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并打造出一個全新的數(shù)字出版生態(tài)體系。
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為《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出版創(chuàng)建了Humanities Commons平臺,他們努力從教師那里取得每一個“教學構件”的許可權,把它們保存到Humanities Commons存儲庫中,以保證這部數(shù)字教材的穩(wěn)定的、永久可訪問性。
4.保護“教學構件”創(chuàng)作者的著作權
重混使用其他老師的教學資源、教學大綱、教學活動、教學評價等“教學構件”,對于借用者來說無疑是一件省時省力的事情。但是,如果沒有一套機制,認可并獎勵創(chuàng)作者的貢獻,就會出現(xiàn)“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最后大家都無法獲得優(yōu)質的“教學構件”。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自2011年以來,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數(shù)字人文研究者創(chuàng)建了多個開放獲取(Open Access)的在線期刊,專門刊登教學大綱、教學活動等“教學構件”類短文章。例如:2011年創(chuàng)辦的Hybrid Pedagogy;2012年首次出版的The Journal of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Pedagogy;2010—2012年出版的The Journal for Undergraduate Multimedia Projects;2016年出版的Prompt: A Journal of Academic Writing Assignments等。這些開放存取的在線期刊,大多數(shù)文章在2—6頁之間,簡潔明了地介紹一個作業(yè)的設計思路等。
開放存取期刊為“教學構件”提供了發(fā)表的空間,教師可以以署名引用的方式分叉、重混這些“教學構件”,使這些來自實踐者的教學創(chuàng)新,不斷得到“迭代”和完善,從而積累形成了一個高質量的“教學構件工具箱”,推動了數(shù)字教學法的高水平發(fā)展。
“教學構件”工具箱中還包含一些綜合性專題教學資源網(wǎng)站,例如,美國歷史協(xié)會建立的歷史教學的綜合資源網(wǎng)站: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Classroom Materials” Repository①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lassroom Materials” repository。網(wǎng)址為:https://www.historians.org/teaching-and-learning/teachingresources-for-historians/classroom-materials。,就是一個美國歷史教師的“教學工具箱”,其中包括史料、教學大綱、教學活動、可視化表達工具等各類可重復使用的“教學構件”資源。
(三)“數(shù)字教學法”的內容編排:關鍵詞方法
很多人習慣認為,教材自古以來就是以印刷教材的章節(jié)結構來編排的,其實不然。教材作為一種表征和傳承知識的媒介,其形態(tài)是隨著媒介技術的演變而變化的[13]。在荷馬史詩的時代,所有的知識和思想都是用口傳吟誦詩歌的方式“唱”出來的;在中世紀“半口語+半書寫”的傳播環(huán)境下,古蘭經、印度科學著作[14]、英格蘭諾曼人的“十進制”書[15]等都采用押韻詩歌的寫作文體。15世紀中葉古登堡印刷機發(fā)明以后,一直到16世紀中期,法國人文主義哲學家彼得·拉米斯才提出了今天印刷教材編排的“拉米斯教材范式”[16]。18世紀普魯士人推行強制義務教育之后,“拉米斯范式”的印刷教材才逐漸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大面積的推廣和應用。
20世紀末萬維網(wǎng)出現(xiàn)以來,學術界、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出版業(yè)一直在探索新的教材形態(tài)和內容組織方法。“關鍵詞方法(Keyword Approach)”就是近年涌現(xiàn)出來的一種新的內容組織方法。以“關鍵詞”作為一種圖書寫作形態(tài)始自于1976年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著作《關鍵詞:文化與社會詞匯》。進入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以后,“關鍵詞”發(fā)展成為一種組織大量素材的“元數(shù)據(jù)”結構。1995年創(chuàng)建的“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在線出版物,采用了“關鍵詞”的組織結構。2001年創(chuàng)立的“維基百科”,也采用了“關鍵詞”的內容組織方式。這種“內嵌超鏈接”的“關鍵詞”結構,一方面為大容量、不斷更新的內容提供了可擴展的組織結構;另一方面,也為“讀者”提供了多種閱讀入口和訪問路徑。
經過廣泛的調研和分析后,《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編輯決定采用“關鍵詞”超鏈接結構,把573個“教學構件”編織在一起,形成“數(shù)字教學法”的“整體概念圖(A Holistic Conceptual Map)”。而確定“關鍵詞”的過程,就是建構“數(shù)字教學法”理念和知識體系的過程。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關鍵詞”的選擇經歷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多次迭代。既有從理論角度的考慮,也受到可行性的制約。一些熱門的關鍵詞,如慕課(MOOC)②關于放棄“慕課”這個關鍵詞,教材介紹中有一句很獨特的解釋:“MOOC給高等教育帶來的危機已基本過去”。和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經討論沒有收入本書的關鍵詞表。而個別編輯們認為非常重要的“關鍵詞”,因為找不到合適的策劃人也只好暫時放棄。最終,經過6輪爭論和妥協(xié)之后,確定了現(xiàn)在的59個關鍵詞,如表1所示。這些關鍵詞涉及傳統(tǒng)人文學科、數(shù)字人文、教學法、社會公平及文化多樣性等多個方面。

表1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關鍵詞③表1按照本文作者的理解,把這59個“關鍵詞”分成了5類,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清晰地呈現(xiàn)“關鍵詞”的大致結構,原文在一張圖中采用了5種不同顏色表示這59種關鍵詞,但并沒有說明每一種色彩的涵義。本文的5種分類略作調整。
這個“關鍵詞”組織結構反映了美國現(xiàn)代語言學會的數(shù)字人文研究者們對于不斷變化的“數(shù)字教學法”現(xiàn)狀的一種理解和總結,未來可能還會擴展、調整等。
為了保證內容的一致性,也為了質量審核的需要,《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為84位“關鍵詞”策劃人(Curator)提供了“關鍵詞”寫作模板。模板包括7項內容:關鍵詞、策劃人、關鍵詞說明、10個教學構件、相關資料、參考文獻和相關關鍵詞。“關鍵詞說明”是對特定關鍵詞的理論描述,“相關資料”則介紹了與該“關鍵詞”相關的項目和行業(yè)標準等,“參考文獻”則介紹了更多的研究文獻,10個“教學構件”是與該“關鍵詞”相關的優(yōu)秀教學實踐案例。
“教學構件”是這部“數(shù)字教學法”的核心要素,也是凸顯教學法的“實踐性”導向,實現(xiàn)分叉、重混的核心單元。這部數(shù)字教材共提供了24類教學構件,如表2所示。

表2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24類“教學構件”
鑒于“教學構件”在教學法中的核心作用,編輯要求每一個關鍵詞的策劃人要為每一個“教學構件”提供三方面的描述信息:(1)簡要說明該“教學構件”的目的或用途;(2)說明其與關鍵字的相關性;(3)使用指南。
每個“教學構件”還要提供6項元數(shù)據(jù)標簽:作者、關鍵詞、教學構件類別、標簽、源網(wǎng)頁鏈接和Humanities Commons版權信息。其中,關鍵詞、教學構件和標簽,提供了3種“教學構件”的元數(shù)據(jù)標注和查詢方式,其余3項是超鏈接,可以訪問作者、原始資源,以及Humanities Commons版權庫中詳細的原始資料等拓展資源。
就這樣,由59個關鍵詞、10個“教學構件”、24類“教學構件”、79種標簽、以及相關資料、參考文獻、源網(wǎng)頁鏈接和HC版權鏈接等,構成了如圖2所示的《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數(shù)字教材的內容結構。

圖2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內容結構
這部在線出版的《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數(shù)字教材,整合了大批與數(shù)字人文和數(shù)字教學法有關的研究文獻、資源網(wǎng)站、數(shù)字分析工具、可視化表達工具等資源,形成了內容豐富、面向實踐、供一線教師分叉、重混使用的數(shù)字教學法“工具箱”。無論容量還是結構,都已經很難再“裝進”傳統(tǒng)的印刷教材了。
(四)如何使用《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數(shù)字教材
打開這部“數(shù)字教材”,首頁如下頁圖3所示,上圖是一段簡短的文字說明,鼠標向下滾動,就出現(xiàn)了下圖所示從A-Z配列的59個關鍵詞。首頁的右上角有一組菜單,最后是一個查詢按鈕。

圖3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首頁
這部以“關鍵詞”為超鏈接結構組織起來的數(shù)字教材,顯然不可能像傳統(tǒng)教材那樣“拿”起來,“一頁一頁”細讀(Close Reading),讀者甚至不可能“窮盡地讀遍”這部數(shù)字教材的每一個頁面、每一個字!研究團隊花了半年多時間,分析這部新型的《數(shù)字教學法》教材。一方面,解析這部新型數(shù)字教材的設計思想、內容結構;另一方面,也在探索這種新型教材的“閱讀”方法和使用方式。總結來看,這部“數(shù)字教材”有三種“閱讀”方式。
1.遠讀
“遠讀”是斯坦福大學佛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教授提出的一種文學研究方法[17]。“遠讀”一改傳統(tǒng)文學研究中聚焦深度閱讀(Close Reading)少量代表性作品的分析方法,轉而采用大數(shù)據(jù)分析的方法,對大型的文學數(shù)據(jù)庫進行宏觀的、結構化的分析。
研究團隊采用遠讀(Distant Reading)的方式,通過反復通讀“介紹(Introduction)”,以及選擇瀏覽“關鍵詞”的方式,了解這部數(shù)字教材背后的故事、梳理這部新型數(shù)字教材的內容組織結構,研究這部數(shù)字教材的組織結構和編輯方法。
2.選擇性“細讀”
為了進一步了解《數(shù)字教學法》的新理念和“教學構件”,研究團隊選擇了Play、Gaming、Future、ePortfolio、Failure等40多個關鍵詞,詳細閱讀“關鍵詞”說明;選擇了200—300多個“教學構件”,進行深度“細讀”,研究這部《數(shù)字教學法》的理念和內涵,還大量瀏覽了《數(shù)字教學法》鏈接的相關資料、參考文獻、源網(wǎng)頁鏈接等,感受這部《數(shù)字教學法》的外圍拓展資源形態(tài)。數(shù)字教材鏈接的資源,經過了精心的篩選,質量高、涉及面廣,是關于數(shù)字人文研究和數(shù)字教學法的優(yōu)質資源。
3.分叉、重混使用這個“教學工具箱”中的教學構件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為教師提供了4種查找和訪問“教學構件”的途徑:(1)以“關鍵詞”為線索,查詢和閱讀與特定主題相關的教學構件。(2)以“教學構件”的24種類型為線索,查詢教材中的教學大綱、學習活動等特定類型的“教學構件”,例如,數(shù)字教材中有78個教學大綱(Syllabus)案例;182個作業(yè)(Assignment)設計案例;26個項目(Project)設計案例;25項學生創(chuàng)意作業(yè)(Student Work)案例等。(3)以“標簽”為線索查詢相關的“教學構件”。例如,有67個教學構件與支架(Scaffolded)有關;143個案例涉及到數(shù)據(jù)分析或可視化表達工具(Tool);有132個供新手教師使用的入門級(Getting Started)教學構件。(4)用主頁右上角的“全文檢索功能”,查詢相關的概念、數(shù)字資源和教學構件等。
多種途徑的查詢、閱讀方式,為分叉、重混使用“教學工具箱”中的“教學構件”,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例如:
(1)分叉/重混“教學大綱”,助力數(shù)字素養(yǎng)課程建設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作者主要是數(shù)字人文研究者,這部合集的“教學大綱”案例中,有40—50門數(shù)字人文課程的教學大綱“構件”,包括數(shù)字人文導論、技術與文化、數(shù)字修辭學、數(shù)字論理及批判性思維,數(shù)字修辭等幾大類,還有數(shù)字修辭跟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課程,如《遠讀19世紀文化》、數(shù)字歷史學、數(shù)字地圖與地理空間人文、音樂地圖等。其中不乏MIT、斯坦福、多倫多大學、哥倫比亞等世界一流大學的數(shù)字人文課程,對于推動中國新文科建設、以及開發(fā)數(shù)字素養(yǎng)、交叉學科課程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其中一些課程本身就是重混的成果。例如,斯坦福大學的一門討論《數(shù)字版權》課程的教學大綱,就在顯著位置標注著“this syllabus remixes”和“remix assignments”①FILMSTUD156/356 Copy This Class (The Art of the Remix。網(wǎng)址為:https://hcommons.org/deposits/objects/hc:31212/datastreams/CONTENT/content。,表明這門課程重混了其他3門課程的教學大綱和其他4個作業(yè)設計。
(2)創(chuàng)意作業(yè)的分叉/重混
在教學實踐中,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培養(yǎng)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抓手就是作業(yè)(Assignments)設計。《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提供了大量可供分叉、重混的創(chuàng)意作業(yè)和項目任務。例如,“在泥板上書寫”“制作圖書”“用元數(shù)據(jù)標注一本印刷書,將其變成一種XML格式網(wǎng)絡內容”等學習任務案例,還有大量的海報制作、聲音剪輯、策劃展覽、制作歷史地圖、制作可視化歷史資料等數(shù)字修辭的創(chuàng)意“寫作”任務,都是可以“拿來”重混的優(yōu)秀作業(yè)和PBL設計案例。
(3)教學評價工具的分叉、重混
這部數(shù)字教材還提供了大量行業(yè)標準、規(guī)范和評價工具,例如,數(shù)字素養(yǎng)標準、團隊合作評價量表、《電子檔案袋的原則和實踐》等工作文檔,為設計針對學生的評價、針對教師專業(yè)發(fā)展評價等,提供可以“拿來”重混的評價工具。
四、《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的啟示
《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在2020年獲得美國數(shù)字人文領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最佳實踐”獎勵。2022年獲得加拿大社會知識研究所頒發(fā)的“開放學術獎(榮譽提名)”,對于推廣數(shù)字教學法、創(chuàng)新“數(shù)字教材出版范式”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對于中國教育的數(shù)字化轉型、新型教材開發(fā)和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對解決教學法理論與實踐矛盾的啟示
教學法理論研究和一線教學實踐之間的關系,有點像基礎醫(yī)學和臨床醫(yī)學的關系。基礎理論知識是一種條塊分割的體系,你專修教育哲學、我專修教育心理學、社會學等,強調專業(yè)深度;教學實踐是一種綜合性、復雜的知識系統(tǒng),不能有明顯的短板,哪一個方面處理不好,都可能出現(xiàn)教學事故。它們實際上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知識體系。
傳統(tǒng)教師教育主要采納“理論指導實踐”的路徑,中外皆然。在面臨互聯(lián)網(wǎng)挑戰(zhàn)的時候,以傳統(tǒng)教學法理論指導教學數(shù)字化變革,實際的結果就是美國那份研究報告的結論“海市蜃樓”。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新課程改革的推行,中國教師培訓也經歷了從專家講授、遠程大規(guī)模教師培訓、“國培計劃”、名師工作室、翻轉課堂、PBL教學、作業(yè)設計、大概念單元教學設計、教學聯(lián)盟、智能教改示范區(qū)、智能優(yōu)秀教學案例征集等多方面的探索,整體呈現(xiàn)出從“理論指導實踐”到“(優(yōu)秀)實踐指導實踐”探索路徑。“實踐指導實踐”的抓手,就是優(yōu)秀的“教學構件”。舉一個例子,哈佛大學視頻公開課《公正:該如何做才好》那個堪稱經典的引入——電車難題,就不是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教授的“原創(chuàng)”,它來自倫理學中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已經有了4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多位學者的不斷完善。
2022年新課程標準已經頒布,在新一輪新課程改革中,如果能夠參考《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搜集一批整合了優(yōu)秀數(shù)字資源、數(shù)字工具、數(shù)字平臺的優(yōu)秀“教學構件”,建立一個國家級的“數(shù)字教學法工具箱”,支持中小學教師通過“改編或借用他人的優(yōu)秀作業(yè)、課堂活動、教學大綱,甚至是講義”等來改進教學,無疑會快速推進中國教育的數(shù)字化轉型,提高新課程改革的質量。
(二)建立數(shù)字教材發(fā)展的基礎設施
進入21世紀以來,“優(yōu)質教育資源共享”一直是指導中國教育信息化發(fā)展的基本理念。從2003年第一批“新世紀網(wǎng)絡”課程建設開始,教育部先后啟動了國家精品課程建設、網(wǎng)絡開放課程建設、慕課、微課等建設項目,積累了豐富的數(shù)字化教學資源。
現(xiàn)在,隨著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分析技術的發(fā)展,世界教育信息化的發(fā)展進入深水區(qū)。在人工智能、病毒學等前沿學科領域,知識增長速度不斷加快、開源平臺、開源代碼、開源數(shù)據(jù)集、大數(shù)據(jù)分析工具等不斷增長,正在徹底改變整個人才培養(yǎng)的基礎設施環(huán)境。
進入“十四五”以來,國務院發(fā)文推動數(shù)字“新基建”的發(fā)展,教育部提出要建設“教育新基建”;高教司啟動了“新興領域教材研究與實踐項目”,在四個前沿學科領域探索新型教材模式和新的人才培養(yǎng)。盤點“存貨”,發(fā)現(xiàn)中國教育信息化發(fā)展積累了豐富的、優(yōu)質視頻教學資源,但是對于數(shù)字出版基礎設施、對教學資源的分類、元數(shù)據(jù)標注等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這是教育新基建的核心樞紐工程[18]。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文學科中的數(shù)字教學法》利用Humanities Commons、Github、Markdown和WordPress搭建的數(shù)字出版基礎設施;以“關鍵詞”建立的可擴展的內容組織結構;通過59個關鍵詞、24類教學構件、79種標簽等建立的元數(shù)據(jù)標注體系等,都值得深入思考、研究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