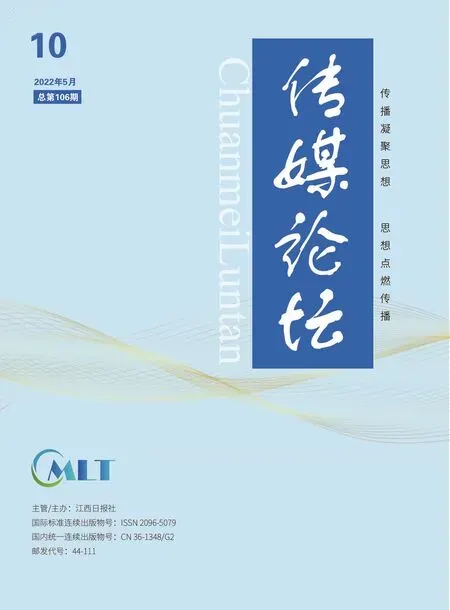風格·對抗·博弈:亞文化視角下的電子競技研究
陳奕瑾
一、文獻綜述
步入新媒介時代的電競文化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煥發出新的存在狀態和傳播路徑。電競頻頻“破圈”,“飯圈粉絲”的涌入,電競選手們成為電競圈里的“意見領袖”,甚至成為“明星”,這些現象都是以往研究未能解釋的問題。 而亞文化這一研究視角為能夠為我們研究這一現象提供一種新路徑。
學界對青年亞文化的研究的線索基本是從芝加哥學派到伯明翰學派再到后亞文化研究。 芝加哥學派領軍人物之一阿爾伯特·科恩(Albert K. Cohen)提出“問題理論”,認為:美國下層青少年由于被主流社會邊緣化而感到了“地位挫敗”,因而采用越軌、犯罪等方式解決問題,由此形成的亞文化就是他們對上層社會的反叛回應。伯明翰學派認為,主流文化或商業文化對亞文化會采取收編的態度,亞文化風格一旦被商業所利用,它必然會變得“僵化”喪失鋒芒,而喪失鋒芒的結果是亞文化削弱或消弭對各種霸權的抵抗力量。20世紀末21世紀初,西方亞文化研究界出現“后亞文化”思潮。后亞文化學者提出了諸如“亞文化資本”“部落”“場景”等新語匯,展現了全球性消費模式下新興亞文化群體的身份表現行為與混雜風格。青年亞文化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十分豐富龐雜,而最能幫助我們厘清如今電競文化發展新態勢的是桑頓所提出的“亞文化資本”這一概念。
英國學者薩拉·桑頓針對后現代的青年亞文化現象,通過對英國俱樂部文化等的分析,在《俱樂部文化:音樂、媒介和亞文化資本》一書中首次提出了“亞文化資本”這一概念。俱樂部文化的“酷樣”時尚被其看作趣味文化,形成基于青年群體對音樂的共同趣味和媒體消費的亞文化集合,并且將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環繞在對亞文化資本的分析中。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亞文化資本被賦予擁有者一定的地位,實現身份的象征,通過客體化、亞文化元素的收集配置來消費和占有亞文化資本符號,最終建立自身的價值與社會認同。
在新媒介語境下,傳統被動的受眾轉變為主動的生產式受眾,媒介文本轉向開放多義,亞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亞文化資本價值更加凸顯。有研究者基于網絡游戲主播的考察關注到注意力經濟的形成,并發現亞文化群體憑借新媒體平臺獲得在主流社會結構中的流動和社會資本,特別表現為通過流量變現向經濟資本和商業資本的轉換。 然而亞文化資本除了在擴大自身的價值和身份認同之外,是否與其他圈層的文化產生交集、相互影響層面是尚未被觸及的。因此,本文將以“亞文化資本” 概念探究考察電子競技亞文化生產過程中多個圈層文化的交融與碰撞。
二、電子競技的亞文化資本邏輯
在《俱樂部文化》一書中,桑頓認為俱樂部的流行邏輯是“酷樣”(hipness),“酷樣”構建出的區隔,賦予青少年群體文化權利的意義。“亞文化意識形態是一種手段,年輕人通過這種手段想象他們和其他的社會群體,堅持他們的獨特個性,確保他們不是蕓蕓眾生里的無名之輩。”
在互聯網時代,青年亞文化產生了新的變化: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賦予青年人未曾擁有的權力,從而獲得文化符號生產的巨大可能。在網絡上,他們可以運用技術構建起種種壁壘,形成一個又一個的“文化圈子”,呈現出“新部落化”的存在樣態。這樣一個個的“圈子”構成了不同青年亞文化類型之間的區隔和界限。
如今,青年亞文化的這類文化實踐刻意形成的區隔更體現在了語言符號層面上。在本文考察的電競文化中,可以發現這個群體有自己專屬的語匯系統,他們將游戲里的詞匯與現實生活中的詞匯進行“拼貼”“同構”,生產出大量的語匯,如“藍領野”“工具人中單”(指法師和打野不吃經濟,把經濟讓出來);“rush主宰”(指靠高輸出快速拿下主宰)等。正如《俱樂部文化》中談論的那樣,盡管大部分俱樂部成員之間實際共享著關于音樂和舞蹈的喜厭、意義和價值,并在整個構建過程中不斷強調著自身與普通愛好者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分非常重要,正如布爾迪厄對于“品味”的討論,背后實際上對應著個人在亞文化群體結構內的位置。位于結構上層的成員,在本文中即傳統的電競圈粉絲,往往是“酷”(hip)的,即他們認為自己是區別于普通愛好者的,是更為專業,更具有“品味”的群體;位于結構下層的普通愛好者,如因為電競影響力擴大而被吸引來的飯圈粉絲等,往往是“不太懂酷的”(confusing coolness),他們則被看作是普通愛好者,是不懂行的。電競圈的這套語匯,不僅使電競群體和其他的亞文化群體區別開來,同時,也將這個群體中的個體緊密地凝聚在一起。
其次,薩拉·桑頓提出的“亞文化資本”一詞,將媒介的考察放在首要位置。桑頓認為“媒介不僅僅是另一個象征性商品或區隔的標志著,而是一個對定義和傳播文化知識至關重要的網絡”。在亞文化發展過程中,小眾媒體的作用不可或缺。雖然互聯網是開放互通的,但是每個群體都有自己默認的“群體領地”。傳統的電競圈粉絲大多聚集在虎撲論壇、百度貼吧等應用程序上,關注的重點也大多聚集在比賽賽事、選手操作等方面。同時,傳統電競粉絲渴望實現自我正名,在虎撲論壇LOL板塊中,電競用戶經常在發帖時將電子競技與傳統體育賽事相比較。 飯圈粉絲作為這類文化活動的“迷狂者”大多集中在微博上,這類粉絲為不同戰隊、選手都建立了“超話”(微博平臺中的超級話題,擁有共同興趣的人集合在一起形成的圈子),在“超話”中,更多地將選手當做明星或偶像,飯圈粉絲的這種做法不符合傳統電競粉絲作為游戲玩家和賽事觀眾的身份認知。 兩種類型的粉絲在不同的社交平臺上共同塑造著電競亞文化。
三、研究設計
“王者榮耀”是騰訊游戲開發的一款MOBA類國產手游,自2015年上線以來風靡整個游戲市場。2021王者榮耀年全球收入超過28億美元,在全球手游暢銷榜上位列第一。而由“王者榮耀”這款游戲衍生出的王者榮耀職業聯賽(KPL)首屆觀賽人次就已突破3.5億,目前總賽事觀看量超250億;KPL這一話題在微博也擁有高達40.4億的閱讀量。選取這樣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比賽,對我們研究紛電子競技亞文化具有積極意義。
本文學習粉絲文化學者詹金斯的研究方法,采取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方法,參與式觀察強調以參與者身份深入個體生活和社群交往的日常情境,細致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文化環境以及環境對他們的態度、行為的影響,深度訪談則以直接對話的方式捕捉研究對象的自我表述和體驗,筆者自2019年起陸續加入電子競技選手或戰隊的豆瓣小組和超話,浸入電子競技粉群內部長達3年,這為筆者既以粉絲身份參與粉絲實地運作又以研究者身份思考提供便利。其次,年輕用戶是電子競技的主要受眾,作為電子競技的資深受眾以及電競文化的主要消費者,考察年輕人對現如今電子競技圈環境的認知對這個行業的良性發展有積極意義。

表1 訪談對象基本信息表
因此,本文按照研究問題預先設計采訪提綱,對在社交媒體中經常參與電子競技話題內容的十位豆瓣小組、百度貼吧成員進行深度訪談,以半結構式的問題方式深入了解該群體的心理態度。同時,研究者根據訪談內容,訪談者關注電子競技的核心,是否為電競選手刷禮物、買周邊等行為對訪談對象進行了分類。
四、研究結論
(一)酷樣:風格的體現與圈層的區隔
在研究者的訪談中,傳統電競粉與飯圈粉絲在具體的電競實踐中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導向。 傳統電競粉絲關注的核心在于技術、個人。而飯圈粉絲的注意力則更多放在選手身上。比如,在消費與電競有關的產品時,傳統電競粉絲幾乎不會購買與賽事無關的產品和服務,“選手直播我沒刷過禮物,去年11月的時候買了票去上海KPL電競中心看了比賽”(訪談對象2),而飯圈粉絲更多會為選手買單,在與選手個人有緊密聯系的事物上進行消費,“我買過俱樂部官方的周邊,隊服、立牌,選手的推廣也買過”(訪談對象3),訪談對象1、4、5在訪談中也提到在選手直播時會刷禮物。其次,雖然傳統電競粉絲和飯圈粉絲都會觀看自己關注的選手直播,但傳統電競粉是出于娛樂、學技術的目的:“選手直播的話,有時候會看幾個小時,有時候中途就會自己去開兩把,然后就不看直播了,因為看直播過程中會忍不住自己想去打兩把游戲”(訪談對象7);“自己喜歡的選手直播的話就看自己的現實情況,看也不會看太久,覺得有點浪費時間”(訪談對象10)。而飯圈粉絲為了支持自己喜愛的選手往往會看完全程,訪談中有3位提到了選手播多久自己就會看多久,“喜歡的選手只要直播就會看,會看到他下播”(訪談對象4)。再者,從粉絲行為來看,傳統電競粉絲的活動往往比較個人化,是原子式的。 這意味著他們的主要實踐是線上或線下看比賽、觀看喜歡的選手直播等,而這些活動大多是自發的個人行為,相對缺乏組織性和統一性。“我追KPL是自己solo追的,而且不加任何專組,不和任何人互粉,在豆瓣和微博都是solo,微博也只是關注戰隊和選手兩個微博,我除了看游戲和他直播之外,很少關注他”(訪談對象7)。飯圈粉絲則不是松散的,而是高度組織化的,甚至出現某一選手的后援會,其中還設立所謂的“后援會會長”這樣的管理人員。
鑒于以上的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我們可以得出: 傳統電競粉將比賽作為關注的核心,比賽表現是衡量選手最重要的標準,并且以個人化、原子式的行為支持者電子競技。而飯圈粉絲有很大一部分是云玩家、過分維護選手,花費大量金錢來支持選手個人而不是比賽本身。
但是在訪談中出現了一個極為有趣且值得關注的現象: 即訪談對象的自我身份認知和其自身具體的電競實踐出現了錯位。 人們對自我身份的認知首先來自自我的社會實踐,傳統電競粉的電競本應對應著:以比賽成績為導向、以關注賽事而非選手為核心。然而在10位訪談對象中,除訪談對象3、8外,其余訪談對象雖都認為自己屬于傳統的電競粉絲,但在他們具體的電競實踐中,只有訪談對象2、7沒有購買周邊或者為選手刷禮物的行為,其他的訪談對象都存在購買戰隊周邊、為選手應援的行為。在筆者追問到,是否會覺得自己的這種行為更偏向飯圈,有悖于傳統電競粉絲的行為時,訪談對象6曾說“我覺得他們直播獲得收益不是很正常嗎? 建議別什么都扯到飯圈”。這種自我身份感知與具體的電競實踐不一致,甚至認為研究者是在用飯圈的帽子對其只是支持喜愛的選手的行為進行污名化。 傳統電競粉絲和飯圈粉絲的邊界由此變得模糊不清。在訪談中,這些認為自己是傳統電競粉的人不斷強調著自身與飯圈粉絲的區別,盡管他們的電競實踐與飯圈粉絲的電競實踐是難以區分、相對混雜的,但是這類人仍然不愿意將自己歸到飯圈粉絲的行列,始終想要保持自己的“品位”,體現著自己的“酷”,將自己與其他圈層的粉絲區隔開來。
在電競亞文化圈中構建起的“酷樣”在兩個圈層中樹立起了壁壘,形成了隔閡,進而上升為亞文化群體權力的爭奪,帶來兩個群體間矛盾的加劇。
(二)圈層對立:兩個圈層粉絲矛盾的激化
疫情之下,傳統體育賽事受到重創。而電子競技逆勢而上,憑借天然的線上優勢,收獲眾多關注,而電子競技的“出圈”必然會改變原有大環境。在談及現在的電競圈和以往相比有什么變化時,10名訪談對象中9位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現在飯圈粉絲過多的涌入,使得傳統電競粉也被迫卷入飯圈混戰的風險之中。 飯圈文化對于電競圈的滲透,可能使原本客觀談論賽事,單純批評選手操作被大量“控評”“互噴”所占據,進而偏離傳統電競粉的初心。飯圈文化很容易傾向一元思維和群體極化,它對于電競圈的滲透和圍攻,漸漸引發了傳統電競粉絲群體的抵牾,兩個圈層之間的矛盾不停激化。
在訪談中大多數訪談者用極低的評價來評價飯圈且透露出對飯圈厭惡:
“我很不喜歡飯圈的粉絲互掐,尤其是同隊兩個選手的分析互掐,我覺得影響觀感,因為就算粉絲再怎么掐,選手們該在一起打游戲還是在一起打游戲,所以我覺得這種吵就是浪費時間。”(訪談對象1)
“我覺得現在電競圈跟追星差不多了,吵架太多了,看都看累了。”(訪談對象3)
從他們的話語中可以看出,飯圈粉絲秉承“我喜歡的選手就算輸了也不是他的原因”等思維,立場先行,讓本該以成績作為核心評判標準的電競圈陷入人身攻擊的混戰中。
電子競技亞文化作為一種主流文化之下的次生文化,所追尋的是小眾且邊緣的文化品格,但同時對被認同又極其渴望。飯圈粉絲的融入,使得越來越多的大眾能夠知悉了解電子競技亞文化,并且在某些實踐中展現出了積極融入主流社會的面貌。 比如飯圈粉絲會產出選手賽場高光剪輯、美圖、手幅等,這種形式對于不懂電子競技的人來說無疑是更具有吸引力的。 正如訪談對象7提到“我大學同學就是因為顏值、剪輯和一些美圖被吸引入圈,當然可以見得這個圈子吸引進來的新粉,很多都是像他這樣的”。在新媒體時代,信息爆炸使得亞文化資本的價值不僅僅在于亞文化圈,而是通過資本的流動,亞文化群體也獲得了在主流社會結構中流動的可能。 比如作為電競亞文化圈的核心群體傳統電競粉在分享、傳播有關電子競技的內容時更多傾向于在小眾媒體上,構建屬于自己的群體,他們不產出不應援,僅僅是集中在個人的技術層面,而飯圈粉絲的美圖、剪輯、使得亞文化群體暴露在大眾面前。因此,傳統電競粉難以實現話語權的壟斷,帶來了廣泛的關于“正統”的競爭,區分也就變得更有價值。
傳統電競粉通過區分不僅劃清亞文化群體與非亞文化群體的界限,也更是通過區分來構建亞文化內部的秩序。即使是在尋求主流文化認同的方式上,傳統電競粉絲也更多宣傳電子競技可以作為傳統體育賽事的正當性來以求“破圈”,如訪談對象8提到“現在比賽里的輿論就是‘贏一場亞運會,輸一場退役’,現在王者榮耀畢竟進入亞運會了嘛,社會對于電競的看法也比以前好一些了”。傳統電競粉通過不斷強調電子競技的體育性質來維護自己的話語權,將自己與飯圈粉絲做出區分。
(三)正和博弈:愈合粉絲群體之間的溝壑
傳統電競圈粉絲與飯圈粉絲之間對抗愈演愈烈,但他們之間溝壑是真的不可愈合的嗎?
盡管大多數訪談者厭惡飯圈,但在關于是否認為傳統電競粉絲更有話語權的這一問題上,多數訪談者們又積極尋求粉絲的對等化、尋求合作:
“只要正常看比賽就應該是平等的,不存在誰比誰高貴一說。”(訪談對象9)
“電競圈粉絲這么多,構成也蠻復雜的,但大家的初心都是喜歡這個隊伍,沒有誰更有話語權一說。”(訪談對象2)
再者,傳統電競粉構建的屬于電競圈的語匯體系并非不可解的。正如訪談對象3在訪談中說到:“這破游戲還有啥看不懂的嗎!”傳統電競粉的用語理解門檻是較為低的,對于長期關注電競圈的粉絲來說沒有無法跨越的理解門檻。并且隨著網絡語言的發展,電競圈的語匯系統已經逐漸摻雜在新一代的網絡語言中,深刻嵌入日常話語實踐,比如,將男生對女生表白用游戲中“交大招”來指代等。傳統電競粉的語匯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掌握、理解,從特定場域、特定主題,變成在社會交往中大多數人都能夠生產運用的。
在傳統電競粉絲與飯圈粉絲的關系中,對抗是長期存在的,有時候表現為兩個圈層之間的分歧,但現如今更多時候向兩個群體之間的正和博弈轉變。 對抗關系走向正和博弈取決于三大因素:貢獻、親密和遠景。
從貢獻來看,在新媒體時代,隨著商業資本對亞文化的推廣,越多的大眾喜歡上亞文化,亞文化群體獲得的關注度越高,亞文化資本所具有的社會價值和商業價值就會變得越高。訪談對象10提到:“競圈飯圈化是必然的,不管KPL還是LPL因為俱樂部運作需要資本化,資本進入市場就會考慮到分蛋糕的、明星選手跑商務,飯圈粉絲的購買力無疑是更強的”;訪談對象3也說道:“說白了只有豁得出去時間和錢的,才是官方在意的,那些路人粉其實也不是KPL官方想保留的對象吧”,相較于傳統電競粉絲,飯圈粉絲崇拜、仰慕甚至狂熱迷戀自己所熱愛的選手,并且在經濟、時間和情感方面都進行超常的投入,他們是積極、主動、創造性地通過消費來構建自己在這個圈層內存在的意義。 這種行為是電競亞文化圈的擴大、發展所需要的。其次,訪談對象7和8都提及飯圈粉絲的涌入有利于電競大眾化:“飯圈粉絲是會帶來一些熱度的,雖然矛盾多了,但熱度同時也一起來了,所以飯圈粉絲涌入我覺得會讓KPL走進大眾的視野里,被更多人接受”(訪談對象7);“飯圈粉絲多了不管是被更多人接受還是變得更烏煙瘴氣,熱度反正是有了,而且我覺得至少是朝著電子競技被更多人認可的方向發展的,亞運會也快要開始了,說明走得越來越遠啦”(訪談對象8)。傳統電競粉絲作為電競圈“原住民”,是他們首先構成了電競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且是電競圈的核心力量。也就是說。雙方都為電子競技的發展作出貢獻,并且兩個圈層相互依賴程度也非常高。
在電子競技亞文化圈內,傳統電子競技粉絲作為電子競技“原住民”,他們關注比賽、技術的實踐行為代表著“酷”,飯圈粉絲注重選手個人、為選手花錢等代表著“不那么酷”。因此也就會出現有些電競愛好者盡管他的實踐行為是與飯圈粉絲并無差別的,但他仍然不愿意在名義上承認自己是飯圈粉絲,始終想要保持自己的“品位”。這種“酷樣”就在兩個圈層中形成隔閡,帶來矛盾。傳統電競粉對飯圈粉絲的鄙夷,MOBA類游戲強對抗性等原因,使得兩個圈層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新媒體時代,信息爆炸時代亞文化資本的價值不僅僅在于亞文化圈,飯圈粉絲的涌入讓傳統電競粉難以實現話語權的壟斷,帶來了廣泛的關于權力的爭奪,形成圈層對立。然而,傳統電競粉與飯圈粉絲之間的溝壑并非不可愈合的。 傳統電競粉構建的電競語匯并非不可解,并且他們一邊低評價飯圈粉絲一邊尋求平等與合作。 傳統電競粉與飯圈粉絲相互依賴,共同為電子競技的發展作出貢獻,走向正和博弈。電子競技現如今已經成為年輕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網絡溝通及時便捷、信息高度發達的當下,傳統電競粉與飯圈粉絲相互對抗在互聯網中不斷上演,本文試圖從亞文化角度來探究兩個群體背后的文化意涵,飯圈粉絲與傳統電競粉絲可以一起促進電子競技的發展,為我們理解電子競技賦予新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