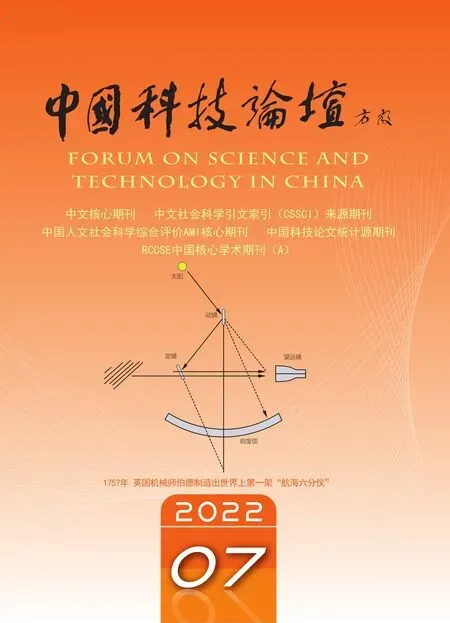美日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及其啟示
李雙美,王 昶,耿紅軍
中南大學(xué)商學(xué)院,湖南 長沙 410083)
0 引言
隨著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物聯(lián)網(wǎng)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shù)的興起,智能制造成為全球重塑制造業(yè)競爭優(yōu)勢的新技術(shù)經(jīng)濟(jì)范式和中國制造強(qiáng)國戰(zhàn)略的主攻方向。關(guān)鍵新材料作為智能制造發(fā)展的基石與先導(dǎo),是全球主要國家必爭的戰(zhàn)略領(lǐng)域[1]。美國在聯(lián)邦政府的引導(dǎo)下,構(gòu)建大學(xué)、國家實驗室、新材料企業(yè)、軍方、金融機(jī)構(gòu)和風(fēng)險投資機(jī)構(gòu)等多主體協(xié)同交互的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促進(jìn)知識前沿探索與研發(fā)應(yīng)用迭代,保持新材料產(chǎn)業(yè)全球領(lǐng)先;日本由政府主導(dǎo),龍頭企業(yè)和科研院所協(xié)同配合,形成了政產(chǎn)學(xué)研一體化的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體系,在新材料產(chǎn)業(yè)的尖端領(lǐng)域表現(xiàn)出顯著的領(lǐng)先優(yōu)勢。可見,構(gòu)建系統(tǒng)完備、運行高效的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成為各國搶占關(guān)鍵新材料競爭制高點的關(guān)鍵支撐。
中國同樣高度重視新材料產(chǎn)業(yè)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2010年,國務(wù)院印發(fā)《關(guān)于加快培育和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的決定》,將新材料列為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2015年,工信部等四部委聯(lián)合發(fā)布《中國制造2025》,再次將新材料列為重點突破領(lǐng)域。在此基礎(chǔ)上,政府進(jìn)一步制定了新材料產(chǎn)業(yè)規(guī)劃、發(fā)展指南、標(biāo)準(zhǔn)領(lǐng)航計劃等戰(zhàn)略規(guī)劃,推動新材料產(chǎn)業(yè)多個領(lǐng)域取得長足發(fā)展。但從整體上來看,中國新材料產(chǎn)業(yè)仍面臨先進(jìn)基礎(chǔ)材料參差不齊,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受制于人,前沿新材料亟待突破的瓶頸[2]。據(jù)工信部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中國32%的關(guān)鍵新材料完全空白、52%嚴(yán)重依賴進(jìn)口。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中國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存在主體間缺乏協(xié)同、研發(fā)與應(yīng)用脫節(jié)、基礎(chǔ)支撐體系欠完善等硬約束。
基于以上分析,深入總結(jié)發(fā)達(dá)國家新材料創(chuàng)新的實踐模式,為中國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的優(yōu)化提供經(jīng)驗借鑒,成為亟需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然而現(xiàn)有相關(guān)文獻(xiàn)主要圍繞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展開研究,尚未聚焦于新材料產(chǎn)業(yè),同時缺乏系統(tǒng)性的創(chuàng)新模式分析框架。鑒于此,本文從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重點領(lǐng)域、著力點和舉措四個維度架構(gòu)分析框架,歸納美國和日本的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對比兩國模式的異同并探析差異背后的原因,并結(jié)合中國國情給出優(yōu)化中國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的實踐啟示。
1 文獻(xiàn)綜述
國內(nèi)外關(guān)于創(chuàng)新模式的研究源于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理論。英國技術(shù)創(chuàng)新學(xué)者弗里曼基于日本創(chuàng)新趕超經(jīng)驗提出了 “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的概念,創(chuàng)新體系由政府、企業(yè)、大學(xué)、科研機(jī)構(gòu)、技術(shù)轉(zhuǎn)移中介等創(chuàng)新主體構(gòu)成,各主體在知識生產(chǎn)、技術(shù)開發(fā)、產(chǎn)業(yè)化過程中協(xié)同交互,體現(xiàn)出明顯的系統(tǒng)性特征[3]。現(xiàn)有文獻(xiàn)基于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理論,對美國、日本的創(chuàng)新模式展開了廣泛研究。
曼哈頓模式和硅谷模式是美國兩種經(jīng)典的創(chuàng)新模式。曼哈頓模式強(qiáng)調(diào)政府干預(yù)和高度集中化管理,政府對其主導(dǎo)的項目進(jìn)行全面控制,自上而下地推進(jìn),力圖搶占科技制高點,促使美國科技領(lǐng)域?qū)崿F(xiàn)迅猛發(fā)展;硅谷模式強(qiáng)調(diào)發(fā)揮企業(yè)主體作用和分散式管理,以市場為導(dǎo)向,以風(fēng)險資本為依托,產(chǎn)學(xué)研協(xié)同創(chuàng)新[4]。雷小苗等[3]基于理論分析和國際實踐,提煉出 “三元串聯(lián)協(xié)同”和 “三元并聯(lián)互動”兩種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的結(jié)構(gòu)框架。當(dāng)前美國創(chuàng)新體系屬于三元并聯(lián)互動類型,政府處于 “弱干預(yù)”狀態(tài),發(fā)揮引導(dǎo)作用的同時保障各創(chuàng)新主體的獨立自主性,大學(xué)是科研活動的重要承擔(dān)者,企業(yè)扮演主力軍角色,瞄準(zhǔn)市場需求,整合大學(xué)、科研機(jī)構(gòu)和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資源,促進(jìn)政產(chǎn)學(xué)研高效協(xié)同[5]。美國產(chǎn)學(xué)研協(xié)同創(chuàng)新模式依據(jù)組建方式可以劃分為大學(xué)科技園模式、企業(yè)孵化器模式和合作研究中心模式等,依據(jù)科研成果轉(zhuǎn)化方式可以劃分為技術(shù)許可模式、大學(xué)衍生企業(yè)模式等[6-7]。
縱觀日本科技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歷程,其戰(zhàn)略思想經(jīng)歷了貿(mào)易立國、技術(shù)立國和科學(xué)技術(shù)創(chuàng)造立國三個時期[8],其創(chuàng)新模式經(jīng)歷了模仿創(chuàng)新、引進(jìn)消化吸收再創(chuàng)新、集成創(chuàng)新、原始創(chuàng)新四個階段[9]。二戰(zhàn)后,日本在政府主導(dǎo)下,基于本國國情制定了嚴(yán)密的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鼓勵國內(nèi)企業(yè)有針對性地從歐美發(fā)達(dá)國家引進(jìn)先進(jìn)技術(shù),并對引進(jìn)技術(shù)予以攻關(guān)、擴(kuò)散、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生產(chǎn)力[10]。隨著科技實力的不斷增強(qiáng),日本創(chuàng)新模式逐漸由學(xué)習(xí)、引進(jìn)、模仿向原始創(chuàng)新階段過渡,政府發(fā)揮主導(dǎo)作用,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穩(wěn)健的投融資體系、健全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機(jī)制和知識產(chǎn)權(quán)體系,且高度重視中小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形成了獨具日本特色的創(chuàng)新體系[9]。
現(xiàn)有文獻(xiàn)從國家和區(qū)域?qū)用鎸γ绹腿毡镜膭?chuàng)新模式展開了大量研究,而產(chǎn)業(yè)層面的創(chuàng)新模式研究相對較少,針對新材料這一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的創(chuàng)新模式分析更是匱乏。此外,現(xiàn)有研究尚未架構(gòu)出系統(tǒng)性的創(chuàng)新模式分析框架。為了彌補(bǔ)這一研究缺口,本文借鑒技術(shù)創(chuàng)新系統(tǒng) (TIS)和科學(xué)-技術(shù)-商業(yè)化 (S-T-B)理論,從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重點領(lǐng)域、著力點和舉措這四個維度構(gòu)建研究框架,重點分析美國和日本的新材料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
2 研究設(shè)計
2.1 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主要來源于以下渠道:一是官方文件與報道,主要來自美國能源部、國防部、國家標(biāo)準(zhǔn)與技術(shù)研究院和日本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省、文部科學(xué)省等官方網(wǎng)站;二是相關(guān)文獻(xiàn),主要來自中國知網(wǎng)、Web of Science、Elsevier等數(shù)據(jù)庫;三是網(wǎng)絡(luò)資料,主要來自與新材料創(chuàng)新相關(guān)的公眾號和智庫,如新材料在線、創(chuàng)新研究、賽迪智庫等。以上三個渠道的資料相互驗證,為案例研究提供了客觀豐富的素材,提高了案例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2.2 研究框架
本文綜合應(yīng)用技術(shù)創(chuàng)新系統(tǒng)和科學(xué)-技術(shù)-商業(yè)化理論,從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重點領(lǐng)域、著力點和舉措四個維度構(gòu)建研究框架 (見圖1),分析美國和日本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

圖1 基于TIS和S-T-B的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的研究框架
(1)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借鑒TIS結(jié)構(gòu)要素理論,從行動者、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和制度三個方面闡述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及特征[11-12]。其中,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的行動者主要包括政府、大學(xué)、科研機(jī)構(gòu)、企業(yè)等,行動者之間遵循一定的制度準(zhǔn)則 (如政策、法律、慣例)開展協(xié)同交互,搭建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共同促進(jìn)知識開發(fā)、擴(kuò)散和應(yīng)用。
(2)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重點探討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重點關(guān)注的新材料領(lǐng)域,按照其應(yīng)用發(fā)展方向劃分為先進(jìn)基礎(chǔ)材料、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
(3)創(chuàng)新突破著力點:借鑒S-T-B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三層次模型[13],圍繞科學(xué)研究-技術(shù)開發(fā)-商業(yè)化應(yīng)用這三個創(chuàng)新鏈環(huán)節(jié),分析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的著力點。其中,科學(xué)研究包括基礎(chǔ)研究和應(yīng)用研究,重點探索新材料前沿理論和共性技術(shù);技術(shù)開發(fā)是指對科研成果進(jìn)行試驗和改良,轉(zhuǎn)化為可以直接應(yīng)用于生產(chǎn)實踐的工藝技術(shù);商業(yè)化應(yīng)用意味著新材料技術(shù)或產(chǎn)品廣泛應(yīng)用于下游產(chǎn)業(yè)。
(4)創(chuàng)新突破舉措:借鑒TIS功能理論,以功能模塊作為落腳點,歸納作用于每個功能模塊的創(chuàng)新突破舉措。TIS功能包括搜索指導(dǎo) (Guidance of the search)、知識開發(fā)與擴(kuò)散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創(chuàng)業(yè)實驗 (Entrepreneurial experimentation)、市場開拓 (Market formation)、合法化 (Legitimation)和資源配置 (Resource mobilization)[11-12],各功能的定義見表1。

表1 技術(shù)創(chuàng)新系統(tǒng)功能的定義
3 案例分析
3.1 美國模式:政府引導(dǎo)-雙輪驅(qū)動-多主體協(xié)同
(1)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美國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如圖2所示,主要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包括政府、大學(xué)、國家實驗室、新材料企業(yè)、軍方、金融機(jī)構(gòu)和風(fēng)險投資機(jī)構(gòu)。政府通過制定戰(zhàn)略政策引導(dǎo)各主體致力于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大學(xué)和國家實驗室基于其全球領(lǐng)先的科技資源和科研實力開展前沿知識探索與創(chuàng)新。新材料企業(yè)積極推進(jìn)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和商業(yè)化應(yīng)用。軍方通過需求牽引加快新材料產(chǎn)業(yè)化進(jìn)程。金融機(jī)構(gòu)和風(fēng)險投資機(jī)構(gòu)為資金投入大、研發(fā)周期長、市場風(fēng)險高的新材料產(chǎn)業(yè)提供資金支持。美國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有限政府。政府發(fā)揮引導(dǎo)作用,通過統(tǒng)籌規(guī)劃有限參與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二是雙輪驅(qū)動。大學(xué)、國家實驗室創(chuàng)新驅(qū)動與軍方需求牽引同時發(fā)力,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輪驅(qū)動加速關(guān)鍵新材料研發(fā)與應(yīng)用迭代。三是多主體協(xié)同。政府、大學(xué)、國家實驗室、新材料企業(yè)、軍方、金融機(jī)構(gòu)和風(fēng)險投資機(jī)構(gòu)跨越組織邊界協(xié)同創(chuàng)新。

圖2 美國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
(2)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美國以滿足國家戰(zhàn)略需求和追求前沿領(lǐng)先為導(dǎo)向,選擇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基于國防軍備的戰(zhàn)略需求,美國的科研主導(dǎo)方向主要向國防軍事領(lǐng)域傾斜,使得與國防軍事緊密相關(guān)的電子信息材料、航空航天材料、生物醫(yī)藥材料等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取得重大突破。其中,電子信息材料包括半導(dǎo)體材料、發(fā)光材料等,航空航天材料包括高溫輕質(zhì)合金、先進(jìn)復(fù)合材料等。基于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戰(zhàn)略需求,美國能源部牽頭構(gòu)建能源材料網(wǎng)絡(luò) (EMN)[14],加強(qiáng)新能源材料研發(fā)創(chuàng)新。其中,儲氫材料、鋰電池材料等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是創(chuàng)新突破的重點領(lǐng)域。為了保持前沿科技領(lǐng)域的國際領(lǐng)先地位,美國重點布局納米材料、超導(dǎo)材料和增材制造材料等前沿新材料領(lǐng)域。
(3)創(chuàng)新突破著力點。
①科學(xué)研究方面,美國高度重視新材料基礎(chǔ)研究,并以基礎(chǔ)研究為引領(lǐng)推動應(yīng)用研究。科學(xué)研究的承擔(dān)者以大學(xué)、國家實驗室為核心,向新材料企業(yè)、非營利性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等多點擴(kuò)散。大學(xué)和國家實驗室將材料學(xué)科與物理、化學(xué)、信息計算等多學(xué)科交叉融合,探索知識前沿。同時,國家實驗室與新材料企業(yè)積極推進(jìn)應(yīng)用研究,突破關(guān)鍵共性技術(shù)。
②技術(shù)開發(fā)方面,美國強(qiáng)調(diào)開拓性創(chuàng)新,新材料企業(yè)和國家實驗室等創(chuàng)新主體著力將科研成果向多個應(yīng)用領(lǐng)域延伸開拓,促進(jìn)新材料技術(shù)的前沿擴(kuò)張。例如,美國大力推動納米材料技術(shù)在電子信息、太陽能電池、儲能裝置等多個前沿領(lǐng)域的融合創(chuàng)新。
③商業(yè)化應(yīng)用方面,美國通過軍方采購釋放市場需求,引導(dǎo)市場主體行為,促進(jìn)新材料產(chǎn)業(yè)市場化運作。軍方采購是美國新材料產(chǎn)業(yè)初期最主要的訂單來源,尤其對于與國防軍備密切相關(guān)的電子信息材料和航空航天材料。隨著軍民融合的深化,軍用市場和民用市場相互滲透融合,軍方采購一方面釋放了對民用新材料的市場需求,促進(jìn)民用新材料應(yīng)用于軍工行業(yè);另一方面發(fā)揮應(yīng)用示范效應(yīng),有效引導(dǎo)民用市場主體的采購行為,加速新材料在民用市場的商業(yè)化應(yīng)用。
(4)創(chuàng)新突破舉措。
①搜索指導(dǎo):技術(shù)預(yù)判與戰(zhàn)略指引。通過技術(shù)預(yù)判和戰(zhàn)略指引為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提供搜索指導(dǎo)。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 (DARPA)和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 (OSTP)根據(jù)國家重大戰(zhàn)略需求,基于前沿技術(shù)探索的長遠(yuǎn)考慮,結(jié)合綜合性部局通告 (BAA)匯集的社會意見,預(yù)判新材料產(chǎn)業(yè)發(fā)展方向,并制定戰(zhàn)略規(guī)劃。美國在第一份 《關(guān)鍵技術(shù)報告》中把新材料列為影響經(jīng)濟(jì)繁榮和國家安全的六大關(guān)鍵技術(shù)領(lǐng)域之首,并相繼出臺國家半導(dǎo)體照明研究計劃 (SSL)、國家納米技術(shù)計劃 (NNI)等重大戰(zhàn)略計劃,引導(dǎo)新材料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發(fā)展。
②知識開發(fā)與擴(kuò)散:多元投入與健全體系。通過構(gòu)建多元化的科研經(jīng)費投入與執(zhí)行體系和健全技術(shù)轉(zhuǎn)移體系,促進(jìn)新材料知識開發(fā)與擴(kuò)散。美國科研投入的來源部門與執(zhí)行主體均呈現(xiàn)多元化特征[15],有利于多方科研主體著力探索前沿知識。為了促進(jìn)知識擴(kuò)散,美國國會頒發(fā)《技術(shù)轉(zhuǎn)移商業(yè)化法案》[16],政府部門聯(lián)合成立國家技術(shù)轉(zhuǎn)移中心 (NTTC),國家實驗室組建聯(lián)邦實驗室技術(shù)轉(zhuǎn)移聯(lián)合體 (FLC)[17],建立了覆蓋國家、區(qū)域、國家實驗室和企業(yè)的多層次技術(shù)轉(zhuǎn)移體系,促進(jìn)實驗室知識成果向產(chǎn)業(yè)界轉(zhuǎn)移和擴(kuò)散。
③創(chuàng)業(yè)實驗:專業(yè)孵化與搭建平臺。建立專業(yè)孵化器和試驗平臺,促進(jìn)新材料企業(yè)開展創(chuàng)業(yè)試驗。一方面,通過建立專業(yè)孵化器為新材料初創(chuàng)企業(yè)提供資金支持、中試基地和商業(yè)化指導(dǎo)。例如,休斯敦技術(shù)中心 (HTC)作為新材料領(lǐng)域的專業(yè)孵化器,孵化出從事納米材料研發(fā)生產(chǎn)的NanoRidge Materials等企業(yè)。另一方面,通過搭建國家標(biāo)準(zhǔn)與技術(shù)研究院 (NIST)和美國材料與試驗協(xié)會 (ASTM)等試驗平臺,為新材料企業(yè)提供專業(yè)化的試驗方法與標(biāo)準(zhǔn)指導(dǎo)[18-19]。
④市場開拓:軍民融合與完善機(jī)制。推行軍民融合戰(zhàn)略,完善激勵制度和法律法規(guī)等保障機(jī)制,打通軍轉(zhuǎn)民、民參軍的雙向轉(zhuǎn)移通道,開拓新材料市場。為了解決軍民分離導(dǎo)致軍工產(chǎn)能過剩而民用市場開發(fā)不足的問題,美國提出了軍民融合戰(zhàn)略。為此,政府制定 “軍轉(zhuǎn)民五年計劃”,鼓勵優(yōu)先發(fā)展新材料等軍民兩用技術(shù),把過剩的軍工產(chǎn)能向民用市場轉(zhuǎn)移;同時,國會頒發(fā)《聯(lián)邦采購精簡化法案》,科學(xué)降低民營企業(yè)進(jìn)入軍工市場的門檻。 “軍轉(zhuǎn)民”與 “民參軍”共同促進(jìn)軍工市場與民用市場深度融合,拓展了新材料市場。
⑥資源配置:政策引導(dǎo)與資源整合。政府通過政策引導(dǎo),促進(jìn)資金、人才和基礎(chǔ)設(shè)施等資源集聚與整合。資金方面,建立了以財政撥款和政府引導(dǎo)基金為主的資金保障體系,充分調(diào)動了產(chǎn)業(yè)界資本和金融風(fēng)險資本。人才方面,堅持貫徹STEM教育戰(zhàn)略,為新材料等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培養(yǎng)和輸送復(fù)合型、創(chuàng)新型人才。基礎(chǔ)設(shè)施方面,著力建設(shè)國際領(lǐng)先的大科學(xué)裝置和科研平臺,并制定 “公共訪問計劃”等政策促進(jìn)資源共享。
3.2 日本模式:政府主導(dǎo)-企業(yè)助推-科研院所配合
(1)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日本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的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如圖3所示,主要創(chuàng)新主體包括政府、大學(xué)、科研機(jī)構(gòu)和新材料企業(yè)。政府負(fù)責(zé)頂層設(shè)計和統(tǒng)籌部署,大學(xué)和科研機(jī)構(gòu)致力于新材料基礎(chǔ)知識探索和共性技術(shù)研究,新材料企業(yè)是推進(jìn)新材料技術(shù)開發(fā)和商業(yè)化應(yīng)用的中堅力量。

圖3 日本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
日本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呈現(xiàn)出兩方面特征:一是政府主導(dǎo)。政府的主導(dǎo)作用自上而下貫穿于戰(zhàn)略規(guī)劃、制度完善和項目統(tǒng)籌等過程,為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設(shè)計完整的技術(shù)路線。二是企業(yè)助推。新材料企業(yè)是日本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過程中的核心助推器,主要體現(xiàn)為堅定執(zhí)行政府指令和有效連接知識端和市場端,加速新材料產(chǎn)業(yè)化進(jìn)程。三是官產(chǎn)學(xué)協(xié)同。在政府的主導(dǎo)下,新材料企業(yè)、大學(xué)和科研機(jī)構(gòu)積極響應(yīng)配合,協(xié)同創(chuàng)新。
(2)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日本以服務(wù)國家戰(zhàn)略需求和塑造產(chǎn)業(yè)競爭優(yōu)勢為導(dǎo)向,選擇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基于保障國家信息安全的戰(zhàn)略需求,日本政府、科研機(jī)構(gòu)和企業(yè)聯(lián)合攻克半導(dǎo)體材料 “卡脖子”難關(guān),使硅晶圓、光刻膠等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實現(xiàn)后發(fā)趕超。為了塑造汽車、家用電器和電子信息等主導(dǎo)產(chǎn)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日本從具有高附加值的材料端開展自主創(chuàng)新。其中,工程塑料、有機(jī)EL材料、非晶合金、鎂合金材料、超級鋼鐵材料等先進(jìn)基礎(chǔ)材料,以及碳纖維、精細(xì)陶瓷等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是創(chuàng)新突破的重點領(lǐng)域。
(3)創(chuàng)新突破著力點。
①科學(xué)研究方面,日本的科研導(dǎo)向從以應(yīng)用研究為主導(dǎo)逐漸向基礎(chǔ)研究和應(yīng)用研究并舉轉(zhuǎn)變,強(qiáng)調(diào)以應(yīng)用為導(dǎo)向的知識原始積累。早期,日本在引進(jìn)歐美國家的前沿知識和共性技術(shù)的基礎(chǔ)上,開展應(yīng)用研究加以消化吸收。隨著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激烈,日本逐漸意識到基礎(chǔ)研究的重要性,開始注重以應(yīng)用為導(dǎo)向的基礎(chǔ)研究和專利布局,從源頭提高創(chuàng)新能力。
②技術(shù)開發(fā)方面,日本新材料企業(yè)秉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致力于工藝技術(shù)的試驗、改良和打磨。例如,日本通過精細(xì)化打磨掌握了半導(dǎo)體材料和精細(xì)陶瓷的核心工藝技術(shù),其他國家難以對其精密的工藝過程進(jìn)行解構(gòu)與仿制。
4.1 水肥管理:苦瓜生長期長,結(jié)果多,對肥水的需求高。定植后結(jié)合灌水,每隔15~20天追一次三元復(fù)合肥,每畝10千克。開花結(jié)果期7~10天噴施1次0.2%尿素和0.3%磷酸二氫鉀混合液。
③商業(yè)化應(yīng)用方面,日本采用縱向一體化方式整合產(chǎn)業(yè)鏈,加速新材料應(yīng)用。新材料企業(yè)通過戰(zhàn)略聯(lián)盟和兼并收購等方式,將上游創(chuàng)新產(chǎn)品導(dǎo)入下游應(yīng)用市場。例如,日本JFE和新日鐵公司與歐美汽車制造商結(jié)成戰(zhàn)略聯(lián)盟,在車型研發(fā)設(shè)計先期階段介入鋼鐵材料的設(shè)計、選型和沖壓試模等,加速鋼鐵材料應(yīng)用于下游汽車制造業(yè)。
(4)創(chuàng)新突破舉措。
①搜索指導(dǎo):技術(shù)預(yù)見與戰(zhàn)略規(guī)劃。通過技術(shù)預(yù)見預(yù)測關(guān)鍵技術(shù)趨勢,制定戰(zhàn)略計劃,為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提供搜索指導(dǎo)。日本國家科技政策研究所 (NISTEP)運用德爾菲法、情景分析等方法,廣泛征集科研院所和產(chǎn)業(yè)界專家的意見[20],預(yù)測新材料技術(shù)發(fā)展前景,并在此基礎(chǔ)上展開戰(zhàn)略部署。例如,日本自第二期科學(xué)技術(shù)基本計劃開始,持續(xù)將新材料列為科技創(chuàng)新的重點領(lǐng)域,并制定超級鋼材料計劃、下一代汽車計劃等戰(zhàn)略計劃,為超級鋼鐵材料、碳纖維等重點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突破提供專項指導(dǎo)。
②知識開發(fā)與擴(kuò)散:二元并重與制度規(guī)范。構(gòu)建非競爭性與競爭性科研經(jīng)費并重的二元結(jié)構(gòu)資助體系[21]和知識擴(kuò)散的制度規(guī)范,促進(jìn)新材料知識開發(fā)和擴(kuò)散。政府非競爭性資金主要用于資助前瞻性基礎(chǔ)研究,競爭性資金主要用于支持產(chǎn)業(yè)化前景良好的競爭性項目,確保基礎(chǔ)性和應(yīng)用性知識的全面開發(fā)。日本提倡 “知識產(chǎn)權(quán)立國”,通過制定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律法規(guī),設(shè)立日本科學(xué)技術(shù)振興機(jī)構(gòu) (JST)等技術(shù)轉(zhuǎn)移中介機(jī)構(gòu)和完善技術(shù)轉(zhuǎn)移機(jī)制,規(guī)范管理新材料知識轉(zhuǎn)移與擴(kuò)散。
③創(chuàng)業(yè)實驗:稅收優(yōu)惠與衍生輔助。政府制定稅收優(yōu)惠政策,科研院所完善企業(yè)衍生的輔助機(jī)制,共同促進(jìn)新材料創(chuàng)業(yè)實驗。日本基于實驗研究費實行稅收抵免[22],提高了新材料企業(yè)開展實驗活動的主動性。產(chǎn)業(yè)技術(shù)綜合研究所 (AIST)等從事新材料領(lǐng)域研究的國立科研院所,設(shè)置了專門的衍生輔助機(jī)構(gòu),為衍生企業(yè)提供技術(shù)支持、基礎(chǔ)設(shè)施和管理咨詢等服務(wù),保障企業(yè)在初創(chuàng)階段可以有序開展實驗研究。
④市場開拓:制定標(biāo)準(zhǔn)與國際經(jīng)營。通過制定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建立市場準(zhǔn)則,通過開展國際經(jīng)營延展市場網(wǎng)絡(luò),促進(jìn)新材料市場開發(fā)和拓展。企業(yè)和科研院所積極推進(jìn)新材料標(biāo)準(zhǔn)研究和制定,搶占市場話語權(quán)。此外,新材料企業(yè)采用海外并購和投資建廠等方式拓展全球市場網(wǎng)絡(luò)。例如,東麗收購國際領(lǐng)先的碳纖維生產(chǎn)商卓爾泰克,兩者協(xié)同發(fā)揮市場規(guī)模優(yōu)勢,使東麗成為全球碳纖維市場的執(zhí)牛耳者。
⑤合法化:政府主導(dǎo)與組建聯(lián)盟。在政府的主導(dǎo)下,企業(yè)和科研院所積極參與,共同組建官產(chǎn)學(xué)創(chuàng)新聯(lián)盟,提高新材料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合法性。日本政府發(fā)揮其角色權(quán)威性,采用項目招標(biāo)的形式吸引科研院所和企業(yè)加入創(chuàng)新聯(lián)盟,加快投入大、周期長、風(fēng)險高的新材料技術(shù)實現(xiàn)創(chuàng)新跨越。官產(chǎn)學(xué)合作項目的示范效應(yīng)有利于營造良好的社會預(yù)期。例如,日本典型的超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 (VLSI)創(chuàng)新聯(lián)盟由政府發(fā)起,以 “項目制”形式聯(lián)合企業(yè)和科研院所攻關(guān)半導(dǎo)體共性技術(shù),硅晶圓和光刻裝置取得重大突破[23],顯著提高了半導(dǎo)體材料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合法性。
⑥資源配置: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與要素保障。政府加強(qiáng)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為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提供資金、人才和基礎(chǔ)設(shè)施等要素保障。資金方面,政府依托于強(qiáng)有力的主銀行制度干預(yù)資金調(diào)配。人才方面,政府鼓勵科研機(jī)構(gòu)和企業(yè)聯(lián)合培養(yǎng)具備多領(lǐng)域知識且專業(yè)特長突出的T型人才,為新材料等新興產(chǎn)業(yè)配備高水平人才。基礎(chǔ)設(shè)施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國立材料研究所 (NIMS)建立了NIMS在線數(shù)據(jù)庫等極具國際影響力的新材料科研平臺。
4 跨案例對比與分析
在分析美國和日本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的基礎(chǔ)上,本文對兩國模式的異同點進(jìn)行了對比分析 (見表2)。

表2 美國與日本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對比
4.1 共同點分析
(1)服務(wù)國家戰(zhàn)略。兩國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的重點領(lǐng)域均服務(wù)于國家重大戰(zhàn)略需求:美國電子信息材料、航空航天材料、生物與醫(yī)藥材料服務(wù)于國防軍備戰(zhàn)略需求,新能源材料服務(wù)于國家能源戰(zhàn)略需求;日本半導(dǎo)體材料服務(wù)于保障國家信息安全的戰(zhàn)略需求。
(2)加強(qiáng)頂層設(shè)計。兩國均采用技術(shù)預(yù)見、戰(zhàn)略規(guī)劃和完善政策制度等方式加強(qiáng)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的頂層設(shè)計。圍繞國家重大戰(zhàn)略需求,綜合多方專家和社會需求端意見預(yù)測新材料產(chǎn)業(yè)發(fā)展方向,并制定戰(zhàn)略計劃和配套的財稅金融制度,保障新材料產(chǎn)業(yè)有序發(fā)展。
(3)注重知識管理。兩國均建立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和技術(shù)轉(zhuǎn)移機(jī)制,規(guī)范管理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的知識成果,促進(jìn)新材料知識擴(kuò)散。
(4)構(gòu)建創(chuàng)新生態(tài)。兩國均構(gòu)建了多主體協(xié)同的新材料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政府加強(qiáng)全局規(guī)劃,科研院所提供知識支持和匹配支持,企業(yè)加速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和商業(yè)化應(yīng)用,彼此各司其職又協(xié)同配合,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示范效應(yīng)提高了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的合法性。
4.2 差異性分析
(1)角色定位不同。美國政府作為 “引導(dǎo)者”,通過制定戰(zhàn)略政策引導(dǎo)大學(xué)、國家實驗室和新材料企業(yè)等多主體協(xié)同創(chuàng)新,體現(xiàn)出開放式創(chuàng)新理念;日本政府作為 “主導(dǎo)者”,從整體規(guī)劃到項目實施自上而下統(tǒng)籌部署,新材料企業(yè)和科研院所在政府的主導(dǎo)下積極響應(yīng)配合,體現(xiàn)出 “強(qiáng)政府”的模式特征。
(2)重點領(lǐng)域不同。美國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的重點領(lǐng)域側(cè)重于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旨在滿足國防軍備和能源需求的同時追求前沿領(lǐng)先,搶占科技競爭制高點;日本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的重點領(lǐng)域側(cè)重于先進(jìn)基礎(chǔ)材料和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旨在突破關(guān)鍵材料技術(shù) “卡脖子”瓶頸的基礎(chǔ)上,使具有高附加值的材料端實現(xiàn)專業(yè)化和產(chǎn)業(yè)化,塑造主導(dǎo)產(chǎn)業(yè)競爭優(yōu)勢。
(3)著力點不同。科學(xué)研究方面,美國非常重視基礎(chǔ)研究,同時以基礎(chǔ)研究為引領(lǐng)推進(jìn)應(yīng)用研究,力爭走在科學(xué)技術(shù)的最前沿;日本非常重視應(yīng)用研究,同時以應(yīng)用研究為導(dǎo)向夯實基礎(chǔ)研究,提高原始創(chuàng)新能力。技術(shù)開發(fā)方面,美國強(qiáng)調(diào)技術(shù)應(yīng)用領(lǐng)域的開拓,提高技術(shù)通用性;日本專注于技術(shù)的精細(xì)化打磨,打造尖端工藝技術(shù)。商業(yè)化應(yīng)用方面,美國依靠軍方采購,在有效釋放新材料市場需求的同時,引導(dǎo)其他市場主體的采購行為;日本采用縱向一體化的方式,將新材料導(dǎo)入下游產(chǎn)業(yè)。
(4)舉措不同。創(chuàng)業(yè)實驗方面,兩國的區(qū)別在于主導(dǎo)推動創(chuàng)業(yè)實驗的主體不同,美國由民間企業(yè)和機(jī)構(gòu)建立專業(yè)孵化器和實驗平臺,推動創(chuàng)業(yè)實驗;日本由政府和國立科研院所完善稅收政策和衍生機(jī)制,推動創(chuàng)業(yè)實驗。市場開拓方面,美國通過軍民融合開拓市場;日本通過國際經(jīng)營開拓市場。資源配置方面,美國通過政策引導(dǎo)整合產(chǎn)業(yè)資本和金融風(fēng)險資本;日本政府依托于強(qiáng)有力的主銀行制度干預(yù)資金調(diào)配。
4.3 原因分析
(1)歷史文化。兩國歷史文化的差異導(dǎo)致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主體角色定位、技術(shù)開發(fā)的著力點不同。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多元文化的嵌入推動其形成一種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培養(yǎng)了人們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開拓精神[24]。因此,美國強(qiáng)調(diào)多主體協(xié)同創(chuàng)新,注重技術(shù)的前沿開拓。日本歷史上長期處于封建社會,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政府在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中一直處于權(quán)威核心地位,加之崇尚工匠精神,因此日本強(qiáng)調(diào)政府主導(dǎo),注重工藝技術(shù)的精細(xì)化打磨。
(2)國際地位。兩國的國際地位差異導(dǎo)致科學(xué)研究側(cè)重點和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不同。美國是世界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和科技領(lǐng)域的唯一超級大國,為了捍衛(wèi)其全球領(lǐng)先的國際地位,美國高度重視新材料基礎(chǔ)研究,并選擇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作為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日本作為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與科技強(qiáng)國,一方面具有較高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面臨美國等先發(fā)強(qiáng)國壓制和中國等后發(fā)國家追趕的雙重壓力,從高附加值的材料端塑造主導(dǎo)產(chǎn)業(yè)競爭優(yōu)勢成為日本鞏固國際地位的重要戰(zhàn)略手段。因此,日本側(cè)重于新材料應(yīng)用研究,并將先進(jìn)基礎(chǔ)材料和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領(lǐng)域列為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
(3)資源稟賦。兩國的資源稟賦差異導(dǎo)致新材料商業(yè)化應(yīng)用模式、市場開拓方式、資源配置方式和創(chuàng)業(yè)實驗舉措不同。美國的龐大利益集團(tuán) “軍工復(fù)合體”通過長期游說政府,使軍工產(chǎn)業(yè)成為三大支柱產(chǎn)業(yè)之首,新材料多服務(wù)于軍工需求。因此,美國軍方在促進(jìn)新材料商業(yè)化應(yīng)用和市場開拓方面承擔(dān)著重要角色。日本主導(dǎo)產(chǎn)業(yè)是汽車、電子信息等民用產(chǎn)業(yè),但由于人口和與國土面積的限制,日本國內(nèi)市場體量嚴(yán)重不足。因此,日本新材料主要通過縱向一體化應(yīng)用于民用產(chǎn)業(yè),通過國際化經(jīng)營拓展市場網(wǎng)絡(luò)。此外,美國資本市場非常發(fā)達(dá),政府稍加引導(dǎo)便能引入民間資本,為民間孵化器推動新材料創(chuàng)業(yè)實驗提供資金支持。日本財閥經(jīng)濟(jì)體下的銀行和財團(tuán)是大型新材料企業(yè)的主要資金來源,中小企業(yè)的融資渠道受限,需要政府干預(yù)調(diào)配資金,并由具有穩(wěn)定資金來源的國立科研院所引領(lǐng)推進(jìn)新材料創(chuàng)業(yè)實驗。
5 結(jié)論與啟示
5.1 結(jié)論
(1)美國采用政府引導(dǎo)-雙輪驅(qū)動-多主體協(xié)同的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政府通過制定戰(zhàn)略政策加強(qiáng)引導(dǎo),大學(xué)、國家實驗室自主創(chuàng)新與軍方需求牽引形成雙輪驅(qū)動機(jī)制,新材料企業(yè)加速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和商業(yè)化應(yīng)用,金融風(fēng)投機(jī)構(gòu)提供資金支持,呈現(xiàn)多主體協(xié)同的開放式創(chuàng)新格局。日本采用政府主導(dǎo)-企業(yè)助推-科研院所配合的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政府通過頂層設(shè)計和統(tǒng)籌部署,自上而下地主導(dǎo)新材料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發(fā)展,企業(yè)在新材料產(chǎn)業(yè)化進(jìn)程中承擔(dān)主角,是實現(xiàn)新材料產(chǎn)業(yè)跨越式發(fā)展的核心助推力,科研院所在政府和企業(yè)的引領(lǐng)下致力于基礎(chǔ)應(yīng)用研究,賦能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
(2)美日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兩國模式的共性體現(xiàn)在服務(wù)國家戰(zhàn)略、加強(qiáng)頂層設(shè)計、注重知識管理和構(gòu)建創(chuàng)新生態(tài)。兩國模式的個性體現(xiàn)在角色定位、重點領(lǐng)域、著力點和舉措四個方面。角色定位方面,美國政府扮演 “引導(dǎo)者”,日本政府扮演 “主導(dǎo)者”。重點領(lǐng)域方面,美國側(cè)重于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日本側(cè)重于先進(jìn)基礎(chǔ)材料和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著力點方面,美國以基礎(chǔ)研究為引領(lǐng)推進(jìn)應(yīng)用研究,強(qiáng)調(diào)技術(shù)開拓創(chuàng)新,通過軍方采購促進(jìn)商業(yè)化應(yīng)用;日本以應(yīng)用為導(dǎo)向基礎(chǔ)研究與應(yīng)用研究并舉,注重技術(shù)精細(xì)打磨,通過縱向一體化加速商業(yè)化應(yīng)用。舉措方面,美國主要由民間機(jī)構(gòu)推動創(chuàng)業(yè)實驗,通過軍民融合開拓市場,依托政策引導(dǎo)民間資本流入;日本主要由政府和國立科研院所推動創(chuàng)業(yè)實驗,通過國際化經(jīng)營開拓市場,由政府依托強(qiáng)有力的制度主導(dǎo)資金調(diào)配。
(3)美日在歷史文化、國際地位和資源稟賦上的差異,是兩國選擇不同的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的深層次原因。歷史文化方面,美國提倡民主自由和開拓進(jìn)取,日本推崇 “強(qiáng)政府”模式和工匠精神。因此,美國在政府的引導(dǎo)下,全社會各主體協(xié)同創(chuàng)新,注重新材料技術(shù)的前沿開拓;日本則強(qiáng)調(diào)政府主導(dǎo),注重技術(shù)精細(xì)打磨。國際地位方面,美國是全面領(lǐng)先的世界唯一超級大國,日本雖是經(jīng)濟(jì)和科技強(qiáng)國,但也面臨美國等先發(fā)強(qiáng)國掣肘和中國等后發(fā)國家追趕的雙重壓力,鞏固各自現(xiàn)有國際地位成為新材料產(chǎn)業(yè)布局重點考慮的維度。因此,美國高度重視基礎(chǔ)研究并重點布局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領(lǐng)域,日本則側(cè)重于應(yīng)用研究并重點突破先進(jìn)基礎(chǔ)材料和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領(lǐng)域。資源稟賦方面,美國國防軍事力量雄厚,資本市場非常發(fā)達(dá);日本主導(dǎo)產(chǎn)業(yè)是民用產(chǎn)業(yè)但其國內(nèi)市場體量不足,各大財團(tuán)是其資本市場的運作主體。因此,美國軍方和風(fēng)險資本為新材料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發(fā)展注入了強(qiáng)大活力;日本則主要由企業(yè)開展縱向一體化和國際化經(jīng)營,加快新材料產(chǎn)業(yè)化進(jìn)程,政府依托于主銀行制度干預(yù)資金調(diào)配。
5.2 啟示
(1)構(gòu)建政府引導(dǎo)-市場驅(qū)動-多主體參與的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協(xié)同攻關(guān)模式。一方面,政府應(yīng)強(qiáng)化頂層設(shè)計,發(fā)揮新型舉國體制優(yōu)勢,集中多主體力量聯(lián)合攻關(guān)新材料核心技術(shù)。為此,政府可以針對性地建設(shè)一批高水平、大協(xié)作、網(wǎng)絡(luò)化的創(chuàng)新平臺,引導(dǎo)新材料企業(yè)、高校院所、金融風(fēng)投機(jī)構(gòu)等多主體協(xié)同創(chuàng)新。另一方面,應(yīng)完善市場機(jī)制,充分發(fā)揮中國超大規(guī)模市場優(yōu)勢,以市場需求驅(qū)動上游創(chuàng)新。促進(jìn)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jié)合,打造多主體協(xié)同、產(chǎn)業(yè)上下游聯(lián)動的新材料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
(2)建立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的識別與甄選機(jī)制,并對重點領(lǐng)域?qū)嵭蟹诸惞芾怼⒕珳?zhǔn)施策。中國應(yīng)統(tǒng)籌把握國際技術(shù)封鎖與制裁的形勢和國內(nèi)重大戰(zhàn)略需求以及技術(shù)長期發(fā)展趨勢,在此基礎(chǔ)上開展技術(shù)預(yù)見,甄選創(chuàng)新突破重點領(lǐng)域。針對技術(shù)成熟度高但趨于低端同質(zhì)化的先進(jìn)基礎(chǔ)材料,企業(yè)應(yīng)構(gòu)建高效的產(chǎn)用結(jié)合機(jī)制,以市場需求為導(dǎo)向,提升材料性能,補(bǔ)足 “有材不好用”的短板;針對核心技術(shù) “卡脖子”且 “市場失靈”的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政府和軍方應(yīng)加強(qiáng)引導(dǎo),聯(lián)合大學(xué)、科研院所和企業(yè)等主體協(xié)同攻關(guān)核心技術(shù),并實施 “首批次應(yīng)用保險補(bǔ)償制度”等需求型政策,加速國產(chǎn)化替代,突破 “有材不敢用”的瓶頸;針對技術(shù)難度高且產(chǎn)業(yè)化程度低的前沿新材料,鼓勵高校院所發(fā)揮主體作用,加強(qiáng)前瞻性基礎(chǔ)研究和知識產(chǎn)權(quán)布局,同時由政府牽頭搭建新材料中試平臺與示范基地,促進(jìn)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與商業(yè)化應(yīng)用,破解 “無材可用”的難題。
(3)加強(qiáng)智能制造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鏈環(huán)節(jié)統(tǒng)籌優(yōu)化與鏈?zhǔn)郊伞R环矫妫瑧?yīng)加強(qiáng)科學(xué)研究、技術(shù)開發(fā)和商業(yè)化應(yīng)用三個創(chuàng)新鏈環(huán)節(jié)的全方面突破。在科學(xué)研究環(huán)節(jié),構(gòu)建多元科研資助體系,保障基礎(chǔ)研究和應(yīng)用研究的穩(wěn)定性,以知識增長驅(qū)動技術(shù)創(chuàng)新;在技術(shù)開發(fā)環(huán)節(jié),鼓勵采用海外并購、技術(shù)引進(jìn)、自主研發(fā)相結(jié)合的方式提升本國技術(shù)能力,實現(xiàn)核心技術(shù)自主可控;在商業(yè)化應(yīng)用環(huán)節(jié),重點把握體量大、高增長的國內(nèi)市場,以新能源汽車和高端裝備制造等重大戰(zhàn)略需求為牽引[25],開展軍民協(xié)同應(yīng)用示范,加速新材料國產(chǎn)化替代。另一方面,應(yīng)強(qiáng)化創(chuàng)新鏈環(huán)節(jié)之間的鏈?zhǔn)郊伞U疇款^組織建立新材料產(chǎn)業(yè)集群和創(chuàng)新聯(lián)盟,實現(xiàn)創(chuàng)新鏈環(huán)節(jié)交互集成、創(chuàng)新鏈與產(chǎn)業(yè)鏈雙鏈融合,推動中國新材料產(chǎn)業(yè)邁上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5.3 局限與展望
本文主要從國家尺度分析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模式,并未選擇具體某種新材料展開具體的分析,尚未能為典型關(guān)鍵新材料的創(chuàng)新突破提供直接的經(jīng)驗借鑒。未來可以選擇半導(dǎo)體、電池隔膜等關(guān)鍵戰(zhàn)略材料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政府、企業(yè)、科研院所等關(guān)鍵行動者的創(chuàng)新交互過程,為我國關(guān)鍵新材料創(chuàng)新突破提供經(jīng)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