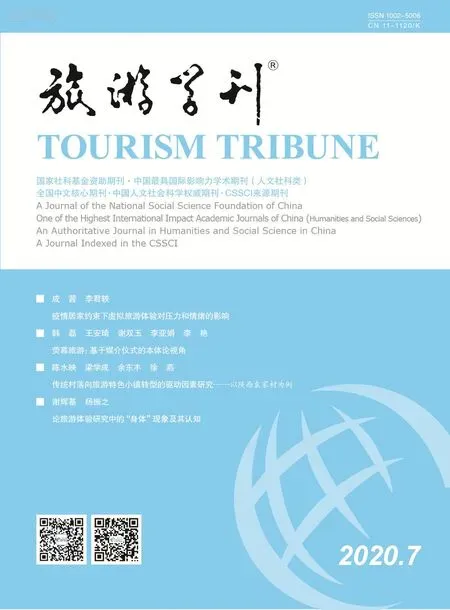目的地依戀記憶的動態表征:從初游到重游的情感遷移
——以海南島為例
董引引,曲 穎
(1.海南大學旅游學院,海南海口 570228;2.浙江工商大學旅游與城鄉規劃學院,浙江杭州 310018)
引言
人地之間的情感聯結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自從段義孚提出“戀地情結”之后,國內外關于地方依戀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隨著現代旅游活動的普及,非慣常性環境、享樂性體驗和暫時性停留的旅游特征使得旅游目的地成為特殊“地方”類型。游客對特定旅游目的地也會產生依戀情感。目的地依戀是人地情感關系嵌入旅游目的地層面的獨特課題。但由于旅游者的短期停留與居民基于長期互動產生的地方依戀具有本質差異。旅游情景下旅游者對目的地的依戀情感遷移機制有待全面探討。
尤其在“情感營銷”轉向的浪潮下,目的地依戀在旅游營銷中具有獨特價值。游客與目的地的情感聯結成為吸引游客重訪和培育游客忠誠的重要因素。雖其穩定性被假定為核心原則,但不同于社區依戀形成中居住時間的延續性。游客對目的地的依戀情感在時間維度上,主要表現為以記憶為載體、以旅游頻次為連接符的特征。目的地依戀作為一種復雜的心理結構,其記憶表征具有時間演化的動態性。
然而以往研究多基于整體性視角,將焦點聚重游者與目的地之間的反饋回路,忽視了重游者也是由初游體驗轉變而來。初游者也會因對大眾媒體知識的吸收或與目的地的直接交互而產生依戀情感。初游和重游作為旅游目的地依戀體驗的一體兩端,是一個連續性的遞進過程,并貫穿于目的地依戀情感發展的始終。在旅游過程中,富含依戀情感的旅游經歷會不斷地以記憶的形式網絡化儲存,并在消費者再次面臨選擇旅游目的地的時候,發揮關鍵作用。但受不同選擇性注意機制的驅動,目的地依戀記憶網絡可能會產生動態化演變。而尋找其中的規律性變化,識別不同旅游細分市場的依戀記憶偏好,對目的地精準營銷具有重要意義。
故本文以海南島為案例地,在目的地依戀的兩個邏輯起點“人”和“地”的基礎上,引入時間演化概念,探討隨著旅游經歷的積累和角色的轉變,游客對目的地的依戀情感記憶在認知網絡結構上的動態化表征機理。
其實,游客在初游和重游的連續性體驗過程中均會對目的地產生依戀情感,且這種依戀之情常呈強化之勢。Williams 等認為,游客與目的地的緊密聯系是在初游體驗后萌芽,并隨著重游經歷的增加而更加牢固。Hou認為,隨著旅游頻次的增加,游客對目的地的依戀會從物理環境向社會文化轉移。目的地依戀作為游客依附地方的主觀心理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造訪次數的增多,其背后內隱的認知圖式和具體心理路徑特征的歷時性和連續性變化亟須關注。
1 研究綜述
1.1 目的地依戀發展的動態性
在旅游目的地營銷中,目的地依戀被認為是導致游客回訪和目的地忠誠的關鍵性因素。目的地依戀作為人地交互經歷所內化為的固定行為模式,其穩定性和持久性一直被假定為依戀理論的核心原則,但作為一種包含時間要素的情感聯結,游客對目的地的依戀情感更傾向一個富有變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Brown 等指出,地方依戀會隨著個人發展、環境和設施的變化而改變。Stokowski表示,游客對目的地的依賴是一個社會性的建造過程,會因個人或集體需求的變化而不斷被改變或再建。Fuhrer 等也認為地方認知是一個不斷變化、不固定的過程。Hammitt 等基于人與地方的深入互動過程,將目的地依戀的遞進劃分為熟悉感、歸屬感、認同感、依賴感和根植感五級聯結強度。
以往研究表明,盡管不斷地訪問某個目的地,游客可能會建立起與居民所感受到的感情相似的強烈情感紐帶,但游客與地方互動的持續時間和頻率通常比居民低。旅游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臨時的、短期的活動,若要建立游客與目的地的情感紐帶,持續性拜訪非常重要,即重游客更可能會形成一種對目的地的依戀感。多次造訪某一或某類旅游目的地會觸發旅游者目的依戀的良性反饋環路。Liu 等認為,重復游客傾向報告與目的地相關的較高水平的地方身份和地方依賴,因為游客首次在目的地積累有意義的記憶的機會有限。但Cheng和Kuo 研究證實,個人也可以與初次游覽的目的地建立情感紐帶。這種觀點主要得到了以下論點的支持:目的地依戀是通過現場參與或與空間環境互動形成的,而不僅僅是與先前經歷相關的參觀前傾向。Yuksel 等也認為游客可能在旅行之前,根據接收到的信息形成期望,開始發展地方依戀的感覺。
1.2 目的地依戀的記憶表征
目的地依戀源于個人與環境之間產生的特殊情感或經驗性的記憶,是人對實體環境產生的情感知覺反應。記憶為理解個人與目的地之間的短期互動過程提供了獨特視角。地方記憶是動態的,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獨立停留的時間長短,可以根據旅游體驗的質量而不是經驗的長度來增加或重新解釋。目的地作為非慣常的環境,游客對目的地依戀情感的持續性面臨著體驗經歷更替的挑戰,但由于記憶的維系,即使遠離依戀的地方人們也會覺得自己依舊和那里保持著緊密的聯系。
記憶是地方依戀的重要組成部分。記憶作為一種心智活動,既是旅游情感體驗的一部分,又直接參與和串聯了旅游地與旅游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在構建目的地依戀上有獨特的作用。時間與記憶的媒介作用使人地紐帶超越環境體驗反應,發展為復雜多義的人類情感。目的地依戀體現了游客對環境記憶的積極情感聯系。Giuliani和Feldman指出,個人與目的地之間的關系是基于比較經驗和記憶的。Erll認為,旅游記憶在人與目的地的關系建立中起著關鍵作用。記憶方式差別關系到地方依戀的不同心理過程,“過程記憶”塑造了地方依戀的核心部分,“自傳體記憶”則是地方認同的重要參照。
記憶對理解目的地依戀在時間軸線上的動態變化有重要的指示意義。人們感知的不僅是地方的現在,還有疊加在可見環境之上的過往記憶。雖然旅游記憶在內容上更多呈現的是“過去”,然而記憶作為旅游活動的衍生和延續,溝通了過去、現在和未來。旅游記憶一方面是對已有旅游行為和體驗的自我總結,另一方面影響未來的旅游決策和實踐。在旅游過程中,富含依戀情感的旅游經歷會被不斷以記憶的形式儲存在腦海中,當消費者再次面臨選擇旅游目的地的時候,人們會依賴記憶來進行決策。即初游和重游的依戀經歷可由記憶來聯結。但同一旅游者在依戀情感驅動下,經歷多次旅游后,其依戀記憶表征可能也會出現差異。
此外,目的地依戀情感的傳達需有一定的記憶載體和依托。依戀之情必須落在具體的空間或特定地方的物質或非物質寄托對象,并構成記憶載體的“錨點”,訴諸某些共有的價值觀念。Lewicka提出了“記憶點”的概念,他提出地方記憶的構成部分內容相當廣泛。Marschall 指出,人們關于一個地方的記憶通常都是意化過的,含有和個人、他人、環境相關的感知及情緒因素在內。但現有研究更多關注目的地依戀的情感成分和行為成分,而忽視其所依附的記憶載體的內在構造如何相互關聯。
1.3 認知網絡模型和選擇性注意機制
盡管依戀通常被定義為對親密關系的單一傾向,但它實際上根植于一個復雜的認知過程網絡,其中包括許多與情景和特定關系相關的依戀表征,依戀情感喚醒主要反映在認知記憶的心理圖式上,對其的解釋主要歸屬于認知心理學范疇。心理學家提出的聯想網絡記憶模型將語義記憶或知識視為由一組節點和關系組成的網絡。節點通過強度不同的關系連接而存儲信息。節點到節點的“激活擴散”過程決定了記憶檢索程度。當編碼外部信息涉及某個節點時,記憶網絡中的該節點將率先處于激活的狀態,并通過連線激活網絡中其他鄰近的節點。故目的地依戀記憶作為心理表征的概念,在提取的過程中也符合認知網絡模型。
但對于初游者和重游者而言,由于旅游經歷和動機的差異,其不同旅游階段的聯想網絡記憶在運行時受選擇性注意機制的驅動而會產生不同變化。選擇性注意是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加工機制對內外界信息進行篩選,以確保有限的認知資源得以高效運行的認知系統。其中,“自下而上”屬于刺激驅動加工機制,即指記憶節點主要受外部刺激的影響,遵循“刺激-反應”的規律,視覺系統在外源性刺激下捕獲注意力。“自上而下”屬于目標驅動機制,是從已有知識概念開始引導注意和信息獲取,達到識別物體和信息的目的。
對初游者而言,由于缺乏先驗經驗,其依戀記憶場主要受目的地景觀的視覺刺激,以“自下而上”的刺激驅動方式捕獲注意。而隨著游覽經歷的增加,依戀情感加深,先驗經驗逐漸發揮作用。“自上而下”的目標驅動會引導重游客關注目的地要素中與自我一致的部分。由于在低頻重游時,依戀情感的排他性不顯著,加之在探索過程中,新出現的、獨特地方性刺激元素仍會發揮作用,記憶網絡運行會呈現兩種選擇性注意方式并駕齊驅之勢。但當處于高頻重游時,隨著依戀情感程度的深化,游客更傾向尋求熟悉景觀,獵奇需求淡化,“自上而下”的目標驅動將會完全占據主導地位。故在選擇性注意引導作用下,不同旅游階段的依戀記憶在遵循“激活-擴散”網絡規律時,可能會出現復雜的演變過程,從而不斷地對依戀記憶表征進行完善和修正。
基于此,本文在目的地依戀的兩個邏輯起點“人”和“地”的基礎上,引入時間軸,探討隨著旅游經歷的積累,游客個體身份在從初游者向低頻重游者和高頻重游者轉變的過程中,受選擇性注意機制的影響,目的地依戀記憶在認知網絡心理結構上的動態化表征機理,分析框架如圖1。

圖1 目的地依戀動態表征的分析框架Fig.1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estination attachment
2 研究設計
2.1 案例地選取
濱海目的地作為以海洋資源為主要吸引力的特殊地方,兼具客觀性和社會建構性雙重特征,是最接近“荒野依戀”的典型形式。而海南島作為我國領土最南端的、唯一的熱帶濱海目的地,自然成為研究目的地依戀的最佳案例地。雖然其旅游發展歷史較為悠久,但近年來進入停滯期特征愈加突出,初游和重游市場比例失衡。在情感營銷轉向下,兼顧初游和重游市場,探討游客對目的地依戀的動態表征具有重要意義。
2.2 樣本搜集
隨著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游客熱衷在旅游網站分享旅游體驗。游記文本是旅游體驗后的自主性記錄,是反映依戀情感記憶的最佳素材之一。為更加全面搜集符合依戀主題,且兼具初游和重游雙重身份的游記文本,選取去哪兒網、馬蜂窩網等國內知名度較高的旅游分享網站。采集標準為:(1)符合Williams等目的地依戀二維度量表(地方依賴和地方認同)的基本思想,如“海南比其他地方更能滿足我的需要”“海南于我而言無可替代”“我對海南強烈認同”“海南對我意義重大”等,最大程度確保依戀文本的準確性。(2)同一ID 在2015—2020 年的5年內最少連續游覽3 次,并有詳細的初游和重游的依戀記憶記錄3 篇以上。原因:5 年短中期時間限制,防止游客依戀情感變化是因外部空間環境變遷而波動;有連續性初游、重游記錄,類似于對同一游客的長線跟蹤調查;3 次旅游經歷更能詳盡展示演化特征。(3)強調游客是因依戀回憶而產生重游,并再次產生了依戀情感,即依戀情感表達貫穿始終(如:“因難以忘卻海南的美,我又重新踏上這座海島重溫舊夢”“海南,你讓我眷戀,我又來了,你依舊讓我心動”等)。共搜集符合標準的ID 有103 個。其中,5 年內游覽3 次的樣本87 個,占比84.47%,游覽4次或5次的樣本僅16個。為保證重游頻次的統一和研究的便利性,僅選用87 個游覽3 次的樣本ID,共261篇游記,將每個樣本的3次游覽分別命名為初游(第1 次游覽)、低頻重游(第2 次游覽)和高頻重游(第3 次游覽),進行分類整理以備后續研究。基于此,可以在保證目的地依戀的兩個基本邏輯“人”和“地”不變的情況下,重點關注心理過程的演變規律。
2.3 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是一種對隱性內容進行客觀、質性描述的研究方法。由于旅游依戀記憶的隱性特質和其依附節點的多樣性特征,需借助內容分析的思想,對具有依戀情感記憶的游記文本進行挖掘,提煉出合理和顯性的記憶節點作為后續分析的基礎,至關重要。故借鑒以往研究成果,本文首先運用ROST Content Mining 軟件對261 篇游記內容進行轉譯,遵循以下步驟:文本預處理-建立詞典-軟件詞頻分析-人工分詞清洗-確立有效高頻詞。以排名前300的高頻詞作為旅游依戀記憶的基本分析單元,首先對高頻詞進一步概念化,采用自下而上的歸納方法提煉旅游依戀記憶要素,整合依戀記憶類目,最終提煉出32 個依戀記憶表征節點,分別歸屬5類依戀載體,如表1所示。

表1 目的地依戀記憶節點表征及主題劃分Tab.1 Node representation and subject division of destination attachment memory
社會網絡分析法:社會網絡是所有行動者及其關系的集合。而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主要關注節點之間的關系,以關系理論和系列分析工具揭示這些關系的模式或結構。根據社會網絡的分析基礎(點、線),可將游客依戀記憶元素作為節點,不同元素在個體游客記憶中的共現作為連線,構建游客依戀記憶元素的共現網絡。基于87 個樣本的261 篇游記,回溯旅游經歷,分別檢測32 個依戀記憶節點其在不同游覽經歷中的共現關系,最終構建初游依戀的21×21 多值網絡、低頻重游依戀的32×32 多值網絡、高頻重游依戀的26×26 多值網絡。并借用社會網絡分析中的指標,對依戀記憶網絡進行點、線、面的全方位解剖,指標具體含義如表2所示。

表2 網絡指標及含義Tab.2 Network indicators and meanings
3 研究結果
3.1 依戀記憶整體網絡形態演變
隨著旅游經歷的積累和依戀情感的驅動,依戀記憶節點規模呈現先增后減的趨勢(表3)。初游時受外源性地方刺激而儲存的記憶點僅21個,在低頻重游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注意力機制并行,記憶節點經歷擴張達到32。但在高頻重游的過程中,游客更傾向于尋找熟悉的景觀,記憶節點逐漸穩定為26個,這也體現了旅游需求多樣化和依戀情感驅動聚合性的雙重特征。然而,網絡密度持續增強,從低密度0.20。逐漸增強為0.46和0.61,記憶節點間的聯系更加頻繁,并伴隨著低網絡效率0.42 向高網絡效率0.56 和0.72 的過渡,節點間激活擴散效應增強。此外,網絡內部結構也逐漸穩固,依戀記憶網絡的類型從隨機網絡發展為具有顯著特征的小世界網絡,聚類系數逐漸增強,平均距離逐漸縮短。多次重游后,依戀記憶網絡形態逐漸定型,其對外抗風險性顯著。

表3 不同旅游經歷下依戀記憶整體網絡指標分析結果Tab.3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overall network index of attachment memory under different travel experiences
3.2 依戀記憶節點權力演變
由于旅游不同階段的記憶節點不同,為便利比較,需對中心性結果進行標準化處理(表4)。

表4 不同旅游經歷下依戀記憶網絡節點中心性Tab.4 Node centrality of attachment memory network under different travel experiences
3.2.1 活躍記憶節點的變化
以不同階段程度中心性排名前5的記憶節點為例,進行綜合性分析,主要體現以下特征:(1)記憶節點活躍度的整體水平不斷提升。在經過多次旅游經歷后,每個記憶元素與其他元素的平均交互作用得到顯著提高,從初游時的47.66,到再游時的50.59,而多次重游后高達52.62。重游會賦予依戀記憶節點更多活力。(2)海洋風光作為海南旅游的主基調,以絕對優勢貫穿目的地依戀記憶發展的全過程。在不同的旅游階段,“海洋風光”均具有顯著的首位度優勢,如從初游時的95,到再游時的89 和高頻重游后的88,但僅在“自下而上”的視覺刺激下發揮最大價值。(3)旅游宣傳對依戀情感的激發作用會隨著旅游經歷的積累而減弱。如“盛名在外”記憶節點在初游階段較活躍,程度中心性高達86,但隨著旅游經歷的積累,其活躍度急速下降,從初游時的第2位,滑落至再游時的第7位,并在多次重
游記憶網絡中消失。旅游宣傳僅對初游者和低頻重游者有效,但對受“目標驅動下”的重游者失效。(4)隨著旅游經歷的增加,社會文化價值被充分發掘,非物質載體的依戀記憶節點開始凸顯并占據重要角色。如“民俗風情”在重游階段排序穩定在前3。游客在重游時關注焦點開始向社會文化方面傾斜。而如“社交活動”作為高級的具身實踐載體,在初游中并未被識別,而是在低頻重游后被發掘,在高頻重游后被鞏固。依戀型游客會尋求從旁觀者向參與者的角色轉變,并期待與目的地的真正融入。
3.2.2 中介橋梁記憶節點的變化
以不同階段大于均值的記憶節點為代表進行分析。(1)記憶節點承擔中介職能的整體能力提升,但差異性趨大。隨著旅游經歷的積累,平均每個元素的中介中心性提高(從2.83 提升為6.65),并伴隨著標準差的急速擴張(從5.29到12.49),即僅有少數元素承擔網絡橋梁的關鍵性作用。這意味著目的地依戀記憶網絡在不斷完善的同時,也是對決定性的核心節點進行不斷篩選和精簡的過程。(2)海南的刻板印象被打破,多樣性旅游價值被發掘。在初游階段“海洋風光”雖占據絕對的中介主導地位,但在重游過程中逐漸被“免稅購物”和“價值認同”所替代,位序跌落至第4 位和第5 位。依戀型游客的旅游偏好具有從觀光旅游逐漸向參與式體驗旅游和情感旅游轉變的特征。這也符合初游向重游過渡的一般性特征。(3)在低頻重游階段,基礎性的旅游供給發揮關鍵性的中介作用。如“免稅購物”聯合“美食”和“旅游設施”等基礎性旅游供給,僅在低頻重游時中介中心性大于均值5.24。低頻重游者對基礎性旅游供給的關注是其嘗試融入目的地的第一步。(4)高頻重游階段,精神情緒載體和具身實踐載體的記憶節點占據主導地位。在高頻重游網絡中,“價值認同”“逃逸遁隱”和“社交活動”等節點中心性大于23,在依戀記憶網絡中承擔著關鍵性的中介職能。這與“目標驅動”引導游客優先關注非物質節點和情感節點的特征相符合。
3.3 依戀記憶網絡路徑演變
以排名前10的強邊權網絡路徑為例,并結合核心邊緣元素劃分,排名前5 的程度中心性元素和中介中心大于均值的元素為核心元素(core,C),程度中心性大于均值元素的為重要元素(medium,M),而其他元素為邊緣元素(periphery,P)進行綜合分析(表5)。

表5 不同旅游經歷下依戀記憶網絡邊權分析Tab.5 Analysis of the edge power of the attachment memory network under different travel experiences
主要體現以下演化特征:(1)網絡路徑覆蓋記憶節點增多的同時,路徑寬度也得到拓展,網絡傳輸效率提高。從初游階段,強邊權僅涉及7個元素,權重值域僅為[5,16],在重游驅動下,節點快速增加至12 和14 個,權重值域拓寬為[7,18]和[10,20]。這意味著隨著旅游經歷的積累,游客對目的地依戀記憶的聯想會更加順暢。(2)核心元素間的極化效應減弱,而核心元素與重要元素、邊緣元素間的互動性增強。初游階段,排名前10 的邊權中,僅涉及兩個非核心元素,80%的強邊權在核心元素間產生,重游階段涉及的非核心元素增多(5個和8個),其被納入強邊權的比例增至40%和60%。究其原因:初游者具有理性消費者的特質,傾向于核心景觀元素間的聯動消費,而重游者作為感性消費者,在目標驅動下,會突破核心邊緣景觀的界線,以情感滿足為游覽標準。(3)網絡路徑具有繼承性和斷裂性并存的特點。在初游向重游過渡中,僅有海洋風光-民俗文化和海洋風光-氣候天象兩條強邊權貫穿始終,整體上斷裂性(占比70%)高于繼承性(占比30%)。但在低頻重游向高頻重游演進的過程中,具有5 條相同的強邊權,繼承性占比50%。這意味著旅游經歷的積累,一定程度上可以強化依戀記憶網絡路徑的穩固性。(4)網絡路徑的空間形態從點狀輻射向長線連接和片狀分散轉移。在初游時,網絡路徑呈現以“海洋風光”為中心向其他元素輻射,強邊權中,海洋風光占比60%,在低頻重游階段,強邊權間呈現線狀連接,典型長線路如:“海洋風光-民俗風情-歷史遺跡-氣候天象-逃逸遁隱”;而在高頻重游時,出現分別以“海洋風光”“氣候天象”“市井生活”和“愛情艷遇”為中心的片狀短線連接。初游者滿足視覺刺激下的單調性景觀游覽,而目標驅動下的重游者傾向長線游和主題游。
3.4 依戀記憶網絡社團演變
對不同旅游經歷下的依戀記憶網絡社團的分析,對解析其局部性聚集具有重要意義,社團類別如表6,為進而考察不同社團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強中心性元素作為社團的主代表命名。節點越大,社團的核心度越高,連線越粗,不同社團間的互動越頻繁(圖2)。

圖2 不同旅游經歷下記憶網絡社團演變Fig.2 The evolution of memory network associations under different travel experiences

表6 不同旅游經歷下依戀記憶網絡社團劃分Tab.6 Classification of attachment memory network associations under different travel experiences
主要演化特征為:(1)社團數量呈現先增后減趨勢。低頻重游社團數量最多,為7個,高于初游(4個)和高頻重游(5個)。低頻重游階段,受雙重選擇性注意力機制的驅動,為游客多主題性旅游探索提供了契機,但當依戀情感的升華后,“目標驅動”下又會弱化部分邊緣性主題。(2)同一社團在初游向重游的過渡中,包容性增強,影響力減弱。如以海洋風光為主的核心社團1在初游時僅兼容4個核心元素,影響力為0.75,低頻重游時,社團1的組合類型為C(3 個)+M(2 個),影響力為0.7,高頻重游時,組合類型為C(2個)+M(2個)+P(2個),但影響力下降為0.6。游客通過與目的地多次深度交互,拓展了對主題社團的外延性認知,但“目標驅動”會沖擊因“視覺刺激”而聚合社團的凝聚力。(3)不同社團之間也存在拆分重組的變化過程。如民俗風情社團經歷了從裂變到升華的過程。以“民俗風情”為主導的社團2,在低頻重游時裂變為以“宗教祈福”為主導的社團4和以“民俗風情”為主導的社團7,但在多次重游后,重組為以“社交活動”為主導的社團2,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人文旅游體驗,即是游客依戀的終極歸屬。隨著旅游經驗的積累,游客對部分主題性景觀也會經歷從好奇探索(被核心景觀吸引)到謹慎審視(細分景觀內涵)再到包容(意義升華)的過程。(4)社團聯動過程的動態演變。初游階段以社團1(海洋風光)和社團3(熱帶植物)的自然景觀聯動為主(連接度為0.8),體現了自然景觀間的抱團式發展;而低頻重游時,社團1(海洋風光)和社團5(民俗風情)的連接最突出(0.8),自然景觀開始向人文景觀跨越式連接;但經過高頻重游后,社團2(社交活動)與社團4(逃逸遁隱)的強聯動(0.8)聯合海洋風光社團1 組成穩定鐵三角。“視覺刺激”易促發自然類景觀的聯動,而“目標驅動”會引導游客關注人文景觀,尋找旅游意義。同時這也符合從觀光游向深度游的演變特征。
4 結論與討論
4.1 研究結論
本文以海南島為案例地,在保證“個體”和“空間”相對不變的情況下,借鑒選擇性注意機制和記憶網絡模型,引入時間演化的邏輯線索,探討游客身份在初游者向重游者轉變的過程中,目的地依戀記憶網絡的動態表征規律。研究發現:(1)目的地依戀記憶整體網絡的內部結構逐漸穩固。多次旅游經驗可以使與目的地相關的認知結構更加精煉、完整和真實。(2)隨著旅游經歷的積累,目的地依戀記憶網絡中的核心節點逐漸從功能性節點向情感性節點轉變,從物質載體節點向非物質載體節點轉變。(3)重游者在“目標驅動”下,呈現感性消費的特征,記憶網絡路徑追溯會突破核心邊緣的界線。(4)游客在與目的地多次深度交互中,不斷地重構著主題社團的內涵和外延。
4.2 理論價值
“目的地依戀”作為“地方依戀”的一個子類,因其獨特的情感營銷價值而被廣泛關注,但在旅游領域研究中,游客能否產生地方依戀曾受到極大質疑。旅游目的地情景下非慣常異地環境有別于社區鄰里、地方重建等強調社會意義的慣常環境。旅游者的短暫停留和居住者的長期互動具有顯著差異。然而,其實游客作為“局外人”,其對目的地的依戀情感在時間維度上,主要表現為以記憶為載體、以旅游頻次為連接符的特征。目的地依戀作為一種復雜的心理結構,其記憶表征具有時間演化的動態性。但以往研究傾向于將其視為靜態結構,缺乏對目的地依戀情感記憶變化的復雜心理結構進行剖析。旅游情景下旅游者對目的地的依戀情感遷移機制有待全面探討。本文采用同一樣本的縱向研究方法,實現了對目的地依戀記憶連續性變化的監測,豐富了時間框架下,對目的地依戀動態表征的理論支持。該研究有助于增進人們對游客在沒有長期不間斷互動的情況下(區別于居民)與旅游目的地發展粘合機制的理解。
研究發現,隨著旅游頻次的增加和依戀情感的深化,游客對目的地依戀情感記憶的關注重點會從物理特征向社會關系和情感認同轉移,這表現出與社區依戀相似的特征。結合目的地依戀的二維度分析發現,目的地依戀記憶傾向從地方依賴維度向地方認同維度過渡。原因可能在于,初游者因更易受拉動(外部,認知)因素激勵,而對目的地某一物質資源產生功能性依戀,而重游者卻受推動(內部,情感)因素驅動,更愿意主動參與到目的地的社交活動中,尋求形成價值認同,從而產生情感性依戀。借鑒Iso-Ahola的研究,目的地依戀記憶的變化可以概括為是一個從“遠離某物”向“主動靠近”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與Fakeye和Crompton的論點是一致的,即初訪者主要受他們對目的地的想象理解的影響,因此更多地關注認知屬性,而重游客往往會受到目的地依戀情感的影響,更注重心理意義,而初游者形成的功能性依賴是激活重游者更高層次依戀關系的關鍵。該研究也是對目的地依戀內部運行機制“黑箱”的另一種重要補充。
4.3 管理啟示
本研究通過區分不同旅游經歷下游客細分市場對目的地的依戀的差異性,為目的地精準營銷指明了方向。對于初游者而言,多途徑的旅游宣傳是培育游客目的地依戀的第一步,“文旅融合”發展戰略是滿足低頻重游者對目的地社會文化知識探究的重要途徑,而塑造地方氛圍、強化游客的地方認同感能夠在更高層次契合高頻重游者的目的地依戀記憶特征。而在旅游景觀組合推廣的過程中,除優先特色核心景觀的強強聯合外,也需要注重不同權力節點,如核心節點對邊緣節點的聯動,以及不同景觀類型間的組合投射,如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搭配,并強化旅游活動等具身實踐的融入。通過培育主題明確的專項旅游形式,提高局部小社團旅游景觀群的包容性,以此來滿足不同旅游細分市場下差異化旅游訴求。
4.4 局限與展望
然而,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仍不可避免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樣本量較少,僅為87人,時間跨度短,僅5年,低頻重游和高頻重游的區分界線僅有以旅游兩次和旅游3次為象征性代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數據的豐度,后期可考慮與實地的長線跟蹤調查相結合,延長時間軸,擴大樣本量,設計科學的細分變量,從而在對研究結果進行多方印證的同時,更精準把控目的地依戀動態表征的規律。第二,由于網絡文本數據的被動性,雖明確選取了因有依戀回憶而產生重游意愿的游記,但由于游客重游動機的復雜性,無法明確量化因依戀情感而重游的成分比例,即無法完全保證所有樣本均百分百滿足依戀情感驅動是重游核心關鍵性主因的條件。而且由于海南目的地的特殊性,也可能會模糊候鳥型重游客和大眾型依戀游客的界線。在未來研究中可選擇主動性訪談的方式,針對性搜集依戀型游客樣本,對研究結果進行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