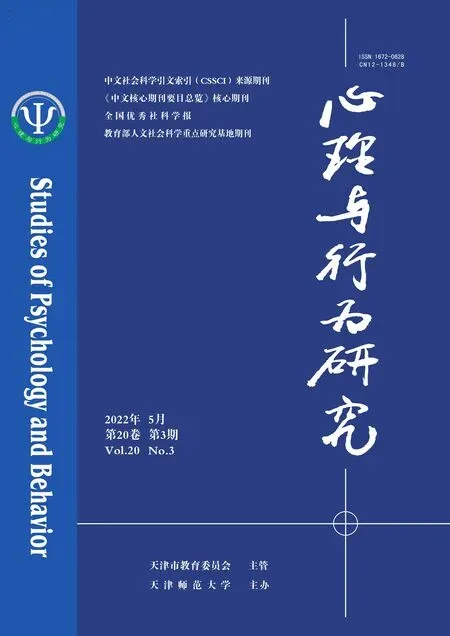社會責任感調節群際替代性排斥中旁觀者第三方懲罰 *
郭豐波 黃佳珊 劉騰飛 谷 莉
(廣東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生命質量與應用心理研究中心,生命質量與心理測評干預重點實驗室,東莞 523808)
1 引言
替代性排斥(vicarious ostracism)是個體觀察到他人遭受排斥時,其自身體驗到排斥感的心理現象(Wesselmann et al., 2009)。經歷替代性排斥的個體,不僅可以感受到被排斥者的痛苦,使得自身基本需求受阻(Wesselmann et al., 2009,2013),還會產生身體疼痛、社會痛苦及負面情緒等,導致自我調節功能受損(Poon et al., 2020)。為緩解替代性排斥導致的消極體驗,個體會對排斥情境進行干預,如補償被排斥者(Masten et al.,2011)或懲罰排斥者(Rudert et al., 2020)。
根據替代性排斥發生水平可將其分為人際替代性排斥(interpersonal vicarious ostracism)和群際替代性排斥(intergroup vicarious ostracism)。群際替代性排斥是旁觀者觀察到內群體或外群體成員被所屬或其他群體排斥時體驗到排斥感的心理現象(Yang et al., 2021)。有研究發現旁觀者會將排斥歸因于排斥源,而非被排斥者,個體即使付出代價也會對無理排斥者付諸懲罰,因此旁觀者行為反應可能不受群體身份影響(Arpin et al., 2017;Rudert et al., 2020)。但也有研究發現旁觀者群體身份會對其干預行為產生影響,如讓被試觀看群體排斥視頻后填寫干預意愿問卷,發現當外群體排斥內群體時旁觀者會對外群體行為進行干預(Abbott & Cameron, 2014; Levine et al., 2002),然而這些研究并未指明具體干預措施;也有研究者通過網絡擲球游戲(Cyberball Game)創設群際替代性排斥對旁觀者行為進行研究,發現即使旁觀者厭惡排斥,也不會對被內群體排斥的外群體進行補償(Lelieveld et al., 2020),但會對內群體被排斥者補償性地拋更多的球(Forbes et al., 2020)。然而,對被排斥者拋更多的球,意味著排斥者接球數量的減少,可視為對排斥者的懲罰。這些研究表明群體身份對群際替代性排斥中旁觀者行為具有復雜影響,因此有必要對群體身份的影響作用進行深入探討。
第三方懲罰(third-party punishment)是個體為維護社會規范而付出個人代價對規則違背者所實施的懲罰行為(陳世平, 薄欣, 2016)。當目睹他人不公平行為時,基于人類社會基因進化模式發展而來的維護群體規范共性,個體會采用第三方懲罰以維護公平(王亞茹 等, 2019)。第三方懲罰不僅可以直接降低違規者收益,相較于補償受害者更能有效維護社會規范(Fehr & Fischbacher, 2004),且可以顯著減少社會排斥(Spaans et al., 2019),替代性排斥中旁觀者對排斥者的懲罰可被視為第三方懲罰。當個體以群體身份劃分并獲得認同后會表現出群體偏見,對內群體更為善意和寬容,而對外群體則更為猜忌和敵意,這種內群體偏愛削弱了針對內群體成員的社會規范執行(Kubota et al., 2013; McAuliffe & Dunham, 2016)。且群際替代性排斥研究發現當觀察到內群體遭受外群體排斥時,旁觀者感受到較大群際威脅,并對排斥者表現出更高攻擊意向(Mendes et al., 2008; Yang et al., 2021)。因此,相對于內群體排斥者,旁觀者可能對外群體排斥者施加更高強度的懲罰。
個體對社會排斥的反應受個人背景、特質等因素影響(Arpin et al., 2017),其中個人特質具有較大差異且不易受外界環境干擾,因此,旁觀者個人特質可能影響其在群際替代性排斥中的行為反應。社會責任感(social responsibility)是個體為了社會繁榮和社會成員共同利益而維護社會規范的態度和行為傾向(沈倩如, 李巖梅, 2020),社會責任感越強越容易感知到維護社會規范的必要性,進而采取第三方懲罰等措施來維護社會規范(陳思靜, 馬劍虹, 2011)。高社會責任感個體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Steele et al., 2008),且對破壞社會規范的行為產生更強的憤怒情緒,進而表現出更高的第三方懲罰(陳思靜, 馬劍虹, 2011)。因此,高社會責任感旁觀者觀察到排斥行為時可能對排斥者施加更高強度的懲罰,且憤怒情緒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替代性排斥中旁觀者會對排斥者行為動機進行歸因,如果不能找出社會可接受的排斥動機,則會將排斥歸因于惡意動機(Rudert &Greifeneder, 2019),并且替代性排斥中缺乏參考信息時旁觀者會認為排斥者具有惡意動機(Wesselmann et al., 2013)。研究表明群際替代性排斥中旁觀者會將組外成員對組內成員的排斥歸因于外群體對內群體的偏見(Yang et al., 2021),因此,當組內成員被排斥時旁觀者會體驗到強烈的惡意動機,相較于低社會責任感個體維護自身利益,高社會責任感個體為遏制群體偏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可能對組外排斥者施加比組內排斥者更高強度的懲罰。Rudert和Greifeneder (2019)還認為旁觀者幫助被排斥者可能使其成為下一個受害者;Forbes等(2020)發現旁觀者更能容忍組內成員排斥組外成員,且不對其進行干預,因此當組外成員被排斥時,旁觀者為避免成為受害者,實施處罰時會衡量排斥者的身份。低社會責任感個體為維護個人利益,避免被群體成員排斥,對組內排斥者施加的懲罰強度低于組外排斥者;而對于高社會責任感個體,由于組內外排斥者均違反社會規范,高社會責任感個體對其均施以較高懲罰。
綜上,先前對群際替代性排斥中旁觀者行為反應的研究并未明確區分補償和懲罰,且未考察旁觀者個人特質對其行為反應的影響。鑒于第三方懲罰能夠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并減少社會排斥(Fehr & Fishbacher, 2004; Spaans et al.,2019),本研究擬采用第三方懲罰來衡量旁觀者對群際替代性排斥中排斥者的行為反應,并進一步揭示旁觀者社會責任感水平對其行為反應的調節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明尼蘇達多相人格調查表的社會責任感分量表對303名大學生進行測評,該量表共32個項目,采用2分計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社會責任感越強,該量表在正常成人中的重測信度為0.76(紀術茂, 戴鄭生, 2004)。參考已有研究(陳思靜, 馬劍虹, 2011),將總分高于均值者劃分為高社會責任感組,低于均值者劃分為低社會責任感組,從中分別招募30人參與實驗,其中一人中途退出實驗,一人對實驗表示懷疑,最終58人完成實驗,高社會責任感組28人(男生6人),低社會責任感組30人(男生11人)。高社會責任感組社會責任感得分(13.79±3.05)顯著高于低社會責任感組(8.30±1.39),t=8.71,p<0.001,d=2.32。被試平均年齡19.48±0.94歲,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實驗完成后給予被試一定報酬。
2.2 實驗設計
采用2(社會責任感:高、低)×2(被試與排斥者關系:組內、組外)×2(被試與被排斥者關系:組內、組外)混合實驗設計。其中社會責任感為被試間變量,被試與排斥者、被排斥者關系為被試內變量。因變量為第三方懲罰強度,即被試懲罰排斥者的代幣數量,數量越多,表明懲罰強度越高。
2.3 實驗任務
2.3.1 網絡擲球任務
采用網絡擲球游戲模擬社會排斥,該游戲可有效用于忽視情境的社會排斥研究(楊曉莉 等,2019)。游戲中三名玩家共同完成30次傳球,通過控制接/傳球次數實現接納和排斥操縱。其中接納條件下每名玩家均可接到十次傳球;而排斥條件下其中一名玩家只能接到兩次傳球。研究中替代性排斥任務要求被試觀看排斥情境的擲球,其中既有玩家被接納也有玩家被排斥的情境,被試作為旁觀者可同時觀看到接納和排斥情境,該任務能夠有效誘發被試的替代性排斥(Wesselmann et al., 2009)。
2.3.2 數量估計任務
采用最簡群組范式操縱群體身份(Tajfel et al.,1971),用于被試與游戲玩家之間形成群體身份。本研究采用“數量估計任務”操縱群體身份,被試完成點的數量估計,依據點估計的結果將其分為高估者和低估者兩種群體身份(溫芳芳, 佐斌,2018)。
2.3.3 第三方懲罰任務
采用第三方懲罰任務評估被試對網絡擲球游戲中各玩家表現的態度。被試被告知,他和擲球游戲中的三名玩家均有50代幣收益,他可以拿出所擁有的部分代幣來減少其他玩家更多收益作為懲罰,以示對該玩家在擲球游戲中表現的憤怒。被試為懲罰其他玩家每拿出1代幣會使該玩家收益相應減少3代幣。被試報酬將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為基礎費用,另一部分為額外費用。假設被試懲罰玩家A投入代幣數為X,那么被試的額外費用為(50-X)×0.08。也就意味著,被試投入的代幣越多,他們最終獲得的報酬越少(朱曉宇, 2020)。
2.4 實驗程序
被試首先對7張大小、數量和空間分布均不相同的黑點圖片進行數量估計。數量估計完成后提供偽反饋,即被隨機反饋為高估者或低估者。然后完成四個7點評分的群體身份操縱檢驗問題,檢驗問題均分高于4分則表明群體身份操縱有效(Arpin et al., 2017)。
隨后被試作為旁觀者觀看網絡擲球游戲,被試被告知與他同時進行實驗的其他三人(用A、B、C表示)將進行30次相互傳球。游戲中代表不同玩家的小人穿著不同顏色衣服作為群體身份標識(高估者、低估者),被試將觀看這個游戲并對三名玩家間的互動進行評估。實驗包括四種條件(見表1),每種條件下玩家A(被排斥者)總是被玩家B和C(排斥者)排斥,即玩家A只能接到兩次球,四種條件呈現順序在被試間平衡。被試每觀看完一個投球游戲,首先,回答是否與其他玩家同組,以檢驗被試是否清楚玩家身份。然后,被要求分別對游戲中三名玩家被接納、被排斥、高興和憤怒程度進行7點評估(Arpin et al.,2017; Yang et al., 2017),通過比較被試對被排斥者和排斥者的評估分數來檢驗排斥操縱成功與否。為便于比較和解釋,將被試對兩名排斥者的評分取均值后與被排斥者的評分進行比較。最后,被試根據各玩家在游戲中的表現決定第三方懲罰強度,被試在自己和每名玩家中進行代幣分配,同樣將被試對排斥者的平均懲罰數量作為第三方懲罰指標。

表1 實驗中四種排斥條件
3 結果
3.1 操縱檢驗
將被試對排斥者和被排斥者的接納感和排斥感評分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所有條件中排斥者的接納感評分均顯著高于被排斥者(ps<0.001,ds≥2.33);被排斥者的排斥感評分均顯著高于排斥者(ps<0.001,ds≥1.12)。進一步將被試對排斥者和被排斥者的情緒評分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所有條件中被試對被排斥者的憤怒評分均顯著高于高興評分(ps<0.001,ds≥1.28),被試對被排斥者的憤怒評分均顯著高于對排斥者的憤怒評分(ps<0.001,ds≥1.10)。這表明排斥操縱有效且被試體驗到排斥感。此外,被試群體身份操縱檢驗得分(4.79±1.29)顯著大于4分(t=4.69,p<0.001),表明群體身份操縱有效,被試對所屬群體有較高認同感。
3.2 不同排斥條件下懲罰強度差異
各條件中被試對被排斥者和排斥者懲罰強度見表2,配對樣本t檢驗表明,所有條件中被試對排斥者懲罰強度均顯著高于對被排斥者懲罰強度(ps<0.001,ds≥0.56)。

表2 旁觀者對排斥者和被排斥者的懲罰強度
將被試懲罰排斥者的強度進行2(社會責任感:高、低)×2(被試與排斥者關系:組內、組外)×2(被試與被排斥者關系:組內、組外)三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社會責任感主效應顯著,高社會責任感個體對排斥者懲罰強度(8.77±6.66)顯著大于低社會責任感個體(3.73±4.31),F(1, 56)=11.85,p<0.01,η2p
=0.18;被試與排斥者關系主效應顯著,被試對組外排斥者懲罰強度(6.93±6.86)顯著大于組內排斥者(5.58±5.62),F(1, 56)=8.51,p<0.01,η2p=0.13;社會責任感、被試與排斥者關系、被試與被排斥者關系交互作用顯著,F(1, 56)=4.98,p<0.05,η2p=0.15,進一步分析表明(見圖1),當組內成員被排斥時,高社會責任感個體對組外排斥者懲罰強度顯著高于組內排斥者(p<0.05, 10.30±9.95 vs.7.46±5.93),而低社會責任感個體對組內外排斥者懲罰強度無差異(p>0.05, 3.52±4.78 vs. 4.48±5.95);當組外成員被排斥時,低社會責任感個體對組外排斥者懲罰強度顯著高于組內排斥者(p<0.05,4.78±6.42 vs. 2.15±2.31),而高社會責任感個體對組內外排斥者懲罰強度無差異(p>0.05, 9.11±7.04 vs. 8.21±9.06)。

圖1 高低社會責任感個體在群際替代性排斥中的懲罰強度
3.3 憤怒情緒在社會責任感和懲罰強度之間的中介作用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憤怒情緒在社會責任感和懲罰強度間的中介作用,將各條件中被試對被排斥者的憤怒情緒評分和懲罰強度平均,采用PROCESS宏程序模型4對上述變量進行中介效應分析。以懲罰強度為結果變量,被試社會責任感分數和憤怒情緒評分為預測變量建立回歸方程,R2=0.14,F(2, 55)=4.41,p<0.05,社會責任感正向預測憤怒情緒,β=0.17,SE=-0.51;t(55)=2.07,p<0.05,95% CI=[0.003, 0.21]。憤怒情緒正向預測懲罰強度,β=1.49,SE=0.58;t(55)=2.56,p<0.05,95% CI=[0.32, 2.65]。憤怒情緒在社會責任感與懲罰強度之間具有完全中介作用,間接效應為0.25,95% CI=[0.03, 0.37];直接效應為0.19,95% CI=[-0.30, 0.62]。
4 討論
本研究中不同社會責任感個體觀看排斥情境的網絡擲球游戲形成替代性排斥,采用數量估計任務對替代性排斥中各玩家之間形成不同群體身份,并采用第三方懲罰方式考察不同社會責任感旁觀者對替代性排斥中排斥者的行為態度。結果發現高社會責任感旁觀者對排斥者懲罰強度高于低社會責任感旁觀者,且憤怒情緒在社會責任感和懲罰強度間起完全中介作用;旁觀者對外群體排斥者懲罰強度高于內群體排斥者;高社會責任感個體對排斥組內成員的組外排斥者懲罰強度高于組內排斥者,而低社會責任感個體對排斥組外成員的組外排斥者懲罰強度高于組內排斥者。
4.1 憤怒情緒導致高社會責任感個體更高的懲罰強度
社會責任感是個體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心理品質,是利他行為的有效預測指標(黃四林 等,2016)。第三方懲罰作為一種重要利他行為,能有效減少社會排斥(Pieter et al., 2019),因此,面對社會排斥時高社會責任感者個體基于利他性驅使可能對排斥者施以更高強度懲罰。研究表明個體面對社會規范違背時體驗到強烈的負性情緒(Fehr &Fischbacher, 2004; Wang et al., 2011),且負性情緒強度與第三方懲罰強度正相關(Gummerum et al.,2020; Lotz et al., 2011)。因此個體觀察到排斥行為時會激發負性情緒,進而導致個體做出更高強度的第三方懲罰。Giesen和Echterhoff(2018)發現觀察到的排斥和自身體驗到的排斥所帶來的消極情緒一致,故旁觀者對被排斥者憤怒情緒的評估,實質上反映了其自身對排斥行為的憤怒。陳思靜和馬劍虹(2011)研究發現高社會責任感個體對破壞社會規范的行為產生更強烈的憤怒情緒,并表現出更高強度第三方懲罰。本研究中旁觀者社會責任感正向預測其對被排斥者憤怒情緒評分,且憤怒情緒在社會責任感和懲罰強度之間呈完全中介作用。這表明高社會責任感個體觀察到他人被排斥時其內化的接納社會規范被激活,激發其強烈的憤怒情緒,進而對排斥者施以更高強度懲罰。
4.2 內群體偏好導致旁觀者對內群體排斥者施以較低強度懲罰
內群體偏好是一種系統性地偏好自己所在群體和群體成員的現象(Masuda & Fu, 2015),當個體對其所屬群體形成認同后,會傾向于采用積極的、正面的方式評估其所屬群體及成員,從而更可能包庇、寬容內群體成員的過失,對內群體成員失范行為給予合理化解釋(Kubota et al., 2013)。這種內群體偏好使得內群體成員的違規行為被群體認同誘發的積極評價所抵消,從而削弱了針對內群體的社會規范執行,降低了內群體被懲罰的可能性與強度(McAuliffe & Dunham, 2016)。研究表明旁觀者觀察到內群體被外群體排斥時感受到更大的群際威脅,且對排斥者表現出更高攻擊意向(Mendes et al., 2008; Yang et al., 2021)。本研究通過數量估計任務對替代性排斥中玩家和旁觀者的群體身份進行操縱,在旁觀者、排斥者和被排斥者之間形成不同群際身份關系,并且這種群際身份得以內化認同。由于旁觀者與排斥者共享群體身份,因此旁觀者可能會低估內群體排斥者排斥行為的攻擊性和失禮程度,從而更包容他們的失范行為,進而導致其對內群體排斥者施以較低強度懲罰。
4.3 社會責任感調節群際替代性排斥中旁觀者的懲罰強度
社會規范是群體成員均接受并遵從的行為準則(Cialdini & Trost, 1998),個體社會責任感影響社會規范激活,高社會責任感個體更容易激活社會規范意識,并維護這種社會規范(陳思靜, 馬劍虹, 2011),而低社會責任感個體更注重自身利益(吳倩, 2020)。Rudert和Greifeneder(2019)認為替代性排斥中旁觀者會對排斥者行為動機進行歸因,如果旁觀者不能找出社會認可的排斥動機就會將排斥歸因于惡意動機。當替代性排斥中缺乏參考信息時,旁觀者會認為排斥者具有惡意動機,并通過補償被排斥者或懲罰排斥者恢復公平(Wesselmann et al., 2013)。研究發現當旁觀者觀察到組內成員被組外成員排斥時會將這種排斥行為歸因于外群體對內群體的偏見,并對排斥者表現出更高攻擊意向(Yang et al., 2017; Yang et al.,2021),而群體偏見是一種違背社會公平規范的行為。因此,當組內成員被排斥時,無緣由排斥和群體偏見會導致旁觀者體驗到強烈的惡意動機。高社會責任感個體為了維護社會公平、遏制社會偏見,會對組外排斥者施以比組內排斥者更高強度的懲罰;而低社會責任感個體為維護個人利益,對組內外排斥者的懲罰強度無差異。Rudert和Greifeneder還認為替代性排斥中旁觀者幫助被排斥者可能會使其成為排斥的下一個受害者。并且,Forbes等(2020)研究發現當旁觀者更能容忍組內成員對組外成員的排斥行為,且不對其進行干預。因此,當組外成員被排斥時,旁觀者為避免成為排斥的受害者,需要考察排斥者群體身份進而進一步衡量對其實施的懲罰強度。低社會責任感個體為維護個人利益,避免遭到群體成員驅逐,對組內排斥者施加的懲罰強度低于組外排斥者。但無論排斥者是組內成員還是組外成員,高社會責任感個體會認為他們均違反了接納的社會規范,進而為維護社會公正對排斥者均施加較高強度的懲罰。
5 結論
高社會責任旁觀者對替代性排斥體驗到更強憤怒情緒,并對排斥者施以更高懲罰;高社會責任感個體對排斥組內成員的組外排斥者懲罰強度高于組內排斥者,而低社會責任感個體對排斥組外成員的組外排斥者懲罰強度顯著高于組內排斥者。旁觀者社會責任感調節其在群際替代性排斥中的第三方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