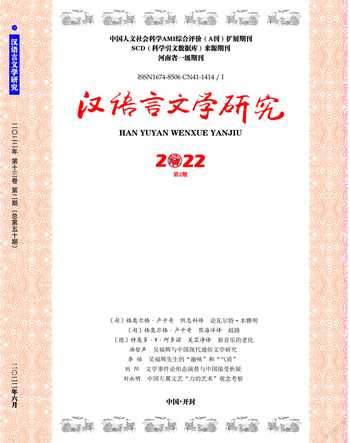論瓦爾特·本雅明
格奧爾格·盧卡奇 陰志科
摘? 要:盧卡奇認(rèn)為,本雅明為現(xiàn)代藝術(shù)提供了深刻且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支撐。本雅明從當(dāng)下意識(shí)形態(tài)和藝術(shù)需求的角度解讀了巴洛克與浪漫主義,經(jīng)過本雅明解讀的德意志巴洛克悲苦劇擁有了內(nèi)在的一致與連貫性,其中包含著揭示藝術(shù)本身的法則的意圖。本雅明認(rèn)為寄喻和象征表達(dá)了人類對(duì)現(xiàn)實(shí)回應(yīng)的根本性分歧,由此盧卡奇也探討了歌德、謝林、索爾格到施萊格爾與諾瓦利斯等人對(duì)象征和寄喻所做的區(qū)分。當(dāng)然,盧卡奇也在暗中把本雅明的思想延伸到了他自己的拜物(戀物)和典型等概念上來。
關(guān)鍵詞:盧卡奇;本雅明;寄喻;物
本文意在闡明,在理論和實(shí)踐兩個(gè)方面,現(xiàn)代主義先鋒派都明顯體現(xiàn)著寄喻(allegory)的精神。
最近幾十年間,批評(píng)家們一方面致力于研究巴洛克和浪漫主義之間的根本關(guān)聯(lián),另一方面探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基礎(chǔ),這絕不是一個(gè)偶然現(xiàn)象。他們這樣做的意圖是為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基礎(chǔ)下一個(gè)定義,并使其合法化,讓后者成為我們所處時(shí)代深刻危機(jī)的代表,成為我們現(xiàn)時(shí)代重大危機(jī)的子嗣與接班人。正是本雅明為這些觀點(diǎn)提供了最深刻且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支撐。他在對(duì)巴洛克悲苦劇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gè)大膽假設(shè),即作為風(fēng)格(style)的寄喻與現(xiàn)代世界的情感、觀念以及經(jīng)驗(yàn)有著最本真的契合度。只是這個(gè)計(jì)劃并沒有得到作者明確公開的宣布。相反,本雅明的文稿嚴(yán)格限定在他自己選定的歷史主題之中。不過,它的精神卻遠(yuǎn)遠(yuǎn)溢出了這一有限的框架。本雅明從當(dāng)下意識(shí)形態(tài)和藝術(shù)需求的角度解讀巴洛克(與浪漫主義)。為此他選擇了這個(gè)狹窄主題,但此選擇尤為巧妙,因?yàn)榘吐蹇藭r(shí)期的危機(jī)元素,與當(dāng)時(shí)德國社會(huì)特定語境中明確無誤的清晰度是同時(shí)涌現(xiàn)的。這是德國暫時(shí)淪為世界歷史(world-history)某個(gè)純粹對(duì)象而產(chǎn)生的結(jié)果。這反過來導(dǎo)致了一種絕望的、只關(guān)注自我的鄉(xiāng)土習(xí)氣,其結(jié)果在于,現(xiàn)實(shí)主義者對(duì)這個(gè)時(shí)代的反抗傾向隨之變得軟弱無力——否則,只有類似于格林梅爾肖森(Grimmelshausen)這樣的特殊情況里,這種反抗傾向才能清楚地顯現(xiàn)出來。憑借這一才華橫溢的洞察,本雅明把研究的主題鎖定在這一時(shí)期的德國,尤其是此時(shí)的戲劇。他無須采用在當(dāng)代通史中常見的方法,即強(qiáng)行使用或歪曲歷史事實(shí),照樣可以對(duì)實(shí)際的理論問題做出生動(dòng)描繪。
本雅明的巴洛克研究從當(dāng)代藝術(shù)成問題的特征角度入手,在對(duì)此研究做出更細(xì)致的考察之前,快速檢視一下由浪漫主義美學(xué)確立的象征與寄喻的區(qū)別對(duì)我們而言將是積極有益的,這也是一項(xiàng)基礎(chǔ)的預(yù)備性工作。這也將反映出,他們的立場(chǎng)與危機(jī)前后的思想家相比依然不那么清晰明確。他們保持中立的立場(chǎng)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diǎn)是歌德本人個(gè)性的絕對(duì)影響,正如我們所見,歌德對(duì)這一問題有清晰的洞察,并且他也認(rèn)為自己的見解對(duì)藝術(shù)的命運(yùn)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在活躍于歌德時(shí)代的藝術(shù)中,那種朝向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強(qiáng)烈驅(qū)動(dòng)力強(qiáng)化了這一元素,但這并不單單發(fā)生在歌德一個(gè)人身上。此外,浪漫主義認(rèn)為其自身處在兩次危機(jī)之間的過渡階段。這便導(dǎo)致了一種特定的、也可能是成問題的、對(duì)這一問題的歷史本質(zhì)的洞見,而且,任何打算界定寄喻的嘗試,其內(nèi)部所蘊(yùn)含的兩難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化解。
謝林在其美學(xué)中①,根據(jù)古典藝術(shù)屬于象征時(shí)代的原則整理了藝術(shù)史,而基督教則被寄喻的法則所支配。謝林的古典藝術(shù)主張以溫克爾曼、萊辛和歌德所確立的傳統(tǒng)作為基礎(chǔ);基督教藝術(shù)則旨在為某種特定的浪漫主義藝術(shù)提供歷史支撐。與其說,對(duì)基督教時(shí)代缺乏真正精確的了解導(dǎo)致了這個(gè)計(jì)劃的含糊不清,不如說,事實(shí)上這個(gè)浪漫主義的視角過于單一了。謝林的觀點(diǎn)消除了我們?cè)缫咽熘南笳髋c寄喻在雕塑領(lǐng)域中的沖突,它甚至把處于現(xiàn)實(shí)主義象征當(dāng)中首要地位的作者和作品解釋為寄喻。索爾格繼承了謝林對(duì)象征和寄喻的區(qū)別,但又在一般理論的層面上對(duì)寄喻做了更清晰的界定②。
處在浪漫主義寄喻危機(jī)趨勢(shì)中的真正理論家是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與諾瓦利斯。為了適應(yīng)這一危機(jī)趨勢(shì),他們之所以過濾并擴(kuò)散危機(jī)的理念以及把寄喻視作對(duì)危機(jī)的表達(dá)方式的理念,與此前概述的歷史哲學(xué)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然而,若納入某種客觀的歷史哲學(xué)之中,這個(gè)問題就顯得不那么尖銳,對(duì)謝林來說尤其如此,施萊格爾認(rèn)為,神話的消亡可能是文化尤其是藝術(shù)(形成)的基礎(chǔ)。盡管施萊格爾依舊希望并堅(jiān)信,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神話有可能找到一條出路,一條打破他自己所處時(shí)代深刻危機(jī)之僵局的出路,但神話的消亡還是被視為危機(jī)的標(biāo)記。因?yàn)閷?duì)施萊格爾而言,每一個(gè)神話都不過是被想象力和愛所變形的東西,不過是一種“我們所身處其中的大自然的象形文字表達(dá)”,所以施萊格爾得出了“一切美皆寄喻”的結(jié)論并不奇怪。“這不過是因?yàn)椋罡哒胬硎菬o法言說的,只能通過寄喻的形式來表達(dá)”。這就導(dǎo)致寄喻在所有人類活動(dòng)形式當(dāng)中擁有某種普遍威權(quán);語言本身在其最原初的顯現(xiàn)形式上,就“等同于寄喻”③。
不難看出,這種分析漸漸傾向于把寄喻從與基督教那古老的關(guān)聯(lián)中分離出來,兩者的關(guān)聯(lián)曾被宗教神學(xué)精確規(guī)定,甚至被條條框框固定了下來。但是,寄喻卻與情感特有的現(xiàn)代式混亂確立了某種親緣性,并且與某種形式的消解建立了親密關(guān)系,這種消解反過來導(dǎo)致了對(duì)象性(Gegenst?ndlichkeit)④的崩潰。正是諾瓦利斯從這種傾向當(dāng)中探尋到一條明確的公式:“故事缺乏邏輯關(guān)系,只有聯(lián)想,不過就是夢(mèng)而已。詩歌旋律動(dòng)人,辭藻華麗,但若缺乏意義或者連貫性,最多也只是停留在理解層面的幾行詩節(jié)而已——就如同一堆由各不相同的物品拼湊起來的碎片。真正的詩歌就像音樂之類,最多只包含某種籠統(tǒng)的寄喻意義和某種間接的影響。”①
浪漫主義者的說法飄忽不定、晦澀而且自相矛盾,與之相對(duì)照,德意志巴洛克悲苦劇經(jīng)過本雅明的刻畫,擁有了內(nèi)在的一致和連貫性,令人印象深刻。這里不展開討論他那些常見的精彩辯論,比如反對(duì)歌德的論戰(zhàn),或者富有啟發(fā)性的詳盡分析等。首先我們必須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他對(duì)巴洛克的全部理解并沒有停留在巴洛克與古典主義的對(duì)比之上,也沒有試圖在矯飾主義與古典主義之間確立某些相關(guān)的、互補(bǔ)的趨向(這是后來某些折中主義者的典型)。他反而朝著自己的目標(biāo)發(fā)起了直接進(jìn)攻,即去揭示藝術(shù)本身的法則。他說:“在寄喻式直觀的王國里,圖像是碎片,是儒尼文。當(dāng)神圣知識(shí)的光輝降臨其上時(shí),它作為象征的美就消失了。整體性的假象被消除了。原因在于,一旦理念(eidos)消失,對(duì)它的比喻便不復(fù)存在,理念所包含的宇宙也隨之塌縮。……對(duì)藝術(shù)問題性的深層次直觀……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其出現(xiàn)是對(duì)自我確證的一種反抗。”②然而,本雅明論證的邏輯導(dǎo)致了這樣的結(jié)論:藝術(shù)的問題性就是世界本身、人類世界、歷史和社會(huì)的問題性;所有這些東西的衰敗在寄喻的意象之中清晰可見。在寄喻里,“觀察者所要面對(duì)的是歷史的希波克拉底面相,它來自一種石化了的、有關(guān)原始圖景的歷史”。歷史不再“去假設(shè)某種永恒生命進(jìn)程的形式,無法抗拒的衰敗也是如此”。然而,“寄喻由此宣示了它對(duì)美的超越。思想王國中的寄喻即實(shí)物王國中的廢墟”③。
本雅明的視角是絕對(duì)明晰的,盡管象征和寄喻的對(duì)立對(duì)所有藝術(shù)作品的美學(xué)定義來說都至關(guān)重要,但從根本上說,二者的對(duì)立并非美學(xué)思辨自發(fā)或有意為之的結(jié)果。它有更深層次的理論來源:人類會(huì)對(duì)自己生活的現(xiàn)實(shí)做出必要的回應(yīng),這回應(yīng)會(huì)促成或阻礙他的行動(dòng)。有了這些,無須贅述就可以發(fā)現(xiàn),本雅明采用了一種更加深刻的方式,處理并深化了現(xiàn)代藝術(shù)的這一問題,而在20年前,威廉·沃林格在他之前就在《抽象與移情》中定義了這個(gè)問題。和前輩相比,本雅明的分析更深入、更有鑒別力,就審美形式的歷史分類法而言,他的分析更具有針對(duì)性和敏感性。正如我們所見,隨之引發(fā)的第一個(gè)結(jié)果就是二元論,它在浪漫派那里是一個(gè)高度抽象的概念,現(xiàn)如今則被具體化為某種基礎(chǔ)牢固的、來自藝術(shù)和意識(shí)形態(tài)之現(xiàn)代危機(jī)的歷史描述與解釋。與沃林格和后來的現(xiàn)代藝術(shù)批評(píng)家不同,本雅明認(rèn)為,為了凸顯象征和寄喻之間的鴻溝,沒有必要將其精神和思想基礎(chǔ)投射回原始時(shí)代。他的成就顯然不會(huì)被以下事實(shí)損害,即社會(huì)歷史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有些模糊不清、不受重視。
因此,本雅明的研究是從這一理念出發(fā)的,即寄喻和象征表達(dá)了人類對(duì)現(xiàn)實(shí)回應(yīng)的根本性分歧。他尖銳地批評(píng)了浪漫主義者的構(gòu)想的晦澀難懂,這一批評(píng)把人們的視線轉(zhuǎn)向這一事實(shí):歸根結(jié)底,寄喻這一模式是建立在破壞人類對(duì)世界的擬人化回應(yīng)的擾亂的基礎(chǔ)之上的,而這種擬人化是審美反映的基礎(chǔ)。但在摹仿藝術(shù)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與自然及社會(huì)特有的活動(dòng)領(lǐng)域的諸多關(guān)聯(lián)之中,人類努力追尋著自我意識(shí),很明顯可以看到,關(guān)注寄喻必然會(huì)破壞審美反映當(dāng)中始終隱含著的普遍人性。我們?cè)谶@里無須籠統(tǒng)概括,本雅明非常肯定地在這個(gè)問題上表達(dá)了他自己的觀點(diǎn):“即使在今天,以下情況并非不證自明的,物高于人,碎片高于整體的優(yōu)先性再現(xiàn)了寄喻和象征之間的對(duì)抗,就對(duì)抗而言,這是相對(duì)的兩極,但正因?yàn)槿绱耍鼈冊(cè)诹α可鲜莿?shì)均力敵的。寄喻式的人格化總是在隱瞞這樣的一個(gè)事實(shí),即它所要做的不是把物人格化,而是通過把物裝扮成人來為物賦予某種引人注目的形式。”④
問題的關(guān)鍵因素至此進(jìn)入了我們的視野。然而,本雅明只關(guān)心為寄喻在美學(xué)(或跨美學(xué))中討回公道。因此,他僅停留在單純的描述上,盡管從概念上講這只是一個(gè)概括性的東西。他忽略了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與擬人化的摹仿藝術(shù)不同的是,賦予事物一種更加引人注目的形式便等同于拜物(fetishize),相反,摹仿藝術(shù)具有去拜物教化(defetishization)的天然傾向,它關(guān)于物的真正知識(shí)都是人類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器。本雅明甚至都沒有觸及這個(gè)問題。但隨后的理論家遠(yuǎn)沒有本雅明那么挑剔,在后來的前衛(wèi)藝術(shù)宣言里確實(shí)頻繁地使用了“戀物”(fetish)一詞。但是,他們當(dāng)然也會(huì)用它來表示某種“原初”的東西——這種表達(dá)呈現(xiàn)出面對(duì)事物的真正原始的、“巫術(shù)”的態(tài)度。不言而喻,他們?cè)诶碚摵蛯?shí)踐中都未能認(rèn)識(shí)到,試圖恢復(fù)一種古老的巫術(shù)文化只可能發(fā)生在想象里,而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他們卻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資本主義對(duì)人與物關(guān)系的拜物行為(fetishization)。即便是時(shí)常用“象征符號(hào)”(emblem)(用其最近取得的含義)來代替”戀物”(fetish)也絲毫不會(huì)改變這種情形。因?yàn)樵诩挠鞯恼Z境里,一個(gè)象征符號(hào)(emblem)如果是未加批判便加以肯定的拜物行為(fetishization),那么它就可以表達(dá)任何東西。
本雅明準(zhǔn)確地洞悉到宗教與傳統(tǒng)在巴洛克時(shí)代是不可分割的聯(lián)合體。這兩種元素的相互作用產(chǎn)生了一種氛圍(atmosphere)(寄喻在此相互作用之中從兩個(gè)不同的角度削弱了所有真實(shí)的客觀再現(xiàn))。我們已經(jīng)對(duì)拜物行為這一趨勢(shì)做出了考察。但是,本雅明也察覺到這個(gè)因素引發(fā)了另一個(gè)處在運(yùn)行過程中的相反因素。“任何人、任何物都有可能意指其他任何東西,這個(gè)可能性對(duì)世俗世界來說是一種具有破壞性但卻公正的裁決:這個(gè)世界的特點(diǎn)之所以如此,因?yàn)樘幵谄渲械募?xì)節(jié)沒有任何價(jià)值。”①這是一個(gè)個(gè)體價(jià)值被貶低的宗教世界,在這個(gè)世界中個(gè)體被維持在一種貶值的狀態(tài)當(dāng)中。反拜物教的物必然具備它自己的品質(zhì)和細(xì)節(jié);反拜物教的物性(thinghood)是一個(gè)確定的個(gè)別事物恰好成其自身的方式。除此之外,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細(xì)節(jié)與客觀整體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必須得到強(qiáng)化。如果諸細(xì)節(jié)可以在超出自身而指向某種本質(zhì)的地方獲得某種癥候性的特征,那么一個(gè)物(object)才可能是被理性規(guī)劃過的,它才可能被提升到單獨(dú)個(gè)體(Besondere)也就是典型的層面上,它才可以成為一種在細(xì)節(jié)上被合理規(guī)劃過的整體。
當(dāng)本雅明正確指出寄喻完全廢除了細(xì)節(jié)以及所有具體客觀的再現(xiàn),此時(shí)他似乎是在對(duì)所有個(gè)體性更徹底的毀滅做出診斷。但現(xiàn)象都具有欺騙性;這種毀滅實(shí)際上暗示著重演。這種替代行為僅僅意味著,互相替代的物與細(xì)節(jié)在它們恰好出現(xiàn)的具體形式當(dāng)中被揚(yáng)棄了。所以這種揚(yáng)棄只會(huì)影響到它們的既定性質(zhì),取而代之的是內(nèi)在結(jié)構(gòu)與它們完全一致的物(objects)。因此,既然個(gè)別之物相互之間被簡(jiǎn)單替代的情況確有發(fā)生,這種對(duì)個(gè)體性的廢除也不過就是它自身持續(xù)不斷的復(fù)制。這個(gè)過程在每一種對(duì)待再現(xiàn)的寄喻觀點(diǎn)當(dāng)中都始終如一,絕不意味著和通常意義上的宗教基礎(chǔ)產(chǎn)生沖突。
然而,在巴洛克本身特別是在本雅明對(duì)它的解讀當(dāng)中,逐漸浮現(xiàn)出一個(gè)新的主題。事實(shí)上,那種超越性不再包含任何具體宗教內(nèi)容(這種超越性為我們剛剛概括過的過程提供了背景)。這完全是虛無主義的——盡管并沒有改變這一過程在根本上的宗教性質(zhì)。本雅明提醒道:“寄喻兩手空空地離去了。邪惡本身,被寄喻珍視為永恒深邃之物,邪惡只能存在于寄喻之中,它只能是寄喻,它意指著與自身不同的其他事物。它所意指的恰恰是它所呈現(xiàn)之物的不存在。”同樣地,本雅明敏銳洞察到此處表述的是“這一主題的神學(xué)本質(zhì)”②。這種主體性的創(chuàng)造力擁有一種與自身相對(duì)應(yīng)的接受模式,這種創(chuàng)造性已經(jīng)超越了所有界限并達(dá)到了自我毀滅的地步。在這里,本雅明堅(jiān)持不懈的嚴(yán)謹(jǐn)態(tài)度給出了一個(gè)至關(guān)重要的評(píng)價(jià):“寄喻是憂郁者給予自我的強(qiáng)大且唯一的消遣。”③本雅明是一位嚴(yán)格意義上的文體家,我們不能忽略掉他筆下的“消遣”一詞所暗含的貶義。當(dāng)物(objects)的世界不再被嚴(yán)肅對(duì)待時(shí),主體的世界的嚴(yán)肅性也必然隨之蕩然無存。
*? 原題為On Walter Benjamin,原刊《新左派評(píng)論》1978年第110期,第83—88頁,英譯者為Rodney Livingstone。摘要和關(guān)鍵詞系中譯者添加。
①? Friedrich W. J. Schelling, Werke, Stuttgart and Augsburg 1956, Vol. 1, 5, p. 452.
②? Karl W. F. Solger, Erwin, Berlin 1815, pp. 41-9.
③? Friedrich Schlegel, Prosaische Jugendschriften, Vienna 1908, Vol. II, pp. 361, 364 and 382.
④? 原文英譯為objective representation,亦有“客觀再現(xiàn)”之意——譯者注。
①? Novalis, Werke, Jena 1923, Vol. II, p. 308.
②?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 176.
③?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 166,p178.
④?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186-187.
①?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175.
②?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233.
③?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NLB, London 1977, p.185.
譯者簡(jiǎn)介:陰志科,溫州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yàn)槲鞣浇F(xiàn)代美學(xué)與近代文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