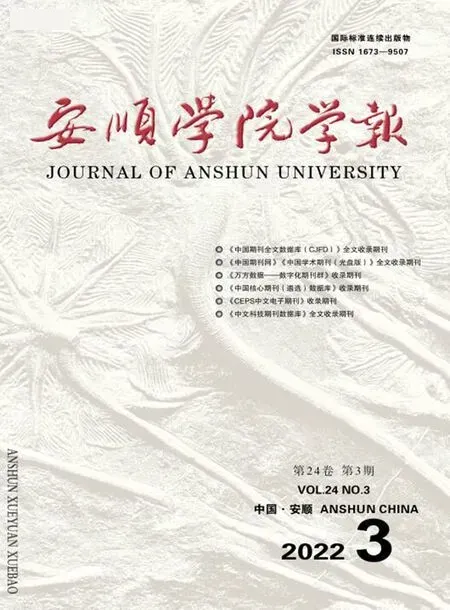安順大屯頂契所見田土交易形態(tài)研究
周 輝 杜成材
(1.安順學院人文學院;2.安順學院旅游學院,貴州 安順 561000)
近年來,隨著各地民間契約文書不斷被發(fā)掘,學界對契約的研究蔚然成風。對于包含“頂”字樣的契約,江南地區(qū)的學者研究最為集中。一是范金民先生關于清代江浙皖三省省級衙門的書吏頂缺文書的研究。就文書形式而言,頂契有契約式與條款式,與民間日常的房地產文書、分家文書、宗祧繼嗣等契約一致;就內容而言,頂契同其他文書一樣,說明出讓或頂賣的原因、價格及交付時間等[1]。二是曹樹基先生基于浙江契約文書對村級土地市場地權變動的分析,繳納了大額押金即“頂首”的永佃權可以轉讓[2]。三是趙思淵先生基于清代徽州田面權交易契約的研究,他將“頂約”“頂首”“頂頭”詞匯的契約統(tǒng)稱為“頂型契約”,分析了其田面權買賣形式的演變[3]。清代各級衙門書吏盛行頂補,江浙等地是頂首銀最為流行的地區(qū)。循此思路,在西南地區(qū)的契約中也發(fā)現涉及“頂”詞匯的契約。一是四川盆地東南部巴縣的契約。巴縣居嘉陵江、長江匯合處,歷史上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重慶東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在清代巴縣檔案所收集的契約中,乾隆年間的頂型契約有2件,均為租佃約,敘物語中使用的句式為“出頂”,道光年間有9件,均為力行的腳力生意,主要有“補頂價約”和“出頂約”“加頂約”三種[4]。二是滇黔驛道東段貴州安順大屯契約,目前發(fā)現的頂契有81件[5]。三是中國會計博物館入藏的明清契約中的“頂契”[6]。從內容上看,江浙皖一帶書吏頂缺文書中,書吏缺儼然是持有人的無形產業(yè),可以轉讓、繼承。巴縣力行的產業(yè)也可以轉讓、補價、加價。從時間上看,江浙書吏頂缺文書時間分布在康熙五十七年至光緒二十七年間(1718—1902年),集中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頂契反映著清代至民國時期的地權變動的情況,今主要利用大屯契約中的頂契,結合范金民、曹樹基、趙思淵等對于地權的論述,分析大屯契約中頂契的田土交易情況。
一、安順大屯契約
目前已發(fā)現的屯堡契約,以手寫為主,極少數為碑刻契約[7]。歷史跨度較長,材料真實具體,細致而深刻地反映了晚清以來黔中漢族農村日常生活中發(fā)生的契約關系。就其訂立的時間而言,上起乾隆中期,下至20世紀80年代初,這就保留了清至民國乃至新中國成立后民間契約的原始樣態(tài)。當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書寫了大量的“契”或“約”的書面材料,范圍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謂“官有公法,民有私約”,凡是公法未及的地方,就會有民間契約被用來記錄民間私約。大屯契約即屬于社會生活類、土地類契約文書,反映了民間百態(tài)和文化習俗,以田契為中心,包括旱地、水田、園地、陰地、宅基等買賣契約。按照契約建立的權利義務關系類型,可以分為買賣契約、租佃契約、典當契約、雇傭契約、借貸契約、身份契約。
統(tǒng)計《大屯契約文書匯編》發(fā)現,該書收錄的520件契約中,買賣契約322件,占比最多(表1)。各朝各代契約中,清光緒年間和民國時期數量最多(表2)。從各朝各代契約文書的歷史跨度而言,清代至民國處于整體上升趨勢,1949年以后數量銳減。民國時期民法中,田骨業(yè)主的收租權視為單純的債權,田面權則是獨立的產權[8]。

表1 大屯契約主要類型一覽表(單位:件)

表2 大屯契約年代分布一覽表
二、大屯契約中的頂契概況
就中國古代契約的書寫形式而言,自唐五代以來,伴隨著契約文書“樣文”的出現以及宋元時期的刊刻傳播,契約文書的套語句式的運用漸趨頻繁,尤其是社會生活類契約文書大量使用了套語句式。所謂套語句式,是指相同或相近結構、固定位置上字詞反復使用的句子[9]。就契約的結構而言,馮學偉還指出,一份契約的結構應包括起首語、率同語、因由語、敘物語、憑中語、收價語、任憑語、聲明語、負責語、結束語、加批語、吉祥語十二個部分;但其中起首語、因由語、敘物語、憑中語、收價語、任憑語、負責語、結束語是必要要件,率同語、聲明語、加批語、吉祥語是可選擇要件。[10]47
據契約的起首語可以判斷契約的性質類型。據統(tǒng)計,共計504件契約中買賣契約共計326件,占比65%,數量最多;其次是頂契,共計81件,占比15%;再次是典當契約和分關契約以及其他契約,合計97件,占比20%。關于契約的類型,王志強在《試析晚清至民初房地交易契約的概念》中指出,在晚清和民國初年的房地交易中最常見的有典、當、賣等[11]。而頂契在大屯契約中數量較多,尚未引起學界關注,因此值得進一步探討。
“頂”字,根據白維國《近代漢語詞典》,意為“轉讓或取得店鋪房屋的經營權或租賃權”[12]391,例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回:“張權正要尋覓大房,不想左間壁一個大布店,情愿連店連房出脫與人,卻不是一事兩便。張權貪他現成,忍貴頂了這店,開張起來。”[13]可見“頂”其實含有轉租的意思,與轉賣不同的是,轉的不是所有權。趙思淵在《歙縣田面權買賣契約形式的演變(1650—1949年)》一文中指出,清代徽州文書之歙縣契約中出現“頂首”“頂頭”類交易用語,其本意是佃戶之間耕種權利的頂讓,“頂首”即押租,所謂“頂”即“轉佃”[3]。

表3 大屯契約起首語及其類別統(tǒng)計一覽(單位:件)
至于頂契各時期數量的變化(見圖1),大屯契約中的頂契共計81件,光緒和民國年間頂契數量較高,其中光緒年間達到最高,多達35件,是同期當契數量(12件)的3倍;民國時期頂契(15件)少于同期當契的數量(20件)。由此可見,光緒年間的大屯村民更傾向于通過田面權的轉讓折現,典當折現的方式則較少。事實上,清代各時期頂契數量都超過了典當契約(見表4)

圖1 大屯契約所見“頂契”在各時期的分布

表4 乾隆朝以來頂契和當契數量一覽表 (單位:件)
三、大屯頂契所見田土交易形態(tài)
大屯契約中的頂契,如下例所述:
例1(吳祖和01)民國三十八年李云先頂廟田文契
立頂明廟田文契李云先,為因乏用,今將本己所置之業(yè)水田乙(一)塊,坐落大薗(園)背后,東抵溝,南抵谷姓界,西抵劉姓界,北抵姚、徐二姓界,四至分明。其田每年秋成上獅子山廟租六斗,親請憑中證上門,出頂與徐云舟名下為業(yè)。是日三面議定,實價云南中洋一百三十元正(整),即日頂主親手領明應用,實銀實契,二比(彼)情愿,并無貨物準折,事(亦)非逼迫等情。自頂之后,任隨徐姓永遠安佃,頂主子孫有力不能相續(xù),無力不能找補,其有房族與(以)及異姓人等不能異言爭論,如有此情,有(由)頂主乙(一)面承躭(擔)。恐后人心不古,特立頂紙一張為據。
酒水畫字清白,管業(yè)證、老契揭交。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李云先押立頂[5]17
可以發(fā)現,民國年間李云先將廟田以“云南中洋一百三十元正”的價格出頂給徐云舟后,買方每年要交租6斗谷,這屬于田面權買賣。大屯契約80件頂契都是田面權買賣之例。所謂田面權買賣,是指將田面權按照一定價格完全轉讓,契約中不包含有關利息的約定,有時具有回贖約定的交易形式。有學者研究認為,明清之際土地市場發(fā)生了重要變化,田賦征收以土地為最主要依據,其土地所有權因租佃關系而形成了土地所有權(田底權,也叫“田骨”)和田面經營權(田面權,也叫“田皮”)的分離。[3]由此可見“頂契”體現的是“田面權”買賣關系。至于所有權的買賣,一般認為是在賣契中體現的,那么,田底權買賣關系是否是賣契中體現的買賣關系呢?田底權買賣契約,在明代又稱“賣田骨契”,是指保有原有土地租佃關系的出賣田地所有權契約。在明清的法律中,把田骨業(yè)主的收租權視為單純的債權,田面權則是獨立的產權。田骨業(yè)主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田面的獨立產權[14]。因而,與民間日常的房地產買賣契約有所不同,是買賣契約中一種特殊的類型。
頂契中的起首語常常在“頂明”后加“永”字,如“立頂明糧田永右九文契”“立頂明永右九糧田文契”“立頂明永右十糧田文契”,也有不加“永”字的,如“立頂明右九糧田文契”“立頂明坐基文契”等。大屯契約中有9件頂契在“右九/十”的前面加永字的。關于頂契中出頂方是否納田租的問題,從大屯契約所見發(fā)現,無論是在敘物語、收價語或者加批語中提及納田租,都表明了買方的納田租責任。以下逐一論述:
(1) 乾隆年間的頂契一般在敘物語部分提及:
例2 載種三升,隨田屯糧伍升,其有大小差役,門戶隨糧辦理。(丁學棟02)[5]789
(2) 嘉慶年間的頂契一般在敘物語部分提及:
例3隨田載屯糧一斗,丁銀、夫役在內,載種四升。憑中上門,出頂與堂叔洪訓名下耕種。是日三面議定,頂價紋銀二十三兩整,親手領明應用,并無花利準折,亦無貪饕逼勒等情。(丁學正02)[5]911
敘物語提及,說明賦稅責任在買方,收價語提及沒有花利。“花利”,白維國版《近代漢語詞典》釋為“收益,利息”[11]805。因此,該契約在收價語中說明出頂人除了頂價之外并沒有其他收益。
(3) 道光年間的頂契在兩部分都有提及:
例4 隨田租谷四斗六升,埂上蠟樹一并在內,請憑中證上門,出頂與堂侄丁朝紀名下耕種。是日三面言定,頂[時]價九二銀八兩一錢整,其銀親手領明應用,自頂之后,契明價足,實銀實契,任隨堂侄永遠耕種納租。(齊少蕓05)[5]29
敘物語中說明田賦有糧賦,沒有他項賦稅。收價語中說明由買方納租。可見道光年間的頂契已經相對完備,在收價語中講明了頂契雙方的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年間的頂契也有正文不提稅賦的,但在加批語中提及。
例5(丁學正13)立頂明糧田文契人楊法祥,為因乏用,今將祖父遺留分受(授)本名下糧田乙(一)塊,坐落大坡腳。東抵牛路,西抵趙姓,南抵楊姓,北抵坡腳,四至分明。請憑中證上門,出頂與丁朝云名下耕種為業(yè)。是日三面議定,得授時價九三銀六兩一錢整,其銀法祥親手領[明]應用。自頂之后,契明價足,實銀實契,任隨朝云永遠耕種管業(yè),楊姓房族人等不得異言爭論。恐口無憑,立頂契永遠為據。
立契日內天(添)二字
其田系有三升屯糧,在坡腳長田乙(一)塊上納
酒水畫字在外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八日立頂糧田文契人楊法祥[5]933
上述頂契(丁學正13)有兩行小字,屬于加批語,其中一行說明文內添字情況,另一行小字則說明糧賦情況。道光年間的這兩份頂契的訂立時間都是道光二十九年。至于為何在加批語提及糧賦,究竟是代筆人習慣不同,還是頂契雙方關系不同,對比楊法祥在同一天立的另一份頂契(丁學正14),可以發(fā)現代筆人都是“王如凡”,但是“丁學正14”中的糧賦并沒有出現在加批語,而是在正文中。
例6(丁學正14)立頂明廟田文契人楊法祥、仝(同)侄光全、孫元妹,為因乏用,今將祖父遺留分受(授)本名下廟田二塊,坐落楊家蕩。東、西、北三至俱抵溝,南抵萬姓田,四至分明。隨田上納廟祖(租)乙(一)石。請憑中證上門,出頂與丁朝云名下耕種為業(yè)。是日三面議定,得授時價九三銀一十五兩整,其銀叔侄親手領明應用,自頂之后,契明價足,實銀實契,任隨朝云永遠耕種管業(yè),楊姓房族人等等不得異言爭論。恐無憑,立頂契永遠為據。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八日[5]935
也就是說,道光年間同一年訂立的三份頂契——“齊少蕓05”“丁學正13”和“丁學正14”,只有“丁學正13”把賦稅放在了加批語中,而且后兩份契約出于同一個代筆人和出頂人,因此不會是代筆人習慣不同造成的。對比這3份頂契的糧賦數量,其不同之處還在于“丁學正13”出頂的是糧田,納糧3升,“丁學正14”出頂的是廟田,納糧1石,“齊少蕓05”出頂的也是廟田,納糧四斗六升。可以發(fā)現小字加批語中出現的糧賦數量較小,這體現了契約的精要之處,不那么重要的內容使用了小字“加批語”。
(4) 咸豐年間的頂契,雖然在收價語中提及上納租谷,但無主語,而且前句主語是出頂方,是否說明此契是出頂方交租呢?從頂契的發(fā)展過程看,并沒有這一先例,因此我們認為此契仍然是買方負責交租。
例7(丁學坤03)咸豐八年徐應柱頂廟田文契
立頂明廟田文契人徐應桂,為因乏用,今將祖父所置廟[田]乙(一)塊,坐落基門口。請憑中上門,出頂與丁朝槐名下管業(yè)耕種。三面議定,價艮(銀)四兩二錢整,徐姓親手應用,每年上納②租谷二斗,至(自)頂之后,徐處不得異言。恐口無憑,立頂字為據。
咸豐八年三月二十六日[5]273
(5) 光緒年間的頂契,在敘物語部分提及交租數額,如
例8立頂明廟田文契人周志興,為因遺(移)業(yè)置業(yè),今將本自己所置明廟田一塊,坐落寨基上。北抵溝,東抵齊姓界,南抵丁姓界,西抵徐姓界,獅子山廟租□□,四至分明。今[請]憑中上門,出頂周富興名下耕種管業(yè),即日言定時九九價銀二十兩零□□□整。頂日志興親手收明應用,此系實銀實契二彼情愿,并[無]貨物準折,亦無逼迫等情。自頂之后,任隨周富興永遠耕安,志興[子]侄與及異姓人等不得異言爭論,如有此情,志興一面承耽(擔)。[恐口無]憑,立頂契為據。
墾(埂)上[樹木]一并在內。
光緒二十年□□□(周邦珍03)[5]233
綜上所述,頂契與賣契最大的不同,即有無租約的問題,頂契中大多是在敘物語部分提及租約,也有在收價語部分提及以示強調之意,也有在加批語中提及——這種情況的田租數額一般較小。
(6)頂契任憑語中的“安佃”。任憑語的結構一般是“自……之后,任隨……耕種耕安”。大多頂契中除在起首語使用“頂”字外,任憑語一般并沒有差異,只有“李光彬31”——《民國二十三年李建章頂廟田文契》中的任憑語標志了頂契的租佃關系特點。賣契和頂契大多使用“耕種管業(yè)”“管業(yè)耕安”等類詞語,“李光彬31”使用的則是“管理安佃”,其中“佃”字表明轉讓的是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另有“吳祖和01”,用的是“永遠安佃”,“王文義01”用的是“永遠管業(yè)安佃”。
例9自頂之后,任隨秀廷管理安佃,建章房族子侄以及異姓人等,不得異言爭論,如有此情,自任套哄之咎。恐口無憑,特立頂契為據。(李光彬31)[5]515
例10自頂之后,任隨徐姓永遠安佃,頂主子孫有力不能相續(xù)(贖),無力不能找補(吳祖和01)[5]17
例11隨田上納屯糧永石九糧一升,……自頂之后,任隨金姓管業(yè)安佃……恐口無憑,立頂契永遠管業(yè)安佃為據。(王文義01)[5]393
(7)賣田骨契中的任憑語。徐嘉露指出,“賣田骨契”(即田底權契)在明代與一般的買賣契約內容基本相同,不同之處在于:“賣田骨契”一般都會載明原租多少,“賣與某名下收租管業(yè)”;而買賣契約是“賣與某人永遠自行管業(yè)”或“賣與某某名下永遠為業(yè)”,顯示的是土地田宅的所有權利的轉移,而“賣田骨契”賣出的則是對土地田宅的收益權,“賣田骨契”都會在契中顯示租額的情況。[15]據此對照大屯契約,找到了唯一一份使用套語“收租管業(yè)”的“賣田骨契”:
例12(丁學棟05)同治十二年陳星堂賣水科田文契
老契
立杜賣明水科田文契人陳星堂,為因需用,今將祖父遺留分授已名下田一坋,坐落大屯邵田壩,大小二塊。其大田一塊,西抵溝,東、北、南俱抵齊宅田,約租三石。其四方田一塊,東、南、西俱抵齊宅田,北抵王宅田,約租一石五斗,載縣屬右十科米八合,攤缺額二合。請憑中證三面勘明,親至踏明上門,杜賣與顧履經名下為業(yè)。是日三面議定,得授時價玖八無砂紋銀六十五兩整,當面兌足,貴平親手領明應用,此系二比情愿,實銀實契,并無貨債準折,亦無貪逼等情。自賣之后,任憑顧處扯田過佃耕安收租管理,陳處房族以及異姓人等不得異言爭論,如有異言,為賣主一面承耽(擔),自干(甘)套哄之咎。今恐人心不古,特立杜賣文契為據。
面揭老契一張
酒水畫字在外清白
永遠管業(yè)
同治十二年三月初六日杜賣文契人陳星堂親筆立[5]795
官契
立杜賣明水科田文契人陳星堂,為因需用,今將祖父遺留分授本己名下田一坋,坐落大屯邵田壩,大小二塊。又四方田一塊,四至均照老契管理約租四石五斗,請憑中證上門,出賣與顧履經名下為業(yè)。載科糧八合,攤缺額二合。得授時價□□銀六十五兩整,親手收清,余詳原契。
賣主陳星堂親筆[5]794
“丁學棟05”是一份官契和老契相接、保存完整的“賣田骨契”騎縫蓋“貴州安順縣印”。從大屯契約中發(fā)現“賣田骨契”除了使用“收租管業(yè)”套語外,大屯契約中還有一些賣契在任憑語中表明“安佃”二字,如“徐起江03”和“徐起江04”,根據頂契與“賣田骨契”在租佃關系上的特點,所謂“賣田骨契”,即田底權買賣契約,是指保有原有土地租佃關系的出賣田地所有權契約。由此可以判斷這兩份賣契所交易的土地存在租佃關系。
例13(徐起江03)光緒五年劉瑞賣科田陸地文契
官契
立出賣明科田陸地文契[人劉]國瑞,為因乏用,今將自置田地,坐落卜氣歌,四□□,老契隨田科米一合。憑中證出賣與田一坋大小公五塊[于]徐大恩名下為業(yè),是日三面言定,賣價市銀六兩整。自賣之后,任隨徐姓耕種安佃永遠管業(yè),劉姓不得異言,此系實銀實契,并無貨物準折,亦無逼迫等情。恐口無憑,立契為據。
內除大樹一根,界內樹木在內
光緒五年七月十七日[5]131
例14(徐起江04)光緒六年劉國瑞賣水田陸地文契
立賣明水田陸地文契[人]劉國瑞,為因乏用,今將本已所置之田一塊,坐落卜氣歌。東抵溝,南、北抵溝,西抵路,四至分明。隨田科米一合,系如右九上納,今請憑中出賣與徐大恩名下為業(yè)。是日三面議定,時價隨市無鎌沙銀二兩一錢整,劉姓親手領明應用,實銀實契,此系二比情愿,自賣之后,任隨徐姓安佃管理,劉姓房族子侄不得異言爭論。恐口無憑,立賣契永遠為據。
光緒六年五月初八日立賣契劉國瑞[5]133
據統(tǒng)計,大屯契約中出現“安佃”一詞的賣契共15件(見表5),根據契約正文有無關于租約的說明,可以認為“胡華珍06”“趙德忠11”和“丁學棟43”這三份房屋地基買賣的文契,既沒有提到租約,也不屬于田土交易,因此不是賣田骨契的范疇。另有“徐世華01”“丁學坤02”“丁學正18”和“戶主不詳06”這四件陸地買賣文契,沒有提及租約,因此無法確定是否買賣的陸地、是否存在租佃關系,故不能確定是否屬于賣田骨契。大屯契約中,根據賣契中的套語“安佃”一詞以及文內是否提及田租的情況,可以確定有8件“賣田骨契”——即田底權的買賣。就其訂立的時間而言,從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至民國年間都存在這種田土交易。其中光緒年間有3起,此間“李應貴”分別在光緒三年(1877年)和三十三年(1887年)發(fā)生了兩筆田底權交易,交易價格合計九九銀46兩。

表5 買賣契約中的“安佃”類契約
論述至此,試圖回答另一個問題,大屯契約中多達326件買賣契約中,沒有使用套語“安佃”的,是否存在類似的“賣田骨契”?也就是說,如果將賣契中提到田租的土地交易都視為田底權交易,那么大屯契約中的田底權交易不止8件。
相比之下,田面權交易契約80件,田底權交易契約8件,可見大屯契約中,田面權交易發(fā)生得更頻繁些。有學者研究認為,在徽州文書中,田面權更容易在土地市場中交易②。總而言之,如前所述,頂契在各朝各代都比當契多,也比“賣田骨契”數量多,田面權交易的市場更活躍。
(8) 當契中的“安佃”。此外,我們發(fā)現當契中也存在同樣使用套語“安佃”的情況。
例15(胡華珍05)立當明瓦房文契人李錦榮,為因今將本己名下廂房二間,坐落大門數(樓)。東抵丁姓,南抵李姓界,西抵李姓,北抵丁姓界,四至分明。親自上門出當與李云奎名下為業(yè)居住,是日三面議定,市用國幣七萬元正(整),即日當主親手領明應用。至(自)當之后,任隨云奎住坐安佃,房主不得異言爭論,如有爭論,此情有房主一面承耽(擔),其房不及遠近歸贖相還。恐口無憑,立當字為據。
后面圓□在內。
民國三十五年古歷八月二十八日李錦榮立[5]11
李錦榮將本己名下廂房出當與李云奎名下為業(yè)居住,以房屋為抵押獲取租金。這種以不動產使用權的轉讓獲取收益權,是當時的一種普遍情形。作為不動產的田地,其“安佃”通過收益權獲取利息。楊國楨先生認為,“田面權”是在永佃權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佃耕的土地能否由佃戶自由轉讓,是區(qū)分“一田二主”和永佃權的根本標志[16]。 田面權的產生,讓土地耕種者看到了獲得土地產權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地權分割轉讓的進程。
四、余論
結合《大屯契約文書匯編》中所刊載的契約,結合語詞從統(tǒng)計入手,初步分析了大屯契約中頂契各要素所反映的田面權、田底權基本情況,并試圖還原大屯契約訂立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土地市場情況。大屯契約所見頂契,在文字表達形式上與有清一代徽州府歙縣“頂型契約”有一定程度的相似,與巴縣乾嘉道時期契約中的“頂約”也具有一致性。這種類型的契約書寫方式,從時間和地域分布來看,在當時東亞白銀流動趨勢之下,伴隨著貿易,書寫方式從書吏頂缺轉到地權變動領域進而影響到西南驛道沿線地區(qū)契約書寫方式的轉變,從而在今天仍能窺見蹤跡,這種文化上的傳播,有待史料上進一步證實。
注 釋:
①上納,意為“向官府交納”,參見白維國主編《近代漢語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1頁。
②參見范金民:《“水程”與“議約”:清代漢口房地產賣契的書立——以徽商文書為中心的探討》,《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1-8頁;王振忠、劉道勝《 徽州文書與中國史研究》中西書局 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