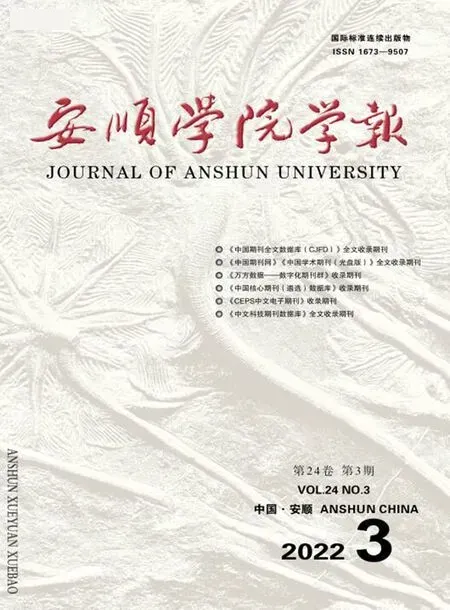吉昌契約文書所見清代黔中屯堡家庭與家庭經濟
林 芊
(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黔中屯堡、屯堡人研究
生活在貴州省安順市為核心的黔中地區屯堡及屯堡人,今天研究者將其置于整個明清時期西南地區社會歷史背景下,視其為獨特的人群,其社會生活與文化稱之為“孤島”。屯堡人身份有兩個方面,作為漢族,他們被今天的研究賦予特別的內涵:作為長期生活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成員,明代就是普通的貴州屯軍成員,因其后代一直保持著明代屯軍身份同,與融入少數民族地區的其他漢族不同,他們是漢族身份;而從漢族身份看,又由于他們與少數民族有較深的社會經濟文化關系,與明末清初大量的漢族移民而言,尤其是清代乾隆時期幾次大規模移民,他們已形成了一種以自身文化為主體的族群,又被視為少數民族。這兩個獨特的“族群”標志便是屯堡人的特征。故在道光年間編纂的《安平縣志》中,一方面稱“屯堡,即明洪武時之屯軍”,因其女性裝束頭飾稱之為“鳳頭笄”,但卻又特別地將屯堡人納入“苗俗”范疇[1]137,同是在道光年間輯錄的《黔南職方紀略》則辨識其“似苗非苗”,并因其婦女裝束與普通漢人異常而稱之為“鳳頭雞”①。后來的史志著述大都沿襲上述觀念。簡言之,黔中屯堡人是一種特別身份的漢族:相對于貴州古老的漢族移民而言,即之前移居貴州,并已少數民族化而在典籍里被名之為“洞人”或者“宋家”“蔡家”等稱呼的漢人,屯堡人是“純粹”的漢人;相對于清代以來的漢族移民,他們則又是多少融合了少數民族色彩的漢族,屯堡人也有了本地化的稱呼,如“屯田子”“里民子”[2]306。
作為明代軍屯的后人,屯堡人與屯堡社會生活的重大變化,康熙時期是一個轉折點。首要的是身份變化,他們改軍衛屯卒為十足的農耕村民。由此而帶來微妙的社會變化,雖然身份發生根本變化,但黔中地區屯堡人與貴州許多地區屯軍身份逐漸與當地民族融合又不太一樣,他們仍然固守著自己屯堡的生活方式,并未融入當地少數民族土著居民中,而以屯堡人的特別身份與當地人包括一些漢族顯著地區分開來。其特別的生存方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而探索原因,如一項研究分析指出,除屯軍身份世襲的普遍特征外,相對于貴州其他地區屯軍,黔中尤其平壩至鎮寧間,軍衛設置更密集,形成屯堡集中連片分布的地理格局;屯軍來源地相對近鄰,有著更相似生活方式;因處于國家交通要沖,更多的與“苗民”發生社會沖突,易于保持自己江南人社會文化習俗[3]。
今天安順市大西橋鎮吉昌屯,就是黔中腹地屯堡人的一個社區(村寨)。吉昌屯是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使用的地名,之前名為雞場屯。據咸豐時編纂成書的《安順府志》,雞場屯作為一個古老屯堡,在衛所時代,隸屬普定衛,處在普定衛與平壩衛之間,是黔滇驛道干線上的一個屯堡。康熙十年(1671年)裁衛改置縣,普定衛改為縣,雞場屯屬普定縣奠安里②,與由平壩衛改置的安平縣(今平壩區)毗鄰,皆屬安順府領縣。民國三年(1914年)安順府改縣,與普定縣劃定疆域,沿轎子山脈為界劃定兩縣境疆域,東南屬安順縣,西北歸普定縣[4]116,120,位于轎子山脈東南的雞場屯改隸安順縣。由于政區不斷變化,雞場屯行政地理先后與普定、安順、安平縣毗鄰,故收集于《吉昌契約文書匯編》內契約文書,既鈐有普定縣印,也鈐有安順縣印。收集于《吉昌契約文書匯編》中的契約,有的是經普定縣正堂核驗頒發花戶完納秋糧的“花戶執照”。又,雞場屯在民國時期與安平縣存在著插花地,故今天雞場屯仍然有當地交糧“上邊交糧于平壩,下邊交糧于安順”的諺語流傳。
黔中地區屯堡人的傳統社會文化研究成果蔚為大觀,佳篇頻出[5],且形成了一門學術——“屯堡學”而具有國家意義,同時也是黔學研究的重要構成。貴州屯堡研究主要關注于明清時期軍屯制度、屯堡社區形成、屯堡人來源及本地化,社會生活如屯堡鄉村及村寨組織,屯堡社會文化、宗教、風習等方面,取得的豐碩成果以連續出版刊物不斷奉獻給讀者,如政協安順市文史委主辦的《安順文史資料》和安順學院“貴州省屯堡研究會”主辦集刊《屯堡文化研究》,《安順學院學報》還設置特別專欄持續刊發最新研究成果,同時也通過史志文獻、專題研究專著等表現出來。可能是因為史料有限,尚少關注屯堡經濟社會生活。但這一薄弱環節,也因遺存的明清屯堡契約文書的發現及整理出版而有所改觀。日前可以利用的公開出版明清屯堡契約文書資料有孫兆霞主編《吉昌契約文書匯編》,呂燕平編《大屯契約文書匯編》[6],前者收集契約文書438件,后者700余件;最早的契約文書是明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二十六日田斌等賣山地契約[7],它們為研究明清時期屯堡社會經濟生活提供了新史料,依據這些歷史文獻展開的研究也豐富了屯堡學研究。
目前對屯堡契約文書的研究,以筆者有限的學習閱讀所見,主要成果集中在《吉昌契約文書匯編》資料提供的信息展開的課題上,如萬明撰寫的《吉昌契約文書匯編》“前言”、孫兆霞對該匯編所作的“前言”,分別解讀了契約文書對研究明清屯堡社會價值及展示的歷史場景。進一步地研究有論文有孫兆霞和張建的《地方社會與國家歷史的長時段型塑——〈吉昌契約文書匯編〉價值初識》[8]、孟凡松和吳羽《明代貴州上六衛屯田研究》、張秀娟的《宗法關系在清代經濟活動中解體的時空差異——基于吉昌契約文書的考察》[9]、梁驕陽的《西南屯堡科田買賣契約的法律史分析——以吉昌契約文書為例》[10]、唐智燕的《俗字研究與民間文獻整理——以〈吉昌契約文書匯編〉為例》[11]和《論近代民間析產分關契約文書的語言特點》[12]等等。上述論文中,孟凡松、吳羽詳細地分析了康熙改衛后,尤其是雍正以來屯田制度變化的特征;孫兆霞、張建據契約文書顛覆了以往研究對軍屯制度消解的主要觀點,并突出了契約文書作為史料在認識和建構屯堡社會價值與可能;張秀娟主要分析了宗法關系在清代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活動中的發展歷程的差異;梁驕陽以科田買賣為研究對象,分析科田買賣的比重、特殊地產、科田糾紛解決價值等內容;唐智燕在參照中國傳統契約文書契式背景下,專注于考證吉昌契約文書在書寫文書時的用字、語言,體現出來的與中國傳統契約文書共性個性,探索屯堡社會特征。最近的研究成果是杜成才博士論文“晚清至民國貴州安順吉昌屯契約文書研究”,主要介紹吉昌契約文書,從文書學如契式書寫、契約文書要件、特定語句,文書內容及內容所涉及的領域問題進行剖析,探討屯堡契約文書的特征及各類文書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生活,據契約本身涉及內涵逐項進行對應分析。最近出版的《大屯契約文書匯編》,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展現,其中如呂燕平“安順屯堡刊刻契約文書探析”、潘玉陶“大屯契約文書淺識”、王舒“土地資源與村民行為關系探究——基于大屯村契約文書的研究”等,對大屯契約文書的價值及相關專題學術問題展開了討論③。
上述主要依據契約文書做出的研究成果,凡涉及屯堡鄉村經濟社會生活,多是對文書內介紹出發,因此,還可依據契約文書包含的豐富歷史信息,更貼近地進入屯堡社會各戶農家作主題研究,從微觀方面對其經濟行為過程所反映出來的家庭經濟、社會生活進行深入的觀察。
二、由契約文書建構起的黔中屯堡家庭、家族與宗族
明代以來黔中屯堡人家庭千千萬萬,吉昌屯汪氏家族成員,就是千萬屯民家庭之一。這里只選擇收集在《吉昌契約文書匯編》內汪氏家族清代各個時期的家庭契約文書資料(《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收集了汪氏家族契約文書103件。其中的清代契約文書成為本文主要事實分析依據),通過分析它們,既可復制歷史上一個小家庭情況,還可通過其家庭血緣的延伸,建構起一個家庭成長為家族、繼而擴展成宗族的歷史進程,從而以家庭為核心窺見屯堡社會成長的一個側面。通過閱讀汪氏家族契約文書,能從中梳理出汪氏家族自康熙時代至民國時期各家庭血緣譜系。
第一,下面所引契約文書為清代吉昌村汪氏家族確定了一個起始點:
立賣明房地基文契人汪爾重,為因缺用,無處出辦,情愿將祖遺自置房屋地基二間、天井牛棬(圈)一個、東廝一個,墻圍在內,東至本家房地,南至本家地,西至街,北至路。四至分明,憑中出賣與族侄汪世榮名下住坐管業。三面議定賣價紋銀八兩四錢、九三銀九兩一錢,共銀一十七兩零五錢整。爾重親手領回應用,系是實銀實契,并無貨物準折,亦無逼迫成交。自賣之后,任隨族侄汪世榮子孫永遠管業住坐,不許親族人等爭論異言。□□等情,爾重一面承當。恐后人心不古,立此賣契存照。
其余地基前后長寬乙(一)尺,將后頭東廝一股,品補胞兄之明□□侄世臣名下。日后不得憣(翻)悔爭論。如有憣(翻)悔爭論,將紙赴公理,干(甘)當重罪。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立賣房地基人 汪爾重
憑本族 胞侄汪美祥 汪世高 汪世型 汪世臣
汪世俊
胞兄汪之云 汪爾富 汪爾質 汪爾明
汪良輔
轉手畫字人 汪之燦
憑中人 鄒倪之 徐上卿 鄒世璉
代書人 胡長年[13]228
解讀契約內容,買賣雙方汪爾重與汪世榮是族侄關系,汪爾重出售的是“祖遺自置”房產,約契又講到“四至本房地”,表明汪爾重與汪世榮共同是一個血緣家族成員;汪世榮購置所得房屋地基二間,天井、牛棬一個,東廝一個,圍墻在內,可見此次出售是一大院房產,其規模表明足以表明汪世榮家庭已是一個成熟的家庭;因此,這次買賣的意義,從后來的歷史進程看,在吉昌屯汪氏家族歷史上是一個新起點。首先,汪世榮家庭是一個新家庭的誕生,而且是一個從本房中新獨立出來的一個新家庭;本房其他家庭如契約“中人”部分所見,有汪爾富、汪爾質、汪爾明等;其次,這個新家庭的出現本身即帶著代際關系,即他不僅是“本房”中的一個新家庭,而且是從其父親共同的家庭中獨立出來的新家庭,盡管不知道其父輩名字,但從其族叔汪爾重名字,可推測出其父名汪爾某人,這樣,形成了一個新的家庭代際關系,即第一代的汪爾某人與第二代的汪世榮家庭。再者,他預示著由本房新家庭發展為一個新家族的起點出現。這是發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事件,汪爾某人與汪世榮家庭肯定是生活于康熙雍正朝代。這樣,康熙雍正朝代的汪爾某人與汪世榮家庭,與后來從中不斷裂變生產的新家庭而所構成的家族而言,即是這個新家族的起點。
第二,作為起點,由汪爾某人與汪世榮二代家庭開啟了汪氏家族在吉昌屯的演進史。家庭的功能就是繁衍后代子孫,每個家庭都不是獨子,又都有延續后代的自然使命,如此生生不息形成家庭代際血脈關系或世系,進而形成家族。這個演進過程也能從契約文書中找到蹤跡,其中分家契約是代際血脈關系的一個重要見證,汪氏家族的分家契約將其世系線索顯示出來。如汪世榮與汪子重父子關系,就是從分家析產時汪子重所得田產上得到證實。據《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汪子重分別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和五十四年(1789年)兩次分家中獲得田產林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十六日汪子重分家所得田產有:下墳底下長田2丘,黃泥田一塊,大塘田2塊,共科米1斗六升4合6勺④,這些田產通過汪世榮一生買進田產比較,就是同一塊田,表明汪子榮通過分家繼承了汪世榮部分田產,這樣就建立起了自汪世榮-汪子重父子兩代的關系。一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十三日分家文書,是汪廷柏與其二子起云、起貴分家,一方面形成新的小家庭,同時也建立起了汪廷柏與起云、起貴父子兩代關系。
梳理上述分家契約看到,汪世榮與子輩汪子重等分家后由一個家庭分解為新的二代家庭;汪廷柏與子輩汪起云、汪起貴等分家后由一個家庭分解為新的二代家庭。梳理買賣及相關契約文書看到,汪起云-汪興燦、興賢-汪純美是祖孫三代家庭;汪純美與汪田弟是父子兩代家庭。一件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回典契約內容顯示,汪朝禮孫汪起云取贖了之前家庭中出當的田產,表明汪朝禮與汪起云為祖孫關系;汪廷柏是汪起云父親,那么形成汪朝禮與汪廷柏、汪起云三代家庭關系。由此形成了起自汪朝禮,經汪廷柏、汪起云(起貴)、汪興燦(興賢)再到汪純美、汪興弟間一脈血緣五代人的家庭關系。
上引分家契約已表明,汪世榮與汪子重為父子兩代人家庭;據今天保存在吉昌村的《汪氏宗譜(颕川-黔腹》⑤記載,汪朝禮是汪子重兒子,由此確立起了汪世榮→汪子重→汪朝禮三代家庭。以汪朝禮為中樞,將其前后家庭血緣親屬關系連接起來,一個開始于汪爾某人,經世榮→子重→朝禮→廷伯→起云、起貴→興燦、興賢→純美→□弟的吉昌屯汪氏血親家族世系便自然地顯示出來。相對于康雍時期的那個汪氏本房,這是一個逐漸演化形成的新家族的譜系。
第三,實際上,汪世榮家族的形成也是一個由家庭發展為家族而演化成宗族的過程。中國傳統社會組織中家庭發展由家族再到宗族,是社會組織生機發育成長的過程,“九族成宗”則是社會組織生機發育成長在社會觀念意識上的反映。
首先,《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收集契約也能簡約地將汪氏九族關系呈現出來。所謂“九族成宗”即是一脈血緣傳承起來的九代家庭世系。吉昌契約文書所見到最早一代汪氏成員名字多為汪爾重、汪爾富、汪爾質、汪爾明等;如果以汪爾某構成的家庭在吉昌的第一代,那么由汪爾重侄子汪世榮構成的家庭則是第二代,他們都生活于康雍乾時代,第三代汪子重(仲)生活于雍正乾隆時代。以此類推,他們的后代第四代汪朝禮、第五代汪廷柏兩代人生活于乾隆末及嘉慶時代,第六代汪起云、起貴弟兄主要生活于道光與咸豐時代,第七代汪興燦、汪興賢等生活于咸豐與光緒時代,第八代汪純美生活于光緒及民初;再加上民國時期的汪純美子□弟第九代,那么,就建立起吉昌屯汪氏起于康熙朝至光緒與民國初期九代人直系親屬血緣關系。各個世代血緣家庭既共同構成起一個家族世系,而九代世系又建構了始于汪世榮,由康熙至民國時期的汪氏宗族。須特別強調的是,契約文書中表述出來的親屬代際血緣關系,與《汪氏宗譜(颕川-黔腹》記載代際吻合,而且契約文書還保留著較《汪氏宗譜(颕川-黔腹》更詳細的親屬成員信息。
其次,宗族往往是一個家族群體,群體成員往往以家支關系表現出來。從契約文書中可見,汪世榮有三子,分別是汪子舜(按照契約書寫習慣順序,他可能是長子——引者注)、汪子美和汪子重。通過分析汪子重家族世系血緣關系建立的方式,從家族關系方面,汪子舜、汪子美在生活中也各自演繹著與汪子重相同的邏輯,從而演化成一個九代的家族世系。那么,一個汪氏宗族的家族群體便在形成中,汪子舜、汪子美就分別是這個家族群體中的一支,即他們既是汪世榮家族世系中的分支,但他們同時也以其分支成組了汪世榮家族群體,他們一起建構起了吉昌屯汪氏宗族。
汪子舜、汪子美家支情況,在《吉昌契約文書匯編》中沒有更詳細的資料。但可從一些契約文書中找到作為宗支的家族演化世代痕跡。如《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收集有幾件“汪田氏”田地買賣與分家契約文書,從內容上看,它們在建構宗族過程中與汪子舜或汪子美家支極有血親關系。汪田氏是誰之妻?契約文書中沒有明確表示。查《汪氏宗譜(颕川-黔腹)》,汪廷柏與其子起云,兩人娶妻都姓田,故很難從族譜中去確定“汪田氏”是誰之妻。但從文書卻可作出一些推測。從土地買賣契約時間看,汪田氏是與汪起云一起,從道光十四年(1834年)就開始購置土地,但在同治七年(1868年)之后就不見其蹤影了,前后時間有24年;她與起云同一時期買進土地,表明她不可能是汪廷柏或汪起云之妻田氏。道光十四年(1834年)四月初一日契約汪廷興將水田1塊出售給堂弟媳汪田氏、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月十一日汪起明將一塊田出售與叔母汪田氏,從契約雙方稱謂表明,汪田氏丈夫應是廷字輩。就上述關系而言,首先,汪田氏只能與汪子舜或子美家族有直系血親關系;其次,汪田氏是廷字輩媳;其三,因汪起明稱汪田氏為叔母,那么汪田氏兒子為起字輩。于是形成了汪世榮→汪子舜或子美→□□□(有字輩)→汪田氏(廷字輩)→起字輩的家族世系。這個世系作為汪世榮后嗣中的分支,他們與其他分支共同建構起了汪氏宗族中核心汪世榮家族。
再次,宗族也是一個擴大了的同宗成員群體。如果將汪世榮家族(包括汪子舜、汪子重、子美家庭)看作吉昌屯汪氏宗族中的核心構成,那么,與汪世榮有親緣關系的其他汪姓成員家庭,也是這個宗族的組成部分。這種關系也在契約文書中能看到他們的軌跡。與汪世榮有親緣關系的其他汪姓成員家庭,我們在文書中可以發現,凡屬于第三代的“子”字輩,而不是汪世榮直系血親的有汪子富、汪子盛、汪子云等;第四代的“朝”字輩有汪朝選、汪朝相、汪朝德等。在這些成員中,汪朝有家庭可能建立起一個血緣家族。有研究指出,從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至嘉慶四年(1799年)汪朝有四次將土地房產等出售,參與其中活動的還有“胞叔”汪子富,有胞兄弟汪朝選、汪朝相等[14]52;乾隆四十九年(1692年)六月十五日賣水田契汪子富稱汪美智為胞叔。雖然他們很難說是一個直系血緣家庭直接延續下來,但他們都有“胞叔”與“胞侄”等稱謂,那么表示出他們間有直系血緣關系;據嘉慶十四年(1809年)契約,汪朝友(有)同子重先、小三、小四、小五等,將田產出賣與堂弟朝禮朝選。比較上述各家庭親屬關系,形成了始自汪美智,經汪子富、朝有(友)再到重先、小五等的四代血緣家庭。上引雍正十三年(1735年)契約文書中,汪爾重也稱汪美祥為胞侄,那么相似地推論,汪美智父輩也應當是汪爾字輩,于是形成了一個由汪爾某→汪美智→汪子富→朝有(友)→重先、小五等五代家庭構成的家族世系。
在吉昌契約文書中,汪子富稱汪子美、子重、子順為“族兄”。這樣的親屬關系與稱之為“胞叔”“胞侄”在血緣是有親疏的,前者是旁系而后者是直系的血緣關系。不同血緣關系的稱謂區別出兩個同姓不同宗的各家支,顯然汪美智、汪子富家族與汪世榮、汪子重家族不是一個本家。但與汪世榮家族一樣,上述家庭演化過程表明,汪美祥家庭也與汪世榮家庭一樣,開啟了本家族的第一步,他們的后續家庭也能形本家族的世系并構成成本家族內的分支,從而建構起九族關系宗族。由汪美智家庭開啟的本家族及由本家族世系建構起建構起的九族關系,構成了吉昌屯汪氏宗族的組成部分⑥。
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本生產是兩種生產,一是物的生產即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一是人的生產,即種族的繁殖。吉昌屯契約文書的土地買賣是物的生產表現形式之一,而分家文書則是種族繁殖形式之一,它們很恰當地將屯堡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展示出來。汪氏宗族的形成成長便是存在于屯堡鄉村社會中一個活躍的社會細胞,其中家庭承襲與承嗣、宗支成長,無不保持屯堡社會組織細胞活力,它由家庭裂變為家庭再擴大為宗族,生生不息地墾殖著黔中腹地每一片土地,建設和維系和發展起一個廣闊的黔中屯堡社會。
三、汪姓家族契約文書反映出的家庭經濟生活
農村家庭經濟最基本的財富就是田地,生產生活都圍繞其展開。它還涉及田地經營方式,如買賣、租佃、典當等。汪氏家族在吉昌屯留下的契約文書,作為歷史文獻,可以再現這里的經濟社會生活,尤其是一戶家庭活生生的經濟場景。
第一,家庭經濟的主要經營活動就是田地買賣。雖然屯堡最初是“軍事單位”,但自明代中期以來,屯堡人的基本生活還是從事屯田生產,所謂“三分守衛七分屯種”。至清康熙朝不斷改衛所為府縣,屯堡本身也就是一個普通農村村寨,屯堡人家庭經濟預期就是能不斷地增加田地以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因而家庭主要經營活動就是田地買賣。《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收載有汪氏家族由乾隆到宣統時期各家庭買賣田地契約,表1則是對這些契約文書進行的一個量化統計,大致可以了解各時期家庭經營田地活動基本情況:

表1 汪氏家族各家庭成員買進田地統計 價格單位:兩/銀
表1顯示出屯戶增加田地的方式通常是通過購置田地實現。通過量化買賣過程中戶主一生進行的買賣次數、購置財產的類型、數量、支出資金等數據,是可以對一戶家庭或者戶主一生聚集財富的經濟活動及經營能力進行觀察。首先:一戶家庭或者戶主買賣行為持續時間長。表1列出各戶主自產生第一件契約到最后一件,前后時間分別是:汪世榮12年、汪子重37年、汪朝禮18年、汪起云24年、汪田氏34年、汪興燦20年。這些持續時間的意義在于表明,戶主買賣行為是伴隨著其家庭戶主地位確立后,也是其管理家庭經濟最佳時期,因此可以說是有能力的戶主持續一生的經濟行為。其次,通過買賣所增加財富,都是為增進家庭經濟實力,不光是食物水平,還可能地改變人居環境。因此買賣財產并非單一田地。如汪子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買進軍輪屯水田4合四抄,最后一次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買江家水井地2塊,但在其37年間在購置田地的同時,也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買房屋地基1間,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買大坡上陰地1塊。相似情況如道光至咸豐時期的汪田氏,其在34年間不斷地購進地購進水田、山地、菜園、房產地基。購置財產的多樣化,不單是農戶家庭經濟經營主要的活動,而且也表現出一農戶家庭的財產結構,它不僅僅是水田,而有其他類型的財產,盡可能地豐富家庭生活。如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十九日從汪田氏從汪鄭氏手中買進正房2間,廂房1個,天井1個,后院東廝1個,菜園一段。
再者,雖然從現存契約文書看,戶主買賣行為頻次不是很頻繁,但一次行為往往出資不菲,如汪世榮在乾隆二年(1737年)一次出資45銀兩購進面積“糧四升”的田塊,咸豐八年(1858年)汪起云出資銀58兩購進面積“糧六升七合”的田2塊。雖然無資料確定他們家庭經濟整體條件,但考慮到當時屯堡地區“小人日食米一升,計值不過四五厘”[1]322,所支出的都是很大一筆資金;至少可以顯示出屯堡人家致力于增進家庭經濟的信心與付出的力度。但從表1所列各戶買賣行為時間間隔看,汪興燦年均次數最頻繁,20年間進行了11一次買賣,而汪子重在37年間只有9次;從買賣行為平均間隔看,平均3年一次;其從增加田產數量來看,一生購進也僅2畝田(9.4升)。表1各戶主購進田畝數量顯示,最多一戶汪興燦,購進田畝也僅4畝(21升),一生為增進家庭財產支出銀兩200余兩。上述情形說明汪氏家族各時期的家庭經濟規模趨小,增進家產資金周轉時間長,須經歷一段時間的儲蓄方才有再次累進家產的能力。整體而言,吉昌屯民都有致力增進田產的期望,但因其財力限制只能是稍事積累而已。
屯堡家庭經濟經營活動實際上也體現出屯堡人家的家庭生活水平。表1顯示,凡一切可利用的土地資源都盡可能地轉化為經濟價值,所謂盡地利豐富日常消費。從物質生產資料看,水田旱地,無論面積大小、地力貧瘠與否;山地草場,屋基陰地,種種類型皆在農戶購進期望中,目的都是為提高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水平。家庭經濟最基本的財富就是田地,生產生活都圍繞其展開,那么,一戶家庭擁有田地總量,就是衡量其家庭經濟生活水平基數。汪氏家族遺存下來的各類文書,為我們了解一個家庭基本田產擁有量提供了文獻,其中最好材料就是分家文書。汪子重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經歷分家,所分得田產面積合計是1斗7升9勺4抄。以科田稅收每畝5升3合6抄計,那么大致有3.5畝左右。分家文書沒有講明時父親還在否,但文書契約表明,汪子重是三弟兄,遵循傳統社會分家“諸子均產”原則,那么,分家時刻原家庭擁有田產至少在18畝左右,再加上部分旱地,即是一農戶家庭擁有田地總量。
一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分家文書表明,遵汪廷柏遺囑其二子汪起云、起貴分家(此時大概汪廷柏已逝世,因為沒有他的買賣田地文契)。長子起云所得墳低下田1塊、大田1塊;小山背后田1塊,秧田上下2塊;麒麟屯墳低下2小塊(內上下2塊),毛兒山山場1塊、團山背后田1塊,汪家水井地2塊,大坡面地4塊,陳家墳邊地1塊,墳低下地右邊菜園左右2塊。次子起貴所得墳低下長田1塊、水井邊田1塊、右邊菜園內中間1塊;白蠟田1塊,小山河邊田1塊,黃混田1塊,老豹河秧田1塊,大壩上田1塊,灣田1塊,石頭旮旯田1塊,大塘路邊田1塊,石洞口地1塊,大凹地1塊,大坡背后長箐菜園地在內1塊,小山園地1塊樹木在內,燕子地1塊。
汪起云、起貴所分財產,合起來應當就是汪廷柏作為戶主時一個完整家庭擁有田地總量。雖然沒有具體的田畝數字,但從田地“塊”數測算其田地應當是一份較大的田地產了。汪廷柏是汪子重的孫輩,如果以汪子重家庭比較,顯然汪廷柏時期其家庭擁有田畝面積與汪子重家庭田面積比較是成倍增長,也不過大致40~50畝余。類似情形也可在同治六年(1867年)汪田氏與其兩子分家是田地的配置量看到。那么似乎可以推論出,吉昌屯汪氏一戶農家的田產(不包括旱地),至少在18畝以上。
戶均占有田地量只是衡量經濟水平的一個參數,而生活水平的質量則取決于人均消費水平,人均消費水平可從人均田畝面積與產量之比來測算。吉昌屯處在黔中地區良好的農業生產地理環境內,明代弘治時期編纂的《貴州圖經新志》對安順府的描述是“地當要沖,山擁村墟;……而臨沃野,疇彌望”;經濟綜合評價是“境土坦夷,物產富庶,甲于它郡……惟貿易日趨于利”;對農作物生長而言是“土地饒沃,宜稻”。[15]又據新編《安順市志》載,乾隆時本地畝產谷200斤[4]707,那么,維系一人一年生活標準大致在田3畝左右,即人均一年必需口糧600斤谷子,若再輔助旱地作物,即可滿足一人一年的溫飽消費水準。從汪氏家族各時期契約文書所載,其一戶家庭擁有的田產在18畝左右。從對《吉昌契約文書編》內數據的分析,以一戶家庭至少以5~6人計,那么平均每人3畝左右,人均基本消費谷600斤左右。平均每人3畝左右人家具體的消費情景怎樣,吉昌屯一件分家文書記載了養膳父親一年必需的生活物質:“每年養膳父親,除田租一石,兄弟各奉養田租八斗、糯谷二斗,包谷各二斗,黃豆各三升,葵花各三升,豬油共一十二斤,鹽八(巴)六斤。”[13]372此也應當是屯堡人家一般的年消費水平。人均田三畝是保障屯堡人生活的基本條件,如果人均三畝以上,則算可過上較好的生活。
從表1也可看到,買賣房產也是家庭經濟主要的經營活動,同時也是從生活資料方面反映出屯堡人家的家庭生活水平。汪氏家族契約文書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是幾乎每一個時期各家庭,房屋地基及附屬設施都在購置范圍內。而且如同購進田地一樣,都不失時機地持續增加房屋基礎,表1所列各戶主,除汪興燦外,一生都有兩次及以上地購進房屋地基。汪朝禮最為典型,表1顯示其有5次買賣行為,其中嘉慶四年(1799年)二月初七與十九日,兩次買賣行為均與房產相關。還另有一件契約文書是他在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初六日購置房產時的記錄,文書內容如下:
立賣明房屋地基文契人汪朝周。為因移業置業,只得請憑中上門,將買明堂叔房二間、東斯一個,出賣與汪朝禮名下住坐。東抵徐家房南抵胡家墻本族地基,西抵買主房,北至路,四至分明。即日得受賣價銀紋九各半一十六兩四錢整。自賣之后,任隨朝禮子孫永遠住坐,賣主親至人等,不得異言。如有異言,朝周一面承當。恐后人心不古,立契一紙永遠存照。
憑中 汪朝相(花押) 汪子盛(花押) 汪子明(花押) 馮永俊(花押) 汪朝選(花押)
叔母汪鄧氏(花押)
代筆 胡鳳鳴
嘉慶十八年九月初六日立賣契人汪朝周(花押)[14]140
汪朝禮三次用于購置房產支出銀50.6兩,超過了購進田產的資金。因此,從作為生活資料的房產買賣看屯堡人家努力擴展住居,凡此行為目的都是為提高宜居舒適度。
四、從清代汪氏家庭經濟理解屯堡經濟社會
汪氏家族的經濟生活,也應當是屯堡每一戶家庭基本的經濟行為。《吉昌契約文書匯編》還分別收載有田氏、陳氏等家庭遺存的清代契約文書各百余件,情形與汪氏家族一樣(明初吉昌屯建屯時共有九大姓,即田、馮、汪、許、羅、胡、鄒、范、馬,《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收載契約中,汪氏家庭最多,故選擇汪氏為例),無一不顯示出,每一個家庭戶主但凡有能力都會持續一生地買進田地屋基等。屯堡人經濟生產與經營活動,直接影響著屯堡經濟制度與社會面貌,而土地占有與地權分配則是經濟社會制度的核心。
汪氏家族契約文書提供了一個觀察土地占有與地權分配的窗口。明代屯堡社會,土地占有及地權的制度性安排,是屯軍(屯民)領種“國家”分配的一分(份)屯田。按照規定,貴州屯田一分在18畝至24畝間,普通軍屯一般18畝。雖然差別在于軍職差異⑦,但屯戶占有田地并不懸殊。以屯戶五口之家,普通軍屯人均3畝。凡屯戶占有分地相同,身份上相當于國家的“份地農”;屯田屯軍(屯民)世代耕種,不能買賣,在理論上維系著一個“均田”的屯堡社會。自明代中期以來屯田制度不斷遭到破壞,屯田買賣逐漸合法化。尤其經過清康熙時徹底地“撤衛改縣”,屯田制度消解。屯田民田化,軍屯田地自由買賣,屯民由軍屯“份地農”轉變為“編戶齊民”的普通自由農戶,吉昌屯汪氏家族自雍正以來至清末的家庭、家族成長,及各時期家庭土地買賣與田地積累,就是社會經濟環境變化的產物。
汪氏家庭社會身份的變化,只是社會經濟環境變化表現形式之一,最重要的是身份變化及持續不斷的田地買賣,推動起地權轉化與重新分配,打破了原有“份地農”維系著一個均田的屯堡社會面貌。那么,這個變化形成的社會地權分配情況如何?解釋社會地權分配現象首先得確定普通農戶占有田地數量。困難是,現存官方歷史文獻中很難有對清代屯堡農戶家庭田地占有量的記錄,但利用吉昌屯出現的各類民間契約文書,是可以對一戶農家田地大致占有量作出分析。
確定普通農戶占有田地數量,首先得測定一戶普通農戶田地基本占有量。分家文書是分析普通農戶田地基本占有量的一個基點。分家往往是家庭成員長大成人,須另立門戶進行,換句話說,也是一戶家庭經濟發展到最“鼎盛”時期對家產進行分割,因而是一個家庭田地占有量“飽和度”的節點。前文對汪氏各家庭分家文書分析指示,汪氏家族自乾隆以來各家庭分戶占量,雖然有少數家庭通過持續地購進田產也有可能達到40~50畝余,但均戶家庭基礎量大致為18畝左右,各時期汪氏家庭增進田地情形當是吉昌屯致力增進田產家庭的代表,這在《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收載田姓或者陳姓等家庭契約文書中也能看到,似乎可以推論出,吉昌屯一般農戶家庭基本擁有田產量在18畝左右。是一個地權相對分散的社會。
什么因素決定了吉昌屯地權相對分散?決定土地分配集中與分散的因素很多,如商品經濟、社會成員身份的復雜性與多樣性、追求財富的手段等等,但另一個社會因素,即社會家庭自身的結構發生著很大的作用。這個家庭自身結構即是不斷的分家,分家是分散地權的一個決定因素。屯堡社會正是由屯軍家庭生生不息的分化擴展而不斷地壯大;當一個家庭財富積累到相當大量的時候,也就是家庭成員分家之時。分家都是家產由諸子均分,每一次分家,也都是對原有家庭長期積累起來的田產的拆分。因此,屯堡社會中,分家是消解土地集中的常數。再從增進方式看,汪氏家族各時期家庭都持續地購置田地,表明都有渴望增進家產的信心,但分戶后新的小家庭,往往經濟能力有限,因而每戶家庭購進田地間隔時間長,購置量又不夠大,限制了家庭田產積累的速率與量的增長,這樣也限制了社會田地向少數個人集中的傾向,有利于屯堡社會內地權分配的平均化。
如果吉昌屯地權分配方式是整個屯堡社會的一個縮影,那么,隨著清代屯田制度徹底瓦解,屯堡社會也性質發生了深刻變化,但由土地買賣等經營田產方式促成的土地分配情形看,雖然土地買賣是一部分人喪失土地而另一部分人增進了土地,推動著地權向另一些家庭集中的傾向,但從汪氏家族為典型的吉昌屯事實看,地權分配仍然與明代屯堡社會“份地農”保持著一個相當水平,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小土地占有為主導的經濟社會。
吉昌屯汪氏家族各時期的家庭經濟經營活動,還反映出屯堡社會的財富觀。契約文書一般都有買賣物、買賣雙方社會關系、買賣原因等內容表述,這些信息交織在一起,從多重角度體現出由農戶家庭構成的屯堡社會財富觀。首先,從汪氏家族買賣契約反映出,凡與生產生活相關物質都是家庭財富。這些買賣物中有田產、房屋地基外,還有旱地、荒壩、山土菜園、陰地、樹木、倉房、牛棬、院落、墻垣瓦片、糞塘、天井、東廝(茅廁)。它們是農村財富的基本類型,其中除了田產外,最重要的就是房屋(或屋基地),因此田產與房屋(或屋基地)構成了農村家庭經濟的主要財產。
第二,流失財產盡量保持在家族范圍內,即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財富觀。據學者研究,吉昌屯買賣雙方社會關系表明,交易雙方大多為本家親屬或親兄弟[13]44,可見雖然吉昌契約文書很少有“先問親鄰”等約定俗成條件句表述,但實際買賣田地流向大多在親屬間內部輪回。縱觀汪氏家族自乾隆到清末的買賣契約,一個很醒目的事實是,汪廷柏次子汪起貴將大量田產多次出售予胞兄汪起云,相似的是,汪起云次子汪興賢也是將大量田產多次出售給胞兄汪興燦,換句話說,汪起云與其長子,都從自己的抱弟手中購進田產,此突出現象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但財富不外流的社會財富觀可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第三,買賣契約文書還體現出另一種與財富不外流不同的社會財富觀,即在涉及財富權益時,唯個體家庭利益至上。從汪氏家族買賣行為雙方關系看,社會人際間關系包括親屬間關系,反映在經濟上,讓位于個體利益的計算。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月初一日汪爾重將一處房屋地基出賣與侄子汪世榮,事過七年之后的乾隆五年(1740年),汪爾重卻對上次交易的公平性提出質疑,聲稱因“房地地價不符”,并請人理講公處,最后侄子汪世榮不得不“再補銀貳兩伍錢”與叔父汪爾重。此事例似乎表明在個人權益方面,時間絲毫沒有消磨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它更在社會意義上深刻地體現出,在財富與親情關系兩端,個人經濟利益始終處優先選擇的頂端。在這種社會財富觀下,許多難于理解的交易行為都變得“合情合理”了。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一次田產買,一塊田出售價僅1.5兩,但雙方仍然對價格斤斤計較。一次買賣過程再現出金錢面前無助于親情的故事:汪朝有嘉慶四年(1799年)二月間兩次賣房屋契約,原因是債務所因。緩解債務本來有多種方式解決而非得出售房產。如可以通過借貸方式還債務,也可以通過親友間求助。可能考慮到還貸能力不足,更可能親友間也不相助,故只能將房產出售與堂弟汪朝禮,堂弟汪朝禮支付銀34.2兩。這是一次不小的房屋買賣;而本來作為“有錢”一方的堂弟,出于親情本可以借錢助堂兄渡過危機,但卻選擇了買賣方式。可見,個體家庭利益高于親屬關系,是屯堡社會財的一種財富觀。
通過汪氏家族各時期家庭經濟的經營活動,還可對屯堡社會進行經濟史的分析。首先在社會經濟關系中,可以觀察到制度變革從政策上對農民生活產生影響。汪氏家庭契約中可見到大量旱地買賣契約。據《吉昌契約文書匯編》編者統計,收集的田地買賣契約300余份,陸地與旱地占106份,此外還有20余份菜園地[13]12,那么旱地占有很大比重。原因在于自順治、康熙時,朝廷都鼓勵開墾荒地,并在政策上給予緩升科或五六年后升科的優惠,在貴州對地頭地角、土丘及土地澆薄則永免升科[16]。故乾隆以來荒地被大量的開辟出來成為旱地,以至于到乾隆晚期荒地開辟已告罄。吉昌契約文書中大量無糧旱地的買賣現象,應當就是“國家”鼓勵開墾荒地政策后的自然成果。同時它與其他社會現象結合,塑造和促進著屯堡社會農村生活面貌。開墾荒地有兩個結果,一是增加家庭消費能力提高生活品質,一是人口增加對居住環境的需求。尤其是后者,當面臨已無荒地可開墾之時,只得向之前本屯或者家族成員所開墾旱地提出要求,通過購置作為房產地基的旱地以新建住宅。這樣,因山地的不斷開墾出來,困人口增加家庭不斷的裂分出新家庭則,形成了貴州農耕社會屯堡村寨景觀基本面貌:家越來越小,村寨越來越大;家庭住宅越來越向高地擴展,屯堡村寨也逐漸形成階梯布形格局。
家庭經濟的經營活動中產生的許多賣田契,內含著屯田制度變化痕跡。吉昌屯賣田契大都有標注田畝面積的說明,往往以該田應納稅賦量表示,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三月初四日汪再昆賣田契,標注田畝面積環節寫作“其隨田科米倉升原糧四升,一升四合一勺”。但也有部分賣田契在標明田賦時,又有“加增”說明,如乾隆二年(1737年)正月二十二日程國珍賣田與汪世榮契寫道:“隨田科米倉升原糧四升,連加增共倉升七升七合”。為何呈現兩種標注?又何為“加增”? 實際上“加增”的表述隱含著兩個信息:一是在經濟制度方面,可能在改衛為縣時,原屯田與科田(民田)征收賦稅時在稅率上有過調整,隨后又恢復舊制。如(咸豐)《安順府志》記載:“康熙十年十二月普定衛改縣后,知府將親轄地征糧之權下放給普定縣,二十六年安順軍民府改安順府時,普定縣畝征銀一錢一分,米一斗一升,后增為二錢,米二斗”[2]457,大概就是出現“加增”的原因。但在查閱現有歷史文獻時卻未見有更多記錄,這里只能是一種推測;一是從社會問題方面看,是對流失屯田清查的結果。清代安順府征收田賦的規則是原屯田畝起科本色米2.18斗,科田每起科本色米5.33升。兩者相差近四倍。自明末屯田制度逐漸消解,尤其是康熙時裁撤衛所,不法屯田所有者為逃避“重稅”,其方式就是“改屯作科”,即在田地買賣過程中將屯田變換身份為科田以減少賦稅,或者以“飛灑”“詭寄”等手段。屯田流失不僅賦稅大量減少,而且“改屯作科”引發許多社會問題,乾隆以來多次下令“清厘田賦”或者“丈田均賦”。田地買賣契約文書中注明“加增”,可能就是清田后的結果。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它都是從底層反映出在衛所改制過程中社會制度變革中出現的一波三折。
田地的社會價格也體現出了屯堡經濟社會的一些特征。如果要深刻測算農村家庭經濟實力與反映農業經濟,那么,田地價格是一個重要標桿。但在田價問題上,雖然吉昌契約都有田地面積與價格關系,由于吉昌屯契約少,很難平均出一個社會基本田價,進而與農戶經濟能力建立上關系。但從部分契約看,吉昌契約內的田價差異很大是一個顯著現象,其中有些田價特別反常,同樣標明相同或相似面積的田,價格卻起伏不定,如咸豐八年(1858年)一次買賣時,6升7合產量的田出售價格是銀58兩,而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一次買賣,7升產量的田出售價僅1.5兩;在有些時間里一些買賣中的田價底得不合常識,田價淪落到了“白菜價”水平,如咸豐二年(1852年)一次買賣時,產量2斗2升(4畝余)的田出售價格僅13.6兩,價格之低似乎不可理喻。當然,影響田價因素較多,普遍的是田地品質有上中下等則不同,但在屯堡地區,最直接的因素在于每畝田所承擔的田賦有關。如前所述,屯田與民田(包括科田)征收田賦時兩者相差了4倍。咸豐二年(1852年),產量2斗2升(增)田價格13.6兩,如果將其視為屯田性質,那么它只能是民田價格的1/4。因此,如果以畝測算,買賣中屯田便益,民田貴就是自然現象了,那些許多看起來是白菜價的田,若以屯田相權衡,就不是不可理喻的情況了。
吉昌屯田地買賣契約文書中反映出的支付媒介,也體現出了屯堡經濟社會又一個特別現象。交易活動中通常的支付媒介是貨幣現金,清代自嘉慶后尤其是道光以后,社會交易的支付貨幣基本上由之前的銀兩變化為制錢,光緒中后期通常為銅錢。從吉昌屯契約文書中看到,自雍正至宣統,汪氏家族各時期支付媒介一直都是以銀兩結算,這是一個很突出的經濟社會現象;由此擴展開來看,如果將貴州分為東西兩部分,今天黔東地區(銅仁與黔東南地區)現存清代契約文書可以看到,乾嘉時期還在以銀兩支付,突然從嘉慶后至道光起基本上使用制錢,光緒中期起則多為銅錢支付。對于支付貨幣的變化,今天人們往往用明清時期“白銀流通理論”作為解釋模式——明代美洲白銀進入中國市場增進了中國的白銀流通與支付,鴉片戰爭后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白銀成了稀缺資源——來解釋黔東地區發生的變化。但從在屯堡社會區的紫云、盤州、安順已發現的同一時期契約文書看,都一直保持著銀兩支付現象,顯然,屯堡地區契約文書卻難支持“白銀流通理論”的解釋模式。如果考慮到清代中期以來安順府發展成一個商業比貴陽還繁榮地區,市場與商品交易對白銀應當有更強烈的需求,那么,清代以來安順屯堡一直通行銀兩支付,應當至少是一個區域經濟史研究的新課題。
雖然個體家庭經濟主要是家庭內部的財產經營,但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通過多種方式與社會發生緊密聯系。而在吉昌屯,每一個家庭經濟都會通過“汪公會”及“抬汪公”活動,構成了吉昌屯的“公共經濟”。屯堡研究中一個公認的知識是,“敬汪公”是屯堡文化的特征⑧,敬汪公的一大民俗活動就是“抬汪公”。吉昌屯不僅設立有汪公廟,而正月十八抬汪公是各屯堡中最為盛大的一個。
傳統的“抬汪公”有一套煩瑣又復雜的事項和程序。據呂燕平研究,完成一次抬汪公活動,至少有5個表演組,而參與服務人員達400人,觀眾達萬人以上,僅2015年一次抬汪公支出費用4萬元[17]。“抬汪公”因一年一度故盛大隆重;因盛大而事項繁多而用貲不菲,因此,抬汪公是一次集村民之財,共“抬汪公”之狂歡,須要一定經濟基礎。為此在歷史上還形成了“汪公會”(今天又稱“十八會”)來組織和完成各項活動。“汪公會”一個主要職責就是籌集經費;籌集經費方式不外通過經營會產。從《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所載文獻看到,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汪公會就有放貸記錄,直到光緒末年。但“汪公會”經營出產方式主要有田地買賣與出佃田地。
“汪公會”經營會產是與村民的互動。作為村民來說,資助方式汪公會有與汪公會發生買賣關系,或者租佃汪公會田。《吉昌契約文書匯編》內就收載有幾件涉及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等時期的汪公會買賣田產契約。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十六日汪起貴出售田5塊與汪公會,該田載糧1.12斗,合兩畝田(70兩銀子)[13]17;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二十八日,汪公會首陳煌文、汪煥之等,將田一處出賣與汪興燦,載糧1升(55兩)[13]53。汪氏家族通過出售或者購置會產,回應了汪公會對經費經濟的需求。同時也看到,汪公會一次買或賣過程中,收或支者都在50兩銀子之上,表明其在與村民經營活動中已積累起相當的經濟實力。
《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收載有一件年代無考的汪公會田冊,不僅記錄了吉昌屯汪公會租佃田產的收益,還可看到汪姓成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據研究者分析,租佃會田戶80戶,承租田約340畝或 410 畝(平壩衛計 340畝;普定衛計410畝)[8]。汪姓家族承佃田地的成員如下:
汪文濱,糧四石,田十七塊,地名下壩、白泥、大壩;
汪朝德、汪朝興,糧四石,田十二塊,地名坐落豬棬(圈)壩、門前河、大壩;
汪朝李,米五斗,田一塊,坐落巖底下;
汪應達,糧一斗,田一塊,坐落白泥;
汪朝梁、汪朝仁,糧二斗五升,田一塊,坐落大壩;
汪朝相、汪廷炳,糧五斗,田一塊,坐落晏家井;
汪廷興,糧一斗六升六合七勺,田二塊,坐落大壩中;
汪朝禮,糧八升三合三勺,田一塊,坐落門前河;
汪子虞,糧三斗五升,田一塊,坐落晏家井;
汪仲德,糧二斗五升,田二塊,坐落門前河;
汪應明,糧三斗七升五合,田一塊,坐落老豹河;
汪應鐘,糧一斗八升五合,田一塊,坐落大壩上;
汪成高,糧七斗五升,田二塊,坐落大壩上、老豹河;
汪成友,糧三斗七升五合,田一塊,坐落田壩中間;
汪應才,糧五斗,田一塊,坐落大橋邊。[13]418-423
如果從吉昌屯居民構成看,全屯至少有17個姓氏,而在承佃會田的80戶中占有汪姓15戶,汪姓可謂是承佃大戶。汪姓承佃經營田合計“有糧”41.85斗;“有糧”是對田地應當繳納田賦的表述,如果以民田每畝糧4升計,那么有糧41.85升折合田100畝,占到了全部的出租田的1/3之一或者1/4之一。可見,汪姓家族成員深入地參與到全屯的公共經濟中去,作出了積極貢獻。
注 釋:
①羅繞典輯:《黔南職方紀略》,點校本,貴州省文史研究館編:《黔南叢書》第二輯,上,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頁。這里需說明的是,今天的“屯堡研究”,通常將屯堡人的“發現”歸于1902年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認為是他到平壩安順做人類學考查時,在其調查報告中關注到稱之為“鳳頭雞”的屯堡人。如萬明在其著述“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中講到:“最早注意到屯堡的, 是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1902年他到貴州飯籠塘(今平壩區天龍鎮)考察,記錄了‘明代的遺民鳳頭雞’……”(載《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35頁)。其實這一說明與事實不符。上引道光時期文獻可知,當時的著述者就已經指出屯堡人特別的漢族身份,并用“鳳頭笄”“鳳頭雞”等詞指稱,后來的鳥居龍藏不過是沿用這一稱謂而已。
②據(咸豐)《安順府志》記載,普定改衛為縣時,舊衛管五十軍屯,今分為四里,奠安里即為其中一里,雞場屯屬奠安里。參見(咸豐)《安順府志》,點校本,第139頁、第146頁。
③上述吉昌契約文書研究文獻,孫兆霞、張建文分別載《吉昌契約文書匯編》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 年第 5 期;孟凡松、吳羽文載《屯堡文化研究》2013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頁;張秀娟文載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15 輯,巴蜀書社2012 年出版,第 382-399 頁。唐智燕文載《畢節學院學報》,2014 年第 9 期;杜成材文載上海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7年;大屯契約文書研究文獻,分別載載《安順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及2021年第2期。
④孫兆霞等編:《吉昌契約文書匯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10年版,第342頁。本文所引契約文書,皆出自《吉昌契約文書匯編》,本文主要論點及揭諸之歷史事實,皆來自對契約文書的分析,由于征引契約文書較多,為避免繁瑣,凡本文以下所引契約文書,非特別需要不再注明出處與頁碼。
⑤汪希鵬主編:《汪氏宗譜(颕川-黔腹)》,《黔腹汪氏宗譜》編修領導小組2001年10月印。另:該宗譜收載入譜的吉昌屯汪姓成員較簡略,如在《吉昌契約文書匯編》中可見到的許多汪氏成員,沒有記載入譜。而且該宗譜在表現家庭成員時,也有錯誤表述之處,如將本是同胞弟兄的汪興燦、興賢,分別為堂兄弟關系等等。
⑥在吉昌屯汪姓村民家藏嘉慶十二年至宣統三年,內容涉及買賣、典當與房產析分等44件契約文書,可以建構起汪朝富→汪起能(倫)、起有、起后→汪興才→汪純有家族世系。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他們是汪世榮家族另一支,但從其字輩推論,應當是與汪世榮家族為共同的宗支成員,他們共同構成吉昌屯汪氏宗族。參見杜成材《晚清至民國貴州安順吉昌屯堡契約文書研究》,上海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139-155頁。
⑦參見王杏《清理屯田事議》:“總旗一名種田二十四畝,小旗一名種田二十二畝,軍人一名種田一十八畝,內各以八畝納糧四石,余外皆為會計糧田,以給助口食等用。”載(嘉靖)《貴州通志》,張祥光,林建增點校本,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頁。
⑧屯堡研究中一個共識,認為地戲、儺戲、敬汪公,祀五顯、話語多帶“兒”音,是屯堡文化的特征。參見蔣立松《從汪公等民間信仰看屯堡人的主體來源》,載《貴州民族》.2004年第1期。又萬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載《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