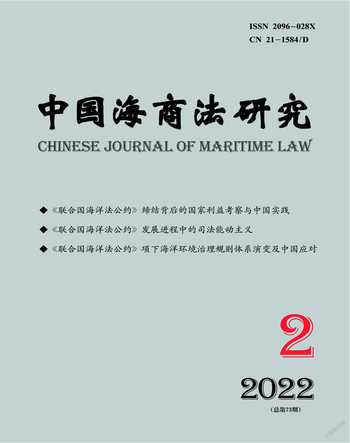《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演變及中國應對
周江 徐若思
摘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是當今海洋環境治理的核心,該公約不僅搭建了海洋環境治理的基本框架,同時也引入“參考規則”將外部環境條約納入治理規則體系之中。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不斷演進不僅影響著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調整,并且隨著21世紀人類對海洋需求的增長逐步呈現出新時代的新特點。中國應當積極應對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變,加強對“參考規則”適用性的研究,在尊重現有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基礎上輸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開展區域及全球合作。
關鍵詞:海洋法秩序;“參考規則”;海洋環境治理
中圖分類號:D993.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28X(2022)02-0025-10
Evolution of the rules system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China’s response
ZHOU Jiang,XU Ruo-si
(Southwest Institute of Ocean & Natural Resources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Currently, the rules system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s the cor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Convention not only establishe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ut also introduces “rules of reference” to incorporat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treaties into the governance system.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ot only affects the profound adjustment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but also show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growth of human demands for the sea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rules of reference”, promote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ctively carry out regional and global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existing marine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law of the sea order;“rules of reference”;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21世紀世界各主權國家紛紛將國家戰略中心由陸地轉向海洋,人類在海洋的活動呈指數級增長,對海洋資源的依賴與日俱增,加之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海運成為連接全球貿易的重要方式,海洋承擔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極具破壞性及不可持續性的捕魚活動、來自船舶的航運污染及船舶撞擊引起的海上航運事故、陸源污染、海洋酸化、珊瑚礁滅絕、全球氣候變化、海上油氣資源開采、核泄漏等問題均導致海洋生物多樣性喪失嚴重,海洋生態環境形勢嚴峻。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日益嚴峻的海洋威脅及挑戰影響著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需要適應新時代的環境保護需求,與新時代出現的海洋環境保護問題同步發展并不斷演進,從而實現對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海洋生態環境系統的有效保護。當前,形成國際空間海洋新秩序并對海洋資源進行可持續開發和利用的努力正在全球范圍內取得進展,海洋環境治理演進內容及未來發展趨勢已成為新世紀的新課題。
一、《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
《海洋法公約》被稱為海洋領域的“憲章性法律”,致力于規定海洋的全部方面,因此難以深入或具體解決每一法律問題,同時在一個高度多樣化的國際社會中,執行一項范圍、程度以及復雜性都無與倫比的公約存在巨大困難。尤其在海洋環境治理問題上,因涉及不同主權國家及地區的利益,特別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養護和利用海洋資源問題上的分歧會更加明顯,難以通過《海洋法公約》對其進行有效的規定。[1]同時,海洋環境的養護及治理是國際環境法中發展最快的門類之一,早在20世紀20年代船舶航行及油污問題便已經開始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1972年聯合國召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和《人類環境行動計劃》,并通過了大量保護海洋環境的多邊及雙邊條約。國際法的社會基礎與基本特征決定了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碎片化。1982年《海洋法公約》通過為海洋環境治理搭建規則框架,創造性地引入“參考規則”,將其通過前以及通過后的各項海洋環境類條約納入《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之中,共同構成《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
(一)《海洋法公約》搭建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框架
《海洋法公約》修改約文議定規則,以協商一致原則作為約文通過的要求。協商一致原則最大程度保障了世界各主權國家的廣泛參與,為約文的起草與通過創設了便利條件。但同時為彌合分歧而修改的協商一致原則也造成《海洋法公約》措辭及表述上的界限模糊,這使其最終只成為框架性規則。《海洋法公約》序言十分清晰明確地界定了“海洋環境保護與保全”的價值,并在正文第十二部分搭建了全面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框架。《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三類內容。
第一,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污染的一般義務。《海洋法公約》重視平衡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護,將海洋污染的多種形式囊括于海洋環境保護與保全的框架之內,同時尊重國家主權原則,規定各國對海洋資源享有主權,即有權開發及利用。《海洋法公約》第192條及第193條注重各國對海洋環境保護及保全的義務與利用海洋資源權利的平衡。第194條至第196條中要求各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污染。
第二,肯定主權國家在海洋環境保護層面發揮的作用,要求各主權國家開展全球性及區域性的合作。《海洋法公約》將開展國際合作列為基本原則,要求各國開展國際合作并制定相關國際規則、標準、辦法和程序。《海洋法公約》充分借鑒之前通過的相關環境類協定,強調區域合作原則便是以1972年《防止傾倒廢棄物及其他物質污染海洋的公約》(簡稱《倫敦公約》)第8條關于在防止污染時盡力達成區域協定的要求為基礎。[2]《海洋法公約》雖采取“要求”一類以供誠意履行的法律義務形式的表述,但這并不影響各國在適用條款規定時的行動自由,開展合作保護海洋環境的性質根源仍為鼓勵性而非強制性。《海洋法公約》要求各國與國際組織合作,照顧發展中國家海洋資源開發及保護能力的不足,提出各主權國家及國際組織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同時給予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前瞻性地提出監測和環境評價制度,要求各主權國家應盡力直接或通過各主管國際組織,監測海洋污染的危險及影響,作出報告并將報告公開發表,對可能影響海洋環境的行動計劃進行環境影響評價;鼓勵各主權國家采取國內立法的形式,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污染。
第三,設置執行及保障條款,規定國家責任以及主權豁免以保障各主權國家環境保護及保全義務的履行。《海洋法公約》第235條對海洋環境保護責任進行概括性規定,明確承擔海洋環境保護責任的兩類主體,即國家、自然人或法人。國家應履行海洋環境保護及保全的義務,同時進行國際合作以對其未履約行為而造成的環境損害進行適當且迅速的補償。對于作為民事主體的自然人、法人來講,若其違反保護及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對于所造成的損害,各主權國家應制定國內法以保障補償及救濟。《海洋法公約》采取合理謹慎原則設置國家責任,國家負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減少、防止海洋污染以及約束管轄或控制下的行動不對海洋環境產生破壞的合理謹慎義務,并要求各主權國家保障損害的救濟及補償渠道。[3]合理謹慎原則要求各主權國家采取措施履行海洋環境保護及保全的義務,注重各主權國家履行義務的形式過程,換言之,只要主權國家對海洋環境的保護及保全制定了相應的國內法規則,并對海洋污染損害提供了及時有效的救濟,便可認為主權國家已積極履行該義務。
承前所述,《海洋法公約》致力于搭建一個海洋環境保護及保全的行動框架,在充分尊重各主權國家主權的基礎上要求國家履行海洋環境保護及保全的義務,注重平衡主權國家利用海洋資源的權利與保護海洋環境的義務,鼓勵各國開展合作,簽訂多邊、雙邊環境協定,以及制定國內法以采取具體措施保護及保全海洋環境。
(二)“參考規則”細化具體內容
從國際法本體論出發,國際法的價值本質是引導各主體建構國際法體系的正當性基礎,國際法基本原則以其基本價值傾向和普遍性引導具體規則的創設與適用。[4]為保障《海洋法公約》能得到廣泛接受,制定者采用協商一致原則力圖最大程度地爭取世界各主權國家的“普遍參加”,平衡各主權國家的利益沖突。尤其在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中,傳統國際法規定的船旗國管轄注重保障“航行自由”,與沿海國注重保護海洋環境利益發生沖突,這導致沿海國管轄權的擴張需求遭到了奉行“航行自由”的海洋大國的激烈抵制。為彌合沿海國、船旗國、港口國之間的利益分歧,保障世界主權國家的廣泛參與,應對海洋環境規則及標準不斷發展的需求,《海洋法公約》第十二部分以框架形式規定海洋環境保護及保全的權利及義務問題,同時創新性地引入“參考規則”以解決具體海洋環境問題。《海洋法公約》通過“參考規則”將通過前的其他環境協定中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納入《海洋法公約》治理體系之中,同時一并將未來新發展的環境協定的規則、原則納入其治理體系之中,[5]平衡了各主權國家的利益訴求,建立了國際規則及標準的體系化系統。
事實上,《海洋法公約》本身并未采用“參考規則”一類的措辭,“參考規則”主要用來指《海洋法公約》允許將其他國際法規則納入公約治理體系的情況。尤其在《海洋法公約》第十二部分海洋環境的保護與保全中,公約多采用“參考規則”來引入外部規則作為對公約具體內容的細化。如《海洋法公約》第207條、第208條規定,各國應考慮國際上議定的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同時制定國內法,但國內法的制定標準應高于國際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第212條規定在減少、控制來自或通過大氣層的海洋污染的行動中,需考慮國際上議定的規制、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由此可見,《海洋法公約》創新性地通過“參考規則”將國際上議定的規制、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納入其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中,共同構成《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的“樹狀”體系。
《海洋法公約》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建立海洋秩序上達成妥協的產物,難以通過直接約束國家行為以實現海洋環境保護與保全的目的,只能寄希望于各主權國家提高海洋環境保護意識,鼓勵各主權國家通過制定國內法、其他具體性公約以及采取全球性、區域性海洋合作的方式進行海洋環境保護。值得肯定的是,作為海洋秩序憲章性法律,《海洋法公約》雖然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政治爭斗的傾向,但其覆蓋面的廣泛性、條款設置的前瞻性以及創新性地設置“參考規則”使得該公約在歷經40年后仍為海洋法秩序的支柱,推動著國際海洋秩序由霸權主義走向權利政治。
(三)《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不足
《海洋法公約》雖然構建了一個覆蓋面較廣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海洋環境治理框架,但也有明顯的局限性。首先,《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保護方面的條款中權利義務邊界規定得很模糊,例如在第192條、第193條中雖規定各主權國家具有開發海洋資源的權利及保護海洋環境的義務,但對如何履行義務則采取合理謹慎原則,要求各主權國家應盡最大努力履行其應當承擔的海洋環境管理及監督的責任,至于海洋環境管理及監督的效果則在所不論。鼓勵各主權國家應當直接或通過國際組織開展國際全球性或區域性合作,但對如何開展合作以及開展怎樣的合作則缺乏細化規定。相關規定的留白從根本上造成了各主權國家對《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的多元解讀,義務界限的模糊勢必帶來履約意向以及履約程度的模糊,也由此產生當前較多的海洋環境治理“搭便車”現象。
其次,《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中的“參考規則”雖擴大了《海洋法公約》的環境監管范圍,細化了海洋環境的監管手段及內容,但由此引發一個問題,即它在多大程度上為《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提供基礎?簡單來說,大部分“參考規則”屬于具有約束力的外部規則,有專屬于自身的締約國,與《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可能產生出入。《海洋法公約》第208條、第210條、第211條第5款中要求各主權國家在適用《海洋法公約》的同時“制定效力不低于國際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的法律、規章和措施”,“制定一般接受的國際規則和標準,并使其有效”,實質上是在要求各主權國家尊重“參考規則”,或至少讓“參考規則”產生同樣的效果。《海洋法公約》將相關環境協定的締約方通過“參考規則”擴展為《海洋法公約》的締約方,實質為各主權國家附加遵守“參考規則”的義務,一定程度上可能突破國家同意原則。同時,將“參考規則”的地位及效力抬升至與《海洋法公約》同等水平,但未明確“參考規則”的范圍,使得各主權國家在遵守適用“參考規則”時容易發生分歧,進而影響海洋環境保護及保全義務的履行。此外,《海洋法公約》雖通過“參考規則”將其他環境類條約納入到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之中,但仍未解決數量上急劇增長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的碎片化問題,同時并未使其在性質上形成統一的法律秩序。在“無組織體系”的障礙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中的不同規則和治理體系使得“碎片化”規制的沖突加劇。
二、《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發展
根據《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參考規則”包含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早在20世紀20年代,海洋環境相關的船舶污染問題就已經引起部分海洋大國的關注。20世紀50年代起,國際社會認識到船舶污染,特別是船舶的油污染對海洋環境造成極大破壞,因此出臺了《國際防止海上油污公約》《國際干預油污事故公約》等一系列規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條約。1972年以后隨著保護海洋環境的一般性條約和地區性條約的陸續締結,國際社會逐步擴大污染源的規制范圍,從規制船舶污染特別是油污染轉向規制全面來源的污染,通過了《倫敦公約》《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防止陸源物質污染海洋公約》等一般性、區域性海洋環境治理條約。同時,197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的原則宣言和行動計劃以及該會議的籌備委員會設置的政府間工作大會制定的海洋環境保護原則也影響了聯合國海底和平利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海床洋底委員會(簡稱聯合國海底委員會)對條約草案的審議。最終,《海洋法公約》決定通過“參考規則”將通過前的相關海洋環境治理規則一并納入《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之中。隨著1982年《海洋法公約》的通過,“參考規則”也根據世界海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以及國際力量呈現出的新對比而在內涵上不斷豐富。
(一)全球治理體系的演進
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導致各主權國家對國際正義產生不同認知,加之國際法獨有的平權性結構也影響了“參考規則”的發展。各主權國家矛盾難以調和的障礙使得國際社會傾向采取不具有約束力僅提供行為指導的方式實現海洋環境治理。《海洋法公約》將“參考規則”定義為國際上議定的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將不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建議、指導納入“參考規則”的范圍之中。1982年以來,國際社會通過了一系列對海洋環境治理具有全局性指導意義的“參考規則”,如1985年的《關于保護海洋環境免受陸源污染的蒙特利爾指導方針》,1992年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及《21世紀議程》《生物多樣性公約》,2015年9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及《21世紀議程》《21世紀議程》描繪了全球各領域可持續發展的藍圖,要求將環境與發展問題納入決策過程,對全球環境合作及建立新的伙伴關系提出了原則性意見。《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又被稱為“地球憲章”,致力于構建全新全球伙伴關系,努力開展各國與社會重要部門、人民的合作,充分認識世界環境的完整性及相互依存性。標志著世界環境保護邁入新篇章,其不僅重視當代的發展,同時注重保護后代的可持續性發展。《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21世紀議程》的進一步發展,為新時代產生的新型海洋問題的治理設定目標,如:預防及減少海洋垃圾及富養化;結束非法、不報告、不管制的捕撈;擴大海洋保護區面積等。[6]
此外,國家主權的相對性及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使國際組織在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例如國際海底管理局便在國際海底資源與國際海底環境規制治理體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海洋法公約》第145條授予國際海底管理局制定規則、規章和程序的權利,以減少海洋污染,保護區域海洋資源。自1994年正式成立以來,國際海底管理局遵循《海洋法公約》的指導,積極制定了多部相關規章。2000年《“區域”內多金屬結核探礦和勘探規章》、2010年《“區域”內多金屬硫化物探礦和勘探規章》、2012年《“區域”內富鈷鐵錳結殼探礦和勘探規章》,均對探礦者的海洋環境保護義務作出規定。2017年國際海底管理局公布《“區域”內礦產資源開發規章草案》,將之前擬定的三個規章進行合并,進一步平衡國際海底區域礦產資源開發權利及保護海洋環境的義務,細化義務的具體履行方式,為不同主體制定不同的義務要求,如承包者的環境保護義務、擔保國的責任義務以及管理局的監督義務,并提供海洋環境保護報告“標準模板”,以指引及規范各主體履行報告義務。[7]國際海事組織及國際糧農組織也積極發揮作用,通過了一系列漁業資源養護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條約。國際海事組織1977年通過《托雷莫利諾斯國際漁船安全公約》,1993年通過《托雷莫利諾斯議定書》替代《托雷莫利諾斯國際漁船安全公約》,2012年通過《漁船安全開普敦協定》,旨在實施《托雷莫利諾斯議定書》的規定。《漁船安全開普敦協定》被認為是打擊非法、未報告及未接受管制漁撈的支柱。國際糧農組織通過《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和管理措施的協定》創新公海漁船檔案的管理保護手段,將管理公海漁業資源的責任有序分擔給各船旗國。同時通過了《負責任漁業行為守則》《預防、制止及消除非法、未報告及未接受管制漁撈的國際行動計劃》,要求沿海國積極采取行動以應對漁業資源養護的需求,并為漁業資源的養護提供了行動及管理標準。“參考規則”不斷細化并擴展漁業資源養護及管理的要求及范圍,突破了船旗國管轄的傳統理念,在海洋環境保護問題上沿海國的身影越發顯現。
除“參考規則”不斷發展、細化外,《海洋法公約》本身也在不斷演進發展。2015年6月,聯合國召開了《海洋法公約》項下第三項執行協定解決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問題的籌備委員會,并為通過具體的執行協定進一步召開多次政府間會議討論具體方案及措施,為保護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多樣性提供法律依據,豐富《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內涵。
(二)雙邊、區域治理體系的演進
1974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開展區域海洋計劃,通過18個區域的海洋環境及生物資源養護公約具體包括:地中海海域1976年通過《保護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約》;科威特海域1978年通過《保護科威特區域海洋環境免受污染合作公約》;東南太平洋海域1981年通過《保護東南太平洋及沿海地區海洋環境公約》;西部非洲海域1984年通過《西非和中非區域大西洋沿岸海洋和沿海環境保護、管理和開發合作公約》;加勒比海域1986年通過《保護和發展大加勒比地區海洋環境公約》;東非海域1996年通過《東非區域海洋和沿海環境保護、管理和開發公約》;太平洋海域1986年通過《保護南太平洋區域自然資源和環境公約》,1995年通過《禁止向太平洋島國輸入危險和放射性廢物并控制危險廢物在南太平洋區域越境轉移和管理公約》;西北太平洋海域1994年通過《西北太平洋地區海域和沿海環境保護、管理和開發行動計劃》;東北太平洋海域2002年簽署《合作保護和持續開發東北太平洋海洋和沿海環境公約》(該公約尚未生效);東北大西洋海域1992年通過《奧斯陸巴黎保護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公約》;東亞海域2019年通過《海洋廢棄物東亞海洋區域協調中心行動計劃》;南亞海域1981年通過《關于南亞海域環境合作的科倫坡宣言》;里海海域2006年通過《里海海洋環境保護框架公約》;黑海海域1992年通過《保護黑海免受污染公約》;紅海和亞丁灣1985年通過《保護紅海和亞丁灣區域環境公約》;波羅的海1992年通過《波羅的海地區海洋環境保護公約》;北極海域2015年通過《北極理事會2015—2025年北極海洋戰略計劃》;南極海域1982年通過《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在相關區域海洋環境及生物資源養護公約的指引下,各區域積極開展區域間合作,保護區域海洋環境及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199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執行1982年12月10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和管理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的規定的協定》(簡稱《跨界魚類種群協定》),要求沿海國及捕撈國通過適當分區方法與區域漁業組織開展切實合作,明確區域內沿海國負有設立并積極參與區域組織管理及養護相關魚類種群的義務。在《跨界魚類種群協定》的指引下,世界各國在小范圍內開展雙邊、多邊的漁業資源養護及管理合作。2000年通過《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魚類種群養護和管理公約》,2001年《東南大西洋漁業資源養護及管理公約》開放簽字,均鼓勵各國積極參與區域合作。
此外,特殊海洋物種的保護也隨著區域性“參考規則”的不斷發展而發展。1991年俄羅斯、英國、美國、日本簽訂《北太平洋海豹保護公約》,致力于禁止對北太平洋海豹的獵殺行為。1992年通過《北太平洋溯河性種群養護公約》,對北太平洋范圍內的溯河性魚類捕撈行為施行限制。1993年國際糧農組織第105屆會議通過《建立印度洋金槍魚委員會的協定》,限制印度洋海域金槍魚的捕撈活動,確保印度洋金槍魚的養護以實現金槍魚的可持續利用。1994年通過《中白令海狹鱈資源養護與管理公約》,建立科學技術委員會對中白令海峽的狹鱈進行科學評估,確定并分配捕撈量。2000年《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魚類種群養護和管理公約》采取限額管理、評估資源以及公示非法漁船名單、設立區域觀察員等具體有效的措施進行相關區域高度洄游魚類種群的管理及養護。
《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規則治理體系還鼓勵各主權國家開展雙邊合作。在《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規則治理體系的鼓勵下,僅中國便與日本、韓國分別簽訂了雙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漁業協定》(簡稱《中日漁業協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韓民國政府漁業協定》(簡稱《中韓漁業協定》),明確應對漁業資源的養護開展合作,并對入漁水域、相互入漁條件、暫定措施水域的范圍及管理均作出了規定。中國還與越南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關于兩國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界協定》,與菲律賓簽署《聯合海洋勘探諒解備忘錄》《關于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與馬來西亞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海運協定》,與文萊簽署《關于海上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與印度尼西亞簽署《中國國家海洋局與印度尼西亞海洋漁業部關于海洋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這些均表明中國積極與周邊沿海國開展關于養護漁業資源、養護管理海洋油氣資源及保護管理海洋環境的雙邊合作。在海洋環境保護治理上,《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體系主要采取就地治理原則,認為沿海國在保護海洋環境及海洋生物多樣性方面的需要比遠洋國家更為迫切,在充分尊重各主權國家的主權權利的基礎上鼓勵沿海國開展雙邊合作保護共同海域海洋生物資源及海洋生態環境。可以看出,在《海洋法公約》通過的40年間,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不斷演進,尤其在與經濟發展關系緊密的漁業資源養護、特殊海洋物種保護以及海底資源開發方面不斷演進并發展。
三、《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未來走向
在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不斷演化的過程中,全球一體化國際進程不斷推動全球治理規則包括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重新調整,推動著國際秩序、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具體而言,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未來走向主要呈現出以下特征。
(一)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內涵進一步豐富
隨著世界經濟不斷發展及世界產業不斷進化升級,《海洋法公約》進一步督促各主權國家開展全球合作及區域合作、與國際組織相互配合、制定國內法、簽訂雙邊及多邊區域協定來不斷豐富“參考規則”,以應對《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海洋法公約》采取分區的形式,將海洋分為領海、專屬經濟區等多個區域,試圖平衡沿海國享有的管轄及養護海洋資源的權利及義務與他國享有的海洋自由的權利及義務。《海洋法公約》規定各國負有管理及養護專屬經濟區環境及海洋資源的權利及義務,同時為保障公海自由,要求船旗國負責公海海洋資源的管理及養護。隨著《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的不斷演進,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內涵不斷豐富,逐步呈現出沿海國、船旗國、港口國共同管理的新局面。
全球環境問題的最高決策機構聯合國環境大會通過梳理與海洋環境保護相關的重要議題,在各主權國家相互協商及博弈之下形成了多份決議,以“宣言”“指導”“意見”等軟法形式指引各主權國家開展海洋環境治理的相關行動,同時各主權國家也不斷修改完善國內法以保護海洋環境。各主權國家、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針對海洋環境治理問題主動作出自愿性承諾,自愿性承諾也成為各主權國家樹立環境保護大國形象并占據輿論制高點的有效手段之一。據統計,2017年聯合國海洋大會上共作出1 400項自愿性承諾,其中二分之一以上與海洋環境問題有關。[8]隨著《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變,“參考規則”形式內涵得到進一步豐富。
除不斷細化“參考規則”,豐富“參考規則”的內涵以外,《海洋法公約》也在積極發展執行協定,擴展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范圍。2015年聯合國大會69/292號決議授權聯合國開展關于國家管轄范圍外生物多樣性保護(簡稱BBNJ)的國際談判。2019年聯合國大會召開BBNJ政府間會議,會議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于養護和可持續利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協定草案》,設立秘書處為欲獲取海洋遺傳資源的主權國家發放許可證或執照,并對BBNJ海洋遺傳資源的利用情況進行檢測,環境影響評估則由將由專業性較強的“科學和技術機構”負責。[9]BBNJ國際談判將國際視角從以往的管轄范圍內擴展至管轄范圍外,以整體性和生態性的視角為海洋環境治理提供方案,標志著《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重大轉變,從控制、預防海洋污染和海洋生物資源的過度開發轉向直接管理和保護生物多樣性。
(二)海洋環境治理規則“自由主義”趨勢進一步加深
隨著全球一體化國際進程的不斷加快,自由主義的國際海洋秩序逐步替代以往強效控制、海權至上的現實主義,逐步以自由、平等、相互對話、合作的思潮席卷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自由主義的國際海洋秩序在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中的體現為世界各主權國家在面對海洋問題時傾向于開展《海洋法公約》項下的全球合作或區域合作。全球合作或區域合作逐步成為國際社會的優先選擇,形成了多利益主體共同參與海洋環境保護治理的新局面。
一方面,海洋環境保護傾向以《海洋法公約》項下區域合作的方式進行治理。區域合作是指地理位置相近的國家因為面臨相同海域的海洋環境問題而開展海洋環境治理合作,通過構建合作框架以及具體行動計劃開展海洋環境保護合作的方式。自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要求進一步開展區域合作以來,區域海洋環境治理體系不斷發展并完善,形成兩類合作模式:第一,規范合作共識,構建區域合作計劃,建立規則以及制度體系。[10]例如地中海行動計劃便是地中海沿岸國家為保護地中海的海洋生態環境而開展的成功的區域合作。作為閉海或半閉海的地中海,因其處在南歐、西亞和北非陸地的包圍下,較為封閉的海域環境導致地中海的海洋污染物不斷匯集,最終導致其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快速喪失以及面臨嚴重的海洋生態環境問題。為此,1975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海洋法公約》的指導下召開地中海沿岸各國政府間部長會議,批準了“地中海行動計劃”,為地中海海域生態環境的保護搭建了治理框架,次年又通過《保護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約》,即《巴塞羅那公約》,為地中海區域合作治理海洋環境提供法律上的支撐。“地中海行動計劃”的成功也增強了各主權國家開展區域合作的信心。第二,構建中長期或短期海洋環境保護合作項目,助推區域海洋挑戰的解決。例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名為“扭轉南海和泰國灣的環境退化趨勢”的南海項目,便是為扭轉南海和泰國灣的海洋環境而開展的短期合作項目,該項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隨著《海洋法公約》的不斷發展,世界各區域海域均形成了各式各樣的海洋環境保護治理區域合作體系,并在《海洋法公約》的指導下發展、衍生出《保護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約》《保護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公約》《波羅的海區域海洋環境保護公約》《保護里海海洋環境框架公約》等一系列環境類條約。
另一方面,海洋環境保護傾向以《海洋法公約》項下全球合作的方式進行治理。《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中的全球合作相對區域合作而言,視野更為開闊,聚焦全球形勢,以《海洋法公約》為框架鼓勵引導各主權國家開展全球合作,鼓勵各主權國家開展雙邊或多邊的海洋環境保護治理合作,對洄游魚類等特殊海洋生物的保護以及跨界海洋污染治理開展跨國合作,并依據《海洋法公約》以及相關的海洋環境保護的國際法條約解決處理海洋環境保護方面的矛盾及分歧。同時,《海洋法公約》鼓勵各主權國家與國際組織開展合作,由此,各主權國家開展與聯合國海洋大會、國際海事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國際組織的廣泛合作,以協商合作的形式容納多利益主體的廣泛參與,推動《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變。
(三)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在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中進一步顯現
《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中的規則和治理還逐步呈現有效性下降、碎片化程度加深的特征。21世紀以來“逆全球化”思潮的進一步發展,不僅影響了全球一體化進程,也深刻打擊著貿易自由化。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沖擊貿易自由主義及多邊主義,在經濟層面上被動斷裂與主動脫鉤全球經濟供應鏈。[11]“逆全球化”浪潮同時也影響著《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變。
一直以來,“逆全球化”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思潮不斷沖擊現有《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致力于獨占國際霸主地位,領導構建國際秩序,一邊通過雙邊及多邊的形式拉攏歐洲及東亞各主權國家,一邊通過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同時,美國也一直主導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海洋秩序。但1982年第三次海洋法會議通過《海洋法公約》時因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導致美國并未徹底實現其通過建構國際海洋規則把控海洋秩序的目的,因此美國宣布不加入《海洋法公約》。美國的矛盾舉動在推動國際法律規則進步的同時,也表明了美國并不愿意讓這些規則限制自身,而是僅將其看作實現本國自身利益的工具,也是從此時起美國霸權主義下的單邊主義及保護主義的苗頭開始顯現。2015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進一步發揮且擴張單邊主義及保護主義。此后在任職期間更是退出了多項國際公約及多個世界組織,其中包括《巴黎氣候變化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同時,美國的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也得到了其同盟英法日澳等國的支持及鞏固。美國主導的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摧毀了國際社會共同構建的國際秩序,也嚴重沖擊了《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
當前,支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國家致力于將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通過重構國際規則、發展國際秩序的方法納入《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之中。當今的霸權主義者不僅通過任意退出國際公約及國際組織的形式實現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目的,還將以促進他們利益的方式重塑國際法律標準。霸權主義者不再滿足以防御、限制適用的方式對待國際法,而是將國際法視為一種促進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工具。一旦傳統的海洋強國放棄全球主義,采取完全的單邊主義及保護主義的立場之時,全球海洋治理體系也便喪失了建立及維持的基礎。其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自然便會面臨各主權國家保護海洋環境的意愿下降、對海洋生態治理合作的需求降低的困境,從而從根本上影響《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發展。典型的如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為規避《倫敦公約》及《〈防止傾倒廢物及其他物質污染海洋的公約〉1996年議定書》(簡稱《倫敦議定書》)的適用,東京電力公司決定采取安裝1公里海底管道的方式在近海海域排放核污水,以利用《倫敦公約》及《倫敦議定書》對陸源排放規制的空白。日本為順利進行核污水的海洋排放,不僅充分利用《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的規制空白,同時拉攏美國及國際原子能機構為其核污水排放行為背書,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在美日同盟霸權主義的影響下,世界很多國家紛紛對日本的行為視而不見,不對該行為進行規制以保護海洋環境,各主權國家海洋環境保護治理及合作的意愿降到了最低點。
支持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的美國未來還將積極介入海洋制度的塑造過程之中。當前,美國并非《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其在參與全球海洋秩序的構建中存在一定角色及地位障礙。美國非國際海洋法法庭成員,難以利用相關國際司法機制實現本國利益,不能參與與《海洋法公約》相關的國際海洋機構,難以有效參與國際決策及未來制度的構建。美國前國務卿克林頓表示:“美國加入《海洋法公約》就是要在其中占據決策者的關鍵位置,以確保攸關美國利益的權利的相關事項被討論時可以有效參與”。[12]未來,美國可能謀求加入《海洋法公約》,積極參與《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變,利用國際制度實現本國利益,重塑國際秩序。
四、應對《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演進的中國舉措
隨著海洋環境保護利益重要性的日趨提升,《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不斷演變,不僅影響著人類當代及后代的發展,也影響著國際秩序、國際力量關系對比。對于中國而言,應對《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變,不僅面臨復雜的海洋爭端及西方海洋大國的打壓,作為海洋治理的后來者,中國也面臨提起海洋相關議題的能力不足等問題。研究《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運行及演進的發展特點及趨勢,有助于中國在海洋秩序迎來重大變革之際制定有效的參與海洋環境治理的行動路線圖。
(一)中國參與海洋環境治理面臨的挑戰
自《海洋法公約》搭建了海洋環境治理框架以來,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不斷發展完善,并有望成為改變當今國際秩序及構建新型國際格局的契機。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當積極參與《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進過程,參與相關規則的制定,維護中國利益,輸出中國話語。然而,當前中國參與海洋環境治理仍然面臨不小的障礙。
首先,中國面臨復雜的海洋爭端。中國與東海及南海沿岸的各主權國家存在復雜的主權爭端、專屬經濟區爭端、劃界爭端以及資源開發利用爭端。同時,自美國“重返亞太”政策實施以來,美國一直致力于拉攏中國海域周邊國家,形成對中國的掣肘,中國海域周邊國家也因背后有美國霸權主義的支持而對中國頻頻挑釁,影響海洋局勢與海域秩序。在海洋環境治理層面,由于復雜的海洋爭端,中國與周邊國家開展的海洋環境治理合作也遠遠少于世界其他海域。中國海域周邊國家甚至借海洋環境保護之名實現其政治權益。如“南海仲裁案”中,菲律賓便將中菲之間的海洋主權爭端通過海洋環境保護的包裝,變成海洋環境保護義務履行爭端,指責中國違背保護及保全海洋環境的一般義務。此外,越南、馬來西亞等國還在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海域單方面劃設海洋保護區,其背后的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其次,現今的國際海洋秩序主要是由話語權較強的西方海洋大國所塑造。西方海洋大國希望利用海洋秩序,控制海洋以實現其世界霸主及管理者的地位。其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也不例外。自中國經濟發展一路高歌猛進以來,中國的經濟、軍事、文化實力均在迅速發展,因此西方國家將中國看作維持其霸主地位的挑戰因素。在海洋環境治理層面,西方國家同樣認識到國際海洋秩序可能將因海洋環境保護的需要而發生改變。因此,西方國家為維持其霸權地位勢必對中國與涉海國際組織的對話及合作、區域合作、中國話語輸出等參與海洋環境治理的行動進行打壓,以免威懾其霸權主義地位。
最后,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參與世界海洋環境治理以及治理規則的構建經驗不足,能力有限。《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簡稱《海洋環境保護法》)雖經過多次修改但仍與《海洋法公約》的規定有一定差距,如《海洋法公約》使用的是“海洋環境污染”定義,《海洋環境保護法》使用的則是“海洋環境污染損害”,措辭的差異容易引起法律解釋與執法上的困惑。[13]再如《海洋法公約》第194條第3款(d)項將防止意外事件及處理緊急情況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列入海洋污染的來源之一,而《海洋環境保護法》第42條至第46條則并未對防止意外事件和處理緊急情況海上設施的污染問題作出規定。此外,中國參與世界海洋環境治理及治理規則構建的經驗同樣有限,在經驗有限、治理能力不足的狀況下,中國在參與全球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相關公約乃至執行協定的制定時,難以提出創造性觀點和輸出中國話語以實現中國利益。
(二)應對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演變的中國路徑
當前,全球海洋治理體系正處在轉型變革的關鍵時期,世界海洋秩序也在發生劇烈變動,《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變可能成為調整當前海洋秩序的關鍵契機。中國應當積極應對《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變。
首先,面對“參考規則”的演進及發展,中國應當進一步厘清“參考規則”的適用門檻。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賓將中國訴至仲裁庭的第3項請求中聲稱中國違反《海洋法公約》保護及保全海洋生態環境的義務,容忍并支持中國漁民采用不利于海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手段捕撈海洋野生瀕危物種。仲裁庭便引用了“參考規則”條款,將《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作為《海洋法公約》的“參考規則”之一,認定《海洋法公約》第192條的“保護及保全海洋環境的一般義務”應當擴大到“防止通過破壞生境間接影響枯竭、受威脅或瀕危物種”,認定中國負有《海洋法公約》規定的合作義務。事實上,《海洋法公約》第192條并未涉及“參考規則”的相關內容,“參考規則”的規定在第207條至第209條等其他條款中,未規定“參考規則”的條款是否可以引入“參考規則”存有爭議。此外,無論是《海洋法公約》亦或是《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均設定國家保護瀕危物種應遵循謹慎原則,即國家只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護海洋環境及海洋瀕危物種則可認定為履行了相關義務。中國為保護海洋瀕危物種不僅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同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對瀕危野生海洋動物作出了規定,并設置執法及處罰措施以達到對瀕危野生物種的有效保護。因此,菲律賓的相關指控于法無據。隨著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不斷演進,“參考規則”的重要性及引用頻次不斷增加,對于“參考規則”的效力及適用性各主權國家均存有爭議。對于“南海仲裁案”結果,雖然中國有著不接受、不承認的鮮明立場,但該案仍給中國帶來不小的國際負面輿論壓力。因此,為防止他國利用海洋環境保護輸出別有用心的政治訴求,利用“參考規則”對中國施加附加的義務要求,中國應當進一步開展對“參考規則”效力及適用性的研究。
其次,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影響下,《海洋法公約》鼓勵各主權國家為保護海洋生態環境開展區域性合作,自由化的海洋秩序也進一步帶動區域化合作的發展。中國一直以來積極履行《海洋法公約》規定的以區域合作方式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義務,與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積極開展區域合作保護海洋生態及環境,簽訂了《中日漁業協定》以及《中韓漁業協定》等制度化協定。中國接下來應當進一步開展區域合作,如與周邊國家合作開展海洋環境監測、合作構建海洋保護區、合作構建區域漁業協同保護機制等。海洋環境保護領域相對于貿易、軍事領域敏感度較低,因此中國可以以此為開端開展與周邊國家的多元、多層次區域合作,以期與周邊國家共建全方位合作體系。
最后,為應對單邊主義及保護主義浪潮的沖擊,中國應首先遵循且尊重現有《海洋法公約》項下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相關規則。單邊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使得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海洋大國在進行海洋環境治理時更加強調本國利益,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進行海洋活動,參與海洋環境治理。完全的自我主義帶動世界各主權國家在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時對其他國家充滿了不信任感。尊重現有的《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有助于幫助世界各主權國家加深了解、互相信任。面對《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體系的不斷演變及發展,中國應當在現有《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律的制度框架下進行制度建設、理論擴展、內涵拓寬,同時引導世界各主權國家共同積極參與《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反對“逆全球化”浪潮。當前,世界海洋環境治理存在利益沖突、政治站位等障礙,存在“行動缺失”及一些國家“搭便車”的現實情況。因此,中國在參與海洋環境治理時,應當輸出中國話語,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凝聚集體理性,引導世界各主權國家了解認識海洋環境對全人類生存及發展的重要性,提升世界各主權國家保護海洋環境的意識;減少世界海洋環境管理與合作中的沖突和矛盾,縮減海洋國家在海洋環境管理層面的成本,尋求世界海洋環境保護的“共通性”,形成海洋環境治理的集體理性;[14]進一步推進《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演變,積極參與并促進各類海洋治理的集體行動。
五、結語
《海洋法公約》搭建了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框架,并引入“參考規則”規定具體海洋環境治理問題。2022年是《海洋法公約》通過的四十周年,在這四十年間,“參考規則”在《海洋法公約》搭建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框架的指引下不斷演進發展,地理層面不斷擴大,由近岸調整擴展至大洋、全球海洋,內容層面不斷深化、具體,從最初的防止海洋污染調整至全面保護海洋環境及海洋生物多樣性。尤其在國際海底區域資源開發與海洋保護、國際漁業資源開發及環境保護、特殊物種保護及治理三個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當前,國際海洋秩序迎來重大變革,《海洋法公約》呈現出內涵進一步豐富、自由主義國際海洋秩序影響加深以及“逆全球化”的特點,中國應當在尊重現有的《海洋法公約》項下的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基礎上積極參與海洋環境治理的演進進程,輸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導海洋環境治理規則體系的演進,積極參與區域及全球合作,同時對可能影響中國權利及義務的“參考規則”效力進行研究,以防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披著海洋環境治理的外衣對中國施行不利的政治性舉措。
參考文獻:
[1]李潔.BBNJ全球治理下區域性海洋機制的功用與動向[J].中國海商法研究,2021,32(4):81.
[2]邁倫·H·諾德奎斯特.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評注(第四卷)[M].呂文正,毛彬,譯.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74.
[3]呂琪.國際造法新進程下海洋環境責任制度的審視[J].太平洋學報,2021,29(11):68.
[4]江河.論軍事活動規制國際法的碎片化與開放性——從“烏克蘭艦船扣押案”切入[J].法學,2020(9):183.
[5]BURKE W T.Importance of the 1982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J].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1996,27(1-2):3.
[6]SDGs目標14「海の豊さを守う」から考える海洋環境の現狀と課題[EB/OL].(2021-01-07)[2022-02-10].https://wearth.tokyo/sdgs-life-bellow-water/#outline__3.
[7]王超.國際海底區域資源開發與海洋環境保護制度的新發展——《“區域”內礦產資源開采規章草案》評析[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8,35(4):85.
[8]崔野.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進展、困境與中國的參與[J].太平洋學報,2020,28(12):81.
[9]方瑞安,張磊.“公地悲劇”理論視角下的全球海洋環境治理[J].中國海商法研究,2020,31(4):42.
[10]吳士存.全球海洋治理的未來及中國的選擇[J].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0(5):5.
[11]江時學.“逆全球化”概念辨析——兼論全球化的動力與阻力[J].國際關系研究,2021(6):7.
[12]Accession to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d ratification of the
1994 Agreement Amending PartⅪ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EB/OL].(2012-05-23)[2022-02-13].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REVISED_Secretary_Clinton_Testimony.pdf.
[13]全永波,石鷹婷,郁志榮.中國參與全球海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機遇與挑戰[J].南海學刊,2019,5(3):77.
[14]全永波,葉芳.“區域海”機制和中國參與全球海洋環境治理[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9(5):84.